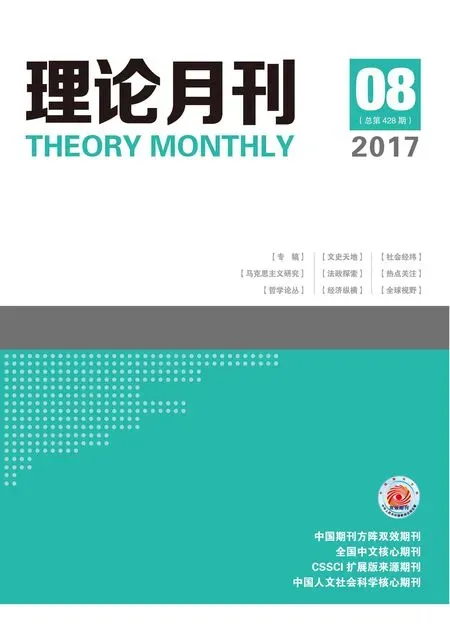论朱荃宰《文通》的文章学思想
□孙宗美,刘金波
(1.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广州 510642;2.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062;3.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湖北武汉 430072)
论朱荃宰《文通》的文章学思想
□孙宗美1,2,刘金波3
(1.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广州 510642;2.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062;3.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湖北武汉 430072)
作为明代资料汇编式文话的代表,《文通》固然因为“辑而不作”在理论建树上稍显逊色。但通过细致考察,其隐藏于编纂思路、材料选取、体例设置以及多篇序言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仍值得关注与重视。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以经史为“文”,“文”以经史为本源;其二,“时”变“文”亦变的辩证文学发展史观;其三,会通古今、明法究变的辨体意识。《文通》的思想来源十分驳杂,《周易》《史通》和《文心雕龙》都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总体上看,其文章学思想不仅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流行的文章观念和文学、史学、经学、科举交织的社会文化生态,也奠定了自身在明代文章学中的历史地位。
朱荃宰;文通;文章学
朱荃宰《文通》三十卷,闰一卷,是存世明代文话中体量最庞大的一部。朱荃宰(?—1643),字咸一,号白石山人,湖北黄冈人。其受刘知几《史通》和刘勰《文心雕龙》影响甚巨——不仅该书书名仿《史通》而来,其体例和内容亦沿袭二书居多。全书除大面积照搬《史通》《文心雕龙》外,还吸收辑录了自先秦以迄明代各类著作①主要包括南宋陈騤《文则》、郑樵《六经奥论》,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明代陆深《史通会要》、杨慎《升庵集》、祝允明《罪知录》、胡应麟《史书占毕》等。,内容涵盖经学、史学、文章学、文献学等诸多领域。故《四库全书总目》评此书“盖欲仿刘勰《雕龙》而作”,“然大抵摭拾百家,矜示奥博,未能一一融贯也”[1]2774。郑振铎亦认为是书“无甚独见”,“体例略类史通。而多引明人语,偶有己见,亦殊凡庸,固不足以与语‘著作’,更不足与文心雕龙、史通比肩也。”[2]289王葆心说:“其书收采颇博,篇目尚赅,但沿明人陋习,多不著所出”[3]16。这些评论都颇中《文通》弊病,但并不能因此全盘抹杀《文通》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该书五篇序言及闰一卷《诠梦》为作者或时人原创,不乏有关《文通》的真知灼见和当时流行的文章观念。另一方面,《文通》在材料的选择吸纳、体例结构的布置、卷次的安排等方面亦有规律可循,不仅从侧面呈现了晚明文章学、史学、经学思想相互交织的历史状况,也可为《周易》《史通》与《文心雕龙》在明代的接受研究提供参考。
1 文原论:“文”以经史为本
中国古代文原论的内涵较为复杂,但其主要有二:一是论“文之本体”,也即本体论意义上的探讨;二是论“文之起源”,属于文章学或文体学范畴。朱荃宰的文原论正是从这双重意义上展开的。
在理学和经术盛行的明代,学者文人往往以明道宗经为文之本体和论文之宗旨,这里面不仅有宋濂、王鏊等建国之初的名臣大儒,也包括一大批朱荃宰式的后代文人。但对于处身晚明的朱荃宰来说,维护儒家道统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而是面临着新语境下的调适和转型。因此,虽然对“道”的推崇并未隐去,但经世与治世已然跻身为朱荃宰研文的主要目的。他十分重视文章的现实作用和价值:“夫文以经纬天地,安定社稷,为宪万邦,兼资一世,故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岂第为先资之蒭狗,酬应之苞苴耶!”[4]2608由此,他进一步明确了编纂“文通”的宗旨。《文通·诠梦》说:
予之述诸通也,实竭其耳目心思,以上继娄、旷、俞跗、聃、黎、牺、炎、仲尼之意,以文究六经诸史百家两藏之用,而优优于礼;以诗歌词曲宫调溯黄钟之源,而洋洋于乐。帝王之道,礼乐备矣。礼乐明备,天地官矣。世无诸通,何以究理乱文质之变、动天下之机、以知诐淫邪遁之害哉[4]3103?
作为经学家和复社成员①清·吴山嘉辑:《复社姓氏传略》卷八湖广之《黄州府·黄冈》下记有朱荃宰简要生平信息(参见周俊富编:《明代传记丛刊》,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作为复社成员,朱荃宰的文学主张恰与复社提倡镕经铸史、关心社会的主张一致。的朱荃宰既有承续先贤思想、维护礼乐道统的使命感,更有“究理乱文质之变、动天下之机、以知诐淫邪遁之害”的宏愿。与之相关,他极致推崇经学的地位,著有多部经学和经世之书。据《湖广通志》卷五十二《人物志》载,其“著有《周易内外图说》《礼记会通》《礼记金丹》《毛诗类考》《孟子年表》《文通》《诗通》《词通》《曲通》《乐通》《韵通》《大学权衡》《中庸权衡》,诸书曾经奏御发礼部颁行。”[5]《光绪黄冈县志(一)》还补充了《经济录》《论世篇》《世史》《尚史》等[6]。
朱荃宰与焦竑友善,《文通》尚未刊刻时即呈焦竑审阅。焦竑也自述二人“臭味之合”而欣然为其作序以示肯定和褒扬。因此,不排除二者在文论思想上有一定关联。以对文道关系的理解来看,朱荃宰的确与焦竑有暗合之处。焦竑曾在《与友人论文》中指出:“窃谓君子之学,凡以致道也……故性命事功其实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则意不能无首尾,语不能无呼应,格不能无结构者,词与法也,而不能离实以为词与法也。”[7]92-93他认为君子之学以“致道”为本,文章亦是如此。文法的探究不能脱离“性命事功”之“实”,“离实以为词与法”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而朱荃宰虽然没有直接论文道关系的言辞,其文以明道的思想还是十分明显的。他在《文通》卷一下设“明道”“本经”篇,分别辑录宋濂《文原》和王祎《文训》②宋濂《文原》以阐道翼教为文之根本,合义理、事功、文章三者为一体。,又在卷三下设“渊源经史”篇,抄录颜之推、柳宗元“文原五经”、王世贞“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论述,均是其视经史为文章本源的明证。明道宗经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先秦时荀子开其先河,魏晋刘勰确立彰显。以《文通》与《文心雕龙》的关系看,《文心雕龙》“原道”“宗经”思想也对朱荃宰产生了一定影响③不同的是,刘勰之“道”虽然也根于人文立论,但较重自然,不局于儒家之“道”。。
道在于经,故明道必然宗经。但在朱荃宰这里,宗经与崇史相并行,经、史共同为“文”之本源。《文通》,顾名思义,求文之“通”也。此“文”专指文章,不包括诗、乐、曲、词④朱荃宰自述:“爰考诸家之书,汇成文、诗、乐、曲、词五编,皆以通名之,求以自通其不通也,匪敢通于人也”(朱荃宰:《文通》,《历代文话》第3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06页)。可见,除《文通》外,还应有《诗通》《乐通》《曲通》《词通》,惜皆未见传世。。但从该书整体架构看,有近一半的篇幅关乎经、史。其中卷一、卷二十六专论经,卷二、卷二十、卷二十二、卷二十七专论史及史著写法,卷七、卷十二、卷十五则收录较多史著文体。朱荃宰认为通经必然通文,他说:“世无经学,故无文学,未有通于经而塞于文者也。”[4]2609此说固然有夸大之嫌,但实则有其道理——他既“以经为文”,又视经为文之“冠冕”[4]2607,故通经即通文。与此同时,朱荃宰对史著的重视可从他对刘知几《史通》的态度见出。《史通》是一部史学通论性著作,其论述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史学理论,二是史书体例和编撰方法。《文通》卷二十、二十二、二十四几乎全部袭自刘知几《史通》,将其有关史书体例、撰著、史官建置的论述悉数收入囊中⑤内容涵盖《史通》的“序例”“称谓”“题目”“编次”“断限”“烦省”“模拟”“采撰”“言语”“探赜”“叙事”“直书”“曲笔”“因习”“载文”“载言”“人物”“鉴识”“辨识”“忤时”等。此外,《文通》卷二的“史法”“史家流别”“史官建置”虽分别抄录明代陆深《史通会要》的“家法”“品流”和“建置”,但《史通会要》原本因续《史通》而来,上述篇目几乎完全采自《史通》的“六家”“杂述”“史官建置”。。史之于文,“分为异体,合为一家”[8]。从文史相通的角度看,这些史书撰著的方法、要求无疑也是文章写作可参照遵循的规范。由此,以经史为“文”之本源,尊经崇史,就成为朱荃宰在文体和文章学上的重要主张,也是他编纂《文通》的思想基调。值得注意的是,《史通》正是在明代中后期得以普遍传行,并对明代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⑥程千帆先生称:“自朱明以迄今兹,治《史通》者亦有多家”(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年,第1页)。研究《史通》成为一门学问,是从明代开始的。。从《文通》大面积摘抄《史通》的情况来看,其影响还波及到了文章学领域,目前尚未引起《史通》研究者的关注。
时人傅汝舟①《文通叙》末署名“天启丙寅季夏望江东社弟傅汝舟”,根据王承丹、尚永亮《辨两个傅汝舟之混淆与误用》(《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可推知,此傅汝舟当为生活在万历、天启时的“江宁傅汝舟”。对《文通》重经史的特点认识十分清楚,他说:“古今来经史子集四部文尔。丈夫不得树奇伐,戮力中原,鞭笞海外,功成名遂归来,胸头一段空明玄澹之旨,如第一月,使后世书生笔我之言为经,编我之言为史,是安得为通三才之子,纵裒然得集,徒覆瓿哉!不得已而著书,尚不讲经史一大事,亦可怜矣。……天地一经,万物一史,人心之生死关于斯,宇宙之明昧关于斯。朱子(按:朱荃宰)上慨述者之无人,下叹作者之灭侣,厥志厥功,通之力钜普哉!”[4]2603傅汝舟不仅视经史为大丈夫在世功业的表征,更将其上升至关乎天地万物、人心生死和宇宙明昧的地位,并以此凸显朱荃宰作《文通》的目的和意义。应该说这种解读是客观准确的。事实上,傅汝舟所持“经史一体”的观念既是明中期以来理学背景下经史关系变化的一种反映,也是当时流行的看法。其所谓“天地一经,万物一史”应为《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的化用。自明代中期王阳明从心学理论出发,明确提出“五经皆史”以后,到了晚明,所谓“六经皆史”“经史一也”的观点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何景明、徐中行、何良俊、李贽、钱谦益等均持相同看法,影响较大者如王世贞“天地间无非史而已”[9]963之说。前述《文通》卷三“渊源经史”篇正抄录了王世贞的这段话,足见朱荃宰也持类似观点。
与尊经崇史且重经世致用的思想有关,朱荃宰更充分肯定了科举取士的初衷和经义、论表、策问等科举文体的价值。他说:“惟经义盛于我明。破承腹结,可以槖籥六经,四股八比,用能舞骖鸟道。他文可以驰骋借资,而经义独难纤毫出入。何也?与庸人言易而与圣人言难也。”[4]2606同时也批评了应考士子在晚明空疏学风下只识“帖括”而不能真正穷理、博古、通今而使圣人之道明的社会现状。他认为,经义等科举文体作为国家取士的重要载体,其最终的意义还是在于通过考察士子穷理博古通今的功夫实现对优秀人才的选拔。他说:“经义,国家用以隽士,以试穷理之学;次以论表,观其博明古;次之策问,观其通今。是以圣贤望士,亦何厚也。夫士诚穷理也,博古也,识时务也,尚何孙于三代哉?然士竟以帖括报之,何太薄也?高者剿一二语录,纵谈名理。其名甚尊而不敢以为非,其罪甚钜而莫不以为功。先圣之道益晦,后生之腹益空,宋銮坡所谓臭腐塌茸,厌厌不振。如下俚衣装,不中程度者也。知其然而然,而无如之何也。间有一二笃生之士,仰慕成弘,必遭偃蹇,即擢科名,父以此戒其子,师以此戒其弟,曰:此马肝也,甚毋食之。夫安得正始之音,复见于今,而无愧于穷理博古通今也哉。”[4]2608“成弘”是明朝中兴期,其间正如董其昌所言:“成弘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程朱之学,立于掌故,称大一统,而修词之家,墨守欧曾平平尔。时文之变而师古也,自北地始也;理学之变而师心也,自东越始也。”[10]260朱荃宰以“成弘”为仰慕,足见其对程朱理学的追崇。
2 辩证文运观:文章之“时”与“变”
研究历代文学的演变,审视其因革损益以用作创作的借鉴,这在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论传统。《周易·系辞》曰:“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它用“通变”来指代事物发展的规律,认为万事万物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必须“惟变所适”,积极地适应、顺从事物的变。此后,刘勰将“通变”引入文学批评领域,借以表达辩证的文学史观。《文心雕龙·通变》云:“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变则可久,通则不乏”。“通”指会通,“变”指变易,分别对应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刘勰创造性地将二者对举成文,使之成为一个阐述文学发展之继承与革新关系的范畴。朱荃宰在《自叙》中以“文”“时”“变”三者为关键词,开宗明义地表达了他对文变时序的看法。他说:“文,时之为也,而变因焉。自羲、仓以迄大明,时也;自图、书以及经义,变也。”[4]2605“时”之“变”是不可阻挡的,故“文”因“时”而“变”,“时”变“文”亦变,变化革新方能延续。因此,在溯文源、析文派以观文之会通并树立为文典范方面,《文通》延续了刘勰的“通变”思想。王在晋在《文通序》中就明确指出:“天地间有有文之文、有无文之文。……作之谓圣,述之谓贤,故古今有无尽之藏,造物有无穷之奥,有文无文皆文也。化无为有,统有为无,穷无尽,尽无尽,则文之通也。《易》曰:‘往来不穷谓之通’;又曰:‘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会必有通,通而后行典礼也,则咸一朱君《文通》之纂本于此。”[4]2598
朱荃宰还认为,文如能应时而生即可产生恰到好处的效果。正如《周易》卦象和象传、彖传的产生一样,其时间自有先后,且不必损也不必益。“文思之圣,理苞系于怀,不能相告以精,时一吐之,无言之意,亦无无言之意,故《易》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无所谓体也。时因图而画,画已耳,不必益也。时因画而象彖系之,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不必损也。”[4]2605这种对“文”与“时”之关系的看法,包含了顺应自然、顺应时代潮流和文学发展趋势的主张,即《周易·象传》所谓“含章可贞,以时发也”,庄子所谓“圣人不巧,时变是守”,也即刘勰所谓“趋时”(《文心雕龙·通变》)。由于时代的发展进步是必然的,那么应时而生的文亦可随时而变,故朱荃宰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命题中演绎出了新意,那就是由此论证了科举文体存在的合理性。他说:“今以时考之,三代不能不秦、汉也,汉、魏不能不六朝也,六朝不能不三唐也,唐不能不宋元也,变止矣。六经不能不子史也,三百篇不能不汉、魏也,汉、魏不能不近体也,宋之不能不词,元之不能不曲也,国家之不能不经义也。”[4]2608以经义为有明一代文章之代表,此论在晚明批判八股文体的风潮中实有惊世骇俗的效果。
朱荃宰的文运论与传统相比增加了有时代性的内涵,那就是有关“理”与“体”(“言”)之关系的辩证思考。如前所引,他认为“文”的核心是“理”,文的首要目的还是处理与道的关系。“理”即是“道”,即是文之“心”。他说:“是故德尊则义深,义深则意微,意微则理辩,理辩则言文,言文则行远。无心之文,犹无声之乐、无体之礼也。”[4]2605对义理的重视无疑是受理学影响;为文贵有“心”,实质是对文章写作之思想内涵的追求。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文章对“理”(“道”)的追求是不变的,且始终“以时言也”。但在不同的时代,这种情况又稍有不同。朱荃宰从历史的角度对文章演变脉络作了较为宏观的审视。他指出,在上古时期,“理”的倾吐表达应时而发,既没有任何人为主观因素推动(故云“无言之意,亦无无言之意”),亦无所谓“体格”讲究(故云“无所谓体也”)——一切皆顺其自然。以《周易》为例,由河图洛书到八卦符号,再到解释卦象、卦辞的彖传和象传,其文本诞生均顺应自然,不讲究体格、损益。及至后来,典、谟、诰、誓、雅、颂、六官三礼、六乐获麟之书,虽“拟议以成变化”,但“因其性反禅继放伐、王迹国史、裒殷益商之实,而以时言也”[4]2608。然而到了近世,情况发生了变化:
后之人亦知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不知作者之所拟议非言也,后人之所拟议者言也。作者拟议之则变化也,后人拟议之则体格也。言愈拟愈下,而六籍始为方圆矣,流而滥觞也,不知六籍为何物。而诸体始为金科玉律矣,浸假而为优孟之衣冠矣,浸假而为沐猴之衣冠矣。有识者懼浸假为轮为马也,于是《典论》《文赋》《雕龙》《流别》《缘起》之属,灌灌于前,渔仲志之,端临考之。部别塍分,则有海虞吴江;博文反说,则有新都弇山,澹园云杜。或徵《七略》而为书,或操寸管而说法,亦綦密也[4]2605-2606。
朱荃宰认为,前人和后人创作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前人以“变化”为创作原则,后人则舍本逐末地追求“体格”之表面,最终导致“言愈拟愈下,而六籍始为方圆矣,流而滥觞也,不知六籍为何物”的后果。有识者担忧文章写作久而久之会逐坠入随心所欲的状态,故自魏晋南北朝起,尊体、辨体之风由此兴盛。而明人则在复古之风熏染下论文重辨体,作文也以前代诸体为学习典范,只是由于师法的重心不同,往往师其貌而遗其神。因此,魏晋以后人们对文体的重视是出于尊经和维护文章正统的需要,与明代复古派片面追求“体格”导致文统失序的做法并非一题。有鉴于此,朱荃宰并不反对辨体,《文通》的一大编纂特色就是辨体基础之上的溯源衍流。他认为辨体虽然是必需手段,但并非最终目的,而是应该在此基础之上以经史为源头,以理、道为本体,树立为文之道。他对挚虞《文章流别集》、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文体明辨》等“皆不本于经史”的做法深为不满,认为这样是“饮水而忘其源”“拱木而弃其韡”[4]2607。
朱荃宰对“理”“体”关系的思考其实是明代文章学中文道关系论的一种代表性观点。自宋濂以始,有关文章与道(“理”)之关系的讨论就一直持续。文道关系既是一个本体论问题,也是政治文化、社会思潮与文学、文学思想交融的产物。尽管有如李攀龙、王世贞等复古派代表对“理”持保留态度(如李攀龙评价李梦阳“视古修辞,宁失诸理”[11]394),但受理学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明人对文章本体的认识多持明道、宗经、致用的观点。这在大多数明文话中都有体现,代表者如宋濂《文原》、曾鼎《文式》、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王文禄《文脉》、谭浚《言文》、黄佐《六艺流别》等。而唐宋派更直接以文章是否载道作为衡文师法的标准。朱荃宰作为文人经学家,推崇道统、主“明道”之说尽在情理之中。据焦竑《文通引》可知《文通》当完稿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左右。考察明代文章学中文道论的发展脉络,处于晚明之际的朱荃宰《文通》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3 辨体意识:会通古今、明法究变
文体研究,尤其辨体批评,是明代文章学中成就最为突出的组成部分。朱荃宰《文通》以尊经崇史为主导,但在结构、体例上则以辨体为中心,文体意识十分突出。全书共列文类逾200种①参考何诗海《〈文通〉与明代文体学》(《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统计的数字。(诗、乐、词、曲除外)并辑录前人相关论述以说明,分门别类,条分缕析,规模宏大。与时变文亦变的文学发展史观相呼应,《文通》采取了会通古今、明法究变的辨体意识。用朱荃宰自己的话说就是:
尽翻往案,经经纬史,纵子横集,起始究变,砭病会通,布纲陈目,设绳悬衡,谢华启秀,吕阴律阳,核古印今,庶几乎可以质鬼神而无疑,俟圣人而不惑,而后知向之蓄疑者不少也[4]3101。
“会通”这一源自史学的思想,在这里成为朱荃宰编纂《文通》尤其是辨体分类时的指导思想。早在先秦时期,“会通”就作为一种宏观考察社会历史变化的历史观念产生。《周易·系辞上》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从此,“会通”在历史观念、撰述思路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中国史学和文学研究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②(汉)司马迁《史记》、(唐)刘知几《史通》、(南宋)郑樵《通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清)章学诚《文史通义》都以“会通”为指导。。朱荃宰《文通》以“通”为名,虽是仿《史通》而来,但更主要的还是反映了编纂者力求会通古今,寻绎各体文章写作特点和变化规律,针砭文病,为文章寻求健康发展道路的意图。
该书几篇序言都指出了《文通》在尊体、辨体方面的编纂特色。如焦竑《文通引》说:“今之能文者,非昔之能文者也。昔之文有体有格,有彀有绳,今之文百不得一焉。盖体势未谙则经营易戾,研磨未审则杜撰滋多,于以鼓行词场,分镳艺苑,难之难已。白石朱君,用心綦苦,勒为是编,搜括既富,辨析复精。譬之大将将十万众,部别垒置,旌旗易色。又譬之五都巨肆,珠宝服贽,各安其所,使读之者因方以究变,即势以抒裁。骎骎乎追踪作者,而不啻与之埒,必是编为嚆矢已!”[4]2600他认为作文贵在对文章体格、体势、体裁的研磨熟谙。朱荃宰《文通》“搜括既富,辨析复精”,其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为文之人“因方以究变,即势以抒裁”。罗万爵则说:“《文通》者,指夫文章家所以通之之道也。弗通不可以言文,若《文通》则靡弗通也。盖朱子尝有忧于此,以为文有体,体有要,有流有别。体与要、流与别之弗知,而举吻若有柱,发趾若有棘,燕越岐于前,迷雾作于上,而能殚吾思境所欲极,积吾学力所欲前,悖矣。”[4]2601焦、罗二人都认为明晰文之体要、流别是作文的前提。在复古摹拟之风盛行的明代,这种对辨体的重视实际是研究作文之法的前提和基础,充分凸显了各类文体的个性与品格。
比之焦竑,罗万爵对《文通》辨体之内容、特色的分析更为细致。其中,“体”与“要”是指文章的体式、规范,“流”与“别”则是文体的演变、继承和区别、创新。早在先秦时代,《尚书·毕命》就有“政贵有恒,辞尚体要”的说法。这个“体要”之“体”,正是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滥觞,说明在文章诞生之初,人们已经意识到文体的存在和重要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一方面强调“洞晓情变,曲昭文体”,一方面认为“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通变》),正是意指文体的发展有继承也有创造。而《文通》的确是通过对文章体裁样式的辨析,在追溯源流的基础上辨别文体之间的差异性,以树立写作规范。明人论文体多强调其古今正变的意识,有利于考察文章审美趣味的历史演变。无论是“体”“要”还是“流”“别”都着力于一个“辨”字。刘勰《文心雕龙》是古代文体批评成熟的标志。他在《序志》篇中明确指出自己的文体研究方法:“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囿别区分”就是辨“体”与“要”,“原始以表末”则是溯“流”与析“别”。可见,对文之“体”“要”“流”“别”的分析是中国古代文体批评中较为通行的做法,而《文通》几乎涵盖了刘勰文体论的所有研究方法。
傅汝舟《文通叙》对《文通》辨体特点的总结也很有特色:“朱子著《文通》,某题勒某式,如珪珠之不可混方圆;某式置某义,如灼沥之不敢背寒热;某义镌某长,如密花酒酿,储有余之味,以待舌永;某长杜某害,如醮符鼎魅,设可畏之像,以遣影逃。读者赞曰:美乎大哉!予谓犹通之曲末焉也矣。”[4]2603所谓“某题勒某式”“某式置某义”“某义镌某长”“某长杜某害”从客观上呈现了《文通》编撰各体文章资料时从“因文立体”到“因体范文”的内在思路,同时也特别强调了《文通》辨体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文通·诠梦》多次言及作者“述诸通”的目的,如“予之述诸通也,所以救其弊而障其澜也。”[4]3101因此,对文体的重视,实际上还是源于文章的实用功能。《毛诗·鄘风·定之方中传》中的解说:“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12]316命龟、施命、铭、造命、赋、誓、说、诔、语正是不同社会活动中源于不同功能需要而产生的文辞。经世致用,文体的产生源于此,辨体的目的也在于此。
总体上看,尽管《文通》的文体批评以援引前人成说为主,但在编纂思路、体例上仍能呈现出编者的文章思想和时代风尚。首先,朱荃宰有十分明确的文体分类意识,突出表现在将文与诗、乐、词、曲各自分列,且对文与诗(含源于诗歌的文体)各自特性有清晰把握。他认为,“文”与“诗”均承担着传播礼乐、施行教化的使命,但“诗”不同于“文”的地方在于其有声律。他说:“以文究六经诸史百家两藏之用,而优优于礼;以诗歌词曲宫调溯黄钟之源,而洋洋于乐。”[4]3103这一文体意识的背后实际隐藏着朱荃宰作为经学家对“经”之“义”与“数”的辩证关系的认识。“经”之“义”即“义理”,指经的思想内涵、精神实质;“经”之“数”则指与“经”相关的形式、陈设规模或程序行为等。相对于“数”而言,“义”是最重要的,它是“经”的价值和意义所在。通常情况下,人们都认为“数”易见而“义”难寻,但朱荃宰通过对《诗》《易》《礼》等诸经之“义”与“数”之关系分析,指出“义”固然重要,但“数”亦不可偏废。《文通》引郑樵语:“盖其始也,则数可陈,而义难知;及其久也,则义指难明者,简篇可以纪述,论说可以传授,而所谓数者,一日而不可肄习,则亡之矣。数既亡则义孤行,于是疑儒者之道,有体而无用,而以为义理之说太胜。夫义理之胜,岂足以害事哉?”[4]3056他进一步针对传《诗》过程中分离《诗》之“义”与“数”(声、乐)的弊病加以批判。他说:“诗,言之精者也,奈何鄙夷之?自适齐入海以来,历代《乐志》,徒载其词,罕传其声。善哉!夹漈之言曰:‘夫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古之诗今之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即尼父亦何以云其所得所也?故他经可以诂解,而《诗》独当以声论,即杜夔之属,所得者已不过《鹿鸣》四篇,况其他乎?钟嵘云:‘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也。’崔豹既以义说名,吴兢又以事解目,盖声失则义起,其与齐、鲁、韩、毛无以异也,乐府之道几乎息矣。”[4]2607时至今日,这样的观点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同时,明确的文体意识自然也融合了对各类文体特性的把握,因此各体的编纂思路也有所不同。朱荃宰说:“文则经史子集,篇章字句,假取援喻,条析缕分,而殿以统说。诗自三百,乐府、古、近,体例艳趋,音叶响,而弁以总论。乐左书右图,词曲右调左谱。经义宪章祖训,起弊维新,衡以先民之言,而黜其饾饤之丑,愤然求通而未能,何异语冰而不晓,向若而不叹也。”[4]2609
其次,尊经崇史的思想与文体观相融合,在文体意识中特别突出经、史的地位,表现出强烈的推崇经史之体的意识①《文通》著录“史”之文体有:历、本纪、世家、列传、补注、表历(年表、人表)、书志、书事、注(起居注、仪注)(卷七)、史赞、赞、传、记、题名(卷十二)等。。对经学文体的崇尚自六朝开始,而史书如《春秋》原本就是经书的一种。对史学著述的重视,无疑旗帜鲜明地强化了史家文章在古代文章学谱系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唐宋以来,源于史家的叙事文体在文章写作和文学批评中地位不断上升的体现。这一文体意识一方面受明初宋濂、王祎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明代学术思潮的转变有很大关系。宋濂《文原》说:“世之论文者有二:曰载道,曰纪事。纪事之文,当本于司马迁、班固;而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13]1406虽然宋濂对文章的划分思路较为狭隘,但以载道、纪事区分文章的做法,实际隐含了对经、史两类文体特性的认识。王祎《文训》云:“文之难者,莫难于史。”又云:“经者,载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后圣复作,其蔑以加之矣。”[14]宋、王都强调了两点:一是六经为文之本;二是重史。这些观点俱为朱荃宰树立文体观的不二法门。
最后,《文通》对经义、论、表、策问等科举文体持有较为客观积极的态度。经义作为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一种重要文体,萌芽于汉唐,形成于北宋,兴于明,被认为是明清八股文的雏形和先声[15]。朱荃宰不仅在自叙中将经义与文、诗、乐、词、曲并提,强调经义“宪章祖训,起弊维新”的重要意义,更在书中收录策问(《文通》卷五)、表(《文通》卷八)、策、论和经义(《文通》卷九)等科举文体,尤以经义篇幅最重。如前所述,朱荃宰对经义的重视实与其辩证文运论及重经世的思想相关。从时变文亦变的文运观出发,他认为经义盛于明是时代与文章发展的必然趋势,经义与宋代的词、元代的曲一样,可以作为明代文体的代表;从经世、事功的立场来看,经义在考察士人通经明理能力并以此为标准衡士取士方面,确有其他制度和文体无法取代的优势。他还指出,经义的写作难度甚于其他文体,不仅因其要在破承腹结之间“槖籥六经”、在四股八比之间“舞骖鸟道”,更因其是“与圣人言”。朱荃宰能于不避“举业流弊”①《文通》卷二十九专设“举业流弊”篇录时人王鏊、杨慎等人批评科举的言论。的同时,从上述几方面充分肯定经义的合理性,为科举文体正名,实属难能可贵。《文通》“经义”节不仅详细介绍了经义之名的由来和渊源,更收录了杜静台、冯修吾、袁黄(了凡)、郑定宇、陶石篑、冯具区、冯常伯、宗履庵、李九我、吴因之、汤霍林、王荆石等人有关八股文写作的言论,是研究明代科举与文章学不可多得的资料。
[1]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郑振铎.西谛书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3]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古文辞通义例目[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4]朱荃宰.文通[M]//王水照.历代文话:第3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5]湖广通志:卷52:人物志[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县志辑:第17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7]焦竑.澹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8]钱念孙.分为异体,合为一家:文史关系漫谈[J].安徽史学,1996(4).
[9]王世贞.艺苑卮言[G]//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董其昌.容台集[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11]李攀龙.沧溟先生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2]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宋濂.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14]王祎.王忠文集[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5]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李利克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8.013
I207.62
A
1004-0544(2017)08-0068-0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75103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6M591625)。
孙宗美(1981-),女,四川西昌人,文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刘金波(1968-),男,湖北大悟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