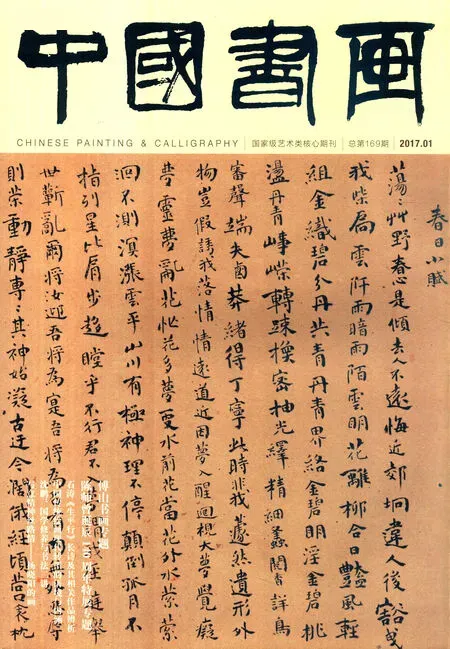延绵与拓展—中国传统绘画现代转型的语境与内涵
延绵与拓展—中国传统绘画现代转型的语境与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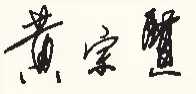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对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绘画的评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有不同的声音,可谓褒贬不一。有人认为20世纪中国画创作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是传统中国画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拓展与推进。也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低谷”,对百年以来一些代表性的,甚至是被称为大师的画家,给予了不肖一顾的评价。不管是褒扬还是贬抑,我们不能不承认,20世纪以来中国画在创作的功能观、价值取向、语言图式及艺术趣味等方面与传统绘画相比都发生了诸多的变革与转换,这种变革的频率、转换的速度与强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衡量艺术成就的高低,不应局限于艺术语言、图式、风格的范畴,更重要的是要看这种艺术是否熨帖了时代文化转换,并以其具有创新性的形式语言,蕴含或折射了时代的风云变化与集体无意识。也就是说,艺术不仅以其感性形式成为历史的视觉证词,其本身就以视觉的形态构建了历史本身。20世纪以来,中国画被质疑、被诘难、被批判、被否定的“机遇”与强度都是其他艺术形式或者说门类无法比拟的。从五四运动前后起直到当下,几乎每一个时期,中国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觉样态都成为一个“靶子”,从百多年前,康有为就发出“如仍守旧不变,中国画学应遂灭绝”,陈独秀直接呼吁用西洋的写实主义“革王画的命”,到抗战时期“中国画的现代化”的吁求,再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画”之名在一些高校被取消,直至80年代的中国画“已到穷途末路”的判断。百年来,中国画几乎没有安定的时光。如此命运,中国画该自我消解、甘于退隐了。但是,在这种无休止的诘难中,中国画不仅没有隐退,没有走入“穷途末路”的绝境,而恰恰坚韧地一方面守望着传统,一方面又不断地革故鼎新,拓展着自己发展的空间,使中国画自身不断地在功能观、价值取向、语汇、图式等方面转换,显示出强大的自我调适更新的机能。每一场诘难风潮之后,中国画的园地里依然郁郁葱葱、一片生机。我们将百年来中国画领域中涌现的大师,如黄宾虹、陈师曾、齐白石、潘天寿、张大千、傅抱石、陆俨少、石鲁等,置于整个中国绘画史上来观照,他们在艺术上的突破与创构并不亚于过往的许多丹青高手、翰墨大家。我们没有理由抽离了具体的卓有成就的艺术家,而妄谈“低谷”,更没有理由信奉“穷途末路”这样的判断。
应该说,每一次中国传统绘画被质疑、被诘难,就换来了我们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再认识与再体认。如果没有五四“美术革命”风潮的激荡,就不会有陈师曾、凌文渊、金城等所谓“国粹派”对中国传统文人画价值的再思考和再体认;如果没有抗战时期对“不食人间烟火”的中国画现状的批判,很难说会有艺术家们的“本土西行”,走向西部,在民族民间艺术中寻找本土艺术大传统资源的壮举;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画存在价值的质疑,很难说会在中国艺术界悄然生发出文化“寻根”的现象,从而使中国画在延绵的文脉中有了自我疆界的新拓展。可以说,正是诘难与冲击,激活了中国本土绘画原有的纳构力,使其从以往封闭式的自我微调转向重构式的大变革。这种大变革超越了中国古代绘画史上自律性的对立法则框架下的微调,超越了不曾停歇的图像“修正”的内部运动。
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变革与转型的意义与价值,不单单体现在中国画笔墨的转化与形式风格上,更表现在功能观的转换与价值取向的转换上。毋庸置疑,长久以来,传统的以文人画为代表的中国画的创作尺度与评价尺度的制定者是文人士大夫,他们是艺术话语权的掌控者,多少文人在笔墨的流转与挥洒中,释放着他们超然遁世的人生态度与“聊以自娱”的逍遥之趣。庙堂式的仙风道骨志气弥漫在千百年来的水墨天地间。的确,也有不少文人士大夫因介入艺术,在笔墨的游荡中抚平了他们人生失意的心灵创伤,成就了他们全新的艺术人生。艺术成为失意者自我拯救的方舟,成为逍遥者的精神家园。超凡脱俗的作为文人内在精神和胸次表征的山水、花鸟艺术在中国传统艺术体系中必然独占鳌头。“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与自娱耳”的艺术价值观必然被文人艺术家所认同。
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民族救亡与生存、制度革命是社会的主题。当族群的生存面临危机的时候,个人的或阶层的精神逍遥何以可能?缘于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直面人生与现实的艺术精神必然被高扬。五四运动以后,艺术改良派、美术革命派、艺术救国论者和艺术工具论者,虽然在艺术观和艺术的价值取向上有所不同,但在反思和批判文人艺术传统上的态度却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传统文人绘画最大的弊端就是在内容上不重现实的表现,而偏重表现文人墨客的风雅之趣和闲情逸志,在表现形式和语言上多尚笔情墨趣,常常是逸笔草草,不重形似。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认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就在于文人画兴起“拨弃形似,倡为士气”。夫士大夫作画“势必自写逸气以鸣高,故只写山川,或间写画竹。率皆简率荒略,而以气韵自矜”。鲁迅先生也对传统文人画只求“墨戏”的艺术旨趣予以了嘲讽与批判。在救亡图存、制度革命的成为迫切任务的历史语境中,一大批艺术家精英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引领艺术从遣性怡情转向现实关怀,并力求以写实的技法直接表现社会现实已蔚成风气,艺术家们自觉地将艺术的视野从“现实的静象”转向火热的生活,从对技巧的关注转向对民众生活的关注,从对优雅的欣赏转向对纯朴的追求,由偏重于个人情趣的抒泻而转向对现实的表现。
虽然,我们不能以全称判断的方式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画都遗弃了超然遁世的艺术理想和笔情墨趣的把玩,但是关注现实,表现现实,为人生而艺术,甚至将艺术视为民族抗争和社会变革战车上的镜子,这的确是20世纪以来包括中国画在内的中国艺术现代性转向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一价值取向的导向下,中国画在功能观、语汇、图式及审美趣味与传统绘画相比上发生了转换,构成了中国艺术现代性独特的内涵。如果谈论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与成就,抽离了特定的语境,忽略了价值取向上的重要转换,仅囿于笔墨、图式、意趣的讨论,就很难弄清楚中国美术新的创获和现代性构建的内涵。
责任编辑: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