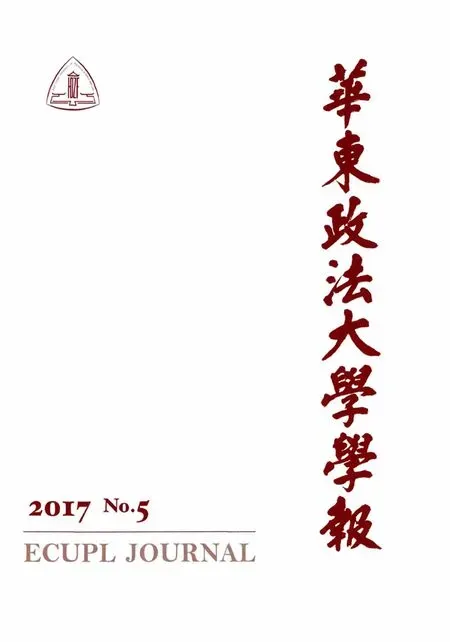民法典中优先购买权制度的体系设计
戴孟勇
民法典中优先购买权制度的体系设计
戴孟勇*
我国现行法规定了10类法定优先购买权,实践中还有大量的政策型优先购买权和约定优先购买权。由于现行法缺乏关于优先购买权的一般性规定,导致不仅各类法定优先购买权欠缺应有的法律规范,政策型优先购买权和约定优先购买权也长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因此,应当利用我国编纂民法典的机会,通盘考虑和设计优先购买权制度。关于优先购买权制度在民法典中的体系设计,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存在五种不同的立法模式。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参考德国、匈牙利的民法典的做法,在民法典分则编买卖合同一章的特种买卖一节中规定约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并明确法定优先购买权原则上应适用关于约定优先购买权的规定。
优先购买权 法定优先购买权 政策型优先购买权 约定优先购买权 民法典
优先购买权(也称先买权)作为现代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为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所承认。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乃至政府文件等也规定了诸多类型的优先购买权。在当前我国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无疑要对优先购买权制度加以规定。问题是,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如何体系性地设计优先购买权制度,目前学界讨论得不多。笔者拟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期对民法典的编纂有所助益。
一、我国优先购买权制度的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实践中存在着种类繁多的优先购买权。根据优先购买权的来源不同,可将其区分为法定优先购买权、政策型优先购买权和约定优先购买权三个类型。
(一)法定优先购买权
所谓法定优先购买权,通常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具体法律关系中的优先购买权,在我国则是指我国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明文规定的具体法律关系中的优先购买权。不同类型的法定优先购买权,其权利客体、成立条件、法律效力及制度价值等方面通常存在区别。
我国目前共有10类法定优先购买权,具体包括:(1)按份共有人对其他按份共有人的共有份额的优先购买权(《物权法》第101条,《民法通则》第78条第3款,《合同法》第340条第1款)。(2)房屋承租人对租赁房屋的优先购买权(《合同法》第230条)。(3)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对单位拥有的职务技术成果的优先购买权(《合同法》第326条第1款)。(4)委托开发合同中的委托人对研究开发人的专利申请权的优先购买权(《合同法》第339条第2款)。(5)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对其他合伙人的财产份额的优先购买权(《合伙企业法》第23条、第42条第2款、第74条第2款)。(6)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其他股东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公司法》第71条第3款、第72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第2款)。(7)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其他成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优先购买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第5项)。(8)市县人民政府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优先购买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26条)。(9)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对珍贵文物的优先购买权(《文物保护法》第58条)。(10)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对外资企业清算处理财产的优先购买权(《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78条)。
(二)政策型优先购买权
所谓政策型优先购买权,是指由国务院的文件、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门规章及文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及文件、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为贯彻特定的政策目标而创设的优先购买权。不同类型的政策型优先购买权,其权利客体、成立条件、制度价值等方面往往也不相同。
我国目前主要有以下10类12种政策型优先购买权:(1)住房制度改革中原住户对单位出售的公有旧住房的优先购买权。〔1〕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鼓励职工购买公有旧住房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88]13号)。(2)住房制度改革中原产权单位对职工出售其所购买的公有住房的优先购买权。〔2〕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鼓励职工购买公有旧住房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88]13号);《国务院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1]30号)第7条;《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1]73号);《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第21条第3款。(3)市县人民政府对购房人转让的经济适用住房或保障性住房的优先购买权。〔3〕参见《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建住房[2007]258号)第30条第3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建保[2010]59号)第11条第1款;《安徽省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办法(试行)》(2013年)第31条第2款。(4)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资产时有关单位对被处置资产的优先购买权,包括以下三类: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时,地方人民政府等单位享有的优先购买权。〔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号)。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重组与处置资产时,企业其他投资者享有的优先购买权。〔5〕参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参与资产重组与处置的暂行规定》(2001年)第7条。③国有企业债转股过程中原企业对被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6〕参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债权转股权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8号)第17条。(5)上市公司对国有股东转让其培育成熟的业务的优先购买权。〔7〕参见国资委、证监会《关于推动国有股东与所控股上市公司解决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的指导意见》(2013年)第5条。(6)有关人民政府或其派出机构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优先购买权。〔8〕参见《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2006年)第75条第2款;《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2009年)第22条;《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2010年)第52条第2款;《厦门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条例》(2014年)第38条第2款、第3款。(7)矿产资源勘查中合作方对对方的投资权益、合作勘察成果的优先购买权。〔9〕参见《中央地质勘查基金管理办法》(财建[2011]2号)第26条第2款;《中央地质勘查基金项目权益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11]3号)第18条;国土资源部、全国工商联《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国土资源领域的意见》(国土资发[2012]100号)第4条。(8)国家对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和文物商店销售的珍贵文物的优先购买权。〔10〕参见《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2005年)第29条;《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2010年)第22条;《宁波市慈城古县城保护条例》(2010年)第15条;《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2012年)第19条第2款第3句;《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2014年)第25条第3款、第53条第2款。(9)原共同共有人对其他原共同共有人分得财产的优先购买权。〔1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2条。(10)联营各方对联营体在联营期间购置的不能分割的房屋、设备等固定资产的优先购买权。〔1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
(三)约定优先购买权
所谓约定优先购买权,是指当事人在法定优先购买权和政策型优先购买权之外,通过法律行为自由创设的优先购买权。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可知,当事人通过遗嘱、合同等法律行为设立优先购买权的,如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及公序良俗,自应承认其效力。
我国现行法虽未明确规定约定优先购买权,但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和地方性法规并不排斥当事人通过约定设立优先购买权。例如,从《合伙企业法》第23条和《公司法》第71条第4款的规定看,当事人如通过合伙协议或公司章程为第三人设立优先购买权,当无不可。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称《物权法解释(一)》)第9条和第13条但书承认,按份共有人之间可以约定:在共有份额因继承、遗赠等原因而移转时或者在按份共有人之间转让共有份额时,按份共有人仍享有优先购买权。这种优先购买权就属于约定优先购买权。〔13〕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66、339页。《广州市中新广州知识城条例》(2012年)第22条第1款第4项第2句关于“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使用权的,应当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约定限制转让的条件,以及依法转让时知识城管委会的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则采用在合同中约定优先购买权的方式,来帮助政府实现其控制此类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流向的政策目标。在司法实践中,也不乏涉及约定优先购买权纠纷的案件。〔14〕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渝民终469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审二商申字第00165号民事裁定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一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1民终956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珠中法民三终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柳市民一终字第581号民事判决书。本文引用的裁判文书凡带有法宝引证码标志(CLI.C.……)的,均取自北大法宝网站;未带有此一标志的,均取自中国裁判文书网。
二、我国现行优先购买权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现行法对法定优先购买权规定得过于简陋,难以为法院裁判案件提供充足的规范依据
我国现行法在规定各类法定优先购买权时,往往只用一个条文简单地指明优先购买权的主体、客体及行使条件,对于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法律效力、行使方式、行使期限及行使效果等重要问题则缺乏规范。这导致各地法院在审理优先购买权案件时难以找到准确的法律依据,严重影响了裁判标准的统一性和裁判结果的可预见性。仅以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为例,司法实践中就存在着债权说、〔15〕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豫法民申字第04698号民事裁定书(CLI.C.664907);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舟民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CLI.C.3557820);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2542号民事判决书(CLI.C.1351978);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唐民四终字第942号民事判决书;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海南一中民一终字第243号民事判决书。请求权或者债权请求权说、〔16〕参见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舟民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CLI.C.3557820);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宁商终字第278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3)沙法民初字第06276号民事判决书。强制缔约请求权说〔17〕参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中中法民一终字第1062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36号民事判决书。等不同观点。这些观点分歧必然会影响各个法院对优先购买权案件的裁判结果,最终既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也不利于保护优先购买权人。
为了解决现行法对法定优先购买权的规范不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一些法定优先购买权作了补充规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房屋租赁解释》)用4个条文细化规定了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物权法解释(一)》用6个条文补充规定了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下称《公司法规定(四)》则用7个条文细化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虽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法定优先购买权的规范不足问题,但却难以为其他类型的法定优先购买权提供规范依据,而且还会导致相关司法解释之间出现矛盾和重复现象。例如,《公司法规定(四)》第20条关于转让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后仍可放弃转让的规定,在《房屋租赁解释》和《物权法解释(一)》中就难觅其踪。又如,《公司法规定(四)》第21条规定的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后果,与《房屋租赁解释》第21条规定的侵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后果和《物权法解释(一)》第12条规定的侵害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效果,也存在明显差异。
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难免破坏优先购买权制度的统一性,并在不同的法定优先购买权之间制造逻辑矛盾。再如,对于在继承的情况下能不能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公司法规定(四)》第16条与《物权法解释(一)》第9条的规定大体相同;对于“同等条件”的判断标准,《公司法规定(四)》第18条与《物权法解释(一)》第10条的规定也基本相同。这种重复规定的做法既不够简洁和经济,也会引发为何对其他法定优先购买权不设立此类规则的疑问,显然不妥。
由上可见,现行法关于法定优先购买权的规定过于简陋,已经在实践中产生了严重的弊端。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来填补相关的法律漏洞,既容易导致各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和重复,也无法提供系统全面的解决方案。有鉴于此,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必须统筹考虑并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二)政策型优先购买权既缺乏设立的法律依据,在现行法中也找不到可资适用的法律规范
我国现有的各类政策型优先购买权,主要是国务院及其部委、最高人民法院或者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为解决一定时期的特定社会问题而设的,各自服务于不同的政策目标,带有较强的应急色彩和浓厚的时代烙印。
尽管政策型优先购买权的设立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在实践中通常会得到法院的承认。〔1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二终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 (CLI.C.1776946);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桂民四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达中民终字第281号民事判决书。因其只要具备相关政策规定的事实条件即可成立,故与法定优先购买权一样具有产生上的强制性。强制设立优先购买权不仅会限制出卖人选择交易相对人的自由,还会影响第三人的利益及交易安全,故应属于民事基本制度的范畴。如果严格按照《立法法》第8条第8项关于“民事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来衡量,这类政策型优先购买权其实是欠缺合法性的。另外,由于现行法未规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关于法定优先购买权的相关规范又过于简陋且具有自身的特性,难以适用或者类推适用于政策型优先购买权,故导致政策型优先购买权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显然,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应当解决政策型优先购买权的合法性及其法律适用问题。
(三)现行法对约定优先购买权未作规定,导致法院裁判相关案件缺乏法律依据
虽然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关于约定优先购买权的成立条件、存续期限、行使条件、行使期限、可移转性等事项,可以由当事人在法律行为中予以约定,但在当事人未就这些事项作出约定的情况下,以及关于约定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行使方式、法律效力、行使效果等事项,仍然需要在法律中予以明文规定,以便给法院裁判案件提供准确的法律依据。然而,现行法不仅对约定优先购买权未作规定,而且对各类法定优先购买权的规定也十分简略,导致法院难以通过适用或类推适用法定优先购买权的有关规定来解决约定优先购买权纠纷,往往只能根据优先购买权的一般原理进行裁判。这种状况既不利于保护约定优先购买权,也不便于法院正确地裁判案件。因此,在编纂民法典时有必要对约定优先购买权加以规定。
三、在民法典中统筹设计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现有的法定优先购买权、政策型优先购买权和约定优先购买权之间具有诸多共性,主要表现在:(1)法律性质相同,都属于形成权。(2)行使条件相同,即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买卖合同和优先购买权人以同等条件表示购买。(3)行使方式相同,都是由优先购买权人向出卖人发出以同等条件购买的单方意思表示。(4)行使期限原则上相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都是在优先购买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出卖事实后的一定期限内。(5)行使效果部分相同,都是首先在出卖人与优先购买权人之间成立以同等条件为内容的买卖合同。
当然,这三类优先购买权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别,主要体现在:(1)成立条件不同。法定优先购买权和政策型优先购买权在有关法律或政策文件规定的事实条件具备时成立;约定优先购买权则在法律行为生效时或者当事人约定的特定条件具备时成立。(2)存续期限不同。约定优先购买权的存续期限由当事人自由约定。法定优先购买权的存续期限往往没有限制,多数情况下与其基础法律关系相始终,如房屋承租人、按份共有人、合伙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优先购买权。政策型优先购买权的存续期限则无统一标准。(3)制度价值不同。法定优先购买权和政策型优先购买权旨在实现特定的立法目的或者贯彻特定的政策目标,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约定优先购买权则旨在践行意思自治原则,仅涉及私人之间的利益分配。(4)法律效力不同。法定优先购买权和政策型优先购买权大多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以便实现特定的立法目的或者贯彻特定的政策目标。约定优先购买权目前因缺乏适当的公示方式,故难以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由于我国现有的三类优先购买权之间既具有诸多共性,也存在一定差别,故若采取目前的这种立法模式,也即仅分散规定各个法定优先购买权的具体规则,而不设立关于优先购买权的一般性规定,则不仅会导致有关法定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出现诸多重复、矛盾或者漏洞,还会使政策型优先购买权和约定优先购买权继续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显然不妥。即便未来立法全部取消各类法定优先购买权和政策型优先购买权,也仍然需要规定约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以便为实践中发生的相关纠纷提供裁判依据。鉴于我国现行优先购买权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法定优先购买权和约定优先购买权又确有存在的必要性,故应当充分利用目前编纂民法典的机会,统筹设计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及其在民法典中的体系位置。至于具体应采用何种规范方式,则可在参考大陆法系民法典的有关立法模式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经综合比较后作出妥适的选择。
四、大陆法系民法典关于优先购买权制度的立法模式
在我国学界所熟知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中,除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民法典未规定优先购买权制度外,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都对法定优先购买权或者约定优先购买权有所规定。根据这些民法典是否规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及其规范方式的不同,大致可将其区分为以下五种立法模式。
(一)在债法编和物权法编分别规定约定优先购买权与法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
1912年1月1日施行的《瑞士债务法》〔19〕《瑞士债务法》,戴永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虽然在外观上与同日施行的《瑞士民法典》〔20〕《瑞士民法典》,戴永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相独立,但实质上是《瑞士民法典》的第五编。两者分别对约定先买权和法定先买权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瑞士债务法》在“买卖和互易”一章第三节“不动产买卖”中,规定了约定先买权的一般规则(第216条至第216e条),内容包括设立先买权的形式要求(第216条)、先买权的存续期限和预告登记(第216a条)、行使条件(第216c条、第216d条)、行使期限(第216e条)、能否移转(第216b条)等方面。
《瑞士民法典》在物权法编“土地所有权”一章第二节“土地所有权的内容与限制”中,规定了法定先买权的一般规则(第681条—第681b条),内容涉及法定先买权的行使条件(第681条第1款、第681a条第1款)、行使期限(第681a条第2款、第3款)、禁止移转(第681条第3款第1句),法定先买权的变更、排除与抛弃(第681b条),以及法定先买权优先于约定先买权(第681条第3款第2句)等方面。此外,《瑞士民法典》还在第682条规定了三类法定先买权,即不动产的按份共有人对应有部分的先买权、建筑权关系中土地所有人对建筑权的先买权和建筑权人对土地的先买权。
瑞士民法采用的这种立法模式的优点是,能够将法定先买权与约定先买权明确地区别开来,为二者分别提供适合自身特征的、比较精细的裁判规则。其缺点之一是,未能将法定先买权与约定先买权的共性抽象出来,导致相关规定之间出现重复。缺点之二是可能导致相关规定之间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例如,《瑞士民法典》第681b条第2款关于权利人可以在行使条件出现后书面放弃法定先买权的规定,在《瑞士债务法》中就没有出现。二者显然未能在逻辑上保持一致。缺点之三是,《瑞士债务法》和《瑞士民法典》将约定先买权与法定先买权的客体均限定为不动产。这不利于解决约定先买权的客体为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时的法律适用问题。
(二)分别在债法编和物权法编规定约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
《德国民法典》〔21〕参见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在债法和物权法两编分别规定了约定先买权的一般规则,由此形成债权性先买权( schuldrechtliches Vorkaufsrecht)与物权性先买权(dingliches Vorkaufsrecht)的基本分类。两者的主要区别是:(1)前者的客体可以为任何客体;后者只能针对土地而设立。〔22〕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465页。(2)前者可以通过合同或其他法律行为设立,后者须依《德国民法典》第873条规定的物权合意与登记而设立。〔23〕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3)前者仅在先买权人与出卖人之间成立法律关系;后者则为一项物权,可以对第三人产生效力。〔24〕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页。
《德国民法典》首先在债法编“买卖、互易”一节中的“先买”部分中,规定了债权性先买权的一般规则(第463条至第 473条),内容包括先买权的行使条件(第463条、第469条第1款、第470条、第471条)、行使期限(第469条第2款)、行使方式及行使效果(第464条)、能否移转(第473条),以及对因行使先买权而成立的买卖合同内容进行调整的规则,例如对第三人应履行的从给付的处理(第466条)、将先买权的客体与其他标的物合并出卖时先买权的行使效果(第467条)、先买权人能否延期支付价款(第468条)、先买权属于数人时应如何行使(第472条)等问题。
此外,《德国民法典》还在物权法编的“先买权”一章中规定了物权性先买权的一般规则(第1094条至第1104条),内容涉及物权性先买权的客体和内容(第1094条、第1095条)、先买权的效力及于从物(第1096条)、就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出卖情形设定先买权(第1097条)、先买权的法律效力(第1098条)、出卖人或第三人的通知义务(第1099条),以及行使先买权之后在出卖人、买受人(或其权利继受人)和先买权人三方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第1100条—第1102条)等方面。
《德国民法典》虽然规定了两类法定先买权,即住房租赁关系中承租人对住房的先买权(第577条)和共同继承人对应继份额的先买权(第2033条、第2034条),但未设置关于法定先买权的一般规则。
德国民法采用的这种立法模式的优点是,根据约定先买权的客体、成立条件及法律效力等的不同,将其区分为债权性先买权与物权性先买权并分别加以规定,既便于当事人选择设立不同类型的先买权,也有利于法院按图索骥裁判案件。其主要缺点在于,一方面,物权性先买权的客体仅限于土地,其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将物权性先买权规定为物权,与物权的支配性特征并不相符。〔25〕德国学说就承认物权性先买权没有支配标的物的权能。参见朱晓喆:《论房屋承租人先买权的对抗力与损害赔偿——基于德国民法的比较视角》,载张谷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2013年总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4页。
(三)仅在债法编规定约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
1.在债法总则中规定约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
《葡萄牙民法典》〔26〕参见《葡萄牙民法典》,唐晓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债之通则”部分“债之渊源”一章“合同”一节的第三分节“优先权之约定”中,规定了约定优先权(即约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第414条至第423条),内容涉及约定优先权的概念及设立方式(第414条、第415条)、出卖人的通知义务及权利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第416条)、将优先权的客体与其他标的物合并出卖时优先权的行使效果(第417条)、对第三人应履行的从给付的处理(第418条)、优先权属于数人时应如何行使(第419条)、优先权的可移转性(第420条)、优先权取得物权效力的条件(第421条)、约定优先权不优于法定优先权(第422条)等。
此外,根据《葡萄牙民法典》的规定,关于约定优先权的某些规定可以经作出必要配合后或者直接适用于都市不动产租赁中承租人的优先权(第1091条)、按份共有人的优先权(第1409条)、土地所有人对地上权的优先权(第1535条)、附有法定通行地役权负担的房地产的所有人对需役地的优先权(第1555条)等法定优先购买权。
《葡萄牙民法典》采用的这种立法模式,既能够全面规定约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又可以妥善解决法定优先购买权的法律适用问题,因而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立法模式。其不足之处是,将约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放置于债法总则中,不尽符合债法总则的抽象化、一般化要求,因为这些一般规则主要与债法分则中的买卖合同有关,难以适用于除买卖合同之外的各种具体之债。
2.在债法分则中规定约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
《匈牙利民法典》〔27〕2013年2月26日颁布,本文引用的条文系笔者译自该法典的英文本。在债法编“转让所有权的合同”部分“特种买卖”一章中,规定了约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第6:221条至第6:223条、第6:226条)。其内容既涉及约定优先购买权的定义及设立条件(第6:221条)、出卖人的通知义务及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条件(第6:222条)、侵害优先购买权的合同的效力(第6:223条)等方面,还包括设立优先购买权的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约定优先购买权取得对抗效力的条件、关于约定优先购买权的规定也适用于法定优先购买权、法定优先购买权优先于约定优先购买权(第6:226条)等规则。此外,法典还规定了一些法定优先购买权,例如在建筑物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相分离的情形,土地所有人对建筑物的优先购买权和建筑物所有人对土地的优先购买权(第5:20条),按份共有人对共有份额的优先购买权(第5:81条)以及因分割而出卖共有物时对共有物的优先购买权(第5:84条第2款)。
《匈牙利民法典》采用的这种立法模式,其实与《德国民法典》对于债权性先买权的处理方式是一致的。由于约定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条件和行使效果均与买卖合同密不可分,故将其规定在债法分则的买卖合同部分中是符合逻辑的。
(四)仅在物权编规定法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
与前述三种立法模式不同,《埃及民法典》〔28〕参见《埃及民法典》,黄文煌译,蒋军洲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并未规定约定先买权,而是在物权编所有权一章“所有权的取得”部分中,专门规定了规定了法定先买权一般规则(第935条至第948条),内容包括先买权的定义(第935条)、法定先买权的类型(第936条)、数个先买权并存时的行使顺序(第937条)、不得行使先买权的情形(第939条),以及先买权的行使程序(第940条—第944条)、法律效力(第945条—第947条)、消灭事由(第948条)等方面。该法规定的法定先买权的客体仅限于不动产(第935条),先买权人包括不动产的空虚所有权人、按份共有人、用益权人、永佃权人及特定情形的相邻所有人(第936条)。
《埃及民法典》采用的这种立法模式,优点是可以为不动产法定优先购买权提供统一的裁判规则,主要缺点是难以解决约定优先购买权的法律适用问题。
(五)仅分散规定具体类型的法定优先购买权,不规定法定或约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
在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的民法典中,仅分散规定了某些具体类型的法定优先购买权,而未规定法定或约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例如,《法国民法典》〔29〕参见《法国民法典》,罗结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5—14条规定了按份共有人对共有份额的优先购买权;《意大利民法典》〔30〕参见《意大利民法典》,费安玲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规定了共同继承人对遗产份额的先买权(第732条)和出租人对分益佃农出售的实物产品的先买权(第2157条)。又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31〕参见《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全译本)》,黄道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规定了两合公司投资人对股权的优先购买权(第85条第2款第4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股权的优先购买权(第93条第2款)和按份共有人对共有份额的优先购买权(第250条)。
这种立法模式的优点是,因其系针对具体类型的法定优先购买权分别设计相应的规则,故可以充分照顾到并体现出各类法定优先购买权自身的特性。但其不足之处是:(1)未能提取法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并加以规定,而这不符合民法典对抽象概括式立法技术的要求;(2)在规定各类法定优先购买权的具体规则时,难免出现重复、遗漏乃至矛盾的现象;(3)难以解决约定优先购买权的法律适用问题。
五、我国未来民法典对优先购买权制度应当采取的规范方式
在前述大陆法系民法典关于优先购买权制度的五种立法模式中,我国目前采取的显然是第五种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本身所具有的诸多不足之处和我国现行优先购买权制度存在的缺陷已如前述,故我国未来民法典不应再采用此一模式。关于瑞士民法采用的第一种立法模式,与我国优先购买权的客体多样化的现实不符,加之其本身也容易导致相关规定之间的重复或矛盾,故我国未来民法典也不应采用这种模式。至于德国民法采用的第二种立法模式,与我国优先购买权的客体主要不是土地并且理论和实践中大多不认为其属于物权的现状不符,故我国未来民法典也不应采用这种模式。接下来的问题是,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采用第三种或者第四种立法模式吗?这需要结合我国的理论与实践详细讨论。
(一)不应在民法典物权法编中规定(法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
应当看到,埃及民法采用的第四种立法模式,系针对以不动产为客体的法定优先购买权而设,与我国优先购买权的类型较多及法定优先购买权的客体多样化的现实不符,故我国未来民法典不应采用此一模式。不过,在之前我国讨论制定物权法的过程中,由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并于2001年出版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曾在第二章“所有权”之下的第八节“优先购买权”中,以法定优先购买权为原型,规定了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第192条-第200条)。〔32〕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4页。2005年出版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物权编》延续了这种做法,只是删除了其中的2个条文(第824-第830条)。〔33〕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物权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219页。这与《埃及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十分相似。起草者如此设计的主要理由是:其一,优先购买权主要是法定的而非当事人约定的权利,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属于一种特殊的物权。其二,由于优先购买权主要涉及所有权的取得问题,故应规定在所有权一章中。〔34〕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326页。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和做法,理由如下:
首先,优先购买权并非都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在我国,约定优先购买权因无法通过登记等方式予以公示,故不具有对抗效力。〔35〕同旨参见李永军:《论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和效力——对我国〈合同法〉第230条及最高法院关于租赁的司法解释的评述》,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140页;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66页。根据《瑞士民法典》第959条、《葡萄牙民法典》第421条第1款、《匈牙利民法典》第6:226条第2款和我国《澳门民法典》第415条第1款的规定,约定优先购买权须在不动产登记簿或者动产的公共登记簿中进行登记,才能取得物权性效力或者说对抗效力。即便是法定优先购买权,如果欠缺适当的方式予以公示,也不宜赋予其对抗效力,以免危害交易安全。〔36〕参见张礼洪:《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之实现——〈物权法〉第101条的法解释和适用》,载《法学》2009年第5期,第52页;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6、1517页。上述观点认为(法定)优先购买权都具有对抗效力,并以此为前提设计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及其体系位置,显然不妥。
其次,优先购买权性质上并不属于物权。在我国,关于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虽然有少数学者采用物权说,〔37〕参见张家勇:《试析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168、169页;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修订版)》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3、744页;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但多数观点赞成形成权说。最高人民法院的主流意见也持形成权说。这与德国和我国台湾的通说是一致的。〔38〕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20、321页;[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史尚宽:《民刑法论丛》,台湾荣泰印书馆1973年版,第152页;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6页。上述观点仅因某些法定优先购买权具有对抗效力,就认为优先购买权是一种特殊的物权,既与我国的主流见解不符,也违反物权具有支配性的基本法理,故不妥当。
最后,上述观点忽视了我国优先购买权的客体多样化的现实。从我国优先购买权的客体看,且不说约定优先购买权的客体可能是股权或者专利权、商标权、网络域名〔39〕相关案例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8)二中民初字第7781号民事判决书(CLI.C.131291)。等知识产权,就是法定优先购买权的客体也不限于有体物,而是包括职务技术成果、专利申请权、合伙人的财产份额、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等财产权在内。〔40〕参见《合同法》第326条第1款、第339条第2款;《合伙企业法》第23条;《公司法》第71条第3款。从这个角度看,上述观点主张将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规定在物权法或者民法典物权编的所有权一章中的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
总之,由于我国优先购买权的类型较多,客体范围较广,加上优先购买权性质上属于形成权,而且并非都具有对抗效力,故我国未来民法典不应在物权法编中规定(法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以免造成民法体系的矛盾、理论解释的困难和司法实践的混乱。
(二)应当在民法典分则编买卖合同部分规定约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
应当看到,无论各类法定优先购买权相互间及其与约定优先购买权之间在成立条件、存续期限、制度价值、法律效力、可移转性等方面存在多大差别,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首要法律效果都是在出卖人与优先购买权人之间成立以同等条件为内容的买卖合同(形成性效果)。在此之后,才会产生该买卖合同是否应优先得到履行或者说优先购买权人是否应优先于第三人取得财产权(优先性效果),以及出卖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效力及其履行效果是否受到影响(反射性效果)等后续问题。如欲在民法典中妥当设计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及其体系位置,就不能忽视行使优先购买权所产生的这三个效果之间的逻辑关系。
由于法定和约定优先购买权并非都具有对抗效力,加之优先购买权的客体不限于有体物,故不应以优先购买权具有对抗效力或者说以行使优先购买权所产生的优先性效果为标准,来提取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并放置于民法典物权编中,否则就难以解释和解决优先购买权缺乏对抗效力或者其客体不是有体物的问题。有学者主张,因优先购买权属于形成权,故若在民法总则中设立权利一节,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可以规定在形成权中。〔41〕参见马新彦、张晓阳:《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兼论优先购买权在未来民法典中的定位》,载《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8页。我国《民法总则》尽管设有第五章“民事权利”,但并未对形成权或者优先购买权加以规定。其实,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系从各类优先购买权中抽象而来,并非对民法典分则编提取公因式的产物,而且涉及很多细节性、技术性规定。将其放置于民法典总则编,既不符合民法总则的高度抽象概括性特征,也不利于人们对该制度的学习、解释与适用。从比较法来看,也找不到在民法典总则编中规定优先购买权的立法例。
笔者认为,行使优先购买权所产生的首要法律效果即形成性效果,在优先购买权的制度构成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前承优先购买权的成立条件、行使条件、行使方式、行使期限等规则,后启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效力以及与行使优先购买权所产生的优先性效果和反射性效果相关的规则。只有从行使优先购买权所产生的形成性效果的角度来提取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才能使这些规则全面涵盖不同类型、不同客体和不同效力的优先购买权,并充分反映优先购买权的形成权性质及其行使条件和行使效果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条件之一是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买卖合同,其行使的首要法律效果是在出卖人与优先购买权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且该买卖合同在成立方式及内容确定等方面具有一定特殊性,故将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放置于民法典分则编的买卖合同部分中,与试用买卖、样品买卖、保留所有权买卖及买回权等特种买卖规定在一处,无论在体系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最合适的。实际上,德国、匈牙利的民法典就是如此处理约定优先购买权问题的。我国未来民法典可以参考这种做法,在民法典分则买卖合同一章的特种买卖一节中,对约定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则加以规定。至于其具体内容,可以综合借鉴瑞士、德国、葡萄牙、匈牙利等国民法典中的相关制度,分别规定以下规则:约定优先购买权的成立条件、存续期限、法律效力、行使条件、行使方式、行使期限、行使效果、可移转性,以及优先购买权属于数人时应如何行使、如何处理买受人应履行的从给付、优先购买权人能否延期支付价款、出卖人将优先购买权的客体与其他标的物合并出卖时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效果、数个优先购买权之间的冲突解决规则,等等。此外,为协调法定优先购买权与约定优先购买权的关系,解决法定优先购买权的法律适用问题,还可参照《匈牙利民法典》第6:226条第3款的做法,专设一个条款规定:“法定优先购买权适用约定优先购买权的有关规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至于各类政策型优先购买权,则应利用编纂民法典之机进行分类清理,使其上升为法定优先购买权或者予以废止,而不宜在民法典中专门予以规定。
目 次
一、我国优先购买权制度的现状分析
二、我国现行优先购买权制度存在的缺陷
三、在民法典中统筹设计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必要性
四、大陆法系民法典关于优先购买权制度的立法模式
五、我国未来民法典对优先购买权制度应当采取的规范方式
* 戴孟勇,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法学方法论与中国民商法研究”(项目号13AZD065)、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法典制定中优先购买权制度的体系性建构研究”(项目号16BFX09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宫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