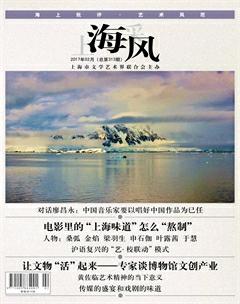走向遗忘的观看
张闳
各位好!我在这里要做一个“反动”的发言,是和会议主题(注:中山大学举行的“视觉,观看与记忆研讨会”)“反向而动”的发言。会议主题讲“记忆”,我却要讲“遗忘”。为了使我所讲的保持内容与形式相一致,我放弃了制作一份可供观看的PPT的企图。
关于视觉,关于观看,我们能说什么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问题。早上开幕式的时候杨小彦教授(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用四幅漫画表达了会议的宗旨,说到学术会议要讨论问题,但不能被问题压倒。可是,我常常被问题所压倒,许多问题对我来说依然是个问题。我接下来要跟诸位谈论的,就是我的一些困惑。
首先,所谓“观看”,在我看来并不是无条件成为视觉问题,乃是在转化为对“图像”的观看的时候,它才是视觉问题。只有在观看事物本身的不在场的时刻,而且事物以图像的形式来呈现的时刻,我们再去观看它的时候,才产生了所谓“视觉问题”。如此看来,实际上视觉问题是一个关于事物的缺席,关于我们对于事物有可能产生的“遗忘”的产物。所以,观看图像是克服遗忘的技术。
接下来我要讲一个事例。我有一位爱好拍照的同事,每次外出,随身总要带上相机,把所有能拍下来的景点和场景,都拍下来。我们将他的拍照行为称作“地毯式拍摄”。有一回,我们一同去欧洲旅游,这位朋友很高兴,早早地做了许多的功课,包括准备相机。他准备了两架相机:一架数码傻瓜机,一架配备多个镜头的单反相机,还特地多买了几块备用电池板和大容量的存储卡,以及一台用来储存照片和视频文件的笔记本电脑。他准备“好好拍一下”!在欧洲,这位朋友大显身手,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之外,他几乎都在拍照。坐在大巴上隔着玻璃窗拍,下车后对着景点拍,自拍和与同伴互拍。导游指点的景点拍,导游没有指点的地方,他觉得好的,也拍。短短十来天里,“地毯式拍摄”战果赫赫,共计有好几千张照片。在回国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几乎闭门不出,在家里整理照片,分门别类,给照片命名,用电脑软件修饰……他让我看他的照片,而他自己却不时地发出惊叹,仿佛是第一次见到照片中的场景。事实上,他已经不记得自己究竟到过何处,也不记得照片中的场景是在哪里、在怎样一种情形下拍摄的。他经常打电话给我,询问他照片中某一建筑是哪个地方的什么建筑。他的整个旅游过程都在拍照,根本就没有留心观看所到之处的情形。只是等到他整理照片的时候,旅游才真正开始。
旅游让他收获了一堆照片,通过这些照片,象征性地占有了照片中的景物。但在他靠不住的记忆里,这些景物与其他任何陌生的照片一样,仅仅是一种“象征”的存在。在具体的旅游过程中,他的真身似乎并不在场,只有照相机镜头代替他,而他仅仅是相机的支架而已。而在照片中旅游,似乎比他的真身在现实中旅游,来得更为真实。地毯式拍照一路拍过去以后,和他记忆相关的非常稀薄。作为记忆唤醒的图片反倒是关于遗忘的图式,他抱怨自己记性不好,又说,幸好拍了这些照片,不然,这欧洲算是白跑一趟。其实是自己的眼睛根本没有看。这个摄影的例子很有趣地揭示了观看和记忆遗忘之间的关系。我们为了记忆而拍摄,可是,拍照并不能够帮助我们记忆,相反,它让我们陷于关于照片的记忆而非事物的记忆。照片成为我们的观看与事物之间的隔膜和障碍。我们的观看和拍摄,与其说是关于“记忆”的,不如说是关于“遗忘”的。
观看从以下几种途径走向遗忘:
第一种:“诱导性遗忘”。图像作为记忆,毋宁说是一种诱导性记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工农兵”图像。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图像体系乃是关于政治性记忆的建构,是对于“工农兵”的选择性的记忆。这种抽象的关于“工农兵”的记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以压抑具体的“工农兵”记忆为条件的,有时甚至以消灭的私人记忆为前提。而且往往需要通过暴力的手段来实现。上午有发言者提到对于照相馆的改造、管理,乃至以后对私人性照片的焚毁,这些行动表明,政治权力在垄断记忆权。图片记录并非必然地指向每个具体个人的记忆。政治权力介入,导致一种选择性记忆和对具体私人记忆的消除,进而构成历史“遗忘”的基础。文革后我们看到仍有大量的私人照片重新浮现水面,这里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关于记忆权的“垄断”与“反垄断”的争夺。
第二种:“记忆短路”。正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呈现出来的那样,记忆会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时间延伸、放大或压缩,但还有一种“记忆短路”现象。在当代艺术中,红色波普艺术的初衷是出于对政治记忆提醒,作为克服遗忘的手段,但实际上大量的当代红色波普艺术却更像是一种遗忘的技术。如王广义的“大字报系列”把文革的宣传画、墙报和当下文化结合在一起,似乎提示着当下的文化和文革的政治之间的关联。但这一点简单的关联,在我看来是一种“记忆短路”。在完成了相似性的简单连接之后,繪画的意义生成过程就结束了,所表现的事物以及要指向的意义就归于终结。这样的图像里面包含的语境和政治性的创伤经验就很快被耗散,并很容易迅速进入到视觉消费领域,进而被遗忘。关于政治记忆、历史记忆、在图像表达方面应该有更丰富、更多的手段。
第三种:“记忆固化”。记忆没有弹性了。晋永权先生在发言中提到的“标准照”问题。在我看来,“标准像”就是对照片的谋杀。“标准照”表面上看似乎是对活着的人物的记录,但它却是死亡的标志。在所谓“标准照”中,时间和空间的凝固不动。人的“标准照”常常用来做遗像,因为在那一刻,生命结束了。所以说,“标准照”与其说是指向记忆的,不如说是基于对死者的缅怀。通过“标准照”,唤起一种追悼和缅怀的记忆,但是一体化的和固化的“标准照”背后,更多是凝固的记忆,除非放在特殊领域里面,否则没有意义。艺术家张晓刚曾对此做了反讽性处理,他用文革时期拍“标准照”的方式,作为对文革期间家庭记忆的反讽。以记忆的褪色、标准化形式下的漏洞和补丁的图像,来作为抵御和批判“视觉固化”“记忆固话”的手段,同时也是对“遗忘”的批判。
第四种:“图像膨胀”。在今天,这种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如前面所说的,我的同事从欧洲回来拍了数以千计的照片,还从其他同事里面要了很多,他整理完了以后,我想他也再不会去看它们了。这是记忆死亡的另一种表征。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机械的反应在一瞬间的抓拍捕捉光影的投射,建立视觉与记忆之间的最浅表的关联。大量的膨胀使我们视觉和记忆回到最原始的状态,记忆如同原始生物一般,依靠机械的反应,依靠图像无限的自我复制和自我增殖,但是留在记忆浅表,而且被大量覆盖。这样浅表的记忆对一个光影刺激机械反应的记忆,实际上是视觉历史记忆关联的一种松弛甚至是剥落。在艺术史上,安迪·沃霍尔曾经通过对这种膨胀和自我增殖的图像的戏仿,表达了对这一现象的反思批判。在今天这种视觉影象工具特别发达的情况下,图像膨胀如同无法遏止的视觉肿瘤,严重侵蚀着正常的视觉记忆。重新思考视觉艺术以及记忆的技术如何面对当下大量的事物膨胀和遗忘的现实生活,这是一个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很抱歉,我的这一场“反动的”发言,不过浅尝辄止,又未能满足诸位的观看欲,徒然占用了诸位的时间。请原谅!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