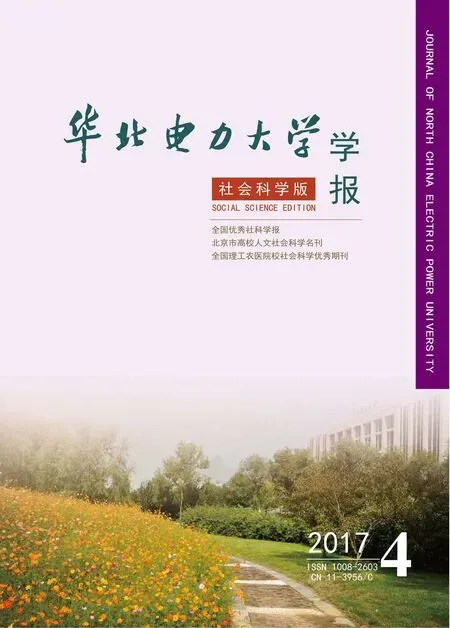“文学”的概念:在取与舍之间
崔 琦
(华北电力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2206)
“文学”的概念:在取与舍之间
崔 琦
(华北电力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2206)
周作人留日时期所撰《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有关“文学”的定义及论述基本来自美国教授Hunt所著《文学概论》。Hunt的目的在于构建“文学”学科在高等学术机关中的位置,构建过程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强烈需求密切相关。周作人对此保有疑虑,因此在编译过程中转而将批判矛头指向林传甲的“文以载道”。
周作人;文章;文学;Hunt
一、问题的提出
1906年夏秋之际,周作人跟随短暂回国的大哥鲁迅,一同奔赴日本东京,开始了自己的留日生涯。在这之后近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即直至1909年鲁迅回国,周作人跟随其兄在东京正式开始了他们的“文学活动”。此次“文学活动”中的《摩罗诗力说》和《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以下简称《论文章》)应当是兄弟俩当时最重要的论“文学”的文章,共同强调文学是国民精神的表现,具有改造国民精神的作用,显示出他们“对于西方近代文学的理解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水准”[1]226。虽然这两篇文章在晚清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从中已可窥见贯穿二人一生的“文学”理想,是解读周氏兄弟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不可否认,留日时期的周作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和鲁迅相同的思想倾向,这一点使得他们更多地表现为一个整体,与其他的留学生区别开来。但若我们在研究中总是以“周氏兄弟”来统摄二人,就容易忽略他们各自所独有的特性。木山英雄提醒我们,虽然两人之间的“分工意识明确可见”,但如果“通过对于资料运用时的选择方式和侧重点等具体事实的分析,亦会引起对于作者自身特性的重新思考”。[1]226
根据日本学者根岸宗一郎的调查,周作人留日时期的《哀弦篇》和《论文章》皆为编译之作,[2]23-32根岸宗一郎对周作人在“编译”中“求取”的一面做了详尽分析,却没有继续追问周作人“舍弃”的部分及原因,这也将是本文研究的起点。本文认为,对文本中涉及到的外文材料研究,不能仅停留在“求同”的层面上,即确认作者究竟使用了哪些材料,更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求异”的动机。也就是说不能单看作者汲取了什么,更要看他舍弃、修改或又掩盖了什么,只有在取舍和选择之间,才能更好地把握作者真正的意图。此外,根岸宗一郎在研究中只选择处理了《论文章》中前半部分所涉及的外文材料,没有继续讨论《论文章》后半部分所对话的中文文本。而本文认为,只有把一个文本放在多个文本的关系当中,寻找其中的差异,找到与原文本形成互文和对话关系的潜在文本,作者的意图才有可能真正的浮现出来。
二、亨德的《文学概论》
进入这篇理论文章之前,还是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周作人在晚年是如何记述自己的这段经历的:
我对于“河南”的投稿,一共只有两篇,分在三期登出,因为有一篇的名目仿佛是“论文学之界说与其意义,并及近时中国论文之失”,上半杂抄文学概论的文章,凑成一篇,下半是根据了新说,来批评那时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的。这本文学史是京师大学堂教员林传甲所著,里面妙论很多,就一条一条的抄了出来,不惮其烦的加以批驳。此外另有一篇,那就很短了,题目是“哀弦篇”。[3]255
时隔近六十年,知堂老人的回忆大体是准确的,但仔细去看,会发现有一个细小的文字上的出入,即原先题目中的“文章”被置换成了“文学”。这一置换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折射出了周作人身处语言环境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提醒我们关注由“文章”(文学)所引发的理论讨论和周作人文学活动之间的密切关联。
“文章”一词是周作人用来对应翻译Literature,考察鲁迅的写作也可以发现,虽然身处日本,兄弟俩却多使用“文章”而非“文学”来翻译literature。其实在周作人写作这篇文章时,“文学”作为literature的日译词已经在晚清流行,梁启超、王国维、徐念慈等人的文章中都已经在现代意义上开始使用“文学”一词。关于周氏兄弟为什么用“文章”而不用“文学”,木山英雄将其放到与章太炎的师承关系上去谈,对比章太炎有意为之的“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的“文学”观,木山英雄认为:“比周氏兄弟更早一步接受了西欧文学观的王国维,经常自觉使用日本造译语‘文学',而周氏兄弟共同的译语,却既与厌恶此种‘新名词'的《国粹学报》和章炳麟同道,同时又有意识地区别于章氏‘过于宽泛'的定义。”[1]224而如果我们把同处汉字圈内的夏目漱石对“文学”的焦虑拿来参考的话,周氏兄弟的选择与其说是“有意识地区别于章氏过于宽泛的定义”,不如说他们从心底里赞同章氏,并在章氏所倡导的“用国粹激扬种性,增进爱国热肠”,造新字和新名词都必须“合小学”等理念的指导下,用“文章”来翻译literature。因此周作人说“此所谓文字上的一种洁癖,与复古全无关系,且正以有此洁癖乃能知复古之无谓。”[4]56这恐怕是“文章”一词最好的注脚。
正如《知堂回想录》所提示的那样,《论文章》的上半部分,杂抄的是宏德的《文学概论》,这在《论文章》一文中也有明确提示。这里的《文学概论》,指的就是Theodore Whitefield Hunt(1844-1930)初版于1906年2月的Literature,Its Priciples and Problems,由美国Funk&Wagnalls Company出版。关于此书在明治日本的流通情况,据根岸宗一郎的考察,东京丸善书店月刊PR志《学灯》1907年5月号的Monthly 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中列有此书,因此周作人很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向丸善订购的。[5]70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Hunt的这本著作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渊源并没有止于20世纪初的这次短暂交汇。郑振铎在1923年第1期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中就列有此书。而八年之后,即1935年9月,时任暨南大学国文系教授的傅东华还翻译出版了该书的全译本《文学概论》,收入王云五主编的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傅东华早年曾参加过由周作人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一度曾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员,1933年7月还与郑振铎主编大型月刊《文学》。从这一粗略的勾画中可以看出,《文学概论》基本上在文学研究会的脉络中被阅读和介绍的。
关于作者Theodore Whitefield Hunt,根据此书的扉页,Hunt时任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教授(Professor of English),是English Prose and Prose Writer和Ethical Teaching in Old English Literature等书的作者。扉二上则写明此书献给“the students of our literary institutions”,即表明该书的性质类似于课堂教科书。该书共两编,各十二章:
第一编
一、解释文学的几个向导原则
二、文学的一个定义
三、文学研究的方法
四、文学的范围——文学与科学
五、文学和哲学
六、文学与政治
七、文学与语言
八、文学与文学批评
九、文学与人生
十、文学和伦理
十一、文学与艺术
十二、文学的使命
第二编
一、文学的阅读和研究之目的
二、文学诸体裁的发生和生长
三、首要的诗歌类型poetic types
四、首要的散文类型prose types
五、史诗epic verse之史的发展
六、诗歌poetry
七、诗学poetics
八、作为文学一种体裁的散文小说prose fiction
九、文学上的未决问题一
十、文学上的未决问题二
十一、文学中的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
十二、文学在自由学问中的地位
从章节安排上来看,此书要处理的问题正如Hunt自己在序言中所说的,是“文学本身”(literature itself)。Hunt认为“文学”是一种“高等而且健康的思想训练(high and healthful mental exercise)”,可以在“训练思想的诸种学科(disciplinary studies)中占有一个位置”。换句话说,“文学”之所以会在Hunt这里成为一个问题,其目的是为了要确立“文学”的范围,将它和其他“人类知识的各大部门”,如科学、哲学、政治、伦理、艺术、语言等划清界限,以努力建构“文学”这一学科在高等学术机关中的地位。因此,他在此书的第二部分中还专门讨论了属于“文学”这一科中的各种类型,诗歌(poetic)和散文(prose),以确立文学研究的范围。
具体来看,第一章“解释文学的几个向导原则”在全书中具有纲领性的作用,清楚明白地交代了Hunt写作此书的动机和目的。首先,Hunt提出存在一种“文学的科学”,即研究文学必须使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按照一套“整齐的程序”,才能成为一种“体系”供学者做研究,因为只有科学的方法才是“唯一合理的观点”,否则难以有“满意的进步”。在第四章“文学的范围——文学与科学”中,Hunt对所谓科学的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即应使用已有的“人类知识”中的各种科学方法如测绘学、经济学、人种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对“文学”提出“科学”的要求,“所以我们有一种文学的科学,正无异于有一种天文学或物理学的科学。”[6]78“近代科学对文学学科的建立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科学和文学密不可分,但并不占着完全相同的领土。科学的目标主要是种族经由发现和发明而得的物质的和工业的进步,以及对于外在的世界求得一个更明白的理解,而‘文学'的目标则主要是关于国民思想和国民趣味的解释。”[6]87因此,必须“把文学的研究从技术的和形式的地位被提高到一种真正的知识的操练的地位。”[6]50由此可见,Hunt在这里所主张的“文学”的独立,是与整个现代知识的分化息息相关的,换句话说,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建立是在与西方现代科学、哲学、政治、语言、伦理、艺术等学科分治的原则上提出的。文学被归纳到了“知识”的范畴里,而这种“知识”的建立是为了塑造和解释国民思想和国民趣味。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辨析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起源,看到它身上所带有的明显的现代性叙事的味道。
接下来,Hunt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时西方学界普遍流行的“显微镜方法”(microscopic method)。这种方法将“诗歌结构上极细微之处上升于原理的地位,将一首诗的制作日期或最初出现日期,字法、格律、词句的次序,全文的标点以及类似的资料看成了主要的研究题目,致将作品的意义和精神,以及隐于作品底下却使它获得生机的那一些属类(generic)元素,倒看作无足轻重了。”[6]60主张文学应从语言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把文学当作一种“思想”的体现或一种“组织”的表现去考察是Hunt在此书中的一个主要观点。在第七章“文学与语言”中,他这样说道:
所谓文学批评家把他的研究的面逐渐缩小,终至只剩了一个咬字嚼字的专家,一个文字和词语的解剖家,在他的文字实验室里工作着,犹之植物学家和化学家在他们的科学实验室里工作一般。当这样的批评家翻开一本散文或诗的时候,首要的问题已不是早时候那些关于风格和趣味的问题,关于情绪,精神以及美的法则的问题,却是关于语根和语变,前附和语尾,正文和余文,古训和通训,等等的新问题。
……
这种倾向在我们的文学教科书里也分明可以看见。现在一般为中学和高等学校编制的文学教科书是愈趋于言语学的方面了。其中所包含的版本批评,注解,解释,定义,以及批评的资料等等,都以求文字学的精密和养成学生的文字技能为主旨。学生的注意是这么专心地使它用在一行一字上,细微的辨别上,和批评意见及校勘争执的历史上,以致没有时间留给他去把那作家的作品当作一件文学的产物而给以一种总括的观察。[6]144-145
Hunt力图将语言和文学分开的努力正好提示了我们literature一词在欧洲语言中意义的变迁。正如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中所整理的那样,Literature从14世纪起出现在英文里,其意为“通过阅读所得到的高雅知识”,16世纪开始,意涵接近于广泛阅读的状态,几乎与现代的literacy(读写能力)相一致。直至中世纪末期与文艺复兴时期,literature的词义开始跟“阅读技巧”、“书籍特质”等意思分离开来,17世纪中叶literature被确立为“具想象力的作品”(imaginative writing),并一直沿用到19世纪,这和浪漫主义的兴起关联密切。[7]268-274
而从Hunt的焦虑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literature一词与读写能力、语言运用及修辞技巧等意思的分离已有近两个多世纪,但在20世纪初的西方大学里却依旧常常把这些归为literature的作品当作运用语言和修辞的经典来阅读。也就是说,直至20世纪初,literature一词的含义仍在不断的变动当中,并没有完全稳定下来。概念的不稳定性与知识生产的需求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被“生产”出来的现代“知识”,而Hunt的论述则清楚地为我们呈现了现代“文学”在“生产”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困难与阻力。因此在最后一章《文学在自由学问中的地位》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所谓“教育的文学”,至如新近所谓“学校对于文学研究的承认”的讨论,其在现代英国文学界和教育界面前的状态,是从来所没有的,原来这样的讨论特别适应于高等教育,和那些正在高等教育训练过程中的人们。若要寻出如今对于这个题目的兴味所以增加的特别理由,那我们手边至少就有一些。其一是由教育本身方面的热心的普遍增加;
那么既然要“生产”并“推广”这样的一种“文学”概念,则必然要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追溯文学的“起源”,即“文学何时及如何最先取得它的具体独立的形式,何时及如何才和它在称为个别民族类型和生活以前所取的各种未成熟和无组织的表现形式开始判别。”[6]7Hunt将文学的起源追溯到一个民族的“口头文学”(the oral literature of a people),包括一个民族nation或一个种族race的“歌谣songs、谚语proverbs、故事legends、传说traditons、未经记录的saga、民俗folk-lore、俗语folk-speech”,并举例“斯干的那维亚诸国作为一属看时,都以富有这种基于民族生活上的文学材料著名于世,史诗如贝奥武夫(Beowulf),就是由那些富于暗示力的北方saga建造起来的。”
很明显,Hunt所提出的“文学”的“起源”是在被颠倒的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即先有建构“文学”的需要,然后才会产生追溯“起源”的诉求。而Hunt追溯“起源”的方法又提示我们,“文学”的建构和民族国家的叙述和想象直接挂钩。因此,“文学”在建立自己起源的时候,早已被烙上了深深的现代性的印记。这一点在第二章Hunt给“文学”下定义时更为明显:
Literature is the written expression of thought,through the imagination,feelings and taste,in such an untechnical form as to make it intelligible and interesting to the general mind.English literature,consequently,is such an expression of English thought to the general English mind.[8]24
这里的最后一句话点明了“文学”的民族特性和其被赋予的民族想象的功能。其所传递的观念可理解“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学”,即一种“民族国家”式的“文学”的思考方式。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在翻译的时候却省略了这一句。
三、 周作人的取与舍
如上所述,Hunt的《文学概论》旨在谋求“文学”的学科独立,实现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政治、伦理、语言、艺术等学科的分治,而这一整套“科学的知识”体系又是直接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和想象的。现在让我们回到《论文章》一文中来。对照英文原文即可发现,周作人对《文学概论》的取舍态度非常明确,即一如其文章标题所示,只选取了第一编的第二章“文学的一个定义”和第十二章“文学的使命”,其余各章内容一概略过,未入其文,对上一小节提到的内容更是只字未提。而第二章和第九章的编译,除了小部分省略不译之外,基本上还是忠实于Hunt的原著(详细的文本对比请见根岸宗一郎的研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为什么同样的内容可以不经修改被移植过来并成为论述的主体部分呢?从第二章跳到第九章,周作人无疑应该通读了全书,很清楚Hunt的写作动机。然而他对其他内容的“舍弃”真的是因为“无用”或“无共鸣”而“舍”吗?如果重新细读《论文章》,得出的答案可能完全不一样。
《论文章》开头即立论,提出“自成美大之国民(nation,义与臣民有别)者,有二要素焉:一曰质体,一曰精神。”“以言国民精神,理亦视此,故又可字曰国魂。盖凡种人之合,语其原始,虽群至庞大,又甚杂糅而不纯,……然究以同气之故,则思想感情之发现,自于众异之中,不期而然,趋于同致。”周作人在这里特意用英文nation来标明国民与臣民的区别,并强调国民精神的再造才是立国的根本。接下来周作人以古埃及、古希腊和“新进之民”斯拉夫民族为例,认为正是因为有伟大的古代文明和“高明华大”的“新文章”,才得“民气日昌”,“前路光明”。也就是说,“国民”的塑造是周作人重新讨论“文学”的出发点。虽然周作人并没有直接引用Hunt的观点,但基本接受了“国民文学”这样一种现代性的叙事逻辑。
接下来,周作人极力批判数千年来中国“文章”“一统于儒,思想拘囚”的历史现状,认为“文章丧死”将导致众人“迷沦实趣,以自梏亡”,而“思想之翦伐于国民,良较帝力为宏厉而尤可怖也!”与此同时,周作人亦批判当时晚清趋于实利的“富强之说”,认为“手治文章,心仪功利,矛盾奈何!”儒教的束缚与经世之业的“文章”观和想象“国民精神”的“国民文学”、“民族文学”水火不相容。因为前者言必尊孔子,只能造就“臣民”,臣属于儒教的臣民。而后者则以“想象”和“虚构”为主,塑造的是“国民”,是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服务的。于是,周作人很自然地就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引入了Hunt的文学定义和文学使命的论述。
有意思的是,在进入Hunt的文学定义之前,周作人对literature一词在西方最初的意思做了一番调查和辨析。
原泰西文章一语,系出拉体诺文Litera及Literatura二字,其义至杂糅,即罗马当时亦鲜确解。挞实图用称文字之形,阔迭廉以文谱为Literature,而昔什洛则以总解学问之事。盖其来既久远,又本无精当之释义,故至今日,悬解益纷,殊莫能定。
这段话是周作人自己归纳的,并非出自Hunt。也就是说,周作人对Literature一词的把握并非本质主义的,他从词义的历史变迁中,把握到了Literature身上所具有的现代性。这与Hunt进入“文学”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Hunt不是从词义的变迁,而是上文提到的诸种学科的知识分类进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追根溯源上,周作人走的比Hunt还远。
接下来,周作人亦没有立即交代Hunt的结论,而是花了大量的篇幅把Hunt的论述过程也全盘引用了过来,即西方历史上已有的诸多文论家关于“文学”一词的定义以及各自的问题所在。Hunt所列举的各种定义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种是过于宽泛的文学定义,将学识和知识都纳入了进来,第二种则将文学的特质限定在想象、感情等标识之上。Literature词义的不稳定性在此再次得到放大。因此,在结束对Hunt的引用之后,周作人说了下面这段话:
虽然,吾为此言,故非偏执一说,奉为臬极,持以量文章,求全责备,必悉合于是而后可也,亦不过姑建此解,为理想文章之象。……天下之文,浩何所极,才性异区,文词繁诡,欲为品别,斯信难矣。第且主一说焉,以为吾心之的,则读书自易,而不至随波逐流,意为谬解,有如呓谵,为大方笑也。
周作人说自己“姑建此解,为理想文章之象”,应并非谦辞。“第且主一说焉,以为吾心之的”。可以说,周作人对翻译过来的这个“文学”(Literature)究竟是什么,是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的。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本身正如乔森纳·卡勒所指出的那样:
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呈现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理念,一种被赋予若干功能的、特殊的书面语言。……文学教育那些麻木不仁的懂得感激,培养一种民族自豪感,在不同阶级之间制造一种伙伴兄弟的感觉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它还起到了一种替代..的作用。[9]38
“宗教”一词的使用在这里可谓鞭辟入里,尤其当我们明白了“文学”在建立的当初就为了创立一套知识体系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Hunt给文学下的定义以及周作人的翻译:
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taste),笔为文书,脱离学术,遍及都凡,皆得领解(intelligible),又生兴趣(interesting)者也。
这里的“意象”对应的英文单词是imagination,也就是“想象”,可以说Hunt的文学定义基本呈现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后文学和浪漫主义之间的紧密关联。正如铃木贞美在解析浪漫主义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时所阐述的那样:当“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这一观念附加到文学上以后,“这种浪漫的情怀在面对现实社会的情况下,就会从理想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现状产生强烈的不满和犀利的批判。针对政治与社会现实的束缚而有所感悟的时候,就会变成革命的浪漫主义。……针对近代社会的现实秩序进行反抗,会产生在精神世界掀起革命的愿望,颠覆伦理和美学秩序。”[10]34因此,很明显周作人是希望借西方“文学”的概念来打破儒教一统天下文章的时局,换句话说,这只是他借来使用的一个理念或工具,所以他才说自己“姑建此解”。
四、教科书中的“文学”叙事
《论文章》的后半部分的对话文本有三个,分别是陶曾佑的《中国文学之概观》(载《著作林》第十三期)、金松岑的《文学上之美术观》(载《新小说》第十七号)和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而周作人着墨最多的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林传甲根本不明白什么是“文学”,却妄作“文学史”,对他的批判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还是批“文以载道”,即言必称孔教的痼疾,第二则是对其未将“小说”纳入“文学史”表示极大的不满。
有意思的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晚清文学一科的设立有直接的关联。1902年张百熙执掌京师大学,拟定《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的功课分政治、文学、格致、农学、工艺、商务、医术七科,而文学科中有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1903张之洞参与重订学堂章程,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文学科的范围缩小到文学和史学,具体共分为九门: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文学。而“中国文学门”中主要课程包括“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种。1904年林传甲经严复推荐,被张百熙聘为京师大学堂国文科教员讲授中国文学课程,而这本《中国文学史》就是当时所写的授课报告,故封面书名上方以双行字注有“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字样”,而据查,此书1904年和1906年两度印行,直到1910年由武林谋新室翻印单行本,可见其流传阅读范围之广。[11]329-333。
正如陈平原所论述的那样,“世人多关注此书与其时已有中译本的《历朝文学史》(笹川种郎作)的关系,这自然没错,只是林著对于笹川‘文学史'的借鉴,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大有来头。”[12]116对照《奏定大学堂章程》即可发现,林著全书共分十六章,与章程中的“研究文学之要义”前十六款完全吻合。因此陈平原认为,“正因如此,谈论林著之得失,与其从对于“笹川著述的改造入手,不如多关注作者是如何适应《奏定大学堂章程》的。比如,常见论者批评林著排斥小说戏曲,可那正是大学堂章程的特点,林君只是太循规蹈矩罢了。……说到底,这是一部普及知识的“讲义”,不是立一家之言的“著述”。”[12]117
然林著的得失并非本文要讨论的对象。在这里笔者想突出讨论的是,Hunt和林传甲身份性质的雷同。上文已有提及,Hunt时任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教授,而《文学概论》也是一部课堂教科书性质的著作。也就是说,两者都在生产一种“文学”的知识,而“知识”的接受者也是可以大致确定的,即首先应该是所在大学里的学生,至于后来书籍经由何种渠道流出校园则另当别论。因此,我们又是否可以将《论文章》中对林著的逐条批评,视作周作人对当时中国大学里知识生产体系的一种批判?这也提醒我们,“文学”知识的生产和现代化与近代大学教育之间关系密切,而时隔近十年之后,即1918年,当周作人走进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等一系列文学课程时,他是否也意识到了自己已经进入到某种现代知识的体制内部呢?当五四新文化大旗举起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的装置已经形成,而身在装置内部的周作人也已很难脱身对此再进行反省了。
五、同时代汉字圈内的“文学”讨论
周作人在留学日本之前,曾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课程分汉文和洋文两种,洋文也就是英语。根据当时的日记来看,周作人在江南水师的这五年时间里虽然学会了英语但并没有接触到太多的英语文学,真正的购买并阅读英语文学,应该是在其抵达日本之后,也就是说,他是在明治时期的日本接触到英语文学和“文学”的。这从他日后的回忆中也可窥见一斑:
我于1906年8月到东京,在丸善所买最初的书是圣兹伯利(G.Sainsbury)的《英文学小史》一册与泰纳的英译四册……我在江南水师学堂学的外国语是英文……自己的兴趣却是在文学方面,因此找一两本英文学史来看看,也是很平常的事。[5]70
我到达东京的时候,下宿里收到丸善书店送来的一包西书,是鲁迅在回国前所订购的,内计美国该莱(Gayley)编的“英文学里的古典神话”,法国戴恩(Taine)的“英国文学史”四册,乃是英译的。说也可笑,我从这书才看见所谓文学史,而书里也很特别,又说上许多社会情形,这也增加我不少见闻。[3]230
华伦女士(Kate M.Warren)所编的《英文学宝库》(A Treasury of English Literature)……于1906年出版,次年又为便利学生所见,分出六册,每册价一先令。我在1908年所买,就是这种版本。……这部书选择固佳,多收古代诗文尤为可贵,——尤其是在中国的学生,现在可以略窥一斑,实在非常便利。……因了勃路克的《古代英文学史》,引起了我对于《贝奥武尔夫》的兴味……[13]398
周作人在这里提到的George Sainsbury的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英文学小史》)、Hippolyte Taine的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英国文学史》)、Gayley的《英文学里的古典神话》、Charles MillsGayley的The Classic Myth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Art,Kate M.Warren的A Treasury of English Literature(《英文学宝库》)以及 Rev.Stopford Brooke的English Literature(《古代英文学史》)都是他日后编写《欧洲文学史》和《近代欧洲文学史》中“英国文学”部分的主要材料来源,同样也是促成他思考究竟什么才是“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而在周作人写作《论文章》的前一年即1907年5月,活跃在明治日本文坛上的大作家夏目漱石,出版了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授课讲义著名的《文学论》。也正是在出版《文学论》的两个月前,他辞去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教职进入《朝日新闻》成为专栏作家。有意思的是,夏目漱石早年(1900年)曾被文部省派往英国留学并于1902年12月回国,而《文学论》就是在英国“广涉英国文学方面之书籍”,却发现“读文学书不能知文学为何物”之后所采用的“以血洗血”的思考结果。”也就是说《文学论》是为了“从根本上究明何谓文学之问题”。这在他1906年11月为《文学论》撰写的自序中已有详细提及。
余少时曾嗜读汉籍。虽修读时间甚短,于‘左国史汉’中,余冥冥里得出文学之定义,漠漠然觉文学即如斯者也。窃以为英国文学亦应如此。……反躬自省,余于汉学虽非有根底,然自信能充分玩味之。余于英语之知识当然不可云深厚,然不认为劣于余之汉学知识。既然学力程度相同,而好恶之别如此之异,不能不归于两者之性质有别。换言之,
……
余闭门谢客,将一切文学书收入箱底。既然读文学书不能知文学为何物,唯有相信以血还血之类的手段了。余誓将从心理之方面穷究文学如何之必要,如何发生、发达、颓废。余誓将从社会方面穷究文学如何之必要,如何存在、兴盛、衰败。[14]194-195
夏目漱石在这里反复提及的让他苦思冥想不得其解的“文学”,指的就是literature的日译词“文学”,这与中国传统汉学中的“文学”二字在字形上一样,但所指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汉“文学”非彼英“文学”,这是当时同处汉字圈内的文人们所共同遭遇的问题,也是由翻译引发的问题。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自序中提到的“远赴天涯一隅之伦敦,为此类显而易见之事苦思冥想,也许是留学生之耻。然而事实是事实。”这里的“显而易见”指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而夏目漱石本人对此是怀疑的。林少阳提醒我们注意《文学论》和日本言文一致运动之间的勾连,认为正是19世纪欧洲被特权化的“文学”概念构成了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前提,而夏目漱石的“汉文学概念是对此种“文学”概念和“言文一致”运动蕴含的同一性框架的怀疑和批判。[14]150-151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视角,同时也提醒我们夏目漱石的“汉文学”概念是在遭遇了18世纪英国文学之后才引发出来的,其《文学论》也好,《文学评论》也罢,其中大量引用的例子都是英国文学。对比上文提到的周作人,促成他思考什么才是“文学”的阅读经历,同样来自英国文学(Hunt的《文学概论》中引用最多的也是英国文学的例子)。其实《文学论》出版的时候,周氏兄弟就已经在日本购买并阅读了此书,对夏目漱石的困惑是了然于心的,这在1931年周作人为张我军的《文学论》中译本作序时已有说明:
《文学论》出版时我就买了一册,可是说起来惭愧得很,至今还不曾好好地细读一遍,虽然他的自序读了还记得颇清楚。夏目说明他写此书的目的是要知道文学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他觉得现代的所谓文学与东洋的即以中国古来思想为根据的所谓文学完全不是一样。我平常觉得读文学书好像喝茶,讲文学的原理则是茶的研究。……夏目的文学论后者可以说是茶的化学之类罢。[15]1-2
这是周作人三十年代的论述,把读文学书比作喝茶,周作人的笔调闲适而轻松。但即便是这样,从周作人的回忆中,我们也从未感觉到他初读《文学论》时对夏目漱石的焦虑感同身受。夏目漱石的困惑他了然于心,即便是过了二十多年,也“还记得颇清楚”,但同样面对欧洲现代“文学”进入汉字圈的历史现状,他的心态却相对坦然,这从他在《论文章》中的“姑建此言”四字中就可以看出。但更多的秘密,或许只有将夏目漱石的《文学论》、《文学评论》和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近代欧洲文学史》对照起来阅读,才会有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吧。
[1]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M].赵京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26.
[2]根岸宗一郎.周作人におけるハント、テーヌの受容と文学観の形成[J].日本中国学会報,1997(49):26-32.
[3]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回想录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55,230.
[4]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J].宇宙风,1936(30):56.
[5]周作人.东京的书店[M]//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瓜豆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70,
[6]Theodore W.Hunt.文学概论[M].傅东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78,87,50,60,144-145.
[7]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68-274.
[8]Theodore W.Hunt.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M].Funk Wagnalls Company,1911:24.
[9]乔森纳·卡勒.文学理论[M].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8.
[10]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M].王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34.
[11]夏晓虹.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M]//《文学史》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29-333.
[12]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M]//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16-117.
[13]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余光[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398.
[14]夏目漱石.文学论·自序[M]//林少阳.“文”与日本学术思想:汉字圈1700-1990.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94-195,150-151.
[15]周作人.序[M]//文学论.夏目漱石.张我军,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1-2.
(责任编辑:王 荻)
Reconsider Zhou Zuoren's Transl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CUI Qi
(School of Humanitics and Social Sciences,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eijing 102206,China)
The concept of"literature"which was discussed in the paper"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iterature and its mission and the loss of China's recent discourse"written by Zhou Zuo-ren during his early study in Japan,was translated from Hunt's Literature.Hunt's attempt of constructing the discipline of literature in the higher academic institution correlates closely with strong demand of constructing modern nationality.Zhou Zuoren had his doubts,so the brunt of his argument was directed at the Lin Chuan-jia's statement of"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Zhou Zuo-ren;writings;literature;hunt
I106
A
1008-2603(2017)04-0090-09
2017-05-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互文性视角下的中国现代作家创作与日本文学翻译研究(1898-1927)”(16CZW044)。
崔琦,女,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翻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