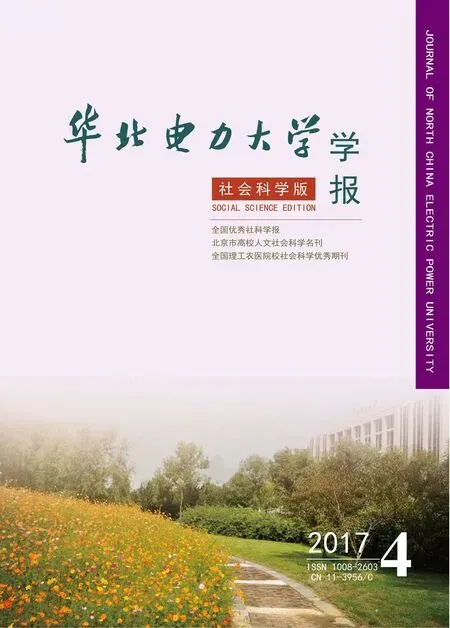受贿罪既遂标准的类型化研究
蔡士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受贿罪既遂标准的类型化研究
蔡士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虽然“客体侵害或者危险说”是目前判定犯罪既遂标准最强有力的学说,但我国对于受贿罪既遂标准的争论却始终没有停歇。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受贿罪侵害的客体存在疑问。“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作为受贿罪客体,既适当的限制了受贿罪的处罚范围,又直观地揭示了权力交换的违法性,因此是其既遂判定的最佳标准。在此新标准下,对于困扰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各种类型的受贿罪既遂也便有了新的答案。申言之,直接受贿中,受贿人收取财物则为既遂;索贿中,索要财物的意思表示予以完整表达,则为既遂;居间受贿中,“收受财物+承诺不正当利益”或“索取财物的意思表示为请托人知悉”,则为既遂。
犯罪客体;犯罪既遂;受贿罪类型
一、问题的提出
与日本等国立法例不同,我国受贿罪只规定了一个“受贿罪”罪名,但具体却存在包括索贿、居间受贿、约定受贿等多种情形。由于许多国家采取将各种受贿情形单独规定罪名,所以既遂标准相对容易确定。目前关于受贿罪的既遂标准问题学界一直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我国学者陈兴良教授主张:无论受贿类型如何,都以收受财物作为既遂标准,[1]此种观点是学界通说。也有学者主张:只要受贿人与行贿人达成了具体的约定,受贿罪就已经成立既遂。[2]另有一部分学者主张:根据贿赂犯罪的的类型,将既遂标准分为两类,其一,索贿罪情况下,完成索贿行为;其二,收贿情况下,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上述关于受贿罪是否既遂的出发点立场都是“构成要件齐备说”,而笔者认为既存的“犯罪客体”说更为合理①目前我国关于犯罪既遂标准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构成要件齐备说”和“犯罪客体侵害或受危险说”。前者是我国通说,认为只要充足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则为犯罪既遂;后者认为根据犯罪客体受到的实际侵害或危险来判定既遂,该说逐渐得到学界支持。,所以希冀以犯罪客体为切入点展开论述。但犯罪客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真正的价值需要通过解释,进而实现被解释对象的具体化。申言之,将受贿罪分为:直接受贿、居间受贿和索贿,在犯罪客体界定的基础上分别讨论各自既遂标准问题。
二、受贿罪犯罪客体(法益)之界定
犯罪客体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同时实践也是检验理论是否合理的最直接方法。目前我国对于受贿罪的既遂标准分歧较大,笔者希冀通过受贿罪犯罪客体的判定机制来打破这一尴尬的局面。但是,运用犯罪客体理论判定既遂标准的前提条件是正确的把握该罪背后的客体(法益)到底是什么?
(一)受贿罪中的法益
对于受贿罪所侵害的法益,国内外理论界众说纷纭。域外刑法一般将受贿罪侵害的法益定位于国家法益。
1.域外关于受贿罪侵害法益的理论现状及评析
在侵害国家法益的各种犯罪行为中,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属于外部侵害,而受贿犯罪被看作是内部侵害,破坏了国家结构的完整性。[3]日本刑法学者大谷实总结认为日本有四种学说:其一,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以及社会对职务的信赖;其二,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其三,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及公正性;其四,公务员的清廉义务。[4]相较之而言,英美法益国家的刑法理论很少触及受贿罪法益的讨论,对受贿罪的危害认识直接和简单。大部分美国学者都是基于“政府应与市场分离,公务行为应与市场经济分离”的原则,将受贿行为视为违反这种“分离”的行为,从确保“自由竞争”的必要性去解释对受贿罪处罚的原因。受贿罪中的公务员实际上是把市场要素注入到了公共领域中去,从而向社会成员提供了一种有害的信息,侵蚀了政府的健康基础。[5]
从现行的受贿罪的客观方面来分析,受贿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并不一定造成消极的影响。而且可能恰恰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政效率,但是该种行为向社会传达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公共权力可以被商品化,而这与契约式社会的初衷是相违背的。申言之,受贿罪破坏了构成社会责任的基础。[6]笔者认为,受贿行为的主体将公共权力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待价而沽,摧毁了建立国家最核心的要素——民意。与此同时,也直接违反了国家、政府、人民赋予的职权。从这一点来看,以“社会大众对于公务员及行为的信赖”作为受贿罪的法益相较之更具有说服力。
2.我国关于受贿罪侵害客体理论的现状及评析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将犯罪客体等同于法益,关于受贿罪所侵害之客体存在简单客体、复杂客体、选择性客体三种学说。(1)简单客体认为,受贿罪侵害的是单一的社会关系,但具体是何种社会关系,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其二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其三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7](2)复杂客体说也有多种不同的组合。其一认为受贿罪既侵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又侵害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8]其二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国家廉政建设制度。[9]其三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和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公正性)以及社会对职务和职务行为的信赖。[10](3)选择性客体。该说认为受贿罪侵害的客体具有多样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等都应该涵盖其中,只要侵害其中任意一客体都应该认定为受贿罪。
复杂客体看似全面,将公私财产与廉洁制度都归结为受贿罪侵害的社会关系,但并不妥当。其一,在通常情形下,受贿罪表现为一种肮脏的“权钱交易”,行贿人心甘情愿地将个人财物交付给受贿人,不存在所谓的侵害公私财产之说。其二,国家机关的工作秩序和廉洁制度是对客体宽泛的定义。因为除了受贿罪,渎职罪同样会造成对该客体的侵害,所以,将其作为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对犯罪的界分功能无法实现。简单客体中的观点之一,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该种规定过于抽象,容易出现上述提及与渎职罪相混淆的情形,而且在现实中,也存在一些受贿人没有违反工作职责的情形,所以该观点有以偏盖全之嫌。观点之二,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作为客体的主张过于强调行贿人的地位,实际上行贿与受贿属于对合犯关系,对于受贿罪而言,应该是职务行为的不可出售性而非收买性。观点之三,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作为受贿客体,该说目前是我国的通说。行为被定性为犯罪,绝不是因为义务的违反,一般是对于权益的损害,[11]笔者认为此种解释是合理的。选择性客体,实际上将受贿罪侵害的社会关系界定为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诚然,受贿罪侵害的客体可能并不单一,但入罪的考量机制是对于行为最主要受侵害社会关系的归纳。换言之,选择性客体对于量刑大有裨益,但无法解决定罪构成要件之难题。
3.笔者的观点及理由
通过以上域内外对于受贿罪侵害法益或客体的评价,不难发现目前观点都存在瑕疵,笔者将受贿罪之法益认定为“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更为妥当。
(1)“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适当的限制了受贿罪的处罚范围。传统观点将受贿罪侵害的法益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按此思路,只要行为人收受了财物,不管是否与职务行为有关联,都应该构成受贿罪。哪怕是正常的社会交往行为也不例外,这难免会扩大法网,限制了国民的行动自由。毋论是在熟人社会的中国,即便是国外法律也允许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礼尚往来,故而不能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道德绑架束缚其行为自由。
相比之下,“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则对行为起到过滤作用,既考虑到正常的社会交往,又巧妙地交往的限度与职务及职务行为关联到一起,可谓恰到好处。
(2)“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直观地揭示了权力交换的违法性。通常情形下受贿人在接受财产性利益后,会表现出对于行为人利益的关切,如果不违反工作规定而满足行贿人之要求,则违法性的根据便会模糊不清。表面上看,该种情形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刑法介入显得多此一举,“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对该种认识予以强有力的回击。一方面,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而言,不能将职务当作商品来予以交换,进而成为个人利益的工具。国家工作人员的宗旨在于服务人民,其报酬来源于民众的税金,所以不应该额外获取各种财产性利益。另一方面,任何人不能为他人的职务及职务行为支付对价。行贿者通过利益与公权力进行交换,虽然有所付出,但就成本与期待的利益相比较,通常是有利可图的。与此同时,行为人明知自己支付交换的是公共权力,与“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相悖,因此也必然具有违法性。
(3)“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比“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更加准确,它表现出对于行贿人和受贿人双方的关切。在我国的刑法思维中,犯罪行为人永远是关注的重点,被害人或者对合犯中的另一方通常被忽视或孤立。“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公共权力被收买的违法性本质,但是它是站在行贿人的角度上去考量的,是一种的单向的。很明显,这种观点忽略了受贿人在正常履职情形下所进行的受贿犯罪。众所周知,行贿与受贿是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所以对其一方客体的界定,都必须要对另一方予以关切。申言之,兼顾买与卖两方才是受贿行为客体的最佳概括,因此,“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是最佳选择。
三、“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在受贿罪中的体现
通过上文的论述,笔者已经论证了将受贿罪的客体(法益)视为“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换言之,“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是判定犯罪既遂的最佳标准。但是,受贿罪作为一种类型化的犯罪,具体可以分为,直接受贿罪、索贿罪和居间受贿罪,而客体在各自的具体表现又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分情况予以讨论。
(一)直接受贿行为中既遂的判定
我国《刑法》第385条第1款规定“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刑法》第385条第2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以受贿罪论处”。这两项规定是索贿类型中最为直接和普遍的情形,探讨直接受贿的既遂标准问题,不能绕开谋利要件的地位,也就是必须要探讨谋利要件是否影响犯罪既遂的问题。
对于谋利要件,虽有主观要件说的观点,但是通说还是将其作为客观要件来看待。即使作为客观要件,但客观要件说的观点也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虽然是直接受贿行为的犯罪构成要件,也即必须存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这不等同于必须实施了相应的实行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可以理解为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特殊行为。实际上,刑法中的故意行为基本上都是沿着一个由准备到着手实行的轨迹运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不例外。[12]此种界定,事实上完全能够把从许诺、准备、实施等谋利行为都涵盖进去,这与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也基本一致。同时反映出我国在腐败治理问题上“从严”的立法意图。有学者认为,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解读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便意味着如果利用职务行为收受财物,但尚未为他人谋利,则仍然属于犯罪未遂。申言之,此时的直接受贿行为成为了复合行为。[13]笔者对于此中观点不敢苟同,直接受贿行为非复合行为,为他人谋利也并非既遂之必备要素。
第一,直接受贿行为并非复合行为。所谓复合行为,是指刑法分则条文中规定的具体犯罪,其构成要件中包含两个以上的行为。申言之,完全充足其中所有的子行为,且行为之间不是一种竞合或重合的关系,而是“互不干涉”的关系,如此才构成犯罪既遂,否则即为未遂。[14]例如我国《刑法》中关于抢劫罪的界定,需要同时满足两个行为要件“采取暴力或胁迫等手段”和“抢取财物”。笔者不否认,在直接受贿行为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法定的客观方面的要件,但它并非是复合行为中的其他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对于行为的性质不会产生丝毫的影响,因为当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时,其已经导致“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的消亡。至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具有为他人谋利的意图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如果认为直接受贿的行为是一种复合行为,也即除了收取财物之外还要为“他人谋取利益”,则索取性受贿罪也是复行为犯。因为,直接受贿行为和受贿行为本质上都是受贿罪,侵害的客体也是相同的,且后者的量刑重于前者。如此比较,索贿行为也应该将“为他人谋取利益”列为犯罪构成要件,而实际上法律却并未做如此规定。因此,直接受贿行为不是复合行为。
第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本身并不会损害到受贿罪的法益。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单纯实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即使谋取的是不正当的利益,也不可能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这一受贿罪的客体,只可能触犯渎职或其他犯罪。真正对于受贿罪法益侵害具有决定意义的行为是收取财物的行为。只有行为人实施了利用职务上便利、收受了他人的财物行为、允诺或者默认以财物与职务进行交换,才真正侵害了直接受贿的法益,构成既遂。
第三,“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表明受贿罪客体所受到的侵害可能来自两个方面,被动受贿(外部)和主动受贿(内部)。具体而言,在直接受贿的情形下,《刑法》条文中规定了两个要素:收受财物和谋取利益(暂不讨论谋取利益的性质),在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时刻,便表明其明知行为的实质是权钱交易。申言之,受贿罪的客体——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被侵害,即便最后没有为他人成功谋取利益。在直接受贿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真正作用在于限制处罚范围,而非犯罪既遂的构成要件。相比较索贿行为,后者的社会危害性更大,所以不需要附加“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构成要件。然而,直接受贿行为中,立法者的意图并不是把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定性为犯罪,而是反对将公共权力作为商品予以交换,所以收受财物是才是重点考量的因素。
第四,在没有其他要件协助判断法益损害程度情形下,从行为人收受财物的客观方面上可以推断其为主观上的“明知”。犯罪的既遂除了违法性的判定,还需要有责性的分析,其中主观上的“明知”不可或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其对于自己的行为需要保持谨慎的态度,收受财物不仅在工作中,在法律层面同样是禁止的。因此,从行为人收受财物举动上,可以推定其具有犯罪的故意。然而,《刑法》中规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无法帮助分析法益的侵害状况,而且对于其性质的争论至今仍未停止,所以摒弃该要素,单纯以收受财物与否作为既遂的标准更为可行。
通过以上论证,笔者认为在直接受贿中应该将收受财物作为判定既遂的标准。
(二)索贿行为中既遂的判定
我国《刑法》第385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以受贿罪论处。索贿行为的主要特征在于,受贿人积极主动地取得财物,行贿人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受贿罪设置的目的,在于使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有章可循,也即不管被动与主动收受财物都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15]索贿罪的既遂标准问题在此处便转化为“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在该罪中的具体体现。笔者认为,国家工作人员索要财物的意思表示完整,既遂形态便予以形成。原因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索取”体现出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权钱交易过程中主动性,使得其对于法益的侵害程度要高于一般的受贿罪,所以不需要收受财物即可构成既遂。索贿行为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公权力所具有的威慑力,迫使行为人给予其财物,它本质上是从体制内部滋生的罪恶,也即“知法犯法”。虽然索贿行为与直接受贿的行为都是对于“职务及职务行为不可交换性”这一客体的侵害,但是前者所体现出的主动性,还间接的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集体荣誉。当受贿人索要财物的意思表示予以完整表达,便表明其愿意进行权钱交易的犯罪目的,对于“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已经造成了彻底的毁损。换言之,这种“不可交换性”在索贿行为中呈现为一种意思表示,而不需要收受财物。
第二,索贿行为纳入受贿罪中,反映出立法者将对于腐败的治理的战线前移,与此对应的法益消亡的时间也随之向前推进。行贿罪与受贿罪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对合犯,国家工作人员主动向他人索取财物,是一种积极侵害国家法益的行为,如果不在法益消亡的时间上较传统受贿罪提前,势必会使索贿行为蔓延开来。行贿与受贿一般是同时出现的,二者的发生概率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具体而言,当社会上行贿的情形增多时,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情形也会增加。但是索贿行为的出现打破了这一规律,如果不积极规制,国家工作人员会在行贿不出现的情况下,独立制造受贿。我国《刑法》第389条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罪”便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当行为人发出索要财物的意思表示时,就应评价为受贿罪的既遂。当然,在这里需要指出一点:意思的表达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默示,只要能为一般的社会人所理解即可。
第三,在犯罪客体的判定机制下,需要正确理解“索取”的含义。对于刑法条文的理解,应该在犯罪客体的语境下进行解读,而不应该机械的将其取义于字面含义。有学者认为“索取”二字的中的“索”不仅有“要”的意思,也有“取”的意思,索取一词究竟是侧重于要还是注重于取,应根据文理和目的作出妥当的解释。[16]笔者认为该种理由值得推敲。其一,从犯罪客体的角度分析,“不可交换性”背后的价值是需要行贿人与受贿人共同坚守的。作为核心人物的国家工作人员,在索要的意思发出,就表示他背弃了信守的职务准则,也摧毁了现存的客体。其二,“索取”一词的含义解读不能违背国民普适性理解。在“索要”一词的理解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误读,国民基本上都将其理解为“一种命令或请求权”。如果脱离了普适性而纯粹地对文字进行咀嚼,势必会使法的解释变得畸形和恣意。其三,索要行为虽然只是单方面提出请求,对方是否提供对价仍有一定的意思自由,但犯罪客体在请求发出之时,已经被摧毁。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这其中的“不可交换性”的主体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当主体发出“索要”的意思表示完整表达出来,便对客体造成了侵害。至于收受财物,可以理解为受贿罪的加重情节,对索贿行为的加重处罚也印证了这一点。
(三)居间受贿中既遂的判定
我国《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罪论处。”居间受贿行为也被称为间接受贿或者斡旋受贿,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工作人员充当着“权利掮客”,但并未直接实施相关的职务行为。为了方便本部分的论述,笔者以“X”代表行贿人,“J”代表居间人受贿人,“S”代表末端受贿人(利用职务便利的国家工作人员)。
关于居间受贿的既遂标准,当前学界认识不一。有论者认为,在居间受贿行为中,只有“X”和“S”,双方最终建立起联系为既遂标准,而不考虑主观期待之目的是否实现。[17]也有论者认为,既遂的标准应该更向前一步,即“X”在“J”的帮助下,完成了对于“S”的行贿方可。然而,在后种观点又可细分为不同的学说:(1)“S”收受贿赂且为“X”谋取不当利益为标准;(2)“S”收受贿赂且为“X”谋取利益为标准;(3)“S”收受贿赂为标准。[18]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对于既遂的要求过于苛刻,而不考虑撮合、转交财物等行为的实质意义,将刑法的领地不适当的向前推进,实践中必然会导致刑罚的泛滥。除此之外,司法机关在证据的收集上也很难予以证明。应该说贿赂实现说的第(1)种学说相对合理,但也存在片面性。居间受贿行为侵害的是法益是“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而该行为又包含了“居间人主动索贿”和“居间人被动受贿”两种类型,所以应该分别以“收受财物+承诺不正当利益”或“索取财物的意思表示为行贿人知悉”作为既遂评价之依据。其理由可以从居间受贿行为的从属性和独立性两个方面来予以论证。
居间受贿行为的从属性主要表现在,居间受贿行为的成立需要“X”与“S”的协助,因为“居间”本质上是一个中间行为。申言之,是否构成居间受贿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贿、行贿的构成与否。然而,这只是居间受贿行为的一个侧面,它也有天然的独立性特质。具体而言,这一犯罪的性质是帮助“X”与“S”实行穿针引线、沟通、撮合。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对于居间受贿行为的既遂标准要求不应该太过于苛刻。“X”与“S”在犯罪的意图上是积极的,只是缺少犯罪目标或者是无法相互之间取得联系,居间受贿人打通了这一通道,使得双方的“权钱交易”得以顺利展开。
第一种情形,居间人被动受贿。该种情况与一般的受贿罪结构上大体相同,唯一区别在于主体是居间人,即存在三方当事人。上文中已经论证,受贿罪的法益为“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但在居间受贿行为中需要阶段分析。有学者指出,所有的受贿罪中,“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非犯罪既遂的判定要素,只需要收取财物即可。[19]笔者不敢苟同。如果单纯以收受财物作为既遂标准,虽然操作简单,但它忽视了居间受贿的从属性。一方面,居间受贿的主体是“居间人”,而居间的含义便是游走于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如果一概以收取财物作为既遂而论,其从属性的地位便无从体现,完全放大了其独立性的特征。换言之,这种做法割裂了居间行为人与行贿受贿之间的关联性,最终呈现的仅是居间人与行贿人之间的一元关系图。而且,收受财物犯罪意图我们无从辨认,可能是正常的人际交往或礼尚往来,也可能是交付于“S”(末端受贿人),自己只是暂为保管。另一方面,单纯的收受财物是无法将其与职务行为关联起来,难以充足基本的受贿罪构成要件,所以认定为既遂显得过于勉强。申言之,将“承诺谋取不正当利益”也作为既遂标准的判定要素,可以进一步强化行为对于法益的损害力度。具体而言,承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说明居间人已经或者即将利用职务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地位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建立联系。也即居间人的地位才真正的形成。所以,“收受财物”和“承诺不正当利益”的共同使用才可以充分证明“职务及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遭受到彻底的毁损。
第二种情形,居间人主动索贿,其类似于上文中讨论的“索贿行为”。对于一般的索贿行为,笔者已经论证了国家工作人员索要财物的意思表示一旦予以完整表达,既遂便形成。然而在间接受贿行为中,由于居间人的存在,容易使得《刑法》第388条规定的受贿人与第385条规定的受贿人混为一谈,所以为了区分二者,有必要将意思表示的主体予以明确化。居间人作为联结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纽带,《刑法》第388条中规定的“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承诺主体是居间人,而非末端的受贿人(“S”)。所以,原本将“索要财物的意思表示予以完整表达”索贿罪的既遂标准,难以在此处适用,需要予以变通。笔者认为居间人自己索取财物的意思为请托人所知悉时作为判定机制最为恰当。它既可以清晰的将居间人的意思表示与受贿人的意思表示区别开来,使行贿人主观上具备犯罪“明知”,也为案件的证据固定与收集降低难度,将其与第385条规定索贿情形界分开来。
[1]陈兴良.受贿罪的未遂与既遂之区分[J].中国审判,2010(2):97-98.
[2]吕天奇.贿赂罪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346.
[3]孙国祥.贿赂犯罪的学说与案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92.
[4]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新版第2版[M].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73-574.
[5]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93-194.
[6]洪浩,夏红.贿赂犯罪本质的嬗变、成因及法律对策——英国反贿赂法律制度改革评述[J].现代法学,1998(3):106-113.
[7]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4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709.
[8]吕继贵.罪与罚——渎职罪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3.
[9]张军.刑法罪名精释: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罪名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第3版[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822.
[10]何承斌.受贿罪客体比较研究[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5):10-12.
[11]邹志宏.斡旋受贿罪研究[M]//于志刚.刑法问题与争鸣.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109.
[12]刘明祥.也谈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24-29.
[13]谢锡美.“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定位思考[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4):40-44.
[14]吴振兴.刑法中的复合行为[J].法学,1992(11):32-33.
[15]邹瑛.受贿罪既遂标准研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4(6):66-71.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出版社,1980:527.
[17]刘光显,张泗汉.贪污贿赂罪的认定与处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410.
[18]赵秉志.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2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345.
[19]郭竹梅.受贿罪新型暨疑难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192.
(责任编辑:李潇雨)
The Research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tandard of Accomplished Crime of Bribes——at the Vision of the Judgement of Criminal Object
CAI Shi-lin
(School of Criminal and Judicial,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00,China)
Although the theory of"object infringed or dangered"is the most powerful theory to determine the standard of crime accomplishment,the debate about the standard of the crime of bribes have never stopped.The main reason is that we have doubt about the object of the crime of bribery."NO exchanging of duty and duty behavior"not only appropriately limits the scope of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bribes,but also reveals the illegality of the power exchange.Under this new standard,there are new answers for the problems that preplexed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ircles long time about the standard of completion of different bribery.In fact,we could go further and say that the standard of completion is accepting benifits in the directed bribery.In the extorting briberys,the standard of completion is conveying their notions of accepting benifits.In the Intermediate bribery,the standard of completion is"accepting benifits and the promise of hunt for illegal benifits"or"the notion of extorting benifits is relized by petitioners".
criminal object;the accomplished of crime;the type of bribes
D924.392
A
1008-2603(2017)04-0043-07
2017-04-25
蔡士林,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