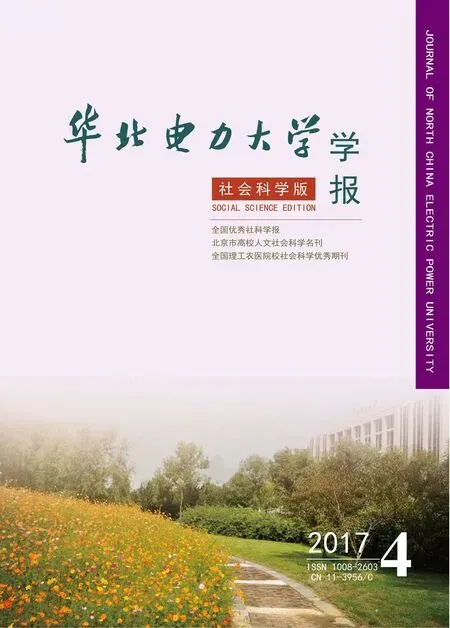生态智慧创新的保护模式与实现路径
杨宇静,曾文革
(1.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 法学院,福建 漳州 363105;2.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45)
生态智慧创新的保护模式与实现路径
杨宇静1,曾文革2
(1.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 法学院,福建 漳州 363105;2.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45)
传统的生态智慧是当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和发展智慧城市所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创新主要采用社会法的“被动保护”和知识产权法的“主动保护”两种模式。然而,这两种保护模式存在权利属性公私有别、主体范围不一致、权利内容形式各异以及权利保障适用的法律不同等方面的冲突。作为现代国家通行的保护创新的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保护生态智慧创新中存在理念功利化,功能不可持续性以及保护机制单一等局限。针对这些局限,文章提出更新理念、重构生态智慧创新的“综合保护”模式,进而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上全面保障、保存和保护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创新。
生态智慧;创新;知识产权;生态化重构
生态文明建设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议题。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决策,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及十八届五中全会首度将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五年规划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史无前例地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使命。发展智慧产业成为我国缓解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1]然而,与此相关的理论和实践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技术化倾向、缺乏完善的生态智慧城市的理论体系、单纯将生态智慧作为投资增长点、未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关联思考及关联研究等。[2]笔者认为,随着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决策和经济形势的日益成熟,准确剖析生态智慧创新的法律保障就显得尤为突出。
作为宝贵的文化资源,生态智慧的保护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一种是生态智慧定格于博物馆的橱窗或散落于坊间的流传,处于“那些由最大多数人所共享的事物,却只能得到最少的关照”的被动保护模式。另一种是生态智慧通过商品化的专利、商标以及著作等知识产权形式再现的主动保护模式。根据“公共地悲剧”理论,“被动保护”模式使得处于公共领域的生态智慧资源被大量闲置,未能充分地发挥时代价值。①“公共地悲剧理论”认为,作为一项资源,公共地拥有许多所有者,而每个人都对这项资源享有使用权,但同时也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这项资源的过度利用。环境破坏便是“公共地悲剧”的典型例子,因为环境的产权难以界定而被竞争性地过度开发和使用。而根据“反公共地悲剧”理论,“主动保护”模式中产权私有化又使得有价值的文化资源不能被自由地获取和使用,进而造成新的资源闲置和浪费。②“反公共地悲剧理论”认为,如果一项资源存在多个权利持有人,每个权利持有人都可能排斥他人使用这项资源,导致这项资源可能无法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造成资源闲置或浪费。知识产权便是“反公共地悲剧”的典型例子,每项专利的持有人都有权排斥他人使用其专利,因为专利权所具有的排他性和独占性可能造成专利技术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这两种生态智慧保护的模式,凸显了处于公有领域的传统知识与私有领域的现代产权之间的紧张关系。笔者认为,如果不厘清生态智慧创新过程中尚未被充分正视的法律问题,就无法准确地理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权利冲突与制度困境,也就无法降低制度的试错成本,难以实现生态文明战略的预期目标。本文的写作旨趣在于从法学视角来探析在建设生态文明和发展新型城镇中保护生态智慧创新的法律模式,并提出相应的实现路径。
一、知识与产权:生态智慧创新中的冲突
(一)权利属性公私之别
从权利来源上看,生态智慧贯穿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与科学理论、文学经典一样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种天然的、不需要经过法律确认便已存在的文明遗产。而生态智慧创新很大程度上是将传统生态智慧资源按照现代知识产权规则转变为法律拟制的产权。从权利属性上看,生态智慧是一种公共资源,某人享用生态智慧得到的收益并不会减少其他人运用这一资源所得到的收益,即生态智慧的使用并不具有排他性。日本《景观法》第二条指出:“良好的景观是国民共通之资产,应予妥善整备与保全,使现在及将来之国民均能享受其恩泽”。“共通之资产”说明良好景观作为一种公共环境资源为公众及后代人所共同享有。而生态智慧创新所带来的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私权,具有明确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内容。我国《专利法》第26条确立了“遗传资源的可专利性”,并在程序上要求专利申请人在专利申请文件中说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这一条文反映出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传统资源在符合创新标准(创造性、新颖性和实用性)且不违反禁止性法律的前提下可以获得具有排他属性的专利权。生态智慧强调生物与文化的多样性、整体性与和谐性[3],而知识产权强调权利的排他性、个体性以及封闭性,使得在处理生态智慧创新时要考虑到这一特殊性,并不宜与其他普遍的智力创作等量齐观。
(二)权利主体范围不一致
从权利主体上看,生态智慧的地域性、民族性体现为生态智慧是特定区域人群的集体财富,其主体为不特定的多数人,甚至是几代人。相比之下,生态智慧的时代性和普适性体现为生态智慧创新的主体是特定的少数人,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加以确认。主体范围不一致往往容易引发权利冲突。海外典型的案例是美国制药企业从印度部落的传统知识中获取关键信息并就此申请药品专利以及澳洲企业将土著传统图腾申请为注册商标等。而近年来,中国传统中医药资源不断受到“生物盗版”的侵害,也凸显了生态智慧与生态智慧创新主体的不统一。
(三)权利内容形式各异
生态智慧的本质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思想。[3]而生态智慧创新是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知识转化为具有创造性智力成果的活动。生态智慧多表现为传统知识和传统技艺,例如: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蒙古族传统刺绣的色彩构成方法、石柱土家族的黄连种植技术等;而生态智慧创新多表现为新技术、新作品、新产品,例如生态建筑营造技艺的专利、生态智慧的理论著作、环境艺术设计作品、生态旅游的商业标签、农产品地理标志等。
(四)权利保障适用的法律不同
生态智慧所体现的传统原真性与生态智慧创新所要求的创造性之间存在知识的社会性与个体性之间的矛盾。生态智慧的管理和保存主要通过《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城乡规划法》等社会法。而生态智慧创新大多通过《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来进行激励和保护。社会法侧重于从社会整体层面对生态智慧进行管理和保障,一般不受市场的驱动和经济利益的影响。而知识产权法侧重于从个体私权层面对生态智慧创新所带来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加以确认,为追求市场利润和经济利益配置权利保障。
二、传统与现代:生态智慧与创新保护
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催生了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法律通过赋予创造性智力成果排他性、垄断性效力以激励创新。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成为国际社会共通的制度选择。生态智慧创新也沿用这样的规则和进路。然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典型的私权,在对生态智慧创新进行保护的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知识产权制度目标的功利化倾向
从全球范围来看,知识产权是近几百年来现代工业革命的制度产物。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体系中,知识产权膨胀和扩张的趋势让立法宗旨出现了南辕北辙的效果。[4]一方面,特定社群的共有生态智慧资源在知识产权规则下转而成为少数人合法的私有财产。大量传统资源被“盗版”或“翻译”成专利技术或商业标记,再以“知识圈地”的形式作为私有资本进入市场以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正如西方学者所批评的“智慧城市的发展更多的是出于市场竞争的企业需要,较少出于城市自身社会智能的需要”。[5]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促进创新”的立法目标不断地受到质疑。有学者感慨,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不在于保护稀缺资源或者促进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而在于精心设计一种制造稀缺资源的制度。[6]知识产权缺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理念,使得其无法有效地回应当前人类所普遍面临的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等世界性问题,从长远来看,对于鼓励生态智慧的创新和传播并无裨益。
就中国而言,从缺少知识财产的概念到被动接受舶来的知识产权制度再到主动确立知识产权国家战略,可见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选择正在经历急速的变革。然而,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专利申请、商标申请的第一大国,但知识产权制度所应具有的传播知识、鼓励创新和促进技术进步等功能并未真正获得充分的发挥。相反的情况是,大批质量不高的知识产权充斥,不但未能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反而成为社会整体创新的桎梏。在生态环境工具论的驱动下,“生态智慧创新”成为企业赢得市场竞争和获得高额利润的卖点,而非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以绿色专利快速审查为例,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设置了绿色专利快速审查机制,给予绿色技术加速审查或优先审查的特殊待遇。但有学者认为,这一制度创新尽管在推动绿色技术公共政策上具有积极的效应,但是从法律正当性角度来看,其显然存在损害专利制度宗旨、理念与功能的危险。[7]从社会长期和整体的发展上看,过于功利化的知识产权布局对于生态智慧的传承和创新可能是成本高昂的,甚至是危险的。
(二)知识产权制度功能的非生态化设计
工业革命以来,各种缺乏整体观和联系观的“技术快餐”并不缺乏创新性但对资源的破坏性开发却把地球推向面临生态危机的境地。“反公共地悲剧”理论已经向我们发出警示。知识一旦私有化便不能很好地为社会公众所获取和使用,权利人为了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甚至可以闲置创新的知识产权以换取市场资源的稀缺性。以生态智慧城市建设为例,凭借知识产权制度的“独占性”、“垄断性”等特点来销售生态智慧创新似乎成为生态智慧城市所必经的一个阶段,尽管目前许多智慧城市遭遇“非智慧性”和“非生态性”的诸多质疑。有些生态智慧城市的建设只是将冠以“先进专利技术”、“生态标签”后的生态智慧作为拉动投资的“卖点”或者是“装饰物”,并非真正地为了推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可能导致那些产权化后的生态智慧创新成果不能发挥应有的社会功效和环境功效。实现生态文明和建设生态智慧城市要求将信息和知识最大化地转化成智力资源,同时使转化过程中消耗的物质、能源、资源最小化。而知识产权制度以经济激励为主的功能更多关注的是权利的确认或侵权的救济。生态智慧产权化后的授权许可甚至侵权诉讼等不仅不利于生态智慧的传播和应用,甚至可能抬高建设生态文明和生态城市的交易成本。
(三)知识产权保护的单一化机制
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一项社会契约和公共政策,除了保护产权人的利益外,还要权衡知识产品的使用者、竞争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除了保护产权,鼓励创新、传播知识、促进社会进步同样需要制度配置相应的保障机制。然而,知识产权扩张在全球盛行,扩大保护范围以及延长保护期限成为各国的普遍做法。[8]《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将知识产权的客体从传统的专利、作品和商标延伸到地理标志、工业设计、集成线路布图设计、未披露信息等。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也不断地延长。以美国版权为例,其保护期限已延长至作者寿命及死后70年。这就意味着被产权保护的作品将在经历“百年孤独”之后才能进入知识的共有领域。反观对其他利益主体的保障,却发现知识产权制度的贡献十分有限。例如,为了应对公共健康危机所设立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机制在实践中鲜能发挥作用。以我国为例,虽然《专利法》中规定了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措施,但到目前为止仍无一例适用这一机制的相关记录。[9]
在知识产权单一化的保障机制中,生态智慧创新更多局限于确认产权和保护财产而忽视知识分享、信息传播以及文化传承等社会化功能。以新兴的合成生物技术为例,社会各界已经开始争论生物合成技术是否可以申请专利、如何界定生物合成专利的保护范围、这些新技术如何保障公众利益以及确保代际间、人际间的公平公正。这些讨论一方面是对现代知识产权制度过于关注财产保护的警惕,另一方面是对知识产权制度缺少社会伦理关照的担忧。而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生态智慧创新通过一系列环境友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得以体现。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因为这些是发达国家的专利技术而无法自由获得和免费使用。知识产权议题成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是否推动清洁技术转移的一个争议焦点。知识产权制度缺少弹性的技术转移机制是目前国际气候谈判陷入僵局的一个主要瓶颈。[10]
三、模式与路径:生态智慧创新的思辨
(一)生态智慧创新保护模式的新理念
恰当的理念定位是构建生态智慧创新保护的首要问题。生态智慧创新是“启蒙反思”的过程。[11]而文化环境主义的兴起正是对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理念的反思。[12]文化环境主义以环境保护运动来类比寻求知识公共领域的保护。虽然管理环境资源与管理知识资源从表面上看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两者都存在共有领域与私有权利之间的矛盾冲突。环境领域中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对环境的污染破坏引起了“公共地悲剧”。在知识领域,由于产权制度“圈走”了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知识,而导致这些知识无法被公众获取和利用。一项科技产品可能由许多专利技术来共同完成,而每个专利技术的持有人基于各种原因(比如价格、限制竞争等)有权排斥他人使用自己的专利,进而造成知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以及社会制度的高成本等公共问题。这不仅是知识产权法制的危机,也将成为文化危机。[13]
类似于环境保护运动,知识产权领域也发起了维护知识公共领域的运动,反对知识私有化对社会进步和公共利益带来的危害。生态智慧创新在当下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具有不可估量的时代价值,因此要从理念上更新创新保护模式,辩证地看待知识产权扩张对传统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利用可能带来的限制。生态智慧创新的保护理念除了重视产权确认外,还在于更好地推广和应用这些智慧资源,进而反哺社会公众,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二)生态智慧创新保护模式的重构
生态化重构是生态智慧创新保护模式的重要内容。生态危机的出现使得知识产权与生态智慧两个互为独立的体系发生了耦合,而知识产权制度的生态化重构是知识产权制度回应生态文明的一种制度选择。[14]正如环境学者所呼吁的,人类不应当站在自然的对立面,而应当在促进自然完整、健康和繁荣的同时来实现自己的发展。[15]知识产权学者也发出类似的呼吁,知识产权不应当只是对抗世界的权利,而应当是服务于世界的责任。[16]知识财产作为法律假定在某些抽象物上的权利,应当更加注意限制这些权利以防止私权膨胀,并且制度设计应当更加注重公益。[17]事实上,生态智慧是动态发展的智力成果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传承与创新交叉重叠,两者互为因果和手段。即便是WIPO和WTO也仍然将划定传统知识与知识产权的界限视为难题。[18]当法律面临这样的尴尬时,将处于共公领域的生态智慧转变为私有财产的过程,应当警惕非理性的权利扩张和膨胀,谨慎和严格地评定智力成果的“创造性”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可持续地维护公共利益甚至是未来后代人获取传统知识资源的整体利益。
以免费文化、自由软件、开放设计、生态专利池为代表的一系列“知识共享”行动呼吁建立信息的生态环境,捍卫知识的公共领域,改善知识产权对创新和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害。以世界前沿的合成生物技术为例,科学家们通过“知识共享”而不是知识产权来推进合成生物学研究成果的传播。2003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成立了标准生物部件登记处,收集了大约3200个标准生物学部件以供全世界科学家自由获取和在此基础上组装更具有复杂功能的生物系统。[19]从生态智慧创新的角度看,“知识共享”模式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而借鉴环境保护运动的知识产权新思路更加关涉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与生态智慧强调的参与主体多元和惠益分享相互契合。
(三)生态智慧创新的综合保护路径
富有弹性的制度设计是实现生态智慧创新保护的根本保障。随着中国生态文明与知识经济从政策的主观选择走向法治的客观必然,关于生态智慧创新,中国的法治应当做出适时的准备和清晰的回应。尽管从世界范围看,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是制度选择的必然结果,但这种选择不能脱离中国具体的国情而僵化地移植或翻版。中国丰富的生态智慧资源有待于从多元的综合路径来实现创新保护。
1.宏观层面:科技法的推广与普及
中国已形成了包括《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普及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一系列完整的科技综合立法体系。这一体系中的立法不是仅对科技活动制定单行法,而是将科技活动所涉及的社会关系作为整体加以综合立法,不仅加强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而且注重从宏观上确保国家对科技事业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注重促进科技成果的迅速转化,注重遏制科学技术对社会负效应的发生。从宏观和长远的发展上看,生态智慧的创新需要从宏观层面上加以整体管理、引导、推广、普及、保存等,才能健康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功能。
另外一项重要的宏观制度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全球对生态景观和智慧城市的需求使得创新前沿更加集中到设计理念以及建造技术上。知识产权所具有的经济激励功能,必将催化生态智慧转化为以专利技术、商业标识、建筑著作权等形式的知识产权。反不正当竞争要求对市场上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限制,规范借生态智慧之名,“刷绿”标榜文明、招揽商机、挤兑竞争者的行为,进而从宏观上保障生态智慧创新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中观层面:社会法的保障
公众参与和集体行动是社会法的重要内容,而社会法强调整体的利益以及利益之间的有机平衡。以社会法来保障生态智慧创新是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整体进步的高度来进行规制的。社会法通过“保全”、“保存”传统知识的原真性等方式来传承和传播生态智慧。《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更侧重整体社会效益的制度保障能够最大限度纠正以非理性方式开发利用生态智慧的行为,并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传承和传播这一集体的资源。与知识产权付费使用的机制不同的是,社会法往往通过援助、合作等形式实现对确定社区、团体或个人的帮助,以鼓励技艺的传承和传播。虽然二者在汉语中都使用“保护”一词,但一个是收钱,另一个却是给钱,其内在机制显然是南辕北辙。[20]社会法所积极提倡的公众参与机制正好与生态智慧广泛的民族性、社会性相互契合。
3.微观层面:知识产权法的保护
知识产权法通过明晰产权来保护生态智慧创新。这从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创造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充分尊重和保证创造者的智力成果是推动和延续整体文明进步的基础。然而,就像环境保护问题,中国不应该重蹈西方先破坏后保护的发展模式;相同地,在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问题上,中国也要前瞻性地看到西方知识产权非理性扩张所带来的局限性。与此同时,中国具有大量处于知识公共领域的生态智慧资源,在强调知识创新和产学研融合的大政策背景下,谨慎平衡知识产权制度实践中公共利益与私有权利之间的关系将具有十分重要和长远的意义。这既是对私权的合理保护,也是知识最终回归社会公众的一种契约精神。
四、结语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创造了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这些丰厚的传统资源和文化遗产为我们治理国家、建设家园、修身养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而中国快速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又为生态智慧的创造和利用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生态智慧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有助于人们理解社会发展与环境危机之间的矛盾,有助于启发人们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然而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生态智慧能够为公众所自由获取和使用;而生态智慧创新则更多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产权化后的生态智慧创新便无法被公众自由获取和免费使用。
尽管知识产权制度能够通过财产保护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生态智慧资源的再创造。但必须警惕知识产权私权对公共资源的圈地威胁和权利滥用。在保护理念和保护模式上,生态智慧同样启示着知识产权制度进行生态化重构,引入“知识共享”的创新理念,除了微观的知识产权保护外,宏观层面的科技法普及以及中观层面的社会法保障等也是我国生态智慧创新所不可忽视的制度配置。
[1]刘远彬,丁中海,孙平等.两型社会建设与智慧产业发展研究[J].生态经济,2012(11):133-135.
[2]沈清基.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基本理论探讨[J].城市规划学刊,2013(5):14-22.
[3]魏连.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主旨探究[J].生态经济,2014(8):141-144.
[4]冯晓青.知识产权法的公共领域理论[J].知识产权,2007(3):3-11.
[5]Deakin M.AL W H.From Intelligent to Smart Cities[J].Intelligent Buildings International,2011(3).
[6]曹新明.知识产权法哲学理论反思以重构知识产权制度为视角[J].电子知识产权,2005(2):56-60.
[7]曹炜.绿色专利快速审查制度的正当性研究[J].法学评论,2016(1):133-140.
[8]Graeme B.Dinwoodie,Rochelle C.Dreyfuss.A Neofederalist Vision of TRIPS:The Resili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m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189-204.
[9]王海洋.我国专利强制许可零实施的原因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9(9):344-345.
[10]杨宇静.论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专利权困境及其制度创新[J].中国环境法学评论,2015:52-64.
[11]程相占,杜维明.环境感知、生态智慧与儒学创新[J].学术月刊,2008(1):22-30.
[12]James Boyle.Cultural Environmentalism and Beyond[J].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2007:5-22.
[13]James Boyle.The Second Enclosure M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J].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2003(6):33.
[14]万志前,郑友德.知识产权制度生态化重构初探[J].法学评论,2010(1):44-52.
[15]佘正荣.生态智慧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73-175.
[16]Robert P.Merges.Justify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289-311.
[17]Peter Drahos.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1996.
[18]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政府间委员会.保护传统知识差距分析草案[EB/OL].http://www.wipo.int/edocs/mdocs/tk/zh/wipo_grtkf_ic_13/wipo_grtkf_ic_13_5_b_rev.pdf.
[19]黄辛.有关院士和专家呼吁——加强我国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力度[N].科学时报,2009-12-22(A2).
[20]郭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模式的质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28-33.
(责任编辑:李潇雨)
Protection Mode and Realization Paths of Ecological Wisdom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YANG Yu-jing1,ZENG Wen-ge2
(1.Tan Kah Kee College of Xiamen University,Zhangzhou 363105,China;2.Faculty of Law,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5,China)
T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is an essentially important resour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wisdom cities.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wisdom are passively conserved by social law and actively protected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se two modes of protections include the different attributes of public-private rights,non-uniformity of subjects,inconsistence of objects and different applic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According to the limitations of utilitarian tendency of legal values,non-ecological and non-wisdom contents and simplified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mode,the comprehensive mode is suggested to secure,conserve and protect ecological wisdom from macro level of technology law to promote technology transfer of innovative outcomes,from meso level of social law to secure public interests and from micro lev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to protect individual rights.
ecological wisdom;innovation;intellectual property;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G124;F592.7
A
1008-2603(2017)04-0037-06
2017-05-11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研究”(15JZD05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重庆大学重大项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农业贸易法律问题研究”(0226005201021)。
杨宇静,女,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能源法、环境法;曾文革,男,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环境法、国际经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