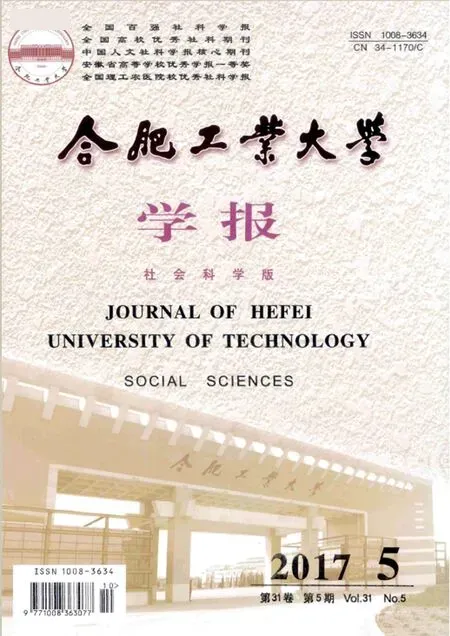中国式孤独
——评刘震云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李 璇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039)
中国式孤独
——评刘震云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李 璇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039)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描写了中国人的“说”的缺失,解构了传统伦理道德。文章认为,小说呈现出了现实世界的荒诞以及在这个荒诞世界中个人的孤独。为了摆脱孤独感,每个人都在寻找消解孤独的方式,但结果总是不尽人意。刘震云采用存在主义关于孤独的言说结合中国式的意境描述了独特的中国式孤独故事。
传统伦理道德;荒诞;孤独;孤独消解方式;存在主义;意境
一、引 言
刘震云作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双重影响下的作家,他的作品一贯关注平民小人物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态度,采用简单易懂的平民化语言,从日常生活的琐细事物中挖掘出平民的精神世界。
“小说的精神是延续性。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1]《一句顶一万句》延续刘震云以往对精神世界探寻的努力,对平民的沟通问题做了再次的深入探讨。作品中的所有人都是孤独的,他们不断地找寻与自己能说得着的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给《一句顶一万句》的评语是:《一句顶一万句》建立了极尽繁复又至为简约的叙述形式。通过塑造两个以“出走”和“还乡”为人生历程与命运逻辑的人物,形成了深具文化和哲学寓意的对称性结构,在行走者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缘起缘尽中,对中国人的精神境遇做了精湛的分析。刘震云传承了‘五四’的文化反思精神,同时回应着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在想着中国之心和中国风格的不懈探索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原创性成就。”[2]
张颐武认为,“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近期传统文学领域的重要收获,也是当下最有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不多见的力作。”[3]“一句顶一万句”原是“文革”期间林彪评价毛泽东的话,刘震云把它作为小说题目并不是缅怀历史,而是为了强调与能说得着的人说的每句话的分量,能让两个人成为说得着的人的那句话的重要性,最终强调的还是摆脱孤独感的重要性。刘震云本人在谈及《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说:“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人多的孤单。”[4]《一句顶一万句》关注的是人的存在问题,讲述在荒诞的现实中平民的孤独。
二、孤独的情感与荒诞的氛围
刘震云一贯关注人的难以言说的孤独感,他的笔下有众多的孤独人物:《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手机》中的严守一,《我叫刘跃进》中的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及牛爱国,等等。作者对孤独感的感知与描写一直没有停歇。刘震云认为,最大的孤独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存在于芸芸众生劳动大众中,他笔下的孤独是中国式的孤独。“我觉得《一句顶一万句》是全面、系统、特别深入地挖掘这种孤独”[5],他这样说自己的作品。
存在主义是20世纪在西方影响最广泛的哲学思潮之一,其强调以人为中心,对研究“人的存在”问题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成就。新时期以来,西方思潮广泛影响我国,存在主义在中国文坛曾引起过广泛的热潮,产生了一批关注“人的存在”问题的作家,刘震云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存在主义将人的孤独与生存的虚无联系在一起,认为正是因为世界的荒诞、生存的虚无,人才会感到孤独。 刘震云的作品与这一观点相契合。他的作品普遍地反映了平民对“说”的畸形渴望的荒诞现实状况。“在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度里,我们只能向知心朋友透露我们的心声。”[6]在有宗教信仰的社会,人们只要找自己所信奉的神就可以倾诉自己的心声,但在中国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人们要倾诉只能找自己的朋友。但自己信奉的神和朋友的区别是,神会为你保守你的话语,而朋友也许会把你说的话告诉别人,因此中国式的孤独是无人诉说的孤独。所以在中国,“说”显得尤为重要。《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背景是刘震云的家乡延津,小说中有个很重要的延津方言词语:“喷空”,据刘震云自己解释说:“就是有影的事,没影的事,一个人无意中提起一个话头,另一个人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搭起来。”[7]由此可见,“喷空”就是有没有根据的事情都可以说,反正怎样说都行,由这件事说到那件事,由这个人说到那个人,就是为了说而说,没有实质性意义或价值。可笑的是这种无意义的“说”在作品中受到杨百利为首的一些人的疯狂喜爱,并且凭借“喷空”,杨百利找到了营生,这反映了荒诞的现实和荒诞的个人。但是存在主义所说的生存的荒诞并不仅仅指世界的荒诞或者人的荒诞,而是强调两者之间的关系,面对荒诞的外在世界,很多人都是选择融入而成为了荒诞的个人。杨百顺和牛爱国为了外人的眼光而去假找自己的妻子就是对荒诞世界的妥协,夫妻之间本没有实质性的感情,却为了形式上的面子去假找。此外,作品中杨百顺和牛爱国等人与自己的妻子说不到一起去,没有话说,杨百顺父子说不到一起,师徒说不到一起,等等。都展现了平民世界由于缺少合适的说话对象而导致“说”的缺乏,因为缺乏才会渴望,也为对“说”的畸形渴望埋下了伏笔。
“说”的极度缺乏与渴望使作品中的人物为了找寻到能与自己说得上话的人不惜背叛中国传统伦理,使人产生了生存的虚无感。传统的伦理道德是维系平民之间关系的重要依据,根据传统伦理道德建构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从属于一个群体,有归属感,不再是孤单的个体,但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一一解构了这些伦理关系。首先是亲情。老杨让儿子去上学,不是为了儿子的前途,而是为了自己的豆腐铺,在纠结是让杨百顺还是杨百利去上学时,他采用作弊的行为挑选了对自己豆腐铺有利的儿子去上——传统的亲情伦理被颠覆,亲情显得苍白无力。在师徒关系上,刘震云也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师徒关系,杨百顺拜老曾为师父学习杀猪,杨百顺与新师母太过计较物质利益,所以,因为杀猪后的分配不均,杨百顺与老曾之间产生隔膜,杨百顺在顾客家里发泄不满,一句话传过许多人的耳朵就变了原本的意味,老曾听闻后将杨百顺逐出师门。在颠覆了亲情和师徒之情后,作者又颠覆了夫妻之情,杨百顺与吴香香婚后生活并不幸福,他俩说不到一起去,而且妻子暗中与老高来往,甚至在事情败露后与老高一起私奔。更为讽刺的是,在吴香香私奔后,杨百顺出走去找吴香香仅仅是因为面子问题,是出于世俗的压力,而不是真心去找。理想中的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的夫妻关系也被解构了。传统友情的伦理解构在作品中体现得最多。古人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本意是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老汪却泪眼汪汪地解释道这是说自己周围没有朋友,所以才会这么珍重远道而来的朋友。下部中的老韩和老丁多年的朋友因为意外得来的不义之财翻脸,牛爱国的朋友冯文修、杜青海、陈圭一、崔志远等人也都相继离开,没有尽到朋友的责任。总的一句话,这部作品颠覆了传统伦理中的亲情、师徒情、夫妻情、友情。作者把人所依托的传统伦理关系一一否定,使人们对自己生存的世界产生虚无感,一切都不可靠,每个人都成为了这个世界上孤独的个体,很难找到自己能说得上话的人。这又构成了人们对“说”畸形渴望,就这样,人们越孤独便越想找个说得上话的人,因而不惜背叛伦理。越多的人背叛伦理,人们就越觉得一切都不可靠,越会觉得孤独,最终形成了一个因果循环。
无论是对“说”的畸形渴望,还是对传统伦理的一一解构,刘震云都给我们营造了一种荒诞的氛围,荒诞的世界总与孤独的情感联系在一起,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无人诉说、无人了解,为了融入这个荒诞的世界而不得不做出荒诞的事情,为了表面的融入而掩藏内心的抗拒,没人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内心,也没人愿意去了解。这样,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孤独个体,如同存在主义者给我们揭示的世界真相那般,人生来注定是孤立无援的。为了摆脱或者说是缓解自己内心的孤独感,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如同作品中的人物一样不断寻求孤独消解方式。
三、孤独的情感与孤独的消解方式
萨特提倡的人的自由是绝对性的,因为人生来是孤立无援的,只能通过自由选择来承担自己命运的重担。就是说人可以自己选择生存的方式来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像作品中荒诞的现实与孤独的个人是类似的,但是每个人追寻孤独消解的方式是不同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一句顶一万句》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是杨百顺的“出延津记”,下半部是牛爱国的“回延津记”,在他们这一出一回的结构中,牵扯出许多也处于孤独并找寻孤独消解方式的人,作品中每个人都有追求,但结果不同。比如作品上半部分主人公杨百顺一直在找寻能与自己说得上话的人来摆脱自己的孤独,但是,好不容易找到了巧玲,却不慎丢失;以为老高是自己的知己,却遭老高“背叛”。令他欣慰的是,在晚年他找到了能理解自己的孙子。吴香香和老高彼此一起摆脱了孤独感,但在延津留下奸夫淫妇的罪名;庞丽娜与吴香香类似。作品中更多地是找寻未果的,她们的孤独消解方式也不尽相同。曹青娥小时候失去了杨百顺,长大后再次寻到侯宝山,已不再是当初那个人,老年时候看似与孙女百慧说得着,其实不然!曹青娥最后的一个用手指的动作,没人真正地理解,她是找寻未果后在现实中将就着的。章楚红和牛爱国都是在得知彼此不能在一起后无奈而绝望地离开的。有的人通过找寻找到了能消解孤独的人,但更多的人是没有找到。寻找这样一个能消解自己孤独的人很难,就算找到了的,也是终其一生或者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也有找到了又失去的,因为在两个人和生活三者之间,有一者发生变化,关系也会变化。杨百顺、牛爱国等人一直在找寻中,其实是人们的精神都在流浪中,寻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
找寻未果在作品中最多,找寻成功的在作品中寥寥无几,而且人们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者给我们呈现当下的社会现实——每个人的孤独,找寻一个能与自己说得上话的人的艰难。这是一种存在主义视角下对中国平民精神现状的观察书写。正如萨特所认为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城堡。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人从根本上是与世隔绝的,所以注定无法相互了解。刘震云对中国平民精神世界的看法与存在主义对人类的想法有类似的地方。存在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思想,其中,“处境意识与生存意识是最鲜明的,也是存在主义的起点。”[8]刘震云的作品始终关注着中国平民的现实处境和生存状态,他擅长从对荒诞的现实描写中凸显精神世界的孤独。在传统文化熏陶与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双重影响下,他看到了中国平民荒诞的处境和孤独的生存状态。《手机》是刘震云看到了现代工具的进步不仅没有拉近人们的距离,反而使人们之间更加疏远,作者开始关注到人们的沟通问题;到后来的《一腔废话》,他感到人们说的话缺乏实质性的意义,说话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内心交流,是人们之间沟通的疲惫与隔阂。
萨特曾说,“他人是地狱!”[9]他认为这句话包含三层意思:首先,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他人,那么他们便是你的地狱;其次,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他人对你的判断,那么他人对你的判断便是你的地狱;最后,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自己,那么你也是自己的地狱。作品中的人物没有意识到“他人是地狱”,他们把自己内心孤独的消解方式只寄托于外在的找寻,希望在与别人的相知中得到解脱,没有正确对待他人。其次,他们也没有正确对待别人对自己的判断,杨百顺和牛爱国去寻找自己的妻子都是因为别人的看法。作品中的人物对外在的过度执着导致他们陷入更虚无的困境,更没办法摆脱自己内心的孤独。孤独可分为外在孤独和内在孤独,外在孤独是人际交往的匮乏导致的表象孤独,内在孤独是精神的孤独,是真正的孤独。在中国古代,外在孤独的人物不少,屈原在《渔父》中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10]。庄子《逍遥游》中大鹏独自展翅翱翔在天空也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孤独,等等。他们都是看起来孤独,却是内心充足、没有为孤独感到忧伤的人。他们虽然都是独自一人,但屈原是以一种傲世独立的姿态藐视众人,庄子独自逍遥于天空中感到的是自由豁达,他们注重的是自己内心的建设,当内心强大了,自然不容易受外在的影响。而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人物只在外在找寻消解孤独的方式,却忽视了自己内在的建设。
四、孤独的情感或及其中国特色
刘震云作为农民的后代,农村的生活形成了其基本的生活观念,导致他自然会以强烈的平民意识对社会进行丈量,对社会中的小人物抱有深切的认同和理解。“在创作作品时同他们站在同一个台阶上,用同样的心理进行创作。”[11]刘震云始终关注着社会平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他小说中的人物都与他自己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他出生在农村,所以对《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人物和心理十分熟悉。但他没有止于对人物进行表面的描述,而是用西方存在主义的观点讲述了中国农民的生存处境与精神状态。 他先是讲述了人的中国式的荒诞处境。平民面对的首先是对“说”的畸形追求,“喷空”也成为了一种爱好,为了“说”每天奔波;为了找到能与自己说得着的人,背叛传统伦理。其次是“形式与内容的脱节”。杨百顺离开延津和牛爱国回到延津的由头都是出于面子和世俗外在的压力去找寻自己的妻子,而且都是假找,只存在于一种形式,这显得尤为荒诞。而这都是典型的中国人的生存困顿。荒诞的生存状况下隐藏的是无人诉说的孤独感。刘震云发现了这一点。正如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曾指出的,作为“存在”的人面对的是虚无和孤独无依并永远陷于烦恼痛苦之中*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虚无》等书对于“存在”的阐释。。孤独是人们普遍的精神问题,而刘震云笔下的孤独则是中国式的孤独。
刘震云从《塔铺》《新兵连》开始,就注重表现群体心理定势而不重视刻画个体性情。为了体现群体像,作者对作品中的人物刻画往往是以姓代名,很少有正式的名字,而且“描写的重点在于人们彼此相近的共性而非迥异的个性上”[12],《一句顶一万句》依旧延续了群体性描写的手法,刘震云在访谈中说到,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所有的人物、所有的孤独和所有的精神流浪就发生在自己的亲人身上。他所讲述的荒诞是农村社会的常态,他所表现的孤独是适用于每个平民的孤独。孤独作为一个文学母题,历来多有文学家描写,但极少有人描写到平民的孤独,孤独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似乎是知识分子才可以有的,平民一直被视为麻木的人群,沉默的大多数。这部作品描写的孤独具有广泛的意义,发现了平民的孤独,将对孤独的描写拓展到平民阶层,为文学开启了一个新的层面。
刘震云的孤独描写与西方存在主义对孤独的阐释有一定的相通之处,都表现了对人类存在困境的探索,但是他作品中的民族因素使得作品有不一样的风采。伟大的作家总会从自己的民族文化中找到切入点,从而进入世界文化潮流。刘震云以存在主义哲学的为视角描写了中国平民的孤独,作品中运用了传统白描的手法,营造原生态的意境。意境是我国古代独创的一个概念,童庆炳认为:“意境是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相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13]童庆炳对意境的定义还仅限于抒情性作品,叙事性作品中也有意境的营造。《一句顶一万句》就是如此。刘震云在作品中营造的是混沌的原生态氛围,混沌一般是指宇宙之初“物质某种原始的没有分化的状态”[14],就是整体感、原始感。中国古代审美重整体、重直观感觉、重意蕴,追求“天人合一”浑然一体的境界。这篇作品中生活流式的叙述方式,使作品整体呈现出一种混沌之感,这种混沌之感不仅给作品增加了古典小说的意蕴,类似于白话小说的平白叙事,还与作品中的个人形成了对比,环境的整体性与个人的孤单性相比照,更显个人的孤独。
五、结 语
刘震云始终坚持着关注平民的创作原则,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采用西方存在主义哲学观点探寻着中华民族平民内在的精神状况,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开启了发掘平民精神孤独的视角。另外,刘震云观察平民世界的角度并不是鲁迅式的俯视,而是平视。他用冷静的笔触书写平民的日常生活,在其中渗透着他对平民精神世界的思考,这些思考与存在主义哲学有相通之处,所以通过存在主义哲学视角来看《一句顶一万句》,可以能够透彻地感悟文本的文化内涵。刘震云的小说流露出对底层人民的人文关怀,从而引导我们对当下底层中国人的处境和生存状态进行思考。
[1]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25.
[2] 中国作家网.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授奖词[N].(2011-09-20)[2017-04-10].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1/2011-09-20/102619.html.
[3] 张颐武.书写生命和言语中的中国梦[J].文艺争鸣,2009(8): 47-48.
[4] 刘玮,刘震云.跟知识分子非同类 冯小刚离大师0.7公里[EB/OL]. (2009-03-20)[2017-04-10].http://www.china.com.cn/book/txt/2009-03/20/content_17473311.htm.
[5] 张晓芳.新世纪小说的大众化取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8.
[6] 河西.刘震云:更大的孤独存在于劳动大众中[J]. 南风窗,2012(5):78-80.
[7] 贺绍俊.怀着孤独感的自我倾诉——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J].文艺争鸣,2009(8):40-42.
[8] 李均.存在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5.
[9] 萨特.萨特戏剧集[M].袁树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67.
[10] 屈原.楚辞[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17:189.
[11] 周罡, 刘震云.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2(3):31-35.
[12] 白烨.生活流 文化病 平民意识——刘震云论[J].文艺争鸣,1992(3):58-62.
[13] 童庆炳.文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24.
[14] 沈小峰.关于混沌的哲学问题[J].哲学研究,1988(2):26-34.
Chinese Style Loneliness: Comment on Liu Zhenyun's NovelATopTenThousandSentences
LI Xu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In the novelATopTenThousandSentences, Liu Zhenyun describes the missing of “talk” of Chinese people and deconstructs the traditional ethics, showing a real world of absurdity and the individual loneliness in this absurd world. In order to get rid of loneliness, everyone is looking for ways to dispel loneliness, but the results are always unsatisfactory. Liu Zhenyun describes the unique story about Chinese style loneliness by using the concept of loneliness in existentialism and Chinese style artistic conception.
traditional ethics; absurdity; loneliness; way to dispel loneliness; existentialism; artistic conception
2017-04-20;
2017-07-13
李 璇(1996-),女,安徽宿州人,硕士生。
I06
A
1008-3634(2017)05-0081-05
(责任编辑 蒋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