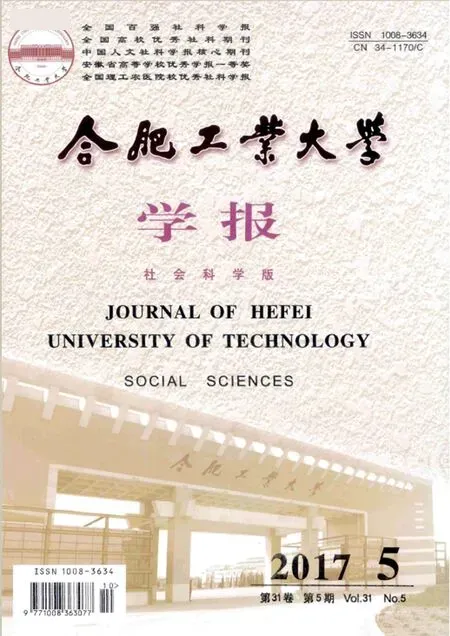权力话语视野下的《瑞普·凡·温克尔》解读
张奇才, 王婷婷
(1.安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2.淮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权力话语视野下的《瑞普·凡·温克尔》解读
张奇才1, 王婷婷2
(1.安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2.淮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文章从权力和话语的角度分析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认为小说从自然景观、男主人公瑞普和政治权力等方面体现了男权的存在。男权为了维护其话语的稳定性、去除话语中的不可预测性和偶然因素,会动用禁律、区别和歧视以及真理和谬误之分对话语进行控制。话语还会通过内部程序自行控制。由于男权及其话语的限制与控制程序,小说中试图进行女性言说的温克尔太太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并且被妖魔化成为一个疯人,被男权话语下的法庭判决为罪犯,背负着男权话语强加的罪名无奈地死去。
男权;话语;女性言说;温克尔太太;瑞普
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瑞普·凡·温克尔》在1819年问世之后,受到评论者的广泛关注。一些评论者关注作品中的神话故事,分析瑞普的重要性以及该作品与欧洲大陆神话故事的渊源。美国评论家莱斯利·菲德勒 (Leslie Fiedler)在评论瑞普时说到:“(他的出现)大大地激发了美国国民的想象力”[1]6。 刘易斯·莱尔利(Lewis Leary)将瑞普比作“美国神话的象征”乃至“守护天使”[2]。安德鲁·巴斯滕(Andrew Burstein)将作品的来源追溯到以德国乡村为背景的德国民间故事《彼得·克劳斯》(“Peter Klaus”)[3]。还有些评论者关注的是作品的历史书写及作家的意识形态取向。杨金才指出,“该小说隐含了深层的历史含义和鲜明的价值取向,即它在国族建构、意识形态和主题意蕴等方面所体现的多重文本内涵。”[4]邹心胜认为“‘瑞普·凡·温克尔’从民族身份的客观变迁、价值观念与民族意识的深层演进两个方面书写了北美荷兰人后裔融入美利坚民族的历史。”[5]莎拉·惠曼(Sarah Wyman)分析了作品中反映的欧文对待新成立的合众国的暧昧态度[6]。一些评论者关注的是小说的“逃跑”主题。罗伯特·弗格森(Robert A.Ferguson)认为该小说反映了一个惧内的被阉割的男人试图拒绝承担成人的责任、妄图永远待在懵懂的少年时代的主题[7]。还有一些评论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小说。薛小惠分析了温克尔太太所受的男权的压迫[8]83-86。朱蒂斯·菲特利(Judith Fetterly)指出,温克尔太太在小说中被单维度地刻画成一个“替罪羊,敌人和他者”[9]。其他的评论者还分析了作品中的酒神精神、荷兰风俗画的影响、陌生化的运用,或从解构主义、比较文学等角度对作品进行了研究。纵观前人所做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研究视角多样,但是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该作品的研究存在着重复研究和研究数量、广度乃至深度不够的现象。这些研究虽然得出了温克尔太太是男权的受害者的结论,却没有深入探讨男权在作品中的表现形式与男权压迫温克尔太太的具体形式。基于此,本文将从权力和话语的角度分析男权在小说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男权对温克尔太太压迫的具体体现,以期为该作品研究做出新贡献。
法国思想家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力量关系,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复杂的网络,是各种势力关系通过持续不断的相互抗争,改变、增强或颠覆它们自身的过程。“权力无处不在,这并不因为它有特权将一切笼罩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中,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被生产出来,甚至在所有关系中被生产出来。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10]。艾拉·莱莎(Iara Lessa)将福柯的话语定义做了归纳:(话语)是由想法、态度、行为、信仰及实践行为所组成的思想系统,此系统也建构了主体及他们言说的世界[11]。福柯认为权力一直存在着,可以产生和限制真理,而话语是权力关系产生言说主体的媒介。话语本身既是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的组成部分。权力和话语都是社会文化构架中必要的、积极的因素。话语的产生并非随意的,而是受到控制和限制的:话语主体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才能进入该话语领域;社会中会存在一定的外部力量通过禁律、区别和歧视以及真理和谬误之分对话语起控制作用;话语还会通过内部程序而自行控制。
一、男权的体现
在福柯看来,“真正权力的实现依赖于人们对权力主体的忽视,没有任何的个人、团体或执行者可以操控国家机器,权力被尽可能高效地、无人察觉地分散在了国家机器当中,从而保证权力主体可以采取必要的行动。因此权力不容易被察觉。”[12]表面上,“瑞普太太(和温克尔太太为同一人物)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恶妇’,而瑞普则成了一名无辜的受害者。”[8]84实则不然,此种误读产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男权的隐蔽性。通过细读,读者可以发现那被隐蔽了的男权。
(1) 自然景观体现的男权 故事发生在卡兹吉尔丛山山脚下,而这座山峰带有着浓烈的男权色彩。“那是阿帕拉钦山脉的一支断脉(dismembered branch of the great Appalachian family),在河的西岸,巍巍然高耸云端(swelling up to a noble height),威凌(lording it over) 四周的乡村。四季的每一转换,气候的每一变化,乃至一天中每一小时,都能使这些山峦的奇幻的色彩和形态变换,远近的好主妇会把它们看作精确的晴雨表。天气晴朗平稳的时候,它们披上蓝紫相间的衣衫,把它们雄浑的轮廓印在傍晚清澄的天空上,但有时,虽然四处万里无云,山顶上却聚着一团灰雾,在落日的余晖照耀之下,像一顶灿烂的皇冠似地放射着异彩。”[13]72此处对山峰的描述明显地运用了拟人手法。小说中不仅使用了“family”(家庭)和“member”(成员)等名词,还使用了给山峰赋予人的动作特征的动词,“披上蓝紫相间的衣衫”。山峰又是“noble”(贵族,高贵)的,它像一顶“灿烂的皇冠”一样象征着权力。“lord it over the surrounding country”不仅表达了山峰的高度,“lord”(男主人)一词也暗示了山峰的男性的属性。小说中女性要通过观察山体颜色的变化来揣测天气,这表明了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和臣服。因此,卡兹吉尔丛山象征着压迫女性的男权。
(2) 瑞普体现的男权 首先,瑞普象征着权力。瑞普上山时,遇到了远古的哈得逊船长和他的水手们。哈得逊船长“每隔二十年总要率领他那条‘半月号’大船上的水手,到这一带来巡视一次,这样他就可以经常来访问他建立功业的地方,察看以他命名的河流和大城。”[13]87是哈得逊船长“最初发现这条河和这一带地方,”[13]87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被理解成这片地方的缔造者,他也成为了权力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服装都是古怪的外国式样;有的穿着紧身白短上衣,有的穿着马甲,腰带上插着长刀,其中大多数人的裤子都和那位向导的一样宽大。同时,他们的面貌也很奇特:有一个是大胡子,阔面孔,一双小小的猪眼睛;另外一个人的脸似乎全给一个鼻子占了,头上戴着一顶圆锥形的白帽子、插着一根小小的红鸡毛。他们留着形形色色的胡子。其中有一个仿佛是首领。他是个身材魁梧的老先生,一张饱经风霜的脸,身上穿着一条镶花边的紧身短上衣,束着一条宽皮带,挂着一柄短剑,头上戴一顶插着羽毛的高帽子,脚上穿着一双红袜子和一双系着玫瑰花结子的高跟皮鞋。”[13]79他们是一群有着怪异着装和奇特外貌以及形形色色的胡子的人。瑞普在山上沉睡了二十年后,回到故乡时带给村民的感受正如同哈得逊船长和水手带给瑞普及读者的感受一样。“他那长长的花白胡子(足足有一英尺长),生锈的猎枪,奇怪的衣服。”[13]81可见,瑞普与这片地方的缔造者拥有着极其相似的外表,他手中“生锈的猎枪”与他们的长刀有着同样的震慑作用,这些相似之处暗示了瑞普与他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表明了瑞普对于缔造者衣钵和权力的沿袭。
其次,瑞普象征着男权对女性的压迫。小说直接提及了瑞普的祖先,“他的祖先在彼得·斯泰弗山特执政的骑士时代,以勇敢出名,并且还曾经随着彼得围攻过克瑞士廷纳要塞(Fort Christina)。”[13]72-73骑士时代曾见证了骑士对权力的追求和对女性的压迫。“骑士制度产生于中世纪欧洲的上层社会…… 骑士精神是空洞的、无内涵的,他们真正所追求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权力……男权社会独自定义了‘理想女性’,女人对此无权提出异议,在不在场的情况下无奈地接受男权的审判。”[14]瑞普的祖先围攻了以“Christina”这一以女性姓名命名的城堡,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男权对于女性的攻击和禁锢。瑞普作为后裔也会沿袭其祖先所代表的男权对女性的压迫。
此外,瑞普占有着非常重要的财产——土地。“就在这样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说句老实话,由于年深月久,风吹雨打,已经破旧不堪),曾经住着一个淳朴善良,名叫瑞普·凡·温克尔的人。”[13]72“祖上传下来的田产在他手里,就一英亩一英亩地少下去,最后只剩一小块玉米和马铃薯地,而且还是附近一带最糟糕的一块地。”[13]74土地在这段描述中被轻描淡写,但是在北美殖民地获得土地是困难重重的。“北美殖民地也出现了小土地所有制。小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主要是通过‘计口制’、‘契约奴制’、‘自占土地’等形式。”[15]根据“计口制”,任何从英国或欧洲大陆自费移入的家庭成员,每人都可以领得50至100英亩不等的土地。根据“契约奴制”,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贫穷的劳动人民以及被强制服役的负债和犯罪的人员在北美殖民地服役一定年限以后便可以获得一定的土地。“自占土地者”大部分是无法忍受地主压榨而逃亡的契约奴,他们冒着危险向西迁移,侵占印第安人的领地或者侵占大地主闲置的土地,成为小土地所有者。通过“计口制”获得土地的前提是必须拥有足够的资金负担欧洲到北美的旅费;通过“契约奴制”获得土地的代价是若干年的服役;“自占土地者”得冒着生命危险才能获得土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土地的获得都意味着高昂的代价。瑞普拥有的通过非主流方式、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很不起眼的土地也成了弥足珍贵的财产。拥有着财产,瑞普也就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也就造成了瑞普和温克尔太太在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中实质上的不平衡。尽管温克尔太太看起来咄咄逼人,但是在家庭中她是在瑞普所代表的男权的威慑之下生活。
(3) 政治权力中体现的男权 独立之前,村民会在小旅馆的前面聚集、聊天,以此打发时间。而小旅馆的招牌就是“乔治三世陛下的红色肖像”[13]75,手中拿着一柄“王笏”(权杖)。独立之后,小旅馆变成了“联合旅馆”,招牌上的画像也变成了“华盛顿将军”,他的手中拿着一把“宝剑”,不变的是门口和往常一样,聚着一堆人。福柯认为,权力无处不在。能体现规训权力机制的一个代表就是边沁(Bentham)所设计的“圆形监狱”。“这是一种全景敞式的环形建筑,中心设有一座瞭望塔,上面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整个环形建筑又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装有两扇窗户。只需在中心瞭望塔上安排一名监督者就可以监视所有囚室里的犯人。”[16]权力作用于民众中的每一个成员,民众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权力的存在和监督。而小说中的在旅馆前聚集的人群同样感觉到了由“乔治三世”和“华盛顿将军”所代表的权力的监督。乔治三世代表的是王权,而华盛顿则代表新成立的美国政府的权力。虽然权力的象征由“王笏”变为“宝剑”,但是实质并未变化。在瑞普和民众看来,两位领导人长着同样一副面孔。而且他们的性别本身就昭示着男权。此外,在弗洛伊德看来,“所有长的物体——如木棍、树干,及雨伞也许代表着男性性器官,那些长而锋利的武器如刀,匕首及矛亦是一样。”[17]象征着政治权力的男人的画像被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男权的象征物装饰着,从王笏到宝剑,从小旅店门前的大树到“联合旅馆”前悬挂着美国星条旗的旗杆,这些象征传递着一个信息——政治权力实质上反映的是男权。
二、男权对女性言说的扼杀
“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是知识传播和权力控制的工具。所有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18]小说彰显了男权,同时也表现了男权控制和限制话语的程序。
(1) 禁律 为了表现温克尔太太进行女性言说的企图,小说中对于温克尔太太的描写几乎都与“说”相关。睡觉之前对丈夫的“帐中说法”(curtain lecture)(妻子在床帐中对丈夫的枕边训话);平日里对丈夫的训诫,“他老婆不断地在他耳朵边唠叨(dinning)个没完,说他懒惰,说他事事不操心,说一家人都要毁在他身上。早晨、中午、晚上,她成天地喋喋不休(her tongue was incessantly going),只要他说了一句话或者做了一件事,就必定会招来她一篇滔滔不绝的家教 (a torrent of household eloquence)。”[13]74-75温克尔太太也会破坏村民聚会时的安宁。“她常常会突然闯到这里,破坏会议的安宁,把会上的人通通臭骂一顿(call the members all to nought),这位可怕的泼妇的利口(daring tongue),甚至连尼古拉斯·维德尔那样尊严的人物也饶不过,她公然责备(charge)他促使她丈夫养成懒惰的习惯。”[13]75
即便如此,温克尔太太也进入不了男权形成的话语。福柯认为:“限制话语的原则……决定话语的应用条件,对话语持有者给予一定的规范,这样便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使用话语了。这次是对言语主体的冲淡;若不符合一定的条件或一开始就不具备资格,则谁也不能进入话语界。”[19]14话语主体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才能进入该话语领域。小说中的温克尔太太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无法进入男权话语领域。小说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通篇没有出现温克尔太太任何的直接引语的言说,所有的言说都是间接地、经过叙述者或故事人物转述的语言。 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是叙述者对人物话语介入最小的引语方式[20],不会受到叙述者思想、情感和态度的污染。温克尔太太被剥夺了直接说话的机会,读者很难了解到温克尔太太真实的言说,很难听到她的本音。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排斥(exclusion)的程序是为人所熟知的。最明显和熟悉的便是禁律(prohibition)。我们明知我们没有谈论一切的权利,一些话题在某些场合是不能谈及的,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随便谈论个什么。”[19]3虽然温克尔太太努力地言说,但是她的声音不能进入也打破不了男权话语。
禁律决定着谈论内容的禁忌。“如果我们能够在对象、各类陈述行为、这些概念和主题选择之间确定某种规律性的话(次序、对应关系、位置和功能、转换),按习惯我们会说我们已经涉及了话语形成。”[21]小说中可以发现这种证明男权话语的规律性。小说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陈述就是“沉睡”。首先是小说的主人公“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表现的“沉睡”的状态。“Rip”可以理解为“rest in peace”(安息、安眠)的首字母的缩略形式,表明瑞普长眠了二十年。另外,村民们的总的精神面貌是沉睡的。村中的闲人坐在客店前的树阴下面,“度过一个漫长的懒洋洋的夏日,无精打采地谈论些村里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话,或者不断地讲些令人昏昏欲睡的、不知所云的故事。”[13]75其次,“沉睡”也和欧文的其他作品如《睡谷传说》(Legend of the Sleepy Hollow)形成一定的互文性。再次,小说中的饮酒也体现了“沉睡”的状态。瑞普“本来是个贪杯的朋友,”[13]79所以他才会“在没人盯着他的时候,偷偷地尝了一口酒”,然后“隔了一会便忍不住又去尝了一口,他越尝越有味,一口口地不断呷着那酒壶里的酒”[13]78-79,村中的闲人聚会的地方也是在小客店(a small inn)的前面。“Inn”的意思是“酒吧,通常是在乡村的可以过夜的酒吧”[22],他们选择在这个地方前面聚会,很可能因为他们是刚刚在“small inn”里消费完的酒鬼,所以才能讲一些“令人昏昏欲睡的、不知所云的故事”,因为讲故事的人和听众都是昏昏沉沉的了。“19世纪初期二十年的过度饮酒致使该段时间的饮酒量达到了北美历史上的最高值,这(《瑞普》)可能就是这段历史的反映。”[7]531-532
“沉睡”的表述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被不断强调和肯定,这就形成了一种男权下的话语构成,即“沉睡是一种理想状态”,试图打破这种沉睡就是一种禁忌。温克尔太太持续的言说就代表着一种与“沉睡”相对的声音。她没有直接言说的机会,从转述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她言说的内容。“他老婆不断地在他耳朵边唠叨个没完,说他懒惰,说他事事不操心,说一家人都要毁在他身上。早晨、中午、晚上,她成天地喋喋不休,只要他说了一句话或者做了一件事,就必定会招来她一篇滔滔不绝的家教。”[13]74-75“甚至连尼古拉斯·维德尔那样尊严的人物也饶不过,她公然责备他促使她丈夫养成懒惰的习惯。”[13]75她控诉着瑞普的懒惰以及村民的集体懒惰的特性。 在一定程度上温克尔太太代表的是勤劳的品质,她所代表的清醒、警觉和勤劳与小说中男权话语体系里的“沉睡”相对立,触犯了禁忌,违犯了男权话语下的禁律,因此必然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2) 区别和歧视 “在我们社会中还有另一排斥原则,不是禁律,而是区别和歧视。我所指的是理性和疯狂的对立。自中世纪中期以来,疯人的话语既已不能像其他人的那样流通。他的言语会被视为无效,不具备任何可信性和重要性,不能作为法律证据,也不能用以认证合同或契约,甚至不能在做弥撒时完成圣餐变体……无论如何,不管是被排斥或是被秘密地赋予理性,严格地讲,疯人的言语是不存在的。”[19]3-4小说中温克尔太太的言说被刻画成一种疯人的话语,剥夺了其有效性,她试图反抗男权的言行也必将失败。
根据《疯癫与文明》记载,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展示疯子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在德国,疯子成了被观看和猎奇的对象。疯人院周围被装上栅窗,人们可以看到锁在里面的疯人。小说中的温克尔太太就被当作一个疯人展示给读者。首先,温克尔太太的言说方式近乎疯狂。“他老婆不断地在他耳朵边唠叨个没完”;“早晨、中午、晚上,她成天地喋喋不休”;“甚至连尼古拉斯·维德尔那样尊严的人物也饶不过,她公然责备他促使她丈夫养成懒惰的习惯。”叙述者对她的言说方式进行了夸张的处理,造成了一种她并非正常人的印象。福柯把疯癫形象归纳为四种:浪漫化的疯癫、狂妄自大的疯癫、正义惩罚的疯癫,以及绝望情欲的疯癫[23]pix。温克尔太太在批评丈夫及村民们懒惰的同时,自以为只有自己是非常勤劳能干的,她所呈现的是一种狂妄自大的疯癫形象。
另外她的持家方式也表明了她的疯癫。“他的那些孩子,也是穿得破破烂烂,野得不得了,就像没有父母似的。他的儿子瑞普,是个淘气鬼,长得和他一模一样,不仅穿着他父亲的旧衣服,保险还能继承父风。通常,总看见他像匹小马似地跟在他母亲脚后面,穿着一条他父亲丢掉不用的裤子,一只手费劲地拉着裤子,仿佛一位华丽的太太在下雨天拎着裙子下摆似的。”[13]74孩子邋遢的形象表明了温克尔太太在料理家务方面的严重失职,以及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也表明了温克尔太太的疯癫的状态,因为正常的母亲是不可能让孩子以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邋遢的方式出现在别人的注视之下的。
温克尔太太的死亡方式也较为特殊。“哦,她也死了,不过这还是不久以前的事;她是跟一个新英格兰的小贩发脾气,血管破裂死的。”[13]86福柯认为,疯癫与激情相辅相成,疯癫的人往往充满激情,他们无以排遣内心的苦闷,常表现得歇斯底里和躁动不安,这种强烈的情绪导致了疯癫更顽固的存在[23]48。根据温克尔太太的女儿的说法,温克尔太太的死因是“血管破裂”,这种死亡原因就更好地佐证了男权的主体视角下温克尔太太的激情和疯癫。
温克尔太太的言说方式、持家方式以及死亡原因在男权话语的语境下被刻意地扭曲,呈现出疯癫的特征,而她本人也被扣上“疯人”的帽子。男权社会的区别和歧视必将淹没温克尔太太作为“疯人”的言说,让她彻底失声。
(3) 真理意志的排斥 福柯认为,“真理意志,在要言说这‘真实’话语的意志中,如果牵涉的不是欲望和权力,又能是什么?”[19]7在本质上真理、真实仍然是受权力主体的权力、欲望所左右的。“真理意志,如同其他排斥系统,得依靠制度的支持:它由各层次的实践同时加强和更新。教育自不必说;还有图书系统、出版、图书馆;过去的学术社团和现在的实验室……这种如此依赖于制度的支持和分配的真理意志往往会向其他话语施加某种压力和某种制约性的力量(我仍然谈的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我想到的是多少世纪以来西方文学是如何寻求将自己建立在自然、‘逼真’、真诚、以及科学之上——一言蔽之,在‘真实’话语之上的。”[19]6-7
真理意志需要依靠学术社团的支持。小说中的一个的学术社团就是由“村中的圣贤、哲学家和其他空闲的人组成的永久俱乐部”[13]75。他们当中有着衣着光鲜、知识渊博的校长戴立克·凡·本麦尔,也有村长兼客店老板尼古拉斯·维德尔,“他们常常坐在这儿的树阴下面,度过一个漫长的懒洋洋的夏日,无精打采地谈论些村里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话,或者不断地讲些令人昏昏欲睡的、不知所云的故事。”[13]75-76这样一个学术社团是权力的核心,掌控着谈话的方向的是村长。作为知识分子的校长戴立克·凡·本麦尔在美国独立后成为了国会议员。村长和国会议员本身就是权力的代表。他们说的是村庄里的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话,而在说话的过程中,村长通过喷吐烟圈的方式做裁决,这就构成了法庭的雏形。这种法庭的雏形实际上是在对那些试图挑战、颠覆男权的“其他话语施加某种压力和某种制约性的力量”。小说中虽然没有写出在俱乐部的讨论被温克尔太太扰乱后俱乐部成员的反应,但是他们肯定不会听之任之,他们必然会对温克尔太太做出相应的裁决。首先,“村里的好心的主妇们……聊起天,谈到了这些事情,她们总是把一切错处都推到凡·温克尔太太身上。”[13]73这不仅仅是因为瑞普给她们帮了忙,更主要的原因是她们已经向男权妥协,接受了乡村俱乐部法庭的裁决,成为了男权的帮凶。 就连温克尔太太的女儿也接受了男权话语下的“真理”,无视母亲二十年来在田间辛苦劳作、在家中操持家务,呕心沥血而积劳成疾,郁郁而终,却帮助男权污蔑母亲,说她是“跟一个新英格兰的小贩发脾气,血管破裂死的,”[13]86把母亲轻描淡写地污蔑成一个心胸狭窄的疯子似的人物。其次,“破坏房屋,或者焚烧房屋以及洗劫房屋里的财物是古代施行的对于被宣布为罪犯的人的一种仪式性地惩罚。”[24]瑞普在长眠后回到村庄时发现,“家里的房屋已经坍败不堪——屋顶已经倒塌了,窗户都破了,大门上的铰链都脱下来了。”[13]82房屋之所以破败,就是因为村民们公然地将温克尔太太认定为试图颠覆男权的罪犯,从而故意破坏了房屋,温克尔太太的女儿和儿子就居住在附近,但是他们也不敢反抗和阻拦村民对温克尔太太的裁决和惩罚。
(4) 男权话语的内部程序 男权话语的内部程序“是话语本身自行控制,即充当分类、排序、分配原则的那些程序,此时似是要控制话语的另一维度:事件和偶然性。”[19]8它包含着评论原则、作者原则和学科原则。通过控制偶然性,这些原则可以降低话语的不可预测性,维护话语的稳定性。
“评论给话语以应有之物从而消除话语中的偶然因素。”[19]10通过不断的评论,话语的活力得以保持,不利于话语的内容被剔除。小说中,对于温克尔太太和瑞普的评论一直在继续,从俱乐部的几位成员到村子里的主妇们,他们总是在数落着温克尔太太试图颠覆男权的大逆不道。瑞普重回村庄后也是被一个老婆子辨认出来,正是她的证言和评论才重新树立了瑞普的身份。瑞普的奇特的经历同样被人们评论,“他常常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每一个到杜立特尔先生的旅店里来的新客人。起初,大家都觉得他讲起来,每一次都有些不同的地方,这一定是因为他才醒来不久的缘故。最后,这段故事才讲得完全和我刚才讲的一样,附近的人,不论男人、女人和小孩,都背得出来。有些人却始终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断定瑞普有精神病,而这个故事就是永远留在他脑子里的狂想。不过,年老的荷兰居民,几乎全都深信这回事。”[13]15通过不断的讲述和评论,大部分人都接受了这个故事和这个故事所体现的男权话语,小说中的男权话语得以保持其活力。
“作者是赋予令人不安的虚构语言以统一性、连贯性,以及使之与现实相连的人。”[19]10将一定的文本归之于一定的作者,使得文本的可信度提高。“简言之,一命题必须符合复杂和苛刻的要求才能融入一学科。”[19]13复杂和苛刻的要求同样消除了话语中的偶然因素。该小说的副标题是“狄德里希·尼克尔包克尔的遗著”,欧文将作者的头衔赐予了叙述者狄德里希·尼克尔包克尔,一位肖像被印在新年饼干上的史学家。小说还被放置于历史学科的范畴当中,以提高其可信度。小说中,熟知当地历史的彼得·范德尔敦克证实了瑞普的遭遇,尼克尔包克尔也证实其亲自与瑞普交谈,此外他的故事还得到了当地法官的证实。
通过话语的内部程序,男权话语下的种种机制如:禁律、区别和歧视、真理的意志都被蒙上了合法的外衣,男权对女性的言说的扼杀就显得颇具合理性。
要而言之,以前的女性主义研究虽然看到了温克尔太太受到的实体世界中的肉体和精神的压迫,但是没有关注到这复杂的男权权力关系网和话语的运作。在权力和话语视角下,我们可以看到,男权话语的抑制程序和内部程序是不可能让异己的声音或言说存在的。由于男权话语的存在,温克尔太太成为了“他者”,她极力发出声音,我们却无法直接听到;她极力地要改变自身和周围人们的生存状态,却因为“众人皆醉她独醒”被看作是异类和疯人,承受着男权话语的制约和惩罚,因为一个“颠覆男权”的罪名而声名狼藉,众叛亲离,郁郁而终。我们知道温克尔太太是一名受害者,但是只有厘清迫害她的种种权力和话语交织的网络后,我们才能真正地为死去的温克尔太太们正名,才能真正地拯救正在或将要遭受苦难的成千上万的温克尔太太们。
[1] FIEDLER L. 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M].New York: Dalkey Archive Press,1996:6.
[2] LEARY L. The Two Voices of Washington Irving[C]//From Irving to Steinbeck: Studie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in Honor of Harry Warfel. Ed. Motley Deakin and Peter Lisca. Gainesville: Univ. of Florida Press, 1972: 22-23.
[3] BURSTEIN A.The Original Knickerbocker: The Life of Washington Irving[M].New York: Basic Books, 2007:125.
[4] 杨金才. 从《瑞普·凡·温克尔》看华盛顿·欧文的历史文本意识[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6):75-79.
[5] 邹心胜.“瑞普·凡·温克尔”的历史书写[J].外国文学研究,2011(3):89-92.
[6] WYMAN S. “Washington Irving's Rip Van Winkle: A Dangerous Critique of a New Nation”[J]. ANQ: A Quarterly Journal of Short Articles, Notes, and Reviews, 2010(4): 216-222.
[7] FERGUSON R A.“Rip Van Winkle and the Generational Divide in American Culture”[J].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2005(3): 529-544.
[8] 薛小惠. 谁是真正的受害者?——《瑞普·凡·温克尔》的女权主义解读[J].外语教学2006(1):83-86.
[9] FETTERLEY J, PRYSE M. American Women Regionalists 1850-1910: A Norton Anthology[M]. New York: Norton, 1992.
[10] 汪民安.权力[C]//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442-456.
[11] LESSA I. Discursive Struggles within Social Welfare: Restaging teen motherhood[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2006(2):283-298.
[12] Wikipedia.Power[DB/OL].(2015-09-10)[2017-08-3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wer_(social_and_political)#Foucault).
[13] 华盛顿·欧文.瑞普·凡·温克尔[A]//荒诞小说.万紫,雨宁,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1.
[14] 何颖. 空洞的荣誉——论骑士精神[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
[15] 周章森. 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土地问题[J]. 杭州大学学报,1987(3):122-128.
[16] 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 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30.
[17] 弗洛伊德. 梦的解析[M]. 丹宁,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231.
[18] 蒋贤萍.“权力-话语”语境下的《红字》[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8):50-57.
[19] 福柯. 话语的秩序[C]//语言与翻译的政治.肖涛,译.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01.
[20] 戴凡.《喜福会》的人物话语和思想表达方式——叙述学和文体学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9):56-59.
[21] 福柯. 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 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47-48.
[22] Oxforddictionary.“pub”[DB/OL]. (2015-09-15)[2017-09-01]. http://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inn?q=inn.
[23] FOUCAULT M.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M].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
[24] FOUCAULT M. Power/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M].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6.
A Feminist Analysis ofRipVanWinkl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Power and Discourse
ZHANG Qicai1, WANG Tingting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232001, China;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232001,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Washington Irving'sRipVanWinkl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power and discourse. Patriarchal power finds expression in natural landscape, Rip the hero and political power. In order to secure the discourse of man and avoid the unpredictability and accidental factors in the discourse, patriarchal power may control the discourse by using prohibition, discrimination,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ruth and fallacy as well as inner controlling mechanism. Consequently, the rebelling voice of Dame Van Winkle is silenced, and she is demonized as a mad woman and criminal, who eventually dies helplessly.
patriarchal power; discourse; utterance of women; Dame Van Winkle; Rip
2017-01-15;
2017-09-07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K2016A0297);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2015AH0035B)
张奇才(1981-),男,安徽凤台人,讲师,硕士。
I106
A
1008-3634(2017)05-0048-07
(责任编辑 蒋涛涌)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