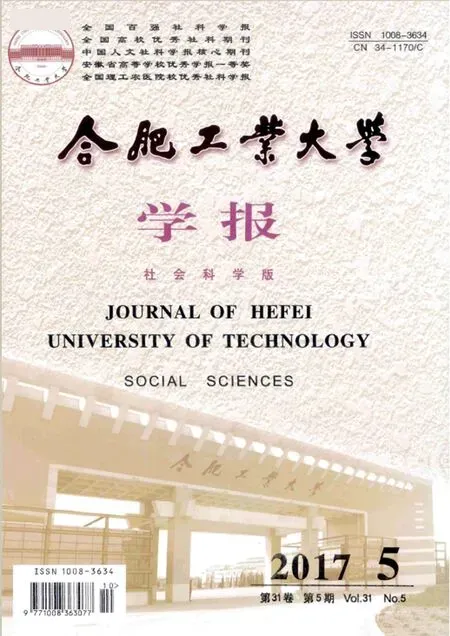张爱玲与夏洛蒂·勃朗特女性意识的差异
封鑫璐, 田德蓓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张爱玲与夏洛蒂·勃朗特女性意识的差异
封鑫璐, 田德蓓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在女性主义的观照下,从哲学观、伦理观和女性书写诗学观等文化因素的影响等视角,分析中西女性意识差异的原因。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女性主义通常以较温和的方式揭露女性自身弱点,解构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并将女性气质视为女性引以为傲的特质,因此在反映女性意识时更加自信;以夏洛蒂·勃朗特为代表的早期西方女性主义对女性缺乏自信,她们常以一种激烈的方式颠覆传统女性形象,并极力排斥女性气质,表现了向男性看齐、被同化在男性阴影里的趋势。因此,在女性主义初期,相比较西方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性别二元对立”的女性观,中国女性则比较深刻与成熟,它以承认性别差异为基础的两性平等观取代了西方平等人权的观念。
张爱玲;夏洛蒂·勃朗特;中西方女性意识;解构性别二元对立;文化因素
中西方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分别产生于民国时期和维多利亚时期。她们虽都趋于为了女性主体发展的女性价值观,但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历史观的观照下,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创作,却蕴含了不同的女性意识和表达方式。夏洛蒂·勃朗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主义意识的典型代表,极力排斥女性气质,并以一种激烈的、颠覆性的、富含对立仇视情绪的方式反抗男权社会。美国女权主义评论家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认为夏洛蒂·勃朗特极具男性话语特色,主要是“模仿”与“内化”男性价值标准,其观点具有反本质主义的倾向。张爱玲作为中国第一代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家,实现了真正的女性书写,传达出较成熟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她承认男女两性的差异,反对男性化的女人,认为女性安于自身性别,反而能更加自由洒脱地畅言自己的女性思维。张爱玲从女性的视角消解男性罗格斯中心主义。她认为女性透析到真实的自己,男性则更能够深刻反思女性的劣根性归根结底源于男性。
张爱玲作品所表现出的女性意识观是:张扬女性本质,同时以较温和的方式解构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从而形成两种价值意义并存的多元局面。这种价值观至今仍能适应多元化的世界潮流,有利于两性和谐健康发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在接受西方女性主义、进行自我建构时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过于激进,甚至是反本质主义的;另一方面又顾虑中国女性主义过于温和而不够彻底。本文分析发现,张爱玲这种成熟的女性意识观为中国女性意识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展现女性意识的方式不同
夏洛蒂与张爱玲虽同为女性,但他们表现的女性意识却完全不同。夏洛蒂塑造了一系列自尊、自重、自爱的女性人物,颠覆了传统的女性角色。她采用激昂亢奋、声色俱厉、轰轰烈烈的方式展现女性意识,否定传统的所谓男性与女性的截然两分。张爱玲则以较柔和的方式,在承认男女差异的前提下,以讽刺的笔触揭露女性所具有的奴性弱点,她试图以此方式来唤醒女性进行反思。
(1) 夏洛蒂·勃朗特:时代英雄的缔造者 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夏洛蒂·勃朗特,一改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观,勇敢地喊出不做“天使”做女人,向我们诠释了形形色色的真实女性,实现了对传统家庭天使的颠覆,造就了一个个时代女英雄。
夏洛蒂认为男女关系应该建立在日益发展的爱慕、尊敬和敬佩,而不是金钱实利和情欲的基础上。她在《简·爱》中塑造了一位自尊、自重、自爱的女性人物。简·爱不再是像萨克雷、狄更斯等笔下的传统淑女那样温柔、柔弱、单纯和顺从,而是具有像男人一样具有孤勇的反抗与叛逆精神,在经济与人格上都保持独立。在《雪莉》中,夏洛蒂塑造的女主人公雪莉是浪漫女性人物最理想的化身,她能够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既能够自食其力,又能主动追求爱情与幸福。
夏洛蒂悲叹那些迫使女性自我克制和屈从,甚至把女性束缚在压抑状态下的清规戒律。她看到了传统女性的悲哀,即女性如果在爱情上遭遇挫折,或者找不到一个可以提供经济支撑和社会地位的丈夫,她们就会沦落到孤立无援的境地。她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女性英雄形象。例如《维莱特》中,露西就是一位自尊自立、具有强烈自主意识的女性:事业上——她怀着雄心勃勃的理想,希望当一位欣欣向荣的教区机构的女校长。感情上——她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传统妇女,她坚持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此外,露西还坚持要培养自己谋生的本领,而不是取得爱情、婚姻和母亲身份的能力。她认为传统的家庭天使平庸、呆板、苍白且拘泥形式,对那些无自主意识的女人持批判态度。女性主义批评家苏珊·古芭(Susan Gubar)和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Gilbert)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指出:“这个魔鬼可能不仅隐藏在天使的背后,而且实际上她也可能潜伏在天使的身躯之中(或者天使的下半身之中)。”[1]
夏洛蒂在作品里强调女性应该在经济、社会地位、权利意识等各个方面跟男性平等,彻底颠覆了传统女性角色和男权文化。
(2) 张爱玲:女性奴性的揭露者 张爱玲以私语空间写作模式,专注于女性内心世界及其身边琐屑的挖掘。将男权社会里备受压制的女性话语供奉在文学的圣坛上,实现女性对主体性和认识体系的构建。她不关注“英雄的宏伟”,而是着力刻画和揭露传统女性人格的特性和缺陷,及最终所导致的命运的毁灭和荒凉。张爱玲通过揭露在新旧夹缝中挣扎存活的旧式少女、太太以及社会底层劳动妇女“他者”的存在,显示出对婚姻中男女平等的渴望。
《花凋》里,郑家的女儿们唯一的追求便是嫁得一个体面的丈夫,那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观念,张爱玲以其冷静的思维和深刻的见解揭露了当时社会的这一弊病。张爱玲的文本里具有众多病态、忧郁、绝望的女性,如《年轻的时候》里,没有受过教育、无自我意识、在旧礼教的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便是潘汝良的母亲的真实写照。《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烟鹂,因没有“自己的房间”而造成孤独麻木无知,只有在浴室才能恢复完全自我的意识,因而经常处于“自闭”与“麻木症”的状态。张爱玲为这种奴性意识备感痛心。
张爱玲笔下的传统女性大都活得没有自我,没有思想,她们的无趣、呆板与麻木或许源于知识和教育的匮乏,然而,在《倾城之恋》里受过良好教育的白流苏的命运依旧让我们感觉那么悲凉。她的出走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娜拉式”的“走出去”,实质上,她苦苦追逐的仍然是一个体面、富足、得以托付后半生的丈夫。但悲凉的是她最后还是委身做了范柳元的情妇。短暂的战争粉碎了一切外在的东西,隔绝了男性文化的时空,资本的消失使男女实现了暂时的平等,但战争的结束却意味着男性文明及其主体身份的恢复,预示着白流苏今后苍凉和虚无的命运。这便是张爱玲笔下走出去的女人,她们也仅是“走到楼上去”,无经济能力就没有解放自己的资本和基础,这是男权社会里没有任何经济能力的女性无奈的妥协。可是,具有经济自立能力的知识女性的命运又如何呢?《封锁》里有经济能力的翠远,依然没有真正独立的女性意识。在她眼中,成为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远没有寻找一门体面的理想婚姻更能体现自身的价值。正如白流苏所认为的,女人只有获得异性的爱慕与欣赏,才能得到同性的尊重。这种观念实质上是用男性欲望客体的男权标准来衡量自我的价值。翠远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缺乏主体意识以及最起码的自我意识,因此她的人生依然是迷茫悲凉的。
张氏对女性自身弱点进行了深刻剖析。她认为女性身上自主意识、主体意识极其荒芜,她们的依附性不是跟随潮流的、表面的,而是几千年来深入女性骨髓形成的女奴意识。张爱玲在批判的同时还传达出一种理念,即女性的悲剧归根结底源于其奴性本质,“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人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2]。因此,她注重女性的自省,并以较柔和的方式促使男性进行自我反思其对女性造成的伤害。这种以温和的方式展现女性意识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展现不同的女性意识本质
张爱玲和夏洛蒂笔下众多女性人物的性格,反映出二者女性主义最本质的区别:张爱玲认为女性气质——隐忍、坚毅与恒定是强大的,对女性气质的认同就是对女性本质的认同,正是这种特质使得女性在面对生活的磨难时可以随遇而安,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夏洛蒂则完全摒弃且排斥女性气质,这实际上是持女人不如男人的性别偏见,并将男性作为女性的典范。
(1) 张爱玲认同女性气质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3]这便是女性的本质特性,如大地一般的安稳与永恒。张爱玲不仅塑造了传统的女性人物,也再现了一系列具有现代思想的女性,她笔下具有丰满女性气质的人物跨越百年,比如《半生缘》中的顾曼桢和《多少恨》中的虞家茵这一类既具有现代女性思想,又兼具女性特质的女性形象非常具有代表性。她们努力求学、追求理想,大学毕业后凭着自己的能力认真工作,担起家庭的重担,这是女性特质中勤劳朴实的一面。她们身上总是那么有朝气,个性中有沉毅、隐忍的一面,可以坦然地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当重担压在她们纤弱而又坚毅的肩膀上时,她们保持着一种娴静的风度,好像仍余勇可贾,这种隐忍、坚毅的韧性便是女性保持其安稳性与永恒性的根本所在。
张爱玲作品中所反映的女性意识观在历代中国文学作品中也有迹可寻。从纵向的历史来看,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如《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在体现女性意识时,女主人公都具独特的女性气质。崔莺莺和杜丽娘以大家闺秀的姿态以柔克刚,以女性特有的坚韧抵制男权的压迫。崔莺莺重爱情、轻功名,一反男权社会因对女性贞洁的过度重视而造成对女性的摧残;杜丽娘勇敢地同父权社会做斗争,为情而死又为情复生;林黛玉的女性气质是在纤弱中融入一种清雅而刚烈的风骨,她直面父权压迫,蔑视功名利禄,要求独立自由。她们看似柔弱,实则坚韧,这种女性气质同西方观念中的温驯、纯洁的“家庭天使”不同。她们在那种柔性力量的作用下,内心坚韧,敢爱敢恨,以自己纤弱的肩膀对抗封建男权社会,使身边的男性变得那么无力与渺小。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太太们以女性特有的优势——稳定与永恒的力量,成为大家族中的主心骨。例如《红楼梦》里贾母一类的角色,她们所具有的综合能力、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势,能以母性的包容与气度协调大家族里面复杂的人际关系,维持家族乃至社会的秩序,这些都是男人所不及的。可见中国历代在展现女性意识时,都是尊崇与赞扬这种独特的女性气质的。对女性气质的认可,就是坚持女性在真正意义上达到与男人平等,那是一种内在的、融入意识里的平等观,而不是浮面的、形式上的一味宣扬政治权力的平等。
(3) 夏洛蒂排斥女性气质 夏洛蒂作品里的人物无一例外地排斥女性气质。例如《教师》中威廉·柯林斯反对亨斯登对鲁本斯画的女人像的偏爱,雪莉厌恶身为女性而仿效男子风度。她自称是老爷,不认同传统的那种观念:不同性别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她对有关外貌和举止方面的习俗礼节很不介意,甚至对生物学上两性自然属性这一概念也提出抗议。在夏洛蒂的观念中,把她当作一个男人来同她较量才是对她平等权利的承认,才是对她的真正认可与尊重。“如果他是优胜者,让他俘虏我,抓住我,使我屈服——让我们以武器对武器打出一个胜负,看看谁是强者。你这个可怜虫,你为拉结服侍七年,难道你不知道你是在侮辱拉结吗?”[4]她认为女性是不需要照顾的,男女之间的较量要完全处于一个公平的战场,男性要完全以对待男人的方式来征服她。她希望自己的作品完全不带脂粉气。这种摒弃女性气质的写作手法在西方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渊源,从古希腊神话美狄亚的杀夫弑子这种男性般的残暴与果敢,到夏洛蒂笔下极具男子气的女性人物,还有伍尔夫塑造的一系列“双性同体”的女性人物,她们发挥“阳刚”潜能,具有男性气质中常有的力量和自由品性。《日与夜》里,她赞美凯瑟琳“为人实在,坦白直率”、“具有男人气质”。她们都在极力标榜,除了生理上的差异外,女性在任何方面都跟男性相同,女性一旦有了权利,其行为就与男人无异,绝无例外。
以夏洛蒂为代表的西方早期女性主义不顾性别差异而强行超越,一味追求无所不能的女扮男装,变成了弗洛伊德(Freud)所说的“阉割的男人”。排斥女性气质,不能正视自我性别,身为女性而感到自卑,这种心理所产生的去性化女性书写,势必会忽视女性的内心世界,也将不利于女性的成长。女性想要在任何方面都奋力与男人并驾齐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平等。以吉列根(Gilligan)为代表的关怀伦理学者对这种观念予以猛烈抨击,他在《不同的声音》(Different Voice)中强调,女性应发展自身特质,享有与男性不同的空间和声音。
以张爱玲为代表的中国女性主义是成熟且深刻的,它承认两性的差异,承认女性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并发现其存在的终极意义,发掘那一个个灿烂的生命,泰然自若地接受生命给予的一切。女性特质既是一种神性,又有一种永恒的定性。
三、产生差异的历史文化原因
张爱玲与夏洛蒂所展现的中西方早期不同的女性意识是深受文化观念影响的。张爱玲出身名门,受传统文化影响颇重,夏洛蒂出身于文化氛围颇重的牧师家庭,二者女性意识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中西方不同的哲学、伦理、诗学观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
(1) 哲学观的差异 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观念,即事物之间存在冲突且不可调和,非此即彼。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指出,自柏拉图以来,西方便崇尚理性传统,这一传统是基于一系列二元对立之上的,“从柏拉图(Plato)到卢梭(Rousseau)、从笛卡尔(Decare)到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所有的形而上学家,因此都认定善先于恶,肯定先于否定。纯先于不纯,简约先于繁复,本质先于意外,蓝本先于摹本等。”[5]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观念影响下,男女完全是两个对立的独立体,必定是冲突不可调和的。因此,她们对男权的反抗与颠覆必定是极端彻底的,她们一再强调在政治上的权利平等,最后甚至要求在举止、心智上都要和男性不相上下。夏洛蒂持有的便是一种“性别二元对立”的女性主义思想,如《教师》里的雪莉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西方女性主义初期在两性平等的进程中,便持这种“二元对立观”,它以一种激昂亢奋、声色俱厉、轰轰烈烈、富含对立仇视的情绪对抗男权社会。
中国讲求阴阳互补、阴阳和谐,《周易》中记载“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6]。男女所分别代表的阳和阴不是绝对的排他性而是相互融合、互相补充的,这是道教阴阳说的基本体现。男人不屈不挠的性格和女人的屈服决定他们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男人负责赚钱养家,女人则负责管家和抚养子女。佛教也重视女性气质,主张女性悲悯、隐忍和屈从。儒家将君臣、父子、夫妇这种纲常伦理关系作为社会等级关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强调男女等级间互相协调,平衡发展。另外,中国文化中也有“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这一说法,可见,在中国传统哲学所张扬的两性和谐观的观照下,中国女性主义初期就形成一种温和舒缓、心平气和、和谐互补的格调。
(2) 伦理价值观的差异 西方在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影响下家族观念比较淡薄,从其源头古希腊罗马时期,家族就有一定的血腥统治意味。例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天神宙斯和其天父乌拉诺斯相互残杀,而后又注定要被更强大的儿子推翻。薄弱的家庭观念,致使女性终生目标虚无,缺乏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当把自身的价值寄托在男性身上时,她们便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取悦男性,以装扮、购物等物化自我的方式获得男性的认同。在这种商品化的状态下,西方女性经常会空虚无聊、虚度光阴,才干和能量无处释放,于是变得不满、忧郁。加之,西方家庭是以小家庭的方式而不是以家族的形式出现,因此,较之东方女性,西方女性不必承担家族的责任与义务。这便出现了赛珍珠(Pearl Buck)在《论男女》中所谓的“火药型”妇女,她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且聪明能干,但闲在家中,常以被欣赏的静态艺术品的状态存在。另外,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极度渴望外面的世界,她们无法从家庭主妇角色中获得满足,渴望在社会上实现自我,这一矛盾的状态压抑得她们焦躁不安、易受刺激。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更加激烈,“女人不仅被看作是有道德的人,而且是有理性的人,她们应该采取和男人一样的方法,来努力取得人类的美德。”[7]她们以一种富含对立的态度极力渴求在社会中的权利和地位,不仅强烈要求推翻父权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还坚决抵制社会文化结构——家庭、教会和学术。
中国在“宗法制”“家天下”的道德伦理观影响下极其注重家族观念,个人的“小家”是整个民族“大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作为“位乎内”的女性,在处理家族大大小小的事务时便体现了自身的价值。中国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并在家务中得到满足。她们关乎家庭中一切事务的运行,诸如拜祭祖先、节日庆典、红白喜事、执行家规,教育子女、照护老人等。将一个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需要女性发挥智慧和才能,就像张爱玲作品《太太万岁》里的陈思珍,一个极精明能干的女子。对家族观念的重视极大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另外,儒家倡导“百善孝为先”,母性因此成为传统社会中一股强大的力量,母亲可以利用孝亲观在家庭中得到更多的权利和更大的尊重,在家族中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当这些女子从媳妇熬成婆之后,“家庭母权”转接到下一代手中,成为周而复始的权利流转。如《红楼梦》中掌管大权德高望重的贾母,是连接整个家族的纽带,王熙凤将成为她的接班人。这种“宗法制”的伦理观保证了女性的地位和自信,致使女性主义不至于秉持性别关系的完全对立,更不会以一种口号式的说教争夺权力,因此在表达自身时得体、从容、低调且温和。
(3) 女性书写诗学观的差异 在西方文化中,女性书写对父权制有着很大的威胁,因而它始终受到强烈的排斥与反对。为此,一些女作家在笔名方面下足了功夫,例如,夏洛蒂首次出版《简·爱》的时候,便采用了一个男性化的笔名柯勒·贝尔,后来的乔治·艾略特也是采用她丈夫的姓氏作为笔名。父权制代表将创作的妇女称为“女学究”和恶魔的女作家,除了公开打击排挤之外,还对妇女文学采取了限制和驯化的手段。“德尔·史班德(Dale Spender)指出,这个策略就是公开私下父权制社会采取公开/私下的二分法。男作家面向公众,为一切读者写作,他们的作品可以公开发表,到处流传。女性作者只为私人圈子内的读者或女读者写作,她们的作品传播面极小。”[8]之后在解构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女性主义出现了“反本质主义”的倾向,这一观念在一些激进者那里发展到完全否定人性,如《阁楼上的疯女人》这一作品便体现了激进式女权主义思想。它提出凡是男性所反对与厌恶的,女性就要去肯定与歌颂。这种极端激进的态度强化了男性对女性书写的排斥。
相对而言,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对才女表现出了更多的偏爱,因而欣赏、表彰、品评闺阁之作的言论远远多于排斥和反对的举动。不同于西方尚武的英雄主义,诗以言情、文以载志是中国社会的风尚,是文人志士普遍采用的文学形式。所以与西方文学史上反对妇女作诗的倾向刚好相反,才女的诗作普遍受到赞誉。“以唐代为例,据近人《全唐诗库》记载,收录唐诗人共2529人,唐代近290年的历史中共产生女诗人270人。再放远目光,从远古的许穆夫人到东晋的‘咏絮才女’,再从‘扫眉才子’薛涛到‘词别是一家’的李清照,从随园女弟子到‘鉴湖女侠’秋瑾,直至‘五四’女作家群,他们在艰难地萌芽、顽强地生长。”[9]这些才女都无一例外受到士大夫的赞美与欣赏。另外,中国女性书写多是具有“怨”的基调的抒情诗,这种哀怨痴缠的基调恰恰与西方的怒斥般的“怒”的基调相反,更能引起男性读者的同情与怜悯,也更容易被接受,所以不存在像西方那样被称为恶魔的女作家。
四、结 语
张爱玲与夏洛蒂·勃朗特分别代表了中西方早期女性意识两种不同的书写维度。中国在哲学上强调阴阳互补,伦理观上注重家庭的地位,诗学观上又历来偏爱才女,这一系列因素导致了中国女性较之西方更具有自信。在这种自信心的驱使下,以张爱玲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女性主义对于自身的弱点勇于自省,敢于讽刺揭露,在表现女性意识时会认可且肯定女性气质。张爱玲作品中所传达的女性意蕴、女性的艰难处境以及女性生存文化都极具女性意识。她强调男性和女性不是对立体而是一个整体,是人类的共同组成部分。同时,男性和女性既是相互独立,又是相互依存的。而以夏洛蒂·勃朗特为代表的早期西方女性主义则以一种激烈的方式颠覆传统女性的形象。究其历史文化原因,哲学观上的二元对立思想,伦理观上家庭观念的薄弱以及诗学观上对女性书写的极度排斥,这种将女性置于“他者”地位的态度致使女性作家的潜意识里始终存在着不自信的因素,女性从而怀疑自身特质的价值,因此在女性书写过程中出现过度弱化女性身份、过度模仿男性口吻的非女性化趋向。夏洛蒂这种女性主义观实质是早期西方的自由女性主义观,其结果是女性从自由的狂欢陷入女性自身主体意识的丧失。这种完全摈弃女性特质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观念,导致女性的文化乃至异性特质没有价值,最终致使女性主义所依赖的核心概念——性别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相比之下,张爱玲以一种含蓄内敛的中式叙事书写出的中国早期女性意识更加理性与成熟,她以一种超前的性别意识解构了性别二元对立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世界观。
[1] GILBERT S M,GUBAR S.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M].State of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1979: 29.
[2] 张爱玲.谈女人.张爱玲文集(第4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68.
[3] 张爱玲.谈女人.张爱玲文集(第4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70.
[4] 于青.勃朗特三姐妹研究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79-180.
[5] 蒋孔阳.美学与艺术评论(第四辑)[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225.
[6] 王弼注,孔颖达撰.周易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0.
[7]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4.
[8] 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75.
[9] 张向荣.文学伦理的人性转换:“身体写作”之反思[J].外国文学研究,2016,(5):43.
Differences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Works of Zhang Ailing and Charlotte Bronte
FENG Xinlu, TIAN Debe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Based on feminis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different feminist consciousnes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such as philosophy, ethnics and female writing. Represented by Zhang Ailing, the early Chinese feminism is more confident, which exposes its own weakness of women, deconstructs the central value system of men in a relatively moderate way and regards femininity as a character to be proud of. Represented by Charlotte Bronte, the early western feminism lacks confidence in women, it subverts the traditional female image and extremely excludes female character in a violent way, which reveals the trend that women regard men as their standard and assimilate in male shadows. Therefore, at the early stage of feminism, western feminism stresses gender binary opposition, which is anti-essentialism. Compared with it, Chinese feminism is more mature and profound, and it takes place of western epual human right with gender equality.
Zhang Ailing; Charlotte Bronte; feminist consciousness of China and the West; deconstruction of gender binary opposition; cultural element
2017-06-22
封鑫璐(1992-),女,山东潍坊人,硕士生;
田德蓓(1956-),女,上海人,教授,硕士生导师。
I206
A
1008-3634(2017)05-0060-06
(责任编辑 刘 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