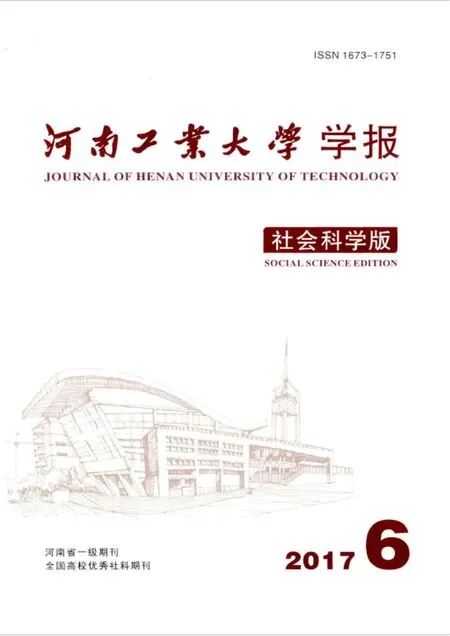论《合欢牡丹》中的女性意识和身份认同
蒋好霜
(广西大学 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
论《合欢牡丹》中的女性意识和身份认同
蒋好霜
(广西大学 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
《合欢牡丹》中塑造了几位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作为新时代的新移民,这些女性是处在他国边缘的离散群体,作者利用这些女性形象透露了两种文化交融中别具特色的女性意识,展示了异乡生活的女性生活中爱的普遍缺失,暗含了作者对人类生存本质——孤独的体验。从书中人物的原乡语境、他者语境、作者的个体语境等多重文化语境入手,分析了《合欢牡丹》中女性意识中的灵与肉、文化根性和异质属性之间的冲突,讨论了新移民女性意识背后的身份认同问题。
《合欢牡丹》; 女性意识 ; 身份认同
美华文学(本文只讨论新移民作家及其文学作品,不包括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及其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一直是比较文学形象学中重要的一部分。作为处在他国边缘位置的离散人群,美国华裔要承受来自异国他者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疏离。同时,自男权社会以来,话语权就被男性掌握,女性处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边缘位置。因此,来自政治共同体构成的他者和男性的他者的双重挤压,使得离散人群中的女性意识及其身份认同尤为复杂。学者赵颖认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女性写作,是以汉语和性别作为特征的文学态势,在这两者纠葛之中,它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文化特质和社会图像”[1]。
《合欢牡丹》是现在定居美国的华文女作家江岚于2015年最终定稿的作品,王红旗认为,这是一部人物故事吸引力很强的小说,是“一部新世纪曼哈顿中国女人的心灵成长史……点亮了华人以及人类灵魂栖息之所的明媚,令人凝思浮想之致远”[2]。小说主要塑造了四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本文通过对《合欢牡丹》中女性意识的分析,讨论女性意识背后的身份认同问题。
1 《合欢牡丹》中女性意识的多重文化语境
作为一部海外文学作品,《合欢牡丹》中的女性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多重文化语境,原乡语境、他者(美国文化)语境以及各种文化碰撞产生的新质语境,这些不同性质的语境是女性意识产生的土壤。
1.1原乡语境
原乡语境是指小说中民族文化的流露,以及中国元素的出现。《合欢牡丹》中的女性都是因为丈夫或自己留学移民到美国的,她们有20年左右的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中国文化对她们的影响根深蒂固,以文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原乡语境折射出传统的中国女性意识。
江岚是中国古典文学博士,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其作品《合欢牡丹》充满了中国元素。书名《合欢牡丹》取自唐代诗人徐仲雅《句》中“平分造化双苞去,拆破春风两面开”,小说意象牡丹在书中多次出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红旗认为:“小说‘合欢牡丹’以唐代诗人徐仲雅一首诗的题目来命名,显示出江岚对‘母国文化’的情有独钟,并深谙牡丹丰富的象征寓意与女性精神符旨的联系。”[3]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并且冠压群芳、卓尔不凡,是百花之王,暗含“中心”之意。《合欢牡丹》中的几位女性在中国的生活颇类《红楼梦》大观园的感觉,都是才貌双全、众星捧月般的人物,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中国,她们是交际圈中的“中心”,暗含着对华人在中国主体地位的肯定,衬托了对这些华人处在美国边缘位置的失落。
《合欢牡丹》的语言典雅清丽,诗意颇浓,正如文学评论家刘俊所说:“江岚以研究古典文学见长,小说语言中经常出现的古典诗词的化用,使她的小说在当代题材中,流淌着古典的文化气韵”。《合欢牡丹》的人物塑造以及场景描写明显地在模仿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沈玉翎的多愁善感、情思敏锐与林黛玉很相似,沈玉翎与刘家鼎幽会地点华丽精致的渲染与铺陈,有模仿《红楼梦》中各种富丽堂皇场景描写的痕迹。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刘登翰也说,《合欢牡丹》颇有《红楼梦》的韵味。王红旗认为:“来自故国‘原乡’的文化记忆、牡丹传说,均成为华裔女性在异国‘他乡’认识、反省、积蓄自我生命活力,从‘小我’蜕变成‘大我’的文化‘母乳’”[3],该评价可谓一语中的。江岚在博客中也写道:“写作动机很单纯的女作家们,总觉得她们‘原产于中国’的文化根本,她们被连根拔起的环境移植……她们色彩与姿势各异的盛开,都是在异乡异质的文化语境里落地生根后昂扬恣意地绽放,挥洒着中华文化精神难以磨灭的芳华,一如牡丹。”[2]可见原乡意识和家国意识在江岚的小说里占据着很大的分量。
1.2他者语境
《合欢牡丹》中的华裔女性毕竟身处美国这个国度,美国是另一类政治文化集体,有着迥异于中国的特点,小说中的人物不可能完全游离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之外,而是时时刻刻都浸润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里,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正像江岚所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异质文化观念不断认知不断适应,对自身文化传统不断回望不断反思,同时又从不同角度对二者的优劣异同不断对比不断探求……都因此染上了浓重的东西方文化相交错、相印证、相融合的底色”[4]。
美国就像是一座城堡,空有华丽的外形,她们在城堡中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自己的爱情婚姻和事业,并面临着无爱婚姻的焦虑,然而,美国仍然对她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是登上去就下不来的地方,移民俨然已经跨越了根系故国、落叶归根的历史阶段。新移民不是因为大陆历史政治原因而被迫迁徙异土,而是为了生活、学业、理想的更高追求来到美国,其实质是与厮守故土理念的相悖,“家园”的含义于他们已然发生变化,异国变成“落地生根”的新家园。江岚在广西师范大学做演讲时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出国是一种主动、自我的选择,华文女作家的乡愁和边缘人意识都在淡化,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由求异转为求同,这是与前代华人作家最不一样的地方。因此,他者文化和他者语境对华人意识及其身份认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王涓涓在准备离婚时,面对以后无学历、无工作的生存压力,无奈地喊出“大不了回国”这句话。然而正像作者所说:“‘大不了打道回府’这种话,如同人家在刑场上面对屠刀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听起来慷慨激昂,事实上一点底气也没有”[2]。不管美国的华裔女性当初为什么来到美国,美国已经成了她们生存发展的第二片土地,于故国的人来说,她们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人士。不管什么原因的“打道回府”,都会被加上一层“不如意”的标签,回国后她们必定面临无法言说的尴尬。因此,美国不仅仅是“他者”,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我”的象征。
这种“他者语境”给了书中人物更多的与原乡文化对比、衬托之后的反省。例如,“同性恋”是一个于中国人来说很难接受的现象,然而在以“文明开放”象征的美国,人们基于更大的文明包容能力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同性恋”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与此同时,已经接受自由开放西方观念的方若施,在面对雍容端庄的孟李秀竹传统的中国香火观念时,不禁莞尔,这些无不是两种文化观念碰撞出的火花。可以说,《合欢牡丹》中的女性形象是在“他者语境”中建构自我,或者变他者异质为自我本体。
1.3作者个体语境
除却原乡语境和他者语境,任何作品都是作者价值观和思想意识的彰显,因此,不可避免地也会面对作者的个体语境。尤其是女性作家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会有更多自我经验的呈现。法国女性主义者艾来娜·西苏就说过:“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5]。
异乡的漂泊经历,使得江岚对移民的生活状态有了全方位的了解和认知;政治文化的差异引起的身份认同焦虑,使得海外移民的生存境遇展现出多重色彩。同时,女性作家的身份使得江岚格外关注移民女性,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作家对女性人生命运的深刻见解。作家通过对女性情感空间的深层次挖掘,揭示了女性强烈的生命意志和女性意识。
江岚既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女性意识,也深受西方平等自由和解放个性的理性主义、女性主义的感染,《合欢牡丹》对女性婚姻爱情的讴歌,反映了江岚重构女性婚姻爱情的勇气,也是后现代语境下对爱情婚姻本来意义及未来意义的反思和探索,其本质是探索人在婚姻爱情上以何种状态存在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江岚超越了仅仅停留在两种文化语境上探讨华人女性婚恋问题的单一层次,向着人的更深层次的本质存在积极进展。
女性作家的身份使得《合欢牡丹》不可避免地闪烁着女性主义的色彩。多数女性主义者认为,反对父权制歧视女性的方法不是抹杀性别差异,而是解构性别等级制,也就是消解男权社会中性别差异所承载的意义和文化。江岚的《合欢牡丹》充分展示了女性的性别特征,比如精致的相貌,姣好的身材,细腻的情感,渴望爱与被爱,以及对男人与生俱来的依赖感,同时也质疑了章明、秦中凯作为男人所认为的女人的社会文化意义,比如“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女人隶属家庭、男人打拼事业的意识,重责任轻感情的中国男性传统意识,等等。
作为华文小说,《合欢牡丹》中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原乡语境、他者语境和作者的个体语境,这三种语境相互拉扯着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使得女性的身份认同显现出多元文化色彩。
2 多重文化语境中的女性意识
在这些多重语境的关照下,《合欢牡丹》中的女性意识在女性身体和灵魂、文化根性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
2.1灵与肉的合一
灵与肉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理论界研究的一个话题,一些学者将灵魂与肉体分开来讨论,认为二者是异质的,分别属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范畴。而在《合欢牡丹》中,恰恰彰显了婚姻爱情中灵肉合一之美。
王涓涓与章明之间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因为从一开始王涓涓就将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截然分开了,灵魂随着背叛的爱情萎靡消逝,肉体却嫁给了章明。章明即使没有家暴,这桩婚姻也是一潭死水,早晚将风雨飘摇,其实质性危机不在家暴,而是王涓涓在婚姻中的灵肉分离导致章明工作压力之余又出现的自卑心理和生活压力。面对一个永远高高在上、心如死灰,就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冰美人,章明说:“在她面前我永远无法证明。她永远高高在上,对我的鄙夷深入骨髓,她甚至不允许我轻易碰她一下……即使在床上,她也是一副慷慨就义的样子,仿佛每一次都是在对我施舍什么。”[2]灵与肉的分离,是王涓涓婚姻失败至关重要的原因。
与此同时,作者通过主人公沈玉翎和刘家鼎的婚外恋,肯定了两性关系中灵肉合一的重要性。刘家鼎在与林锦凤不幸的婚姻生活中逐渐丧失了性能力,他看过医生,找过小姐,通通没有用,“他作为男人的生理机能已退化,他只能承认自己老了,无可奈何地老了”[2]。然而,在与沈玉翎接触后,他自己也惊异于身体的反应,他恢复了属于男人的那种能力,以及伴随着那种能力而来的男人的自尊,因此他对沈玉翎说:“你给了我一个奇迹,枯木逢春的奇迹”[2]。
随着不幸婚姻和岁月老去的不只是刘家鼎的身体,还有他的灵魂。多少年来,刘家鼎在商场上摸爬滚打,早已习惯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人与人之间有目的的交往方式。他“自认为处在这一辈子的流金岁月,只要按部就班地走下去,生活里再也不会有什么事能令他大惊小怪”[2]。沈玉翎的爱恋使他重新对人生燃起热爱,为他展开生命里荡气回肠的华彩乐章,他“忍不住要痛恨,痛恨为什么不能用黄金万两,买一个太阳不下山?!”[2]刘家鼎的灵魂在与沈玉翎的关系中实现了与肉体的合一,沈玉翎也惊异于刘家鼎带给她的性爱的高潮体验,他们实现了灵与肉的交融,只有心灵与肉体之间绝对的彼此忠诚,才能实现这种交融。
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女性更多的是一种生理意义和生殖意义上的存在,是男性的性欲工具,是使家族香火延续的生殖机器,这两方面作用强调的其实仅仅是在女性肉体上的作用,女性的精神及灵魂则一直处于空白状态,好像并不存在。小说表达的灵与肉的合一,本质上是对中国这种潜移默化的传统论理价值的批判与反思,也是对人性的彰显。
2.2女性意识的文化根性和异质属性
江岚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江岚认为,牡丹挥洒着中华文化难以磨灭的芬芳,这在《合欢牡丹》中体现得也特别明显。当然,《合欢牡丹》中的女性意识不可能不受到西方文化(他者)的浸染,会在中国文化根性的基础上,也显示出异质属性。
书中的女性意识表现出强烈的中国传统女性意识,例如王涓涓的“女性献祭”意识、方若施的“婚姻归宿”意识。作为《合欢牡丹》中主要的女性形象之一,王涓涓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她以成为“贤内助”作为女性的“职业工作”。她一门心思争当贤内助之天下典范,在章明抱怨她不出去工作时,她竟然说:“操持家务才是女人的天职和本分”,还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古有明训,玉翎出去工作也是她自己的选择,不是被什么人逼的”[2]。王涓涓的生存哲学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献祭传统,其实质是对女性依附于男性的肯定。作家江岚最终否定了王涓涓这种生存哲学,这说明,中国传统的女性献祭伦理已不适应开放上升中的现代社会,在西方理性主义、女性主义的包围中,古老的中国传统女性意识必将消失。为此,小说安排了王涓涓离婚后迅速融入紧张充实的工作生活、迅速成长为成功职业女性的情节。
方若施是《合欢牡丹》中引人注目的一个女性,她特立独行、坚强刚毅,正如小说中所写的:“这就是方若施……性格独立磊落;能吃苦,不流泪。人生的旅程当中若不幸与艰难困苦短兵相接,也只当一脚踩到了狗屎,打落门牙和血吞,照样仰头挺胸,横行竖过”[2]。然而,细读之下,方若施也不过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女性伦理影响的女强人。到了剩女的年龄,她本能地开始感到焦虑,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她本能地选择了很有家势的孟繁星,所谓“青蝇之飞不过数武,附之骥尾可至千里”“从此她不必单凭自己一股牛劲往前冲,不必担心撞了墙也无人搭救,孟家将是她的坚强后盾”[2]。在定亲会上,韩悦纳闷方若施怎么带了俗气的全套纯金首饰,赵明中嘀咕戴了孟家祖传首饰的方若施将从此失去自由。方最要好的朋友沈玉翎感叹这才是方若施真正想要的,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一直等待直至青春逝去的代价,沦为剩女的代价。方若施出类拔萃,却不惜放弃一直孜孜以求的事业,婚后做全职太太,这仍然是一个“依靠男人”“借男人彰显自己”的女性,与一般女人并无异样。
书中女主人公沈玉翎是一个有着独立工作、业余兴趣,敢于追求爱情自由、个性解放的新女性的代表,应该说是最能体现西方现代观念的女性代表,然而她也时时焦虑婚外恋情的曝光,还说这要是在以前的中国是要进猪笼的等言语。沈玉翎既有着中国女性婚姻伦理的传统,又有西方女性自由解放的思想,体现的是两种文化的交融。
3 与“他者”共融——平等对话基础上的身份认同
《合欢牡丹》在呈现女性意识多元性的同时,也显示了女性身份认同的困难和焦虑,所谓“合欢”,本身就意味着多元共存,这就使当代华人女性的身份认同显得暧昧,或者说这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否命题,所谓的身份认同只是女性存在状态本身。然而,新移民女性的身份认同焦虑虽然作为事实成为客观存在,但人们不可一味地去迎合西方思想,遗忘历史,摈弃过去,否则,必将失去自我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很难解释和确立自我,并重新失去“自我”,导致新的身份认同危机,沦落到西方强势权威的边缘。如果能合理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不回避西方先进的思想观念,在保持自我的同时与“他者”共融、平等对话,就能减轻或者消除身份认同的焦虑,达到一种“君子和而不同”的美好状态。
新移民是在中国生活过一段岁月的中国人,因此不可能完全抹杀掉他们思想深处的中国传统论理、习惯、风俗等痕迹,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很不一样。正如冯烨在《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他者”研究》中所说:“对于新移民来说,‘中国’不仅代表居所含义地理空间概念的出生之地,而是意味着一种具有养育、恩泽、回归的慰藉意义的情感归属与心灵皈依,因此,当北美新移民作家去国离家后,对故园的书写就成为其作品中重要的主题内容。”[6]既然无法擦除故国的记忆,就不妨吸取其中有价值的成分,为我所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好多中国人的古老民族传统只要不过度,就会升华成一种很有魅力的人格力量。《合欢牡丹》中,方若施遇到困难时打落门牙和血吞,照样仰头挺胸,横行竖过的精神,其实质是在中国就养成的恬淡隐忍的性格。恬淡隐忍,只要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愚昧麻木,就不失为一种美好的品格。在严歌苓的代表作《扶桑》中,扶桑尽管饱受苦难的折磨,沦为妓女,但仍然散发着东方女性神秘、随遇而安、吃苦耐劳、宽容隐忍的魅力人格,并成为白人贵族少年克里斯忘我的爱恋对象。但是,我们也不可一味地沉迷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之中,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不合时宜的女性价值观念,例如《合欢牡丹》中王涓涓的“嫁夫随夫”的献祭传统,就是应该早早被抛却了的。
与此同时,新移民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为了更高的理想追求而自愿移民美国的中国人,他们脱离了前一代移民在政治历史原因下的被迫背井离乡,本质是对“厮守故土”观念的背离,其“文化乡愁”的情结也越来越淡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飞跃提升,美国也改变了对华移民政策,华人在美国的际遇也相应地改善了很多。通过各种途径移民美国的华文女作家,远离故土之后的漂泊无助感和被边缘化的消极情绪亦被消解许多,个体积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愿望提升。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同区域之间来自文化上的对抗和心理隔膜逐渐降低,华人可以自由往返于美国和大陆之间,领略中美不同的文化风情。以上各种原因,使得北美华人新移民们往往一边回忆、留恋故国,一边在新土地上毫不迟疑地前进、发展,即使遇到艰难困苦,也不会再有回国躲避的意识,而是理智地将自己的生命移植到新的土地上,就像是《合欢牡丹》中的牡丹意象一样,须得连根拔起移植,才能获得新生。然而总归是先有了牡丹这个物质意义上的存在,才有了之后的所谓移植和新生。新移民女性在保持自我的同时,也须汲取西方先进思想观念,与“他者”共融,只有如此,方能在新的环境中游刃有余,避免单一身份认同导致的尴尬。
[1] 赵颖.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女性写作[J].小说评论,2012(4):197-202.
[2] 江岚.合欢牡丹[M].厦门:鹭江出版社,2016.
[3] 王红旗.华裔女性精神生命的花朵——解读旅美女作家江岚的新长篇小说《合欢牡丹》[J].名作欣赏,2015(31):68-72.
[4] 江岚.《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出版[N].文艺报,2016-7-8(4).
[5]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M]//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6] 冯烨.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他者”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4.
ONTHEFEMALECONSCIOUSNESSANDIDENTITYINBLOOMINGASAPEONY
JIANG Haoshuang
(SchoolofArts,GuangxiUniversity,Nanning530004,China)
Several distinctive female characters are portrayed inBloomingasAPeonyand as green horns in the new era, these female characters are scattered groups on the edge of other countries, disclosing their distinctive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he blending of the two cultures, revealing the universal absence of love in the life of the women who live in a foreign land, implying the author's experience of solitude as the essence of human existence.The paper focuses on multi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book such as the original context, context of the others, the author's individual context, analyzes the conflict between spirit and flesh, cultural root and heterogeneous attributes in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of Blooming as A Peony, and then discusses the problem of identity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new immigrant women.
BloomingasAPeony; female consciousness; identity
2017-07-06
蒋好霜(1991- ),女,河南漯河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
1673-1751(2017)06-0075-05
I106.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