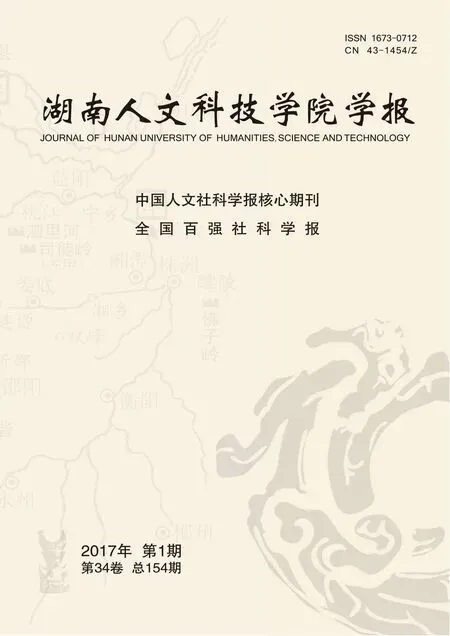论莫言作品中侠客形象的反传统性
彭 玲,周智敏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文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
论莫言作品中侠客形象的反传统性
彭 玲,周智敏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文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莫言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侠客形象,这些侠客形象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性,其反传统性主要体现为在行为基础上对“义”的反叛、在体貌武艺上对“强”的颠覆、在精神风貌上对“豪”的消解三个方面。莫言对传统侠客形象的颠覆,与传统作家的影响、外来思潮的导引以及其民间叙事立场息息相关。从莫言笔下的侠客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其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态度、对传统侠客文化的矛盾心理及其特有的平民美学观念。
莫言;侠客形象;反传统
侠客之所以不同于常人,其根本在于“侠”。“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书中将“游侠”与“私剑”并称[1]555,又说“带剑者”的特征为“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1]564。在这里,韩非子是以侠客的行为来界定“侠”的概念的。其后,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侠”的概念进一步补充:“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2]与韩非子相比,司马迁更精确地写出了侠客的三个特征:其一,“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其二,救人于厄、不在乎生死的勇敢;其三,施恩不图报、“羞伐其德”的谦卑。这三点可以概括为侠者的“义”。到了东汉,荀悦再论“侠”时又别有拓展,认为侠者“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3]。这里的“侠”需要“立强于世”,即“义”之外,还需要“强”,“强”既指强健的体魄又指高强的武艺,否则就无法做到“立强于世”。以后的魏晋至唐,“侠”多见于文人诗歌,因此,“侠”也就沾染了魏晋慷慨放浪的风骨和盛唐豪迈高扬的气格,具有“豪”的特点,并且绵延后世。至唐末,“侠”的概念已基本完善,传统侠客的形象也基本定型,即综合了“义”“强”“豪”三方面的特点。三者中,“义”是“侠”的行为基础,“强”是“侠”的行动要求,“豪”是“侠”的精神面貌。
莫言一反传统,在其系列作品中创造了与传统侠客不同的侠客形象,其侠客形象的与众不同主要体现在行为基础、体貌武艺、精神风貌三个方面。首先,在行为基础上,莫言并没有把“义”作为行侠的基础,有的侠客行为甚至与“义”相悖离;其次,莫言作品中的侠客形象在体貌武艺上与“强”差之千里;再次,莫言笔下的侠客形象在精神风貌上也不具有“豪”的特点。莫言对传统侠客形象的颠覆,与传统作家的影响、时代思潮的导引以及其民间叙事立场息息相关。从这些侠客的形象上,我们可以看出莫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态度、对传统侠客文化的矛盾心理以及其特有的平民美学观念。
一、侠客形象反传统性之表现
(一)在行为基础上对“义”的反叛
在传统侠客观念中,“义”是侠在处事上至为重要的准则。明代宋濂谈到“侠”时说:“受恩能尽死,义重身则轻。”(《义侠歌(效白乐天体)》)“义”所包含的既有私人之间的小义,又有家国天下的大义,无论大小,侠客之行为若不从“义”出发,就不可称“行侠”,同样,没有行侠之事,就只能妄谈“侠客”。因此,“侠”与“义”有着至为重要的依存关系。但是,莫言在其创作中消解了“义”与“侠”之间的重要联结,使“侠”对“义”的要求变得十分边缘化。例如,在《我们的荆轲》中,作为侠客的高渐离说:“出名之心,人皆有之。”[4]8“你可以批评一个侠客的剑术,而不应该去议论他的道德。”[4]9这里,首先强调了“名”之于侠客的重要性,然后说侠客的道德不应议论。前者直接摆脱了“义”对侠客行为的束缚,后者为这种摆脱提供了有力证明。在传统中,人们对侠客有着“立节操而显其名”的要求,而莫言颠覆了这种要求,使其“显其名而无论其节操”。先决条件中的“立节操”,也即传统侠客要求的“义”被莫言边缘化了,而传统侠客所不齿的“名”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正是在这样的准则之下,荆轲求的不是刺杀成功的“义”,而是刺杀失败的“名”。除了荆轲的行为与“义”相悖离外,《酒国》中余一尺“我要肏遍酒国的美女”[5]145的誓言,也直接与“义”的要求形成冲突。
(二)在体貌武艺上对“强”的颠覆
传统侠客往往强健威猛且具备高超的武艺。但是,莫言在塑造侠客时,大胆颠覆了传统侠客在身体素质和武艺要求上对“强”的要求,其笔下的侠客在身体素质上或矮小,或残疾,或极度平庸,武艺也表现出参差不齐的水平。如在《酒国》中,余一尺直接被塑造成一个侏儒,“二尺左右的身躯”[5]142,还“生着一种古怪的皮肤病,遍体鱼鳞,一动流黄水”[5]100,“像个妖精”[5]172。这与传统侠客所拥有的正面、高大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同时,以往文人墨客所吟咏的侠客的潇洒形象在此也被嘲弄——余一尺的形象古怪、阴森,甚至带着猥琐。在另一部作品《丰乳肥臀》中,孙大姑也一反传统侠客之常态,出场的时候“瘦骨伶仃、面容清癯”[6]16。颠覆更为彻底的是孙大姑的死,它直接构成了莫言对传统侠客赖以生存的“武”的反讽。孙大姑轻松地给了两个日本兵耳刮子的举动,显示了传统侠客对于武艺的得意与自豪,可是一转眼又被日本兵开枪打死,“栽倒在上官家的穿堂里”[6]7。莫言对这种死亡方式的轻描淡写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由前面对孙大姑的神勇描写转而变成了一种戏谑。
也就是说,莫言笔下的侠客形象并不具备潇洒身姿,即使有横槊于世的武艺,被置身于枪炮之下也显得无能为力。莫言宣告了武侠“力折公侯”时代的结束,同时也完成了自身冷幽默式的侠客形象的第二层颠覆。
(三)在精神风貌上对“豪”的消解
传统侠客在精神风貌上一般具有“豪”的特点。这里的“豪”有两层意思,其一,指豪迈不羁的性格,昂扬奔放的的激情;其二,是对人生远大理想和抱负的追求[7]。这两者密不可分。传统侠客中的多数形象都具备这种特质,如《虬髯客传》中的李仲坚,《水浒传》中的武松、鲁智深,《霍小玉传》中的黄衫客等。与之相反,莫言笔下的侠客则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这种“豪”的气质。他笔下的侠客有的行事踌躇,有的贪婪好色,有的尖酸刻薄,与传统的豪侠气质形成鲜明对比。如《我们的荆轲》中,犹豫与怀疑代替了侠客的豪迈和昂扬。田光的自杀,是一种对自己身体能力的极度怀疑;荆轲的犹豫,是一种侠客不该有的跌宕畏葸。此外,高渐离对狗屠的感慨,秦舞阳的临阵而惧都是对豪侠气质的悖离。在莫言笔下,传统侠客那种超脱于凡夫俗子的豪迈气质被消解,一个个被拉下神坛变成普通人。除了上面提到的田光、荆轲等人外,《丰乳肥臀》中的孙大姑也被揭下“豪迈”面纱,以一种庸常的面貌出场。孙大姑的出场是在和孙子们玩围剿公鸡的游戏中展开的,与普通老太无异。随后,在去上官家接生的情节里,孙大姑又对吕氏进行讥讽,侠客的严肃与神圣意味消失殆尽。与其说孙大姑是一位侠客,不如说是一位普通的村野农姑,有着村野农姑的尖酸刻薄、无聊乏味,而没有侠客的豪情满怀、义薄云天。
二、侠客形象反传统性之探源
莫言对传统侠客形象的颠覆并非无意之举,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一)传统作家的深刻影响
莫言曾多次提及鲁迅对他的影响。例如在创作上,莫言经常模仿鲁迅的写作风格:他多次在作品中营造出与鲁迅小说类似的悲凉、滑稽的氛围,有时甚至使用相似的情节来构建自己的故事。这种模仿使得莫言笔下的侠客形象带上了鲁迅式的反传统特征。莫言曾说:“读完了这篇小说(《铸剑》),我感到浑身发冷,心里满是惊悚。”[8]可见,《铸剑》给莫言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莫言笔下,多数侠客都有宴之敖的影子:这些侠客行侠与宴之敖一样不以“救人于厄”为目标,而是为报仇而报仇,表现出一种无意识的自觉。如《酒国》中余一尺救肉孩,《月光斩》中神秘侠客“杀”县委副书记等情节,都是莫言对鲁迅写作风格潜意识的靠近。莫言的这种靠近也使其笔下的侠客有着传统侠客“从未有过的从容、充裕、幽默与洒脱”,以及“鲁迅固有的悲凉”[9]。
除鲁迅之外,在侠客形象的塑造上对莫言影响最大的当为蒲松龄。莫言不仅在多个公开场合说自己深受蒲松龄的影响,而且还在与友人的私信中说道:“《聊斋》是我的经典。”[10]不难看出,《聊斋志异》在莫言心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他的创作也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就包括莫言对侠客形象的塑造:首先,《聊斋志异》中有近1/10的篇目涉及了侠客[11],听着聊斋故事长大的莫言正是从这些故事中获得传统侠客的第一印象。其次,《聊斋志异》中某些看待侠客的观点也直接影响了莫言笔下侠客形象的塑造。不过,莫言并未照搬《聊斋志异》中的观点,而是对其辩证地看待,吸收其中新颖的部分。如莫言对荆轲这个历史人物的看法,其实就是对《聊斋志异》中《聂政》《商三官》《田七郎》②等篇目重新评价荆轲的直接呼应。在《我们的荆轲》中,莫言既表达了与《聊斋志异》类似的对荆轲行动失败的批判,又展现出现代人对特定历史时期侠客境遇的同情。最后,蒲松龄作品中的奇幻色彩也增加了莫言在塑造侠客时带有玄幻色彩的可能性,因而,莫言笔下的侠客都不是非常明晰的现实主义侠客,而是具有一定魔幻色彩的侠客。
(二)外来思潮的积极导引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的嬗变使得作家们不得不对自身的写作进行思考和改变,不少作家为自己的写作找到新的出口,一时间文坛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例如,韩少功等人对“文学的根”的探索,马原等人对传统文本叙事方式的颠覆,这都是对其写作方向的自主性转变。在这段文坛极为热闹的时期,莫言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但是,这并不代表莫言没有对自身写作进行思考。在军艺学习的日子,莫言进行了大量的阅读,他希望从中找到自己在写作上的出路。当读到外来作品时,他“震惊”[12]了:“这彻底粉碎了我旧有的文学观念。”[13]这促使他摒弃传统写作方式,走上反传统之路。莫言创作的《欢乐》《红蝗》等作品,正是他在反传统之路上踏出的第一步,同时也是20世纪80年代非常典型的、受到外来思潮影响而改变传统创作方式的例子。在他踏出第一步不久后,文学的边缘化问题就逼近了他,莫言陷入困顿:“预感到我不能像别人一样去下海、经商做生意,我知道我还要写作,但很难坐下来。”[14]恰逢此时,社会上兴起了武侠小说的阅读潮,港台的武侠小说大量涌入内地。武侠题材由此进入了莫言的视域,在大量阅读武侠小说后,他开始自己第一部武侠小说的创作。莫言用戏谑的手法将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改写成了一篇45 000字的武侠小说,旧人物阿庆嫂、郭建光都成了身怀绝技、会使暗器的武林高手[15]。但是,这部小说遭到《花城》杂志的退稿,随即被莫言付之一炬,这可视为莫言反传统的一次失败尝试。但莫言没有气馁,不久之后,他就创作了反传统意识更为强烈的《酒国》。在《酒国》中,主角余一尺作为一位豪华酒店的经理,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商品经济潮的受益者,同时也是一位侠客。这个现代与传统身份叠加的形象,集中反映了莫言对这个风云剧变的时代的深刻思考。在其后的作品中,莫言笔下的侠客也经常被设置在类似环境中。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纷繁的文坛环境中,莫言既没有迷失,也没有跟随潮流亦步亦趋,而是在潜心的阅读中慢慢开拓自己的视野,结合自己的经验,灵活地运用外来资源,最后完成了自己在创作上的一次蜕变,走上反传统之路。
(三)普通民众的叙事立场
莫言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写作”[16]67。基于这种立场,莫言很多作品的颠覆性就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在莫言之前,多数作品都是基于知识分子的视角去写作的,“侠客”形象往往被文人化和高尚化。许多作品对于侠客“滥杀无辜”的现象视而不见,以致侠客的传统形象要么极端理想化,要么极度妖魔化,从而备受争议;此外,由于作者的语焉不详或故意设置,侠客的行踪、相貌、日常行为也常常神秘莫测。与此不同的是,莫言的平民叙事立场,使得他笔下的侠客,无论行踪、相貌还是日常行为都变得公开化和寻常化。同时,这种平民立场也决定了莫言对侠客形象的态度——既不将其崇高化,又不将其妖魔化:一方面,莫言以笔下人物狭隘的小农、小市民意识消除传统中崇高的侠客形象认知;另一方面,以人物的朴实情感纠正传统对侠客嗜血、滥杀的偏见。例如《丰乳肥臀》中,孙大姑从进上官家门对吕氏的刻薄反击,到抛弃个人恩怨救助鲁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刻薄并非因为她大奸大恶,而是由于她有着老百姓狭隘的报复心理。同样,其救助的行为也并非出于“赴士之戹困”那样的侠客情怀,而是基于普通民众素朴的本性。
莫言笔下的侠客既狭隘又广博,既尖酸又朴实,与普通民众无异。这些侠客首先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其次才是一个侠客,造成这种写作效果的正是莫言作为老百姓的民间叙事立场。
三、侠客形象反传统性之内蕴
(一)批判现实社会的态度
“关注现实,批判现实,介入现实”是我国固有的文学传统,也是莫言一贯秉承的创作理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日趋上升,莫言也实现了自己“每天吃三次肥肉馅饺子”[16]38的梦想,但他并没有沉浸在梦想实现的喜悦里,而是警醒地看到了经济腾飞的背后,个别官员投机取巧,导致部分底层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的现象。在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现实后,一方面,莫言选择揭露这种贪腐现实,如《天堂蒜薹之歌》里政府官员不顾农民死活控制蒜薹价格,《酒国》里以酒量食量评定官员等级等情节,都是莫言对官员贪腐现象的揭露,都受到莫言无情的鞭挞。另一方面,莫言借助传统中富于正义意味的侠客来为老百姓伸张正义,如《天堂蒜薹之歌》里的张扣和高马,《酒国》里的余一尺和丁钩儿。但是,这些侠客最终都在巨大的黑暗势力下被打击、同化。这体现了莫言清醒的批判意识:既清楚地认识到解决官员腐败不可依赖于传统办法,又认识到侠客自身不可忽视的个人局限。
(二)矛盾的侠客文化情结
在莫言的侠客故事里,悲凉中暗含热忱,尖刻中又蕴惋惜,这种抵牾透露出他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矛盾情结。传统的侠客故事常常以侠客为主角,以侠客的行为牵引故事发展,其行为的终止也意味着故事的结束,而莫言的侠客故事充满了对这种传统逻辑的颠覆。在莫言的笔下,侠客可能作为配角出现,还可能作为身份模糊的人物出现,这使得读者很难准确指出真正承担侠客责任的人物所在。如在《月光斩》中,整个文本包含三个独立的故事系统,每个系统中都有可以称作侠客的人物,但这些侠客的身份又可以被质疑。从可被称作侠客的角度看,莫言对传统侠客形象应具备的某些因素依然相当迷恋。众所周知,传统侠客形象往往和兵器崇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月光斩》中,莫言围绕月光斩塑造了神秘女子和几位为刀而死的铁匠的人物形象,这是莫言留恋传统侠客文化的一种表现;从身份模糊的角度而言,《月光斩》中的神秘女子和几位为刀而死的铁匠都依靠“月光斩”和“侠”产生关系,一旦剥离了“月光斩”这一要素,他们都很难被称之为侠客。
侠客身份的模糊性折射出莫言对传统侠客文化的矛盾态度:在认同中有背叛,在颠覆里又有追认。一方面,莫言对传统侠客文化中一些古老的因子,如武艺、冷兵器等的书写随处可见,由此可以看出,莫言对传统侠客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莫言在情节设置上减少了这些因素的出现次数,弱化了这些因素对侠客正统形象的塑造作用。莫言对传统侠客文化的态度,歌颂与批判共存。作者在谈到《我们的荆轲》时也说:“批判是肯定有的,但同时也有歌颂。”[4]193这正是对这种矛盾态度的注解。
(三)特有的平民美学观念
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创作姿态决定了他朴素的平民美学观。传统的侠客作品由于其题材本身的特殊性,往往和平民主义倾向相抵触,表现出神秘的特点和文人化、高雅化的倾向。莫言则反其道而行之,大胆运用平民化的写作手法对传统侠客题材进行改造,这使得其笔下的侠客形象具有极其鲜明的平民色彩。这种平民色彩在具体的文本中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作品中侠客的生活内容琐碎、庸碌,与传统侠客生活中舞剑、奏箫等具有高雅情趣的生活内容相去甚远。例如在《我们的荆轲》中,几个侠客的生活内容无非是喝酒、吹牛、斗嘴,充满了小市民生活的琐碎与庸碌。更有甚者,狗屠最在意的是“最近绿豆价格大涨、绿豆粉的价格也跟着暴涨”[4]10,这种传统妇孺才关心的琐事却成了莫言笔下侠客在意的事情。其二,侠客的家国情怀被消释,侠客的行为不再为“救人于厄”而服务,侠客的人生追求不再崇高和绝对正义。莫言笔下的侠客,既无大恶也无大善,只具有普通民众朴实、温暖的个人情愫。如《姑妈的宝刀》中,孙家姑妈吟唱着古老的民谣,做着庸碌的农活,俨然一副安享天年的姿态。
综上所述,莫言笔下的侠客形象与传统文化中的侠客形象形成强烈反差,既体现了莫言独特的审美追求,也为当代及后世侠客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方向,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和文学史意义。
注释:
①《聊斋志异》中表现蒲氏荆轲观的作品如:《聊斋志异·聂政》:“余读刺客传,而独服膺于轵深井里也……至于荆轲,力不足以谋无道秦,遂使绝裾而去,自取灭亡。轻借樊将军之头,何日可能还也?此千古之所恨,而聂政之所嗤者矣。”《聊斋志异·田七郎》:“七郎者,愤未尽雪,死犹伸之,抑何其神?使荆卿能尔,则千载无遗恨矣。”《聊斋志异·商三官》:“然三官之为人,即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
[1]周勋初.韩非子校注:修订本[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2]司马迁.史记:评注本[M].韩兆琦,评注.长沙:岳麓出版社,2016:1693.
[3]荀悦.两汉纪[M].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158.
[4]莫言.我们的荆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5]莫言.酒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6]莫言.丰乳肥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7]周先慎.侠客精神漫议[J].寻根,2003(4):38-39.
[8]莫言.莫言谈《铸剑》[J].鲁迅研究月刊,1999(8):44.
[9]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35.
[10]兰传斌.莫言与蒲松龄和《聊斋志异》[M]∥杨守森,贺立华.莫言研究三十年:下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327.
[11]张曼.浅论聊斋志异中侠客形象特点[J].青年文学家,2016(11):61.
[12]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加西亚·马尔卡斯和福克纳[M]∥杨守森,贺立华.莫言研究三十年:上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316.
[13]叶开.野性的红高粱:莫言传[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253.
[14]莫言,王尧.与王尧长谈[M]∥莫言.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15]李桂玲.莫言文学年谱[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121.
[16]莫言.用耳朵阅读[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责任编校:彭巍颐)
On the Unconventional Images of Xiake in Mo Yan′s Works
PENGLing,ZHOUZhi-mi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udi 417000,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1980s and the1990s, Mo Yan built a series of Xiake (swordsman) characters in his works. These character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s as they do not conduct themselve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virtue of righteousness; they are far from being strong in terms of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martial arts; and they are neither wild nor ambitious. Mo Yan′s untraditional characterization of Xiake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writers, the inspiration of foreign thoughts, and the viewpoint of the writers′ folk narrative. From these Xiake characters, readers learn Mo Yan′s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s the social realities, his contradictory ideas about the traditional Xiake culture, and his special aesthetics as an ordinary man.
Mo Yan; images of Xiake; unconventional
2016-12-06.
彭玲(1979—),女,湖南宁乡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学理论、美学;周智敏(1995—),男,湖南涟源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文学院2013届本科生。
I207
A
1673-0712(2017)01-008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