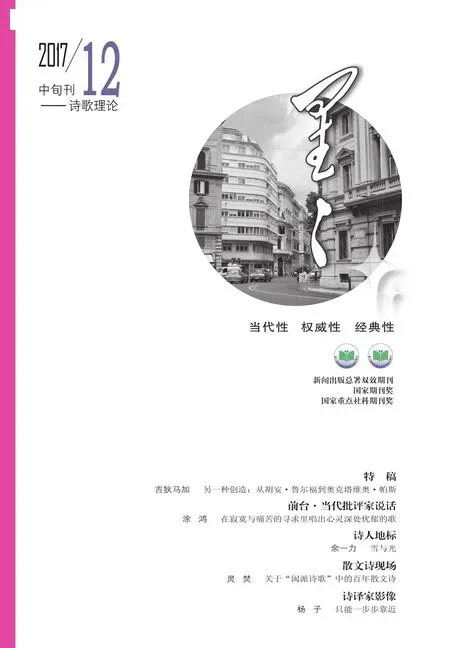“刺入”时间的“尖音符”
——保罗·策兰对王家新“晚期”诗学理念与诗歌创作的影响研究
孙云霏
保罗·策兰,20世纪中叶德语诗坛的杰出诗人。1920年11月23日生于东欧多民族集居区布考维纳省首府切诺维茨的一个犹太家庭,自幼受母亲影响将德语奉为母语。1941年纳粹党卫队占领切诺维茨,大肆迫害、屠杀犹太人,策兰一家均被抓入集中营,其父死于痨病,其母被纳粹枪决。策兰于1944年获得保释并于次年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1945-1947),后途经维也纳(1947-1948)并结识奥地利女诗人英格博格·巴赫曼,1948年移居法国巴黎(于1955年获法国国籍),并于1951年结识法国艺术家吉泽尔·德·勒斯特让热,一年后成婚并生二子(长子仅存活30小时)。1970年投纳塞河自尽。策兰生前共出版《骨灰盒之沙》(1948)、《罂粟与记忆》(1952)、《从槛到槛》(1955)、《语言栅栏》(1959)、《无人玫瑰》(1963)、《换气》(1967)、《线太阳群》(1968)七部诗集,去世不久出版《光之逼迫》(1970)、《雪之部分》(1971)两部诗集。1986年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策兰诗文集》,1997年出版《策兰轶诗和遗诗》、《策兰早期作品》。目前国内译介的作品有《保罗·策兰诗文选》(王家新 芮虎译)[1]、《保罗·策兰诗选》(孟明 译)[2]、《心的岁月——策兰和巴赫曼的通信》(王家新 译)[3],翻译的国外研究著作有《保罗·策兰传——一个背负奥斯维辛寻找耶路撒冷的诗人》(李尼 译)[4]、《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李春 译)[5]。
策兰诗文在欧洲战后日耳曼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一定地位并不断升温,而国内外国文学研究对其诗歌及意义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开掘,以比较文学的视域对其进行审视更是空白。作为策兰诗歌的主要中译者之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写作”的主要倡导者王家新,在其“晚期”诗学理念与诗歌创作中显然受到策兰诗歌的影响,体现于:(1)大量译介策兰诗歌[6],译介过程中伴随着对策兰诗歌的深入理解与对其诗学观的认同;(2)发表大量文章对策兰诗歌进行解读,对策兰诗学观念进行阐释[7];(3)“晚期”诗歌创作中体现出来受策兰影响的症候。由于当下西方各思潮、流派、作品的大量汇入,作品间早已有意无意地充斥着互文性,使得对当代作家进行影响研究、尤其是探寻某一国外作家对其的影响存在厘清和界定的困难。但策兰诗歌的独特性、王家新对策兰诗歌译介和解读的大量文章以及王家新诗歌创作中的某些“症候”使得以影响研究的研究方法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王家新在深入开掘策兰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后,在中国当代的时代语境下,从诗学理念到诗歌创作均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这对于当下如何看待中西文学间关系、如何在吸收和借鉴国外文学思想与表达方式的基础上走出自己的独创之路、当代文学创作的来源与出路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探索性的深刻实践。本文从王家新对策兰翻译观的认同及其对策兰诗歌的翻译入手:王家新认为翻译要洞见“诗的精髓”并在母语中“分娩”出来,并非与原作逐字逐句的对应;从而进入策兰的诗歌观念,探讨王家新对之进行的解读与认同;策兰对王家新诗歌的影响主要在精神维度而不是具体技艺上,但诗歌的形式本身就已承载诗人的写作态度与深邃思考,从文本形式及“形变”的某些症候中,可以解读出影响与异变;“形变”一方面由于诗歌文体以及作家对创造性进行追求的“影响的焦虑”,另一方面则因为王家新始终坚持“中国话语场”观念,对自我、民族、时代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与“承担”,以坚定的“个人书写”的姿态进行不懈的精神追求。
一、翻译:“作为诗学的对话”
诗人策兰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先后译过莎士比亚、魏尔伦、叶芝、豪斯曼、艾吕雅、叶赛宁、莱蒙托夫、曼德尔施塔姆、赫列勃尼科夫、叶甫图申科、马雅可夫斯基、帕斯塔尔纳克、康斯坦丁·斯罗切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翻译:打破传统中规中矩、逐字逐句的翻译模式,将主体性最大程度地渗入译文当中,改变语词词性和语词间的连接方式、句法结构、诗节形式等,以对话的态度完成“解释性翻译”。王家新在《从“晚期风格”往回看——保罗·策兰对莎士比亚的翻译及其对我们的启示》中例举:
“原诗的第七句、第八句、第十句的后半句、第十一句、十二句分别为:
Yet what of thee thy poet doth invent
He robs thee of and pays it thee again.
…beauty doth he give,
And found it in thy cheek;he can afford
No praise to thee but what in thee doth live.
然而,你的诗人所创造的
那从你劫走的,会归还于你
他所给予的美,
又在你的面颊浮现;他不能赞叹别的
除了在你身上那活生生的一切。
策兰对后三句的译文为:
…er kann dir schoenheit geben:
Sie stammt von dir-er raubte,abermals.
Er ruehmt und preist: er tauchte in dein leben.
给你他能够给予的美:
而它来自于你——再一次,他窃取。
他赞颂并获取:他突入你的生命。”[8]
策兰将第八句的“rob”挪到第十一句,对语词进行浓缩,使得诗歌节奏从深沉抒情变得简短有力,并以“tauchte”进行强调。显然,这已大为更改了诗歌的原貌甚至原意,但却获得超于莎翁诗歌之外的“黑暗的美”——“突入你的生命”:以有力甚至强暴的“突入”言说生命中不可磨灭之事,不是感觉、印象、回忆,而是在言说的当下就被确指和命名了,在言说的当下就发生了,这种极度的以语词体验生命的方式在策兰的翻译中被创造出来。同时,从翻译的语言形式上也能看到策兰自己的诗歌风格,凝缩、破碎、紧迫的节奏和压抑的氛围。王家新认为,这种翻译使得原文与译文变成“共生”关系,并通过语言的搏斗促成语言更新,从而在语言本身获得黑暗中的力量[9]。概括来说,就是译者并非“忠实”于作者的字面原文,而是把握作者的精神维度,与作者展开诗学对话,并在对话中获得超于自身视域的精神力量,再让语言自行言说出来。在《“盗窃来的空气”——关于策兰、诗歌翻译及其他》中,王家新认同策兰的翻译方式,并指出自己的翻译观:翻译只是通过对话而进行的对于自身存在的确认,同时获得母语的创造性突破,即“一是力图跟自己心爱的伟大诗人保持相近的精神纬度,二是探测汉语的容度的深度。”[10]并在发掘策兰独特的诗学翻译中,深入思考其对当下中国经典译介的启示:传统的“信达雅”翻译模式是否存在弊端?对国外经典进行译介的目的是什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承担的责任与使命是什么?我们有否必要对于语言和存在的关系进行观念更新?这些问题在其对策兰诗歌翻译的过程中不断被提出与思考,希望以此带给中国翻译界一点启示与活力,“在‘五四’前后,翻译对一种新的诗歌语言曾起到‘接生’作用,在此后新诗的发展中,翻译,尤其是那种‘异化的翻译’已成为新诗‘现代性’艺术实践的一部分,成为推动语言不断变革和成熟的不可替代的力量。”[11]王家新从策兰那里获得了自己较为成熟的翻译观,并通过对策兰诗歌的翻译实践之,且在翻译过程中对孟明、北岛等人的译文进行了批评。
王家新为什么能够在众多翻译大家中发出不同的声音?在《喉头爆破音——对策兰的翻译》中,王家新回顾对策兰诗歌的翻译,最初根据汉伯格的英译本,后更为看重乔瑞斯的翻译,原因在于乔瑞斯并不为了美文和通顺而背离原意,相反,通过一些切于原文的语言变动更为透彻地洞见了策兰的语言[12]。策兰语言的本质是什么?策兰诗歌的语言之上承载着怎样的诗学观念?这种语言与诗学观的把握是王家新践履翻译观的翻译实践的前提,同时也是自身诗歌创作的重要精神来源。
一、语言:“刺入”时间的“尖音符”
策兰早期的诗文语言较为规范,音韵和谐,隐喻和形象明晰生动,但五十年代后发生转变:语词大量破碎,语词间深度疏离无法缝合,跳跃性极强,大量出现地质学、矿物学、晶体学、天文学、物理学、解剖学等“无机物”语言,反美学、反人类性、反解读的特点鲜明。这种语言转变是诗人在对语言进行深沉的审视与反思后,艰难地抉择与书写出来的,而正是策兰中后期的语言及其承载深刻地影响了王家新“晚期”的诗学理念与诗歌创作。
策兰使用的语言是极具重量的,而语言使用所呈现的诗歌形式则成为策兰诗歌的独特所在——语言承载策兰深刻的诗学观与生命观。策兰的母语是德语,但造成犹太大屠杀的刽子手的母语也是德语,德语承载着二者共同的文化根基,如此,如何使用语言对奥斯维辛这段历史说话?奥斯维辛时期,音乐被纳粹借来成为鼓动性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诗歌中的音乐性还能传达真实吗?奥斯维辛之后,灾难不断被抒情化书写,被同情性消费,这样的“反思”方式是否具有虚伪性与新的欺骗性?灾难已是策兰的生命,诗人无法选择对其背弃和遗忘,于是,对德语写作的坚持本身就成为一种对待灾难的态度:德语是造成灾难的深层文化根源,但直入灾难并承担灾难的只有德语(使用德语之外的语言意味一种旁观的姿态),它要以自己拒绝自己,拒绝造成纳粹文化的一切可能性根源。策兰中后期的语言拒绝日耳曼诗歌的抒情传统,打破由海德格尔揭示出的荷尔德林的审美源头,甚至拒绝诗歌本身所要求的可读性——可读性在灾难后成为一种普泛的同情和怜悯,而情感宣泄已把历史消费得一干二净,相反,策兰要通过语言“赢回现在”,通过语言直接命名和确指(而非想象、回忆与猜测)灾难与灾难后“真实”的“现在”。“人们可以标上不同的符号:今天的尖音符,历史的沉音符——也有文学历史的——长音符——延长号——属于永恒的。我标上,我别无选择——我标上尖音符。”[13]“尖音符”是一个“刺入”,是对流俗的线性时间的尖锐唤醒,以极具紧缩的方式把握住“现在”并对之进行迫切注视。由此,策兰的语言拒绝审美、拒绝理解,审美与理解只能让人在阅读完后以臆想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道德虚荣;策兰的语言极具障碍性,而恰在这种“窒息”的写作与阅读中,某个时刻被直接确指出来;但策兰的语言又具有致命的精确性,因其诗中的每一个词都是被“赢回”的,是靠“痛苦的精确性”透视出的,能够抵制虚无和情感的混乱。语言“穿过”事件和时代,它不以事后回忆者的姿态“跳过”,当它“穿”过时,便“刺入”时间,“诗歌不是没有时间性的,诚然,它要求成为永恒,它寻找,它穿过并把握时代——是穿过,而不是跳过。”[14]
策兰面对时代以拒绝的姿态“赢回现在”,将正被遗忘和已被遗忘的灾难带到“当下”,他的语言的穿透力就在那真实显现的“穿”之中,在那对于时间精确地“刺入”,在于“刺入”时紧迫的窒息的凝视——这是对历史最深沉、最透彻的把握,是在一般当下对于遗忘的决绝与抗拒。这种由语言所带来的诗学观深刻影响了王家新,使其对于当下中国诗歌写作的“承担”进行反思与开掘:所谓的现代人并不是认识和接受现代这一永久的时刻,而是“选择一种和这个时刻密切相关的态度”[15],以诗歌拒绝一般的当下,沉入生命之底,以“赢回现在”!
二、“凝视”:“拒释性”词语与“慢”动作
策兰以诗歌语言“刺入”时间,也就是对“赢回的当下”进行“凝视”,这种“凝视”首先体现于诗歌中“拒释性”词语的运用。例:
那是一个
把我们抛掷在一起,
使我们相互惊恐的,
巨石世界,太阳般遥远,
哼着。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什么?从语法上看,“那是一个”“巨石世界”,这个世界使“我们”被抛掷在一起并相互惊恐,这样,“巨石世界”似乎是一个隐喻,指涉巨大而封闭的、不可抗拒的被抛境遇,以及境遇中人的惊恐和颤栗。但既然我们生存在这“巨石世界”中,又怎么能够说“遥远”?同时,“太阳般遥远”也可指涉“哼着”,虽然遥远但如同太阳持续发光一样,哼着的声音虽然微弱但不停歇。这个“巨石世界”究竟指涉什么?只能说它通过意义的相互消解成为一个“拒释性”词语——无法通过字面意思、主体经验或是语境进行释义,由此“那是一个”也拒绝着解释,我们从文本中得到的,只有一瞬间的“真实”开敞:“我”作为个体被真实抛入“巨石世界”,“惊恐”这一主体性情绪内在于“我”又是这“巨石世界”自始至终存在的,这时“我”的主体性消失,只有原始的惊恐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并在封闭的“巨石世界”中充斥与弥散。时间性与空间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延展,与生俱来的“惊恐”既是主体的,又是永恒的。再如:
在你的晚脸前
一个独行者
漫游在夜间
这夜也改变了我
某物出现
它曾和我们一起,未被
思想触摸
——《在你的晚脸前》
“你”是谁?“你”可以是一个同伴,甚至是位女伴,但“独行者”立刻否定“你”的 存在,同时暗指“独行者”只能是“我”。这样“你”是指“我”头脑中已逝者的魂灵吗?那么“某物”指涉什么?它曾未被“思想触摸”,意思是现在已然和你和我被思想触摸过了,也可以说“你”已经被“我”用思想触摸过了:死者只能被生者用思想的方式回忆、死亡只能被思考。但“某物”在夜里出现了,当它出现的时候拒绝被“思考”、被理解。“晚脸”在这里是一个“拒释性”词语,它无法用经验进行对应性理解,突兀的呈现也拒绝着语境释义,只是将一种“真实”的时刻揭示出来:在夜的某一时刻,“我”与死去灵魂的“真实”碰触(不再经由思想,而是发生在当下),这时魂灵对“我”显现的就是一张“晚脸”,它如夜一般黑暗而无处不在。因为“拒释”,它无法被理解、无法被转化成其他语言,也就无法因获得情感或审美的满足而以回忆的、猜度的姿态臆想灾难。“拒释性”词语因为突兀的呈现而获得最大限度的“凝视”,从而真实地“刺入”时间,直指灾难的发生——这是策兰通过语言自身承担灾难的态度与方式。
“拒释性”词语对于存在的深入掘进与深刻凝视,在情感、物象、回忆的混乱中保持稳定并精确“刺入”,与王家新的诗学观念产生强烈共鸣,并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吸收与创造:这体现于将策兰名词性为主导的“拒释性”词语变为动作性“拒释性”词语,将“拒释性”名词所带来的时空延展变为“拒释性”动词所带来的持续缓慢。“力量需要物质支撑,注意力需要具体之物来收敛和集聚,当人们集中全力到一件具体可感的实际动作中时,那些漂浮的幻想或是无谓的焦躁不自觉地消失。”[16]这种对于“动作”的“凝视”并以“拒释”的方式呈现,使得某一动作在进行的当下被精确性捕捉并获得语言直指存在的深度与力度,“刺入”时间并在持续缓慢中延展开来,从而获得稳定的精神力量。
整个冬天他都在吃着桔子
有时是在餐桌上吃,有时是在公交汽车上吃有时吃着吃着
雪就从书橱的内部下下来了
有时他不是,只是慢慢剥着
仿佛有什么在那里面居住
整个冬天他就这样吃着桔子
尤其是在下雪天,或灰濛濛的天气里
他吃得很慢,放佛
他有的是时间
仿佛,他在吞食着黑暗
他就这样吃着、剥着桔子,抬起头来
窗口闪耀雪的光芒。
——《桔子》(2006)
“吃着桔子”到底意指什么?诗中持续地、不断地重复着“吃”这一动作,但却始终拒绝我们对这一动作进行具体释义。王家新本人也反对将“吃桔子”明晰地解释出来,甚至以自我解构来强调动作的不可释义性,“比如我写‘去年一个冬天我都在吃着桔子’/我吃的只是桔子,不是隐喻/我剥出的桔子皮/如今还堆放在窗台上”[17]。重要的并非“吃桔子”究竟意指什么,而是这个“拒释性”动作所集中的诗人的“凝视”:在排除情绪、物象、回忆的混乱之后,“吃”凝聚着“他”全部的注意力,是一种生存境遇在当下的全部显现,也就是对时间的“刺入”。但与策兰“刺入”时间直指灾难发生的当下不同,通过反复、持续,动作在时间的展开中被放“慢”了,成为生存这一过程的某种承担方式,并获得着稳定的经验性力量。王家新的动作是一种深刻的选择和承担的方式,不同于“第三代诗人”通过动作来消解意义(比如韩东《关于大雁塔》:“关于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同时通过动作的反复和持续获得一种“慢”的诗学内涵,“这种‘慢’的诗学显然有意识地抵制了那种即兴涂抹式的写作,而把诗歌写作深化为一种冷峻克制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在所谓‘后现代’的众声喧哗里无疑具有它的诗学意义。”[18]
总之,通过动作“刺入”时间、通过“拒释”获得“凝视”,通过持续缓慢延展时空并获得稳定的力量,是王家新对策兰诗歌“拒释性”词语的深入把握和创造性的发展。面对战后战争文学成为人们道德感和同情心消费的对象,策兰通过“拒释性”词语直呈灾难发生的当下,拒绝任何回忆的猜测与臆想;而王家新面临的是中国当代的精神困境:物质性消费大肆纵行的今天,人们已然面临精神的匮乏与存在的虚无,只有通过对“动作”这一与自身确切相连的方式进行深入思考并精确把握,才能承担起一天生活中所需承担之物,并通过反复、持续地在生命之流中发生,进而获得稳定的经验和精神力量,从而承担起全部生命。二者的共鸣之处在于通过“拒释”“刺入”时间,以“赢回现在”。
三、“词语碎片”与“诗片段”
除了直接使用“拒释性”词语,策兰拒绝读者对自己诗歌进行解读的另一方式就是大量的“词语碎片”,即词与词之间的深度疏离,诗歌早已不完整而支离破碎。例:
眼睛之圆在栏杆之间。
荧光虫——眼睑
向上划动,
释放出一瞥。
虹膜——女游泳者,无梦又阴郁;
天,心灰色,一定很近。
斜着,铁插口里
熏烟的木屑。
靠光感
你猜出那灵魂。
(假如我像你。假如你像我。
我们不是曾站在
一个信风里吗?
我们是陌生人。)
砖块。上面
紧挨着,这两个
心灰的笑:
两个
满口的沉默。
——《语言栅栏》
吴建广在《“两个满口的沉默”——保尔·策兰“语言栅栏”的结构分析》中详细考察了本诗的词语结构,将其中的名词分为十个门类:“(1)天文:天。(2)气象:信风。(3)人际:陌生人。(4)视觉:眼圆,眼睑,一瞥,虹膜,光感。(5)动物:荧光虫。(6)宗教/心理:灵魂。(7)神话:伊丽丝。(8)体育:女游泳者。(9)表情:笑,沉默。(10)物事:语言栅栏,栏杆,铁插口,木屑,砖块。”[19]仅是名词便有十个种类之多,且类属之间跨度极大,词语间极为疏离,句法结构被词语间的拼接组合所解构,全诗给人以破碎而无从解读之感。
策兰使用“词语碎片”使得诗歌因释义性的匮乏而返回语言自身。关于“词语碎片”,王家新在一系列文章中呈现出递进的两种解读倾向:(1)“词语碎片”与“无机物”的语言均是为了拒绝“同一性”,呈现为反审美、反人类的特征。奥斯维辛之后,策兰对德语产生深刻的质疑,他拒绝与纳粹同一文化传统的语言抒情性和音乐性,甚至反对语言的“人类性”。于是,在诗歌中他拒绝流畅的表达形式,代之以破碎的、“无机物”的语言(“无机物”本身只能呈现为一堆无意义的“碎片”);(2)它与策兰的“沉默”有关,是“沉默”中发出的“喉头爆破音”。策兰极为看重“沉默”,“是的,诗歌——今天的诗歌——显示,我相信只有间接的——并非低估——选择词语的困难,句法急剧的坡度或为了省略句所作的清醒的感觉,——诗歌显示,显而易见,一个朝着沉默的强烈的倾向。”[20]王家新在《喉头爆破音——对策兰的翻译》中说到策兰的“沉默”与“喉头爆破音”:“但我想,不仅是母亲在集中营的惨死,策兰所经历的一切,都会作用于他的诗学:荷尔德林的疯癫、卡夫卡的喉结核、‘戈尔事件’所带来的伤害、存在之不可言说和世界之‘不可读’,等等,都会深深作用于他的诗的发音。”“然而,也正是在这最终的沉默中,在被历史和形而上学的强暴‘碾压进灰烬里’的那一刻,语言发出了它最微弱,但同时也是最真实、最震动人心的声音——这就是策兰的‘喉头爆破音’!”[21]因为奥斯维辛中的殉难者已然死亡,已然归于沉默,生者发出的任何声音都不再表征真实,语言在此已经“终结”。但“他对他的语言也有所期待和要求:‘它必须穿过它自己的无回应,必须穿过可怕的沉默,穿过千百重死亡言辞的黑暗。……它只是穿过它,它穿过这一切并重新展露自己’。”[22]言说不可言说的“沉默”,以言说作为“回答的沉默”,这种朝向事情本身之真与语言的绝对纯粹的努力,使得言说变得极为困难,甚至只能“爆破”出来。“词语碎片”就是克服巨大的语言之难后的“一息尚存”。
王家新极为看重策兰与语言的搏斗与依存。在《无花果养大的诗人》中说,“策兰的写作,就这样与语言构成了愈来愈深刻的关系……正是在他所进入的词语的‘黑暗’、‘断裂’和‘沉默’中,他承担了语言的诞生、诗的诞生。”诗人只能通过语言对真实予以展示和呈现,诗人注定要返回语言。王家新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同样深刻的关注与思考着语言,通过语言对存在进行承担,并创新出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诗片断”。
“诗片断”最早是王家新在《回答四十个问题》中提出来的。而早在1991年他就创作了第一篇“诗片断”《反向》。其后又创作了《词语》《临海孤独的房子》《另一种风景》《游动悬崖》《蒙霜十二月》《冬天的诗》《变暗的镜子》等,王家新初接触策兰也是在1991年,很难有直接的证据指明是受策兰诗歌对于语言的“紧张”关注所产生的,但在译介策兰诗歌时期频繁进行“诗片断”创作,意在通过“诗片断”强调词语本身——“或许更接近于诗歌的本来要求——它迫使诗人从刻意于形式的经营转向对词语本身的关注。”[23]不能不说受到策兰语言观很大的影响并与之产生共鸣。例:
这即是我的怀乡病当我在欧罗巴的一盏烛火下读着家信,而母语出现在让人泪涌的光辉中……
在你上路的时候没有任何祝愿,这就是流亡。
神学在迫使语言成为启示录,而语言却喜欢教堂外面的阳光,以及那在阳光中迸放的石头。
而生活再一次要求我的,仍是珍惜语言,并把它保持在一种光辉里……
当树木在霜雪的反光下变得更暗时,我们就进入了冬天。冬天是一个黑白照片的时代。
——《词语》
简短而破碎的“诗片断”,语句之间毫无关联而仅以空格隔开,数句统摄在一个诗题之下,有时一个诗句便有一个次级标题。所涉内容极广,天气心情、生活感悟、历史深思、哲理灵光……在日常生活的平凡经历和诗思语言的瞬间突围中获得张力。但正如《词语》这一题目所明示的,王家新的“诗片断”重视的是“词语”本身,通过词语“刺入”时间并展现出一个当下的生存境遇来,“他所提倡的从词语入手,而不是从抒情或思考入手进入诗歌,直接引领诗人或读者对生命与存在的发现,从根本上把握诗歌。”[24]
策兰通过“词语碎片”的方式拒绝德意志的抒情诗歌传统,拒绝语言的可解读性和可阐释性,同时发出“沉默”与“语言”之间极为艰涩的“喉头爆破音”——语言自身与“碎片”的呈现方式就是他对灾难极为深刻的思考;而王家新的“诗片断”同样高度关注语言,以“片断”的方式展现“语言”对日常生活时间的“刺入”,展现当下人的本真境遇(因为存在不可能一直开敞,所以“片断”的唤醒才是人真实的生命状态)。王家新是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对语言问题进行反思:它没有策兰“语言”对于灾难的极度紧张关系,但同样面临着现代消费社会所带来的日常平庸与意义虚无。王家新为语言选择了一个承担点:个人。在个人最本己的境遇中,以语言突破日常生活的重围获得真实的显现,并进而忠诚于自己的时代。
四、“赢回现在”:“个人写作”
王家新“晚期”的诗学观与诗歌创作深受策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敏锐捕捉与深刻洞察策兰独特的语言及语言承载的诗学观和生命观,并通过翻译与策兰进行精神对话;把握住策兰以语言展示的“拒绝”态度,拒绝德语中的一切文化传统、拒绝大众在理解后产生同情从而将历史“消费”,以“拒释性”词语和“词语碎片”的语言形式“刺入”时间,直指灾难发生的当下,从线性时间中“赢回现在”;同时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语言表达形式,即以“慢”动作和“诗片断”来展示人的本真境遇,以抵抗日常生活的平庸和消费时代的精神虚无。
“慢”动作和“诗片断”与策兰“刺入”时间、直指当下相呼应,但更为强调“刺入”时间、展现境遇、获得真实后所拥有的稳定的力量——只有获得这种精神力量才能深入文学与生活的内部,才能对个人与时代进行承担,这与策兰始终以语言“命名”“确认”灾难并保持语言的极度紧张有所不同。究其原因:(1)诗歌文体要求语言具有极高的创造性,在策兰“影响的焦虑”下,王家新要以自己的独特性来进行诗歌书写;(2)策兰的无可复制除了个人因素外,同样源于他所处的时代,而王家新面对的是当下中国的语境,他要对自我与时代进行深入反思,以诗歌书写进行“承担”。
当代诗歌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朦胧诗在九十年代已经落潮,政治话语和宏大主题的暂时退隐并没有带来诗歌发展的乐观态势,取而代之的是商品化时代对诗歌造成的“边缘性”地位,并由此产生对于诗歌本质与写作形式的质疑与论争。在物质丰富而精神虚无的时代,在汉语文化流亡与失落的年代,王家新始终倡导回归生命的真实,重建诗歌的精神,形成独特的中国话语,而这种诗学理想要则通过“个人写作”的实践来“承担”。“个人写作”意味着拒绝空洞的、宏大的时代主题言说,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和个人理性出发,以直视自身的存在来对时代生活进行透视和反省,它既拒绝意识形态,也拒绝大众文化;“个人写作”意味着对时间的“刺入”,意味着“艺术进入了你的最自我的困境”[25],从而深刻洞察人的历史境遇,洞察生命自身真实的开敞与显现,以获得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在持续、反复的思考与透视中趋向稳定,并能够以此抵御时代的虚无,从而对自身生命进行“承担”;同时,当个体真正把握住当下,对当下采取“赢回”的态度,也就把握住了时代的真实,对时代进行着“承担”。策兰诗歌中极度紧张的语言和直指二战灾难是远离我们的当下语境的,当策兰以“拒绝”的态度直现真实,以“拒释性”词语和“词语碎片”的语言形式“刺入”时间并对之进行“凝视”和把握,深刻震撼与影响着王家新,而在中国当代语境下,王家新更为强调稳定的精神力量的获得,以在浮躁的社会进行个人与时代的“承担”,反映在语言上,则是其独特的“慢”动作与“诗片断”的表达形式。“他是一个用生命而写作的人。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里,人们应该怎样面对生活,面对生命,尤其是对命运的承担和对民族的思考。在众多的诗人里,王家新做到了。”[26]
注 释
[1]保罗·策兰诗文选[M].王家新、芮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保罗·策兰.保罗·策兰诗选[M].孟明 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德]保罗·策兰,[奥]英格褒·巴赫曼.心的岁月——策兰和巴赫曼的通信[M].王家新、芮虎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4][美]约翰·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一个背负奥斯维辛寻找耶路撒冷的诗人[M].李尼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5][美]詹姆斯·K·林恩.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M].李春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与芮虎合译《保罗策兰诗文选》(2002)、《心的岁月——策兰和巴赫曼的通信》(2013),及在各刊物上新译的一批策兰晚期诗歌。
[7]包括:王家新.奥斯维辛之后,爱情是可能的吗[J].齐鲁周刊,2016,(29);王家新.翻译作为回报[J].上海文化,2013,(11);王家新.“我证实了你,你证实了我”[N].光明日报,2013-09-08(005);王家新.从“晚期风格”往回看——保罗·策兰对莎士比亚的翻译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文艺研究,2013,(04);王家新.喉头爆破音对策兰的翻译[J].上海文化,2013,(03);王家新.“伟大的嘴仍在歌唱”——从策兰的一首诗谈起[J].扬子江诗刊,2013,(01);王家新.“伟大的嘴仍在歌唱”——从策兰的一首诗谈起[J].西部,2013,(01);王家新.“嘴唇曾经知道”[J].山花,2012,(21);王家新.策兰诗文选[J].文学界(原创版),2012,(10);王家新.“你的金色头发玛格丽特”——德国艺术家基弗与诗人策兰[J].青春,2012,(04);王家新、王东东.盗窃来的空气关于策兰、诗歌翻译及其他[J].上海文化,2012,(02;王东东、王家新.“盗窃来的空气”——关于策兰、诗歌翻译及其他[J].文学界(专辑版),2012,(02);王家新.策兰诗选[J].文学界(专辑版),2012,(02);王家新.阿多诺与策兰晚期诗歌[J].上海文化,2011,(04);王家新.创伤之展翅——读策兰《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J].名作欣赏,2011,(10);王家新.诗人与他的时代——读阿甘本、策兰、曼德尔施塔姆……[J].延河,2011,(03);保罗·策兰,王家新.策兰后期诗选[J].江南(诗江南),2010,(06;王家新.“你躺在巨大的耳廓中”——有关策兰翻译的札记[J].江南(诗江南),2010,(06);王家新.保罗·策兰后期诗选[J].延河,2010,(07);王家新.在这“未来的北方河流里”——策兰后期诗歌[J].延河,2010,(07);英·巴赫曼,保·策兰,芮虎、王家新.心的岁月——巴赫曼、策兰书信集[J].散文选刊,2009,(12);王家新.“奥斯维辛”之后的赋格——中学语文教材诗歌解读与欣赏(二)[J].中学语文教学,2009,(09);保罗·策兰,王家新、芮虎.保罗·策兰诗选[J].诗林,2009,(04);王家新.你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J].诗选刊(下半月),2009,(08);王家新.你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J].人民文学,2009,(07);王家新.无花果养大的诗人[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保罗·策兰,王家新.保罗·策兰诗歌[J].诗选刊,2007,(07);王家新.隐藏或保密了什么[J].红岩,2004,(06);王家新.绝望下的希望[J].书城,2003,(02);王家新.哀歌[J].青年文学,2000,(01);王家新,芮虎.保罗·策兰诗选[J].当代外国文学,1999,(04);王家新.保罗·策兰: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J].当代外国文学,1999,(04).
[8]王家新.从“晚期风格”往回看——保罗·策兰对莎士比亚的翻译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文艺研究,2013,(04):36-36.
[9]参见王家新.从“晚期风格”往回看——保罗·策兰对莎士比亚的翻译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文艺研究,2013,(04):36-42.
[10]王东东、王家新.“盗窃来的空气”——关于策兰、诗歌翻译及其他[J].文学界(专辑版),2012,(02):10.
[11]王家新.翻译与中国诗歌的语言问题[J].文艺研究,2011(10):24.
[12]参见王家新.喉头爆破音——对策兰的翻译[J].上海文化,2013,(03):52-63.
[13]保罗·策兰.子午圈——毕希纳奖获奖致辞[A]//保罗·策兰.保罗·策兰诗文选[M].王家新,芮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96.
[14]保罗·策兰.不莱梅文学奖获奖致辞[A]//保罗·策兰.保罗·策兰诗文选[M].王家新、芮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77.
[15]王家新.奥尔弗斯仍在歌唱——现代性与英雄的一面[A]//王家新.为凤凰找寻栖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
[16]袁一月.王家新2000年以来诗思诗作研究——以“晚期”为切入点[D].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24.
[17]王家新.答荷兰诗人Pfeijffer“令人费解的诗总比易读的诗强”[A]//王家新.未完成的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121.
[18]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16.
[19]吴建广.“两个满口的沉默”——保尔·策兰“语言栅栏”的结构分析[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3.
[20]保罗·策兰.子午圈——毕希纳奖获奖致辞[A]//保罗·策兰.保罗·策兰诗文选[M].王家新、芮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93.
[21]王家新.喉头爆破音——对策兰的翻译[J].上海文化,2013,(03):61-62.
[22]王家新.无花果养大的诗人[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23]王家新.回答四十个问题[A]//王家新.游动悬崖[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206.
[24]王丽.持续的到达——王家新的诗歌世界[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34.
[25]保罗·策兰.子午圈——毕希纳奖获奖致辞[A]//保罗·策兰.保罗·策兰诗文选[M].王家新、芮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96.
[26]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