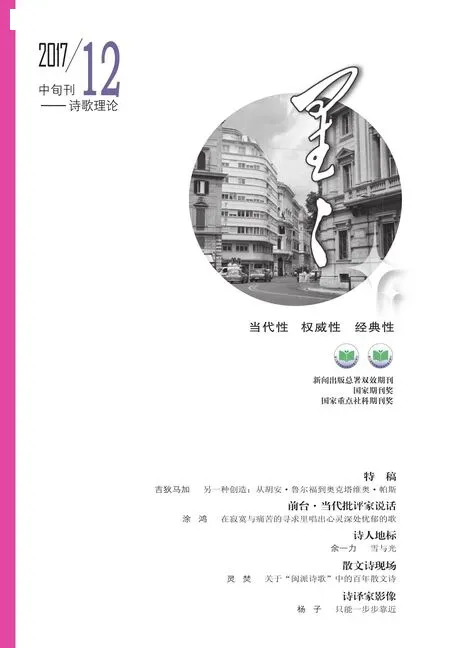雪与光
——王家新的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
余一力
讨论王家新诗歌是有难度的。不仅因为珠玉在前,资料众多,也不只是因为诗人的诗歌创作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更有当下时代对于严肃精神的无意识回避。但文艺批评应当承担必要的责任和难度。当代学者张桃洲指出:“王家新的诗歌写作和诗学思考共同显示出了这个时代所必须的信念:在对时代喧嚣的默默忍耐、承受和抵抗中,将诗歌事业进行到底。”[1]对于这样的诗人,我们不该回避。
一、黑色的树——幽暗诗境与自我流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新诗在表现苦难、尤其是与历史语境和时代特征密切关联的苦难时乐于使用整体性词汇:如伟大、崇高、民族等等。私人化的生活际遇与生命体验要么为时代所抛弃,要么被表述为“低俗”的感官快乐。王家新对于这种倾向是有质疑的,在《回答晋美子的二十五个诗学问题》当中,他提出要有一种对于“大词”的警惕,但也肯定了语言的敏感应当包含一种历史的意识。最终,在谈到自身的诗歌创作时,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也许每一个诗人身上都宿命般地带有一种他那个时代在语言上的规定性和局限性,而他们自己对此是浑然不知的。”[2]这使得王家新在诗歌创作当中很早就开始自觉地与时代和风尚拉开距离。他在《我的八十年代》当中对同时代的诗人有过这样的思考:“作为诗人和叛逆者,也是历史上光辉的不复再现的一代。但是,这只是就诗和他们曾体现的‘诗歌精神’而言……人们与他们所反抗或厌恶的东西究竟拉开了多大的距离?”[3]诗人从这些诗歌流派的方兴未艾和时代的兴奋感当中看到了曾经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远离“红小兵”的酸楚。在《少年——献给我的父亲、母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我的鼻子前,是挥之不去的/福尔马林味/我的眼前,是仍在膨胀的冰”[4]。这种酸楚直透语言,使诗人不自觉地拒绝食肉(吃肉在仪式上兼有吞噬和庆祝之意),主动放弃热闹的人群。他以里尔克的诗为座右铭:“……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将诗歌创作视为孤独终点和秘密精神事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是王家新诗歌创作的一个关键时期。1989年,海子与骆一禾两位诗人的猝然离世,给他以极大震动;而同时期发生在国内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对时代和处于时代当中的每一个个体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1989年冬天,诗人在西单白庙胡同阅读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米沃什,感受诗性对于灵魂的深刻冲击,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一个相信艺术高于一切的诗人/请让他抹去悲剧的乐音。[5]”这是对浪漫历史的过往挥手告别,也是对必然来临的当下诗性的迎接。在个人新集《塔可夫斯基的树》中,王家新选择1990作为他的起点,但他本人却于1992年踏上了前往英国的旅途。告别热血沸腾的八十年代,选择站在远处遥望九十年代。这是诗人建构自身当代性的一种方式。阿甘本是这样描述当代性的:“当代性就一个人是与自身时代的一种独特关系,它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通过分离和时代错误来依附于时代的关系。”[6]远离中国的九十年代,在英伦三岛阴霾的天空下,列车的窗口和倾斜的街角都成为诗人思考的新维度,诗人对着自己说着无用的语句:“人类理应生存下去/红色双层巴士理应从海啸中开来/莎士比亚理应在贫困中写诗”[7],严寒和距离让他更好地审视自己、观察时代。并对诗歌有着更为深沉的认识。在《伦敦随笔》中,他以高昂激扬的态度赞颂凡·高的艺术价值:“你会再次惊异人类所创造的金黄亮色/你明白了一个人的痛苦足以照亮/一个阴暗的大厅/甚至注定会照亮你的未来[8]”
旅居国外的经历让王家新日益认识到孤独和远离时代的可贵,认识到诗歌语言超越作者意图之上的冥冥天意(或许就是语言的整体性意图)。诗人的责任在于表现个体的精神高点和世界的深邃隐秘而非按部就班地完成时代的语词实验。他对于凡·高的称颂是他对于像诗歌一样崇高艺术价值的自信,亦是他对于诗歌创作的重新认识。更为直接的词语逐步取代了空洞的自我宣扬,带着“不可抵达”的意义进入到诗歌当中,不断地引导读者去发现语言的光辉和明丽,发现生活的成熟与深沉之处——譬如树和冬天。王家新认为自己的创作受到北方的冬天和树影响很深,尽管他出生于大巴山畔、汉水之滨,后来又到江城读书。但正是“北方在地理和气候上的广阔、贫瘠、寒冷、苍茫,却和我生命更深处的东西产生了呼应,也和我身体中的南方构成了一种张力。”[9]由此引发的地理情怀让他在异国他乡的冬天,镌刻他的思考和《词语》:“静默下来,中国北方的那些树,高出于宫墙,仍在刻划着我们的命运。”[10]这样的词语和诗句简直是带着温度和声音闯入我们的阅读,是在北方有过生活经历的人才会明白的景象:在明亮高原的下午之后,无边的黑暗快速降临。诗人才能丢开一年四季的温暖和寒冷,碧绿与苍黄,直接告诉读者:“树木比我们提前到达。在冬天,树比我们显得更黑”。这是一种难于言状的黑。是一种带有光明色彩的幽暗。美国诗人托尼·巴恩斯通认为王家新“显现了自我的暗影及世界背后的世界,回应了格奥尔格·特拉克尔、詹姆斯·赖特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等人的‘幽暗本能’诗学”[11]。这种不可描述的黑与深藏在影像之后的幽暗诗学很可能是王家新提及凡·高的主要原因。在足以照亮大厅的明亮之外,有一个生活/日常语言不可及的艺术高点,幽暗、不为人知。但这种“黑”却正是艺术照亮生活的根本原因。诗人应当站在暗处,这样他才能更好地观察光明和感知黑暗。即使王家新本人并不希望把自己的诗歌创作与《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联系起来,但仍肯定自己的出国经历,并一再把自己的诗歌创作理念与布罗茨基、米沃什等流亡作家相联系。永远站在同样的位置去描写生活必然是有局限性的。流亡者由于他们的经历从而获得了新的叙述角度和眼光。
回到阿甘本关于当代性的描述,看待王家新和他的国外经历时,我们可能会有新的视角,正如诗人在《另一种风景》所言:“你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却呼吸着另外的空气/问题是我只能这样,虽然我可能比任何人更属于这个时代[12]。”诗人在面对同时代时应该保持一种不和时宜的自尊心:就像罗兰巴特所讲的The contemporary is the untimely——这当然意味着于时代和风尚话语的自我隔离,自绝于潮流和历史语境之外。但如果不是诗人,又应当由谁来进行这种巨大的冒险,遵从诗意的召唤,面对生命的幽暗呢?在回答“诗人何为”的问题上,王家新比我想象的更加坚决:“在伟大的诗歌中,有一种伟大的失败。”[13]
二、寂静的雪——对保罗·策兰的翻译、吸收与再创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王家新的意义不仅是诗歌创作的又一起点,还因为他发现了他精神当中最有认同感,并开始对其诗歌进行细致入微的翻译和解读的诗人保罗·策兰。尽管很多人会把王家新与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等人联系在一起。他本人也翻译过如曼德尔施塔姆、勒内·夏尔的诗歌并肯定了这些诗人的诗歌理念对自己的影响。但保罗·策兰是真正对王家新的诗歌创作和翻译工作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的那个人,让他“不断地重返”生命,产生一种经历、身份和心灵的认同。
策兰是一位怎样的诗人?他出生在1920年的一个犹太家庭——带着噩运气息的黑色历史在1942年压垮他的父亲,并洞穿他母亲的脖颈;这种可怕的经历渗透了诗人的全部生命和作品。他又是一个流亡诗人,战后因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他来到巴黎定居,从此远离罗马尼亚故乡,直至1970年在米拉波桥绝望地纵身一跃。黑暗和沉默是策兰的代名词,它始于《死亡赋格》的“黑色牛奶”,却不止停留于此。王家新说策兰的诗歌是在绝望中带着希望,他词语中的黑暗呼吁读者一次又一次地回归,直到作为一种共同体被照亮。
无独有偶,王家新在回望自己的创作时也经常性地提及生命当中那些不可说的残酷场景和诗歌对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归。早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的记忆在《少年》、《在那些俄国电影中》《那一年》当中反复出现,但诗人却无意过度阐述过程而更愿意描述一场失语症:“而我的喉咙开始发痒/我想说话,不,我想唱歌,不/我想呼喊,也不——我陷在/一场永恒的雪里。”这与策兰在《法兰克福·九月》当中写到的“这冒充的/寒鸦/之早餐/喉头爆破音/在唱”[14]何其相像!策兰说“在一切丧失之后只有语言留了下来,还可以把握。但是它必须穿过它自己的无回应,必须穿过可怕的沉默,穿过千百重死亡言辞的黑暗。”[15]这种对由生命的经历引发的对于语言的关注应当是策兰之所以如此让王家新着迷之处。他与策兰在德国真是不期而遇,天作之合。
对策兰而言,让他绝望的不仅是苦难的人生命运,还有某种残酷的文化气候。他来到巴黎后并未因其诗作大红大紫,相反却卷入到“戈尔事件”当中,承受着来自各方的指责和攻击;这也加剧了原本内心敏感的策兰精神上的压力和负担。在翻译策兰诗歌时,王家新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在《保罗·策兰诗文选》的序言中,他说策兰“是一位‘德语中的客人’。这是一位流亡者的德语。它使策兰与德语文化中心地带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16]这句话由经历了中国新诗的八十年代,却在九十年代选择远离的王家新说起,仿佛既是在评论策兰,也是在评论他自己。他在冬天吃着橘子,看塔可夫斯基的《牺牲》,寻找哥特兰岛上那株孤单的树——“除非有一个孩子每天提着一桶/比他本身还要重的水来”[17]。这首诗是王家新与汉语诗歌的距离:保持距离不是为了向陌生人倾诉痛苦,相反是为了更好地进入,开启一种新的破解残酷生活的方式。
王家新最欣赏晚期的策兰。《线太阳群》里的“一棵树”成为他新集的某个重要隐喻。《盔甲的石脊》的“插刺穿裂”和“缝隙之玫瑰”也许启发了他在《岛上气候》里写下“远山那亮丽耀眼的光,如一道鲜艳的伤口”。但比起这种简单的比附,更重要的是对于“后期”和“晚词”的态度,那意味着经历、过去、回归和重新认识;而对于苦难而言不去诉说苦难是困难的。阿多诺引用克尔凯郭尔耐人寻味的比喻来表述奥斯维辛之后:“在曾经裂开了一道可怕深渊的地方,如今伸出了一座铁路桥,旅客们从桥上可以舒适地向下俯看那深渊”。[18]诗人置身于他者的苦难之外,面对一堆坚硬的废墟无法下咽,只能以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关照一场人性之恶的苦难悲剧,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诗歌的背叛。阿多诺之所以认为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之不可能,正是诗歌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所谓的诗意游离于真实之外被不断质疑。诗歌建构了一种苦难之外的虚假,苦难因此失重。
策兰的诗,尤其是后期诗歌读起来永远是令人不舒服的。如《淤泥渗出》中“巨大的划行的孢子囊里/仿佛词语在那里喘气”,《可以看见》里面“成果叛逆和腐烂的骨髓/追逐着十二颂歌”,还有那首著名的“气孔眼睛/褪去疼痛的鳞,在/马背上”都创造着一种让人呼吸紧张、精神停滞的语言裂痕和抵抗性。阿多诺认为“晚期风格”是充满缝隙和悖论的:“客观的是那碎裂的风景,主观的是那唯一使之发亮的光。他没有谋求它们彼此和谐综合,他作为一股分裂的力量,将它们在时间中分开,以便将它们存储永恒,也许在艺术史上,晚期作品是灾难。”[19]这样的气氛,在读王家新的“后期”诗歌里也能发现。试以《冰钓者》为例:“他们专钓那些为了呼吸,为了一缕光亮/而迟疑地游近冰窟窿口的鱼/他们的狂喜,就是看到那些被钓起的活物/在坚冰上痛苦地甩动着尾巴/直到从它们的鳃里渗出的血/染红一堆堆凿碎的碎冰[20]”冰钓者的狂喜和为了呼吸与光亮,被甩在坚冰上面腮边渗血的鱼,难道和策兰“撕去疼痛的鳞”没有一点点关系吗?诗歌中的“我”是诗人自己吗?也许是,但也许并不是;因为那条“漫步的坝堤”是一个非个人化的指涉,是站在废墟和痛苦之外的集体认知。他们从浪漫主义的角度出发,因此对血视而不见,更不用说诗当中“呼吸”一词可能蕴含的深意了。而直面词语与生活真实的诗人则会走到跟前,面对染红的碎冰失语,除了“恐怖”无话可说。失语者只是那个见到事件本身的人吗?恐怕也不是——这是一个卡夫卡式的问题。“他是一个人?他是每个人?”
关于“每个人”的问题必然关联到王家新的代表作《回答》。耿占春很早就意识到这首诗超越个人经验的价值:“《回答》由一系列新的提问所构成,是对生存的古老的疑难、磨难、命运之谜在当代历史语境下的提问。它是把问题从个人生活及其道德维度转向历史和命运维度的一种努力。”[21]这一论断多么像阿多诺对于策兰和后奥斯维辛的评述。尽管痛苦的烈度不可相比,但转化的方式却惊人的一致。细致的读者还会发现《回答》与《孤堡札记》之间的关联,因前者第三节“这些天我住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古堡里……向一种黑暗的命运致礼”与后者第十五节“这也许就是我,出没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古堡里”的相互呼应。而对于《回答》一诗当中的个人经验描绘,《孤堡札记》里讲述了这种经验的历史境遇与当代命运:“试着给自己讲出一个故事来/但就是讲不出来/没有故事,故事就像一把磨损的椅子/已轰然散架”[22]。在《回答》当中诗人解答了为何故事无法被讲述:不同的话语在自由的旗帜下爆发冲突,被归结为同样的谎言。在此处诗人用“背叛的金色号角”来吹响这场名义上的个人化叙事(实际上集体记忆随处可见),耿占春指出这种故事的讲述“只是一种外部的脱离自己心灵的叙事”。实际上,《回答》标志着一场现代性的叙事与词语危机,不只是诗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以共同的语言再现过去——历史因此充满着修辞与虚构——而又无法完全地建构历史并与个人经验形成自洽。《回答》的意义就在于这些无法真正再现的细节在被呈现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意义,一种观点认为《回答》一诗展现从七十年代的革命话语到世纪末的绿卡、汽车之间的历史维度。诗人在此诗当中揭示出的偶像的堕落与理想的破灭,从而批判了中产阶级世俗化的生活姿态。但《回答》可能不止于此。因为唯一具有经验意义的叙事乃是那些有可能建构反例的叙事,而此诗恰恰表明了我们的生活无论从经验、语词抑或历史的角度无法重建。于是,一代人永远会感慨“我的这首诗也写得过早——多少年后/它注定会为另一只手无情地修改。”一代人也因此必然接受这种整体命运,即使它意味着个人化的消亡和对时代的无情反讽,但那毕竟是一条向上的,并在时间层面上不可逆转的道路。
三、明亮的词——“翻译”生活的诗人自觉
新世纪以来,兼有诗人和翻译家双重身份的王家新对诗歌语言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不仅要表达日常含义,更要突破这种表象展现精神的高地与心灵的深邃。这种超越日常语词含义的诗歌语言,不妨称之为“纯诗”语言。它不等于通常指称的纯诗,纯诗一般被认为是一种语词的实验,而非超越。作为诗人的王家新其实并不完全接受语词实验式的诗歌创作,他的成长经历与精神探寻支持他写作更加深入历史,与个体命运、社会事件和民族命运产生交集的诗歌。但紧靠生活的语言在表意上的贫瘠,又促使诗人不得不拉开与具体语境的距离。如《瓦雷金诺叙事曲》提到的:“一首孱弱的诗,又怎能减缓/这巨大的恐惧?/诗人放下了笔/从雪夜的深处,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的间歇中。”[23]日常语言构建的诗歌在现实的苦难与命运的苍凉面前是如此的软弱无力,以至于诗人必须要寻找新的语词建构方式,来对抗作为不合时宜的一分子必须面对的恐惧:沉重的生活、严酷的年代和精神的流亡。这种自洽的“纯诗”语言要深入生命的本质,表达词语非异己与派生的内在神性。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这种语言的探寻与对诗歌的翻译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在试图表达一种整体性意图。本雅明在《翻译者的任务》当中指出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不断把诸语言令人敬畏的成长付诸检验,看看它们隐藏的意义距意义的敞露还有多远,或者关于这一距离的知识能让我们把这一距离缩小到何等程度。”[24]而让我们感到欣喜的是,诗人本身即参与了这一工作,并在对保罗·策兰的诗歌翻译当中一次次回到语言——这一语言显然不是日常语言。在回答“对现代汉语的破坏与重建”这一问题时,王家新以自己的方式肯定了本雅明的翻译理论:“虽然我们使用现代汉语写作,但一旦进入诗歌,它就成为另一种语言,即在现代汉语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与系统中自成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在其性质上是‘不可推广与普及的’,变化的只是诗歌本身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永远只能用一种有别于诗的方式来说话。”[25]王家新以极大的热情让自己的诗歌介入现实,但又十分警惕去使用现成的词语和句子。他在力图以“翻译”的形式将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意义引入到超越历史的互补和自我完整之中。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翻译”由于要突破诸多语言能指的障碍,消除词语在生活当中所负担的沉重与异端,必然带来非常直观的痛苦体验。胡国平评价王家新的翻译诗作时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如同诗人,译者也是神圣卷入语言的命运,持续解释生命苦难并召唤希望的人;并且如同写作,真正的翻译也是对语言困境和可能性的呈露。”[26]王家新在新世纪以来反复提到要“回到策兰”,实际上也是在对策兰的翻译和自我的诗歌创作当中找到了一种深沉而持久的精神激荡和跨越语言的诗歌张力。他找到了语言的整体性意图及其纯粹性。对于诗人所处的当下语境来说,这种带有痛觉的翻译和写作也许不能通往某个理想的彼岸,但“来到这里你只能把自己献给虚无”[27]也是一种无声的抵抗。如利奥塔所言:“艺术所能做的并不是去见证崇高,而是去见证艺术自身的绝境和苦痛。它并不去言说不可言说之物而是去说它无法说出它这一事实。”[28]诗歌不仅能以理想的方式刻画世界,也可以选择存在与表象之外,见证不表达的表达性所蕴含的光辉。
回答本文一开始的问题,王家新的诗歌研究在当下的意义和价值。引用他喜爱的诗人勒内·夏尔的话“诗人不能长久地在语言的恒温层中逗留,他要继续走自己的路,就应该在痛切的泪水中盘作一团”,王家新表达了他的诗学观点与诗歌理想。的确,诗人应当有这种对于超越的自觉和“创造形式的渴望”(曼德尔施塔姆),承担翻译生活和探索语言的重任。即使随之而来的是阵痛与泪水。
注 释
[1]张桃洲:《现代诗歌的位置》,《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10页。
[2]王家新:《回答晋美子的二十五个诗学问题》,《诗探索》,2003年第1期:第27页。
[3][4][5][7][8][9][10][12][13][17][20][23][27]王家新:《塔可夫斯基的树》,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102,3,37,42,242,16,31,216,171,208,5,187页。
[6]阿甘本:《何为同时代》,《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第4页。
[11]张桃洲:《王家新诗歌研究评论文集》,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420页。
[14]本文所引策兰诗歌,均来自《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王家新译诗集》,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
[15]保罗·策兰:《不莱梅文学奖获奖致辞》,《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王家新译诗集》,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318页。
[16]王家新:“来自黑暗的灯”,《保罗·策兰诗文选》,王家新,芮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18]王家新:《阿多诺与策兰晚期诗歌》,《上海文化》,2011年第4期:第35页。
[19]西奥多·阿多诺:《贝多芬:阿多诺的音乐哲学》,彭淮栋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29页。
[21]耿占春:《没有故事的生活》,《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6期:第113页。
[22]王家新:《孤堡札记》,《山花》,1999年第8期:第100页。
[24]本雅明:《翻译者的任务》,《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6页。
[25]陈东东、黄灿然:《回答四十个问题》,《为凤凰寻找栖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页。
[26]胡国平:《母语分娩时的阵痛》,《南方文坛》,2015年第1期:第69页。
[28]转引自冯冬:《表象的灾难:论保罗·策兰诗学的发生》,《外国文学》,2016年第1期: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