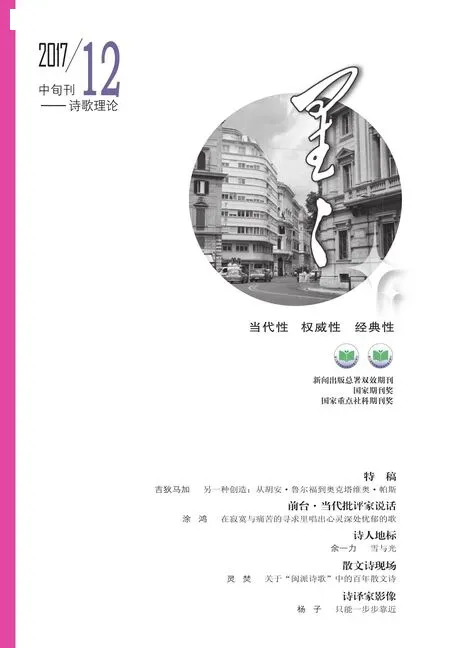另一种创造:从胡安·鲁尔福到奥克塔维奥·帕斯
——在北大中墨建交45周年文学研讨会上的演讲
吉狄马加(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当我在这里说到胡安·鲁尔福、奥克塔维奥·帕斯的时候,我便想到一个关键的词:创造,或者用一句更妥帖的话来说那就是:另一种创造。我想无论是在墨西哥文学史上,还是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甚至扩大到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上,胡安·鲁尔福和奥克塔维奥·帕斯都是两个极具传奇色彩并充满了神秘的人物。最有意思的是,与这样充满了传奇又极为神秘的人物在精神上相遇,不能不说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宿命的味道,首先,让我先说说我是如何认识胡安·鲁尔福这个人和他的作品的。我没有亲眼见过胡安·鲁尔福,这似乎是一个遗憾,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神奇的人,当然不乏有你十分心仪的对象,但都要见面或要认识,的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对胡安·鲁尔福这个人和他的作品,从我第一次与之相遇,我就充满了好奇和疑问,好奇是因为当我读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平原烈火》和中篇小说《佩德罗·帕拉莫》之后,我对他作为一个异域作家所具有的神奇想象力惊叹不已,记得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样的阅读给我带来的愉悦和精神上的冲击毫无疑问是巨大的,可以说就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我把一本不足20万字的《胡安·鲁尔福中短篇小说集》反复阅读了若干遍,可以说有一年多这本书都被我随身携带着,以便随时翻阅抽看。因为阅读胡安·鲁尔福我开始明白一个道理,此前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地域主义”写作,虽然在语言和形式上都进行了新的开拓和探索,不少作品具有深刻的土著思想意识,对人物的刻画和描写充满着真实的力量,尤其是对地域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呈现更是淋漓尽致,在这些作品中厄瓦多尔作家霍尔赫·伊卡萨的《瓦西蓬戈》、委内瑞拉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的《堂娜芭芭拉》、秘鲁作家阿格达斯的《深沉的河流》、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的《广漠的世界》等等,如果把它的范围扩大得更远,在非洲地区还包括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小说四部曲《瓦解》、《动荡》、《神箭》、《人民公仆》,肯尼亚作家恩吉古的《一粒麦种》、《孩子,你别哭》和《大河两岸》等等,当然还有许多置身于这个世界不同地域的众多“地域主义”写作的作家,这对于二十世纪而言已经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对他们的创作背景和作品进行解读,不管从政治层面,还是从社会和现实的层面,都会让我们对不同族群的人类生活有一个更全面更独到的认识,因为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对自己所属族群生活的独立书写,而不是用他者的眼光所进行的记录,这些作品的一次次书写过程,其实就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一次次确认,这些杰出的作家在后现代和后殖民的语境中,从追寻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源头开始,对重新认识自己确立了自信并获得了无可辩驳的理由,可以说,对于第三世界作家来说,这一切都是伴随着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蓬勃展开的。但是,对于胡安·鲁尔福来说,他不仅仅意味着这一切,虽然他的作品和生活毫无争议的属于那个充满了混乱、贫困、战争、动荡而又急剧变革的时代,但他却用近似于灌注了魔力的笔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人鬼共处的真实世界,这种真实的穿透力更能复现时间和生命的本质,胡安·鲁尔福最大的本领是他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时间观念,他让生和死的意识渗透在他所营造的空间和氛围里,他用文字所构筑的世界,就如同阿兹特克人对宇宙、对生命、对时间、对存在,所进行的神秘而奇妙的描述,这种描述既是过去,又是现在,更是未来。在二十世纪众多的“地域主义”写作中,请允许我武断地这样说,是胡安·鲁尔福第一个也是第一次真正打开了时间的入口,正是那种神秘的、非理性的、拥有多种时间、跨越生死、打破逻辑的观念,才让他着魔似地将“地域主义”的写作推到了一个梦幻般的神性的极致,难怪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回忆录中深情地回忆,他很早就能将《佩德罗·帕拉莫》从最后一个字进行倒背,这显然不是一句玩笑话,我们今天并非毫无根据地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是胡安·鲁尔福最早开始了魔幻现实主义写作的实验,而其经典作品《佩德罗·帕拉莫》是一个奇迹,是一座再也无法被撼动的真正的里程碑,一个兴起于拉丁美洲的伟大的文学时代,其序幕被真正打开,胡安·鲁尔福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佩德罗·帕拉莫》开创了现代小说的另一种形式,它将时空和循环,将生命和死亡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了一起,它是梦和神话穿越真实现实的魔幻写照,在此之后,不仅仅在拉丁美洲,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后来者都继承遵循了这样的理念,成长于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许多先锋作家,他们都把胡安·鲁尔福视为自己的导师和光辉的典范。胡安·鲁尔福之所以能得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作家高度评价,并成为一个永远的话题,那是因为他从印地安原住民的宇宙观以及哲学观出发,将象征、隐喻、虚拟融入了一个人与鬼、生与死的想象的世界,并给这个世界赋予了新的意义,据我们所知,在古代墨西哥人的原始思维中,空间与时间是相互交融的,时间与空间在不同方向的联系,构成了他们宇宙观中最让我们着迷的那个部分。最让人称道的是,胡安·鲁尔福的写作并不是简单地将原始神话和土著民族的认知观念植入他所构建的文学世界中,他的高明之处是将环形的不断变化着的时间与空间联系在了一起,这种生命、死亡与生命的再生所形成的永恒循环,最终构成了他所颠倒与重建的三个不同的世界,这三个世界既包括了天堂,也包括了地狱,当然也还有胡安·鲁尔福所说的地下世界。胡安·鲁尔福的伟大还在于他把他所了解的现实世界,出神入化地与这些神奇的、荒诞的、超自然的因素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也让他的书写永远具有一种当代性和现场感,他笔下的芸芸众生毫无疑问就是墨西哥现实世界中的不同人物,他们真实地生活在被边缘化的社会的最底层,但他们发出的呐喊和声音通过胡安·鲁尔福已经传到了世界不同的角落。我对胡安·鲁尔福充满了好奇,那是我在阅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他所给我带来的从未有过的启示以及对自身的思考。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看,墨西哥原住民和我们彝族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墨西哥人不畏惧死神,诞生和死亡是一个节日的两个部分,他们相信人死后会前往一个名叫“米特兰”的地方,那里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我们彝族人把死亡看成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人死后会前往一个名叫“石姆姆哈”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天空和大地之间,那里是一片白色的世界。彝族人认为人死后会留下三魂,一魂会留在火葬地,一魂会跟随祖先回到最后的长眠地,还有一魂会留给后人供奉。是因为胡安·鲁尔福,我才开始了一次漫长的追寻和回归,那就是让自己的写作与我们民族的精神源头真正续接在一起,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今天,我都把自身的写作依托于一个民族广阔深厚的精神背景成为了一种自觉。记得我访问墨西哥城的时候,就专门去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进行参观,我把这种近似于膜拜的参观从内心看成是对胡安·鲁尔福的敬意,因为我知道从1962年开始他就在土著研究院工作,他的行为和沉默低调的作风,完全是墨西哥山地人的化身,那次我从墨西哥带回的礼物中最让我珍爱的就是一本胡安·鲁尔福对墨西哥山地和原住民的摄影集,这部充满了悲悯和忧伤的摄影集可以说是他的另一种述说,当我一遍遍凝视墨西哥山地和天空的颜色,心中不免会涌动着一种隐隐的不可名状的伤感。胡安·鲁尔福这个人以及他的全部写作对于我来说,都是一部记忆中清晰而又飘忽不定的影像,就像一部植入了流动时间的黑白电影,因为胡安·鲁尔福所具有的这种超常的对事物和历史的抽象能力,他恐怕是世界文学史上用如此少的文字,写出了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民族隐秘精神史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许是因为我的孤陋寡闻,在我的阅读经历和范围中,还没有发现有哪一位作家在抽象力、想象力以及能与之相适应的语言能力方面能与其比肩。
而奥克塔维奥·帕斯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现实存在,这个存在不会因为他肉体的消失而离开我,他教会我的不是一首诗的写法,而是对所有生命和这个世界的态度,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不认为诗歌可以改变世界。诗歌可以给我们启示,向我们揭示关于我们人的秘密,可以为我们带来愉悦。特别是,它可以展示另一个世界,展示现实的另一副面孔。我不能生活在没有诗的世界里,因为诗歌拯救了时间、拯救了瞬间:它没有把它杀死,没剥夺它的活力。”作为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虽然不是第一个,但确实是最好的一个将拉美古老史前文化、西班牙征服者的文化和现代政治社会文化融为一体写出经典作品的划时代诗人,他的不朽长诗《太阳石》,既是对美洲原住民阿兹特克太阳历的礼赞,同时也是对生命、自我、非我、死亡、虚无、存在、意义、异化以及性爱的诗性呈现,他同样是二十世纪为数不多的能将政治、革命、批判性、对现实的干预并与自己诗的写作把握得最为适度的大师之一,难怪他曾说过近似于这样的话,政治是同另一些人共处的艺术,而我的一切作品都与另一种东西有关。我们知道二十世纪是一个社会革命和艺术革命都风起云涌的时代,在很长一个阶段不同的意识形态所形成的两大阵营,无论是在社会理想方面,还是在价值观念方面以及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判断看法,都是水火不相容的,而在那样一个时期大多数拉美重要诗人和作家都是不容置疑的左翼人士,当然这也包括奥克塔维奥·帕斯。但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奥克塔维奥·帕斯就表现出了思想家、哲人、知识分子的道德风骨和独立思考的智慧能力,他对任何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的看法和判断,都不是从所谓的集体政治文化的概念出发,而是从人道和真实出发去揭示出真相和本质,1968年10月20日在特拉特洛尔科广场屠杀学生的事件,就遭到了他的强烈谴责,他也因为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辞去了驻印度大使的职务,可以说,是奥克塔维奥·帕斯在墨西哥开创并确立了一种独立思想的批评文化,打破了不左即右二元对立的局面,他的这种表达政治异见的鲜明态度,甚至延伸到了他对许多国际重大事件的判断,比如引起整个西方和拉美左派阵营分裂的托洛茨基被暗杀事件,就是他首先提出了对另一种极权以及反对精神自由的质疑,也因此他与巴勃罗·聂鲁达等朋友分道扬镳,他们的友谊直到晚年才得以恢复。他创办的杂志《多元》、《转折》,是拉丁美洲西班牙语世界不同思想进行对话和交锋的窗口,他一直高举着自由表达思想和反对一切强权的人道主义旗帜,他主办过一个又一个有关这个世界未来发展带有某种预言性的主题讨论,这些被聚集在一起的闪耀着思想光芒的精神遗产,对今天不同国度的知识分子同样有着宝贵的参照和借鉴作用。奥克塔维奥·帕斯是最早发现并醒悟到美洲左翼革命与这一革命开始将矛头对准自己的人之一,他的此类言论甚至涉及到古巴革命后的政治现实,南美军人政权的独裁统治,各种形式游击组织的活动,东欧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境况以及对美国所倡导的极端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精准批判。他发表于1985年的《国家制度党,其临终时分》一文,对该党在奇瓦瓦州操纵选举的舞弊行为进行了揭露,这一勇敢的举动使墨西哥大众的民主意识被进一步唤醒。在这里我必须说到他的不朽之作,当然也是人类的不朽之作《孤独的迷宫》,是因为它的存在我们才能在任何一个时候,瞬间进入墨西哥的灵魂。《孤独的迷宫》是墨西哥民族的心灵史、精神史和社会史,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墨西哥民族心理和文化现象的罗列展示,而是打开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孤独面具,将这一复杂精神现象的内在结构和本质呈现给了我们。在一次演讲中帕斯这样告诉听众:“作家就是要说那些说不出的话,没说过的话,没人愿意或者没人能说的话。因此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并非电力高压线而是道德、审美和批评的高压线。它的作用在于破坏和创造。文学作品与可怖的人类现实和解的强大能力并不低于文学的颠覆力。伟大的文学是仁慈的,使一切伤口愈合,疗治所有精神上的苦痛,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刻照样对生活说是。”我要说,伟大的奥克塔维奥·帕斯是这样说的,同样他也是这样做的,他用波澜壮阔的一生和无所畏惧的独立精神,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为我们所有的后来者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从胡安·鲁尔福到奥克塔维奥·帕斯,这是一条属于墨西哥,同样也属于全人类的必须被共同敬畏和记忆的精神遗产,它们是一种现实,是一种象征,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是一种创造,也正因为这种充满了梦幻的创造,在太阳之国的墨西哥谷地,每天升起的太阳才照亮了生命和死亡的面具,而胡安·鲁尔福和奥克塔维奥·帕斯灵魂的影子,也将在那里年复一年地飘浮,永远不会从人类的视线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