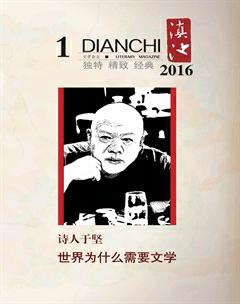口吐莲花
马卫巍
我同学刘大嘴天生是个说相声的料。比如上初中时,我们每天要背诵那些难以理解又难以念顺的文言文,还要记住那些碎蝌蚪般的英语单词,弄得脑袋都大了,这小子却独自在一旁大声念“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这小子嘴皮子利索的很,摇晃着脑袋,能够迅速进入自我陶醉的状态。用我的话说:“你一本正经的面容真他妈像快要挨老师揍的样子。”每次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刘大嘴就笑,他笑起来带着一种憨态,憨态可掬,就像电视里的大熊猫,粉嘟嘟的腮蛋子都一颤一颤的。老师最终还是发现了我们,啪啪两块粉笔头准确无误的落到我俩的脑门上。老师气呼呼的说:“刘大嘴、孙小二,你们再在那里傻笑,就都给我滚出去!”
刘大嘴马上不笑了,能把刚刚出嘴的笑声一下子又咽下去,他咽笑声的时候含着一口唾沫,“咕咚,咕咚”,然后两个肩膀一耸一耸的,笑声便在肚子里横冲直撞了。我能听到他肚子里“叽里咕噜”直响,那些笑声一定在里面连环爆炸了。我没有他这个本事,咬着牙憋也憋不住,瞪着眼憋更憋不住,只能笑的更厉害,抽抽搭搭的鼻子眼泪一大把。老师已经从讲台上走下来了,我看见他攥起了拳头,眼睛里升起了两道火焰,立刻主动站起来走到了教室门口。刘大嘴冲着我努了努嘴,而且还扮了个鬼脸。
“他妈的刘大嘴!”我心里恨恨的骂了句。
刘大嘴的嘴其实并不大,只是嘴唇稍微厚了点。“嘴唇厚,吃四方!”这是刘大嘴经常说的一句话。他对他的两片嘴唇自豪不已,曾多次骄傲的对我们说:“嘴唇厚是我们这一行最大的优点,以后就得靠这两片嘴巴子吃饭。孙小二,你的嘴片子薄,可你吃过肯德基吗?你尝过麦当劳吗?”真的,我们那个年代别说肯德基麦当劳,就连他妈的芝麻糖火烧都很难吃到。刘大嘴骄傲的说:“我跟我爸去省城汇演,吃过这个,又酥又脆还外焦里嫩,香得很呐!”他一边说一边咽唾沫,咕咚一下又咕咚一下,勾得我们也跟着咽个不停。刘大嘴除了爱笑还爱说,并且说什么都
绘声绘色的。这家伙,嘴皮子厚,说起话来当然得天独厚。
刘大嘴住在县城小十字街的艺术团家属院里。小十字街虽小,却是县城的中心,就像现在北京的长安街一样,繁华得很。小十字街道上分布着县委、县府家属院,分布着邮电局、工商局、公安局等各个部门的家属院,都是清一色的红砖碧瓦小房子,是县城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些家属院里,数着艺术团的家属院热闹,这些人平日除了演出、排练,在家里的时候也不安分。一到清晨,要么这家传来喊嗓子的声音,要么那家传来拉胡琴的声音,偶尔还传来一阵狗吠猫叫,这些声音荡漾在小十字街的巷道里,简直是悠远辽阔波澜起伏。
在艺术团演员们里,刘大嘴最瞧不起他爹。刘大嘴他爹刘解放是一名哑剧演员,只要上了台,他那张嘴就好像让针线给缝起来一样从不说话。“这叫啥本事?不就是在台上卖傻充愣吗!”刘大嘴看着他爹在台上表演,小声嘟囔着给我们听。刘大嘴这话说的有点过,哑剧其实不好演,既要编一个完整的故事,又要用面部和肢体的夸张变化来完美的表现出来,他在台上演,观众在台下笑,真正互动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当他爹在台上表演到高潮的时候,我几乎能从座位上笑的出溜到座位底下去。刘大嘴撇着厚厚的嘴唇,带着不屑的神情对我说:“你至于吗?真有这么好笑吗?”刘大嘴越是这么说,他的脸上就越是严肃,他不是看表演,好像在看一场葬礼。
刘解放表演哑剧几乎炉火纯青,这与他下的苦功有关系。这人有点怪,怪的让人摸不着头脑。他一天说的话,加起来没有十句,几乎无时无刻都在表演哑剧。吃饭、穿衣、上厕所不用说,就连和刘大嘴交流,也得用肢体动作表示。刘大嘴有次说过,他爹有次演出回来肚子饿了,嘴上却硬是不说,冲着他一个劲的比划,扮作吃饭的样子,动作可怜又可笑。刘解放的意思很明显,想要刘大嘴给他做点饭吃,可刘大嘴硬是没理解明白,还以为他爹给他带回来了好东西。刘解放见刘大嘴不为所动,气的骂了句“你娘的笨蛋”!自己出去找吃的去了。
刘大嘴不喜欢哑剧,但对他爹表演哑剧也无可奈何。他每当交学费伸着手要钱的时候,他爹才会说句话:“小子,知道我为啥演哑剧了吧?哎,一家人等着我买米下锅呐!”刘大嘴有时候也挺可怜他爹的,演哑剧都演得魔怔了,跟谁都不大爱说话,嘴巴子上像抹上“哥俩好”胶水,一张嘴也就成了吃饭用的摆设。他爹嘴里的“一家人”指的就是他们爷俩。刘解放的老婆是在刘大嘴三岁的时候跟一个魔术师跑的。她给刘解放留了一个纸条,上面仅写了一行字:“我已过够无声世界。”
刘大嘴知道他妈为什么跑,为的就是他爹这张不说话的嘴巴子。团里的那个魔术师就很能说,就跟个唱大鼓说相声的一样,一时半刻不说话,就能憋得百爪挠心。
“我听别的人讲过,魔术师很有能耐,他一伸手,就能从空气里抓出一把花花绿绿的票子来。”刘大嘴告诉我:“他会一种咒语,每天都需要念念有词,就能把人的心勾住,让你不由自主的跟着他走。”
我对此不以为然,我说:“魔术绝对是骗人的,没有哪个人能凭空变出钱来。说白了,那个魔术师就是个骗子。”我没见过那个魔术师,但我听说过他的故事。他最有名的魔术就是“空中捞钱”。表演的时候,从怀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毛边纸,然后用火点燃,这些火焰和灰烬就像蝴蝶一样在空中飞起来了。这时候,他伸出手不断地捞着那些袅袅的烟雾,一把、两把、三把,然后一转身说声变,一叠整整齐齐的钞票便在手里了。魔术師能“捞”到不同面额的票子,有一毛的,有两毛的,也有两块、五块的,碰上台下的观众多的时候,他还能“捞”到五十、一百的。刘大嘴他妈肯定是受了魔术师的诱惑,被他不知不觉的骗走了。
我听人说,刘大嘴他妈叫夏小可,当年在艺术团里跳民族舞,人长得娇俏可人,是天生的美人胚子。刘解放把夏小可弄到手的时候,颇费了些周折,不过也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刘解放这人有一股执着劲,凭他一天天难开金口的样子,想追上夏小可无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刘解放有他的办法,就是天天做一件事——给夏小可打饭。这个活有人抢着干过,借着送饭的时机说几句话儿,套套近乎。但他们给夏小可打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坚持不了多长时间,送几回见夏小可不上钩,也就送着没劲了。刘解放送饭却有一股子持之以恒的劲头,一天三顿风雨无阻,一下子送了将近一年。
有天演出后,刘解放又屁颠颠把饭菜送到夏小可面前,并且做出了“趁着热,你快吃”的肢体动作,有点滑稽,更有些可笑。夏小可气呼呼的说:“刘解放,你他妈的别再缠着我好不好?”刘解放嘿嘿一笑,他把饭菜推到夏小可面前,认认真真地作了一个动作:“我愿缠你一辈子。”夏小可哇的哭了,她捶打着刘解放,小鸟依人般的拥到他怀里。“刘解放,我他妈算毁在你手里了!”刘解放使劲搂着夏小可,闻着她发丝里的味道,舔着她的眼泪,把她抱到化妆台上。刘解放的动作是粗鲁的、单一的,像一匹野狼。据说,那一天夏小可呼喊的声音荡漾在空荡的排练房里,像一只受伤的小鹿,更像一只欢快的黄莺。他们在演出之地完成了神圣的成人仪式。刘解放粗重的呼吸压抑而又极具释放之力,让整个排练房都燃起熊熊大火,夏小可点点艳红洒在排练房的每一个角落,像一朵朵正在盛开的梅花,让人生出无限陶醉。
我无聊的时候总想,若没有魔术师的出现,夏小可会不会和刘解放白首一生呢?魔术师表演节目的时候,夏小可给他配舞,给他递“活儿”,两个人配合得天衣无缝。两个人排练时,魔术师的两只手在夏小可身上一闪,手里的票子就变没了。他的动作迅疾、麻利,嘴里吹着口哨,一缕长发滑下来,遮挡住了半边脸。
“钱呢,钱呢?”夏小可惊讶地问,她的脸上涌上了一朵桃花,绯红色的,艳丽得让人喘不过气来。魔术师就抱住她,他说:“你猜……”夏小可有些窒息,她无力地推搡着魔术师,气喘吁吁地说:“别闹,快变出来……”魔术师一把
抓住她的两只乳房,从缝隙里掏出了两张崭新的
票子。
魔术师和夏小可就变成了两条鱼。
魔术师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把两个人变没了,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无影无踪。
想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刘大嘴幽幽地对我说:“我妈走了也好,每天守着一个木头疙瘩也没什么意思。你是不知道,我们家除了喘气声和老鼠磨牙的声音,几乎没有任何声响。”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叹了口气说:“兄弟,委屈你了。”
刘大嘴后来学相声,与刘解放也有一定关系。刘解放挣钱靠的是不说话,但刘大嘴偏偏要凭着一张嘴养家糊口。艺术团里的这碗饭不是那么好吃的,不一定非得身怀绝技,但肚子里也得有点真本事。我们高中还没毕业,正愁着能否考上大学的时候,这小子已经休学在团里打杂,同时领着一份百把十块的临时补助了。刘大嘴练嘴,刻苦用功是出了名的。我下了学去找他玩,练功房里空空荡荡,他正对着镜子练功。“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拎着个喇叭……”这小子口若悬河,两片嘴皮子啪嗒啪嗒直响,颇有范儿。看到我来了,他停下练功,找了把椅子让我坐下,还给我泡了一茶缸子茉莉花末子。
我知道这小子肚子里的坏水。他有些不好意思,一个劲的搓手,在几平米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像一条精瘦的哈巴狗。刘大嘴嘿嘿一笑,露出一嘴白牙,他把茶水放到我手里,不好意思的说:“小二兄,麻烦你把这封信交给莫晓美,就说我想说的话都在这里面了。”
刘大嘴慎重地把一封有些皱皱巴巴的信封递到我手里,压低了声音说:“事成之后,我好好请你搓一顿。”
我坏坏的问:“你们办成好事了?”
“哪能呢?”刘大嘴的脸蛋腾的一下子红了,这一红不要紧,嘴皮子也变得不利索,他断断续续地说:“莫晓美她……她……没给我机会。”
刘大嘴是真心的喜欢莫晓美,正如他喜欢相声一样,一旦碰到她,眼神就被莫晓美的身子拉直了。莫晓美是我们班里的一朵花,一朵茁壮成长的牡丹,含苞待放,娇艳欲滴,任何一个男生都恨不得过去掐一下。不过,莫晓美平时不苟言笑,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浑身都带着刺儿,男同学和她搭讪,总会碰一鼻子灰。刘大嘴有对付莫晓美的办法,他肚子里的段子张口就来,一些笑话能顺着嘴皮子蹦出来,每次都能惹得莫晓美哈哈大笑,像挂了一串铜铃铛。不过,莫晓美人长得漂亮,骨头里自然透着傲气,她明白刘大嘴的意思,但却对他若即若离,她耍着手段呢!
我把刘大嘴的信交给莫晓美的时候,莫晓美竟然当着我的面快速的看了一遍,她对我说:“你回去告诉刘大嘴,老地方见。”
“老地方,哪里的老地方?”我故意问道。
莫晓美转身就走,她的背影冲着我说:“你个小毛孩子懂个屁!”
“你才懂个屁!”我心里骂道。看着莫晓美扭着屁股走人的样子,我恨恨地说:“你臭美啥,刘大嘴早晚得把你办了!”说实话,莫晓美的屁股蛋子很好看,两团肉紧绷绷的,摸起来一定很爽,她的两只奶子提前发育了,激荡在胸前,像两座直挺挺的小山丘。有一回我突然梦见了这两只奶子,白晃晃的,像两团火焰。莫晓美双手托着它们,两粒小红豆散发着迷人的光芒,美得让人沉醉。她笑着对我说:“刘小二,你敢吃吗?”我一跃而上,双手差点抓住它们,这时候我竟然从梦里醒了过来。这场梦让我心神荡漾,久久不能忘怀。再见到莫晓美的时候,我不敢直视她,不敢看她的胸脯。这是一对——他娘的凶器!
我把莫晓美的话传给刘大嘴,刘大嘴竟然兴奋的一蹦老高,这个熊人高兴地手舞足蹈。“能成,能成,我俩能成!”
刘大嘴和莫晓美约会的老地点竟然是艺术团的后台化妆间,这地方平日里没人,空空荡荡的让人心里很不舒服。别看演出的时候人來人往观众如潮甚是热闹,真到空下来时,竟然有些冷清的让人心里发毛。刘大嘴这小子很不厚道,这是第一次告诉我他俩的约会地点,也顺便让我给他把风。他告诉我说:“哥们,你好好的在幕布里藏着,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你就学狗叫,汪汪汪,汪汪汪,拜托你了……”这小子一脸的乞求相,让人不好意思回绝。我心里清楚,这种鬼地方平日里根本没有人来。
他俩在化妆间里很长时间,一开始不说话,都在沉默着,平静如水,让我等得也不耐烦。我心里想:“你个刘大嘴,平时练就的嘴皮子到这时候成哑炮了,你追莫晓美真他妈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过了一会,刘大嘴突然说话了。
“晓美,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须少结实成,别看有的人长得比我好,家庭背景也比我好,可这都是暂时的,我们的幸福生活要凭自己的双手拼搏……”
“我不信,就凭你两片嘴,能让我以后幸福?”莫晓美打断刘大嘴的话,有些气鼓鼓地说道。
“我不是说过嘛,我就是一粒枣,现在虽然青涩,但日后必定成熟,你就等得肯甜枣吧,保准你甜掉牙!”
莫晓美就笑,笑起来像一串铃铛,在空荡荡的剧场里横冲直闯。莫晓美说:“谁稀罕你这种小野枣,还成熟呢,就是熟了也是酸的 ……”
刘大嘴肯定用什么东西捂住了她的嘴,他模模糊糊的说:“那你尝尝是甜的还是酸的……”我听见“唔……”的一声,然后就没了动静。剧场里恢复了平静,平静如水,我只能听见他们的呼吸了。
刘大嘴的呼吸粗重,像一头牛在大口喘气,“呼哧……呼哧……”莫晓美则呜呜的在喘,稍带着丝丝无力的呻吟,“嗯……唔……”这种声音真他娘的撩人!我觉得嗓子眼涌上一口粘粘的液体,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我慢慢退出来,闪电般跑出剧场。我知道若再不出来,我也会憋得喘不过气来的。
真不知道,他们这样下去,会不会憋坏了?
实际证明,他们两个没有憋坏,反而徜徉在这种感觉里不能自拔。整个下午,他们在化妆间里激荡,浪花拍打着海岸,海岸容纳了浪花,他们两个化成了一汪溪流。
刘大嘴和莫晓美结婚的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正在为找工作发愁,可他们的孩子都快生出来了。莫晓美挺着大肚子进了刘大嘴的家,这小子一下掉进蜜罐里了。刘解放内退,刘大嘴转正顶上,一家人也就有了烟火气。
刘解放还是不爱说话,一切靠肢体语言表达,变成了一只彻底的闷葫芦。莫晓美对刘解放这个“哑巴”公爹是不满意的,她爱说话,也爱听别人说话,更爱听刘大嘴说话,但刘解放不言不语在眼前晃过来晃过去,真够烦人的。
刘大嘴和莫晓美的女儿刘莲儿出生后,小孩子爱哭,一旦哭起来就不带停的,抽搭抽搭,一副可怜样儿。刘大嘴和莫晓美使出浑身解数,孩子依然哇哇直哭,急的满身是汗。刘解放接过来,充分用上了他的哑剧绝活,逗样给孩子看。他一会变成一只大猩猩,一会变成一只哈巴狗,一会又变成一只大公鸡,孩子便破涕为笑了。
刘大嘴跟莫晓美解释:“咱爹不是一无是处,你看他哄孩子还是有一套的嘛。”
有一次我去刘大嘴家喝酒,这小子抱着他女儿幸福地说:“小二,咱俩认个干亲家吧,让我闺女管你叫干爹。”
我差点把刚进嘴的二锅头喷出来。“我他妈还不知道丈母娘在哪儿,从哪里变个孩子认你做父啊?”
刘大嘴就压低声音说:“你抓紧找,找到了抓紧办事。女人就是这德行,你得要有霸王硬上弓的劲头,想当年,我就是这么办成的……”
莫晓美正好端着一盘刚弄好的炒鸡蛋过来,她嗔怪的骂了句:“刘大嘴,你少他妈吹牛!”
刘大嘴就慌忙的给我夹菜,他笑着说:“喝酒,喝酒……”
莫晓美在他身边坐下来,幸福的像一只牡丹花。
刘大嘴在艺术团打红,或者说在我们当地一炮打红,是因为相声段子《口吐莲花》。这个活儿不好演,捧哏的要营造紧张的氛圍和气氛,逗哏的要不温不火不急不躁,两个人一唱一和,需要配合的天衣无缝。刘大嘴说这个活儿的时候,请了一位老演员给他逗哏,也算给他把场。
那天刘大嘴出尽了风头。他把头发梳的跟牛舔的一般,灯光打在上面,乌黑铮亮,这小子的双眼炯炯有神,散发着点点光亮,让人看着神气十足。
刘大嘴说:“我这戏法可是祖传的,厉害着呐!”
老演员说:“您这戏法是什么名儿?”
刘大嘴说:“我这叫口吐莲花。”
老演员说:“怎么叫口吐莲花呢?”
刘大嘴说:“您给我倒一杯水来,我就慢慢地掐诀念咒,一憋气我咕嘟咕嘟的,喝了。喝完之后,我蹲档骑马式摆开架子,用我的丹田气功把水再从肚子里提上来,一张嘴还能把它喷出来。喷出来是个水球,这水球慢慢悬到半空中,然后啪这么一开,变成了一朵莲花,莲花当中站个小娃娃,冲着台下三鞠躬,鞠躬之后落到地上,还是那点水。”
刘大嘴说活儿的时候,手足舞蹈,收放自如,台下掌声一片连着一片。
刘大嘴说:“一请天地动,二请鬼神惊,三请毛老道,四请孙伯龄,五请桃花女,六请老周公,七请小悟禅,八请是沙僧……请来金少山,又请裘盛戎,请来马连良,又请谭富英,请来奚啸伯,又请梁益鸣,请来侯宝林,再请高德明,请来花小宝,再请王桂英,请来王佩臣,又请宋慧玲。早请早到,晚请晚到,如若不到,铜锣相叫。接神接仙,八抬大轿。凉水泼街,黄土垫道。腊月二十三,糖瓜祭皂,请高香,抓草料,麻雷子,二踢脚,五百一堆,少了别要。腌菜瓜,酱青椒,喝豆汁儿,吃巴豆,跑肚拉稀,吃药就好,走走留神,汽车来到,大车切轴,三轮放炮,老头儿咳嗽,小孩儿撒尿,法院过堂,手铐脚镣,机关枪,迫击炮,快看新闻,今日晚
报,哈咿叭嘎,顶好顶好,抬头一看,神仙来到
哇……”
老演员说:“您倒是口吐莲花啊!”
刘大嘴说:“哎呀,我全咽啦!”
台下掌声雷动,差点把舞台房顶掀翻了。那个年代,越是简单的娱乐越是受人喜欢。刘大嘴就这么红了。
那时的剧团业务很忙,每个星期都要下乡演出三五天。刘大嘴会提前把尿布洗好,几乎够用一个星期。洗尿布这个活不好干,特别是粘着婴儿屎的尿布,很难洗干净。刘大嘴却特爱干这活儿,而且干的很带劲。
“坡上立着一只鹅,坡下就是一条河。宽宽的河,肥肥的鹅,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他干活的时候喜欢练绕口令,这是他的拿手绝活,一段段绕口令在嘴里嘎嘣脆,如同倒一粒粒小豆子,一气呵成。他越说越快,洗尿布的动作也就越快,水盆里哗啦啦,洗尿布刷刷刷,一块块尿布溅着水花,洁白却又柔软。他的家里荡漾着童子尿的气味,荡漾着童子屎的气味,荡漾着莫晓美奶水的气味,荡漾着他满身上下荷尔蒙的气味……一片片尿布像一面面旗帜,飘荡在院子里的晾衣绳上,飘荡在院子里的桃树枝上。刘大嘴荡漾在尿布水的湿气里,他的两边嘴唇越发的像两条香肠了。
莫晓美已经不是当年的莫晓美,她脸蛋上的肉快赶上屁股上的肉多了,两只奶子晃荡在胸前,鼓鼓囊囊的,让人看了都有点脸红。她这人特会享受也特别爱吃。刘大嘴下乡演出回来时,都会拎一包当地的小吃,有猪头肉,有酱猪蹄,有烧鸭子,有红焖驴肉,这些东西都便宜了莫晓美的嘴。我第一次领着媳妇到刘大嘴家串门的时候,刘大嘴竟然一次性上了近二十道菜,各色各样,荤素齐全。他刚买回一台冰箱,里面装的都是好吃的,羡慕得我媳妇直骂我没出息。
剧团里还是红火过一阵的,刘大嘴台上说相声,台下把厂子卖票,颇有春风得意的范儿。我那时看节目都不用买票花钱,只要往剧场门口一站,刘大嘴准会屁颠颠跑过来领着我进去。有一次我爹过生日,刘大嘴颇有心机,特意跑家里来送了一叠免费门票,请我一家人去看节目,挺让人感动的。在他的相声段子里,我最喜欢《口吐莲花》。他说这段的时候可谓卯足了劲,逗哏卖力,捧哏到位。他把长袍马褂穿在身上上台鞠躬行礼后,一个包袱接着一个包袱,抖的恰到好处,笑点还是很多的。刘大嘴的嘴,真的能口吐莲花了,干净利落,水到渠成。当年,凭着《口吐莲花》这个段子,在省里汇演中曾夺得一等奖,着实让他风光了一阵。
刘大嘴这人特别能说还特别能喝。这么说吧,我们几乎穿一条裤子长大,在一块喝了二十多年酒,我就从来没见他醉过。我俩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我是插不上话的。“我跟你说,我们团里可热闹了,你见过演丫鬟的小翠凤么,这娘们都四十多岁的人了,还故作清纯。”刘大嘴说话的时候,就像说相声,声情并茂,让人看了也算是一种享受。他一边喝酒一边吧嗒嘴,嘴里从来喷不出酒末子和菜末子。“小翠凤想勾搭团里新来的小武生,每日里擦脂抹粉,一天三换衣服,别说还就真成了。”
我说:“喝喝喝。”
莫晓美说:“臭不要脸。”
刘大嘴却哈哈一笑,“这算啥,事后小武生逢人便说,我算完啦,亏大发了,我掉进无底洞啦!”我们就笑,笑的昏天地暗。
刘大嘴也有伤感的时候,有一次他搂着我,几乎带着哭腔:“自我正式登台第一天起,我老爹从来没看过我表演节目。”刘大嘴有些动情,他叹着气说:“老头子这就快废了,一天天不说话,马上丧失语言功能啦。”
我劝道:“你一家人的话都被你一个人说尽了,知足吧。”我同情地拍了拍刘大嘴的肩膀。这小子也开始发福了,浑身肉颤。
刘大嘴喜欢相声,愿意为中国相声事业奋斗一辈子,正当他信心百倍想要大干一场的时候,这个在我们县城存活了六十多年的剧团解散了。剧团的解散让刘大嘴始料不及,他每天忙着练功,陪着老婆孩子享受热炕头的温存,早就流传剧团解散的传闻他哪能听到耳朵里去呢。解散那一天,领了买断工龄的钱之后,团里的东西该卖的卖,该扔的扔,该分的分,刘大嘴只拿回了一块响木和一把扇子。他几乎哭着一路到家,然后坐在屋里一言不发。屋子是剧团当年分发的,后来每家交了三千块钱,屋子就变成个人的了。刘大嘴有这么个容身之所算是不错的。这些年来,周围的房屋该扒的扒,该建的建,剧团的这些小平房饱经风霜,已經风烛残年了。它们孤独的坐落在高楼大厦的包围之中,早就失去了往日的色彩和生机。
他让莫晓美喊我过来喝酒,莫晓美由一朵花变成了一头大象,走起路来呼哧呼哧乱喘。她的屁股越发的大,身体越发的胖,脸部却越发的光亮,像一尊活菩萨。
“你说咋就完了呢?”刘大嘴这次真的喝大了,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弄得我也挺伤感的。醉眼朦胧之间,我看见刘大嘴的头顶已经秃的差不多了,几抹稀疏的头发软绵绵躺在铮亮的头顶上,如同秋季里的野草,丧失了一切生机。刘解放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鹤发童颜,几乎仙风道骨。莫晓美刚给女儿刘莲儿买了新衣服,娘俩正在那里比划,笑的前合后仰。
刘莲儿简直是莫晓美当年的翻版,出落得凸凹有致。这孩子学习不咋地,倒是像极了当年的刘大嘴。她把头发染得黄黄的,把嘴唇抹得红红的,把衣服穿得少少的,像一朵水灵灵的莲花。刘莲儿的身材继承了莫晓美当年的优点,凹凸有致,轻柳婀娜,屁股蛋子紧绷,两只奶子紧挺,活脱脱一个美人胚子。这闺女初三还没毕业就在学校里谈恋爱,引得好几个男孩子为她打架斗殴争风吃醋。刘莲儿被老师教训了一通,竟跑回家和学校彻底拜拜了。
刘大嘴的悲伤只是个人的,他家人似乎对他的下岗无动于衷。他吧嗒着嘴说:“剧团解散就解散吧,人下岗就下岗吧,这时候走一步算一步,人总不能让尿给憋死吧。”我敬他酒,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刘大嘴用买断工龄的钱招兵买马,自己干起团长来了。这家伙贼心不死,还指望着用所谓的艺术养家糊口呢。可这年代,人们都钻进电影院、放映厅、卡拉 OK里面去了,谁会去看他所谓的艺术呢?有天,我正和媳妇遛马路,正看见刘大嘴骑车慌里慌张的朝前奔,他的两片嘴唇上起了大大的血泡,让人触目惊心。我在后面喊:“刘大嘴,你干嘛去?”
他一边用力蹬车一面高声回答我:“晚上我团里有演出,一定要来捧场啊!”
我冲着他的背影回答道:“好,一定去!”
我媳妇噘起嘴来,有些不情愿的说道:“晚上咱不是去看电影吗?”
我拉着她的手说道:“你看大嘴多不容易啊,咱又没有别的能耐,去看场演出权当帮帮他吧。”媳妇是软心肠的人,她叹着气说:“你说他这是何苦呢?”
剧场里的人稀稀拉拉的,也就二十几个人,各个无精打采地坐着,有些心不在焉。刘大嘴几个人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要来多少掌声,演出也就草草结束。谢台之后我请他喝酒,他推辞没去。他又慌张的跑了,他说:“改天再聚,刘莲儿这闺女又不争气啦!我得去处理处理。”
刘莲儿竟然怀孕了,这让刘大嘴嘴上的血泡更加浓密,一个接着一个,争先恐后的往外挤。他领着刘莲儿偷偷做了流产手术,让莫晓美陪着在家休养。
刘大嘴这么能说,几乎能口吐莲花,竟然问不出刘莲儿究竟是跟哪个黄毛小子好上的。刘大嘴问急了,刘莲儿就把眼睛瞪得老大,她气鼓鼓地说:“当年你和我妈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刘大嘴一屁股坐在那里,半天没说出话来。
刘大嘴这个人比较活泛,在县城里搞艺术混不下去,他就把他的艺术团搬到乡下去,并且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莲花湾歌舞团。我听到这个名字时,马上想起了他的拿手活《口吐莲花》。乡村正在发生蜕变,刘大嘴瞅准了这个时机,把他的莲花湾艺术团弄得风生水起。他买了一辆二手的大箱货车,平时哪个乡镇立市建集,哪个村子搞个专场,都会一溜烟开过去,倒也忙的不可开交。
不过,刘大嘴从此再也没有请我看过他的演出。我碰见他,他的眼神很不自在,仿佛在躲闪什么似的。我笑着说:“你小子发财后是不是见利忘义了,当年你和莫晓美成就好事可是我的功劳呢,怎么,把兄弟忘了?”
“小二哥哎,你千万别多想,我哪能是那种人!咱俩穿一条裤子长大的,我这点德行你还不清楚吗?我的莲花湾艺术团经营的还行,但就是不好意思让朋友们看到,怎么说呢……”劉大嘴有些着急,他抓了把稀疏如草的头发,叹着气说:“怎么说呢,说出来丢人……”
我有点发懵。“你不偷不抢,凭着耍活吃饭,这有什么丢人的?”
刘大嘴就拉着我的手说:“咳!别问别问,兄弟赚了都有酒喝,走走走,咱兄弟俩弄几杯去。”
喝酒的时候,刘大嘴最终的话题还是回到嘴上那点事情上来,他说:“我都一年多没说相声啦,憋在肚子里的绝活使不出来,真他娘的难受!二哥,你好好听听,你看看我落功了没有?”说毕,他把一杯酒喝干,竟然当着我的面说起绕口令来。
“天上有个日头,地下有块石头,嘴里有个舌头,手上有五个手指头。不管是天上的热日头,地下的硬石头,嘴里的软舌头,手上的手指头,还是热日头,硬石头,软舌头,手指头,反正都是练舌头。”刘大嘴说的还是很溜,想必这几年也没落下练功,但他的两片嘴唇不再像当年那么红润了,涌上了一些白皮,白里透着紫,怎么看都像两条死鱼挂在嘴上。
饭馆里的人纷纷喊好,呼啦啦送上了热烈的掌声。刘大嘴意犹未尽,他倒满酒冲着我冲着大伙喊道:“谢谢,谢谢!”然后一仰脖干了。
我笑着说:“老小子你完了,你嘴里的唾沫星子喷我一脸。”
刘大嘴听后,趴在桌子上呜呜地哭了。我想劝他,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我端起酒杯冲着他说:“兄弟,我祝你艺术之树长青,祝你发大财走好运!”
刘大嘴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笑:“二哥,借你
吉言啊!家里还指望着我呢!”那天,我们都醉了。
我曾自己掏包买票看过他的一场演出。那天我去邻县出差,恰巧看见刘大嘴支起来的荷花湾艺术团。他的艺术团说白了就是一个偌大的蒙古包,钢管支架,帆布外皮,四周再围了一圈铁栅栏,只留下一个门口卖票收钱。我看到他的荷花湾艺术团时并没有太大的惊讶,但当我听到门口的两只大喇叭里传来刘大嘴的广播录音时,惊得我差点掉了下巴。
“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各位南来北往,东西而行的先生们、女士们,叔叔大爷婶子嫂子们,我们是驰骋南北独一无二的莲花湾歌舞团,在这里,你们将会得到帝王般的享受,将会感受一场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艺术盛宴……”
我仔细听了听,马上能猜出这是刘大嘴两片嘴唇碰击后发出的声音,这个声音我再熟悉不过了,几乎独一无二。从小到大,刘大嘴就指着这个活着了,他家的莫晓梅和刘莲儿也指望着这两片嘴唇活着,当然,他那位木头似的几乎变成哑巴的老爹刘解放也指望它们吃饭。换做刘大嘴的话说,他家有三个活宝,都是享福的命,只有他自己是“口吐莲花”的命,真想吐出“莲花”,除非他成神。
喇叭里的声音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们莲花湾歌舞团表演的节目有曲艺、有杂技、有大变活人,更有你想不到的刺激!我们莲花湾歌舞团有帅哥,有靓妹,有童男也有童女,更有你想不到的特殊表演……”刘大嘴的嘴真的可以“口吐莲花”,这些广告词繁琐、啰嗦、复杂、冗长,既不合辙押韵,又不讲究平平仄仄,但他说来却是那么流畅、自然,这些词几乎是自己溜到嘴边的,一不小心便蹦出来了。我觉得这哪是说话,这分明是机关枪嘛。
偌大的“蒙古包”里挤满了人,同时弥漫着各种气味。几位表演魔术、杂技、曲艺的演员心不在焉的,演出时根本没卖什么大力气。刘大嘴上台时,依旧说他的《口吐莲花》,捎带着说个返场小段。他精神头十足,起范儿也有号召力,几个回合下来就能要到掌声。表演结束后,他拿起话筒用他独特的嗓音和话速喊道:“先生们、女士们,下面将是我们莲花湾特有的脱衣舞节目,惊艳刺激,让你心动、让你激动,更能让你不能自拔,请大家伸出你们热情的双手,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美女们上场!”
在美女们的热舞中,刘大嘴在一旁喊着:“脱,再脱……”那些半老徐娘便把三角裤头往下脱了一下,又往下脱了一下。在五彩缤纷的灯光中,一撮撮小黑草若隐若现,引来阵阵尖叫。
我有些失落地走出莲花湾歌舞团,天空中竟然飘起了濛濛细雨。
刘大嘴出事后,莫晓美是三天后找到我的。这女人越来越有菩萨像,面色圆润,肩宽体阔,长着一身白肉。她告诉我,刘大嘴让派出所抓起来了。
莫晓美带着哭腔说:“莲花湾歌舞团让派出所封了,相关人员也被遣散了,单单抓了我家那口子,说是公开表演淫秽节目,要交五万块钱罚款才能放出来。”
我心里说,刘大嘴是团长,不逮他逮谁呢?我告诉莫晓美:“你别着急,着急也没有用,目前最要紧的是先把刘大嘴弄出来。”
莫晓美哭着说:“弄出来好办,可哪有钱呢?”
我反问道:“刘大嘴这两年挣的钱上哪去了?”
莫晓美抽抽搭搭地说:“花了……”
我有些无奈地看着她,摆了摆手说:“你先回家吧,我去想办法。”
说是有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我一个穷书生,当了将近二十年的小科员,手里也没有什么积蓄。东拼西凑,我和莫晓美才凑了三万块钱。我把三万块送到派出所时,派出所所长才慢悠悠发了话:“刘大嘴不是有箱货车么,不是有钢管帆布嘛,卖了吧,卖了换成钱就能把他放出来了。”
这无疑是最好的办法了。
刘大嘴出来时几乎变了一个人,莲花湾歌舞团在他被放出来时候,二手箱货、钢管、帆布等已经被一个南蛮子买走了。南方人很精明,善于察言观色,他看着我和莫晓美焦急的神情,马上猜到了我们所遇到的困境。这家伙一脸精明像,不急不躁不温不火,竟然把价格压了再压。我和他争论的时候,他总会笑呵呵的说道:“没事的啦,你们可以另找别人的啦……”人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莫晓美一拍大腿说了俩字:“成交!”
刘解放亲自到看守所接的刘大嘴,老头子精神头十足,除了一头白发之外,面色红润,动作麻利,乍眼一看,让人觉得他成了刘大嘴的儿子。刘大嘴一路无话,独自沉默,往日口吐莲花的本事一下子憋在肚子里。刘解放冲着他比划,意思是说:“你出来了,咱们一家就团聚了。”
我连忙說:“出来就好,出来就好,只要有人在,就能东山再起……”
刘大嘴的眼泪无声地滑了下来。
刘解放见到儿子哭了,一时间竟然愣在那里,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急得手足舞蹈。这老头拍着胸口,吭哧吭哧地说:“大嘴,别……别哭,我给你说一段儿……”
我们几个人停下来,惊讶地看着刘解放。这老头儿精神焕发,神采奕奕,立马进入到演出时的状态。他屏气凝神,慢慢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口说道:“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拉着五斤塔嘛。从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拉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拉塔嘛喇嘛的塔嘛。提拉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提拉塔嘛的喇嘛一喇叭……”
刘解放这位哑剧演员,终于爆发出了最强烈、最紧凑、最急迫的声音,他双目放着光芒,脸颊涌上一抹红晕,他越说越快:“也不知提拉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坏了别喇叭哑巴的喇叭。也不知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坏了提拉塔嘛喇嘛的塔嘛。提拉塔嘛的喇嘛敦塔嘛,别喇叭的哑巴吹喇叭!”
刘大嘴咧开嘴,搂着他爹刘解放哭了个昏天地暗。
刘解放的嘴从此如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拾,老爷子能说大段大段的绕口令,几乎不带卡壳的,简直是红豆碰绿豆嘎嘣嘎嘣脆。刘大嘴的嘴倒清闲下来了。有回,他领着刘解放在公园里散步,老爷子突然说:“听说你有个祖传绝活。”刘大嘴打了个机灵,试探着说道:“口吐莲花啊。”
刘解放把腰杆一挺,有板有眼的问:“什么叫口吐莲花呢?”
刘大嘴说:“您给我倒一杯水来,我就慢慢地掐诀念咒,一憋气我咕嘟咕嘟的,喝了……”
爷俩儿站在红彤彤的夕阳余晖里,完美的把这段《口吐莲花》说了一遍。
派出所通知刘大嘴把他失散多年的母亲领回家的时候,这家伙正在为刘莲儿的事情发愁。
刘莲儿又一次怀孕,已经四个月了。刘大嘴再次问到孩子的父亲时,刘莲儿平静地说:“你别问了,问了我也不会说的。”她依偎在莫晓美的怀里哭着说:“我和他一见钟情,只是他走了,消失了……”
刘大嘴张了张嘴,又把到嘴的话憋了回去。他和莫晓美把刘莲儿领到医院后,医生说:“这胎不能打了,若是再打,你家闺女很可能要绝育。”
刘莲儿平静地说:“那就留着,生下来。”
刘大嘴二话没说,领着刘莲儿出了医院。
夏小可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认认真真的听了一段刘解放的绕口令。这个老太太早就失去了当年的光鲜与美丽,岁月把她身上最美丽的东西都给削没了。刘解放爱上了说话,爱上了绕口令,对于夏小可的归来他波澜不惊心若止水,仿佛,夏小可只是他的一个最普通的也是最忠实的听众。夏小可的脑子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她能认出刘解放,但不认识刘大嘴、莫晓美和刘莲儿,碰上脑子坏的时候,她谁也不认识,只会默默地小声嘟囔:“魔术,魔术……”她被魔术师变没了,仿佛去了另一个世界,这么多年来杳无音信,别人已经把她遗忘了,可时间把她的青春
年华压榨完毕之后,突然又把她变了回来。这些年,她是怎么过的?魔术师怎么样了?她和魔术师曾在何处安身?这些都变成秘密了。
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
小十字街依旧孤零零的坐落在这座城市里,安静的活着,波澜不惊。但用一位分管领导骂娘的话说:“这地儿真他妈是一块毒瘤!”刘大嘴一家人就住在这块毒瘤里面,他们是一粒微尘,或者是一粒细菌。
刘大嘴领着刘解放、夏小可、莫晓美和刘莲儿从十字街里走出来,一家人一下子跳进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之中。我见到他时,他正扶着刘解放和夏小可坐在公园的长凳上,然后让莫晓美领着挺着大肚子上刘莲儿围着广场遛圈儿。刘解放对这呆呆发愣的夏小可说:“黑化肥挥发发灰会花飞,灰化肥挥发发黑会飞花……”
刘大嘴见了我,高兴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眯眯地说:“二哥哎,过几天刘莲儿快生了,你可要来喝喜酒!”他又走近一步小声说:“检查过了,是个大胖小子,哈!”
我握着他的手,十分滚热。“祝贺,祝贺!”
刘大嘴又说:“看见我爹了没?他老人家已经把绕口令练到非常之高的境界了。改天我还要挑班演出,我们爷俩儿任主要演员,保准一炮打红!”
“绝对红,绝对红!这真是个好主意,哥们。”我反过来,拍了怕他的肩膀说道。
广场上想起了一段优美的旋律,拉杆式音响里传来齐豫独特的嗓音:“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出开,一花一净土,一土一如来……”
刘大嘴十分自然的加入了跳广场舞的行列,他的身影在老头老太太这只庞大的队伍中并不怎么显眼。这家伙跳的很享受,抬腿甩胳膊外加摇头晃脑,沉醉并且沉迷。我看着看着,突然找不到刘大嘴到底在哪了。
城市中五彩缤纷的灯光映照着刘大嘴的身影,如同一朵美丽的花儿,花儿在绽放,散发出灿烂的光芒。
这是一朵正在盛开的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