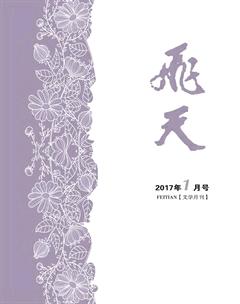《同尘》:心碎的说谎者
闫倩
一、复制与互补的镜子迷宫
单从已经给定的结构来看,《同尘》的骨骼脉络无非是许多多刘小美、许百川以及朵焉几大主人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剧表演模式,同一个舞台上咿咿呀呀唱着各自的悲喜交加,有锣鼓的喧嚣也有散场的寂寥,原本单纯完备,本身无可厚非。但从故事与人物构架的深层肌理来看,作者始终痴迷的是一种构建平衡与对称的渴望,这种渴望几乎如幼年时期搭建积木时对整饬的焦虑和对破坏的恐惧那般强烈。《同尘》不论是在人物形象设定还是故事情节设置以及场景道具的安排中,作者都始终处于对齐整的执著与渴望中。有自命非凡的乡村艺术家许多多,自有在名利场清高暧昧的电影导演许百川;有因为美丽获罪的刘小美,自有在空虚寂寞里画地为牢的朵焉;有许多多为之疯魔的《问道图》,自有许百川苦心经营的《卖画记》;有许多多走南闯北、抛弃任其野蛮生长的儿子傻子,自有许百川万水千山走遍也难相逢的女儿;有许多多落难处雪中送炭的女企业家,自有刘小美彷徨时无故闯入的政府官员……人物无论飞扬还是坠落,作者都在很大程度上专注于某种相似性的构造。这种形式给予了《同尘》内部“镜子迷宫”般的形态——出路丧失却不失希望,滞于困顿却仍旧挣扎。
许多多的行动和精神从表面上看是由他假想中与刘小美的爱情关系和实现艺术家梦想这两条线决定的,但不能被忽视的事实是,《问道图》中的幻境很大程度地篡改和规定着许多多的行动逻辑。许多多眼中《问道图》的奇异之处在于:
我看见一只蜘蛛从画上爬过,接着有一只飞蛾粘到画上,它在那里扑闪着翅膀。原来是粘到蜘蛛织好的网上了。飞蛾正好落在书生的长袖之上。它努力挣扎,就像是向书生求救。那时候蜘蛛在山间的树上,发现飞蛾之后,它就转身回来了。它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上,接着走在云彩上,从云彩里出来就到了山间的沟壑上,它顺着沟壑一直往下走,很快就要走到飞蛾身边了,飞蛾已经晓得自己是穷途末路,于是它伏在书生的衣袖之上,不再挣扎。它绝望的样子让我产生了同情之心。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这一只飞蛾。我正准备起身帮一帮飞蛾,这时候我忽然看见书生的衣袖挥舞了一下……接着我看见那只绝望的飞蛾摆脱了蛛网的束缚,欢快地飞到云彩里去了。它在云彩里变成了漂亮的蝴蝶。显然是书生救了飞蛾……
《问道图》提供了一个救赎性幻境,弱者因某种荣宠或是机缘被拯救,困局被打破甚至获得了升华。像画中的“飞蛾”“寻求施救者”或者“等待被拯救”是串联人物命运的一条暗线。
张三元作为许多多在洛镇上唯一一个朋友,唯一对他所有的说法都深信不疑、甚至完全相信许多多是可以飞翔的人。他们二人各自疯癫,本就属洛镇人取笑和排斥的边缘人物,卻能抱团结盟,让许多多生出些暖意和自信来。刘小美的存在和获取刘小美的爱情(即使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对许多多而言本身具有更宽广的救赎意味,是造成许多多人生欢喜与悲哀的主要源头,也是许多多在追求艺术的名义下“出走”和“归来”的根本理由。许多多如“飞蛾”扑向刘小美,这段“拯救”关系只有在许多多那里偶有落脚之处,其余全部落空。许多多虽是“飞蛾”,但刘小美并非前来搭救的“书生”,它只是对《问道图》里的一段虚幻关系的戏仿与重构。除此之外,在许多多眼里,杜先生、许百川、季老等人都是许多多艳羡的对象,他们在现世的成功成为许多多实现艺术家梦想的终极目标,与他们结交或者获得他们的救助成为许多多实现理想的主要途径,他们也是许多多人生道路重要拐点的设计者与参与者,许多多“等待被拯救”的愿望在表面看来貌似都一一达成,但实际上却是步步落空,许多多最终以丧失艺术才华和《问道图》的真迹为代价。
在许多多落难时刻伸出救援之手或者加害之手的所有人中,并没有一个人像《问道图》中许多多看到“书生”搭救“飞蛾”那般拯救他,这种拯救关系从一开始就是许多多的虚妄和幻觉,而作者用人物和事件搭建起的“寻求施救者”或者“等待被拯救”的逻辑层层叠加来证明拯救的失落与不可靠。这套拯救不可靠的逻辑放在刘小美那里同样奏效,以同样悲哀的姿态演练了一遍。在刘小美人生中行走的形形色色的男人如企业老板、摄影师、官员等,甚至在她最爱的许百川以及最爱她的许多多那里,刘小美获得一份这世上大多数女人都拥有的现世安稳的愿望也求无可求了。值得思考的是,在《同尘》中作者有鲜明的城市和乡村书写的立场,对于洛镇的两大主人公而言,他们被拯救的愿望屡屡落空是否也就意味着农村与乡土的没落和拯救的无可能呢?
二、被修葺的家族神话
除了《问道图》衍生出的虚掷和妄求之外,尔雅在《同尘》中还提供了另外一重意义完整的叙述空间,那就是由许多多和他父亲不断建构的家族传奇。对先祖辉煌业绩的追述本是一个锦上添花、美中作美之举,但作者选择让这一事件进入文本的时机正是许多多孩子生病夭折、妻子远走高飞、父亲神志不清之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谓十分恓惶惨烈。受到致命打击的许多多父亲突然开始说话、突然开始在院子里挖坑掘土,给傻孙子讲述先祖的光辉事迹。作者在此选择强行切入文本的方式,将部分的叙述权力交到听父亲讲述的许多多和傻子身上,“他对傻子说……”此时许多多作为主要讲述人的话语权和可信度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只能小心翼翼将讲述开始的紧张感转移到傻子身上,暂且将这个传奇来一番大致的勾勒:他的爷爷是洛镇力气最大的人,有一次洛镇大洪水,从里面捞出了三头骡子、两匹马。最后捞出来了一个女人。她的头发有五尺那么长,十斤那么重,像是乌黑闪亮的缎子。在这期间,为了更加确定和巩固许多多中心叙述者的地位,作者以辩解的方式削减许多多讲述的不可靠性——“到我父亲开始讲故事的时候,我才晓得父亲并不糊涂,他其实还很清醒;他对着傻子说话,但实际上是说给我听。”即使许多多父亲将这个故事讲三年,不断地在里面增添内容,许多多依旧在建构自己权威的叙述的身份“不过等我听了很多次后,我清楚地晓得,我父亲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至此许多多才将所有的叙述权力从他父亲那里小心地腾挪过来,开始一段新的全知全能的讲述。
此一番讲述从先祖家业的鼎盛到历经灾难、到先祖乐善好施的德行、再到文采武功的修为,无不以轻快的节奏“我先祖……”“我先祖……”拉动叙事和情节的运作,到先祖许文举时故事更是动荡传奇,讲得惊心动魄——抢得美人归,家族兄弟激战匪帮三日之久,再到迷恋这个女子到魔怔。而许多多的太爷爷也就是那位潜心收集书画的先祖许守章的故事也是集以上才子佳人的结构和传奇性、神秘性于一体。这位太奶奶的身世更加离奇,被從洪水里捞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带着一本《河洛书》,精准地预测洛镇的吉凶福祸,在某天变成一条鱼游走。这位太奶奶的神秘行径直接牵引着家族的兴衰,家族里出现一位反复讲一个故事十年的太爷爷。在许多多享有足够代言权力的时候,叙述又开始被收缩和质疑:“我根本不相信父亲所说的话。那些先祖的荣耀和苦难很可能处于父亲的杜撰,或者是他把一生收集的关于洛镇的传说全部归集于自己的祖先。由于不断重复自己的想象,那些故事逐渐变成了真实的景象。”
正是由于叙事口径在微妙中的调整,家族故事的传奇性才被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魔幻现实主义并没有让许多多的家族故事往神秘的道路上相去甚远,而是在一代代相似性病症的叙述中论证某种沉淀的、来源于基因密码的非理性的狂热和激情。这也就将许多多的精神内核最大程度地历史化、集体化,成为洛镇这篇土地的隐形气质和内在脉络。
三、暴露的说谎者和自欺者
许百川是《同尘》中极富暧昧色彩的角色,他可以在艺术圈子和商业领域都穿梭自如、名利双收,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左右许多多、刘小美以及一众女演员,也可以清高自诩,横眉冷对圈里的蝇营狗苟。他反反复复地自我确认着对朵焉的爱:
我们从未互相厌倦,即使对彼此熟悉到如同自己的身体。我们相拥而眠。我看见怀抱中她的美丽面庞。听见她自由、均匀的呼吸。她永远的迷迭一样的香气。她嘴角孩童一样的口水。那时候我在想,即使你拿世上所有的珠宝、青春和美貌来交换,我也不会给你;我甚至可以放弃梦想、生活,以及我半生追逐的电影……朵焉在床上熟睡。她发出细微均匀的呼吸。她蜷曲着身体,一条腿露在被子外面,光滑、饱满、美丽。她的怀里抱着一只枕头,仿佛孤单的孩子……我忽然落了泪。我几乎不能控制。我想我要到哪里去。然后,我该拿她怎么办呢。
而与此相应的是,朵焉总是在强调许百川是个骗子,表现得神经质、歇斯底里,动辄就会破坏东西、伤害自己,怀疑许百川与任何一个女人的关系,像一个不可救药的精神病一般消耗着对方。貌似在文本表面,这种紧张、尖锐的对立都是源自朵焉的无理取闹和任性妄为,实则是许百川在精神上欺瞒和隔离着朵焉,以致其疯狂。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专门探讨过人说谎的问题,在他看来说谎者完全了解他所掩盖的真情。一旦他有这个说谎的意向,他既不企图掩埋这个意向也不企图掩饰意识的半透明性,这个意向对后面所有的态度实行调节控制。那么朵焉的疯狂和许百川掩盖的真相就在于——“朵焉。我的女人。她微笑的样子、说话的样子、走动的样子,她身上淡香的气味,很像是另一个女人。有时候在恍惚之间,我以为那些时光并未过去……她是上天给我的一份最好的礼物。”朵焉与他女儿的相似性构成许百川画地为牢欺骗和囚禁朵焉的真正意向。如此看来,唯一一个章节关于朵焉的内容并不是为了粉饰他俩的爱情,而是把朵焉作为暴露和拆穿许百川谎言的最核心力量,将许百川失落的往日时光和隐秘的精神世界敞开。
跟许百川反反复复的自我确认一样,许多多更是将“你晓得的”“你晓得”这种直接被宣布出来的意向即使是他内心否定的对象,还是在表面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不同之处在于,面对根本的、被规定的态度时,许多多把它更多地转向自身,也就是萨特所讨论的“自欺”。许多多自欺行为的暴露更大程度是由刘小美的目光和视角展开的。“我是艺术家,电视台不应该跟一个艺术家收钱……我看着他说话的样子。我知道他在说假话。他的脖子和衣服领子上污迹斑斑,连耳朵都是脏的,至少一年没有洗过澡。他要是卖出了画儿,能是这个样子吗?……他说他已经攒了一万元了。他只要再攒够两万,就可以租一间小铺面了……还有,你要不要花钱?我有一万元,你想花就随便花,就当你自己的钱。他的样子看起来神神道道的。我就像他失踪了多年的亲戚。他愿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看。”这本是许多多辗转良久重逢刘小美时的幸福时刻,沉浸在这个场景里的许多多一定是幸福并骄傲的,但他的一言一举在刘小美的眼里却是可怜、悲哀,甚至是招人嫌恶的。同一事件里多重讲述视角的穿插和互相渗透的确形成了相互印证和拆台的强烈悲喜气氛。小说里的女性人物除了担当她在故事里的现实使命,更是承担了拆解和破坏情感关系中男性人物精神实质的结构功能,朵焉、刘小美都是如此。
“如果你理解凝视脚下黑暗的深渊能使人平静,那么你就不会往下跳。”朱利安·巴恩斯在他1984年的《福楼拜的鹦鹉》里如此写道。同样,一口气读完尔雅的长篇《同尘》,也有一种久在水底窒息却能抑住歇斯底里的笃定和安然。正如本书的末尾处所言:“我大声喊叫着她的名字。我的声音如此明亮,整个城市的人们都停止了走动。整个城市的人们都在看着我。那时候,我穿过街道、人流、汽车,向着她奔跑起来。”对,就是最后这个心明眼亮、有了个方向的“奔跑”让这一处起起落落、光浮影动的往事最终熨帖得像一个结局,哪怕此前历经过怎样的溃败。
(《同尘》,作家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
评论责任编辑 子 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