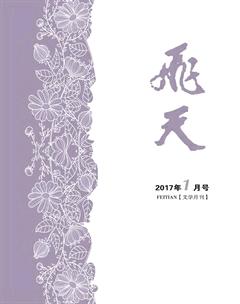临洮李满天
尧山壁
接到笔会通知,喜出望外。临洮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地方。“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是我启蒙的诗歌之一。作为边关要塞的象征,临洮是边塞诗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地标,一个闪闪发光的文化符号,一个家喻户晓的诗歌意象。中国诗史上众多大牌诗人,唐朝的王勃、王昌龄、孟郊、李白、杜甫、高适、岑参、韦庄,宋代的苏轼、陆游,莫不趋之若鹜,落在它的枝头,采花酿蜜,源源不断地给中国豪放诗派注入血液。
另一个原因是著名作家李满天,河北省第一届作协主席,我的前任。忘年交,亦师亦友,他正是临洮人。是李满天创作了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形象——白毛女,小说《白毛女人》发表在1942年6月延安《解放日报》,后来改编的歌剧,名扬天下。可大多观众只知贺敬之而不知李满天,为此主持改编的周扬于心不忍,一有机会就站出来替他说话。偏偏李满天为人低调,从不借《白毛女》宣扬自己,以致周围的人也有所不知。不像如今,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习惯把原作者称之为“××之父”。调侃一下,李满天真正是“白毛女之父”——白劳。
李满天离世已经二十四年,有时我觉着他还活着,回老家临洮养老去了。借此机会,去寻找他,寻找他与临洮的一些故事。
飞机在中川机场降落。果然是黄土高原,地是黄的,天是黄的,河是黄的,连刮过的风也是黄的。乘汽车穿过兰州市向南,公路两旁是连绵不断的黄土高坡。七道梁是市区的边界,进入长长的隧道,像一管望远镜,眼前出现了点点绿色。出口外便是临洮县,变了另一种景象,路边有了绿树,坡上有了绿草,沟里有了绿油油的庄稼,好像沙漠里见到了绿洲。心里纳闷,这一切是怎么变出来的?
到安家嘴答案有了,洮河,眼前出现的一条大河。远看还不解气,下车走到它身边,好生打量一下。一百多米宽的河床,浅绿色的河水,水汽蒸腾,浪花欢跳,一个个漩涡张着大嘴唱歌。洮河欢快地流着,有声有色。
洮河是黃河上游第一大支流,源于甘南碌曲西倾山,地高流急,冬不结冻,满河碎冰,“洮河流珠”是一稀世奇观。进入临洮境内,水势平缓,便于灌溉,“洮河千里,唯富临洮”,形成一条二百多里的米粮川,人称塞上江南。同时自古也是屯田之地,有“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之美誉。
又几十里抵达县城。这临洮真个好风水,西临洮河水,东靠岳麓山,顺风顺水,气象不凡。怪不得李满天如杜甫诗中所说:“年少临洮子,西来亦自夸。”提起家乡,就像作诗:襟带河湟,控御陇秦,西北咽喉,丝路枢纽,名在阳关之上,位与敦煌比肩……建城已经两千三百多年,临洮县志上说,汉城在北,唐城在南,宋城在中。李满天印象里已是明清建筑,站在东山俯瞰,东西南北四条街成丁字形,加上四条辅街是卍字形。街道整齐,林木葱茏。左宗棠做陕甘总督,提倡种树,临洮境内植树一万三千三百株,严加管护,损一树杀一人。李满天幼时,还曾看到“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尖”的景象。我这次住在县招待所,院里一棵大树,树干埋了半截,树冠郁郁葱葱,见人就问什么树种,没人答得上来。来了一位四川客人,说是青,他们那里的常见树种,是一个“移民”。
李满天1914年生于县城线市街毛家巷,老宅已经改造成楼房,面目全非。只有他上过的养正小学还在,后人不肯动它。临洮一向崇文重教,汉时以“举孝廉”闻名天下,宋时设西罗“番校”,是中国最早的一所民族学校,左宗棠都陕甘,建书院二十所,修复书院十所,义校十所,就有洮阳书院和一所临洮义校。李满天就读的养正小校,是开明乡绅杨明堂创办的,捐银一千八百两。杨明堂清末秀才,师范毕业,有志于教育。其父想给他捐个知县,他却热衷于捐资兴校,先后创建农校、女校等十余所,花费白银万两,受到甘肃省政府、民国总统黎元洪嘉奖。杨明堂办校认真,每个学校都定了校训,“勤苦朴实”,“端谨朴诚”等。养正小学的校训是:“养心存大志,正气做完人“。刻在校门口,也刻在李满天的心上,一辈子不曾磨灭。
毛家巷临近城隍庙,前后左右聚集了几十家洮砚店铺。洮砚与端砚、歙砚并称中国三甲。洮河中的绿色水成岩,莹润如玉,叩之无声,呵之出水珠,用以制砚,储水不耗,历寒不冰,涩不留笔,滑不拒黑。发墨快,研磨细,浓淡相宜,得心应手,深受文人青睐。陆游说:“玉屑名笺来濯锦,风漪奇石出临洮。”黄庭坚说:“洮州缘石含风漪,能淬笔锋利如锥。”洮石深绿而带水纹者叫绿漪石,带黑斑者叫墨点,带珠砂点者叫柳叶青,夹杂黄色痕迹者叫黄标绿奇石,最为名贵。古诗说:“洮砚贵如何,黄标带绿波。”石材经过下料、制坯、雕刻,制成形形色色上百品种,拟人状物、类山临楼,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精美绝伦。
少年李满天放学之后,常常出入砚铺,这儿看看,那儿摸摸,流连忘返。父亲早亡,祖父年迈,母子二人种几亩薄田,十分想拥有一方砚台而手中少钱。一次看一位师傅雕“牧童放牛”,将近收尾时稍有疏忽,碰掉一只牛角,功亏一篑,十分懊丧,举手要把它摔掉,李满天急忙拦住,一边哀求把残砚施恵于他,一边从怀里摸出几枚早被小手摸光的铜钱。师傅看孺子可教,免费赠送于他。李满天得了洮砚,发奋习书。买不起碑帖,但临洮寺多,九庙八殿、七祠六牌、四庵一宫,挨家摹写匾牌楹联,进步飞快,小楷作文经常在全校展览。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郭沫若传到临洮,乡绅杨明堂办了师范学校,经常邀请江苏南通教师来校讲课,也把一些进步文化教育理念带进临洮。李满天办了一份《新临洮报》,新锐思想加上清秀字迹,给古城打开了一扇亮窗,人们争相抢购,也对贫瘠的家庭有所补贴。不料激进言词冒犯了当地财主,串通县长要抓他送监,不得不躲避一下。
出逃前一个黄昏,李满天独自一人来到东山,先到升仙台跪拜老子——李耳是他陇西房李家的始祖;又到超然台揖拜忠愍公,就是杨继盛,号椒山,河北容城人,明嘉靖朝兵部主事,因谏仇鸾开马市,错贬临洮典史。杨继盛到临洮,除积弊,开煤矿,兴教育。为兴教拿出薪酬,卖掉乘马,又变卖夫人首饰,在岳麓山建超然书院,亲自授课,从者五十余人。置校田两千亩,补助困难生员。又在城内圆通寺设书馆,招收藏回学生三百人,政声显赫。第二年离任时,逾千人含泪相送。回京后因弹劾奸贼严嵩,被车裂京城西市,年仅四十岁。后门生邹应龙、张万纪(临洮人)扳倒奸党,完成遗志,杨继盛被追封“忠愍”。临洮人为了纪念他,于城内建杨忠愍公祠,将东山超然书院改名椒山书院。杨继盛手书的两副楹联,“十两黄金轻一芥,百年名节重千斤”,“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被少年李满天抄来做座右铭。
黎明,母亲送别儿子于三岔河桥,望着桥下一去不回的洮河水,抓住儿子衣襟不肯松手,老泪淌在多皱的脸上,曙光的殷殷如血。李满天强作笑颜,谈古论今。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从这儿出发,开通丝绸之路,我们这儿才吃上葡萄、石榴、苜蓿、核桃、大葱、大蒜。名僧法县、玄奘从这儿出发,渡流沙,过葱岭,九九八十一难取回真经。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从这儿出发,翻山越岭到西藏和亲,换回来几代人的和平。儿子此次出门,也许会取回真经,使穷人过上好日子。
李满天怀揣一方洮砚到了北京,卖字刻章,代写书信,一边挣钱糊口,一边到北大旁听。1935年正式考入北大中文系,参加了“民先”,一二九运动爆发,他是组织者之一。七七事变后投奔延安,进鲁艺文学系二班,任班长。1939年深入敌后,到晋察冀抗日前线。1947年挺进大别山,南征北战,枪林弹雨,一方洮砚始终带在身边。
解放后任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省文化局副局长。脱下军装,想起土地,重返河北,一头扎进定县西建村搞农业,一呆就是五年。冀中平原旱地多,望天收,使他想起故乡洮河盆地,河渠纵横,自流灌溉,年年五谷丰登,他就是在洮惠渠边长大的。我堂兄告诉一个故事,他在曲阳县修王快水库,从定县来了个老农,建议从曲阳到定县修条水渠,能增加一百万亩水田,线路图他都画出来了,细问才知道是作家李满天。1965年春节刚过,我俩来到临西县东留善固村,一片沙窝,又没水源,他组织打井,春寒料峭,跳进水里,衣服挂了一层冰,明光光好像盔甲。他身在农村,为农民写作,反映农民的喜怒哀乐。长篇小说《水向东流》三部曲,被誉为河北平原的《创业史》。中篇小说集《力原》,受到茅盾先生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那个时代“问题小说”的代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李满天到正定县深入生活,发现和培养了贾大山,我作为县委顾问,也常常去凑热闹。三个作家一台戏,贾大山唱梆子,我唱京剧,李满天唱秦腔,还唱洮岷花儿:“想你想得睡不着,抬上板凳院里坐。星星数了三遍多,一直数到月亮落。”县委想让贾大山当文化局长,大山不愿出山,还是李满天设计赚他下山。李春雷的报告文学《朋友》,有七处提到李满天的名字。
李满天一生最贴近的古人是杨继盛。记事时门前的闹市已改名椒山街,公园里的亭子叫“忠愍祠”,连日常提水工具都叫“杨杆”。心里有了杨继盛,做人做事常带血性。1979年,青年作家李克灵写了一篇小说《省委第一书记》,主题是废除干部终身制,老干部让贤。年迈的省委主要领导以为影射自己,稿子从已经编好的《河北文艺》撤下来,还专门出了一期红头文件,通报批评。而且打了还要罚,要处分作者,下放当工人。李满天看不惯,认为学术问题应与政治区别开来。要吸取以往教训,不要先无情打击,过后再甄别平反。苦口婆心反映意见,最后讲到全国党代会上。领导以势压人,李满天则不畏权势,结果被勒令辞职。这振臂一呼,引起社会反响,李克灵免遭一劫,也保护了更多青年作者。后来证明,《省委第一书记》是一篇好作品,干部终身制废除了,李满天的职务没有恢复,他已经超过六十五岁了。令人不解的是,后来发表过一篇报告文学《省委第一书记》,是北京作者写的,专门写那位年迈领导事迹的,他肯定知道此中内情。全省上下议论纷纷,他也没有辞职。
话说回来,李满天也并不想当官,何况文联、作协的职务也不是什么官儿。厅级干部他都当了三十多年,还不照样出无车,常年在乡下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乐得无官一身轻,安心地写小说,有短篇有中篇,还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地委书记》。1990年带妻子回临洮,母亲不在了,杨明堂不在了,东山依然在,洮河照样流,椒山祠修茸一新,洮恵渠又在延伸。让他感慨的是,临洮这座西北名邑、陇右重镇,已经被铁路线甩在一边。两千多年的郡、路、府、州治,专员公署,1929年降为县级,风光不再了。他想,文脉也不会完全输给铁路,兰州人有事还往临洮跑。
李满天病重住院期间,探望者络绎不绝。他是一个乐天派,照样开玩笑。没人时,给我说有两大遗憾,一是《地委书记》没有写完,二是爱人李茵的问题还没解决。李茵1945年入党,1947年参加工作,正科级。1958年号召干部下放,动员大会后没人报名。李满天是党组副书记,动员自己家属带头,下乡当农民,一下就是二十年。好容易等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相同情况的人都解决了,就卡住她一人,可能因为《第一书记》的问题。当初下放,为国家担担子,家中的担子一人担,没了他谁担?这让我想起从前在创作会上他讲的,作家是苦命人。他还引用司马迁的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离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而今不光他苦,连老婆也成了苦命人。
遗体告别那天,人山人海,一半为李满天,一半为李茵。贾大山说了句心酸话:“创作了《白毛女》的人,他成了白毛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