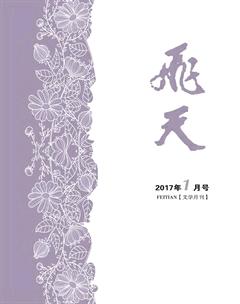命 运
程平
我爸被消化科专家怀疑为不好的病,做了好几个检查,到下午才能得到结果。我在住院大楼下花坛边的长椅上坐下,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眼前的海棠花开得浓艳,然而它们不过是一树树血红,在我心里激不起一丝春意。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只能说,医院是个折磨人的地方。门诊楼大厅前人来人往,每一张面孔上浮现着一张检查单,他们的脚步那样混乱,如同行走在逃难的轮船夹板上。我呢,坐在一座荒岛上或是在另一只小船里吧,我们之间隔着茫茫的水雾。门诊楼冷峻地矗立在一片阴影里,当我把目光投到远处日光下的地面时,一种苍凉和忧伤混合着的浑浊感缩紧我的前胸后背。我需要到那边坐坐了。可是我爸出去一阵子了还没回来,他就是从这里走开的,说他到医院背后的花鸟市场转转。我只好在这里等着了。
身后的平台上有脚步朝我这里走来,一种虚弱和拖沓的脚步声,这不是我爸的走路。这个脚步在我背后的右方停下了,发出轻微的衣服的窸窣声。这个人似乎是在朝我脸上看着。我被一片暗影笼罩了,支棱起神经感觉着,他是一个乞讨者或是打扫卫生的抑或是看病的人吧。正当我准备扭头的时候,一个嘶哑的声音低声叫响了:
“小宁……”
我在记忆里迅速地寻找着这个熟悉的声音,就看见了这张熟悉的脸面。我不由地惊愕了:我和他不过四五年没有见面,他竟变成这副样子了,头发稀少而花白了,脸瘦得厉害,横七竖八地挤满了皱纹,尤其眼角周围,密得像刻画的。
“是弘强啊?”我在惊愕中站起来握住了他的手,“你怎么也来这里?”
他木然地笑了笑,滑稽地挤了一下眼睛,“我来给自己检查检查。”
“哦,你怎么了?”我看着他的脸,除了过分的憔悴还有几分怪异,“你一下子瘦成这样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这话一说出嘴,我立刻有些懊悔,对病人不该说这样的话的。
“唉,我有病啦,”他示意我坐下,我俩几乎同时坐下了,“前两年就检查出了糖尿病,这最近又神经不好,睡不着觉,看这眼睛,老挤个不停。”
我认真注意他的时候,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大幅度地挤了一下,接连又猛地两下,完全是不由自主的那种抽动,让看的人替他干着急。
我不忍心再观察他的脸了,望着他的曾经差不多是我的两倍如今和我差不多粗细的腿,斟酌着说一些安慰话:“你是有些挤眼睛,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症状在小孩身上很常见呢,大概就是一种什么植物神经紊乱病吧。”
“你说的挺在行,大夫也说过这样的话,可是药吃了好多,没见什么效果。”
“这种毛病,吃药就是见效慢,得一个过程,心理放轻松就会好些的。失眠也是那样,估计是你心理负担太重了吧?”
“是啊,就是这样的……”他焦枯的大巴掌拍了拍我放在长椅边上的手背,“就是这样的,你真的挺懂。”
“呵呵,”我淡淡地笑了笑,“你不要忘了,我过去可是爱看医学书的。所以,你这真算不了什么毛病,不要太当回事,自己调节好自己的心理……”
“唉——”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这我知道,可是哪有那么容易?我的心理负担确实太重了,不容易调节的。嗨,我把自己弄得太累了……”
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有些话他不好说出来,有些话我也不好问;但我心里明白,他目前是什么处境,在学校里经历了什么变化,我大致是知晓的。这么多年里,我身在森严的县委大楼里,心依然牵系着那所遥远的乡村中学,我的青春消逝在那里的尘埃中,有一个人至今在那里没有离开。可是毕竟离开那个学校十多年了。那时候我和宋弘强是亲密的同事,因为年轻人爱和年轻人在一起,早晚打打篮球,夜里去街上的歌舞厅里唱歌跳舞,他是语文教研组的组长,我们没有什么隔阂。如今人家已干了五六年的校长了,面对领导时人们难免会生出些许卑微感来,而对于他,我也算个政府人员呢。人的身份变了,说话自然就不一样了。
沉默了一瞬,我只好轻描淡写地说:“是啊,你也不容易,如今的校长不好当,事情多,责任大,加上现在学生难管理,是挺累的。抽煙吧。”
我摸出一支红塔山烟给他抽,我这烟不好,请他别嫌弃。他瞅了瞅我的烟,摆摆手,说他戒烟有两年了,见了领导也不给发烟。不过他很快又主动向我要了一支烟,我拿出打火机给他点燃。他猛吸了一口,徐徐地吐出,凝紧眉头望着远处的什么地方。我们不说话,但因为都在吞云吐雾,所以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
“还是抽烟好啊!”他已经抽完了半支烟,眉头舒展了一些,依然那么地望着远处,“抽烟能让人得到一时的放松,我想再抽烟了。”
“怎么能呢,烟戒了就不要再抽了,不好。”
“唉,我知道不好,可是都混到这一步了,哪管那么多呢?有时候整晚整晚地睡不着,第二天头昏脑胀的,还得去应付人家的公事,真的累啊。”
“失眠是挺费人的,找个好医生调理调理,会好的。说到底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就知足吧,混得挺好的,多少人羡慕还达不到呢。一个中学校长也统领着几十名教师吧,这年头学校分来的净是女青年,开会时老兄你风流倜傥地在前面一坐,多风光啊!”我跟他说起了轻松的玩笑。
他就苦笑了笑,脸上显出些愉快的颜色,跟他说这样的玩笑,在过去会让他得意得满脸红光一阵子,我深知他的秉性。
“唉,还是你好,小宁,还是你好啊!什么心也不用操,生活安逸,说真的我羡慕你。”他手里的纸烟快燃烧到过滤嘴了还深深地吸了一口,若有所思地眯缝着眼睛,左眼——他自己是右眼——剧烈地抽了几下,粗大的喉结那里缓缓地蠕动着。他抬起手用衣袖不停地擦眼角,“你说咱那时候多好,平平淡淡也快快乐乐的,说起来挺怀念的。可是人生没有回头路啊!你看我现在,弄得多惨的。唉,忙忙碌碌的,孩子孩子不争气,女人又老跟我吵。身体弄成这样了,到头来又得到了什么呢!你在上面干着,知道现在的形势,这社会给人的压力确实太大了——也怪咱有时候没有把自己把持好,可是你又知道,以前社会不是这样的,混个一官半职谁不想着落点好处?可是现在社会又变成这样了,真是愚弄人啊!嗨,也算是社会的牺牲品了。”
这时候我的电话恰到好处地响了。我接完电话发现他在怔怔地望着我,等待我再次听他诉说,眼睛更厉害地挤了几下。
“我现在,唉,自己落到这一步了,又能怪谁呢!”他好像好不容易才遇到一个倾听对象那样抓住了我,也不顾我的情绪,自顾自地又说开了,“总之是不平顺,人走败运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缝,这两年学校教学成绩也上不去,学生接连地出了几起事,代课老师捅的乱子,上面追查下来都推我头上了。有的老师还恩将仇报呢,这里反映那里反映……”
我突然想到,如果听到他这番话,有一个人会高兴得笑的。我打了个哈欠,拿出手机看微信,妻子给孩子包了饺子晒在朋友圈了。十二点过十分了,门诊楼大门前还坐着不少人。
“现在的公事形式又多,你知道的,三天两头地来检查的,正事没时间干,净跟着瞎转。”
我忍不住问:“学校里能有什么形式搞呢?”
“嗨,如今学校里形式可多了,你离开学校久了不了解。就这最近,什么安全的、综治的、营养办的、消防的、食药的、标准化验收的、省上‘迎评的,精准扶贫的也添乱呢,乱七八糟的差事,一个连着一个,个个都是责任。‘校长是第一责任人,真是要命!校长又不是万能的,这破校长他妈的干得人真是泼烦。现在的老师也不好使唤,公事要大家干么,推三扯四的,他们看着我这样,巴望不得我倒掉呢……”他滔滔不绝地讲着,神情有些激动了。
我坐立难安。一辆救护车凄厉地叫着冲上住院部侧面的弯道,几个医生抬着担架候在那里,我心里一阵凄惶,不再看了。我爸还没回来呢,我可没心思再听宋弘强说什么了。这时候他的电话响了,他拿出手机看着,迟疑了一下才接了,说了没几句就挂了,丧气地摇摇头,似乎是学校的什么事。他就黯然地看了看我,好像看陌生人那样,又像近视似的皱了皱眼睛。这样子有些荒诞,过去他脸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神情。他刚才那么自主地给我说了一堆充满幽怨的话,让我怀疑他有点神经质。我狐疑地观察他,这时候他抬起胳膊擦眼角的眼屎,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开始打哈欠了。
我怕他不厌其烦地继续说下去。从内心深处我对他的处境挺同情的,如果有时间并且有个不错的心情,我愿做他的倾听者,甚至开导开导他,但是今天很遗憾。其实有些事不用他说我也知道的。要是愿意说说他如何贪婪地敛财或者纪委下来查账的事,我倒是想听听,但他只字不提,敏感地提防着我,这说明他没有什么不正常的。门诊大厅门侧的台阶上坐着的一个妇女掀起衣服给怀里的孩子吃奶,身旁坐着一个女孩子抱着一瓶饮料喝,孩子的爸爸哪里去了?他们是给怀里的那个小孩看病吧?他们就那么地坐着等下午的上班时间吗?我的心里紧缩了一下,再过几个小时才能知道我爸的检查结果,谁知道他会是怎样的?我得想什么办法摆脱弘强,要是他再开始长篇诉说,我除了厌恶别无选择;不要忘了我们来医院是干什么的。
他似乎意识到我的不用心,知趣地说:“小宁,对不起,我今天啰啰嗦嗦跟你说了这么多,你看我这脑子,混混乱乱的,自己都不知道跟你说什么了,只是觉得咱过去能谈得来,还把你当成过去那样,心里压抑着什么就跟你说什么了。你看我现在这样子,嗨,让你见笑了。”
我释然,又有点羞愧刚才对他那样的想法,说:“没什么,感谢你信任我,老兄,乐观些吧,一切会好起来的。”
“但愿吧……”他的眼角耷拉着,似乎想睡着了。
我给他发烟,他没有拒绝,我俩又抽上了。我主动跟他提到了给我爸检查病的情况,想听他说句宽慰话呢,他只是皱着眉头抽烟,麻木地点点头,或者又引到了他自己的病况上。我便看到了他本性里自私冷漠的一面,彻底厌恶了。正要给我爸打电话,就见他小跑着往这边来了,褂子搭在肩膀上。他一手提着一塑料袋君子兰苗子,另一只手端着一棵开得热烈的盆花。弘强起身跟我爸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我和我爸都惊诧于他告别时那样的匆促,那样的言语也不近礼貌。他过去可不是这样。他下了台阶往前走了,佝偻着胸,步履迟滞,好像在地上寻找自己的影子。
“这不是新明中学的老师吗?”我爸望着宋弘强的背影问我。
“是的,人家当校长都几年了。”我轻淡地说。
“我知道,宋家湾人么,他爸过去和我很熟悉呢。应该跟你差不多年龄的人么,看上去那么苍老。当校长有什么好呢?还是平淡的好,无官一身轻。”
我爸颇为得意地炫耀他的花,买得多便宜的,在县城里那一盆君子兰要卖多少钱呢。对我爸这种贪便宜的行为我向来是很看不惯的,他都不知得了什么病,还在这等事上花心思。然而我爸是不以为然的,并不认为他会得什么大病,到饭馆的时候还高兴地跟我谈他在花鸟市场的见闻呢。这方面我不能较真,他能这样其实挺好,不管有没有病,人的心态很重要的。面端上来了,我爸让我先吃,他从衣兜里摸出一包药吃了,我的心情又沉重了。我的心情大概是顯在脸上了吧,我爸又安慰我了,让我不要担心,他不会有大病的,他那样的身体怎么会有大病呢,让我安心地吃饭。这饭我怎么能吃得专心呢?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真实心理。宋弘强从面馆前缓慢地摇过去了,高大而弯曲的身材,下巴往前探得很低,正如老山羊的形象。我的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他的背影远了,给我撇下一团阴影,一挤一挤的眼睛、枯槁而呆滞的眼神、眼角里黏糊糊的眼屎、鼻孔里奓的像公猪性器官周围的黑毛、哀怨的沮丧的声音,如影视画面里的特写镜头忽明忽暗地在我脑海里闪现。更要命的是,他的那样的阴影和我对我爸的忧心搅和在一起了,我的心情糟糕极了。
终于等到了检查结果,多么让人焦灼的等待过程啊,然后拿去给专家看。诊断结果是我爸有胃溃疡,开了药。我不放心,拿着检查单找另一个大夫看,诊断还是胃炎和胃溃疡,增加了胃炎这一项,这不大要紧的。我爸就怨怪我花冤枉钱了,让他受了那么大罪,那么多钱还不如给他买几盆花呢。你老人家这是什么话嘛!谁都希望来医院的结果是白扔掉几个钱而不要检查出什么大病。我心里到底是轻松了。取了药从医院出来,天色不早了,我把车开得很快。
经过红场梁时我爸指着宋湾村给我讲风水方面的话。我不大信风水方面的事,不过宋湾村的风景很不错的,地形开阔、舒展。正是如画的仲春时节,夕阳快下去了,这个村子沉浸在一片金光里,看着让人心情爽朗,学校墙外的那一圈钻天杨和垂柳,绿得颇有诗意。在村旁的一弯平地里,散落着很多坟墓,我爸指着山脚下一座很大的两边长了两棵柏树的坟地给我看,那是宋弘强家的老坟。这我知道的,多年前我们学校老师去给他爷烧过三年纸呢。我爸问我注意到坟前的那几块碑了没有?大理石的,前两年刚立的。宋弘强弟兄撺掇他爸把老坟给翻修了,坟穴用青砖砌起来的,因为给坟“拨向”的事宋弘强爸弟兄几个闹得很凶,这半个片的人都知道。这事我爸不说我还不知道呢,我就想到宋弘强有多迷信了。越是当官的人越是迷信,宋弘强弟弟宋弘民如今是红山乡的乡长。我和宋弘民是初中同学呢,弟兄俩自小就没了娘,冬天穿件蓝棉裤,没有套裤,裤裆那里时常积着云茬一样的尿垢,那情境至今印在我的记忆里。不过宋弘民念书很优秀的,因为刻苦,他总是第一名,我只能第二名,后来他考上农校出来当了乡政府干部,我考上师范出来当了老师,和他哥哥宋弘强工作在一个学校。我和宋弘强也是师范校友呢,只是我进校的那年他刚好毕业了,听说学校常给他照顾,勤工俭学或贫困补助什么的总少不了他的。
如今人家宋弘强弟兄可谓光宗耀祖了。然而今日看见宋弘强的那副模样,真不敢恭维。我调走后的几年里宋弘强才当上领导的,后来又当了校长。关于宋弘强的当校长有个戏剧性的典故。老校长李录生好赌贪色,和村里的一个学生偷在一起,两人在办公室里睡觉,被捣蛋学生从外面锁了门。那天正好来了检查的,宋弘强开了门把局里的领导请进校长办公室,李录生和女学生躲在套间里面大气都不敢出。检查的领导刚走,李录生女人找上门来,踢开了套间门,那女生跳窗的时候扭伤了脚没能逃脱,被李录生女人抓住打了一顿。女生的妈妈闹到学校来,轰动很大,李录生没脸在那里混就调离了,彻底告别了领导生涯。宋弘强名正言顺地当了校长。后来我从好几个人嘴里听过这样的话:那门并非学生锁的,而是宋弘强作弄人,李录生女人也是他从家里诱哄来的。这个传说恐怕不是空穴来风,据我跟宋弘强相处多年的了解和对他们关系的分析,那事他完全干得出来。当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过是“莫须有”罢了。
宋弘强干校长有十多年了吧?那年头他一直风光得很,脸面发胖了,腰杆子挺直了,大背头梳得顺溜,买了辆桑塔纳开着,乡政府的桑塔纳2000,他的桑塔纳3000。他当校长正好赶上学生的“两免一补”政策,新明中学学生多,经费充裕,据说他很能勤“捞”致富的,要发给学生的补助或是教师的福利,他瞅着瞅着就装进自己腰包了,富有得让多少人眼红呢。那年头,走运的不止宋弘强,大环境如此。有人戏笑说,晚上在县委家属院里徘徊的人,一棒子打倒十个,有九个是背着一包“红张张”来跑中学校长、卫生院院长的,抢劫客也盯上了那里的买卖。
可是如今风声紧了,有一批人的日子不好过了。于是他们怨社会,还有人怨祖坟,到底该怨谁呢?我曾经为自己的清贫而羞愧——我不过是个俗子,如今呢,又有些人要庆幸自己的清贫了,而有些人要苦于自己的腾达了。想想今天看见的宋弘强的情状,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时间过得真快。那天给孩子开家长会回来,办公室里就我一个,百无聊赖中一杯接一杯地喝茶。有人敲门框,我抬脸看,就看见了王子兵肥嘟嘟的红脸戳在那里,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我把他请进来,两个人戏谑地亲热着,给他冲了包县长办公室偷来的金骏眉、发了支红塔山,还看不上抽,要好烟。我就这烟,不抽拉倒。子兵把我的办公桌翻遍了,没有找到一支烟,就拿出他的黑兰州给我抽,笑话我一个干行政的连包好烟也没有受贿到。我这算什么行政?至今连个待遇也没解决呢,这崽子都快评副高了。
“谁让你调呢?你不调如今也能弄个什么领导,副高早揽到手了。”
“唉,要知道如今这样还不如别调呢,教师工资高,又有乡村补助,工资比我高一千好几呢。你们现在抽黑兰州,我就这红塔山还得数着根根抽呢。”
“你得了吧,揣着大款叫穷。我们那两个穷补助你们也看上?政府可怜我们乡里人的,你们的灰色收入不知比我们肥多少!”
“什么灰色收入?连个灰色屁都没有。真的,猛然想想,还挺怀念咱们新明中学的。”
“你哪里是怀念新明中学,你是怀念刘雪梅呢。”
“你那麻雀嘴,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自己脸都红了。提起她,我的心如一锅沸腾的五味粥。刘雪梅比我迟两年分配到新明中学,她是我们中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女教师,她一来我就第一个追求她,我积极地给她收拾房子,给她做饭。她的容貌平淡得如同新明村的水土一般,但那双眼睛还是能够吸引几个男人的,尤其人家是有工作的。我和她处了有半学期,处得足够深了,子兵却告诉我刘雪梅跟乡政府的民兵专干搞在一起了。我像侦探家那样搜寻到了蛛丝马迹,并且我的一根筋不可扭转,将人家堵在她的房间里。那时候,羞辱和绝望让我简直——唉,不堪回首。由于某一种心理,我索性和中心小学的民办教师吴瑞芳谈起了对象——之前她对我示过意我还没有把人家放在眼里。要不是刘雪梅对我的打击,我就不会和吴瑞芳结婚;不和她结婚,我就沾不了她舅的光调到团委,大约也就不会有我们的祥瑞窗帘城;没有窗帘城,哪有我的大房子住哪有我的朗逸車开?这话就俗了。最是她生给我的一对宝贝,是我此生的骄傲呢,活泼聪慧,两个都上初中了,学习成绩从来都名列前茅。你说我是该恨刘雪梅呢还是该感激她呢?
我就转移了话题:“弘强现在怎么样?”
“宋校长么,”子兵轻淡地撇了一下嘴角,“嗨,现在可怜了,可怜了,那样子你没见——”
“我见过,不久前我在市医院遇到了,眼睛一挤一挤的。”
“挤眼睛那时候还算好呢,现在所有的五官都挤,嘴一歪一歪的,脖子一拧一拧的,正像羊羔疯发作时的样子,鼻子也皱,这样——”子兵站起来模仿着,我忍不住想笑,但这事我能笑得出来吗?子兵又学起宋弘强走路的样子来。
“有那么严重吗?”我惊诧地问。
“这还不算什么,你没见现在头发都白了,人瘦得快成一把干柴了,晚上睡不着觉,一天萎靡不振的,净打哈欠,有时候半夜就来学校了,像夜游虫一样。有一天早上——就是上周的一天——天蒙蒙亮,我从厕所出来看见校长办公室门开着,就寻思这么早这老鬼在里面干什么呢?我走进去,黑灯瞎火的,好不容易才寻见人,在办公桌旁的一摞打印纸上躺着呢,蜷缩得像只鸟。那么大的沙发放着偏要躺到打印纸上睡!我看着一动不动,怕是出事故了呢,就唤了一声,那‘哼了一声,我又唤了一声,那又‘哼了一声。我见没事,就转身往出走,没想后面那就‘嚯地翻起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嘛!没看见我在睡觉吗?那声音,哎呦,恶狠狠的,从没见过哪个人那么凶过,眼睛瞪得像豹子一样,黑影里都能瞅见呢……”
“听那样子是不是精神出问题了?”
“恐怕快了。”这时候子兵端起茶杯喝水。
“茶怎么样?”我卖弄的目光望着他。
“好么,领导喝的茶能不好?”子兵又说开了宋校长,“真是精神出毛病了,只是这最后一段日子,看着是明显了,我几次发现一个人说话呢。一个女老师请产假了,物理课没人带,给谁也分配不下去,就你校长没代课么,就自己带了。他那样的情况能代什么课?家长会上闹得凶得很。”
“怎么能那样?那么大一个学校,几节课都排不下去吗?”
“病猫吓不住老鼠,以前把老师管得那么严,现在没几个人把他放在眼里了。尤其刚毕业的那几个年轻人,势利得很。弘强盛的时候都像哈巴狗一样,争着舔尻子呢,半夜里提着五粮液鬼鬼祟祟敲人家门,现在那落难了,看你的笑话呢……”
“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这两个成语从我嘴里脱口而出。
“就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那心里能不堵吗?还有更过分的呢!一天上早操,八一班班主任没到岗,班里队伍乱得很,校长跑去人家窗子上看——也怪他轻贱,被人家一口咬住,‘你窥探个人隐私呢,我两口子睡觉是你看的吗?要不是我和永林几个拉住,差点被人家捶了一顿,气得都说不出话了。屋漏偏逢连阴雨,这事直接加剧了,快崩溃了。精神压力大得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又惊醒,怕纪委来查他呢。嗨,那可怜样,迟早的事。”
一壶水喝完了,我又打来水烧,“弘强都落到那一步了,还把个破校长的位子有什么留恋的,想不通!”
“不是留恋,也是早想歇了,给教体局把招呼打了,辞职申请都交了,局长下来了解情况,丢着一个烂摊子呢,局长哪敢让歇?‘这情况,你继续干着,我的局长不歇了你别准备歇!能怎么办?屎壳郎支桌子硬撑着。”
“弘强这几年干得不错么,丢了个什么烂摊子?”我不解地问。
“哼,怎么能没烂?烂得不是一般呢!一心想着给自己撸钱!弘强那人你又不是不了解,胆子大着呢,当了这十几年校长,贪污的钱我们做梦都梦不了那么多,现在风声紧收敛些了,以前连学生的補助都敢下手呢。惠风家园一套房产,佳宇大厦一套房产,市里一套房产,还是复式的,县城里一院地皮,陇南一个铅锌矿里还有股份呢,你算算得多少万?他两口子工资能挣多少钱,不都是贪污来的么?拉上三十套桌椅,账上能报六十套,一学期办公用品都能报十几万,去年光硬化学校院子和操场、改了一下电路,你知道报了多少?五十万!”
“花多花少不都花的是学校经费吗?”
“当然,花的是学校经费,但有些项目你报不了。就是学校背后修的那栋宿舍楼把他套在里面了。”
“宿舍楼怎么个套法?”
“关键那楼不是学校的经费修的,是从银行里贷款自行修建的,一百万,指望着住了学生收住宿费挣钱呢。现在学生少了,一年收的钱还不够银行利息。”
我听着对贪官的惩罚从来总有一种快意,但这事摊在了宋弘强身上,我竟对他生出些怜悯之情来。“修那楼的钱学校经费没办法报吗?”
“报不了,没立项,什么手续都没有,谁给他报?”
我还要说什么,同事进来了,也就不好再说了,子兵要去团委办公室交团费,说告辞了。
宋弘强最后竟落到了这种下场,在唏嘘之余,我为他痛惜。我想起了很多教育人的道理,也想起了很多名言警句。我甚至为他想着救赎之路。
救赎之路不是没有,我想着,假如他把吃进去的吐出一部分——只一部分,自己把那宿舍楼的贷款垫付了,局长也许就允许他辞校长了,那样他就解脱了,可以安心养病了。如果是我,我会那样做的。可是宋弘强会那样做吗?
过了不久,市里关工委的要去新明中学举办活动,我们单位要去个陪同的,我主动要求去了。我没有见到宋弘强,是副校长(一个不大认识的年轻人)接待的。我问宋校长怎么不见?副校长说宋校长有事请假了,我也不好多问。没有看见刘雪梅,子兵去哪个学校“同课异构”了也不在。
学校的几个头头领着关工委的人去搞捐书仪式了,我没有跟他们去,一个人在院子里怀旧。沿着前院子走了一圈,学校变化不大,没有见到一个老同事。物是人非啊,我感触万端。洒在这里的记忆太多了,我在这里初恋,也在这里失恋,我在这里快乐,也在这里伤痛。后来,我在一排宣传栏那里立住,橱窗里贴了很多老师的照片,整齐得像烈士陵园的墓碑,基本都是陌生的面孔。排在第一位的自然是宋弘强,我只扫了一眼就滑过去了。我迅速地找到了刘雪梅,从一个暗淡的角度专注她。她一点也显不出人老珠黄之气,脸面很丰满,皮肤光洁,没有一个斑点,没有一条皱纹,眼睛里散射着没有被岁月风干的妖媚,这都是电脑美化的效果。再看简介,工作二十年,评上中级七年了。我和刘雪梅的关系告吹后,她曾对我表示过悔恨之情。嗨,说这些干什么呢!我的目光又滑到前面的宋校长脸上,他那健硕的脸庞(大约是三四年前的照片吧),大背头高高梳起,黑发茂密如同他家祖坟上阴翳的树冠,阔嘴笑得很有气度,浓眉剑竖,有几分周永康的气质。教导主任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体育老师顾青源,这个曾经在五中引诱了很多女生的声名狼藉的家伙被发配到新明中学,竟也混了个领导职务,有些事蛮有意思的。
在这次换届选举中,默默无闻的我有幸被提拔了一把,调入文化馆,解决了个副科待遇。平日自诩为视功名利禄如流水呢,一不小心得到了这个,竟也惊喜而且自豪了。
这时候我听到一个关于宋弘强的很不幸的消息,他精神出问题住进市三院了。我问了一下子兵,消息属实。在新明乡政府举行的党代会活动中,宋弘强没有把工作做到位,派去参加会议的老师代表到会的连一半也没有,新上任的乡党委书记气急败坏地批评了宋弘强,告诫他这是犯了政治错误,要抓他个典型。宋弘强的精神受不住这最后一鞭子,彻底崩溃了。我抽了一支烟,默思良久,不知说什么话好。
责任编辑 赵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