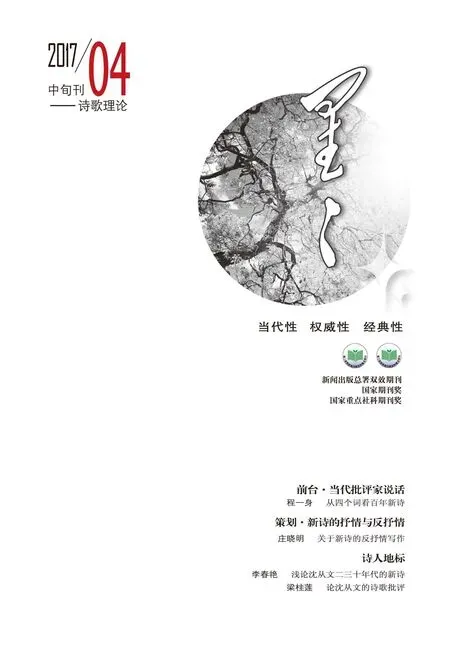论沈从文的诗歌批评
梁桂莲
论沈从文的诗歌批评
梁桂莲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不仅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独具特色的诗评家。他的诗评以感悟、印象入手,“道他人之所未道,言他人之所未言”,显示出其不同流俗,独立创美、寻美的诗性气质。虽然他曾自谦地说:我并不懂诗,尤其不懂近十年来的诗。”[1]“我提不出什么特别意见,因为我并不怎么懂现代诗。”[2]但从其《沫沫集》、《新废邮存底》等关于诗论的文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沈从文对诗歌审美赏鉴的独到、精准,而且也为其引导现代新诗发展、纠弊诗歌恶化趣味的拳拳之心所折服。他的诗歌评论,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就是在今天,也依然闪耀着诗性的光辉、智性的启迪。
一
身为作家,沈从文特别注重诗歌的本体表现,这也成为他论诗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很多论文和书信中,沈从文都提到了“诗之为诗”所必备的文体要素和情感特征,认为:“诗应当是一种情绪和思想的综合,一种出于思想情绪重铸重范原则的表现。容许大而对宇宙人生重作解释,小而对个人哀乐留个记号,外物大小不一,价格不一,而于诗则为一。诗必需是诗,征服读者不在强迫而近于自然皈依。诗可以为‘民主’为‘社会主义’或任何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但是否一首好诗,还在那个作品本身”[3]。对“诗必需是诗”和“作品”的要求,既成为沈从文知人论诗的基础,同时也使得他以“审美”入手,抓住诗的文体特征,专注于对诗歌本质的阐扬。立足于此,沈从文既爬梳整理了现代新诗的发展及成败得失,又对二三十年代的著名诗人诗作品评赏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主张。
首先,沈从文认可诗歌是情绪和思想的载体,认为,“好的诗不是供给我们一串动人悦耳的字句了事,它不拘用单纯到什么样子的形式,都能给我们心上一点光明。它们常常用另外一种诗义保留到我们的印象里,那不仅仅是音律,那不仅仅是节奏。”[4]在沈从文看来,诗意、情绪是诗歌的灵魂,是音韵、节奏、字句等形式的附丽。虽然音韵、节奏、语言是诗歌的文体基础,但好的诗歌,最终是以其诗意存在的,而不是以其字句存在的。因此,诗歌作为诗人有感而发,有声则鸣的文本,必然会“包含一些较深的观念”,或者“解释一种抽象原则或表现一种具体事实”,“给读者一种较深较持久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不只是个‘工作员’,还必需是个‘思想家’”,以诗意感动人,为人们的心灵带来光明,带来希望,烛照理想。
其次,诗歌的情绪、诗意,必须借助于音韵、节奏、语言等形式的有效表达。沈从文认为,诗歌是一种有限制的艺术,“它的成立是多少有点限制的。它必须以约见著,用少数文字起多量效果。它与散文分别就在此。诗要效果,词藻与形式能帮助它完成效果”[5]。“说外行话,我总觉得诗应当是一种比较精选的语言文字,在有限制的方式上加以处理的艺术。在表现上它至少得比普通散文讲究些也经济些。”[6]在沈从文看来,新诗虽然是一种形式较为自由的文体,不拘于格律、字数的限制,但却天然缺少了旧诗的节奏、韵律,也缺乏散文的自由,因此,好的新诗更需要对语言、词藻精选与安排,从其见出节奏,见出旋律,见出诗意,即以约见著,以少量的文字达到言有尽、意无穷的效果。换句话说,诗歌是一种具有自身文体规范的艺术,诗人必须遵守这种规范,在不自由中寻找自由,带着镣铐跳舞。否则,便不能算诗,更不能算好诗。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论诗既注重诗意的阐发,同时也注重音韵、节奏的调和、整饬,二者有机融合,不可偏废。在这方面,沈从文既非单纯的形式论者,也非单纯的题材、内容决定论者。他从诗的文体规范出发,尊重新诗发展规律和诗歌写作原则,始终要求诗意的朗照,以及形式上语言的简约、节奏的整饬、音韵的和谐,既反对空洞的流于形式的“颓废主义”,也反对不要形式的“诗八股”。针对二三十年代诗歌“重内容轻形式”的散文化倾向,沈从文在论诗时重点谈到了形式的必要和有效,既反对五四初期新诗否认“旧诗是诗”的“形式上无所谓,在内容上也无所谓”的“太杂乱,太随便”的写法,也批评了三十年代流行的朗诵诗只要朗诵不要诗的努力,认为“单纯的诵既不能用为旧诗传达的工具,当然更不大适用为新诗欣赏的媒介”[7],“许多诗关于文字排比处理的方法,都太不讲究,极端的自由,结果是无从朗诵”[8],要求新诗必须得“重语言讲形式”,“在辞藻与形式上多注点意”,以形式和音节来传达出诗歌所必需的音乐性和意境美。
二
本着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的诗学主张,沈从文对现代新诗及诗人进行了梳理评价。在看待新诗发展及具体作家作品时,沈从文的视野更加开阔,不拘于某个诗人或某部具体作品,而是将其放在整个新诗发展的历程中进行衡量评价或与其他类似作品进行比较鉴赏,由此,其评论就既抓住了时代脉搏,又富有自己的特色。
在《谈现代诗》中,沈从文提到了自己身为编辑、读者的评诗标准:“我在工作上得看诗谈诗,照例对于‘诗’先有个传统概念:‘诗其所以成为诗,必出于精选的语言,作经济有效的处理。’并用读白话诗习惯方式,看看这个作品从散文水准上,从近三十年白话诗水准上,有没有能够保持应有的明朗、条理和综合文字能力,作成纪录突破的新意,以为取舍。”[9]用这种方式读诗、评诗,虽然与一般人不同,但正好反映了沈从文评诗的基本要求与原则。
一是要有“突破的新意”。
身为作家,沈从文十分重视艺术的独创,评诗也不例外。由此,沈从文不仅肯定新诗的大胆试验、创新,而且也对那些具有独创精神的诗歌及诗人不吝赞美。如五四新诗虽然数量多,质量参差不齐,很多诗都不能算真正的现代诗,但沈从文在看到这些问题的同时,仍积极肯定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五四先驱者打破传统、努力革新的精神,称赞他们“每一个作者,对于旧诗词皆有相当的认识,却在新作品中,不以幼稚自弃,用非常热心的态度,各在活用的语言中,找寻使诗美丽完全的形式。且守着那与时代相吻合的思想,使稚弱的散文诗,各注入一种人道观念,作为对时代的抗议,以及青年人心灵自觉的呼喊。”[10]这一期的新诗,虽然在试验中牺牲了,但五四先驱者的这种勇敢革新,冒险试验的精神,却是不容抹杀的。正是这种不断试验的努力,才使得新诗从最初的白话诗起步,却并不限制到最初的失败,而向前发展到后来的完全和工整美丽。刘半农作为一个语言学家,其诗歌创作并不突出,但沈从文从五四诗人中拈出刘半农,肯定他以江阴方言入诗的口语试验和方言试验——“为中国十年来新文学作了一个最好的试验”,用不普遍的文字,不普遍的组织,唱为一切人所能领会的歌谣,比其他的诗歌美丽多了。[11]虽然这类歌谣创作,得到一个失败的证据,但沈从文并不以成败论英雄;相反,他更重视新文学从一切形式中试验、发现、完成的可能。在这方面,失败的教训与成功的经验同样伟大。又如汪静之的《蕙的风》一经发表,即受到一些道学家的批评,但沈从文却从青年、情欲的角度,肯定汪静之不受道德观念的拘束,写出了“青年人对于男女关系,所引起的纠纷”,以及“对于女人由生理方面感到的惊讶神秘,要求冒险的失望”、“欢悦的奇迹”,虽然幼稚但仍不失其为纯粹。在论《论汪静之的〈蕙的风〉》时,沈从文抓住汪静之诗歌“任性”、“青春”的特点,既将它与同时期的其他情诗比较,又将它与后来的徐志摩等人进行论述,既肯定了他在简单、纯粹上所达到的成功,又指出了他“如流星的光明”即刻消灭于时代兴味,为他在文坛上进行了定位。
二是要有精巧的形式组织。
在不少论文中,沈从文都提到了形式、技巧对写作的重要意义。在诗歌评论中,沈从文不仅重视作品在形式、技巧上所达到的高度,而且也不遗余力地对这些作品进行了赞美。最突出的就是他对新月诗派的重视及论述。
新月诗派作为“五四”后兴起的诗歌流派,在中国新诗史上,有着将新诗从革命引入建设,努力使诗回归自身文体建设的贡献。沈从文称颂新月诗派对诗艺的探索以及他们努力使诗成其为诗,使诗成就到一切优美的组织的创作。如他称赞闻一多“最先能节制文字,把握语言,组织篇章,在毫不儿戏的韵、调子、境界上作诗”[12],“用一个画家的观察,去注意一切事物的外表,又用一个画家的手腕,在那些俨然具不同颜色的文字上,使诗的生命充溢的。”[13]朱湘“是个天生的抒情诗人,在新诗格式上的努力,在旧词藻运用上的努力,遗留下一堆成绩,其中不少珠玉”[14],《草莽集》“代表作者在新诗一方面的成就,于外形的完整与音调的柔和上,达到一个为一般诗人所不及的高点。”[15]徐志摩“所长是使一切诗的形式,使一切不习惯的诗的形式,嵌入自己作品,皆能在试验中契合无间”[16]……闻一多作为“新格律诗”的提倡者,其诗歌冷静、节制,不仅讲究节的匀称、句的均齐,而且十分注重音节、辞藻排列组合所构筑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在闻一多的提倡下,新月诗派积极践行诗的格律化主张,纠正了早期诗歌的散文化、滥情主义倾向,促进了诗歌的自觉和自律。沈从文从新诗发展的历程出发,高度评价了新月诗派的诗作和成就,虽有溢美之嫌,但仍不失公允。
除新月派之外,沈从文还评价过刘半农、俞平伯、周作人、郭沫若、焦菊隐、李金发、卞之琳等人的诗。他称赞卞之琳会选择文字,从语言里找节奏,风格朴质而且诚实;批评陈梦家的诗“句子的美皆有一种放荡的姿态”,“却不能使人在那些记号上感到‘美’”。[17]周作人则与之相反,“使诗朴素单一仅存一种诗的精神,抽去一切略涉夸张的辞藻,排除一切烦冗的字句……这成就处实则也就是失败处”[18]……在沈从文看来,诗美不仅是文字、辞藻等形式的美,而且也是意境、情感的美,文字、辞藻、节奏、音韵等,作为诗歌的基础,只有在与情感、内容有机融合时,才能成为美的、可欣赏的,否则就会以文害意,走入歧途。
三
在《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中,沈从文提出了评论的原则:一是评论,“应注意到作者作品与他那时代一般情形。对一个人的作品不武断,不护短,不牵强附会,不以个人爱憎为作品估价”,二是“评论不在阿谀作者,不能苛刻作品,只是就人与时代与作品加以综合,给它一个说明,一种解释。”[19]本着这样的评论原则,沈从文论诗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与特色。
一是从作品出发。作为编辑、读者,沈从文评诗,既没有先验的理论设定,也没有突出的政治导向,他以作品解读为基础,既注重诗人、诗作因时代、个人原因所形成的风格面貌,同时也注重诗人与其他同时代作家在风格上的异同。在这方面,沈从文虽注重文本,但并不唯文本是举,而是结合时代、新诗发展的历史进行整体论述,既将同流派的诗人、诗作放在一起比较,同中求异,又将不同诗人、诗作放在一起,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前者如他在《论闻一多的<死水>》中对同样是新月派诗人的闻一多、徐志摩和朱湘的诗歌比较,后者则如他对焦菊隐《夜哭》与汪静之、于赓虞的比较:“……显示青年为爱而歌的状态,汪静之作品有相近处,表现青年人在失望中惊讶与悲哀,则于赓虞作品,与焦菊隐作品有类似章法。”[20]两种方式的合理使用,不仅能予作品于完整说明、解释,揭示出作品、诗人在时代及诗史上所达到的成就和地位,而且也将个人与历史融合起来,使得其诗歌评论具有了一种整体观和诗史性。
二是独抒己见,敢说真话。沈从文论诗不人云亦云,不以个人爱憎为作品估价,也不因同好而对作品护短,在这方面,沈从文基本恪守了自己提出的评论原则,做到了“实事求是”。如他批评施蛰存、林庚、金克木等人的诗歌风格、语言时直言不讳,认为“惟作者要新,嫌笔下符号不够用,结果把语体文已不常用的‘之、乎、者、也’单字也经常用上,‘然而’、‘于是’、‘所以’等词,也统统搬入诗里去。……所谓诗,内中多数也自然而然成为不可理解毫无意义的东西了。……他们所走的路并不‘新’,只算是一条‘僻’路。走僻路,成就不容易大,那是很显然的。”[21]对流行的以文言虚词等入诗的做法,沈从文直言这会将诗歌带入“僻”的歧途,因此大胆批评,毫不避讳。又如他对时下流行的革命诗歌、朗诵诗注重宣传效果,而忽略艺术创造的批评,也是就作品、艺术本身说话,且毫不委婉、直陈要害,认为这些诗歌虽思想正确,但在艺术上却是缺少使人信服的理由的。
诗歌评论是诗史研究的基础。沈从文的诗歌评论,虽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和较强的主观性,缺少学理的思辨和理论的映照,因此不可避免具有偏颇之嫌或武断之论,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二三十年代流派迭出、思潮蜂拥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沈从文不逐名,不为利,他以文本解读为基础,注重诗歌的文体规范和表现,以新诗发展的整体格局来论诗,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诗歌创作和评论的核心问题,也道出了新诗发展的实际情形。这些言论,直到今天,对当代新诗发展及诗坛而言,仍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注 释
[1]沈从文:《新废邮存底续编·谈文学的生命投资》,《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58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
[2]沈从文:《新废邮存底续编·致柯原先生》,《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74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
[3]沈从文:《新废邮存底续编·致灼人先生二函》,《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3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
[4] [17]沈从文:《〈群鸦集〉附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11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
[5]沈从文:《新诗的旧账——并介绍诗刊》,《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94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
[6]沈从文:《新废邮存底续编·致今是先生》,《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5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
[7] [8]沈从文:《谈朗诵诗》,《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242,23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
[9]沈从文:《谈现代诗》,《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7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
[10] [11] [15] [18]沈从文:《论刘半农〈扬鞭集〉》,《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122,126,123,12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
[12] [14] [21]沈从文:《新诗的旧账——并介绍诗刊》,《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96,96,98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
[13]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死水>》,《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111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
[16]沈从文:《论徐志摩的诗》,《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10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
[19]沈从文:《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2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
[20]沈从文:《论焦菊隐的<夜哭>》,《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120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