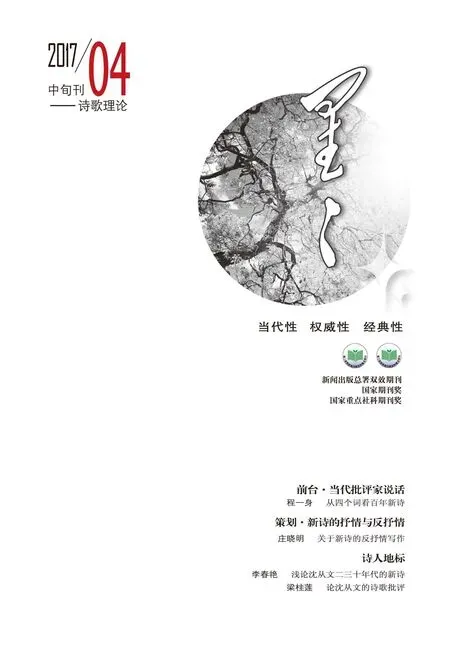触人间草木,经尘世旅途
——论爱斐儿诗集《朝圣者》的精神建构
李及婷
触人间草木,经尘世旅途
——论爱斐儿诗集《朝圣者》的精神建构
李及婷
《朝圣者》是诗人爱斐儿转向散文诗领域所创作的第四本散文诗诗集,前三部诗集无不呈现着诗人的特色写作,是诗人所进行的个性化书写。而《朝圣者》除了继承诗人原来特有的“药理性”审美之外,同时体现出企图建构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人皆草木”,诗人深谙此道。《朝圣者》里的几乎每一首诗都以草木为伴,体尘世之情。诗人徜徉在天地之间,用心感受草木的灵魂,在一呼一吸之间,走上朝圣之路。路上有鸟语花香,有微风细雨,也有孤独与徘徊。诗人沉浸在或平坦或坎坷的旅途中,静谧地回归到自我本身,建构了一个“大爱”的精神世界。本文将试图探讨诗人在意象的选择、张力的营造、主体的塑造的过程中所建构的一个欲逃离尘世最终回归尘埃,用爱对抗浮世的精神世界。
一、意象的选择:草木春秋
所谓意象是指凝聚着诗人情感的对象。无疑,不同的诗人,意象的选取会有不同的倾向。即使是同一意象,在不同诗人的笔下,也会诠释出大相径庭的韵味。可见意象的选择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选择不同反映出诗人的写作特色也不一样。诗人选择一个或者零星的几个意象,可能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不存在必然性。但是如果一个诗人选择相同类别的意象出现于一本诗集的绝大多数诗歌中,这样的意象选择就有了探讨的必然性。扒开意象群的外壳去看,我们便能窥探其意象群背后被诗人赋予的精神世界。诗集《朝圣者》的意象就主要集中在草木与代表时间性的对象两个方面,诗人在体悟草木的同时,感念出大自然承载着时间的厚度,建构了一个物我同一与融入时间虚无的精神世界。
朱光潜老先生说过:“你只要有闲工夫,竹韵、松涛、虫声、鸟语、无垠的沙漠、飘忽的雷电风雨,甚至于断垣残屋,本来呆板的景物,都能变成赏心悦目的对象。”[1]p1这句话与爱斐儿的意象选择倾向不谋而合,大自然的万事万物都被她召唤进诗里。在《朝圣者》中,我们随处都能看到茶花、油菜花、绿甘蓝、蒲公英、玫瑰、梅花、荷花、黄莲花、菊花、格桑花、八里香、小草、香樟树、苹果树、水杉杏花树、麦田等这些意象。笔者将这类的意象群纳入草木这一类。草木本无情,但是“在聚精会神的观照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1]p33爱斐儿观察草木时,便是撇弃了他们的实用价值,专注于意象本身。这个时候,物与我的界限便慢慢模糊,分不清庄周化蝶还是蝶化庄周了。诗歌《蒲公英》就是诗人与蒲公英展开的一次犹如知音的对话。诗歌的前半部分使用的是第三人称“她们”,仿佛是想将自己的伯乐介绍给读者认识,读来让人觉得亲切俏皮。连续五个“喜欢过”,与其说是蒲公英对阿尔山的热爱,不如说是诗人的情感与蒲公英内心的纯真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后半部分直接用第二人称“你”,“我一边走,一边看你花开遍地,仰着头,眼神装满爱,面对河流或者湖泊,每一朵都可以成为画面的中央。”一幅诗人俯身与蒲公英对话的物我合一的画面便呈现在读者面前,仿佛诗人已变成一朵蒲公英,成为了“另一颗含笑的心”。诗句中并没有把诗人想说的一五一十地告诉读者,而是掩藏在意象群背后。这就如海明威所说的“冰山艺术”:冰山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海水面上,八分之七则在海水面以下。爱斐儿的散文诗是具备这个特点的,我们无法一目了然地明白她的深沉含义。正如恩格斯所说:“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大量的意象便起到了使诗歌陌生化的作用,爱斐儿就如一个行走在天地之间的天使,她梦游阿尔山、阅读玫瑰峰、对影科尔沁、爱上雨树等。她忘乎自我,与草木达到相通,她爱草木,草木便进入她的世界。诗人通过草木意象群的书写,忘却自己的个性和意志,专过纯粹的自我,建构了一个物我同一的精神世界。
“春秋”即是指时间。诗集《朝圣者》的意象除了有大量草木,还有像桥、流水、火车、铁轨、年轮等这些具有延伸性和虚无感的时间意象群,呈现出时间的过去、现在、将来的三种状态,故事的绵延之感已摆放于前。“现在就是一个不间断的否定(不是)过去而是肯定(是)将来的虚无化过程。”[2]P445也就是说“时间的真正起点是将来而不是过去。”[2]P445《相遇拱宸桥》中是“我”对拱宸桥的告白,过去的事早已“瓜熟蒂落”“被翻毛了边”,“我已无大事可记”。可见,在诗人看来,与拱宸桥的相遇相知并非开始于过去,而是“现在,我终于可以站在你身边,以亲人般的心腹之音对你说:‘若遇到让你万箭穿心的人,就去用魂灵度他吧’。”是因为有了将来的“假如”,所以“我”现在便站在你面前与你对视。体现了诗人对时间的思考。爱斐儿说:“只有遇见流水,才能接近时光与花香”,(《请用水声载我》)这与孔子在河岸上看着浩浩荡荡、汹涌向前的河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进行了横跨几千年的精神上的对话。古往今年,很多作家都将时光的流逝比作流水,用具体的事物比喻不可捉摸的,便有了一种具体而微的感觉。爱斐儿似乎对流水情有独钟,她会“临水而居”“忘记奇迹和俗世的繁荣景象”;她会“不管潮落舟横,不忆旧时歌舞”;她会感叹“我的一生就像一滴水经过河流”等等。在时间的无涯里,诗人处于一个淡然的拜访者角色,看到了自己于时间不过是将来开始前的沧海一粟,尘土中的一颗粉尘罢了。此外,诗歌《一截铁轨穿过不老的光阴》以“铁轨”这个特殊意象来表现自己对“消失和碎片”的“信任与好感”。“铁轨”本就有故事的沧桑之感,它承载着若干陌生人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当我们踏上旅途,铁轨便载着我们去下一站,而在铁轨之上的我们早已是携带着过去与现在的个体。爱斐儿用我们所熟知的意象来表达对时光不可捉摸的参悟,能够激起读者的共鸣。最后,“年轮”本就是指树的年龄,自然就承载着时间。“我从树木的年轮和花开花谢中认出你”(《新生》),“而你在一层比一层更缜密的年轮里等着我”(《兴安落叶松》)。诗人将自己置于时间的洪流之中,在富有故事的意象前,思考时间。时间不过是一个微小的过程,我们能做的就是进入时间,享受过程。爱斐儿在时间的虚无面前并没有张皇失措,而是将自己置身其中,闭目感受这不可触摸的时间。
与其说是诗人选择了“草木春秋”作为意象群,笔者觉得“草木春秋”臣服于诗人更为贴切。波德莱尔说:“你聚精会神地观赏外物,便浑忘自己的存在,不久你就和外物混为一体了。”[1]P130诗人与其意象群早已分不清彼此,二者的高度融合,为我们呈现了一种物我合一滑入时间无垠疆界的精神世界。为浮躁的现代人,提供了一汪清泉。在快速发展的今天,能够驻足下来,与草木通心,与春秋同行,是诗人给予我们难得的精神世界。
二、张力的营造:丰富情感
“张力”作为术语,首先是物理学里的概念,是指当物体受到两个不同力的作用时,其内部存在的一种相互牵引力。诗歌领域的“张力”是由艾伦·泰特在其《论诗的张力》一文中最早明确提出,英文名称为“tension”,是新批评学派的重要观念之一。泰特在文中明确指出“我所说的诗的意义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延和内涵的有机整体。”[3]p137泰特坦言:“好诗就是内涵与外延的统一”。[3]p140换言之,泰特认为好的诗歌是至少两种不兼容的元素构成的新统一体,各方是对立关系,由此在对立状态中互存所形成丰富意义。泰特从张力的角度发现了诗歌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同时奠定了“张力”说的理论基础。“张力”这个概念被后来的学者发展引申,意义变得更为宽泛,“成为诗歌内部各矛盾因素对立统一现象的总称。”[4]p109诗集《朝圣者》里的诗歌正是搭乘诗人想象的列车,进行的一次诗性张力的旅程。爱斐儿在具有淡然与绵延性特征意象的基础上,从语言的张力以及诗性与俗性的张力的多元冲突中拓展诗味,构建了一个相互冲击抗衡最终归于平静的精神王国。
爱斐儿的语言犹如草木一般,渗透着清新之味,风雨之后更显其芳香;犹如品茶一般,需慢慢饮,方能品读出她语言的甘甜。诗人语言的张力体现在词语的悖论,以及由此构成的比喻的悖论。所谓悖论,是一个逻辑术语,是指“一个在表面逻辑意义上矛盾甚至荒谬的陈述,但它最后却会以某种方式获得合理的解释”。[3]p174不难看出,词语的悖论即指表面上矛盾的词语,构成看似不成立的比喻,实际上形成张力,拓展其深意。诗歌《青花瓷》组诗之《窑变》中写到“多么炙热的窑火,都会慢慢熄灭。曾经那么盛大,如今就有多空寂。”“炙热”与“熄灭”,“盛大”与“空寂”看似矛盾,却统一于青花瓷的一生。“一会儿被捧在手里,一会儿跌入尘埃”,只有经历了最热烈与最冰冷的情感的冲击,才能“承担起巨大的使命”。在词语的悖论中,形成了青花瓷的性格张力,表达诗人对具有青花瓷特征的一切事物的思考。又如《深入秘境》中,“勇士收回漂流四方的心,用内心的绿洲去换下途经的沙漠,用静谧的星光去换下烈酒。”这一系列的具有对比性质的词语形成了一个比喻的悖论,构成一种造境之奇。勇士回归,用平静与美好的东西换取粗糙与热烈。在这样的张力场中,作者的“秘境”意味便更深厚了。仿佛是轰轰烈烈之后,倾心于平静,却终难忘怀曾经的跌宕。“一场美梦紧抱另一场美梦”,看似平淡的词语才会焕发出多元的魅力。诗集中《相遇拱宸桥》、《彼岸与此岸》、《丝联166——记杭州的一处工业遗址》等都是作者通过构造词语的悖论,形成的独特张力场。使笔者前文提到的作者所选意象的情感更为饱满,诗歌的世界也更为丰富。
诗性与俗性的张力是诗集《朝圣者》的另一个突出特点,诗歌来源于尘世,本就带有几分俗性,这便与诗集所呈现出的诗性形成另一对抗衡的张力。《朝圣者》中出现的地名大多都是现实生活中可寻觅的,比如位于京都的小月河、位于浙杭一带的湘湖和拱宸桥、位于内蒙的阿尔山、位于吉林的天池等等,诗集中出现的地名都能够在中国地图上找到其归属。诗人在这些代表红尘的地方寻找诗性的存在,将诗性与俗性的张力统一于诗歌中。“如何在红尘之中,一眼认出自己的灵魂伴侣/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去爱吧,就像四月的花朵爱着蜜汁。从春天开始爱起,/你就是春天。”(《所有的痛苦修行都是一种练习》)爱斐儿了解人情世故,故称世界为“红尘”。但她并没有落入俗性的枷锁,而是在痛苦修行中寻找到诗意,从春天开始爱,如花朵爱着蜜汁般。在红尘与超脱的爱之间,构成一种极具的张力之美,诗人爱世界万物的纯真跃然纸上。另外一首《经过尘世》:“尘世这么满”“尘世拥有天然的吸引力”,这些都表明诗人在创作时已把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观察着尘世的一切,“比如商品、学识、三餐、权利、思考、斋戒”等,这些在诗人看来“尘世是满的”。故诗人不愿被淹没于尘世,而是“他们只是经过尘世这一段路程,留下爱的身影,美的足迹”,这是一种“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诗性的境界。在超然的诗性与溢满的红尘之间,形成无限丰满的张力,个人化的情感上升到人类的共有的思考和探索上来。诗性与俗性的张力在诗集中随处可见,如《湘湖望》“不管潮落舟横,不忆旧时歌舞,更不为闲愁所误”,又如《老开心茶馆》“我就可以暂且寄下扁舟一叶,也暂且撇开人间烟火”,以及《光与影》“这好意深深的尘世,常常因为光的一闪念,让我看到好看的马匹,静止了奔跑和路途”等等。真正的美不仅是指物也不单单指心,而是心与物的统一。爱斐儿将具有俗性的“物”带入诗歌,用诗人内心的诗性与其对抗,在张力场的场域上,使诗人脱离尘世又能热爱尘世的精神世界呈现出来。
意象的选择体现了爱斐儿的个性,而张力的营造使她的个性趋于饱满的状态。在语言的张力下,诗人清雅的特征更为凸显,犹如阳光下的花香更为幽远。诗人通过营造诗性与俗性的张力,使诗集笼罩在整体美的氤氲下,从俗性来,却褪去铅华,走向诗性。故,诗人通过张力的营造,使意象所寄托的情感更为丰富。诗人建构的世界也如高山一般,有了起伏,更具吸引力。
三、主体的塑造:以爱朝圣
笔者所说的主体是指诗人所塑造的叙事者“我”,在爱斐儿的笔下,“我”是一个具有独立性格的主体,是带领我们进行了一次朝圣之旅的主体。《朝圣者》里每一首诗里都有一个叙事者“我”,只是有时这个“我”就站在读者面前,有时隐藏在诗歌背后,需要读者寻其声音抓其形体。诗人通过主体“我”的塑造,使整个诗集立体起来。我们跟随这个主体经历她的经历,感悟她的感悟。最后在一次次的洗礼下,走上朝圣之路,明白这样的路途需要有百草相伴。在欲逃离尘世却不得的矛盾心理下,终于明白,爱尘世亦即脱离的第一步。这样的旅途亦没有终点,是一个带着爱朝圣的过程。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塑造,第一个是诗人的独语,换句话说,就是“我”的一个自我定位。第二个是与他人的对话,主要包括第二称“你”与第三人称“她们”。首先,我们来看“我”是怎样进行心灵史的展开,怎样在喃喃自语中定位自我。诗歌《临水而立的时候》:“最终,我会选择临水而居。忘记奇迹和俗世的繁华景象,从此与时光、爱和美为邻。”人都会有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我”想忘记尘世的所有,和抽象的意象做邻居。毫无疑问,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主体“我”对尘世的厌恶,为尘世所困,欲逃离的急切心理。这让我想到我国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他“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与爱斐儿所塑造的主体此刻的阶段是一致的,是为生活羁绊,欲脱离的。“自我是在反思中发现的,如果反思和被反思的东西是绝对合一的,则并无反思,也就并无自我。”[2]p439所以,主体“我”是在自我的不断反思中前进的。慢慢地,厌恶尘世的情绪得到消解。诗篇《在最深的尘世爱你》:“最深的尘世有你、有我”、“在这最深的尘世,我学会了用寂寞的比喻替代一些热烈的词语,就像百草爱着四月的水滴,我爱这尘世的时候,就是在深深的爱你。”“我”从厌恶尘世到抽离尘世后,回归到对尘世的热爱。“我们”是在“尘世”相爱,不是脱离这个大背景的。此外,“我”直言“我”爱尘世便是爱“你”,爱屋及乌,是由“爱尘世”推及到“爱你”。以此可以看出,“我”已脱离了尘世所给予的枷锁,得到了自由,带着爱在朝圣。《王者归来》中说到:“所以,魔戒始终无法得逞,人间始终有爱!爱可以使人产生强大的力量,产生足以抗拒黑暗的力量。”爱斐儿笔下的主体“我”因为有了爱的盔甲变得日益勇敢,能够过滤尘世的浮华,回归到对尘世的热爱。这何尝不是一次爱的朝圣之旅。当然,诗集中有很多类似的诗篇,笔者在这里就不再赘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通过“我”的独语,展现了“我”的心灵史。主体“我”从陷于红尘到洗尽污浊,爱上尘世这样一个发展的形象。
其次,“我”在与他人的对话中,形象变得饱满。因为“我”与他人在情感上有了共鸣,所以便展现了主体性格的其他方面。如诗篇《草原深处的牧歌与琴声》:“对你,我频繁使用了辽阔这个词”、“它们和我一样,心止于曦光和露水,同属安静的一族,却以不为人知的药性,丰富着你深刻的内容。”“你”是指被赋予了诗人情感的草原,“它们”是草原上的万物。在与“你”“它们”的对话中,“我”似乎找到了定位,“我”是安静的主体,却有其存在的特殊性,丰富着草原,丰富着这个世界。可见,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我”找到了自己在尘世的位置,“我”具有“不为人知的药性”,默默且享受着存在与茫茫尘世中。又如《熔岩上的苔藓》:“她那么小,小的像苔藓一样——其实就是苔藓”“虽然连最小的香气也不曾拥有,仍只是满心伤悲而欢喜地爱着。”这篇的“我”并没有直接出现在读者面前,而是向读者娓娓道来苔藓的内心。苔藓虽微小,但她的喜怒哀乐是真实的,她也诚实地爱着。这首诗从侧面说明“我”觉得世间万物都有爱的能力,在这个能力范围内也都存在着真实的或喜或悲的情绪。此外《心中有红马》中“也许它只是另一个我,不是它代替我,就是我代替它爱着——这无边的尘世和万物生灵”,更能体现出诗人“大爱”的情怀。主体“我”走遍山川河流,与红灯笼、与“二马”、与玫瑰峰,与金达莱等进行对话。虽每一场对话都是独立的,但却能从中窥探出共性。即“我”是愿意用“爱”来消解尘世之“恶”,热爱着世间万物的主体。
由此可见,“我”在低语中从尘世抽身,明白若想获得自由就得回归到热爱尘世的起点;“我”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懂得世间万物都值得爱。所以,“我”是一个既独立于尘世又热爱尘世的主体,是一个以草木为伴,带着爱走向朝圣之路的主体形象。诗人所建构的精神世界,至此达到最为紧密的和谐。“我”是整个精神世界的最直接承载者,在浮华世界,带着对世间的大爱进行朝圣。
总之,爱斐儿诗集《朝圣者》是她又一带有鲜明特色的作品。她择草木春秋为意象,延续了特有的“药理性”,却又有所不同。《朝圣者》散发的是草木的清香,幽远而又深沉,在时间的绵延中实现物我同一。为了使建构的精神世界更为丰满,爱斐儿营造了诗歌的张力场,语言的张力使意象更为饱满。此外,她还将俗性带入诗歌中与诗性进行碰撞,凸显出特有的草木幽香的精神世界。最后,诗人在诗歌中成功塑造了一个具有“大爱”精神的主体,“我”带着爱一路走向朝圣。诗人在诗中说:“总有一些事物迫使我们卸掉周身的疼痛走向朝圣。”(《光明澄澈》),我想诗歌大概就是爱斐儿走向朝圣的伴侣及动力。我们有理由期待诗人接下来具有特色的创作,为我们建构一个与浮躁的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的精神世界。
[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李梅英.“新批评”诗歌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赵毅横选编.“新批评”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