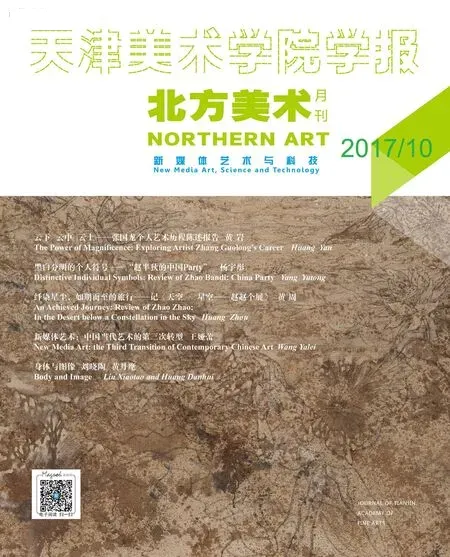新媒体艺术: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三次转型
王娅蕾/Wang Yalei
在中国艺术史的划分中已有一个比较普遍的概念,即将1979年以来的中国艺术称为“中国当代艺术”,这个概念从提出至今已近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依然没有出现公认可以取代“当代艺术”大概念的新命名。与传统的水墨、书法、油画、雕塑、版画甚至综合材料等艺术形式不同,有一个新的艺术门类在“中国当代艺术”创立之初并未被包含进来,而在这三十几年中迅速成长为可以比肩前述传统艺术门类的新的存在。这一艺术门类直至今日在概念上依然有争议,但最为广泛的一种称呼是“新媒体艺术”。
前“新媒体”时代:从录像到网络艺术
新媒体艺术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有过相当大的命名分歧,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中有行为、装置和摄影作品,但还没出现可纳入今天的“新媒体艺术”概念的形式,到20世纪90年代初,不同于传统“拍电影”形式的“录像艺术”开始在中国艺术界出现——美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建立艺术与科学结合的实验室,西方录像艺术的主要发展期从20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而90年代在中国出现时依然是新鲜事物。1996年9月14日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画廊举办的影像艺术群展“现象·影像”的组织者之一邱志杰曾提及:“我接触录像是在1990年,德国汉堡美术学院的教授带一批录像带到浙江美院来播。我和颜磊正在版画系读书,看到这些作品挺激动的,私下里就开始接触。当时张培力在做政治波普,来我们系学丝网版画,我们很熟,1991年还到他家里看《洗鸡》的录像作品。我自己尝试做录像是在1993年,为《书写一千遍兰亭序》做记录。后来我发现录像画面必须经过处理,否则质量保证不了,才开始做关于录像的实验。当时我们身边有一群人玩这个,颜磊后来到《北京青年报》工作,在他影响下,朱加也开始做录像。1994年王林策划的《媒体的变革》展出时,我已经完成了‘卫生间’等一系列的录像。”①
1996年,中国互联网开启了民用市场,这个时间倒是比西方的网络互联时代晚不了几年,在一线城市最早接触网络的敏感的艺术家也开始利用初期的网络来进行一些小范围的尝试。2000年左右,紧跟欧美的艺术风气,中国也开始出现了用“新媒体艺术”命名的展览。依然引用邱志杰的话:“90年代中期我们讨论的都是录像艺术,没有‘新媒体’这个概念,到1998年、1999年,全世界突然流行起这个词,各地原来的录像艺术节统统被改名为‘新媒体艺术节’,比如阿姆斯特丹的‘WWVF国际录像艺术节’(World Wide Video Festival),柏林的Transmediale等,到1999年前后清一色改名为‘新媒体艺术节’‘超媒体艺术节’。”有相当数量的艺术家认为新媒体艺术并不能列入中国当代艺术的范畴,而应该属于“世界艺术”的一部分,因为新媒体艺术的发展与中国的国情和现状关系不大,从技术手段、理念到展示平台都与全世界(主要是欧美国家)的新媒体艺术水准看齐,但是从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它并不能脱离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土壤而单独存在。
与邱志杰等第一代从“录像艺术”逐渐摸索出来的艺术家和策展人不同,新一代的新媒体艺术参与者和组织者大多有相关专业的留学背景,比如曾经在北京奥运期间策划过新媒体艺术大展“合成时代:媒体中国2008——国际新媒体艺术展”的策展人张尕则更了解西方新媒体艺术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我在国外很多年了,80年代后期去德国读柏林艺术大学。当时在国外还没有“新媒体”这个艺术概念。但是90年代初我到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读书时,因特网已经在大学里流行,只是没有在社会上广泛应用,直到1993年第一个视觉浏览器出现,因特网及电脑才成为大众媒介。我在1991年开始接触网络,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可能性。因为当代艺术发展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从某些角度来说已经开拓到一个极限,很多模式都满足不了我对艺术的需求。这个时候因特网作为新的媒介出现,为艺术开拓了新的更大的空间。
也是在90年代中期,在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出现了“网络艺术”运动——这可能是20世纪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艺术运动,在此之后直到现在都没再出现过“运动”的概念。我当时也算是其中一分子,在纽约举办网络艺术沙龙,还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每个月举办定期讲座。帕森斯学院提供场地和设备(我在那里教书),这在纽约是很难得的资源。1997—1999年,网络艺术在纽约非常热门,艺术家们常常定期聚会。1998年我在纽约做了一个“链接及其超越”的论坛,召集了古根海姆博物馆和 Dia Center的媒体艺术策展人、Posmasters等重要的媒体艺术画廊,还有多个学校以及艺术家来参加讨论。当时三百人的礼堂都坐满了,现场讨论非常热烈。第二年我又做了一次,算是续篇。这可以说是纽约艺术圈第一次专门针对新媒体艺术的大型研讨会。
我觉得现在已经没必要去强调“新媒体”的概念,“媒体艺术”这个词也许更宽泛更不会被误解。因为“新”是个不断变化的概念。现在所说的“电子艺术”实际应该指的是90年代前电子管和晶体管作为媒介的艺术,而现在数字技术则成了“电子艺术”的基本元素。就国外来讲,90年代中期开始有“新媒体艺术”这个词的出现,但“新媒体”最先是在技术领域出现的,是因为网络技术的出现,最早使用网络技术和互动技术的公司被称为新媒体公司。
张尕叙述中“使用网络技术和互动技术的公司被称为新媒体公司”这一概念更接近于今天普通民众对“新媒体”的理解,比如微信平台的后台操作就被称为“新媒体运营”。与艺术中独有概念的来源不同,新媒体这一概念从其他行业借用而来,这也是今天的一些理论家对此诟病的原因之一。
但是毫无疑问,新媒体艺术本身是依附于科技发展而产生并得以发展的一种艺术手段,即使很多艺术家已经在重新尝试low tech(低技术)艺术形式,但技术在新媒体艺术形式中依然是占据主体地位的,美国麻省理工(MIT)实验室就同时盛产科学产品与艺术项目。不同于大陆对西方new media概念的直接翻译引用,台湾艺术界在概念命名方面显得更固执一些,早期只有录像艺术的时候,台湾与大陆的命名并无分别,近年来网络成为艺术家的创作主体之后,台湾的艺术理论家和评论家们一直用更加具体的“数码艺术”“数位艺术”和“数字艺术”等近义词来称呼新的艺术形式,但在概念范围上,台湾所称的以上“数×艺术”与大陆的“新媒体艺术”并无分别。有些大陆学者借鉴了台湾的命名概念,比如厦门大学教授黄明奋所著的《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就将数码艺术的肇始时间追溯到邮政网络、电报和电话系统的媒体传播——他认为后来的网络传输和邮件系统正是前述媒体技术的传承,“媒体网络”(不是网络媒体)是数码艺术的创作和传播主体,这也是西方新媒体艺术理论研究的主要观点之一。但这样说来,“新媒体”这个看似更加笼统的概念似乎要更直接和贴切。
大陆新媒体艺术家对这一点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认知。邱志杰同样认为:“其实媒体艺术和大众传播媒介有关:在大众传播媒介是书籍的时候,媒体艺术是版画;在大众传播媒介是报纸杂志的时候,媒体艺术是摄影;到大众传播媒介是电视的时候,媒体艺术是录像艺术;而现在互联网时代,媒体艺术就是网络艺术。所以我个人觉得用‘媒体艺术’这个词更准确一些,现在不能再说摄影是新媒体艺术,连录像也已经是‘老媒体’了,但它们还是媒体艺术。”而国内最早介入新媒体艺术创作的先行者之一胡介鸣也同样认为:“一直以来对新媒体艺术的界定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因为‘新’是有时间性的,是建立在不断淘汰的基础上的,从这一角度看,我对新媒体艺术比较倾向于‘刷新’机制层面的判断。”
新媒体不确定:难以归档的历史
“2002年MAAP(亚太媒体艺术节)有个在中国的项目,策展人是范迪安和皮力,负责人是我。展览是在中华世纪坛办的,几十名中外艺术家参加,已经是很大型的展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当年还有一个日本新媒体艺术展,是在中央美院画廊举办的,知道的人就更少。我们现在能在网上看到的信息,大都是2004年以后的,也就是从张尕做的‘国际新媒体论坛’开始,前面的那些项目都被遮蔽掉了。从2004年往前追溯,基本上直接到了邱志杰和吴美纯在1996年做的‘现象·影像’展,那个展览除了所谓的‘现场记录’之外还有一本文集,上面都是转译的西方新媒体理论文本,但是有谁看到了呢?几乎没有人见过。同样很少有人看到的还有一个1997年在杭州做的录像观摩展资料。有人给过给我一本1997年‘国际纪录片论坛’的文献资料,那个论坛是在中国做的,请了国际上很多做纪录片的大导演,我一看时间觉得很奇怪,那个时间竟然有这么大的活动,但我们好像没人知道。到2002、2003年我们跟歌华合作成立了一个公司,叫DV研究中心,做了所谓的‘第一届’国际DV论坛,也请了很多人,有丹麦DOGMAE95、德国柏林电影节和ZKM的专家,国内也请了很多专家。……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4年以前这段时间,中国新媒体发展的线索非常非常多,但是没有人去做这种整理的工作。这种‘被遮蔽’的状态跟当时所谓的‘官方’和‘独立’的环境有关系,当时没有媒体让外边的人知道那么多信息。个体独立印刷的册子本来就有限,只有圈子里的几个人和自己的朋友知道。甚至有些本来在做所谓录像艺术的人——比如田苗子和张冬辉——后来都消失了,不做艺术了。田苗子现在有点要回归的意思,重新开始做动画片。高士明当时也和很多人一起做装置和录像艺术,2000年以后基本就不做了,偏理论研究去了。皮力是很早就研究录像艺术的理论家,还出了几本书,但是现在估计也没有精力做这些东西。”以上来自另一位新媒体艺术策展人李振华的口述,在今天对资料的重新查找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被遮蔽的类似展览还有2000年的“中国网络影像艺术展”、2001年的“附体影像艺术展”等,李振华提到的2004年举办的“国际新媒体艺术论坛”只有寥寥网络资料,到2005年的“第二届北京国际新媒体艺术展”相关记录才逐渐增多。
对于十几年前的这段历史,我们恐怕只能推测——首先由于当时新媒体艺术命名的多样性,从“录像艺术”“影像艺术”到“互动艺术”(2002年的一个“互动艺术展”是以行为艺术为主体的活动,不同于现在的红外线互动装置作品展)、“多媒体艺术”等名称均有使用,在艺术史的记录中一时难以进行统计和归类;其次,新媒体艺术在当时的艺术形式中过于“新”,除了一群参与者和组织者或许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大多数的理论研究人员仍在观望,而官方记载对于新形式的滞后接纳也让新媒体艺术史有了一个短暂的空白期——这一点,在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与普及中都是很常见的现象。
令艺术主体发生改变的新媒体艺术
现在回到最开始的论题,为什么将新媒体艺术——而非所谓的新水墨、后现代、再写实等概念——视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三次转型。当代艺术的第一次转型事实上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开启和复兴,经历过“文革”的断档,1979年开始的当代艺术重新发现了“人”或者说“个体”的存在,让普遍的谎言回归真实,虽然没有技术上的完全革新,但在当时意识形态的最大现实前提下,充分完成了一种价值观的引导和变革。第二次转型则是从1992年以后开始,让市场介入甚至主导了艺术的走向,这之后的后续变化是始料未及的,艺术品天价、“炒作”、“泡沫”等负面词汇纷至沓来,但在当时,市场是艺术的唯一出路。这条路的发现和尝试仍是对西方艺术行业模式的照搬。
直至2000年以后(确切来说应该在2003、2004年前后,红外线互动装置、网络艺术等各方面都有相当成熟的中国艺术家作品在展览中展出,此前以录像艺术和含摄影在内的影像艺术为主)中国新媒体艺术成为一个确定的艺术门类,此时西方的新媒体艺术理论仍在摸索和推进阶段,而国内在数字技术、高科技技术方面的科学发展水平也与国际同步,终有一门艺术门类的地域壁垒被打破,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比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艺术观念被彻底打开——在数字、网络、手机等传播媒介的艺术创作中,每一件作品都可以被无限复制,无限再创作,也因此有无限的版本在传播中成立,包括形式相对固定的录像艺术和互动艺术,在被播放或互动的时刻,主动权就被观众卸下了。“作者——艺术家”的概念愈加模糊,得以成立的是作品本身。有人说这是博伊斯“人人都是艺术家”观念的再现,其实不尽相同,博伊斯时代被打开的是“艺术”这一概念的边界,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解释为艺术,而新媒体时代的艺术是被分解和重组了——不仅艺术本身,整个人类社会的观念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化。
这种分解——传播——重组——传播……的模式更类似西方古典时期的炼金术,冶金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哲学思考的大爆发,因为人们亲眼看到自然规则中已有固定形态的物质被摧毁,这启发了他们放开头脑的禁锢,对物质分解和重组的思考,打开了人类作为旁观者的眼界。炼金术在今天的科学解释中几乎被定义为巫术,但在当时,它对人类打开思维的规则功不可没。后来科学家确立了分子-原子结构,圆了炼金术无法解释的历史遗留问题,可是到了当代,数字传输给人类哲学带来的冲击力可以类比冶金术带来的思维启发。所有视觉可见的、虚拟的物质都成了两个简单数字组成的碎片,连最基本的分类都不再维持——人们信赖自己的所见,但数字传输系统的拆分重组令人怀疑“所见”的真实本质。人类理论上的推进与反复并不意味着所谓考古与再现的关系,人类的大脑使用比例在不断进化,但维系人类群体的是观念,观念来自最初的猜测,猜测证实并被多次证实,最终形成真理。这样的求证与反证始终是有机的动态平衡,包括数学与物理这些基础学科,都建立在动态平衡的人类对已有世界的猜测证明的基础上,所谓现实,如果与人类的视觉系统、感知系统、表达系统有所相悖,那么人类是无法认识到的——所谓世界无限,这是错的。人类对世界认知的边界是人类身体结构的构成边界,我们认为是真理的,事实上不过是解释人类狭隘世界的一种最合理的猜想。总之,猜想永远没有“对的”,而只有合理的。网络导致的超越空间的质子化传输让时间同样被加速,在许多科学猜想中,物质传输最终将达到“穿墙渗透”的状态,意即原有实体在传输中被分解为质子、原子,到达传输目的地后再重新组合起来。实现原态充足的必然方式是原子和质子组合的关系——序列。这种传输方式在网络传输中已经实现,影像-声音在传输前被分解为0、1,相当于正电子和负电子,经过有序的数据编组传输,在到达目的地后依照原有序列产生重组,最终得以原样呈现,这个过程是不存在传输损耗的(经过编辑的序列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序列,原有序列的传输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奇林斯基在媒体艺术理论著作《媒体考古学》导论中提到:“《在另外的地点和另外的时间》已经产生出了这样一种时间意识,而从地点的角度来看,这种意识对我们不再是未知的了:在巴勒莫我们找到的是克拉科夫,在纽约我们碰到的罗马,在弗罗茨瓦夫我们看到像布拉格、佛罗伦萨或者耶拿这样的一些城市都会合到了一起。我在任何时间都不再搞得清当时我是在哪里逗留。那些具有不同于通讯地址的数据的时间段、时刻、时期,开始凭着它们各自的作用和价值而互相渗透。”这一点在今天的世界中更为明显,网络对影像的实时传输让城市的面貌趋同,这种趋势将在人类的普遍智慧足以驾驭网络这一突发新事物之前愈演愈烈,这正是上述理论的具象化结果之一。
迄今为止,人类的艺术尚不能脱离整个人类社会的环境而单独存在,在数字传输与网络媒体给人类观念带来的冲击与改变面前,艺术的转型必然在发生。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次转型发生于“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第二次转型发生于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的20世纪90年代初,那么第三次转型自然而然承接于数字和网络全面普及的2000年以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但只有网民达到一定数量,进入社会的人群都已适应了网络生活之后,变革才真正开始。
注释:
①本文所引用材料主要来自王娅蕾2009—2010年在《艺术世界》杂志之“新媒体 | 口述”栏目刊发的整理文字,其中部分文字为未公开发表的第一手资料。本段落来自《艺术世界》杂志总第233期《邱志杰:我从不玩“堵枪眼”和“扣扳机”》,邱志杰口述,王娅蕾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