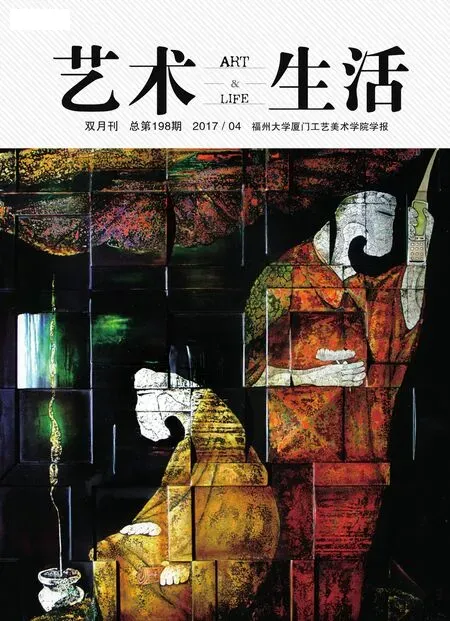笔墨与造型:徐悲鸿马画精神论
桑盛荣
(西安培华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100)
自16世纪西学东渐以来,西方文化的涌入及其影响,构成了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分野,被动形成“中国画”的称谓。同时,20世纪20年代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衰落,革命潮流汹涌澎湃,民族主义高涨,“德先生”与“赛先生”逐渐成为社会思潮的共识。而中国画在以元明以来逐渐对“逸笔草草”“墨戏”荒寒意境的追求,笔墨形式的过度膨胀,对于物象逐渐偏移,荒率枯淡,尤以董、王“拟古、模古”,显现出羸弱、残山剩水之貌。而康有为振聋发聩提出“今工商百器皆籍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1](P105)这些传统中国画的末流被认为是国民羸弱、精神贫乏在美术上的对应表现。在如此境遇之中,导致对于“中国画”的革新要求。革新或者说改良传统文人画成为众多志士的必然选择。在如此的时状境遇中,徐悲鸿的马画一方面继承传统绘画的笔墨精神;另一方面兼容西方绘画造型意识,呈现出阳刚雄劲的国民精神诉求,开始了改造中国画的进程。
一、传统笔墨与西学造型观念的确立
徐悲鸿自幼受到以父辈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具有非常浓郁的传统古典文化情结,以致终身谨守以古文写作。那么他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改良,“佳者守之”和“垂绝者继之”,主要应该指中国绘画的传统写意精神,对此他并没有进行彻底否定,只是继承了唐宋具有形神兼备绘画的写意精神。而他要“改之不佳者”,应该是指违背中国古典绘画精神尤其是元明以来文人画末流,对于所指系统的过分膨胀,也即对于造型意识的忽视,只在于墨戏心态以及逸笔草草的过分追求。而“未足者增之”即是西方坚实的造型技法,正如苏立文的评价“因为他(徐悲鸿)真诚地相信他的学生所需要的不是根据肤浅的现代派,而是西方技巧的坚实基础”[2](P140),可谓一针见血。徐悲鸿改良中国画的策略在于对于西方写实造型的吸收与借鉴,扬弃元明以来所指系统的过分膨胀,以中国绘画雄伟阳刚的笔墨观念取代传统的纤弱姿媚。
笔墨,是中国画构造画面形象的最基本的元素。“笔墨是中国画的命脉,也是中国画区别其他画种最根本的标志性的本体语言。”[3](P308)因此对于中国画笔墨的认识,实际标志着对中国画的认识,也决定徐悲鸿对时状的判断以及时状中的实践与选择。而明清以来文人画对笔墨过度张扬,潜藏背后的是对于董其昌南北宗论的继承,这与中国人的审美基调温柔敦厚、执允中和相一致。相反,随着1840年以来,中国政治与经济的步步衰败以及国际地位的一落千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学者们以欧美绘画的写实标榜为科学,写实绘画反映社会人生即是民主。而身处时状语境中的徐悲鸿依然不能幸免,在法国巴黎的求学过程之中,对野人画派、达达主义、现代派等敬而远之,自觉地接受了欧洲学院派写实主义绘画风格,这正符合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写实主义的学理背景对于中国画家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人们看到艺术与生活现实的直接关联。”[4](P113-124)与此同时,改良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是以反对传统文人画以元明以来粗率的笔墨替代造型,传统精微表现物象的技艺被贬低的流弊,从而推崇唐宋绘画并以复兴传统北派绘画风格。“北派之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襟期愈宽展而作品愈伟大,其长处在‘茂密雄强’,南派不能也。南派之作,略如雅玩小品,足令人喜,不足令人倾心拜倒。”[5](P194)这样以“茂密雄强”肯定了北派画风,以“雅玩小品”否定了南派。而徐悲鸿旅欧期间“故手一册,目速写之,积稿殆千百纸,而以猛兽为特多”[6](P11)。对“猛兽为特多”观摩与速写,不难看到徐悲鸿对于雄健奇强阳刚风格的青睐。而阳刚雄健的风格即是有悖于笔墨流滑、甜靡羸弱、平淡自然毫无生气的八股山水。可见徐悲鸿将元明以来人文画末流笔墨流滑的弊端等同于中国国民精神的羸弱,以致肯定力量、雄伟以及对北派艺术的追求就不难理解其中的精神趋向与精神价值。
书画同源,中国画重要的笔墨,即书法中线条功力直接传达于绘画中的笔墨功力。对书画同源他具有深刻的认识:“中国书法造端象形,与画同源,故有美观。”[7](P240)同时又在书学方面推崇魏碑的雄健、壮美,继承其师康有为“勿顿学苏米,以陷于偏颇剽佼之恶习,更勿学赵、董,荡为软浮流糜一路”[8],而欣赏商周甲骨文、钟鼎文、汉魏北朝的碑帖,“尤其喜欢倪云路、王铎、傅山等人的行、草书,常对我称赞‘倪云路字格调最高’”[9](P151)。不难理解,徐悲鸿书学一方面主要侧重于雄伟、猛气横发的阳刚范畴;另一方面明清“狂态邪学”一派其书法与绘画皆是以笔墨纵横为主旨,着重于笔墨意识的高扬。这一点对中国画史异常清晰的徐悲鸿不能不知道,而更推以名不经传“文苑失位”,艺苑同样失位的徐渭为现代书画第一人。这样从心理层面不难揣摩悲鸿的书学与画学,看重在于中国画的本质元素笔墨,而笔墨恰巧是中国画的本体。
同时,在旅京期间,“丁巳走京师,游万牲园,所豢无几,乃大失望。是时多见郎世宁之画,虽以南海之表彰,而私心不好之”[6](P204)。另外,据徐悲鸿自道,在巴黎“以写安德罗克勒斯之狮曾赴巴黎动物园三月,未曾得一满意称心之稿也”“述工作虽未懈,而进步毫无,及所疑惧。”[6](P505)这样虽“未懈”,但仍无法以西方写实素描的造型观念去审视客观世界,才得以“未能满意称心”“及所疑惧”。可以说,从“私心不好之”到“及所疑惧”,悲鸿已经无意间显露出个人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笔墨写意的钟情。可见,徐悲鸿在本土已无意识地确立了中国画的笔墨观念。陈传席所言“他(徐悲鸿)最欣赏的画家齐白石、傅抱石、黄宾虹、张大千等等,却恰恰不会素描,也不是以素描为基础,也不是以写实为特征”[10](P62),正是说明了徐悲鸿传统文化心理,对于中国笔墨的理解与重视。对此,马鸿增大声疾呼:“请问,不懂笔墨,能画出那样精美的水墨奔马吗?”[11](P71)
造型,是西学东渐以来对中国绘画冲击最为猛烈的且最不易被时人接受的观念。而所谓造型,即是指在画布的二维平面中展示三维感性效果,用明暗、凹凸、透视、色彩等具有科技含量的技巧,以瞬间的视觉展示客观的真实。可以说,造型是西方乃至欧洲艺术最为核心的艺术观念。徐悲鸿斥责“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着眼点就在于元明以来为物象外在形式的放逐,只关注于笔墨的恣肆膨胀,从而导致的陈陈相因的摹古拟古之风。在谈及中国山水画时,徐悲鸿这样说:“天之美至诙奇者也,当夏秋之际,奇峰陡起乎云中,此刹那间,奇美之景象,中国画不能尽其状,此为最逊欧画处。”[12](P15)而所谓西方造型观念,即是对外在的刹那间的主观感受和对色彩的敏锐觉察力,同样也认识到中国画在此方面的缺陷与不足。对此他于1919年所画《三马图》以及后期《大树双马》急切地付诸于色彩。可以说他的造型意识的选择是基于对中国画流弊清醒的认知基础上的,所以他旅欧学画,却在现代派日益兴盛的大潮中不迷失,以致在1926年归国探亲看到国内对西方现代派趋之若鹜之现象,深恶痛绝:“欧洲自大战以来,心理变易,美术之尊严蔽蚀,俗尚竞趋时髦。”[13]“写人不准以法度,指少一节,臂腿如直筒,身不能转使,头不能仰面侧视,手不能向画面而伸。无论童子,一笑就老,无论少艾,攒眉即丑,半面可见眼角尖,跳舞强藏美人足。此尚不改正,不求进,尚成何学?”[12](P16)可以说,对中国画清晰的认知结构“写人不准以法度”即是对西方绘画以解剖、透视、明暗关系具有科技含量的技巧的重视。正如徐悲鸿自己所言“皆对实物用过极长时间的功,即以马论,速写稿不下千幅,并学过马的解剖,熟悉马之骨架,肌肉组织,然后详审其动态及神情,乃能有得”[14],终形成了强烈的造型效果。
同时也正如苏立文所言:“徐悲鸿内心执著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更大的作用,很快他便形成了一种用传统的具有书法性的笔墨来进行写实性创作的面貌。”[15](P207)可见,徐悲鸿以写实的西方造型意识促进中国笔墨精神的改良。这一“内在理念”灌注于徐悲鸿的精神世界之中,逐步形成了以中国绘画的笔墨精髓为主导,兼容西方造型意识的独特艺术观念。所以徐氏改良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在其“艺术实践中,他(徐)并没有放弃笔墨,而是有选择地研究、运用和改造笔墨,努力把严格的造型与生动的笔墨结合起来。”[16](P124-135)
二、笔墨与造型观念下的马画
书法是中国艺术的浓缩,一个画家对于中国画的理解完全可以反应在他对书法的理解上。而中国画的基础,其实就是书法功力。所谓中国画笔墨,就是书法用笔的特质。徐悲鸿深受传统文化的滋养,一方面秉持其师康有为的教导,对魏碑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在康有为所收藏的书画佳作之中纵横驰骋,逐渐形成了浓烈的个人书法风格,基本解决了中国画的笔墨观念的障碍。而八年的旅欧西学,加之从小临摹吴友如的界画,逐渐形成了写实的造型意识。但在徐悲鸿的马画中,造型与笔墨是一种科学的融合,准确地讲,是中西方绘画观念长期、自然、水道渠成的相互借鉴与吸收。
早期马画如《三马图》[17](P33)(1919年)中的马匹与郎世宁所绘御马具有非常地相似性,具有鲜明的三维空间效果,光线从西南摄入,投射矫健的马身之上,形成暗淡的阴影效果,而画法主要采用平涂,三匹马造型各异,如三球各自顾盼生辉,正如“西洋画如打台球,三球相距或远或近,顺者易合,逆者每违”[18](P72)更加衬托出画面造型意识。除在造型意识具有相似性之外,三马更为高大,稍远的昂首阔步,身体前仰似有奔跑之意,而前两匹马,身体稍后仰,其中白马眼睛似有迷离之意,而棕色马略显胆怯,同时结构精密,法度谨然。也许正合徐悲鸿此时境遇,总体充满谦和之意,以“推崇宋法,务精深华妙,不尚士大夫浅率平易之作”。而此时,西方摄影术传入,早期绘画在追求“惟肖”逼真的同时,或受到照相术的影响,具有照片效果,融入了西方绘画造型技法,稍有雕塑的痕迹,尚未有意识地融合中国画的传统笔墨,并未形成雄健阳刚的笔墨观念。虽形成了早期具有东方色彩的造型意识,但这样虽以笔墨画就,却不能称为中国画。
此后,“五四”高扬的激进思想逐渐退潮,众多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对待中国画的态度即出路问题,也逐渐对以西画为主导产生质疑。而1929年国民政府在上海举办全国美展,掀起了“国画复兴运动”,相继提出“中国文化的本位”主张,强调“负有复兴中国现代艺术之作家”的努力。这样开始了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笔墨精神重新整理中国画,越来越看到文人画的精神价值,“用传统风格作画,就是宣告一个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忠诚”[1](P60)。这样中国画从边缘逐渐又回到主流。1926年在《古今中外艺术论》中,徐悲鸿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对于中国笔墨意境的关注。“吾个人对于中国目前艺术之颓败,觉非力倡写实主义不为功,吾中国他日新派之成立,必赖吾国固有之古典主义,如画则尚意境,精勾勒等技。”[18](P68)1930年“是时多见郎世宁之画,虽以南海之表彰,而私心不好之”[19](P199-200)。可见徐悲鸿已经有意识摆脱康有为的束缚,彰显对忽视中国笔墨意趣“私心不好之”。而在具体笔墨表现上《马》[17](P34)(1930年)开始有意识地以中国画的笔墨意识进行构图与书写。其中马首棱角鲜明,凌厉恣肆,而眼睛与耳朵以及马身的轮廓线均以中国画的意境概括能力,浓墨一挥而就。在马鬃的处理上,虽然以大写意的笔墨挥洒,但在腿部关节的处理上并未彻底贯彻书法笔墨。这一点在此后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鲜明地对比。在此,徐悲鸿明显有意识地对传统笔墨与西方造型的融合进行探索。
可以说1930年以后,他的马画真正开始以笔墨参以西方造型,从尊重客观的写实到物我合一的交融境界,逐渐到达人格化的表现;从笔墨较为细弱逐渐转入雄健遒劲;
主观意识逐渐增强,那种崇高、雄健气贯长虹的姿态逐渐显现;马的壮伟、浑厚、笔墨强劲为主要特征的艺术风格逐渐得到确立。对此苏立文曾认为1930年“他尝试将传统笔墨技巧与他在巴黎所学来的写实性人物造型相结合……显示了画马的娴熟技巧”[2](P136)。而若以画册而论[17](P43),1935年的《毋食我黍》至1939年《霜草识秋高》《奔驰》无疑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完成了对于传统中国画笔墨寄兴的审美境界。同时,正如前文所述,徐悲鸿对中国画批评正是基于中国画对形、色感受力的缺乏。如果说早期他急切地改良赋予马画以色彩,那么到了1930年以后,却有意识地放弃孜孜追求的色彩,以黑白两色构建自己的笔墨世界。笔墨,也在造型观念的基础上得到了修正,突破了马匹的轮廓笔墨的局限性,扩展为体面用墨的纵意,达到了笔墨与造型的浑融。“徐悲鸿的中国画笔墨无处不渗透着欧洲近代写实绘画的造型因素。”[20](P85)如在《霜草识秋高》中,对各种笔锋的兼用,并通过虚实、粗细、浓淡、枯润、轻重等变化而消解了图像的轮廓,而又以大写意没骨画法使外轮廓与内体面容为一体。马首笔墨凌厉,眼睛黑色饱满,窄脑门,大鼻孔,大眼睛,嘴唇张开,牙齿外漏;马胸、马腹线条以篆书的笔意,而在腿部用笔剔除传统以线勾勒,已经摆脱单纯的涂抹,在关节处亦以篆书、中锋用笔,用笔顿挫虚实。在用墨方面,马尾用焦墨与湿墨并用,而在头部又以涨墨点染,其笔既概括又富有变化,长短、宽窄、浓淡、黑白参差错落;而在身躯方面以留白的空间点缀,又构成“点醒”提升精神与光影效果,“用光影以显示体积与分量感”[16](P12-135)具有西方素描的痕迹;在1940年《群马》则黑白灰各种黑色层次穿插变化,显示出用笔的雄肆之风。把强烈的黑白对比分布在马的头部和肩部,马身躯的阴影部分则采取柔和的灰调,由于黑白灰的结合,画面又产生了西方的焦点透视功能;在马的肢体时,时而隶时而篆,刚劲,雄健;鬃毛和尾部则运用了书法的飞白的苍劲,淡墨与焦墨相结合,形成了润燥的笔墨效果,而为了凸显马的雄健恣肆气贯长虹的气势,尤其在奔马中拉长了马腿的线条与长度。在此,批评徐悲鸿的林木也不得不承认:“在动物画上,徐悲鸿优秀的书法素养也开始发挥其潜力。他的画马用线十分自由、生动、活波,中锋与侧锋并用,长长短短,粗粗细细,有时快速飞扫,有时缓缓慢写,浓淡、提按、顺逆种种讲究都出来了。”[21](P358)而“种种讲究都出来了”正是林木看到了徐悲鸿熟练的中国画笔墨意识,以书法的笔墨表现解剖透视,却呈现出阳刚遒劲的审美风格。
另外,他的马画凌空飞动的气势,豪放不羁、气势壮阔的马尾及鬃毛,更显出战无不胜、勇往直前的中国气派。而徐悲鸿的许多作品均来自传统诗文范畴《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九方皋》等并以题诗自况“浇心中之块垒”,而他的马画更是如此。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驻沪十九路军与上海民众联合抗日,而徐悲鸿感受此热情,奋笔疾书《独立》,表达出希望国家摆脱积弱,向往独立强盛。而在1935年《奔马》所题“此去天涯将焉托,伤心竞爽亦徒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1940年身居马来西亚,听闻鄂北大捷,奋笔疾书《群马》,并提“昔有狂人为诗云:‘一得从千虑,狂愚辄自夸,以为真不恶,古人莫之加’。悲鸿时客西马拉雅之大吉岭。鄂北大胜,豪兴勃发”。1941年徐悲鸿客居他乡,却对于第二次长沙会战,更是“忧心如焚”,题画《前进》“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也。企予望之。悲鸿时客梹城。”[17](P3)马的昂扬奋进,奔腾不息承载了他爱国的情感并将情感画作一种昂扬战斗的精神,用马的造型意识而表现出来。
可以说徐悲鸿的马画,一方面秉持自己的传统文化身份,而另一方面以西方焦点透视的造型观念介入中国画的笔墨精髓之中。“他(徐悲鸿)的画马既体现了西方绘画严格的透视、解剖要求,又表现了中国画的写意渲染和书法用笔的趣味”[22](P145),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阳刚风格。如果说唐之韩幹,元之赵孟頫均画马,如人品性,追求的是温良恭顺,虽偶有运动感,却牙齿不外露,鼻孔较小,失其真实并以肥为美而显雍容华贵。那么徐氏的马已经摆脱了“荒寒野逸”,形成了以崇尚雄奇、刚劲、凌厉的审美原则。而为突出阳刚的美学风范,在造型写实的基础上特意拉长了马颈与马腿,而在马尾上基本放弃真实的下垂,增其摆动姿态,大写意“飞白”干湿融合;同时舍弃了传统的马画“画肉不画骨”,而以风骨兼备“一洗万古凡马空”。而“画家在作画时要有自己的创造,有取舍,有强调,虚实处理,有画家自己的意图,有画家独到的创造”[23](P224),而所谓有“自己的意图”与“独到的创造”正是以雄健阳刚之气承担国民精神的重塑。“艺术家即是革命家,救过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苟能提高文化,改造社会,就是充实国力了。”[24](P81)正如前文所述,元明以来的笔墨荒寒放逸,正是中国衰败在艺术上的表现。那么徐悲鸿的中国画阳刚笔墨的诉求即是一种精神和方法,以拯救衰颓的国民精神。“今日中国一切衰败之病根,在偷安颓废,挽救之道,应易以精勤与真实,而奋发其精神。”[25](P58)可以看到徐悲鸿对于阳刚美学的诉求,不仅仅是对中国画笔墨荒寒的变革,更是国民精神气质的革命。而以此逻辑查验,不难理解他猛力批判文人画末流的荒寒、枯淡、残山剩水、枯木竹石的阴柔,认为赵、董的缺少血性、追求温柔敦厚之风,正是国民精神在绘画上的极端表现。而坚持对外来艺术“必须自有根基,否则必然成为两片破瓦,合之适资人笑柄而已”[6](P114)又凸显传统的民族文化身份。对此,他的爱徒艾中信所言“他画马不是单纯地画马,而是在马的身上寄托他自己的心情和意志,反应艺术家对生活、对于社会、对于祖国以致整个世界的看法。”[17]
概而论之,徐悲鸿的时状语境之下,马画采用西方的造型意识以阳刚雄健的画风艰难地改造传统文化人末流的弊病,承担起了改造国民性的重任,那么他“出国学习西方艺术,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艺术的技巧与形式来改良陈陈相因的传统画学,更是背负着一份民族崛起和文化抗争的使命”。[26](P10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