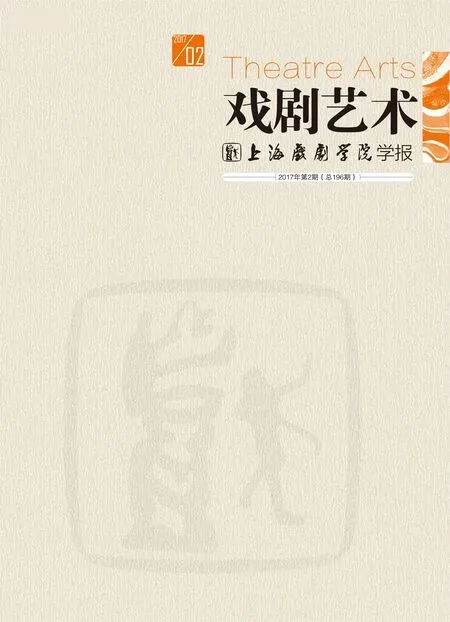《席》与《等待果陀》:京剧对“荒诞剧”的改编
■冯 伟
《席》与《等待果陀》:京剧对“荒诞剧”的改编
■冯 伟
戏曲对“荒诞剧”有过两次改编,分别是1982年魏子云改编自《椅子》的《席》和2005年当代传奇剧场的《等待果陀》。虽然看似相去甚远,但戏曲与荒诞剧在思想背景和表演形态上均可呼应,如禅宗思想和丑角代表的喜剧精神。《席》的主创并未深挖尤奈斯库与中国文化的共性,加之缺乏统筹的导演,作品沦为创新不足的应景之作;而当代传奇剧场的团队在高扬艺术家主体性的同时,充分把握原著的精髓和京剧的长短,突破剧种对演员的限制,丰富了戏曲跨文化改编的可能性。由此亦见对话原则和艺术家能动性对跨文化戏曲改编的重要意义。
荒诞剧 京剧 《席》 《等待果陀》 跨文化戏曲
1982年,被马丁·艾斯林称作荒诞派①剧作家的欧仁·尤奈斯库应邀赴台访问,台湾戏剧界为表示欢迎,决定排演尤氏一剧。几经斟酌,决定以京剧改编,邀请军中剧团“大鹏剧团”的哈元章和马元亮扮演《椅子》中的夫妇,请著名学者魏子云操刀。此事在台湾戏剧界轰动一时,主流媒体竞相报道,并为尤奈斯库举行访谈和座谈。这是戏曲改编荒诞剧的首例。时隔20余载,由吴兴国所创的当代传奇剧场于2005年改编《等待戈多》(台译《等待果陀》),并重演数次。此次改编亦是剧团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如果将两部作品置于跨文化戏曲改编的整体脉络中,不难发现其与众不同之处。
据初步统计,改编外国经典的戏曲作品已达数百,其中绝大多数是对莎剧,尤其是其中名剧的改编。易卜生、布莱希特、奥尼尔、斯特林堡的作品及希腊戏剧亦不乏改编之作。相较之下,除布莱希特,其他西方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作品(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剧等),即便剧本完整、叙事清晰,也很少被改编。原因不难设想。从被改编作品角度审视,备受青睐者多为雷曼在《后戏剧剧场》中提到的“纯粹戏剧”和“非纯粹戏剧”,其核心在文本,强调人物、情节、冲突,聚焦社会生活,并以再现为主要的表现方式。[1](P.47)在实际操作中,这类作品因为与戏曲的诸多共性,不难进入戏曲的框架,并使用戏曲的文化符码。此后,剧场要素逐渐摆脱文本的奴役,开始获得独立;而人物、情节等,则难以维系其主导地位——须知,人物和情节对戏曲几乎不可或缺。于是,戏曲本身的特性也构成原因。以文本为核心的戏剧作品,主旨是在行动中塑造人物,而文本重要性淡去之后,人物和行动则很难居于核心,一旦人物塑造不再是要务,以行当为根基的戏曲演员就很难发挥本事去形塑人物和表现技艺②——毕竟戏曲自身表演形态的丰富和卓越,使改编者难以割舍其剧种特色。在认识到自身长短之后,选择与剧种亲和力强的作品则顺理成章。而选择淡化人物塑造、几乎零情节的荒诞剧,相较之下,则有些不可理喻了。
除了对戏剧形式兼容的考虑,思想性也是一大要素。因为现当代戏曲作品中文学性卓绝的凤毛麟角,所以部分改编者寄望引进西方经典来弥补戏曲作品思想性之不足,其中学者们青睐的人文主义、启蒙、妇女解放等具有现代性特色的观念是热点。由于重视原剧中的观念,改编者在诸多方面对原著均亦步亦趋。相较于“纯粹戏剧”和“非纯粹戏剧”,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戏剧蕴含的观念,尤其是所谓“荒诞性”,与戏曲遗产本身,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在即时性上,也不为急需为戏曲寻找现代性的实践者和研究者看重,更何况光靠文本挪用,也无法完全把握此类作品的精髓。
在这种背景下,《席》和《等待果陀》的位置确实尴尬。但戏曲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戏剧在艺术上是否真的如此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是否由其他原因导致?跨文化戏曲是否还有更多的可能性?为了回应这些问题,本文试图针对上述两个改编,进一步追问:两次改编策略如何?有何异同?荒诞剧和戏曲能否相互阐发?改编荒诞剧和改编其他作品有何不同,对戏曲跨文化改编有何新的启示?在回答之前,本文暂且搁置前文所述的戏曲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戏剧之隔阂,从理论上探讨荒诞剧改编成戏曲的可能性,并以此为标,来分析两部改编之作。
一
为了沟通,跨文化改编首先需要找寻一个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往往是文化间的异同和相互的映照。不难发现,戏曲之所以能适应荒诞剧,是因为在三个方面都能找到“出发点”:形而上学、语言和表演。
戏曲生长于中国文化,承载传统思想;荒诞剧也自有一套独树一帜的形而上学体系。大量的跨文化戏曲改编,都必须面对剧中不可或缺的宗教或哲学要素,并在中国文化中寻找对应物。一些普世的观念,尚可移植,③但很多时候文化符码并没有对应物,为剧情需要,只好生硬地强加,④其结果,如宫宝荣所言,“往往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令观众无所适从”[2](P.140)。荒诞剧受西方战后思潮影响,将代表逻各斯的上帝驱逐,而失去上帝的人类则与最后的家园断绝联系,成为无能为力的被放逐者,一切形而上学、宗教和超验的意义都被剥离。虽然戏曲与宗教关系密切,但多被世俗化,鲜有荒诞剧这样的世界观。⑤艾斯林对荒诞剧的理论建构主要基于加缪式的存在主义,而存在主义在东方的共鸣者,就有佛教。以佛教的视角审视,荒诞剧关注“人的状态的荒诞性带来的这种形而上的痛苦之感”[3](P.8),并试图揭露世界之空和无意义。这种关联为戏曲改编荒诞剧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础。
除了形而上学的特点,艾斯林还为荒诞剧总结了一大特征:“彻底地贬低语言。”[3](P.9)在语言观上和荒诞剧最接近的是禅宗。禅宗独特之处在于否定文义,不立文字但又不离文字,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拘泥经文,呵佛骂佛。禅宗和荒诞剧对语言工具的怀疑,根本的指向是理性思维。由此,艾斯林敏锐地发现,禅宗和荒诞剧都拒绝“概念思维本身”[3](P.296)。在语言观这个层面,荒诞剧被战后反思语言和逻辑的思潮裹挟,并呼应占主导的后结构主义。因此,学界不乏将后结构主义与禅宗语言观相比较的研究。⑥反思逻各斯,目的在于消解遮蔽世界真相或人性本然的外部建构。而荒诞剧能否重新将式微的佛教思想引入戏曲,引入之后效果会如何,姑且拭目以待。
厘清思想背景的联系,还需探讨表演上的可行性。荒诞剧的非文本要素对演出的阐释不可或缺,“以舞台本身的具体和客观化的形象创造一种诗”[3](P.9),但本文探讨重点不在舞美等,而在演员的表演风格。荒诞剧中的表演出格,与基于斯坦尼体系的自然主义戏剧相去甚远。“剧场本身就是具体的现实,无须频繁地依赖外部现实,因此荒诞派剧作家需要演员有超越了寻常自然主义风格戏剧的精湛技艺。”[4](P.56)如尤奈斯库偏爱木偶式的人物,强调人的机械性和行为之怪诞[5](P.26),而贝克特突出人之能动性的缺乏和精神肉身的分离。他们对演员都有近乎苛责的要求,并令其放弃斯坦尼体系的表演方法,以此获得一种风格化的效果。由于风格化与喜剧有天然的联系,他们也常起用丑角来执行喜剧的表演程式。以本文要探讨的两部剧为例,《椅子》的副标题是“悲闹剧”,而《等待戈多》则是“悲喜剧”⑦,二者的中心语都是喜剧,足见作者对喜剧性的看重。在两部作品中,喜剧性主要不依赖戏剧结构,而是丑角的表演。起用丑角,原因有二:第一,丑角行事乖张,暗合荒诞剧对反戏剧的追求;第二,丑角表演夸张,肢体表现长于言语表达,符合荒诞剧对喜剧性和非文本要素的看重。戏曲丑行相较其他行当所受约束最少,甚至可以适当地破坏程式,自由发挥。荒诞剧在表演上不可或缺的反戏剧性和喜剧性,在所有戏曲行当中,只有丑角才能执行。
丑角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也不容忽视。西方戏剧丑角的渊源有:白痴和疯子、圣愚、宫廷弄人等。其共通之处在于以荒诞不经的言行点出真理,但又不会被人当真。在《李尔王》《哈姆雷特》等作品中,我们不难从丑角扮演的弄臣和掘墓人身上找到形而上学的印迹。西方丑角的基本特征是不合时宜,这种不合时宜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代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反常存在状态。[6](P.208)丑角的这一历史渊源也有人类学色彩。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丑角和丑角式的人物层出不穷,如俳优、疯僧等。历代禅师中有大量离经叛道、行事疯癫的人物,装扮和言行举止都不合于俗。在《禅与喜剧精神》一书中,海耶斯探讨了禅师和丑角的相似。在他看来,丑角和禅宗大师一样,“模糊界限和常规的区分,且行为总是不可预期”[7](P.88)。他们的言谈举止具有很强的“表演性”——换言之,总是有言外之意要表达。但言外之意无法通过分析获得:恰如“丑角表演几乎不需要观众进行阐释”[8](P.113),禅宗也看重门徒直观的悟性(而非理性)。⑧禅师们“截断理路、解构语言、取代文字、直指人心”[9](P.36)的做法,根本上就排除了理性分析。海耶斯所谓的丑角是西方传统中的丑角,但戏曲的丑角能否与其等量齐观?王季思曾将参军戏等打诨手法和参禅相比,认为禅师“竿木随身,逢场作戏”[10](P.243)。康保成在《傩戏艺术源流》中,也分析了净角与佛教的渊源。[11](P.188-211)从人类学视角来看,丑角与智慧的关联,并不受文化所限。由此观之,丑角也能联接荒诞剧和戏曲。如果将戏曲的丑角放入禅宗的框架,重建荒诞剧与禅宗的关联,未必不能生发精妙的禅机。
二
戏曲与荒诞剧的异同和映照使沟通成为可能。在跨文化戏曲中,理想的沟通并非仅为求同存异,也非通过重复来强化陈见或体系,而是相互对话,给彼此带去新的文化阐释和美学范式。这也是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精华所在:所有的文本和话语都是特定时空语境的产物,一旦语境改变,意义就会更换。文化对话便是将彼此置于对方的语境中,生发新的意义,其中,相互理解是对话的前提。因此,对话的过程在于深刻理解彼此后,再以不同视角相互关照。反观诸多戏曲的跨文化改编,因为欠缺根本的相互理解,不少作品与原著未有深入对话,给人换汤不换药之感,重复吞噬他者、或被他者吞噬的老套。如果贯彻了对话原则,跨文化改编无法单纯复制原著形神,也无法完全保有戏曲特质,结果只能是重释过的原著,以及重塑过的戏曲。然而,文化和戏剧本身不具能动性,对话有赖于作为主体的改编者团队。在对《席》和《果陀》的分析中,本文亦重点强调对话的主体。
《席》剧改编策略如下:戏曲编剧和学者魏子云受戏剧教授胡耀恒所托,将《椅子》酌情删减,改换文化背景,并将对话改作念白和唱词。期间,魏子云还得到黄美序和刘琍两位戏剧学者的指点和支持。魏子云自认不敢对原著提出新的阐释,便在国剧的框架中忠实原著。同时,他也承认,到了创作后期,他将个人情感投射到了老人这一角色之中,将其改造成一个儒家色彩的人物。[12](P.28)对此,刘琍提出了批评,认为此剧既无新的阐释,又不忠实原著,尤其是魏子云对原著做了不少删减。[13](P.142)此剧蓝本为老生老旦戏《清风亭》,人物造型、说白唱腔、舞台位置动作等,都用了老戏中的规范。[14](P.9)更重要的是,《清风亭》和《椅子》“都呈现着人生在日暮途穷中所感到的苍凉,在苍凉中所燃烧的希望,以及在希望幻灭后的自了余生”[14](P.10)。胡耀恒另邀富连成科班出身的哈马两位师兄弟扮演夫妇。其中哈元章为台湾四大老生之一,而马元亮演出以小花脸为主,兼演老旦,有“戏篓子”[15](P.57)之称,只是根据评论,在此剧中马主要以老旦应工。文武场亦做相应设计,用以配合剧中上场客人的身份——尽管客人都不存在,只是通过暗示表示登场。原剧中五十多把椅子,因为照顾舞台大小和京剧演员施展身段的空间需要,减为十二把。此外,限于经费,灯光未遵循原著要求,只是保留了普通演出的照明效果。按照台湾当时京剧的惯例,此剧亦无导演。整体而言,此剧恪守京剧程式,对原著少有发挥。演出结束之后,评论界一致肯定,此剧的演出,突破了国剧可以表现的题材范围,因此意义重大,但在具体的操作上,也有不少建议和批评。时隔三十载,今日的评估未必细致,但或许更加客观和全面。
从剧本来看,此番移植最大缺失在于对原著阐释的失落,从而令其在进入中国文化背景后,成为无本之木。但这并非不可避免。尤奈斯库曾多次提及创作与佛教乃至禅宗的关系,如《椅子》中舞台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你所看到的两三个人物,只能算是某种流动性构筑的枢纽:大体上说,他们也是没有实质存在,转眼即逝而且不稳定,注定要像红尘世俗一样化为烟云乌有。”[16](P.34)按照佛教的观点,万物处于流转之中,生长消灭便是空无。他甚至认为外部世界是我们心智主观武断的杜撰和创造,[16](P.35)这样的观点与佛教一切皆幻梦的看法相似。而经历过二战的尤奈斯库,也不难有一切皆苦的观点:“我的确认为生活像一场恶梦,既恐怖又痛苦,令人难以忍受。”[17](P.228)他对逻辑和语言的态度则更是接近禅宗:“我的剧作是建立在‘无意义’、‘不像真实’之上,建立在逻辑之外……有必要认清逻辑并不能表明真理,承认我们无法认清‘真象’。”[18](P.217)而以禅宗视点来看,认识世界无须“迷著经教,拘泥文字,陷于知解和妄念的窟穴中而不得自拔,不得觉悟,不得解脱”[9](P.36)。作品中椅子的充斥以“有”反衬宇宙之空无,但这空无也并非仅仅是空无而已——如谢克纳曾指出,“我们必须在《椅子》中寻找一种能让我们与虚无面对面的东西,因为这种虚无的深渊将我们与永远无法抵达的事物隔离开了”[19](P.66)——换言之,《椅子》中有一种针对虚无的积极的、启发性的精神力量,需要观众去领悟。剧中老人的喋喋不休但又毫无内容,实际上暗示了语言的无力和无用,莫不对应禅宗“不假文字”的初衷;而以禅宗视角看,老人一生的智慧无法言说对应禅宗沉默的哲学。最后,尤奈斯库不忘以幽默作为作品和禅宗的桥梁:“我在戏中所提出解决人生的方法是‘笑’,在精神上与禅宗很接近。”[20](P.271)尤奈斯库对禅宗的理解是,禅师和佛陀之笑,是明心见性后的超然之笑,而这种超越式的顿悟,也是尤奈斯库所追求的。以上种种,改编者完全没有领会,而是将原剧生硬地纳入京剧体系,忽视了形而上学的考虑。
改编的缺失还体现在表演方面。当时台湾京剧界正举行军中竞赛,哈马二人忙于比赛,百忙之中筹备和演出此剧,投入有限,直接挪用戏曲程式,敷衍一番了事。剧本改编于九月底完成,而十一月初便上演,期间只有一个月时间排练——传统剧目无需太多排练时间自不待言,但因为此剧是新作,若要求成,也只能借用和组合传统程式。然而,光靠京剧是否足够?刘琍批评道,“《椅》剧中所有夸张、离谱的言辞、动作,京剧都无法承纳”[13](P.142),而最终结果是,该闹剧没有“闹”起来。 黄美序和胡耀恒在排练中曾建议加入西方戏剧的表导演方法,但因为他们是外行,建议不符合京剧表演艺术的规范,未被采纳。[21](P.14)曾有学者总结,“尤奈斯库对丑角式和木偶式人物的塑造,……表现的不是人类行为的荒诞,而是人类状况的荒诞”[22](P.89),足见演员身段与形而上学的关联。因此,黄美序指出,建议老生老旦加上西方默剧的身段,但这对演员要求太高,最终未能如愿。仙枝在演后也一针见血地论道,若用丑角和老生来演,效果势必会有改善。[23](P.127)可惜的是,老生和老旦的身份和体制,并无法容纳两个插科打诨的丑角。而“戏篓子”马元亮原本可以发挥所长让演出更加丰富,但可惜的是,他并未如此尝试。对传统的恪守预先排除了原本可能实现的效果。
简而言之,因为两个文化的浅层对话,在形而上学的处理上,此改编并未给京剧带去新的启示,而在表演艺术的发展和突破方面,此剧更是如履薄冰;原剧也并未因为京剧的改编而焕发新生。此次改编主要是学者操刀,演员配合,沟通和投入有限,学者难以对艺术突破提出有说服力的意见,而传统科班出身的演员也坚守传统,无意违反京剧的规范,因此改编沦为命题作文式的应景之作。其问题之根本恐怕在于缺乏一个统筹的导演,去将原著的精神、改编者的诠释、演员身段的设计、舞美等要素整合起来。马元亮虽早就担过大鹏剧团的主排,但实际上并非话剧意义上的导演,对舞美、布景等并无太多经验,[15](P.492)遑论京剧之外的内容。而缺乏具有能动性的导演,改编便不可避免地落入传统的窠臼。黄美序在演出之后反思道:“假如有一群有国剧训练和素养的艺人,他们只把自己看成认真的‘舞台’工作者——而不是‘国剧’工作者——并能百分之百地接受导演的意见去做,他们能不能把荒谬剧演得很成功呢?经过一再的‘大胆假设’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21](P.19-20)黄美序颇有先见之明,因为吴兴国后来的作品映证了他的观点。而《席》之失,只有在《果陀》的映照下,才会更加明晰。
《果陀》将原剧中的“戈多”改作了“果陀”,从而将存在主义和基督教背景换做佛教,尤其是禅宗。此外,它还肢解了京剧的表演程式,按照贝克特的要求取消文武场,成为一出“反京剧”。乍一看,如此操作问题多多,但在评判之前,不妨先从哲学和艺术形式两个层面来分析其做法是否可行。
虽然贝克特并未受佛教直接影响,但却从受过佛教影响的叔本华处获知佛教思想;⑨且有不少学者论证,包括此剧在内的诸多贝克特作品与佛教关系密切。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意大利学者法罗纳以佛教视角解读《戈多》的文章。在详细分析后,他论称,此剧“反思人类处境,并阐明了佛教四圣谛的苦、集、灭,道”[24](P.168)。与尤奈斯库一样,贝克特对语言的态度,也类似禅宗。贝克特曾写道,他倾向的表达方式是:“没有什么可表达,没有什么可做表达的依凭,没有什么可做表达的出发点,没有能力表达,没有欲望表达,但又非表达不可。”[25](P.103)此语听起来像绕口令,但结合禅宗对语言的游戏态度不难看出,贝克特强调的是“不离文字”,即在对语言的怀疑之余同时借助语言来表达。在剧中,“角色相互交谈,但无法交流任何事情,因为这种体验已经无法交流”[26](P.251)。而与此同时,“这类脱节的对话的使用突出显示了语言的分裂和一切意义的消失。它导致一个诗的世界的出现”[27](P.220)。对这种诗性的把握,理性和逻辑判断无能为力,只能依赖“明心见性”。除了使用诗性的语言,原剧中还有大量悖论式和同义反复式的对话,而这些都属于禅宗语言策略中的“间接”交流。⑪
由以上观之,将贝克特置于佛教的背景之中,理论上可行。而从吴兴国的个人经历和生命体验来看,也有迹可循。吴兴国曾慨叹母亲一生之悲苦,并明言此剧为母亲而作,[28](P.95)而更加隐蔽的线索是他与禅宗的多番相遇。吴兴国从1997年开始酝酿此剧,一直未找到理想的演绎方式。2005年因为患病,在法鼓山随圣严法师打坐修养,某一天顿悟,脑海里突然浮现一棵树和一条路的影像,于是找到禅宗作为依托。[28](P.94)而在2002年,吴兴国曾在高行健编导的《八月雪》中扮演禅宗六祖慧能,也在其2004年莎剧改编作品《暴风雨》中加入禅宗的元素。由此可见,禅宗精神与吴兴国一直如影随形。在《果陀》中,两位衣着破烂、行为怪诞的丑角酷似禅宗故事中的疯僧,说话颠三倒四,话中有话,与禅宗的机语颇为相似。而剧场中喧闹和寂静的对比,配以古琴的旋律,极富禅意,所以吴兴国说:“《等待果陀》的两位流浪汉在游戏的话题无聊中建立永恒,并不断否决自己的语言和行为,这是六祖慧能的‘无生无灭’之说吗?而剧中人经常在喧闹之后的静止画面,又能点出‘法本无动与不动’吗?”[29](P.56)
吴兴国忠于内心体验和艺术直觉,面对贝克特的文本和京剧,却也保持了一贯的大胆作风,毫不束手束脚。原剧大多角色是丑角扮演,吴兴国和盛鉴二人均是老生演员,但却以丑行打底,破梭一角以花脸马宝山应工,而垃圾一角则完全使用武丑林朝绪。在部分否定了语言本身对意义的有效传递之外,贝克特的作品依赖丑角的肢体来传达真理。对此笔者在他处已有讨论,在此不作赘述。⑫吴兴国使用丑角,除了形而上学的考虑,也是为了突破身段的限制。改编此剧,并非像以往一样,思考“如何在形式上突破,如何创新”,而是“当作一个演员功课”[30](P.213)。 他深知《戈多》一剧以欢闹著称,而肢体到位与否,直接影响最终的效果和“笑果”。原本京剧的肢体语言已经很丰富,但李立群多般嘱咐,“不要让观众睡着”[31],吴兴国便意识到典雅之京剧的不足,从而请来熟悉西方喜剧表演的金士杰训练演员。金士杰熟知原剧演出的精髓,为达喜剧效果,迫使演员们重审和重组京剧身段,亲自教授马戏团和打闹剧丑角的表演方法,并设计了一些走位和笑点。这种与京剧、尤其是京剧老生无关的要求,对已经跨行演出多年的吴兴国而言,或许不难,但对其他经验尚浅的演员,则几乎难以忍受。吴兴国表示,一开始盛鉴因为年轻,对自己的京剧训练颇为自信,不愿接受金士杰这位京剧外行的指导,[31]但因为时间的加深和吴兴国的劝导,盛鉴也迈出京剧的框架。他回忆道:
整个排练和演出的过程和以往任何作品都不一样。根本没有现成的程式可用。……排练过程是非凡的创造过程。在金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借助已有的技巧,借助刚学的西方丑角的技巧,借助对那些莫名其妙的破句子的阅读,创造了一种新的表演风格。[32](P.269)
对演员而言,表演此剧意味着对已经塑形的京剧身体的突破。当老生演员吴兴国和盛鉴以丑角的心态对待程式,并虚心接受金士杰的指导时,其身体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而这种不拘于形的姿态不也体现了禅宗的思想?
此剧的表演风格已非中规中矩的传统京剧,而是一个包含诸多喜剧手法、但又保持了高度风格化和节奏感的杂糅体。如吴兴国所言:“有金士杰协助进行第二度的开发,演员所吸收的接近生活写实表演和幽默的创意,活化了原设计的唱、作、念、打架构,表演经过他的指导,使得全剧有了更明确的目标。”[29](P.56)在金士杰和吴兴国的合作和统筹下,此剧在理念上和实践上都有了章法可循。所以导演了贝克特几乎所有剧作的沃尔特·阿斯姆斯(Walter Asmus)看到吴兴国此剧之后,才会激动地与之彻夜长谈,并发出感叹:“看到你们用这种形式表演的时候,有一种节奏把内在的、形而上的、以前从未开发的东西表演出来了。”[33](P.13)
阿斯姆斯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吴兴国的改编于他既熟悉又陌生:此剧身段设计,一是有意挪用西方打闹剧和歌舞杂耍场等的戏剧程式,使演员的身体有了荒诞剧追求的怪诞感;二是借助京剧固有的节奏,以风格化实现了贝克特戏剧作品追求的音乐性⑬。阿斯姆斯对京剧程式的陌生并不干扰对此剧精神的把握,因为京剧被打碎之后,程式本身的意义已经淡去,观众无法以寻常看京剧的眼光打量此剧,只有悬置对京剧的固有理解,重新以身体去体会表演带来的感触,而这种感触,结合禅宗的背景和古琴音乐,则给人以形而上学的思索。至于吴兴国是否忠实于贝克特,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并不重要,因为《果陀》是一个经过了充分对话的作品,“中西合璧,浑然一体”[34](P.359),而非简单的并置和拼凑。
三
荒诞戏曲以最极端的姿态,前置了跨文化改编中暧昧和亟待说清的问题。通过比较上述两个改编,可以重审前文提出的关键问题。首先,充分的对话对改编必不可缺,上述两个作品,一个忽视对话,一个充分对话,在对本传统潜能激发的程度上,高下可判。由于荒诞剧对西方戏剧传统的反叛,故完全忠实传统,则无法获得作品需要的效果。因此,深思熟虑后的破和重立,是荒诞剧给京剧表演带来的最大收益。其次,所谓跨文化对话,实际上是艺术家主体的行为,有能动性的发挥,而非不同文化自身的相遇。以此来看,改编质量和成败,不取决于文化的相异或者相似程度,而取决于艺术家在调动文化资源时的能动性和创造力。面对远不如荒诞剧极端的外国戏剧,艺术家们又能有哪些创造性的发挥?实验自然不该被排斥,但需要以对话式分析和实践为前提。跨文化戏曲的一种理想模式是,摒弃“因地制宜、符合中国国情”的借口,摒弃拼凑程式、批量生产的做法,而是拥抱异质戏剧的挑战,激发深层次的反思,探索新的表演可能,从而推动戏曲的发展。
注 释:
①本文所谓荒诞戏曲,不同于《潘金莲》这样的“荒诞川剧”。魏明伦本人也承认西方荒诞剧与自己所谓荒诞川剧的区别。(见魏明伦《我做着非常“荒诞”的梦》,选自《戏海弄潮》,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年。“荒诞剧”这一说法在西方学界一直有人质疑,本文探讨的两部剧确有共性,并可以归入荒诞剧的范畴,但这并非意味着,艾斯林探讨的其他剧作或剧作家也是如此。关于此话题,宫宝荣曾在《中法戏剧交流中的误读现象之浅析》谈过,其他细节,笔者将在日后另文讨论。本文沿用“荒诞剧”之称谓,亦是因为两次改编的主创均如此理解两部作品,即便可能是误读,也能说明“荒诞剧”这一概念对其改编的影响。
②虽然莎剧也以人物复杂著称,同时戏曲也大量改编莎剧,但不难看出,实践者总是能找到比较便捷的行当套用策略:一是削弱莎剧人物的复杂性,直接削足适履,塞进戏曲的行当,如上海京剧院《王子复仇记》中雷欧提斯以花脸应工;二是演员打破行当的限制,不拘一格地吸收其他行当的程式,如当代传奇剧场《欲望城国》中敖叔征夫人扮演者魏海敏。
③ 如彭镜禧和陈芳取材莎剧《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河南梆子《量·度》,便将基督教背景换成了道教背景,且大量引用道教思想(如“天道好生”)来回应原剧中的基督教观念(如“爱人如己”“宽恕之道”)。
④此类案例以《哈姆雷特》中克劳迪思忏悔一场为代表。西方天主教有忏悔得拯救的传统,但在中国却无相应例子。大陆的越剧和京剧改编中都保留这一段,若要苛责,此等处理在文化上说不通。
⑤ 关于戏曲与宗教各个层面的联系,参见郑传寅《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9-378页。
⑥如王又如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后结构主义和禅宗以及庄子语言策略的共性:解构的策略、对语言边界的突破、间接交流。荒诞剧和后结构主义实际上有大量的重合之处,因此,语言观与禅宗也有相似。(Wang,Youru.Linguistic Strategies in Daoist Zhuangziand Chan Buddhism:The OtherWay of Speaking.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3.)
⑦关于此剧与喜剧的关系,参见冯伟《〈等待戈多〉与西方喜剧传统》,载《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⑧方立天总结禅宗“不立文字”的语言观,认为取代文字启发弟子的方式包括:棒喝,借助身体活动曲折地表现;体势,以各种姿势来表达;圆相,在空中或地上画圆,以象来启发;触境,令禅修主体从被接触的对象开悟;默照,以打坐默契真理(37-40)。
⑨Rosen,Steven J.Samuel Beckettand the Pessimistic Tradition.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6.
⑩Foster,Paul.Beckett and Zen:A Study of Dilemma in the Novels of SamuelBeckett.London:Wisdom Publications,1989.
⑪ 参见⑥,175-186.
⑫ 参见冯伟《〈等待戈多〉与西方喜剧传统》。
⑬ 贝克特曾说,“戏剧就是跟着音乐走”。 (McMillan,Dougald,and Martha Fehsenfeld.Beckett in the Theatre:The Author as Practical
Playwright and Director.London:J.Calder and New York:Riverrun Press,1988.16)学界也不断有学者分析贝克特作品中的音乐性。如《贝克特与音乐性》(Beckettand Musicality),《萨缪尔·贝克特与音乐》(Samuel Beckettand Music), 《贝克特与音乐之交融》(Headaches Among the Overtones:Music in Beckett/Beckett in Music)等著作。
[1]汉斯·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M].李亦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宫宝荣.当代中国戏曲舞台上的西方经典——兼谈改编的独创性[J].剧作家,2013(6).
[3]马丁·艾斯林.荒诞派戏剧[M].华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4]McTeague,James H.Playwrights and Acting:Acting Methodologies for Brecht,Ionesco,Pinter,and Shepard.Westport,Connecticutand London:Greenwood Press,1994.
[5]Ionesco,Eugène.Notes and Counter Notes.Trans.Donald Watson.New York:Grove Press,1964.
[6]Beré,Marcelo.“Clown:A Misfit by Profession — Misfitness and Clown’s Principles of Practice.”Comedy Studies4.2 (2013):205-213.
[7]Hyers,M.Conrad.Zen and the Comic Spirit.Philadelphia:Westminster Press,1974.
[8]Weitz,Eric.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Comedy.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9]方立天.禅宗的“不立文字”语言观[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1).
[10]王季思.玉轮轩曲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2]魏子云.〈椅子〉与〈席〉——改编法国荒谬剧为国剧的心声[A].魏子云编.法国椅子中国席[C].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
[13]刘琍.尤涅斯可的足下之灾——从〈椅子〉到〈席〉[A].魏子云编.法国椅子中国席[C].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
[14]胡耀恒.回顾〈椅子〉的平剧演出[A].魏子云编.法国椅子中国席[C].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
[15]王安祈.台湾京剧五十年[M].宜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02.
[16]尤涅斯可.尤涅斯可论〈椅子〉[A].蔡源煌译.魏子云编.法国椅子中国席[C].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
[17]林怡俐.尤涅斯可访问录[A].魏子云编.法国椅子中国席[C].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
[18]石鼓歌.尤涅斯可访问记——荒谬剧大师谈他的剧作[A].魏子云编.法国椅子中国席[C].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
[19]Schechner,Richard.“The Enactmentof the ‘Not’ in Ionesco’s Les Chaises.” Yale French Studies 29 (1962):65-72.
[20]荒谬的人生,荒谬的戏剧——尤涅斯可与我京剧坛人士首度接触讨论纪实[A].魏子云编.法国椅子中国席[C].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
[21]黄美序.〈席〉的形成与意义[A].魏子云编.法国椅子中国席[C].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
[22]Norrish,Peter.New Tragedy and Comedy in France,1945–70.Basingstoke and London:Macmillan,1988.
[23]仙枝.法国椅子中国席[A].魏子云编.法国椅子中国席[C].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
[24]Faraone,Mario.“‘Pity We Haven’t a Piece of Rope’:Beckett,Zen and the Lack of a Piece of Rope.” The Tragic Comedy of Samuel Beckett:Beckett in Rome,17-19 April 2008.Eds.Daniela Guardamagna and Rossana M.Sebellin.Rome:Universitàdegli Studidi Roma,2009.156-176.
[25]Beckett,Samuel,and Georges Duthuit.Proust;and Three Dialogues:Samuel Beckett&Georges Duthuit.London:John Calder,1976.
[26]Iser,Wolfgang.“Samuel Beckett's Dramatic Language.” Modern Drama 9.3 (1966):251-259.
[27]米歇尔·普吕讷.荒诞派戏剧[M].陆元昶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28]吴兴国.形塑新中国戏曲[J].二十一世纪,2009(4).
[29]吴兴国.残缺与慈悲的笑容[J].福建艺术,2006(1).
[30]卢健英.绝境萌芽:吴兴国的当代传奇[M].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31]冯伟.吴兴国访谈.2014年5月15日.
[32]Li,Ruru.The Soul of Beijing Opera:Theatrical Creativity and Continuity in the ChangingWorld.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0.
[33]李言实.我们要为等待而等待吗?访台湾当代传奇剧场艺术总监吴兴国[J].上海戏剧,2015(9).
[34]李伟.20世纪戏曲改革的三大范式[M].北京:中华书局,2014.
Title:The Feast and Waiting for Godot:Jingju’s Adaptation of Absurdist Plays
Author:FengWei
There have been two cases of xiqu’s adaptation of plays from the so-called theatre of the absurd,one ofwhich isWei Zi-Yun’s adaptation of Eugène Ionesco’s The Chairs in 1982 and the other Contemporary Legend Theatre’s adaptation of Samuel Beckett’s Waiting for Godot in 2005.Absurdist plays and xiqu havemuch in common,particularly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Zen Buddhism and the comic spirit embodied by the clown(chou).This was ignored in The Feast,the adaptation of The Chairs,and emphasized in Waiting for Godot.With no director to coordinate various parties,The Feast lost what it could have obtained from Ionesco.On the other hand,artists in Contemporary Legend Theatre highlighted their subjectivity and an understanding of both Beckett and jingju(Beijing Opera),which ended in a creative violation of jingju’s conventions.Thus the encounter between xiqu and theatre of the absurd in 2005 opened a new ground for intercultural xiqu,which demands the principle of dialogue and the valorization of artists’agency.
theatre of the absurd;jingju;The Feast;Waiting for Godot;intercultural xiqu
J80
A
0257-943X(2017)02-0022-10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