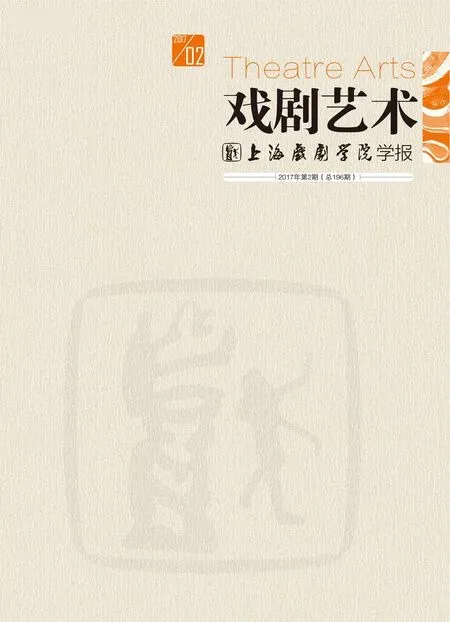作为摹仿、技艺与知识的悲剧
——西方“诗辩”起点处的悲剧理论重探
■唐 珂
作为摹仿、技艺与知识的悲剧
——西方“诗辩”起点处的悲剧理论重探
■唐 珂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文艺理论史上“为诗辩护”的首部系统性著作,也是西方诗学理论的鼻祖。在诸多艺术门类中,亚里士多德选择悲剧作为代表,通过对悲剧的理性化、系统化乃至哲学化,实现对艺术创作的正名。本文力图厘清亚氏悲剧理论的构建机制,并对“摹仿”“技艺”等古典诗学重要概念正本清源。
悲剧 《诗学》 摹仿 技艺 知识
在西方文艺理论的漫长演变过程中,有一条从对文艺创作之特质的界说逐渐发展为积极有意地为“诗”辩护、辨明的线索。西方“诗辩”的演变史是人们对创作艺术之核心观念的传承、挑战、变革的历史。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文艺理论史上“为诗辩护”的首部系统性著作,也是西方诗学理论的鼻祖。此时的“诗”涵盖文学艺术创作的各门类,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诗辩是集中通过对悲剧的界定和推演得以实现的。亚里士多德对文艺创作的正名,是通过把悲剧作为创作技艺的代表纳入其形而上学体系而完成的。本文将立足于源语言文本的细读考释,力图厘清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构建机制,并对“摹仿”“技艺”等古典诗学重要概念正本清源。
一、 “技艺”与“知识”辨析
在古希腊时代,“诗”是缪斯女神统领下的各门艺术的总称。柏拉图从正义/不正义的辩证思考出发,在道德和政治的视野下批判诗,诗首要是一种教化的方式、手段,谋求城邦福祉始终处于探讨技艺、知识和诗的背景中。柏拉图未曾创建一门以文艺为专门对象的诗学,亚里士多德则基于形而上学和分体学(mereology)完型出自己的创作论。亚氏诗辩将柏拉图的神启说置于一旁,其根本点和立足点是把诗作为一种技艺()乃至“科学”“知识”来展开辩护。
《伊翁》中著名的“迷狂说”将诗与神启联系在一起,看似赋予诗崇高的地位,事实上,柏拉图通过界说这种使诗人处于非理性状态而作出好诗的“缪斯的迷狂”,从而把诗定性为神启、迷狂、灵感的产物,并降至较知识()、技艺等而下之的地位。诗人由神明的感召说出自己尚乏理解的话,这在继承和发展希腊理性主义思潮的柏拉图看来距理智、真理远矣。此处诗人自身不能提供知识和创造知识的观点,与《理想国》第十卷诗人被贬为只提供影像的摹仿者(,普遍对应的英译是“imitator”)而非真正的制造者(,“poet”的词源)的论断相呼应。“如果说柏拉图通过‘迷狂说’揭示了诗人的‘非理性’特征,从而间接说明诗的‘非真理’特征,那么他通过‘模仿说’是想直接说明诗的‘非真理’性质。”[1](P.49)《理想国》卷 2、卷 3 的确肯定了乐教()的正面作用,不过卷7又指明这些教育是低层次的,不如数学和辩证法。在智慧的视野下,柏拉图认为灵感不如理解(,在英译文一些语境中即译为knowledge),技艺和知识的核心是理解。显然摹仿和作诗不是真正的技艺“”,作诗和颂诗依凭的不是技艺之长,而是神意所遣。需要注意的是《会饮》提到的某种真正的“诗艺”,它不同于旧诗人的诗艺,而几乎等于“哲学”,达到“”即“知识”的层面。因此我们必须审慎辨析“”在古希腊不同语境下的内涵。
“技艺”这个词在古希腊哲人那里绝不陌生。 该词后转为拉丁语“ars”,在英译文献中被译为“art”或“craft”。 在色诺芬那里,“”和“”是可互换的概念,“”的主干意义是“懂得如何做某事”,技能和知识没有分别。在柏拉图的语境中,每种技艺必定具有一种功能,也是其目的);匠人、手艺人为实现某种功能、目的而做工,实现这个目的的基础是理解它,匠人、手艺人心中必当存在着作品的模型或形式()。在《理想国》里,“”尤指事物存在的原因和原则,因此多被译为“理念”“理型”。①《政治家》(258e)中,爱利亚客人区分了与实践活动无关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原文是 “”。(“那让我们这样来把知识分为实践性的和纯理论性的两大类吧。”)[2]形容词“理论性”(),显然与“”(知识、理解)同一词根。此处的“”和“”概念本身没有实质区别。柏拉图亦曾将技艺与经验()对立探讨:技艺能够观照和解释事物的本性和原因,这一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一致的;《高尔吉亚》(464c)提到技艺与经验的另一个不同点在于技艺诉求的是对象的福祉,此处也照应“诗非技艺”的另一理由,因为在柏拉图那里,除了颂神诗、赞美诗以外的文艺几近都是无益于城邦的败德之物。
柏拉图从政教和真理的视野贬斥诗,亚里士多德则通过把诗置于技艺、科学的维度为诗辩护。在此必须澄清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中,“”和“”具有与柏拉图哲学不同的所指,也在不少场合各具不同的内涵,可以译为“科学知识”(英译多为“scientific knowledge”,或简称“知识”)、“科学”“认识”“学问”。亚里士多德无疑把创作视为技艺,但是这种技艺如何能够达到“科学知识”的维度?这是一个需要审慎解析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对西方文艺理论史的最大贡献,是从形而上学的立场出发,通过对悲剧的界定和推演,提出了一套系统化的创作理论,从而对文艺创作正名,“悲剧”正是这种“创制科学”的代表。亚氏的创作论完全不提柏拉图的神启说,而把创作的生成机制纳入其形而上学体系。“悲剧”能跃居知识和技艺的行列,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能根据普遍的理念划分为不同种类,它也能揭示普遍的智慧——它的内在结构和运作过程具有知识的特征。诗人的创作并非一定是为探索真知,但是杰出优秀的创作确实能够达到“”的高度。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即对经验和技艺做了区分,“人通过经验获得知识和技艺;如普洛斯所言,‘经验造就技艺,无经验诉诸运气’。当对一类事物的普遍判断从经验的许多观点中生成的时候,技艺就产生了”,“经验是对特殊事物的认识(),而技艺是普遍事物的认识”。(《形而上学》981a)[3]在此,知识和技艺的基本所指具有同一性:“技艺而非经验才是知识()”。(981a)亚氏从实用目的和求取知识智慧的角度区分了不同的技艺,并对感觉—经验—技艺—智慧排出高低等级:智慧是思辨科学的研究对象,它是最高的科学。“既然存在某种关于自然(笔者注:此尤指关于本原)的知识/科学,那么显然还另外存在有实践科学()和创制科学()。”(1064a)(“”英译即“poetics”)。“每一门科学都必定从某种意义上认识到‘所是的东西’并且把它用作起点。”(1064a)作为偶性的存在显然不具有原因和原则,因此任何科学所研究的“是什么”必定具有某种普遍性。诗人的创作并非总定旨在探索真知,拙劣的诗人创作的作品显然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对杰出优秀的创作进行理性的后设(meta,台湾译法)反思,从中探索普遍性、超越性的规则,进而指导创作,这确实能够达到“科学知识”的高度。
要对一种研究对象进行专门的科学研究,由范畴分析入手进行“属加种差的定义”(genus-differentia definition)是亚式形而上学的基本方案。在据说是亚里士多德授课讲稿的《诗学》开篇,作者如是说:“关于创作本身()和它的种类(),每种创作的特质……诸如此类的问题,让我们来谈谈吧。”他的探讨将依据自然()之序从首要的原理开始。 (1447 a8-13)[4]亚里士多德要探讨的是文艺创作的“技艺”,他通过“媒介”“对象”和“方式”这三种种差()来界定和分析属于“创作”这个大的“属”()之下的不同“种”(,species)②——悲剧、史诗、喜剧等等,并对比分析其性质、功能和要素成分。
在此插一句,范畴分析与定义法并非亚里士多德始创,柏拉图在《智者》中借爱利亚客人的申言曾细致探讨。(253d-254a)[5](P.71-72)如詹文杰在《智者》中译说明中所言:“从词源上看,‘’出自于动词‘’(生成),因此更接近于‘种族’或‘谱系’,而‘种类’是从中引申出来的更抽象的意思”。[6](P.181) “”本义指视觉上的外观,引申为“种类”。在柏拉图的意义上,“”是与“假象”()相对的、心灵所“见”之形而上层面的真相,“柏拉图经常用它(以及‘’)来表示与一般物体有别的、事物之不变的‘范型’(),这时候我们通常译作‘理念’。”[6](P.181)由此可见,对分类的后设思考与对理念-实相的探寻本就密不可分。
二、作为摹仿、技艺与知识的悲剧
亚里士多德的摹仿首先首要地具有“再现”的含义,他把摹仿纳入求知的手段之一。谈及诗的起源,亚氏并非诉及神启,而是诉诸自然,把诗的产生归于人的天性。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经验证明了这样一点: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例如尸首或最可鄙的动物形象。(其原因也是求知不仅对哲学家而言是最快乐的事,对一般人亦然,只是一般人求知的能力比较薄弱罢了。我们看见那些图像所以感到快感,就因为我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8](P.10)不仅如此,创作作为对自然的摹仿,它的内在结构和运作过程具有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自然的造物规律及其目的论(teleology)的特征。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的第四因——终极的、最为重要的目的因源自恩师柏拉图,亚氏汲取并发展了柏拉图的观点,并运用于对诗的探讨中:
总之,悲剧是从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悲剧如此,喜剧亦然,前者是从酒神颂的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后者是从下等表演的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这种表演至今仍在许多城市流行),后来逐渐发展,每出现一个新的成分,诗人们就加以促进;经过许多演变,悲剧才具有了它自身的性质(),此后就不再发展了。(《诗学》1449a)
这段话的主语始终是悲剧。作者以“客观”第三人称的(与柏拉图对话录大相径庭的)行文方式呈现出悲剧自然自主的生成演化过程,最后一句话尤其意味深远——“”英译多为“its own nature”或“its own natural form”,它是悲剧发展的动因和最终目的,在此意义上被讨论的悲剧便抵达“理念”的层面。如卢卡斯(D.W.Lucas)所说:“悲剧的形式如同一个有机体的生长,不断发展,直至实现它的目的,它的潜能完全实现。”[4](P.86)正因为文艺创作是一种潜能或曰能力,所以负责展现这个从可然到实然的过程的情节(而非人物性格)是作品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最能体现亚里士多德诗辩理想的创作体裁便是悲剧。
在《诗学》的整体论述中,悲剧同自然事物一样,其生成与运动的整个过程的目的是为自身之所“是”,因此悲剧是理性的产物,观众(亚氏心目中的理想观众)的情感也处于理性的规约之下。在前边所述的“属加种差的定义”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还把生物体的有机体概念引入对创作规则的指导:
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一件事件可能完整而缺乏长度)。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所谓“头”,指事之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发生者;所谓“尾”,恰与此相反,指事之按照必然律或常规自然的上承某事者,但无他事继其后;所谓“身”,指事之承前启后者。所以结构完美的布局不能随便起讫,而必须遵照此处所说的方式。[8](P.21)
在诗里,正如在别的摹仿艺术里一样,一件作品只摹仿一个对象;情节既然是行动的摹仿,它所摹仿的就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那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8](P.24)
基于其形而上学的思辨体系,亚里士多德在申言创作向善的同时把悲剧的衡量标准确立为它是否能够创作一套妥善的情节、摹仿完整的行动,情节编排比人物设置更为重要:“悲剧艺术的目的在于组织情节(亦即布局)……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性格’则占第二位。悲剧是行动的摹仿,主要是为了摹仿行动,才去摹仿在行动中的人。”[8](P.18-19)另外,从亚氏对悲剧的定义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亚氏对悲剧的青睐远胜于史诗、抒情诗等其它文体的原因正是出于古希腊悲剧与史诗、抒情诗相区别的体裁结构,以及亚氏对“真诗”“好诗”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赞同“诗”应当表达善、正义、美德,并通过为诗的创作设立规则、肯定好诗的益处来声援诗存在的合法性。悲剧摹仿比一般人好的人,喜剧摹仿(讽刺)比一般人坏的人,因此也就具有教化的意义。柏拉图痛斥诗人引发感伤癖、哀怜癖,培养和煽动心灵的低劣部分,让情感凌驾于理性之上,亚里士多德则对摹仿引发的情感及其快感予以肯定——悲剧能够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情,使
《诗学》的另一要义在于申明和阐释摹仿不只是消极意义的复制,它可以是理性的产物,为着善的目的,它能够超越当下现实,洞察到具有类型性、普遍性、本质性、规律性的“真知”,在此意义上,摹仿具有创造原创之真实的能力。[10]诗比历史更具哲学性(),这是亚里士多德颠覆其恩师柏拉图的惊天之语:
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8](P.24)
对于柏拉图指责诗人的摹仿不符合真实,亚里士多德予以正面肯定:诗人“必须摹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8](P.78)
一般说来,写不可能发生的事,可用“为了诗的效果”“比实际更理想”“人们相信”这些话来辩护。为了获得诗的效果,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8](P.85)
上述的话语行为已不同于前文给悲剧下定义时的陈述方式,而是呈现出言说者(亚里士多德)积极主动的“以言行事”和主观介入的语义模态——“必须”“可”。在此,亚里士多德把创作比拟哲学性思辨,作为一门创制科学,诗的创作不必是尽可能忠实地摹拟现实,而可以是在理性思辨的基础上创造出不存在的新事物,发现事物背后潜藏的普遍规律。
最后,亚里士多德的诗辩可称为典范诗学的论证方式:以最好的艺术创作为标尺,肯定杰出优秀的作品确实能够达到“知识”的高度。这种论辩方式也为菲利普·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沿用,直至二十世纪,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的《伟大的传统》、艾略特(T.S.Eliot)、特里林(Lionel Trilling)与新批评诸家,都是以拔群的典范作品作为批评的尺度与标杆来衡量和确定文艺创作的准则、范式和方法。
三、戏剧哲学与哲学戏剧
与亚里士多德集大成式的、前后论证较为连贯一致的诗学理论相比,柏拉图著作集中呈现的诗学观无疑充满了论述者自己的迟疑和矛盾;亚里士多德通过将戏剧理论化、哲学化的方式为诗辩护,柏拉图旨在逐诗,然而他的对话录本是一篇篇多声部交响共鸣的哲学戏剧——以辩证法结合修辞术,遍地比喻和神话故事辅助说理,贯穿着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通过人物的激烈交锋、矛盾踌躇推动哲学论证的深入。
柏拉图从政治教化和真理的视域下贬斥诗,但是却也有所保留地肯定了乐教的正面作用,尽管它们不如数学和辩证法。最具代表性地体现出柏拉图诗论内在张力的是 “高贵的谎言”()一说。《理想国》第二卷已提到可以用假的故事来培养教导孩童护卫者,到第三卷,苏格拉底在标举真实高于一切的同时也指出,欺罔之言于神无用,而对凡人来说是一种有特殊功能的药,也只有此时它是有用的。普通人不能接触它,必须交付于医生之手,因此只有城邦统治者为着城邦的公利方可使用这剂药。(389b-c)此谓“高贵的谎言”即是“假的”、虚构的神话或寓言故事,苏格拉底在论述它的时候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那么好,我就来讲吧。不过,我还是没有把握我是否能有勇气,是否能找到什么语言来表达我的意思,首先说服统治者们自己和军队,其次说服城邦的其他人:我们给他们教育和培养,其实他们一切如在梦中。 (415d)。[11](P.128)
在细致地讨论了如何开展护卫者的教育之后,苏格拉底踌躇犹豫但仍说出了这样一个高贵的谎言,这实际表示先前讨论的方案措施并不足以解决城邦和城邦护卫者将面临的问题。“高贵的谎言”存在的目的及合理性,在于它可用来防止护卫者变成色拉叙马霍斯式的统治者,并说服真正的(有政治技艺的)统治者把城邦的事情视为己任,愿意劳心劳力地统治城邦。苏格拉底的踌躇犹豫生动地昭示了他既要捍卫自己的理性主义立场,亦无法忽视和回避“摹仿”的力量。在《理想国》第十卷,正义、不正义的本质得到揭示,苏格拉底在申明诗的非真理性之后,转而自己创作了一个神话故事:正义者的灵魂和不正义者的灵魂在死后世界的命运截然相反。此时的苏格拉底——这个柏拉图哲学戏剧中的第一男主角事实上自己担当起诗人的角色,或者说躬亲为诗人作了示范。
四、小 结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为其悲剧摹仿论所展开的辩护是为革新柏拉图的摹仿论,悲剧的摹仿能跃居知识和技艺的行列,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能根据普遍的理念被界定和分类,能够揭示普遍的智慧——它的内在结构和运作过程具有知识的特征。通过对悲剧的系统化和科学化,亚里士多德实现了对文艺的正名,悲剧正是这种“创制科学”的代表。
注 释:
①本文的写作受恩师张汉良先生和前辈詹文杰老师的指点良多,亦多受教于“知止”中外经典读书会对《理想国》的讲读,谨致敬意与感谢。
④《智者》中译本第71页注:“这两个词的混同使用似乎是柏拉图中晚期对话录(如《巴门尼德》、《斐来布》、《蒂迈欧》和《礼法》)出现的一种倾向。”([古希腊]柏拉图《智者》,詹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1]詹文杰.教化与真理视域中的诗——重思柏拉图对诗的批评[J].世界哲学,2012(5).
[2]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3Atext%3A1999.01.0171%3Atext%3DStat.%3Asection%3D258e
[3]Aristotle.Metaphysics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Hugh Tredennick and G.Cyril Armstrong (tra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笔者译文亦参考(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Aristotle.Poetics.Introduction,Commentary and Appendixes by D.W.Lucas.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
[5](古希腊)柏拉图.智者[M].詹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詹文杰.真假之辨——柏拉图〈智者〉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7]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8](古希腊)亚理斯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9]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8卷)·论古典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0](受教于)张汉良.亚里士多德的“摹拟”创作论与诗辩[A].刘强编.原诗(第1辑)[C].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1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Title:Tragedy as Mimesis,Technique and Knowledge:Theory of Tragedy at the Initial Point ofWestern Apologia Poetica
Author:Tang Ke
Aristotle’s Poetics is the first systematic work to defend “poetry” in the western history of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art,it is also the originator of the western theories of poetics.Aristotle chooses tragedy as the representative for art,rationalizing,systematizing and philosophizing it to justify art.This essay attempts to clarify themechanism of Aristotle’s theory of tragedy,and to investigate the forma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poetical concepts of“mimesis” and “art”.
tragedy;Poetics;mimesis;technique;knowledge
J80
A
0257-943X(2017)02-0043-08
[本文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8批面上资助一等资助(《话语符号学视域下的西方“诗辩”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2015M580343)、2015年度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资助(《话语符号学视域下的西方“诗辩”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15CG31)。]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