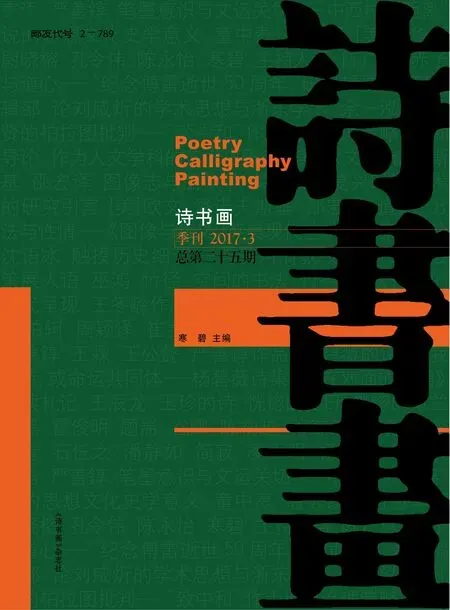杨碧薇的诗
杨碧薇的诗
坐在对面的爱情
密林甩着尾巴上的泥浆,金钱豹
从猎枪下跃起
发光的流弹朝夜空喷射
一米外,海啸已经喑哑很久了
我所有的器官
还在你的馀澜中慷慨
连同我,虚度的部分
悲情城市
明月清风作伴,我们推杯换盏。忘返于
伟人、英雄、得势的跳梁小丑
各自拥立的庙宇。百兽,
钢筋丛林里起舞,赞颂转基因的生活
幸福的无神论。
周公砍倒菩提树,
焚香,给活着的梦做千年道场。
酒肉穿肠,每个人都受了伤,
一清二白,约等于不明不白。
一愣,箸间翻动的鱼肉,
已随浓汤残骨隐遁。
绿洲上的楼兰,早比我适应,在饥渴与
饱足间,被笙歌搂住
日益虚胖的腰。它努力生长自己
机器的一面。出产鬼魅、佳丽、谎言和表演。
轮椅上的圣人,他们胯下
永不断流的排泄物,新浪娱乐头条,共创今日
最发达的景观。
不必举刀,
我们已臣服于食色之身。不去回望
时光深处啊,那单薄的爱,噙住
最后的乐观,
在枪口下杀身成仁。
这一切与欢乐共存。此刻,法华寺灯影圆柔,
我拖行滞留的影子。
一双内忧外患的鞋,
停在水洼肆虐的十字路口,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红,或者黑
每个夜晚,那
该死的,抽去我的魂,
留一座倦怠的
美艳之躯,供养
拼命想拱出皮囊的白骨。
在漂移的床上,我
一口口吸着黑暗。
飓风里,海潮颠沛流离,
没有指南针,也没有灯。
深刻的空,把它浸血的獠牙
磨到最犀利,
要准备张牙咬了!
覆巢照亮宇宙,完卵还在舞台上
表演喜剧。
昏昏欲睡的观众们,谁也不会鼓掌,
但谁也不会反对。
那该死的,它柔软并且动听,
紧紧缠着我的脖子,
吻我的耳垂。
睁着眼,就以为看得见么?
我在纸上写下的,
只是:
空白,空白,空白。
阳光铺满窗前
我又闻到了那只鱼跃出深海
扎进云层,翻搅起的蓝色海藻味
在极速摇晃的频率中,射线
滑翔于甜腥与流离的句意
无论怎样,三月是如约到来了
树林里那间堆满灰尘的屋子,该清洗清洗了
一个人,在黄昏的掌上行路
春风浩荡,眼目空阔
意外的温暖随风浮沉
有些被拈走,有些被浪费
海上灯
众生之声渐远渐灭
小旋风,轻卷林间绿叶
月色如柠檬汁,挂微笑于苍穹
潮水环绕灯罩
我静坐海中央
爱我的人,活着的,死了的
都揣着糖果,回到我身旁
风也来了,吹起一场欢宴
但我竟想离开
在宇宙中悬空行走,走到尽头
推开一扇门
灯光与摇篮,从门缝里向我伸出手
我一生的绝望缀满狂喜
妓
我的前男友穷得丁当响
只好租房住在城中村
搬来前他购置了锅碗瓢盆
半旧的一套画具,舍不得送人
我乘绿皮火车来看他
硬座车厢的十五岁民工
小心又专注地盯着我的胸
房东是对古稀伉俪
太太癌症晚期,不愿住院
每天和老伴楼下晒太阳
他们发呆,猫和狗就打盹
卫生间每层楼只有一个
三楼四楼紧闭着门
我尿急了,往二楼奔
撞见一位女人
她三十五六岁
颈上的香浓过了敌敌畏
长满雀斑的脸,涂着墙上涂的粉
打呵欠只见纹路纵深的大红唇
后来知道了
这个四川口音的女人
寓居此地已九个春秋
每晚带回不同的男人
晚间新闻一闭嘴,她和她的姐妹
准时站在小巷口拉客
她总是穿着一双
腊肠般灰头土脸的旧红色马靴
紧绷的裙子,绷出大腿的肥肉
裹不出挺翘的臀
而我习惯了趴在窗台上
俯视
她们站街的情形
一天晚上,雨愈发淋漓
路灯下的飞蚊早当了逃兵
“她们不打伞吗?”我喃喃自语
回过头,前男友正支着画架
专心画我穿肚兜的背影
她带回一个男人
他喝多了,用手揪她的头发
她成了倒栽的扫帚,被风翻卷着连滚带走
从此我不再趴窗窥视
白天去公共浴室洗澡,在楼下遇到她
“妹妹,”她对我说,“最近贼很多,
出去一定要锁好门。”
前男友,依旧在画我的裸体
常常打击我的小说比我的人还幼稚
除了说我没有文学天分,他还补充:
“下笔前,你应该读一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
可是我不想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的骨头好轻
我用香皂代替了沐浴液,买最便宜的惠好卫生巾
“我们去买烤鸭吧,”
我夺下他的画笔,“我三个礼拜没吃肉了。”
买回烤鸭,她正坐在走廊上吃泡面
她不知道对马尔克斯来说,走廊是阿玛兰塔唯一的空间
她只知道一袋康师傅多少钱
她还说:“你的烤鸭买贵了,
最便宜那家,要一直走,
把这条街走通,到尽头。”
因为没钱,我只能三个礼拜或是更长时间
才能吃一顿烤鸭
那时我二十岁,毫无性欲
夜半醒来,只想吃肉
前男友的画,一幅又一幅堆在房里
像一只只寻找太阳的眼睛
有一天我说:“朋友给我介绍了个工作,
内衣模特,我拒绝了……”
话没说完,他的手掌已经蜷起,只剩食指还直着
他指着门对我吼:“你给我丢脸,滚!你滚!”
我们时常吵架,打碎过碗、碟、镜子、水杯
房东的猫和狗也斗得不消停
楼上住的超市收银员,一回家就开大音响放刀郎
只有二楼的她,除了在巷口例行招摇
都安静得像是死掉了
她必须安静
她对谁说话都客气
但对谁都面无表情
她只对捕猎她的男人们笑
笑得放荡又谨慎
笑得像她的黑色网眼丝袜
自诞生时,就千疮百孔,再也没有多馀的破洞
这个城中村,诞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年纪比我小,却已孕育出脏兮兮的网吧、
两元店、菜市场、露天小吃摊……
破旧的公共电话亭是固定的摆设
捏紧双手狂奔的肯定是小偷
每回我穿梭在热闹的人群中
就想起她的声音:
“大哥,过来耍哈子嘛!”
她站在巷口,如一头挂牌自销的白羊
而房东夫妇,连抗癌药的价格也不关注了
面对来来往往的人
他们只微笑,不评论
我的小说又被退了稿
我蹲在角落里
左一刀,右一刀,狠命削着土豆皮
“天越来越冷了,你应该加件外衣”,
前男友说,“如果没有,你穿我的也行。”
我开始发火,我们打架
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
忘了谁狠狠扇着谁,左一掌,右一掌
“够了!”我捂着脸叫,“我的眼睛好疼!”
他松开手,血从我左眼流出来
同时流下的,还有泪
我,是穷疯了的孤儿
这个时刻,终于找到了哭泣的理由
他来不及细看,拉着我
就往城中村的小诊所跑
“对不起,如果你的眼睛瞎了,
我把我的挖出来给你。
可是你不要哭,你哭,我的心就疼。”
诊所的老太婆,慢悠悠地扶正她的眼镜
慢悠悠地,拾起桌上的注射器
为我打了破伤风的针
刚要离开诊所,里间的手术室
就走出面色苍白的她
她捂着肚子
我捂着眼睛
相视,我们苦笑,默默无言
彼此的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意义
这一晚,没见她在巷口拉客
窗外只剩下,擦过刀尖的风声
前男友为我洗脚
“吵架时,我真想杀了你。
可现在我发誓,以后一定要娶你”,他的泪坠入热水里
“我也一样,”我说,“可是狼外婆用的注射器
不是一次性,我好怕会得艾滋病。”
“如果真那样,我们就一起去死。”他保证
我累了:“别想那么多,你去画画吧。”
他把我的脚捂进毛巾:“昨天,你去买菜时,
我把画具卖了,交了水电费。”
不久后她又开始招客
还是那身行头,只不过加了件PU皮外衣
每次遇见,我们就微微笑
话却更少,话很多馀
“你的眼睛好啦?”有一天她突然问
“是的,”我答。可我知道
心里的有些伤痕,左一道,右一道
再也好不了了
前男友开始看求职书
用红笔,在成功励志学上圈圈点点
他不再打击我写不好小说
而是让我教他写公文
窗外的梧桐树,投映在墙上的影子
一天天瘦下去
我想,我应该离去了
再见,2008年的昆明
我想去同她告别,她的房门紧闭
门旧了,门上,几道红色漆纹在撕裂
我想起,已数日不见她的踪影
我吸了吸鼻子,把可能流出的泪
倒绷回眼眶里
我早已忘了
房东的猫狗是什么毛色
也忘了她的样子
只记得她染过的黄头发
那一蓬来不及被收割的稻草
散落在灰色的荒野上
写下这些话时,我涂着香奈儿的口红
抹着范思哲的香水
有很多次,我尝试用各种偏执的自宠
补偿自己的二十岁
不是因亏欠或遗憾
而是怕那种疼痛永不消失
更怕那种疼痛,下一秒就消失
最后一次见到前男友
他已当上了公务员
他的眼肿得像水蜜桃,不明白我为何要分手
当时我和他一样迷茫
多年后我想
可能是因为
那年的枫叶红了,他忘了带我去看
可能也因为
他再也不是艺术家
童年往事 组诗
1.药店
那年暑假,槐树叶绿得不要命
每天我都去霜子家药店和她玩耍
每天,总有青年们来买注射器
话不多,步履匆匆
除了注射器,他们的目光
不触碰其他东西
有时流浪儿替他们来买
最小的七岁,黑瘦的手臂上,针眼斑斑
霜子说他没有名字。她在抽屉旁找补零钱时
我别过头,专注于
三档式落地风扇,卷起的满屋子中药香
恍惚、迷人又清凉
一天清晨,在去药店的路上
半条街的人围堵在巷口
一位满头霜花的母亲跪在中央
泪和鼻涕糊了满脸
一双手,已在地上捶得血肉模糊
像两团捣得稀烂的柿子,滴着窒息的浆汁
别人拉她起来,她却挣扎着向下
仿佛要寻找疗伤的地缝
用额头将地表撞裂
咚……我的脚底震一下
咚咚……连震两下
咚咚咚……漫长的回声,盖过号啕和警笛
透过人群,我看见
她的儿子,昨天还出没于药店的瘾君子
尸体与流浪狗无异,僵硬的身姿
出卖着母亲最后的尊严
那天药店的风扇坏了,还好风吹起口哨预习秋天
门外的槐树叶沙沙作响
我和霜子下五子棋
我说:“那个眼睛像牛一样的人死了。”
“我早就晓得,”她拈出个双三,“一看他就活不长的。”
霜子比我大一个月,从小帮父母看药店
能分辨出瘾君子的样貌,预测其寿命
下午四点,我们用彩色塑料管编五角星
雷阵雨刚过,来了一副新面孔
“买一支注射器,”他说
……
霜子在她儿子满月时发来微信
城区改造,老槐树被砍了
她辛苦了半辈子的父母终于肯转让出药店
闲居颐养天年
嗯,陈氏安宁药店,满屋子的中药
可治郁、祛邪、安心、宁神,不可招魂
现在它们的香味都消散了
但我的记忆还在
它变成了一支一针见血的注射器
稍不留神想起九岁那年的夏天
它就又稳、又狠地扎向我
扎向我!无声无息,但它从未失手过
2.三街的录像带
像写错的一笔,出旧城门
笔锋陡然一转。三街,城市的尾巴
旧马路上,上帝失手抖落尘烟,覆盖斜阳青瓦
夏日黄昏。群鸦、红蜻蜓、川A货车
老右派半醉半醒的二胡声
生禽市场阴魂不散的鸡屎气
共赴油锅,为七点整的新闻调味
敬老院的瞎眼婆婆,拄着拐杖跑到街中央
骂天、骂地,骂1968年揭发她的前夫
和那个腰细屁股大的狐狸精
天黑了,她没能骂走
堵了一生的黑
而“小香港”次第亮起的霓虹灯管
越来越粉嫩
那一年,三街的青年们
负责整个九十年代的无所事事
青龙白虎古惑仔、台球群架镀金链……
罗胖子的旧书摊,不再出租古龙金庸
专提供港台录像带
从三街到皇后大道东
青年们比父辈懂得更多,却在一样的棋局里
流离失所
整个七月,耶稣忘记垂帘听政
时而艳阳高照
时而暴雨倾城
不管天气怎样,我都撑上
米老鼠图案的伞,从南到北,横穿三街的胸腔
跑过脸如面具的乞丐、挥刀乱砍的疯子
吓唬小孩的智障男……
直到进了外婆家的楼道
才放慢脚步
在提前降临的星空下
深呼吸
外婆午睡时,我就
趴在阳台上发呆
对街的楼房,窗户大敞
一男一女在看录像带
男的,头发自然卷,有一双凹陷的大眼睛
是三街第一批吸毒仔中,最像诗人的一位
女的二十出头,皮肤如小麦
穿上金色吊带衫时,样子很美
听说她陪很多男人睡觉,挣钱给他花
陌生的海浪声,自云层跌泻
电视上,陌生的男女用陌生的粤语
试探陌生的世界
忽然,男孩捧过女孩的头
他们拥吻,闭上眼睛
贴紧的身体之间,一枚隐形的果冻在轻颤
角落里,耶稣扬手,将折翼的天使
从袖口吹出
远处青山悠悠,一排排松树敲响竹琴
山外还是山,只有风到过那里
楼下,流浪儿光着脚板
走过石板路的履痕苍苍
我碗里的木瓜凉粉,碎如玛瑙,在烈日下惝恍
那对孤独的情侣还在亲吻
在四处漏出海绵的破沙发中,他们越陷越深
未知的录像带,辟开了整个世界最后的退路
雪花飞溅的屏幕,像一盏半坏的灯
忽明忽暗,从我的六岁,一直闪到现在
但那折翼的天使
还没有循着光斑飞回来
3.枪,或石头
妈妈,你至少得给我一把手枪。
我将和你一样,来不及被分娩痛击,
就饱尝欲望与冷暖。
微温的血,终于穿上缎面礼裙,迎接
不可抗拒的。
失控的风雪,裹紧一个男人不要脸的坚硬;
不要命的白鸽,在飞升中坠落。
教室里的轮奸事件,再一次
把她的尖叫吊到银杏树上,
蓝巨星发起高烧,黑洞对症下药。
妈妈,我不想再看见,
课本里掉落的安全套、女厕里的弃婴。
我把童贞举过头顶,
它闭上眼睛,朝悬崖奔去。
妈妈,我的手在颤抖,
不只是因无形的扳机在震动。
金色的盾牌,早已将我们驱逐到
玫瑰与蛇的流放地。
在那里,皇后与丐女共用一对乳房,
裂壳的坚果,在海上流浪。
而这里,旋转木马脱离了轨道。
童年的玩伴做了雏妓,提着红灯笼,在光天化日,
为世界提供多馀的明亮。温驯的猎物,纷纷预支
长腿丝袜的美学。只有我还在害怕
山丘与春天,在我身体上生长。
妈妈,抱抱我、抱抱我吧!
赶快让我缩小、缩小,
回到你的子宫,在月朗霜白的秋夜,
回到胚胎回到受精卵回到无。
你没有枪,也没有石头,
但我必须爱你,
爱你灿烂的白发、你留不住的青春,爱你背上
永远也卸不下的十字架。
我又多么恨你。
为何你像退回地下的井水,任火烧大地,
却越来越忍耐,
越来越沉默。
4.活路
煤块,大口吞噬着
越烧越旺的火苗,用燃烧反证
正在毁灭的自身。
阿金奶奶捂着胸口,每咳嗽一下,
黑暗的弧度,就扩大一圈:
“不读了,要找点活路。”
阿金像个失灵的皮影,
与面前的菜汤,一起在火舌里屈伸。
水沸,翻滚,
白菜叶变色变软,是冬天腐朽的躯体里,
煮烂的心脏。
从开学起,阿金那件墨绿色的破毛衣,
就没有脱下过;他的表情也不变,
沉默、低矮,需要缝补。
“阿金的命没你们好啊!
他妈早就跑啦!爹在坐牢。
我老了,累不动了。读书,没钱……”
“我不读了!要找活路。”阿金终于开口。
手里的锅铲,在锅壁上“嗞……”地刮过。
红光、蓝光、白光、紫光,搏击着,
蓬蓬作响。
活路,在我们方言里,是指“工作”。
与“活”有关,便意味着与死相抗。
十二岁的阿金,站在世界尽头,
为“口舌”之需,
提前领略“活”字的三点水,
第一点是血,第二点是汗,第三点是泪。
放寒假那天,阿金的座位,还在教室里空着,
空出一条活路。
活路,就是绝路,
没有反面,不准回头。
那年,阿金家的旧瓦房,是二街与三街过渡处
最醒目的一颗钉子。在一排排根基不稳的新楼房中,
它将尖锐的部分,狠狠扎进大地。
但十多年后,
当我带着不变的乡音,重回陌生的故乡时,
它也被连根拔起,和阿金一样
消失了。
5.笑脸
灯芯绒窗帘,海棠红,如一块生锈的铁片
把风挡在外面
头七后的第一个晴天
我站在她家客厅中央
初春的湿气蒸腾着,涌过地表
半旧的贝壳风铃,影子撞在天花板上
大年初六人们推开房门时,她已经死了
赤裸的身体上麻绳纠缠,线条与线条之间
肉,如破碎的几何块
被切割,突出
像个煮烂的粽子,到处溢出豆沙馅
双脚,捆紧;双手反绑在身后
指缝里发黑变紫的色块,是血液凝成的干壳
一团灰扑扑的布条,堵在她紫绀色的嘴中
她的眼睛,睁着
涣散的瞳孔,追着你不放
还有那看不见的
千万双眼睛,覆盖她每一个部位
像一个个尖钩,把你的眼睛,钩着
几天前,有人看见她去药店买糖浆
说快开学了,得把自己的百日咳尽快治好
几天后,她的死,以及她丈夫婚外恋的谣言
成为正月里
人们饭桌上最时髦的下酒菜
听说这半年来,她常常抱着年幼的儿子
在校园里闲坐、发呆
死活不愿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没有法医鉴定结果
很快她就被丈夫拖去火化了
葬礼很体面,全校师生为她送行
我们戴着白花,队伍挤满了三条街
春天来得真快,更快的是夏天
她的丈夫又结了婚,她住过的房子
被转卖给四川生意人
人们的下酒菜,变成更新鲜的时蔬
《泰坦尼克号》、长江洪灾、世界杯足球赛、银河之星大擂台……
讲台边,曾摆放她钢琴的地方,被改造成图书角
儿童节的合唱队,不再有她打拍子
长卷发随着节奏,一波朝左,一波滑向右
新来的音乐老师不会唱歌
他常带男生们打球
教他们三步上篮,如何把柔韧的圆
玩弄于鼓掌之间
我们迅速长大。白带初潮喉结变粗学会写情书
还珠格格windows98谢谢你的爱1999
千禧年,小升初。毕业照上
所有老师站在第一排
人太多,她的位置,也没被空出来
但我常常想起她死之前的那个夏天
一个傍晚,我路过她娘家
她站在院子里
身后,一串串蓝色的牵牛花,如群星闪耀
风,灵巧地钻过她的麻花辫
她的双腿微微张开,大喇叭裤有顺畅的垂坠感
嘴唇,有着一贯的
浅浅的苍白,向上扬着,对我笑着
多年后,那张笑脸突然挂在北京的黑夜里
矜持的初秋,为之轻轻一抖
一个死人,她在十月的夜风里对我笑着
一个死人的笑脸,从路灯下冒出来
从水里浸出来
贴着窗棂飘过来
钻进北上的动车追过来
无法伸冤,也喊不了疼,只是笑着
我感觉到我的乳房
被戴了一整天的胸罩
勒得那样疼
两根看不见的金属条
将突如其来的凉意收束、钳紧,推入我的胸腔
而她的笑脸,贴满我周围的空气
钢琴声,踩着童年的黑白键
纷沓响起
6.疯女人
疯女人又开始裸奔了!
人们奔走相告
刚搓好的汤圆,不煮了!
刚拆封的鞭炮,不放了!
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套上棉鞋
赶紧跑出门去看热闹!
一丝不挂的疯女人,像个膨胀的鸭梨
荡着丰富的果汁,跑着内心黑白相搏的马拉松
从北门街冲到南门街,所向披靡
此刻,她是高高在上的长跑手
心生爱慕的男粉丝们,壮着胆子跟风
捏她的屁股,摸她的奶子,挠她小腹下
幽黑的森林
她只是嘻嘻笑着,抓一把雪塞进口中
再抓一把雪,朝他们甩去
人们叫好、鼓掌
远处,第一挂爆竹声层叠涌来,雪霁天晴朗
在小城
春节=大鱼大肉+喝酒划拳+走亲访友+麻将+上坟+疯女人
疯女人不疯,年味就会寡淡
疯女人受了别人家团团圆圆山珍海味的刺激,必然疯
在欢乐的日子里,忙了一年的人们
需要一道裸奔的风景
元宵后,有关部门迅速行动
全力、坚决、果敢,抓住无法无天的疯女人
扭青她两条胳膊,扯下她一缕头发
扔她到精神病院去
她年幼的儿子,戴着破了三个洞的毛线帽子
跟在有关部门屁股后面追
一边哭,一边伸出舌头
将流到唇边的鼻涕舔几舔
“妈妈!妈妈!”他扯破了嗓子叫喊,没人理会他
当新鲜的粽叶被成捆买走时
疯女人也坐回到菜市场
她的衣服,干干净净的
脸,干干净净的
她用一个扎了针孔的大号矿泉水瓶
给蔬菜们冲冲洗洗、补充水分
小葱,干干净净的
蒜叶,干干净净的
母亲牵着我的手,走到她的摊位前
“大姐,买我的菜!好吃,不贵,
买我的菜!”
她拙拙笑着,接稳母亲递过的钱
又多拈了两根小葱,塞进母亲的菜篮
“大姐,羡慕你们啊!
娃儿还小,我想死,可死不了。
得找点事做,又做不成别的,命贱,只能卖菜!”
风吹起她一缕刘海
她突然不说话了,两团乌云,擦着睫毛飘过
关于疯女人,我最后的记忆是
那年冬天,她又发了疯,在街上裸奔数日
跑到政府大楼对面,抓刘记点心铺的小笼包吃
正在对顾客笑脸相迎的刘老板,转过身来
一巴掌扇掉了
她刚放到嘴边的包子
她嘻嘻笑着,又伸出手
朝竹笼边上够
他更怒了,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掰得一个趔趄
她还没站稳,拳头
铁锤一样落到她头上,梆梆梆
他又伸出尖头皮鞋,朝她没命地踢
她被踢得蹲下去,捂着肚子嗷嗷叫唤
他不打算停,仿佛要撒出自己受的半辈子的气
“疯婆娘,老子看你还敢不敢拿,敢不敢拿!”
围观的人们默不作声,空气紧张得
如一条一撕就要豁出血的伤口
“呜——”她像条被抽去骨架的母狗
软成一团。眼睛里发红的世界,稀里哗啦
颠倒的黑洞,稀里哗啦
“别打了!她一个疯子,能懂啥子道理?”
满头银丝的老太太,推开人群挤进来
弯身护住她,将一件半旧外衣
披在她耷拉的狗皮上
刘老板骂一声娘,拳头悬空,胡子还在发抖
人们摇头的摇头,咂舌的咂舌,渐渐散开了
她还蜷伏在雪地上,两个眼圈乌青发紫
细血,从嘴角渗出,络绎不绝
“呜……”又呻吟一声
在上帝的轻叹中,婴孩,从水中被托起
阳光熠耀,碎玻璃割伤瞳孔
镜子挂上了霜,镜中万象无动于衷
多年后,我打听起故乡的疯女人,所获信息如下:
疯女人,姓段,名不详
自幼癫狂,由寡母抚养大
曾有短暂婚史,夫蜀中人士,亦癫狂
于某年发狂出走,至今未归
育一子,亦生而狂,始龀,未进学
混迹于市井,偷盗成性,为人所恶
悠悠廿馀哉,疯女人寡母亡,其子弱冠,母子相依为命
两疯同处一室,因神昏志昧
竟行云雨,暗结珠胎
消息一漏,满城风雨
幸有关部门相援,扭送疯女人至医院
……听张家保姆说
做人流那天,疯女人很乖,只是问:
说好的,今晚,给我吃碗面——加番茄鸡蛋的行不?
此后,信息中断
在北国的初冬,连夜里,我停笔数次
感到自己就要被
即将涌来的文字,大刀挥砍
但我仍然安在,肉身与光明交错
战栗或平静着,在此时,在此地
来去如风的,只是她——
一个疯女人,站在时光的路口
穿着那身干干净净的麻布衣服
她来不及回头笑一笑
便被迎面卷来的暴风雪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