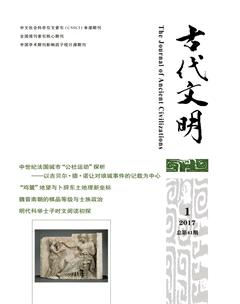魏晋南朝的棋品等级与士族政治
杨鑫
提 要:棋品制的出现与汉魏以降围棋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魏晋名士将围棋作为展现自身独特的文化风貌的手段,因而围棋得以作为魏晋风度外化的物质载体而流行。作为一种等级序列,棋品在外在形式上模仿了王朝实行的九品官品制度。从现有材料来看,棋品制产生的时间应该是在东晋,认为棋品形成于曹魏的观点并无充分的依据。东晋南朝时期,棋品的评定主体经历了“个人—官方机构—皇帝”的变迁,这与人物品评的演进趋势相一致。南朝时期棋品等文化等级评定的盛行体现了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后力图在文化领域建立独立于政治秩序的文化等级秩序的努力。而棋品评定主体的变化则显示皇权已经将文化这一士族传统的优势领域纳入到了自己的控制之下,即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了。
关键词:棋品;魏晋南朝;士族;皇权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1.010
魏晋南朝的棋品制不仅是近代以来的围棋段位制的滥觞,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的围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以往学者已经有所讨论,对魏晋南朝时期棋品的产生时间及其出现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考察。1在此,笔者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以往讨论尚不充分的问题加以若干补充,以期能够增进对棋品本身及其与当时政治、文化的联系的认识。
一、棋品制产生的背景
棋品制度之所以在魏晋南朝时期出现并得到发展,这与围棋自身的发展及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首先是围棋自身的发展。关于这一时期围棋发展繁荣的原因及其表现,以往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笔者在此想要强调的是围棋技术的发展。由于围棋棋局自身存在形态的关系,当时围棋技术的具体情况今天已不得而知。不过尽管如此,仍然可以从文献记载中看出当时围棋技术方面的一些情况。
东汉人桓谭在其《新论》一书中将棋手划分为高低不同的三个层次:
及为之上者,张置疏远,多得道而为胜;中者务相绝遮,以争便求利;下者守边地,趍作罫,白生于小地。1
在此,桓谭划分棋手等级的依据是其下棋的风格。事实上,不同的棋风之间很难说有高下之别。认为一种棋风高于另一种棋风,这更多的只能说是作者的个人喜好。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人对围棋的风格流派已经有所认识并作出了一定的区分。按照围棋技术的发展规律,魏晋南朝时期的围棋技术理论必然会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文献中,的确能够看到一些相关的迹象。《隋书·经籍志》中即著录了《棋势》、《棋图势》等多种与围棋相关的书籍,而其所引的阮孝绪《七录》中亦载有《围棋势》、《高棋图》等数种文献。2这些书籍现在均已散佚,其内容不得而知。不过从古代的围棋术语来看,“势”、“图”等一般用来指局部(主要是角部)的特殊棋形及与之相关的固定下法,如“金柜势”、“大角图”等。笔者推测,《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这些围棋文献名称中的“势”、“图”很可能也是这个意思。虽然对其具体的棋形与变化尚不清楚,不过基本可以断定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固定的局部变化,即出现了较为简单的定式。这些早期的定式的出现无疑是当时的棋手在长期的对局实践中进行总结的结果。这显示了当时的围棋技术的发展。
其次是魏晋风流对于围棋发展的促进。关于魏晋风流,袁行霈先生有这样的概括:“所谓‘魏晋风流,是在魏晋这个特定的时期形成的人物审美的范畴,它伴随着魏晋玄学而兴起,与玄学所倡导的玄远精神相表里,是精神上臻于玄远之境的士人的气质的外现。简言之,就是魏晋时期士人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也可以说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现。”3在这里,袁先生从玄学的角度对魏晋风流进行了解释,认为它实际上是士人内在的玄学精神的外化。这一认识路径是很有意义的。这种玄学精神的外化固然可以通过士人日常的言谈举止来表现,但很多时候也是出现在某些特定的行为模式之中的,如放浪形骸、处变不惊、不亲世务等就可以看作是较为固定化的名士行为模式。而围棋恰恰也成为了展现士人内在的玄学精神的一个重要工具。在《世说新语》等文献中常可以看到士人通过围棋来表现其不同于常人的特殊精神、气度的事例。如《世说新语·雅量》中的一段著名记载: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4
上段材料常被作为解释魏晋风度的实例来使用。在此,谢安通过下围棋表现了其宠辱不惊、不为外物所动的独特气度。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如阮籍听到母丧的消息时下棋不辍、王坦之在居丧期间与来客下棋等,不再备举。从这类事例中可以看出,围棋在魏晋士人展现其内在的玄学精神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工具意义。也正是因此,围棋与服药、饮酒等行为一样成为了当时的士人所热衷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南朝时期,魏晋风流一直是作为一种历史上的人格典范而存在的。时人将“正始遗风”、“竹林遗风”等词语作为对士人的较高评价就说明了这一点。因而,围棋作为魏晋风流的一个象征在南朝继续延续了其在士人群体中的流行地位。
关于魏晋南朝时期门阀士族热衷于围棋的现象,文献中多有记载,以往学者也已有所揭示。笔者想要补充的是,尽管这一时期的高门士族对围棋活动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但他们的实际围棋水平恐怕并不甚高。《南齐书》记江斅事时云:“斅好文辞,围棋第五品,为朝贵中最。”1从整个围棋爱好者群体来看,江斅的棋力能够居于九品中的第五品已属不易,可以算是当时棋坛上的高手了。不过五品毕竟只是九品棋品的中间等级而已,江斅的五品棋品就已经是朝廷重臣中的最高等级,由此也可以想见当时以高门士族为主体的朝臣的围棋水平普遍并不高。此外,在文献中所能见到的一些位居一品的棋手,如江彪等也多非当时的高门士族。2从这些迹象来看,魏晋南朝时期的高门士族的士人尽管对围棋有很大的热情,但其水平却未必在当时的棋坛上居于领先地位。不过文献中也记录了很多位居高品的门阀士族,对此又应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在这里需要考虑正史等文献自身的书写方面的情况。历史文献作为一种对史实的记录本质上是经过了历史书写者主观的选择的。一部具体的历史文献不可能将当时的所有人物均纳入记载的范围,而是只能从中选择在政治及文化活动、社会地位等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特别是政治地位较高者作为写作的对象。魏晋南朝的高门士族由于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就有更多的展现其政治、文化等方面才能的机会,更可能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就,这样他们进入历史书写的几率当然要比普通人大得多。因而正史等文献中有大量的高门士族围棋活动的记载主要是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社会地位,而并非是他们在围棋水平上居于同时代的领先地位。江斅的五品棋品已经是朝廷重臣中的最高等级了,那么必然有很多水平更高的人是在朝贵的范围之外的。他们之所以大多没有被记载下来也主要是由于其社会地位较低且在政治活动中没有较为突出的事迹。
这就涉及到了围棋在魏晋南朝的高门士族的生活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对待围棋的态度的问题了。如前所述,魏晋南朝时期围棋的发展与魏晋风流有密切的关系。而魏晋风流本质上则是士人将其内在的玄学精神转化为外在的行为模式。围棋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工具的作用。士人通过围棋活动而展现其在玄学精神影响下的与众不同的精神面貌与行为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门士族之所以会对围棋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围棋是他们介入魏晋风流、进入名士行列、展现个人人格魅力的一个重要媒介。他们主要是通过参与围棋活动来表现自己的风度气质,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则相对不那么重要了。因而可以看到,这些士族门阀虽然大多对围棋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但普遍水平却不甚高。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热衷于围棋的主要是北来的侨姓士族,如王导、谢安、羊玄保、褚胤、江斅、王抗、谢沦、柳恽等。而吴姓高门士族则似乎对围棋兴趣不大,见诸文献的南方士人中的围棋高手只有虞謇等极个别的例子,其他如会稽夏赤松等也并非出自吴姓世家大族。事实上,吴姓高门士族不仅自己对围棋缺乏兴趣,而且他们对时人热衷围棋的现象还有所批评。如《南齐书·虞愿传》云:
(宋明)帝好围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每饶惜之,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帝终不觉,以为信然,好之愈笃。(虞)愿又曰:“尧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3
传说尧的儿子丹朱不肖,尧发明了围棋来教育他。4虞愿即以此为据,认为围棋本来只是尧用来教育其愚钝不肖的儿子的游戏而已,皇帝不应该对此有所喜好。而颜之推对于时人过于沉迷围棋的现象也有所批评:“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躭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1在颜之推看来,围棋虽然是“雅戏”,但是沉迷其中则会影响人的精力,因而要有所节制。论者认为这“说出了当时儒学之士对围棋活动的基本看法”,2其说是。事实上,对于前述虞愿的意见,也可以这样来看待。唐长孺先生曾指出,东晋以后江南土著与渡江侨旧在学风上有所区别,侨人重玄学而南士重儒学。3而
会稽虞氏又是传统的吴姓文化士族,因而他们基本也是秉持儒学的价值立场的。基于儒学的价值取向,吴姓士族对于玄学及作为其外化的表现的名士风度是持有批判态度的。如与虞愿同族的虞预就“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4这样来看,前述虞愿对围棋的看法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可见,在刘宋王朝的后期,亦即侨姓士族南渡百余年后,传统的吴姓士族对于魏晋风流、名士风度依然是抱有一种否定的态度的。5
再次是人物品评与中正品、官品制度的影响。关于人物品评与九品中正制的中正品对棋品产生的促进作用,以往学者的研究已有所揭示。笔者这里要补充的是官品的影响。曹魏在创立九品中正制的同时,也创制了对其后的政治制度影响极大的九品官品制度。较早时期学者大多认为九品官品的产生是受九品中正制影响的。近年来阎步克先生则指出官品的制度渊源主要是朝班制度,6此后周文俊先生的研究也强化了这一判断。7按照阎、周二位先生的意见,则官品与中正品是来源不同的两套位阶体系。而如果从等级序列的外在形式来看,则相比中正品,官品与棋品更为相近。我们知道,魏晋南朝时期的中正品虽然在名义上分为九等,但在其实际运作中,是以灼然二品为最高等级的,一品只是虚设的品级,并无人被评定为这一等级。方北辰先生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认为由于九品中正制系模仿《汉书》中的《古今人表》一篇而来,而在《古今人表》中被列入第一品的只有自三皇五帝以降至周公、孔子的诸圣人。这些圣人是后人不能比拟的,因而中正品的第一品也就虚悬而不实际授人了。8阎步克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测九品中正制在实际运作中也没有七、八、九这三个品级。9可见,中正品虽然在理论上分为九个等级,但在实际运作中使用的很可能只有二至五品这五个等级而已。而棋品与官品则是九个等级均被用于实践的,并无虚设的等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棋品与官品在等级的形式上更为接近。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棋品与中正品之间的关联。刘宋时期“围棋州邑”的设置就充分的证明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笔者这里只是想补充说明一下,除了中正品之外,创始于曹魏的九品官品对棋品制度的形成很可能也有重要的影响。
可以说,正是上述的这些因素为魏晋南朝时期棋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乃至是必然性的条件。
二、棋品创置的时间
较早对棋品产生的时间进行考察的是明人王世贞,他认为:“弈之有品,启自刘宋,盛于泰始。”1不过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如下文所论,在现有材料中,在刘宋之前就已可以看到有关棋品的较为明确的记载。王氏显然是将棋品产生的时间推后了。近年来,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主要有棋品产生于曹魏与产生于东晋两种观点。2征诸史籍,后者更为合理,以下加以说明。
主张棋品产生于曹魏者,其依据主要是陶珽编次的百二十卷本《说郛》中所引的曹魏邯郸淳所著《艺经》中的这段文字:
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不可胜计,未能入格,今不复云。3
在此,作者提出了“围棋之品”的概念,并将之划分为名称不同的九个等级。这样来看,似乎曹魏时期就已经有了棋品制度。但实则不然。
首先,这里所列的棋品中九品的名称似乎不尽符合当时人的观念。大致来说,这里用以指称棋品等级的入神等词语在中古的语境下均具有一定的哲学内涵。张如安、郭永勤等学者对其中的名称进行了考察,认为其符合曹魏时期的语言习惯,时人以之来指称围棋品级是完全可能的。4应该说,一些棋品等级的名称确实是比较符合曹魏的思想观念的,如入神、具体等词即是。但另一些词语的情况则不然。如作为第九品名称的守拙一词,这一观念大致是从晋宋之际开始成为士人较为推崇的一种流行价值取向的。这在陶渊明等人的诗文中有明显的体现,5
而在西晋之前则很少见到含义相近的词语的使用。再如作为第二品名称的坐照一词。此词系佛教用语,从词义来看,它可能是由《庄子》中的坐忘一词衍生而来。不过在现有文献中,坐照一词是从唐代开始才见诸文献,唐之前则似未见到相关的用例。6生活于曹魏时期的邯郸淳显然是不太可能用这些西晋之后才流行起来的词语来作为棋品等级的名称的。
其次,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说郛》中所引的这段材料情况比较复杂。邯郸淳的事迹主要见于《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卫二刘传》裴注所引的《魏略》中的记载。7虽然《魏略》的这段材料中并未述及邯郸淳著有《艺经》一书,但《文选》注文中却引用了邯郸淳的《艺经》,应该说他曾著有此书是没有问题的。8但《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等元代以前的目录文献对于《艺经》一书都没有著录。众所周知,《隋书·经籍志》是参考了梁代阮孝绪的《七略》而编写的。可见至少在阮孝绪编撰《七略》时,《艺经》一书就已经散佚了。9而《艺经》的这段佚文又是首见于陶宗仪的《说郛》一书。即在《艺经》一书散佚数百年之后突然出现了一段前所未见的佚文。这种此前未见引用且其书不见于前代目录著录,而后世又出现的文字很可能是后人的造伪。1虽然目前尚无确定的证据可以证明《说郛》所引用的这段《艺经》中的文字系出于后人的伪造,但从以上迹象来看毕竟是很可疑的。以这样的一条存疑的孤证来论证棋品产生于曹魏时期是比较危险的。2
此外,即使《说郛》所引不误,这条材料确实是出自邯郸淳的《艺经》,也不能凭此就认定曹魏时期已经有了棋品制度。围棋的等级划分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对棋手的分等,即某一棋手属于某一级别;其二是对棋力的分等,即将依高下划分出若干不同的围棋水平的等级。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从属于棋手个人的等级。前者如现代的段位制。棋手通过参加段位赛(或取得一定的比赛成绩)而被授予一定的段位,这个段位是用来标志其个人的围棋水平高下的。后者则是较为抽象的规定了若干围棋水平的等级,而并没有将具体的棋手纳入这一等级序列。如中国当代的段位制在设立之初规定职业段位分为九级,业余段位分为七级,职业段位中相差三段让一子,业余段位中相差一段让一子等。在不考虑相应的棋手的情况下(或者是这个制度刚刚被制定还没有向棋手授予段位的时候),这就只是一个关于围棋水平高下的一个抽象的分等体制。前引桓谭《新论》中“上者、中者、下者”的等级划分就属此类。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先有对棋力的分等,然后才有对棋手的分等。只有在围棋等级制的制度框架确立之后,棋手才会被授予相应的段位。这一过程在现代是连续的,二者之间的时间间隔很短。但是在并无前例可资依循的棋品创制时期二者的时间间隔却可能是比较长的。很可能是人们首先设置了标示棋力高下不同的等级并为之赋予特定的名称,而在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将当代的棋手纳入到这个等级序列之中。在明确了围棋等级制的这一特点后,再来看《说郛》中的引文就会发现,其中被标以“入神”等名称的九个等级在没有具体语境的情况下并不能确定是棋力的等级还是棋手的等级。如果仅就这一段文字来说,很可能是作者采用当时流行的名词为围棋水平划分的等第。这个等级序列似乎仅是对围棋水平进行的抽象的分等,而并没有将具体的棋手纳入其中。因而,这条材料并不足以证明在邯郸淳写作《艺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棋品制度。
综上,就目前的材料而言,笔者认为棋品制度产生于曹魏时期的观点还缺乏明确的证据。
主张棋品制产生于东晋者所依据的证据则是范汪的《棋品》一书。检诸文献,此书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中均有著录,3但不见于《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及其后的《宋史·艺文志》等目录学著述。是此书在唐代尚存,而至晚在南宋初期就已经散佚了。不过《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中却保存了此书的两条佚文。《世说新语·政事》“何骠骑作会稽”条中刘孝标注引范汪《棋品》云:“(虞)謇,字道直,仕至郡功曹。”1同书《方正》篇刘注又引《棋品》云:“(江)虨与王恬等棋第一品,(王)导第五品。”2高华平先生认为“从这两处残文来看,《棋品》正是既叙录‘棋手的生平籍贯,又明分品第,铨衡人物的。”3从前引的后一条《棋品》佚文来看,范汪在该书中已经明确的依棋力高下为棋手划分了等级,这与前述的《艺经》中可能是以棋力为对象的分等有着本质的不同。范汪在《晋书》卷七十五中有传,其人活动时期跨越两晋,且本传中并未提及其编撰《棋品》一事,故该书的具体成书年代尚难确定。不过从该书中著录了会稽虞氏的虞謇来看,则很可能是作于东晋时期的。虞氏虽然是江左较有地位的士族,但毕竟不是朱张顾陆一类的高门文化士族。而西晋时期北方士人对江左士人颇怀轻视的态度,4若是在南渡之前,范汪是不太可能将虞謇列入其书的。虽然在范汪之前可能就已经有人做过了类似的等级划分,但就现有的材料来说,暂时将东晋时期范汪的《棋品》一书作为棋品制的起源是比较稳妥的。
三、东晋南朝时期棋品评定方式的演变
由于史料的缺乏,关于魏晋南朝时期的棋品制度的具体制度架构及其运作方式,尚难以知其详情。这里仅就其评定方式的演变过程加以述论。
东晋的棋品除前述范汪的《棋品》一书外,《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袁遵的《棋后九品序》一卷。5袁遵在《晋书》中无传,其生平事迹不详。《魏书》卷九十七《岛夷桓玄传》、《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中均述及桓玄讨伐司马元显时杀吏部郎袁遵之事。6检诸魏晋南朝文献,袁遵之名仅此一见。如果写作《棋后九品序》的袁遵就是此人的话,那么他也是东晋后期的人了。东晋时期的文献虽然记录了王导、江虨等人的棋品等级,但其中却并没有关于棋品评定活动的记载,而且东晋诸帝也未见有喜好围棋者,因而这一时期的棋品等级很可能是由私人自行评定的,即范汪等人根据其个人的见解并参考他人的评论等因素而为当时的棋手划定等级并将之著录成书。
这样的一种棋品评定方式应该说在制度上并不完善。私人著述的形式决定了其等级判定的信息来源主要是著述者个人的目见耳闻,而个人的信息渠道总是较为有限的,难以获得同时期所有的围棋高手的信息。如有些棋手可能会由于家世、官位不显等原因而未被评定者所知。因而这样评定出的棋品其所涉及的棋手范围实际是比较有限的,只能说是对评定者的交往范围内的棋手进行等级划分。且这种个人进行的等级评定也缺乏客观的衡量标准,评定者个人未必有机会与其所划定等级的所有棋手当面对弈,一些棋手的棋力高下很可能是他听别人转述的,这就有了道听途说之嫌。即使是本人亲自对局的棋手,评定者自己也未必就能够对对方的棋力做出非常准确的判断,进而为之安排恰当的等级。此外,个人进行的等级评定也有可能会带有个人的情感色彩,如他对特定棋手的好恶等。
在宋代,棋品评定活动仍时有进行,如羊玄保、褚胤即获得了较高的棋品。1到了宋末,又出现了围棋中正制度。《南齐书·王谌传》云:
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王)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2
此事的具体时间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述,不过从宋明帝任用太子右率、中书郎(王谌时为中书郎)、尚书郎等朝官的任职者担任中正来看,当是在其即位之后。即宋明帝在其即位之后、仿照当时九品中正制的形式设置了围棋的中正制。从中正制这一制度形式来看,可以说其较东晋时期的私人棋品评定已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中正制下,围棋中正可以对本地区的棋手进行较为全面细致的察访并与之直接接触,通过对局等方式了解其围棋水平,从而避免了私人著述中存在的个人了解范围有限与道听途说的因素,而且这一制度化的组织形式也有助于避免个人情感对等级评定的影响。虽然《隋书·经籍志》中并未著录有关刘宋时期棋品等级的文献,不过“观中正之名,可知意在评定等级”,3很可能是当时的棋品评定情况并未著为篇章抑或虽然写定但至梁时已然散佚。需要注意的是,前引文中仅言以建安王刘休仁为围棋州都,而九品中正制是每州设置一州都(即州大中正)。这样来看,宋明帝的围棋中正制度所涉及的范围应该是只限于一个州,4而并未在全国普遍实行,其范围还是比较有限的。此外,关于这一制度的具体实施情况,文献中未见有相关记载。因而,围棋中正对棋手个人水平的认定是通过个人察访抑或组织区域内的比赛则不可确知。
在齐梁时期,棋品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即出现了由皇帝主持的棋品评定活动。《南齐书·萧惠基传》云:
永明中,敕(王)抗品棋,竟陵王子良使(萧)惠基掌其事。5
又《南史·柳元景传》云:
梁武帝好弈棋,使(柳)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6
又同书《陆慧晓传》云:
大同末,(陆)云公受梁武帝诏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并集。7
上引第一条材料中既称“敕”,则令王抗定棋品者当为齐武帝萧赜。而后两条材料则明言是梁武帝下令评定棋品。虽然这几次评定棋品的具体工作是由萧惠基、柳恽、陆云公等人负责的,但是做出这一决定的却是齐武帝和梁武帝。《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梁武帝所撰《围棋品》一卷,8
可见在棋品等级确定并成书后,也是由梁武帝以主持者的身份署名的。1即虽然皇帝未亲自参与其事,但棋品的评定却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较之东晋时期范汪等人的私相撰述,宋明帝以“任总百揆,亲寄甚隆,朝野四方,莫不辐辏”的建安王刘休仁担任围棋州邑的州都显示围棋的地位已有了很大的提升。2而齐梁时期皇帝亲自主持棋品评定活动则犹有过之了。如果说围棋中正评定的棋品较为接近中正品的话,那么代表最高政治权威的皇帝主持评定的棋品则带有官品的色彩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上引第二条材料中的“定棋谱”一语,即当时的棋品评定是以棋手对局的棋谱为依据的。这显示当时棋手的棋品等级是在考察了其个人的实际水平后做出的判定。虽然这一形式较之现代的段位赛仍有差距,但与此前的私人著述等方式相比无疑是有明显的进步的。
综上,东晋南朝棋品评定由私人评定变为官方设立围棋中正评定,又变为皇帝亲自主持评定,即棋品评定的主体经历了“私人—官方机构—皇帝”的演进轨迹。这显示了围棋在当时的社会地位的日益提升。
四、棋品的政治意义
就围棋的本质而言,它只是一个竞技型的游戏而已。不过如前所述,在魏晋南朝这一时期围棋之所以在士人中流行,主要是由于它是作为魏晋风流的外在表现而存在的。即它是士族群体所追求的名士行为规范的一项内容。而这种观念也赋予了围棋特殊的意义。
以往学界对魏晋南朝士族的研究较多的着眼于婚、宦两个方面,即从社会层面与政治层面对士族群体进行考察。这样的研究视角对于认识中古士族当然是很有必要的。不过从本质上来说,士族首先还是作为文化资源的占有者而存在的。众所周知,魏晋以降的中古士族主要是由东汉时期的大姓名士转变而来的。这些大姓、名士一方面通过家族势力控制着地方的察举、辟召等选举权,3另一方面也通过累世传经的方式垄断了学术等文化资源。唐长孺先生在讨论魏晋时期士族的形成时指出:“其士族地位决定于某一家族在魏晋时的政治地位,特别是魏晋蝉联的政治地位”,4其说甚是。不过文化因素在士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是需要注意的。日本学者上田早苗指出江左士族的“清官”观念源于东汉名士的理念与生活方式,5由此可以看出名士文化对于士族这一特殊阶层形成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这些士族在获取较高政治地位的同时,还是当时社会中文化资源的占有者。即如陈寅恪先生所论:“东汉以后学术文化……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依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有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门盛族常不可分离也。”6可见,在魏晋南朝时期,士族阶层是作为学术文化资源的垄断者而存在的。事实上,某一家族的政治地位会由于家族成员的能力、现实政治的波动等因素而时有变化,相比之下,其在文化领域的优势则较为稳定。可以说,文化优势是魏晋南朝士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在分析侨姓士族得以在江左建立贵族体制的原因时即首重政治文化方面的因素,1洵为灼见。田余庆先生的研究也显示了学术上的“由儒入玄”是一个家族成为士族的重要条件。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士族主要是作为文化贵族而存在的。士族通过占有文化资源、从事文化活动而保持、显示其在社会中的贵族地位。既然如此,围棋作为士族所热衷的一项文化活动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即它与人物品评、清谈等成为了士族阶层特殊地位的重要外在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棋品评定的变迁脉络与当时的人物品评,即所谓“乡论”的演进过程是非常相似的。日本学者川胜义雄认为魏晋时期的统治者通过九品中正制构建了不同层次的乡论体系,进而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贵族制的社会结构。3关于川胜氏所提出的乡论的重层结构的观点还可以继续讨论,4不过魏晋以降,统治者的确是通过九品中正制将发端于东汉的人物品评纳入了官方的政治体系之中,使之成为了帝国选官制度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人物品评的话语权从个人身份的名士手中转移到了王朝设置的各级中正那里,即是乡论的话语权从私人转向了官方机构。而到了南朝,又出现了皇帝在诏书中宣布“荡涤乡论清议”的现象,学者认为这显示了南朝皇权的强化。5可见,在南朝时期,皇帝已可以干预作为地方官僚机构的中正的乡论、清议结果,亦即皇帝拥有了品评人物的清议话语的决定权。这样来看,在魏晋南朝时期,作为人物品评的清议活动的权力主体经历了“名士(个体的知识分子)—中正(官方机构)—皇帝”的变迁。这与前文所讨论的棋品评定主体的演进轨迹是基本一致的。
与私人出于对围棋的爱好而撰写棋品著作一样,皇帝主持评定棋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其自身喜爱围棋。对此,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南齐书·虞愿传》云:
(宋明)帝好围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每饶惜之,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帝终不觉,以为信然,好之愈笃。6
又如《南齐书·萧惠基传》云:
当时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吴郡褚思庄、会稽夏赤松并第二品……(齐)太祖使思庄与王抗交赌,自食时至日暮,一局始竟。7
又《梁书·陈庆之传》云:
(梁)高祖性好棋,每从夜达旦不辍,等辈皆倦寐,为庆之不寝,闻呼即至,甚见亲赏。8
又《南史·到彦之传》云:
(到)溉特被(梁)武帝赏接,每与对棋,从夕达旦。9
可见,宋明帝、梁武帝等人本身就是围棋爱好者,且对围棋颇为投入,这无疑是其亲自参与棋品评定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如前所述,乡论话语权的掌控者在魏晋南朝时期经历了由个人到官方机构再到皇帝的变化,这体现了南朝时皇权的强化。而这一时期棋品评定的主体也有着类似的变迁趋势,那么是否也可以从皇权强化的视角来对此加以解释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从本质上来说,围棋只是一种竞技类的游戏,而棋品则是对游戏的参与者的水平高下做出的等级划分。这与王朝的政治秩序似乎全然无关,与关系到官员选任的乡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不过如果将围棋作为高门士族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来看,则其意义就有所不同了。日本学者冈崎文夫已经注意到南朝皇帝虽然多是出身次等士族,但在其即位后却有着明显的高门士族化的倾向。即他们通过与高门士族通婚、参与其文化活动等方式,来使自己融入高门士族的圈子。1赵立新先生进而指出,南朝的宗室在融入高门士族群体的同时逐渐取代后者成为了社交群的中心。2即皇室成员不仅参与高门士族的文化活动,而且成为了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主持者。也就是说,南朝时期的皇室成员取代了高门士族控制文化话语权的地位。这可以看作是军人出身的南朝皇帝在夺去了高门士族的军事、政治权力后,其皇权扩张的又一重要表现。而如前所述,魏晋南朝的士族在本质上是文化士族。进入南朝时期,随着次等士族与寒人的崛起,侨姓高门士族在政治领域受到了明显的冲击,这从他们担任重要职官的情况即可以看出。3
虽然他们的政治地位从政治的主导者下降到了皇权的合作者,但其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对文化领域的控制仍然可以使之在江左社会中居于优势地位。可以说,他们代表了独立于政治权威的文化权威。出身次等士族的南朝皇帝要想重新确立皇权秩序,则势必要在政治上压制侨姓高门士族之后进一步在文化上降低他们的权威地位。前述赵立新先生所揭示的南朝社交中心由士族变为宗室就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朝皇帝取代高门士族成为文化权威的过程。
上文所讨论的魏晋南朝棋品评定主体的变化则可以看作是观察这一进程的另一个视角。围棋本身只是一种竞技性游戏,不过如前所述,在魏晋南朝它已成为高门士族的普遍爱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高门士族表现自己文化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手段。即高门士族通过围棋所带有的名士文化色彩而显示自身作为社会中的文化贵族的身份地位。虽然在政治上他们被迫让出了权力,但是在文化领域他们对皇帝而言是居于优越地位的。参与围棋活动就正是这种优越性的一个构成要素。而以高门士族为主要著录对象的棋品则是他们在王朝的政治地位序列之外另行构建的一个文化序列。如前所述,棋品作为一种等级体制在形式上借鉴了王朝官品的九品模式。即虽然皇帝凭借其政治权威确立了一套政治等级制,但高门士族也可以建立一套与之独立的文化等级制。而二者在外在形式上的相似则体现了士族以文化权威对抗政治权威的态度。在魏晋时期,棋品一类的文化等级评定著作较为少见,而在南朝时期则除了前述棋品类文献之外还有钟嵘的《诗品》、庾肩吾的《书品》、谢赫的《画品》等类似著述出现。这显示了当时的士族力图在文化领域确立由士族主导的等级秩序的努力。唐长孺先生在考察南朝士庶区别强化的现象时指出:“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团业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来保护自己”。4对于当时士族所进行的棋品等文化等级评定活动也可以从这个视角来加以认识。即这些活动是在士族的政治权力受到削弱、其社会地位受到威胁时,他们为了显示自己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以对抗当时的政治权力而采取的措施。1
事实上,这一文化等级序列在当时的社会中也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接受,这从正史中每每述及士人所拥有的棋品就可以看出。显然,这构成了一股潜在的对抗皇权秩序的势力。而皇帝如果想在社会中确立皇权主导的一元化秩序,则势必要将这些独立于皇权的文化等级序列纳入到皇权控制之下。于是就出现了宋明帝设立作为官方机构的围棋中正及梁武帝亲自主持评定棋品的事件。而他们的目的则在于控制棋品这一本来由高门士族所掌控的文化等级序列,进而消解高门士族在文化领域相对于皇权的对抗性力量。或许可以这样说,宋明帝、梁武帝等人在与人对弈时是以围棋爱好者的身份出现的,而当他们钦定棋品时则主要是出于在文化领域扩张皇权的目的了。2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朝皇帝亲自主持棋品评定实则与唐代皇帝钦定士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二者的目的都是以由皇权主导的等级秩序来取代原本由贵族主导的疏离于皇权(甚至是具有对抗性)的等级秩序。3南
朝的棋品评定活动在梁武帝时达到了高峰,却也随着梁武帝时代的终结而销声匿迹。其原因在于随着侯景之乱后南方蛮族登上政治舞台,士族的时代结束了。4此时的士族已经丧失了其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也就无力建构棋品这一文化领域的等级秩序了。对于皇帝来说,既然高门士族已经不具备在文化领域对抗皇权的力量,他们也就不必钦定棋品等级以抑制士族了。
可以与此形成参照的是北朝的围棋活动。受南朝高门士族热衷围棋风气的影响,北朝也不乏围棋爱好者。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焘就曾因下棋而不理会臣下奏事、5甄琛“颇以弈棋弃日,至乃通夜不止”、6高孝瑜“覆棋不失一道”、7宇文贵“好音乐,耽弈棋,留连不倦”等。8且北朝也不乏围棋高手,如:“高祖时,有范宁儿善围棋。曾与李彪使萧赜,赜令江南上品王抗与宁儿,致胜而还。”1可知北朝棋手范宁儿曾在出使南朝时战胜了南朝的顶尖高手、位居棋品一品的王抗。可见,北朝不仅是较为流行围棋,而且也出现了棋力不逊于南朝的棋手。
不过尽管如此,从现有文献来看,北朝却从未出现过棋品评定活动。不论是北朝的皇帝还是士族,都没有为北朝的棋手编订一份棋品等级。且不只棋品,诗品、书品、画品等也从未在北朝出现。其原因即在于北朝士族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较弱,而其皇权又较为强大。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在北朝,贵族一般难以成为纯粹的贵族,仍然保持着豪族的性质。”与南朝不同,北朝士族的影响力更多地集中于地方州郡的层次而较少能够进入中央。2陈爽先生指出北朝的高门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对皇权存有依赖性,作为士族,他们具有较强的官僚色彩。3虽然北朝的士族有属于自己阶层的文化风尚,但他们并未像南朝的高门士族那样在文化领域拥有可以独立于皇权的话语权。在异族皇权主导的政治一元秩序下,北朝士族无力在文化领域建立一套独立于政治等级的文化等级序列。北朝士族既然没有独立于皇权的文化权威,因而由士族主导的文化等级序列也就不可能出现了。
唐代之后,围棋技术有了明显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相关著述,然而其中却极少有类似六朝的棋品这样的为棋手进行等级评定的著作。明清时期虽然有“国手”的称呼,如所谓“明清十八国手”等,但这与东晋南朝时士族模仿王朝官品秩序而建立的棋品等级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究其原因,固然与社会上已不再流行人物品评有关,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在于此时的文人士大夫已丧失了相对于皇权的独立性,无力在皇权主导的政治秩序之外另行建立一套文化等级秩序了。至此,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了。
(责任编辑:王彦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