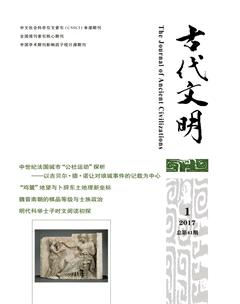春秋战国“舆人”辨正
李毅忠
提 要:先秦文献中的舆人有二义,均可从“舆”的字源上找到依据,均非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其一,由从事农业的庶人阶层中征发而来的夫役。这是具有临时性的身份,战时主要负责搬运车舆,亦可参与军事性伪装,平时从事筑城、抬棺等,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多有舆的编制。舆人在参与某些劳作时归由皂管辖,在职务等级上低于皂而高于隶,但这并不意味着该人群本身的社会地位也低于皂。其二,特指造车箱的工人。
关键词:舆人;国人;庶人;春秋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1.005
在先秦典籍中时常出现关于舆人的记载,对于该人群的性质和地位,古人、近人和今人有着多种不同的解释。首先,传统注家多释舆为众,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形:1,“皂,造也,造成事也;舆,众也,佐皂举众事也。”12,“舆则众也,谓卫士无爵又无员额者”,是与“无爵而有员额者”之皂相对的群体。2即是说,舆与皂往往被作为成对的概念考察,但前者以舆为地位低于皂的贱役,后者则以其为等级地位较低的卫士。其次,近人、今人对舆人又有几种不同解释:1,舆人是“奴隶”,甚至有人认为舆人是奴隶中的“沉底儿”。32,“舆应放在民众或平民之列,而不能排除在外”,4若进一步细分,或认为其为地位高于庶人者;5或认为其属“国人”中等级地位较低者,6亦有以其为“国人”中的士阶层者。73,舆人是造车工人,战时可临时充当与其本业不符的力役(此说同将舆人划入平民阶层范畴之说部分重合)。84,舆人“是一种临时职业”,“也有是农人被征为役徒者”,1惜所论未详。存在着如此多的说法,可见舆人的性质、身份和社会地位仍是一个亟待搞清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史料文本的分析对比,厘清舆、舆人的含义,以就教于方家。
一、舆、舆人与舆人之官
由于我国语言具有一词多义的特殊性和模糊性,在考察舆人本身之先,首先来看“舆”字字源上的演变趋势和特点,这应有助于正确理解舆、舆人的含义。《说文》:“舆,车舆也,从车舁声”。2甲文“舆”作:(前5.6.6);(佚949);(掇2.62);3(佚945;续3.12.6);(新2818)。4甲骨文中舆或为人名(合06667),或为地名(掇2.62),难以从上下文判断其义。该字金文少见,战国时期舆字作:(杂27,六例);(日乙90);5(秦下表59)。6总体而言,在字形上变化不大。罗振玉释舆为:
案,《考工记》“舆人为车”,此象众手造车之形,轼?轸轵轛皆舆事,而独象轮者,车之所以载者在轮,且可象,它皆不可象。举轮,则造车之事可概见矣。7
但此说遭到李孝定反对:
契文从、从舁,不从车,盖既象车舆之形,舆者,人之所居,若从车,则并舆轮而象之,不得独谓之舆矣。契文象众手举舆之形,其初疑当与兴舁同意,篆文从车者,形之伪变也。8
马叙伦之释与李孝定类似,并有详证:
伦按,舆者,即车箱,所以载人及物者也。《仪礼·士丧礼》郑注:“其车之轝状如床”,轝即舆也。《史记·张耳陈余传》《索隐》引郭璞《仓颉解诂》:“箯轝,举土器”。似《仓颉》有轝字,今本书无。然玄应《一切经音义》引《仓颉》:“轝,举也,对举曰轝也”。对举曰轝,直是舁字,则《仓颉》本字作舁也。郭书之轝即舆之异文。9
舁,《说文》:“舁,共举也。”段注:“谓有叉手者、有竦手者,皆共举之人也。共举则或休息更番,故有叉手者。”10马氏并证舁、轝关系:
承培元曰:“舁即‘舆臣隶之舆。《吕览》曰:‘厮舆白徒,注:‘举物之夫也。是舆当为舁也。”刘考生曰:“舁为兴所从得之声”……伦按,共举也,当作共也,对举也。舁即兴举,轝之初文。”11
由上述诸家对“舆”及关联的“舁”之释可知,舆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指车箱,一指共同抬举。马氏、李氏均主张车箱之义从抬举之义的兴、舁演化而来,而《左传》中所见两例“舆榇”皆用共举义亦可作为此说之证。12
因先秦典籍中关于舆人的记载相对可数,又以《左传》、《国语》中出现频率最高,为便于分析,这里首先将《左》、《国》各条目中的舆人辑录于下,再以其它典籍参互观之:
(1)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舆人诵之,曰:“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得国而狃,终逢其咎。丧田不惩,祸乱其兴。”13
(2)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以自诰也。1
(3)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2
(4)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3曰:“称舍于墓。”4
(5)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5
(6)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赵孟问其县大夫,则其属也。召之而谢过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晋国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武之罪也。敢谢不才。”遂仕之,使助为政,辞以老。与之田,使为君复陶,以为绛县师,而废其舆尉。6
(7)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7
(8)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8
(9)季康子使冉有吊,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与有职竞焉,是以不得助执绋,使求从舆人……”9
又有称“舆”而实指舆人者:
(10)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10
(11)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舆曳柴而从之。11
(12)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12
(13)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产使舆三十人迁其柩。13
在《左》、《国》之外的先秦典籍中关于舆人的记载有:
(14)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14
(15)舆人为车,轮崇、车广、衡长,参如一,谓之参称。15
(16)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16
(17)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17
(18)善用兵者,诸边之内,莫不与斗,虽厮舆白徒,方数百里,皆来会战,势使之然也。18
首先从这些条目来看舆人所从事的事务。条(3)、(4)、(5)、(10)、(11)表明,军中有舆人,其中在第(3)、(10)、(11)中,其在战时拖曳木柴或作其它军事性质的伪装;(11)则昭示舆人地位低于直接参战的军士,不在“乘车者”之列,和军队直接作战无关,(3)中秦军绑缚舆人,将其伪装成俘虏进而包围商密这一举动同系其证。综合这几例可知,在军中的舆人当为力役,其所从事的实即后世军队中役夫一类的后勤工作。《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平丘之会时,晋军“次于卫地,叔鲋求货于卫,淫刍荛者”,放任割草、采樵之人扰乱地方,卫人不堪其扰,向叔向请求道:“刍荛者异于他日,敢请之。”可知军中尚有割草、采樵之人担任后勤工作,但与舆人分工不同。另结合《左传·昭公六年》载楚公子弃疾适晋过郑时“禁刍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树、不采蓺、不抽屋、不强匄”,可以推测,除舆人、刍荛外,在春秋时期的军队中还存在着其他从事后勤工作的门类。
此外,条(6)显示,舆人参与筑城;条(9)、(13)显示,舆人参与抬拉棺材。在条(9)下,竹添光鸿笺云:“舆人盖丧车之人。观舆迁柩、舆曳柴,似执推挽之役者。”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舆或舆人皆贱役”,“执杂役者”,“迁柩亦用舆人,此舆人盖即辇柩车者,从舆人盖执绋之谦词”。2均以舆人为一种从事贱役的役徒,在性质上,与军中之舆人并无根本差异。联系到舆字从舁得义,上述各条目中的舆或舆人可归为一类。至于《左》、《国》之外的典籍中出现的舆人,若认同马叙伦考证所援引之例,(17)、(18)两条亦属此类。
(14)、(15)、(16)这三条记载中的舆人,显系造车工人中造车箱的门类。由此可见,先秦典籍中主要存在着两种舆人,一为征发的服役者,一为造车工人中造车箱者,二者可各自从舆字的两层含义找到源头。这两种舆人既不可混同,更不可相互取代,尽管他们的工作内容均与车舆有关。《左》、《国》并无以舆人特指造车工人的用法,这也是应当注意到的。
对于条(8)申丰论藏冰一节,杜注:“舆、隶皆贱官”,3以此处的“舆人”为一种下级官吏;童书业先生则认为,山人、县人指郊外之人,舆人、隶人指国中之人。4联系到这里讲的是采冰和藏冰之事,若以最终藏冰处为圆心、至采冰处为半径,则山人、县人、舆人、隶人分别由外至内地处在这条半径的不同位置上,因此童说有一定道理。然而此处涉及的几类人各自的性质,囿于材料,想要真正弄清是困难的,可与之系联的仅有体现舆人社会阶等的条(12),其原因在于这两处的舆人均与隶人相联系。对此,笔者将放到后文讨论。
接着来看与舆、舆人相关的职官,分别有七舆大夫、舆尉、舆帅、舆司马、舆臣、舆嬖等名目。除上文条(6)的“舆尉”外,见于《左》、《国》的还有:
(19)遂杀丕郑、祁举及七舆大夫:左行共华、右行贾华、叔坚、骓歂、累虎、特宫、山祁,皆里、丕之党也。5
(20)里克告丕郑曰:“三公子之徒将杀孺子,子将何如?”丕郑曰:“荀息谓何?”对曰:“荀息曰‘死之。”丕郑曰:“子勉之。夫二国士之所图,无不遂也。我为子行之,子帅七舆大夫以待我。我使狄以动之,援秦以摇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赂,厚者可使无入。国,谁之国也!”6
(21)是故杀丕郑及七舆大夫:共华、贾华、叔坚、骓歂、累虎、特宫、山祁,皆里、丕之党也。丕豹出奔秦……今又杀臣之父及七舆大夫,此其党半国矣。7
(22)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皆受一命之服。8
(23)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赐之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9
(24)初,栾盈佐魏庄子于下军,献子私焉,故因之。赵氏以原、屏之难怨栾氏。韩、赵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而固与范氏和亲。知悼子少,而听于中行氏。程郑嬖于公。唯魏氏及七舆大夫与之。1
(25)知铎遏寇之恭敬而信强也,使为舆尉。知籍偃之惇帅旧职而恭给也,使为舆司马。2
(26)舆嬖袁克杀马毁玉以葬。3
(27)周原伯绞虐其舆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舆人逐绞,而立公子跪寻,绞奔郊。4
条(25)的舆尉、舆司马,《左传·成公十八年》分别作上军尉和上军司马,5注家遂据此以为舆尉即上军尉,舆司马即上军司马,然而参看(23),司马与舆尉并举,则与此说抵牾。吴曾祺云:“舆尉,主役属徒众之官,不必指上军;下‘舆司马,亦不必专指上军也”,6至确,条(6)因绛县老人年已老迈却仍被征发筑城,赵武“废其舆尉”足证舆尉系专门负责征发与管理舆人之官。(22)和(23)的舆尉、舆帅均受一命之服,官在大夫之列;从命服序次来看,二者相同,由此可推测,如同候正即候奄一样,舆尉、舆帅当是对同一种官职的不同称谓。需要指出的是,赵武所废舆尉与(23)的舆尉虽同名,但前者可由执政任免,后者则由国君任命、有命服,显然处在不同的阶等上,这是存在舆编制之一证。
舆司马除见于(26)外,亦见于《周礼》夏官司马之属,间于军司马和行司马之间,然而具体执掌阙文。贾公彦据《周礼》疏曰:“军司马当宰夫、肆师之等,皆下大夫,四人;舆司马当上士,八人;行司马当中士,十六人。余官皆无异称,此独有之者,以军事是重,故特生别名。”7然而《国语·晋语八》载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问于时任舆司马的籍偃,籍偃答道:“偃也,以斧钺从于张孟,日听命焉。”张孟(张老)时为中军司马,主管军法,籍偃直接听命于中军司马而非舆尉,则舆司马也主管军法。籍偃是晋国大夫而非上士,若《国语》与《周礼》中的舆司马同名同实,《周礼》之载与贾疏则显失当,因此,舆司马的职司当如童书业所言,为“司舆人之军法者也”。8
七舆大夫总是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名称而出现,它是对七个人的称呼还是一种官职名称很难确定。注家对七舆大夫有两种解释,一为国君主管兵车的七位舆帅,在条(19)下,杜注,“侯伯七命,贰车七乘”,孔疏:“《周礼·大行人》云:‘侯伯七命,贰车七乘。贰即副也。每车一大夫主之,谓之七舆大夫。”接着他又引服虔语作出了第二种解释:“下军之舆帅七人属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军舆帅七人,往前申生将下军,今七舆大夫为申生报怨;栾盈将下军,故七舆大夫与栾氏。”9就晋惠公所杀里、丕之党的七舆大夫均有名有姓而言,似乎后一种说法更可信,尽管是否真如服虔之说——仅为对下军舆帅的另一种称呼或统称——仍可置疑。然而可以确定的是,由国君任命的舆司马不在七舆大夫之列,因为在条(24)中,当栾氏之乱作时,舆司马籍偃虽也受到牵连而被囚,却非栾氏之党。
另一个与舆人相关的可能职官“舆臣”见于条(27)。原为周王畿内封国,前635年,晋文公迁原伯贯于冀,仍袭旧称。杜注本于《诗·大雅·公刘》《毛传》,释“曹”为群,10实际上,将“使曹”看作这位不堪原伯绞暴虐的舆臣之名似更文从字顺。从上下文来看,他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为直接管理舆人的官员并深得舆人信任,其出逃导致舆人们对原伯绞的反抗。由于舆臣之名仅见于此处,其职位高低无法判断;原国比晋国小得多,执掌或同于晋之舆尉。(26)的“舆嬖”大概也与其相类,是管理舆人之官受宠者。
综上所述,虽然限于材料,与舆人有关的许多官职难以明确判断职司,但在春秋时期的晋国军队中确实存在着管理舆人的舆的编制。舆人平时服各种力役,战时虽不直接参与作战,但却和刍荛等一道负责后勤保障,有时还参与伪装迷惑敌人,对军、行等战斗编制有辅助作用。其它诸侯国的相关文献资料虽不如晋国丰富,然而(27)的信息透露出,舆的编制在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中普遍存在。《淮南子·兵略训》云:“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淫舆,无遗辎,此舆之官也。”1《淮南子》虽为汉代文献,但其所记载的舆官职司描述得非常具体,并可与《左》、《国》之载相互发明,在这一语境下,其所从事的只是搬运辎重一类的工作,完全不涉及造车或修车之事。《晋书》载昙达攻白坑时的誓词云:“王者之师,有征无战;粤尔舆人,戮力勉之!”2这里若按旧释释舆为众,便无需用《尚书》与金文多见之“粤”字连接,当系用古义,将军中直接作战的师与搞后勤的舆人分言。
二、舆人的社会地位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传统注家释舆为众是模糊而不准确的,因而对判断舆人的社会地位无太大帮助。日本学者吉本道雅《春秋“国人”考》一文在考证国人的同时也论及庶人,考论精当,其成果可拿来作为确定舆人社会地位的标尺。但首先要指出的是,徐亮工先生考证认为,国人是与私属相对的一个术语,体现的是对“国”之臣民与“家”之臣民的不同占有关系,且与“国野”之制无涉:“‘国人既不是地域的概念,也不是阶级或等级的区别。卿大夫作为国君之臣,为公室‘官守者,是为‘国人的上层”。3而据吉本道雅考证,广义国人所指范围很广,他国采用“国号+人”(如鲁人、齐人等)的记述方法所指的某国之人往往可以和国人互换,可包含自诸侯至工商等在(国都的)城壁内居住的各阶层,但由于大夫以上的人(包括部分“士”)都多有名字,所以国人往往用于指那些不具名的下层大夫和士。狭义的国人则主要指住在城壁之中,承担兵役但并不承担力役的人,“无一例从事农业、力役的事实”。国人和其意不明的“民”、“小人”中承担兵役的群体重合,所以国人还包括“士以下的兵役承担者”(他同时认为,国人或亦包括工商,但文献中的实例证据极少)。与此同时,多与国人对言的庶人“一般住在城壁之外”,由“其庶人力于农穑”等记载可表明庶人的本业为农业,他们与“民”中本业为农业的群体重合,但庶人与国人并无重合之处。4这二位学者的切入点各不相同,徐亮工先生的论述主要就国人的性质而言,如果对国野之制问题存而不论,那么吉本道雅对国人在细节上的考察仍是值得参考的。
在此基础上,首先来看被征发的舆人的社会地位,条(6)透露出较多有关其性质和来源的信息。绛县老人必为参与城杞的舆人,因而才有资格去吃晋悼夫人所赐之食并在被怀疑时理直气壮地作答。他自称小人,这里的“小人”并非道德观念范畴,而是指实际的社会等级,即《左传·昭公六年》所谓:“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之小人,被“废”的是贵族身份,而被“降”的则当是剥夺平民身份,小人只能被“降在皂隶”了,5小人的身份比“皂隶”要高,至少要更自由一些。老人来自绛县,并不住在国都城壁之内,平时由县大夫管辖,属于农业生产者,这和“庶人”部分重合;当舆尉将其临时征发筑城时,即成舆人,事毕后再回去务农。国人承担的是兵役而非力役,则舆人所来自的阶层不应在国人之列。绛县老人得以仕进,正同铁之战时赵鞅誓师时的“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一样,1是在特殊情况下,平时并无此机会;而与赵鞅誓词相对应,绛县老人能够仕进,又证明其亦不应在“人臣、隶、圉”的范畴之内。
从舆人之诵的内容中也能看出其所从来阶层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条(7)有较具体的反映,这个阶层的人可拥有衣冠、田产,且子弟有受教育的权利;童书业认为,这是国人而不是庶人阶层所能拥有的。然而,子产新政之所以有“取我衣冠而褚之”之举,或许正是见到这些人“衣冠”有僭、与他们的身份不符,为了使“上下有服”,理顺等级关系,才对他们加以遏制打压。庶人作为自食其力的自由民,生活在主要借助传统家族进行统治的村社之内,“子弟”应即《左传·桓公二年》所谓“分亲”,拥有与其身份地位相符的衣冠、田产是应当的,并非只有国人才可拥有私人资产。由此可见,作为一种被临时征发的役徒,舆人(主要)来自庶人阶层,即本业为农业的“民”或“小人”,由于其临时性,将其视为一个阶层是不适当的。
舆人往往采用“诵”的方式对上层阶级进行规劝。“诵有怨谤之意”,2《说文》以讽、诵互训:“诵,讽也。从言,甬声。”3即以婉言、隐语进行讽谏,其特点是有音节上的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即《毛诗序》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4可以设想,被征发而来的舆人在集体劳动时,将当时身边发生的一些大事小事编入类似于夯歌的诵中,一有助于集体协作劳动,二可驱除疲劳,(1)、(4)、(5)、(7)皆属此类;因其劳作之地往往与统治阶级相距不远,就可直接被统治阶级听到,(4)、(5)则其例。这又成为民情上达的一个管道,有的还由作为君主耳目的工、师等乐官在各地采风有目的地收集后上达,对统治者进行讽谏,而开明的统治者对此也很重视。《诗经·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刍荛者亦是工、师的采风对象,联系《左》、《国》军中有刍荛者并与舆人分工不同之载,可知舆人与刍荛者身份相去不远,因此后人往往二者并举。如东汉杨震为河间人赵腾陈情于安帝:“乞为亏除,全腾之命,以诱刍荛舆人之言。”5《魏书·张彝传·上采诗表》云:“故询于刍荛,著之周什;舆人献箴,流于夏典。不然,则美刺无以得彰,善恶有时不达。”6《晋书》载庾冰上表云:“或借讼舆人,或求谤刍荛,良有以也。”7
文献中还常见谤这种进言方式,它与讽诵不同,虽也非直陈,却是不拐弯抹角、不留情面地指责,厉王止谤使国人道路以目的故事众所周知。在《左传》的记载中,统治者非常重视并努力不被谤,8如果被谤,则努力“分谤”,9即加以平息。就文本而言,除国人10外,行谤的群体有远臣、11民12与庶人13等。舆人作为来自民、庶人的一分子,虽可行谤,但他们往往采用诵的方式讽谏,大概正是因其劳作的特殊性而致。另一方面,从这种讽谏的形式及统治者的态度亦可看出,在通常情况下,统治者为舆人提供的环境相对宽松,作为“小人”,即使对君子有一些讥刺之语,君子们也不会打击报复,正如宋国华元所做的一样。1
要讨论舆人的社会地位,还不能不考察(12)中的十等人。在这十等人中,学界对士以上的身份争论较少,但自皂至于牧则历来争论较大。一些学者认为自皂至台的六等人皆为奴隶,2也有的学者认为自皂舆至圉牧的八等皆属家内奴隶性质,3还有人认为他们都是平民。4通过前文的分析和对比可知,(12)中的舆显然与临时征发而来的服役者或造车工人不类,在本文从典籍中析出的如此多的关于舆、舆人的条文中,它仅可能与(8)系联。因此,要明确地证明这类舆的社会地位是很困难的,只能综合其上下文语境所涉及的人群进行分析。
皂的本义为黑色,《广雅·释器》:“黑也”;5
《集韵》释皂之一义为“黑色”;6《广韵》:“亦黑缯”,7因而文献常称着黑衣者为皂。又以皂即“枥”,为养马之厩枥,《管子·轻重戊》载:“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8有人遂依此释皂为养马的下级官员,如孙诒让释《周礼》中“趣马,下士,皂一人,徒四人”之“徒”:“徒掌在皂养马,故古书亦通谓之皂。左昭七年《传》云‘士臣皂,此徒亦为下士之属,与彼正相应。”9俞樾则云:“皂者,《赵策》所云补‘黑衣之队,卫士无爵而有员额者,非今皂役也。”10这与他接下来释舆人为“卫士无爵而又无员额之众”是相继的,是根据战国的情况作出的推论,有推翻前人对皂、舆解释的意图,然而却仍无法令人信服。无论持何种说法,注家均依循着(12)的限定,认为皂的身份地位近于士但略低。《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若大盗礼焉以君之姑姊与其大邑,其次皂牧舆马,其小者衣裳剑带,是赏盗也。”这里将“皂牧舆马”与“君之姑姊与其大邑”对言,皂牧可被视为自皂至于牧的人;舆马当指车马的物。既然可以被当作赏赐之物,那么皂牧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和自由民不同。参诸“降在皂隶”之语观之,皂的身份就较为特殊,一方面拥有职位,社会地位和下士相近,大抵为附属于士阶层、对士以下的阶层进行管理的执行者;另一方面其人身自由又受到一定限制,并非自由民。
关于隶身份的争议更大。注家认为,隶为罪人,属役徒之列。《仪礼·既夕礼》:“隶人涅厕”。郑注:“隶人,罪人,今之徒役作者也。”11郑注《周礼》“罪隶”:“盗贼之家为奴者”。贾疏:“罪隶,古者身有大罪,身既从戮,男女缘坐,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故注云盗贼之家为奴者。”12而这似与其它文献中的隶又有区别。晋栾盈之乱时,身为“隶”的斐豹以杀掉栾氏的勇士督戎为条件,要求焚掉作为奴籍的丹书,而范匄必须“请于君”才能焚烧这份丹书,13它一方面表明隶的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另一方面表明这些军中之隶并非范匄的私属,他无权私自更改隶的身份。铁之战赵鞅誓师时云:“克敌者……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14则表明庶人、工商与人臣、隶、圉之间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免”去的同样是奴籍。《国语·晋语一》载:“其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飨,为人而已”,隶农不占有土地,是“隶”之一种。若上述记载姑且可作为将其划入奴隶阶级的证据,那么与之相对,《国语·晋语四》“皂隶食职”,说明皂、隶有菲薄的禄;《左传·襄公九年》:“工、商、皂、隶不知迁业”,则表明皂隶与工商一样都是固定的阶层,社会地位虽低于工商,但拥有自己的固定职业——在条件好的情况下,他们安于本分;若条件不好似亦可改变职业。参校观之,绝不可将隶简单视为不占有生产资料、没有人身自由、为奴隶主进行生产劳动、完全听命于奴隶主、可以被随意买卖和杀死的那种绝对意义上的奴隶。
既然文献中皂、隶之义仍难有的论,不妨换个角度来看,条(12)列举的十等人是就“待百事”(执行各类政事)而言,并未涉及庶人、工、商,应该说,体现的只是春秋等级社会的一个方面,即职务上的等级关系,而这正与“皂隶食职”相关。文献中常皂隶并举,皂总与隶相伴生而存在,似可直接管理隶;加之前文所引“降在皂隶”,“皂隶”的地位似低于“小人”,那么,夹在其间的舆、舆人似乎也无法超脱出这二者之外。而与此同时,当工、商、皂、隶等下层阶级在文献中作为相对固定的组合被提到时,却少有提及舆人的。综合考虑,有理由认为,作为主要从庶人阶层征伐而来的、有临时性的舆人,当该群体被编入被称为舆的编制之中、在从事某些劳役的过程中,可能会由长期、稳定地率隶人服劳役的皂人统辖下工作;然而这并不能表明这类舆人是比皂的社会地位低的阶层,而只是由于皂的近便条件或对工作的熟悉程度等诸方面原因,使舆人受到皂的管辖,在职位等级上显得稍低一些。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舆人有二义,均可从“舆”的字源找到根据,均非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1,舆人系主要由从事农业的庶人阶层征发而来、具有临时性的人群,类似于民夫,与军事等有较密的切关系;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存在着舆的编制。舆人战时主要负责搬运辎重,亦可参与伪装;平时从事筑城、抬棺等。与在职务等级上相对固定的皂、隶不同,皂、舆、隶之舆可能体现的是舆人在参与劳作时归由皂管辖,舆在职务等级上低于皂而高于隶并不代表该人群本身的社会地位也低于皂。2,特指造车箱的工人。在《左传》与《国语》中第一义多见,而第二义则常见于《周礼》和面向战国时期的文献。
(责任编辑:王彦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