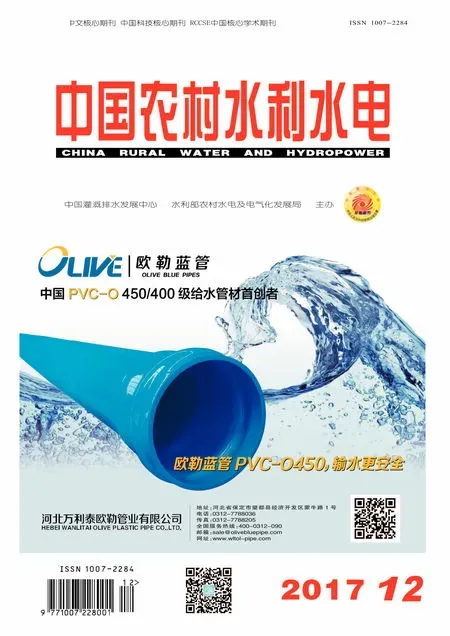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的困局及其法律应对
——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李 祎 恒
(河海大学 法学院,南京 210098)
1 问题的提出
作为农田水利发挥效用的“最后一公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以下简称小农水)在整个体系中一直处于重要但欠缺足够关注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小农水是连接水源和农田之间的关键,虽然细微,但不可缺少;另一方面,小农水面广、量大,建设和管护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给公共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而且小农水大多不具备经营条件或者经营成本和收益不成比例,普遍存在“重建轻管”的现象[1]。
针对小农水工作中存在问题,国家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产权制度改革就是其中一条主要的路径。从2002年国务院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和2003年水利部的《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颁布实施以来,各地相继出台了小农水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力图从明晰产权的角度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小农水建设,并落实管护主体和责任。然而从目前看来,小农水产权制度改革并不能说是完全成功,甚至在很多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有失败之虞。对此,本文拟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从调研情况出发,分析小农水产权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对相关立法进行对比分析,以应对小农水产权制度改革的困局。
2 南京市小农水的整体情况
2.1 南京市小农水的基础情况
从调研情况来看,23.8%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村拥有灌溉泵站,23.2%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村拥有塘坝,19%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村拥有水渠,18.5%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村拥有抽水机或水泵,12.5%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村拥有小型水库,但是只有1.2%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村拥有喷灌设施,还有1.8%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村拥有其他类型的小农水。在这些小农水中,建设于2000年以后的占21.1%,建设于1990年代的占17.8%,建设于1980年代的占20%,建设于1970年代的占18.9%,建设于1960年代和1950年代的各占6.7%。2000年以来,随着“三农问题”关注度的日益增加,小农水的建设也比较多。从兴修类别来看,兴修最多的为疏通河道,占28.5%;其次为兴建农村灌排设施,占27.8%。此外,修建水渠占25.3%,修建水库占11.4%,拦河筑坝占7%。
灌溉方法和灌溉方式决定了农民对小农水的使用频率和依赖程度。从灌溉方法来看,大部分农民所使用的灌溉方法为沟灌,占59.1%。除沟灌外,漫灌的占21.2%,畦灌的占12.1%,湿润灌的仅占7.6%。在主要的灌溉方式方面,自行采用机械抽水灌溉的占66.7%,依靠村或小组有组织地抽水灌溉的所占比例为19.7%,也有农民的主要灌溉方式为人力挑水或运水灌溉,占10.6%,靠天灌溉仅占3%。在生产机械化的进程中,原来大多依靠体力的种植方式转向了越来越多地依靠机械,因此在灌溉方式方面,大部分村民选择了机械抽水灌溉。
灌溉水源的情况也极大地影响了小农水的需求。在灌溉水源来源的选择中,灌溉水源来自于池塘和水库的占53%,灌溉水源为周围的河流与湖泊的占40.9%,灌溉水源来自于地下水的占3%,来自于天然雨水的占3%。数据显示,农民所在村发生过灌溉缺水情况且情况较为严重的所占比例为18.2%,发生过灌溉缺水情况但不严重的占48.5%,而没有发生过灌溉缺水情况的所占比例为33.3%。这就是说,66.7%的村民所在农村发生过灌溉缺水现象,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
2.2 南京市小农水产权制度的实施情况
改革开放后,小农水产权不明晰、管理责任无法落实等现象普遍出现,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2]。在这种情况下,各地都对小农水产权制度进行了改革,并希望藉由小农水产权制度改革,使得小农水的建设和管护责任得以明确。从南京市的情况来看,小农水产权制度改革也主要集中于建设和管护两个方面。
小农水建设的投入不足是小农水产权制度改革需要解决一大问题。从出资情况来看,19.7%的小农水建设是由村里集资的,乡政府出资的占31.6%,区县政府出资的占6.6%,市级以上政府出资的占15.8%;个人投资仅占3.9%,可见小农水建设主要是由政府出资。即使是由集体和农民自行建设的小农水,大都也有政府补贴,占88%。
虽然从目前来看,政府投资是小农水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但对于政府来说,公共财政负担过重迫切的要求建立市场化的小农水资金筹措机制,因而在产权制度改革中,社会投资被视为未来小农水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对于村集体和农户等受益者来说,小农水的建设资金同样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在政府已经承担了小农水建设的主要责任的情况下,小农水的受益者更加不愿意增加自己的负担。从调查情况来看,假设需要10 000 元建设小农水,村集体和农户愿意出资1 000 元以下的占91.2%,愿意出资1 000~5 000元的占5.3%,愿意出资5 000元以上的仅占3.1%。
相对于建设来说,维护更是小农水工作的难题,并与小农水的产权问题密不可分[3]。从调查情况来看,87.7%的村对小农水进行定期维护,12.3%的村无定期维护。在定期维护中,维护周期在1-3个月之间的占19.1%,维护周期为半年的占46.8%,维护周期为1-2年的占25.5%,维护周期为2年以上的占8.5%。除定期维护外,当小农水无法发挥效用时,50.3%的受访农民会直接要求基层水利服务部门派人维修,37.7%的受访农民会拨打政府服务热线要求维修,6%的受访农民表示会自己维修,6%的受访农民要求村集体维修。
维护主体的明确和维护经费的支出是小农水产权制度实施的关键。实践中,小农水的维护主要由受益者和基层水利服务站负责,但是不同的主体对小农水维护的认识并不统一[4]。对于受益者来说,在小农水主要由政府建设的情况下,54.4%的受访农民认为其不是小农水的产权人,所以不应该负担运行维护费用;15.6%的受访农民认为维修小农水的费用应该由全村农民均摊;还有30%的受访农民认为应该由村民与村集体共同承担小农水的维护经费。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南京市已经取消了农田灌溉用水水费制度,但是在实践中,却并非如此。对于小组或村里组织统一灌溉是否需要收费的问题,认为收费的所占比例为56.1%,回答不收费的占43.9%。此外,在小农水产权制度改革中,也允许通过拍卖、承包或租赁方式获得小农水产权的主体向使用设施的农民收取费用,因而事实上存在收取“农业水费”的现象。而对于基层水利服务站来说,其经费的来源渠道比较单一,主要是公共财政的定额补助,占64.1%;还有10.3%来源于基层水利服务站开展的多种经营,3.5%来源于基层水利服务站提供的技术服务,其他来源渠道占21.8%。但是由于小农水维护费用巨大,91.1%的受访基层水利服务人员认为管理和维修养护经费不足。
在小农水产权制度改革中,主要是通过拍卖、承包、租赁、转让、股份制合作等方式,移转小农水的经营权。从调查情况来看,47.6%的受访者表示,承包、出租或转让小农水的决定是由村民委员会集体表决决定的;31.7%的受访者表示是由全体村民投票决定;其他受访者对此表示不清楚。对于承包、租赁或转让的小农水,71.4%的受访者表示村集体采取一定的监督措施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进而保证农田用水灌溉;3.2%的受访者表示没有采取监督措施;其他受访者对此表示不清楚。对于小农水产权制度改革的效果,62%的受访者表示,小农水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完全市场化的方式并未实现预期的效果,很多承包、出租或受让小农水的经营者因为入不敷出而退出了;但是也有19.4%的受访者表示,小农水产权制度改革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只是因为农业生产基础状况的变化,约定的经营期尚未届满,然而旧有的小农水已经被新建的小农水或其他设施所替代,无法实现经营目的;其他受访者表示对此情况不清楚。
3 小农水产权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在讨论小农水产权制度实施中的问题之前,有一个前置的问题需要予以明确,即小农水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实施小农水产权制度。作为农田水利体系中的一环,小农水相关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且只有一个,即服务于农业生产。基于此,我们可以识别产权制度安排中不好的实践[5]。即通过“合目的性”的考察,来查明现有制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以为制度的调整奠定基础。
现有小农水产权制度主要是围绕小农水建设的资金来源和小农水管护的责任承担等方面进行框架建构。但是从南京市的实践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显而易见的是,过往的产权制度改革没有真正意义上建立产权制度体系,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改革。由于主要采用承包、出租、入股等方式,小农水的所有权并未发生变动,因而这种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质是通过移转经营权来明确管护主体。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经营小农水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经营者往往只愿意承担日常的管理[6]。当小农水的维护需要大量劳动力、资金或者技术上的投入时,还是由基层水利服务站来承担责任。此外,小农水产权制度的有序运行有赖于水价机制等市场化制度的形成。然而,不论是在南京市,还是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农村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市场机制尚未得以全面建立,这就使得小农水产权制度改革本身成为政府行政管理的目标,而于农业生产无益。申言之,从1981年水利部发布的《关于在全国加强农田水利工作责任制的报告》、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水利产业政策》到2002年国务院批准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2003年水利部颁布《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小农水产权制度改革一直是因应改革开放以来农田水利发展机制、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需要。但在探索的过程中,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发生了异化,从服务于农业生产转向为产权制度改革而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尤其是在农田水利市场化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要求社会来承担小农水的建设和管护责任,既对小农水自身属性的考虑有所欠缺,也高估了社会资本介入的积极性,而这种异化也使得小农水产权制度改革最终陷入困境。具体在小农水建设方面,小农水产权的初始取得有着先天上的缺陷,在公共财政作为小农水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时,问题已经初现端倪;当需要清晰的界定小农水的产权,并保障产权人的利益时,这种缺陷更会被放大。当政府投资建设小农水时,小农水建设用地分散,一般不进行征收。这种长期实际占有的行为“掏空”了土地产权的内容[7],使得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无法对被占用的土地行使相应的权利,本质上应属于征收。不过由于政府负担了小农水的建设费用,小农水又是为了农民的农业生产服务,而且南京市已经不向农民收取农田灌溉用水水费,土地被占用的土地产权人一般不会有所异议。但是如果要求集体经济组织或是收益农民为小农水的建设出资(即投资者是受益者),则很难获得回应。其原因在于,小农水建设的正外部效应缺乏足够的制度激励[8]。在自己享有权利的土地上建设使他人获益的小农水,却因为市场化机制的不健全而无法向他人收取费用,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是一种成本大于收益的行为。而对于纯粹的社会投资者而言,除了回报乡里等慈善目的外,其投资建设或是参与建设小农水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获取相应的利益。但在此情况下,小农水就会成为集体所有土地和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社会投资者所有的建构筑物的结合。而且,社会投资者既未向土地权利人支付补偿,还要向其收取小农水的使用费用,显然得不到受益农民的同意。因此,如果不能明确小农水的产权基础,那么小农水的产权一直就会处于模糊的状态,也无法吸引社会投资者的注意力。
在小农水管护方面,产权制度改革的困局主要表现在管护主体负担的管理和维护小农水的责任与其享有的权利不对等[9]。上文已述,南京市小农水的管护经费长期处于投入不足的状态。调研数据显示,南京市小农水管护每年需经费约2亿元,而目前公共财政的投入不足1/10,资金缺口甚大。这一问题在全国农田水利工作中也是普遍存在[10]。小农水产权制度改革试图通过产权流转来使包括受益农民在内的社会投资者参与小农水管护,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的负担。然而,产权制度改革目标异化的一种表现就是希望明确小农水的管护主体,从而将管护责任转移给社会主体,但忽视了应当同时赋予管护主体以相对应的权利。据此,产权制度改革并未使得小农水产权彻底的清晰化,而只是小农水管护责任的清晰化。对于产权人来说,小农水的产权实质上不但不能使其从中获益,反而剥开产权的权利外衣,所见皆是义务和责任。
4 《南京市农田水利条例》与《农田水利条例》的立法应对
4.1 《南京市农田水利条例》的积极应对
小农水产权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产权制度改革的效果,各地为应对这些问题都相继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考察各地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制度设计:一是谁投资、谁所有与谁受益、谁所有并行(《黑龙江省农田水利条例》),二是谁投资、谁受益、谁管理(《湖南省小型农田水利条例》),三是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谁管理(《山东省农田水利管理办法》),四是谁投资、谁管理与谁受益、谁管理并行(《江西省农田水利条例》)。在国家层面的《农田水利条例》出台之前,这些地方性立法对小农水可能的解决路径进行了探索。南京市也于2016年1月1日实施了《南京市农田水利条例》,对小农水产权制度相关的建设、管护等内容作了规定。
在建设方面,《南京市农田水利条例》针对小农水建设中的产权模糊问题,着重构建了两个机制。一是在工程用地方面,按照小农水的不同情况,占地面积较大的小农水应当办理建设用地手续,田间地头的小农水用地则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解决。这一规定的积极意义在于,扭转了一直以来小农水建设用地不征收、不补偿的局面,明确了小农水建设的程序;即使是无法进行征收的零碎用地,也可参照办理建设用地手续的情况,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协商,对土地被占用的农户予以一定程度的补偿。这就为明晰建设后的小农水产权奠定了基础。二是在资金投入方面,《南京市农田水利条例》明确了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承担小农水的建设的主要责任,按有关规定从国有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同时,鼓励受益者和社会主体投资参与小农水建设,并由政府进行补助,从而建立多主体、多渠道的农田水利建设投入机制。与其他地区的规定不同的是,《南京市农田水利条例》不讳言政府的法律责任,而是将农田水利定性为基础性公益事业,更进一步的明确了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主要责任人的身份。从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来看,在市场化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一味的强调产权或是责任的移转,并不利于小农水事业的发展,反而会使农民产生抵触情绪,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南京市农田水利条例》积极的给出了现行体制下保障小农水建设的可行路径,同时也为小农水建设的市场化预留了发展的空间。
在管护方面,《南京市农田水利条例》确立了谁投资、谁管理、谁使用、谁受益的原则,提出针对小农水建设资金的不同来源,确定小农水的管护主体。对于社会投资兴建或政府和社会投资共同兴建的小农水,有约定依约定,一般由投资者承担管护责任,或由投资者委托他人进行管理。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投资兴建或由政府补助兴建的小农水,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管护责任。《南京市农田水利条例》作此规定的目的在于,通过使用、受益、管理三者一体的制度设计,明确了社会投资者对于小农水享有相应的权利和需要承担的义务。当然,如果仔细探究其立法基础的话,应可发现这种规定是针对受益者与社会投资者的身份重合的情形,这既是为了鼓励社会投资者不仅参与小农水建设,还要参与到实际的农业生产中来,吸引城市资本投资农业,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也是为了提高农民自身的积极性,从单纯小农水受益者转化为小农水的管理者。
4.2 《农田水利条例》的模糊与折中
相对于《南京市农田水利条例》来说,2016年7月1日起施行的《农田水利条例》一个显著的差别在于对农田水利的定性。《农田水利条例》不再强调农田水利整体是基础性公益事业,提出农田水利建设实行政府投入和社会力量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兼具公益性质和经营性质;而农田水利管护仍然具备较强的公益性质,主要由公共财政投入,并通过创新投入机制,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专业化服务组织开展农田水利管护工作。基于此,《农田水利条例》构建了全国层面的小农水产权制度体系。一方面,《农田水利条例》作为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法规,其中的多条规定涉及所有权人,本身就是对于小农水所有权的一种确认。虽然《农田水利条例》没有具体界定所有权的取得,但暗含了对《物权法》中基于事实行为取得所有权规定的赞同,即“谁投资、谁所有”。需要注意的是,《农田水利条例》没有对小农水建设占用土地的取得做出明确规定,只是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用地需求。上文已述,如果不对土地产权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回应,那么投资者所取得的小农水产权终究只是建立在沙子上的城堡,缺乏稳固的基础,也不利于调动农户的积极性。但我们仍然可以将此视为一种意味深长的沉默,即《农田水利条例》的模糊性规定允许地方立法继续探索合适的制度安排。
另一方面,《农田水利条例》在确定小农水运行维护主体时,实现了所有权、使用权和受益权的分离,规定小农水的运行维护经费应当由所有权人负担,使用权人、受益人或所有权人委托的主体具体负责小农水的运行维护。在实践中,小农水产权制度之所以难以实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明确管护经费究竟由谁来承担。在没有明确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情况下,管护经费投入不足已经成为常态。《南京市农田水利条例》是以政府作为小农水管护的主要责任人,经费也主要由公共财政支出。《农田水利条例》则是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处理办法,即在规定政府应当建立运行维护经费合理负担机制的同时,要求所有权人负担管护经费。从产权的角度来说,这是理所应当的。而且,在合理负担机制作用的前提下,即使是社会投资者,其所承担的管护费用也不会与其享有的利益出现明显的不对等的情况。更不要说大量的小农水是由政府投资建设或是财政补助建设,其管护经费应由所有权人——政府承担。这样一来,小农水的管护经费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而不影响产权制度实施的效果。
5 结 语
从《南京市农田水利条例》与《农田水利条例》的规定来看,前者是地方性立法,后者是行政法规,虽然对农田水利事业性质的认识有所差别,但在小农水产权制度的建构上,却都是针对制度改革的困局进行立法。但正如上文所述,产权制度不是万金方,让市场在小农水供需关系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仍有赖市场化机制的健全[11]。因此,现阶段推进小农水工作,可以以市场化作为切入点,但不应当回避政府的主导功能。对于具有基础性、公益性性质的小农水来说,立法只有在此基础上充分保障投资者、受益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够形成稳定运行的产权制度。
□
致谢:本文根据南京市农业生产的区域分布情况确定了样本规模和抽样比例,在南京市水利局(现水务局)政策法规处的协助下,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37份,特此感谢!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完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机制研究”课题组.我国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机制:一个政策框架[J].改革,2011,(8):5-9.
[2] 苏百义.农田水利工程产权的历史回顾与思考[J].水利经济,2000,(4):25-27.
[3] 董国华.农业水利化“重建设轻管理”困局之解[J].人民论坛,2011,(28):66-67.
[4] 周晓平,郑垂勇,陈 岩.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动因的博弈解释[J].节水灌溉,2007,(3):54-57.
[5] 艾琳·麦克哈格,巴里·巴顿,阿德里安·布拉德布鲁克,等.能源与自然资源中的财产和法律[M].胡德胜,魏铁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67.
[6] 刘小勇,王冠军,王健宇,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研究——进展情况及问题诊断[J].中国水利,2015,(2):11-13.
[7] 李祎恒,邢鸿飞.论征收补偿中财产权法制保障的基本模式[J].南京社会科学,2014,(5):99-105.
[8] 王英辉,薛英焕.我国农村水利设施产权困境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3,(9):168-172.
[9] 吴清华,冯中朝,李谷成.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与管护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以灌溉设施、农村公路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5,(4):248-255.
[10] 张嘉涛.对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的反思[J].中国水利,2012,(14):35-38.
[11] 俞雅乖.“一主多元”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供给体系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2,(6):5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