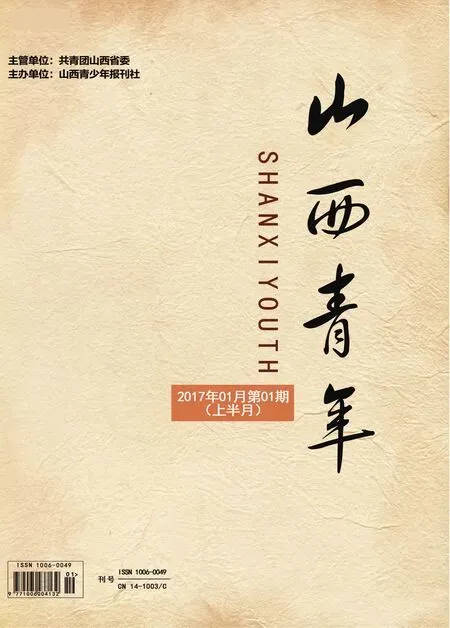周紫芝的精神世界与人格悖反
李国跃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浙江 横店 322118
周紫芝的精神世界与人格悖反
李国跃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浙江 横店 322118
周紫芝从早年的长期贫困、对政治疏离,到中年时期的积极上书、体察百姓之苦、用兵之险,到最后晚年给秦桧父子写歌颂谄谀的诗文,其中精神世界的变化一脉相承,这种人格的悖反是现实与政治对人性的摧残。
周紫芝;精神世界;人格悖反
周紫芝,字少隐,号竹坡,宣城人。中青年沉沦下潦,晚年得官。在南北宋之际,他的诗词均负盛名。沉沦下潦的生活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创作极丰,一生留下大量的诗篇,他用文字记录了一个士大夫的欢愉愁怨的心灵辙迹。本文着力于从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和晚年时期探讨身处在两宋之交周紫芝的精神世界与其一生初衷与晚景悖反的原因。
一、青年时期
早在周紫芝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无书不读,尤其喜欢诵读前人的诗文,甚至为此耽误了学业,写成的文章和古人相比也毫不逊色。有一次老师称赞他的文章,小小年纪的他竟然就说出了“这样的文章得名是够了,但我要得就得万世之名”的豪言壮语,可见其内心的见识与志向。
然而他所生长的年代又是北宋政治最黑暗的年代,北宋的新党和旧党先后上台执政,每次上台就对对方进行清洗,新旧党争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周紫芝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崇拜屈原,因为他欣赏屈原那种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气节以及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舍我其谁的气概,尤其是屈原对祖国与朝廷的忠贞,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以至于多年后,他在《哀湘累赋》还表达了对于他的无限敬仰。他同样追慕“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那种亦官亦隐,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气同样为他所激赏,因为一生贫贱的他和陶渊明实在有太多的相同之处了。陶渊明对生死穷达的看法,无不和他心心相印,他对物质的要求很少,他对精神的要求更多。他诗词文赋无一不精,学问自承元祐学术,和苏黄门人张耒、李之仪渊源极深,他温和的性格和深刻的思想与苏轼如出一辙。但在“党狱十年犹未开,谗口嚣嚣苦相訾”的严酷政治环境中,整个士林都噤若寒蝉,他也只能选择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禁锢带来的只可能是反弹,他在诗文中还是留下了对整个时代的呐喊。公元1117年,他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在舟上看到了为宋徽宗运送的花石纲的大船在河上一艘接着一艘,老百姓为此毁家破业,他不禁泪下沾裳,想要以士子的身份上书言事,规劝皇帝,但想到上书后肯定要遭到杀身之祸,对国家也于事无补,只好默默忍受,痛恨自己的懦弱。
二、中年时期
中年时期,他适逢金兵气势汹汹吞辽灭宋,黎民涂炭,宋室南迁,在胸中被积压已久的他积极上书言事,在那篇著名的《上皇帝书》中,他为高宗建言献策,指出了当时政治的三个弊端,鼓励高宗树立信心,吸取徽钦二帝的前车之鉴,信任和倚重大臣,不被战场上的暂时胜负所动摇,不被朝廷上小人的谗言所迷惑,力排众议,乾坤独断。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他跟所有的人一样,也渴望出现像唐朝郭子仪一样的人物,勘定祸乱,“三关故地何时得,二帝征銮几日回”,他日夜叹息,渴望收复失地,“微生一蝼蚁,播越念皇舆”,他每饭不忘君恩,渴望迎回二圣,“万夫各解甲,四海均清凉”,他时时祝祷,渴望天下太平。当闻知太学生陈东因上书言事被杀后,他愤而写下了《次韵韦深道哭陈谏议》:“自是群奸误圣君,初心岂愿作忠臣。平生劲气埋黄壤,当日嘉言在紫宸。谏议裂麻方伏閤,诸公鸣玉自垂绅。向来六子俱诛灭,此道于谁较屈伸。”他痛斥群奸蒙蔽圣听,面对大义,满朝文武竟然无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而陈东作为一介士子,他的勇气又是何等让人钦佩。
然而宋室南迁的这些年,他自己却不断地颠沛流离,躲避兵祸,前后三次躲进深山,甚至以落叶覆盖自己的身体,痛苦的经历让他先前的血气之勇慢慢转变成了对现实的冷峻思考,在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控诉了战争对人的伤害,“白骨在草间,零落不相属”,战争使得人口凋零,“田家终岁负耕糜,十农养得一兵肥”,朝廷豢养庞大的军队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最后直接发出了“莫养兵,养兵杀人人不知”的呐喊。这也就为他晚年得官时更倾向和议政策,甚至为颂扬秦桧父子埋下了伏笔。
三、晚年时期
晚年的他看淡了功名,曾感慨“我生无誉亦无毁,老去功名薄如纸”,他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无誉无毁”,但由于他给秦桧父子写了大量的阿谀谄媚之诗,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好的名声。在六十一岁那年,他终于当了一个小官,这时候绍兴和议已经达成,高宗生母韦太后被放南归,朝廷下诏令词臣作歌诗,满朝文人纷纷秉笔。也就在这一年秦桧生日那一天,他也加入了歌颂的队伍,开始了第一次的献诗,此后几乎每年秦桧的生日,他都要献诗。当然他的文采也慢慢得到了秦桧的赏识,三年后,他以非进士出身的身份担任了六部架阁官掌礼兵部。此后他一年三徙,担任了枢密院编修官,当时秦桧的儿子秦熺担任枢密使,成为了他的上级,幸运来得太快,他自然对秦桧父子感恩戴德。
慢慢地他交际的圈子也扩大了,清要的职务让他常常和同僚们结游西湖,诗酒留恋,但是上层的斗争更加激烈,官场上的勾心斗角让他有些不适应,在临安呆了十年后,他最终知道这不是自己想要的,自请外任出知兴国军,离开帝都,一路上他心情愉快,访求前贤留下的遗迹,写下了大量诗篇,到了兴国后他仍然保持了少年时无书不读的习惯,创作量有增无减,最后在他七十二岁那年,他辞职归隐庐山,两年后去世。
四、初衷与晚景之悖反周紫芝的一生,从胸怀大志到疏离政治,从积极上书到谄谀秦桧,他的一生有太多的悖反。他出身寒士,少年时也曾经参加科举,儒家的学问内以修身,外则经世济民,这是根植于所有文人士大夫骨子里面的。但随着屡试不第,从政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他干脆放弃了,但他又不事产业,虽然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但生活的贫困也在折磨着他。绍兴六年春,同乡友人徐伯远见他清寒,赠送他五十亩田地,但可悲的是周紫芝却连耕田的耕牛都没有,无法耕种,自己又无力购买,不得不再向这位朋友再求取一牛。不得不承认长期生活的贫贱会使人失去一些人格的自由。
自从建炎元年上书无果后,他就奔走各地,过着类似清客的生活。最后到达临安,获得一官半职的时候他是很知足的,俸禄虽薄,起码不用再到处奔波了,但监户部曲院的官职实在不合自己的期待,所以他才那么渴望再上升一步,他在诗中对这时候处境的描述是“欲归归尚难”,何其悲也。然而随着朝廷与金和议的达成,朝廷刮起了一股歌颂秦桧功劳的潮流,他便也成了被潮流裹挟的大多数了。以他的才华,写这种诵诗当然不是难事,虽然未必管用,至少可以得到宰执的好感。
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他性情温和,与苏门学子渊源深厚,反对那种激烈的变革和主张,主张政治的平衡与稳定,所持立场更倾向于平民,孟子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长年的身处下潦,使得他对老百姓的苦难有着更深切的了解,所以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他没有像某些大臣一样盲目主战,他更侧重与南宋朝廷自修内政。他对当今局势的分析是“使子房为谋臣,侯公为说士,犹未足以决胜负而定安危也”。他对士兵的骄惰和懦弱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他在《输粟行》中写道“良农养兵与胡竞,胡骑不来自亡命”,他本人则亲身经历了溃兵变成盗贼对人民的残害。所以宋金和议在他看来虽然面子上不好看,但是符合老百姓和国家的利益,所以高宗和秦桧的和议政策在他那里并没有心理障碍,更何况他以非进士出身的身份任枢密院编修官,知遇之恩又岂能忘怀,所以每年为秦桧写那么多“老而无耻,贻玷汗青”的贺诗既是职务的需要,也是他内心对秦桧的真实感激。十年的京城生活虽然安逸,但也使他再次看清了官场的险恶,不断用诗词去寻求慰藉,所以后来他自请外任,这时他的创作又开始喷薄,他的天性本身就属于自然,现在“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终于做回年轻时“不忘初心”的自己了。
I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