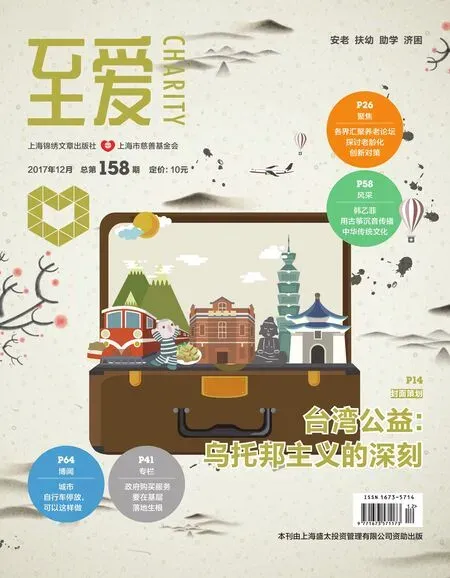政会脱钩改革中地方政府何为—以A市B区为例
文|周俊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自2015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脱钩总体方案》)以来,各地纷纷开展脱钩改革,从相关报道来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脱钩改革都进展顺利,成效显著。然而,研究通常认为,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中总是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如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导致政策执行偏差,又如政策制定者与政策目标群体之间过长的距离可能会导致目标群体抵制某些具体的政策内容。那么,这些问题在政会脱钩这场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中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它们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又有哪些问题是与地方政府的执行行为直接相关的?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于2017年6—7月间对A市B区的政会脱钩改革进行了调查,走访了相关管理部门、部分第一批脱钩试点对象(之所以称脱钩试点对象,是因为第一批脱钩名单中有并不属于行业协会商会的社会团体)和部分尚未被列入脱钩名单的行业协会商会。
一、地方政府是脱钩改革中的积极行动者
为紧跟中央和A市政府脱钩改革的步伐,B区于2016年7月召开了第一批脱钩工作试点会议,公布了30多家第一批脱钩试点名单,其中既包括行业协会、行业商会、联合会、促进会等经济性社会团体,也包括行业学会、研究会等学术性社会团体。
脱钩名单的确定经过了自下而上申报和民政部门最后确定的过程。30多家脱钩对象中有近1/3并非主动申报,而是由政府“选中”成为脱钩对象。另外,30多家脱钩对象中属于“直接登记”(A市早在2012年就对部分行业协会商会实施了直接登记政策)的占到80%以上,仅有为数不多的属于“双重管理”,即存在业务主管单位。仍为“双重管理”的脱钩对象中仅有少数几家与业务主管单位有财务或人事等方面的关联。
为保证脱钩改革的顺利进行,B区民政部门制定了专门的脱钩工作方案,并派专人电话联系每家脱钩单位,要求其按时填报和递交相关材料,以及进行相应的组织变革。组织变革的内容主要包括“五分离、五规范”中脱钩对象可以自行操作的部分,比如如果有在职政府公务人员在协会商会兼职,那么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辞去公职或者辞去社团职务;又如要求脱钩对象在规定时间内修改组织章程并报送民政部门审核,等等。
召开座谈会、培训会,开展课题研究等是B区政府推进政会脱钩工作的另一重要举措。民政部门希望通过各种会议,使脱钩对象认识到脱钩改革的重要意义,提高参与积极性。B区民政局还开展了多项与脱钩改革相关的课题研究,主要包括对行业协会商会综合监管、内部治理革新等内容,课题研究被认为能够帮助管理部门及时掌握脱钩改革中的各种情况,为下一步工作做准备。
从总体上看,在A市B区政会脱钩工作中,政府扮演着积极的政策执行者的角色,一方面落实中央政策安排,另一方面又对政策进行了地方性解读。在政策执行过程中,A市B区投入了大量资源,尤其是权威资源。
2017年5月,B区开始启动第二批脱钩试点工作,但遗憾的是,响应此批脱钩试点的行业协会商会寥寥无几,而与此同时,第一批脱钩试点对象不断反映出各种问题,B区政府面临大量难题。
二、脱钩对象对地方政府行为的评价
行业协会商会对中央的总体脱钩方案无不持欢迎态度,但是,在地方的政策执行中,对那些已经进入脱钩试点名单的脱钩对象来说,脱钩改革并不那么令人欢 迎。
在A市B区,第一批脱钩试点名单上被“点名”脱钩对象无不表示对这一结果非常无奈:“我们没有任何准备。”“我们不知道为何被选中了。”而其他组织也多少觉得成为第一批试点单位有些突如其来:“要我们先脱,那就先脱吧。”
在“脱”什么的问题上,第一批脱钩试点的30多家对象中有近2/3认为:“我们没有什么可脱的。”“我们本来就没有业务主管单位。”“我们从来没拿过政府一分钱,也没有政府的人。”于是,它们能够做的就是配合民政部门的各种要求,比如花一个多月时间填写各种表格,按新的要求变革章程等。
对于确实需要脱钩的组织,A市B区脱钩工作的重点是“五分离”。按政府要求,有的脱钩对象搬离了政府提供的办公场所;有的不再接受政府的房租补贴;有的清退了政府兼职人员;有的不再与业务主管单位合作开展培训等项目。对此,脱钩对象也并非没有意见,尤其是对政府不区分情况,统一定制变革要求,以及不为“分离”设置缓冲期的做法非常不解。比如关于办公场所,不止一家负责人提出:“A市房租这么高,协会刚脱钩,还没有找到业务,如何生存?企业补办尚能获得一些补贴,协会为何不能?”
“五规范”同样是脱钩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A市B区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尚不到位,脱钩对象一直不清楚“五规范”的具体内容。一些实施了“分离”的组织负责人很迷茫:“现在业务主管单位什么都不管了,我们有事情找谁?政府怎么管我们?有没有新的管理方案和工作流程?”更让他们觉得不可理解的是,原来与业务主管单位合作的一些项目大多也被收回去了,“那以后还有没有合作”“合作关系怎么建立”等问题在访谈中反复被问起。
A市B区第一批脱钩对象对脱钩中政府部门的一些具体做法更是颇有微词。一家行业协会的理事中有两名在职公务人员,民政部门要求其在一个月内予以清退。该协会负责人说:“协会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要清退理事也必须经过会员代表大会,能不能等大会召开?”民政部门的回答是否定的。于是,该协会不得不违反协会章程行事,对此,该协会负责人评价说:“这就是行政权力的任性。”
从总体上看,作为脱钩政策的目标群体,脱钩对象基本没有政策参与权和发言权,处于明显的被动状态。脱钩对象虽然在形式上配合政府要求,但对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却多有质疑和批评。
三、脱钩改革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及其影响
政会脱钩改革的目标是厘清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使行业协会商会成为依法自治的社会团体法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规范化的政会关系。A市B区对中央政策的执行不能说背离了这一目标,但在一些方面却存在偏离目标的问题。
首先,A市B区政府单方面圈定部分脱钩试点对象,将与政府无依赖关系的行业协会商会、非经济性社会团体纳入脱钩试点名单的做法,暴露了其“指标型”的政策执行导向,即政策执行并非完全围绕政策目标,体现政策精神,依据政策内容,而更是要取得执行效果(尤其是数量上的效果),以便向上级汇报和获得上级肯定。
其次,A市B区政府无论是在政策执行方案的制定过程中,还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都没有充分考虑目标群体的复杂性,存在方案“一刀切”、实施行为专横甚至违法等问题。比如强制要求行业协会商会不经会员代表大会同意清退其理事会成员,即侵犯了行业协会商会作为社会团体法人的权利。
再次,脱钩理应是一个“分离”与“规范”同时进行的过程,脱钩后应如何监管行业协会商会,如何规范行政委托和职责分工关系等问题,应该在脱钩试点开始之前就有基本方案,这样才能使行业协会商会在“分离”后较平稳而快速地进入到“规范”期。A市B区政府虽然也开展了与“五规范”相关的研究与政策拟制工作,但直到第一批脱钩试点结束,也没有就规范问题拿出正式意见和方案。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A市B区政府在选择性执行脱钩政策,即积极执行简单易行、更易出效果的政策,而对同样重要但执行难度大、难以出效果的政策进行模糊化处理或延后执行。
对脱钩政策的目标偏离直接影响脱钩后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甚至影响行业治理。脱钩政策中的“脱”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作为目的的“脱”是要建立规范的政会关系,作为手段的“脱”是要促进行业协会商会自主发展,若规范的关系无法建立,发展也难以谈起。遗憾的是,A市B区的脱钩工作重“破”甚于“立”。“分离”工作迅速有力,而“规范”工作相对迟滞,致使大部分脱钩后的行业协会商会资源丧尽而又缺乏缓冲期,并因此陷入发展困境,与此相伴随的则是行业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化自主治理,政府在行业治理中的作用得以扩 张。
四、脱钩改革中需要建立共赢机制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A市B区政会脱钩改革中,政府在某些方面积极而强势,在某些方面则缺乏作为,脱钩改革的总体进程并不那么理想,脱钩政策目标也并非完全按中央政策在推进。这提出了讨论脱钩改革中地方政府的行为限度和行为方式的必要性。下面就脱钩改革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定位简要地提三方面建议:
1.作为中央政策的地方执行者,地方政府有权对脱钩政策进行地方性解读,从而制定具体的政策执行方案,但这些工作一方面应以中央政策精神、政府目标和基本政策内容为前提;另一方面应以“法治”为基础,不得与现行法律法规相违背。
2.选择性政策执行虽然能带来短期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不但影响政策效果,而且会减损政策执行者的权威。地方政府应充分认识“分离”与“规范”的依存关系,在脱钩政策执行中集中精力攻克“规范”这一政策难题,在政策实施之前制定明确而具体的政策方案,以避免部分行业协会商会“一脱就死”。
3.目标群体是否配合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地方政府在脱钩政策执行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行业协会商会这一目标群体的复杂性,并通过各种渠道听取、搜集目标群体的政策建议和意见,以此为基础拟制政策执行方案,及时对执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
概而言之,脱钩改革不是政府的独角戏,正如《脱钩总体方案》中提出的,政会脱钩改革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和需要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有两个主体,这两个主体需要密切配合、协同共进,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