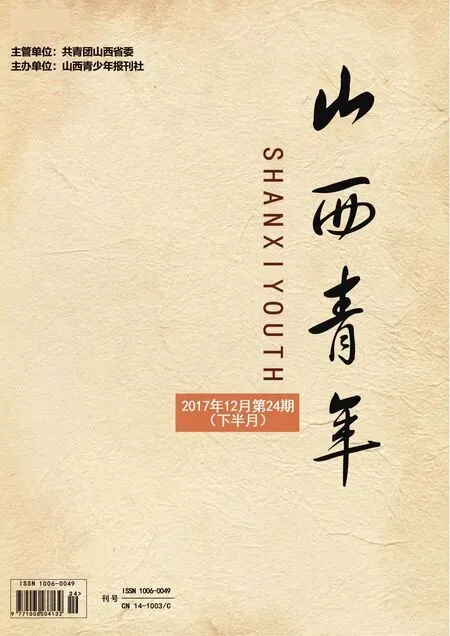浅析《水在时间之下》的生死本能
陈虹宇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浅析《水在时间之下》的生死本能
陈虹宇*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方方《水在时间之下》描写了汉剧名伶水上灯从被弃到成长为红极一时的汉剧名角,经历种种后,最终归于巷陌的传奇一生,其中的跌宕起伏实际上是一次次生与死的激烈交锋。方方用集中而猛烈的戏剧性冲突将小说中的人物逼至极端的环境,淋漓尽致的展现人在面对生存困境的本能选择。本文仅从生死本能的角度浅析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
《水在时间之下》;方方;生存困境;生死本能;水上灯
作为女性作家,方方一向对女性命运多有思考和关注,在2008年出版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中,作者秉持了一贯的传统,但选择了将一个女戏子的独特人生作为叙述对象,这个选择便奠定了这本小说叙事的波澜起伏。小说写了唱汉戏的女艺人“水上灯”的传奇人生,她的出生便是伴着母亲早产,父亲离奇惨死,一系列的偶然把一个本应生活优渥的富家千金抛向了世界的底层,开始了多舛的一生。在经历了无数坎坷之后的她也赢得了自己的光华,却在这个极端之下,她断然地抛开一切,隐于巷陌,孤独终老。方方在塑造“水上灯”形象之际,同时也塑造了陈仁厚、水文、万江亭、玫瑰红等一系列在生死之间挣扎的人物。
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中,表述了“生本能”和“死本能”这一组相对的概念,提出他所认为的整个有机生命都具有普遍性能,即本能是什么,“本能是有机生命中固定原有的一种恢复事物初始状态的冲动。”接着,他又提出了:“一切生命的最终目标乃是死亡。”这也表明了,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的最终表现和最终归宿是死亡,正因为生命的本质是从无到有的,它的终结也必然是从有到无。生命追求的最终是死亡,回到最初的状态——无。由此可知,所有的生命都具有死亡的本能。方方的小说中,除却对女性生存的思考,生与死亦是她不变的命题,在生与死挣扎的过程中,她擅于将人置于极端,尤其是极端的恶境,在这样的艰险中审视人对于生死的选择,她喜爱生的艰难,但对于死,她似乎赋予了更多的宽宥,因为生命的本质是死,死亡是人一生中必经的极端,而这一种极端又含着一种平静悠然,不似生的苦苦挣扎,“死”在方方笔下是美好的,她将死亡的名额分予了她所偏爱的、悲悯的人物:在安定与浮华中挣扎的慧如,生性懦弱但心地淳厚的杨二堂,为爱不顾一切的万江亭,陷于亲情与爱情沼泽中的水文,这都是方方对这些人物命运的圆满终结:既然活着无法摆脱纷乱,那么死去,便是对生命的升华。
“水上灯”的养母厌倦贫穷的下河丈夫,又得知自己以为的命运的“绳索”仅仅是玩弄她,她在大水来临之际选择了以洪水洗清她的屈辱,洗净她的不忿,在水中选择了死亡;杨二堂在经历了妻子离世、养女卖身之后,心中绝望愈甚,他成了行尸走肉,于是,“这天半夜,到底杨二堂死在了医院,他没给水上灯留下一句话”;对玫瑰红一往情深的万江亭,面对戏迷对他结婚的不满预想时不置一词,面对强取豪夺的肖锦富时亦是毫无畏惧,却在爱人玫瑰红结婚当天,选择了割腕;不知情的水上灯的大哥水文疯狂的喜欢上了水上灯,纵使其后知道了一切真相,这份爱也只是掩埋而非消逝,他“一遍遍回忆着他认识水上灯的整个过程”,最终死在了乱刀之下,“全身没有一块好皮,死的好惨”。死亡并不可怕,它反而将人的生命推至了一个真正的永恒,所有的爱恨情仇在“死亡”之下都得到了宣解。方方在小说中极力渲染生之艰辛,活着比死更难受,死去的人可暂得宁静,而生的人却还要在浮华闹市中苦苦挣扎,他们挣扎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而所有的对错都在角色就要迈向死亡时,他们又获得了平静,故而,即使是死者,他也是永生。在生命最终的归宿中,他们面对的是有望的欢乐和光明,这种生与死的对立,让人在对生绝望时,又产生对死的向往。
自然,与死亡本能相对应的是人类同时也拥有生之本能。如果说死亡是最终的归宿,是必然的结果,那么,生的本能就是不顾一切地阻止人顺利的死去,也就是说,生与死的矛盾让生命的历程更加的复杂,生存的形态也因为这种本能的作用而变得丰富多样。方方的小说便是在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拼搏的过程中构建出她的叙事模式,超我是死亡本能占主导作用的,代表着罪感,是良知或内在的道德判断,然而自我却以生存为目的,唯我原则使得人们排斥他人,以获得自身的生存。在生的欲望阻止死的本能过程中,必会发生冲撞而人的斗争性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显现了一种残酷冷血的现象,这时候,超我退却,剩下的往往是艰辛的生存。在开篇中水上灯说:“她叫水滴。一滴水很容易干掉,被太阳晒,被风吹,被空气不声不响消化,结果我这滴水像是石头做的,埋在时间下面,就是不干。”她的一生,便是与人“斗”的一生。甫一出生,她便知道“自己到这世上来就是与它作对”。母亲的早产以及父亲对母亲的宠爱引来了大房的不满,父亲为躲避争吵,抱着二哥出去游玩,结果竟是横死街头,她的出生与父亲的死亡便是“斗”;而母亲“为了这份富贵和安宁,她什么都肯忍”,于是在她的生存和女儿的命运之中,她选择了自己,抛弃了水上灯,这也是“斗”;水上灯幼时随着养父杨二堂下河却受到了来自二哥水武的欺辱,“水滴对有钱人的仇恨虽是从这天开始;而同时,水滴对有钱人的向往也是从这天开始”,这种痛恨和向往的矛盾伴随了水上灯的一生,她能在养父离去时毅然卖身,也能在被杨小棍出卖时果断逃脱,她在生与死中,从来都是选择了生,她的天性中似乎没有死的本能,却又一直与“死”较劲,她的婚姻表面上是自主选择,本质上却是又一次对生的选择。在水上灯的角色塑造上,方方给了她极大的自由,她只是依据生存本能行事,水上灯想活,想更好的活,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时,她又想着怎样更好的活,追求精神上的更大的自由,她对于是非善恶的一贯追求,对于民族大义的不舍不忘,对于师恩养恩的念念在怀,这些都让她活下来了,并且是更好的活。在现实逼仄中,水上灯似一朵浮萍般,随处生长,却又有着浮萍所没有的坚韧。在小说中,可以发现贫穷固然是生存的一道枷锁,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必然,但方方在其中并未加入个人的褒贬,不管是水上灯卖身葬父,或是为了躲避水文而投向张晋生的庇护,她都不置一词。她始终都有一种人性的关怀,虽然写出了人的本能,写出了人的本我的无节制欲望化,但她又能加入自己的愿望,期待超我对自我的审视,所以,在小说中,水上灯的身边总是有一盏明灯的陪伴,从一开始的杨二堂、菊妈,到万江亭、余天啸、陈仁厚,他们都用自己独有的人性普照着水上灯因生存而滋生的罪恶,从而纠正,让其回归。
弗洛伊德等人看来认为,生命的起源于目的都是为了死亡,而他所说的死的本能并非要将个体领向死亡,而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因此生与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方方笔下,死亡的模式并不拘泥于一种,小说在结束时,所有的仇恨,所有的怨憎都在死亡面前消失殆尽,显然,方方把死亡看成是人生最终的美好归宿,是人们的最终结局。但她仍然认为死亡是严肃的,历经磨难的水上灯在极恶或是极美中丝毫没有想过以死来告别这个世界,在她看来,生便是希望,这一种本能驱使着她阻止着死的进程,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在对抗中又衍生出一套完整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它们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水上灯用命与周上尚打赌,在她眼里,自己的命不如自己执着的信念重要,但她又为着这一赌注奋力拼搏着,在生与死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方方让水上灯的每一个预言或多或少的得到了印证,而她的生死本能也在这一次次的预言中相互搏斗,这实际上更加圆润了水上灯的人物性格,丰富了其人生历程。而一个人的生死本能的斗争也必将牵扯入许多,水上灯从未动手害死过任何人,但每一个人的死亡或直接或间接的又与之有所联系:她的父亲,她的恋人,她的丈夫,她的姨母,她的养父母……这些人的死亡固然有死的本能的作用,但又何尝不是水上灯生的本能与他人的生存的碰撞?
生死本能在人的一生中绝不是孤立存在的,生本能代表着潜伏于个体生命中的进取性、创造性,是一种向上的蓬勃的生命活力,而死本能则是对于这些的破坏性。当水上灯丧失了她的爱,她的恨,丧失了所有时,她也丧失了生的本能,她选择了隐于巷陌,她“洗净脂粉,脱下绸缎,换下高跟的鞋子,剪短了头发,着一身蓝布褂出没于陋巷中”,与其说她在此时死的本能占了上风,不如说她生的本能已然湮灭,“这世上没有什么可以抛弃我,只有我抛弃它”,她放下了所有的繁华,也挣脱了所有的束缚,她的生死本能在她选择归隐的那一刻,已经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
[1][奥]弗洛伊德(Freud,S),著.自我与本我.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4-9.
[2]方方.水在时间之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3]尹文丽.精神分析视野中的方方小说[D].华侨大学,2013.
陈虹宇(1994-),女,汉族,四川达州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
A
1006-0049-(2017)24-19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