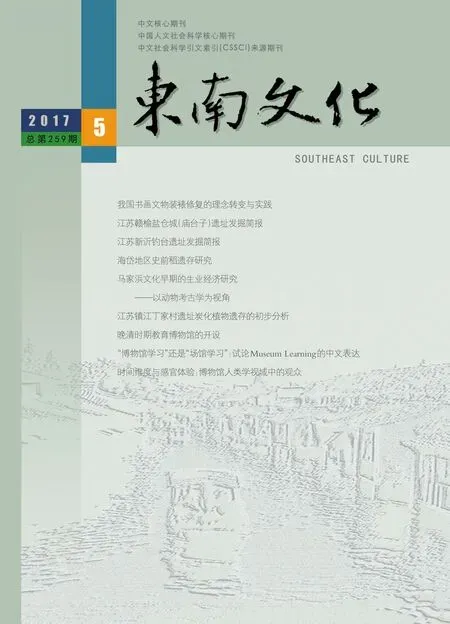时间维度与感官体验:博物馆人类学视域中的观众
潘 宝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 云南大理 671003)
时间维度与感官体验:博物馆人类学视域中的观众
潘 宝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 云南大理 671003)
博物馆通过展览将物品建构为展品的时候,也为观众的感官体验创造了条件。在博物馆空间中,物品以展品的形态影响了其在人类社会中的绝对时间;而观众这一暂时性的身份与地位,使得其在博物馆空间中的感官体验过程是在其相对时间中完成。观众参观时间的暂时性,使得展品在博物馆空间中的存在是以刺激观众感官体验为前提;观众感官体验过程中的展品,是物品的绝对时间在现代性社会中延续的一种形式。而博物馆与公众之间距离的缩小,亦使得博物馆通过展品与观众试图重构“物”与“人”的关系。
展品 策展 时间维度 感官体验 博物馆人类学 观众
一、博物馆的时间维度与观众的感官体验
博物馆通过展览将物品转变为展品,即通过博物馆的作用机制,物品脱离了其原有的文化生境,以展品的形式再现于博物馆空间中。博物馆展品可以超越观众的生命历程,与某时某刻的观众处于同一时间维度中。物品在转变为展品的同时,亦在通过观众的参观行为,使得展品被观众所凝视(gaze),展品成为某种珍宝、艺术品或某种承载历史记忆的符号。伊万·卡普(Ivan Karp)指出:“在珍品艺术博物馆中展览的所谓的原始艺术品,是被隔离在玻璃柜里的,以其最少量的信息,凸显了艺术是与欣赏博物馆的展品有关,这与艺术被假设为参与博物馆策展类似。”[1]当观众身处博物馆外部空间时,其由现代性社会所主导的身份与地位,影响着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对现有物品的认知;而当观众身处博物馆内部空间时,能够刺激其感官体验的各种展品,都因“观众”这一暂时性的身份而被赋予了神圣性意涵。这种神圣性指的是观众将其参观博物馆视为与现实生活相异的一种感官体验过程,将展品视为一种满足其文化需求的物品。
(一)展品的长久性与观众的暂时性
展品的长久性存在与观众的暂时性存在这一无法弥合的时间差异,使得“物”与“人”两者无法因为时间的延续而永恒共存。因为“人”对“物”所产生的作用,使得观众在凝视展品的同时,亦将社会中的个体与博物馆中的观众,建构为两种不同感官体验过程中的主体。现代性社会无法解决个体对物质长久占有的欲望,即“人”对“物”的绝对占有,这种占有在博物馆作用下转变为个体对某一展品的凝视。
“人”与“物”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异,通过观众对展品的感官体验,在有限的时间维度中共存于博物馆空间。日本人类学者山口昌男(Masao Yamaguchi)曾指出:“在艺术博物馆与文化—历史博物馆中,物品一般按照它们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顺序来陈列。在时间上相互关联的物品,转而被置于同一个空间情境中,这种重新组合,铭刻于观众的记忆里。博物馆的这种置换机制就像机器一样将时间转变为空间,从而确保了博物馆作为社会记忆的机器而被利用。”[2]这就意味着,博物馆空间中的物品可以作为长久的“物”而存在,即对于博物馆外部空间来说,这样的“物”拥有绝对时间,从其被博物馆收藏的那一刻起,“物”被博物馆保护,以便人们利用。而对于博物馆内部空间的观众来说,这一身份在存在之初就决定了其只能作为短暂的“人”而存在,即这样的观众拥有相对时间。从其进入博物馆空间之时,观众的身体与感官被博物馆控制与吸引,每一个体在体验其成为博物馆观众的同时,也在体验着由博物馆展品所带来的感官刺激,这种体验是在其相对时间中完成的。因为个体无法与物品长久共存,且个体之间感官体验的差异,也使得这种相对时间造成了展品无法对观众产生相同的效果;同样,观众自然也无法与展品长久共存于同一空间中。这种时间上的差异造成了博物馆在将物品转变为展品的过程中,注定要以观众的感官体验作为其策展的重点之一。观众的感官体验赋予了博物馆展品现实的社会意义,也决定着博物馆展品在多大程度上以“物”的形式反作用于“人”。
博物馆通过展品反作用于观众,既可以表现为通过博物馆所生产的知识教育观众,亦可以表现为通过博物馆的策展活动控制观众的身体、意识,也可以表现为凸显展品的诗学与政治学等价值,从而在心理层面影响观众对展品的认同,更能够将观众的感官体验凝聚于由展品所建构的参观过程中。但这种反作用并不长久,当观众走出博物馆,随着观众这一身份的消失,展品反作用于观众的效果也随之消逝。而恰恰正是在观众参观博物馆这一暂时性的行为中,博物馆在展品与观众之间,建构起了能够影响观众的视觉与听觉,甚至是触觉、味觉、嗅觉等感官体验的活动。肯尼斯·哈德森(Kenneth Hudson)曾指出:“在交流中感官是很重要的。在正常情况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有规律地使用我们的五种感官,但是在博物馆中,就像是在看电影或者看电视,只剩下视觉和最小程度上的听觉这两种感官在发挥作用。结果,博物馆的展览和观众的参观都过于理智化了。我们没有机会调动我们的触觉、味觉和嗅觉。”[3]这种部分感官缺失的体验活动,将展品与观众之间的时间差异进一步拉大而非缩小。也就是说,博物馆空间的存在,并非是在弥合“物”与“人”之间的时间差异,而是进一步固化了展品存在的长久性与观众存在的暂时性,即博物馆空间有可能既保证了展品存在的长久性,又保护了物品以便能够长久地被博物馆利用;观众身份的暂时性使得展品长久性的存在成为可能,观众是碎片化的观众。
(二)展品的绝对时间与观众的相对时间
碎片化的观众意味着个体在转变为观众的同时,亦被博物馆塑造为不同的个体,且被不同的展厅、展品区隔,被博物馆空间碎片化为单独的个体;而每一个体在凝视展品时,不同的观众基于自我的感官体验,以自我的方式理解与解释着展品。这种自我的方式,依托于观众自我的相对时间,基于自我的价值判断,以个体的方式有选择性地凝视不同的展品。面对展品,在个体层面上,其感官体验也有可能被展品所构建的展览碎片化为个体的某种心理作用,从而扩大某一种感官的效用。威斯特兰娜·阿尔佩斯(Svetlana Alp⁃ers)曾指出,“衡量一个博物馆是否成功的方法,应该看观众是否能够自由且充满兴趣地在博物馆中游走,而非在观众与展品之间放置类似普及型的耳机等设备,从而充当说教者的角色”[4]。这就说明,暂时性的观众意味着当个体将自我的有限时间消费于博物馆空间的时候,展品所彰显的“物”的价值因其绝对时间的存在,而与观众这一“人”的角色是不平等的。相对于长久存在的展品,观众的身份注定是暂时性的;当观众离开博物馆并再次成为现代性社会中的个体的时候,展品亦失去了观众的凝视,展品再次成为了博物馆的物品。但展品绝对时间与观众相对时间的相互影响,并不因为某一观众离开博物馆而结束。对于博物馆的展览来说,展品的绝对时间保证了物品拥有不断进行凝视的观众,亦保证了“人”对“物”的绝对占有与控制,这种占有与控制不仅仅体现在感官活动中。展品不因某一观众的离开而消逝,亦不因个体生命历程的结束而终止其对“人”的影响。因此,博物馆的展品在影响观众感官体验的同时,亦影响着博物馆的时间维度。
博物馆的时间维度既通过展品的绝对时间影响着观众的感官体验,亦通过观众的相对时间影响着展品的策展。因为博物馆的存在,“物”在社会中的角色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不论如何变化,对于博物馆来说,各种形态的“物”的持续存在,都与其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绝对时间相关。人类社会创造了“物”、生产了“物”、使用了“物”,而当某一“物”历经绝对时间的打磨,不再被人们生产、使用的时候,即将濒临消逝的时候,尤其是在经过社会动荡、战争等影响之后,人类活动对自身创造的“物”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后果,激起了人们延续“物”的绝对时间的冲动。人类社会又会收藏“物”、保护“物”、传承“物”、展览“物”,“物”的占有者的角色亦在发生变化,其由最初的创造者、生产者、使用者,演变为收藏者、保护者、传承者。人类社会对“物”的占有欲望在博物馆时间与空间的作用下,使得人们期望通过博物馆来控制“物”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绝对时间,试图决定某一“物”何时被保护、被传承、被展览,而这种控制也进而延伸至观众的感官体验过程中。
二、观众感官体验过程中的博物馆展品
从展品的绝对时间来说,观众在博物馆中凝视“物”的同时,往往也意味着这些“物”已经脱离了其最初的创造者与使用者以及与其相契合的历史背景,这样的“物”需要博物馆这样的机构为其建构新的文化生境,以便“物”继续存在于现代性社会中。
(一)现代性社会中观众感官体验的过程
对于观众来说,其感官所体验的“物”有可能只是博物馆这一机构为了赋予“物”新的表征(representation)而重新建构的“物”。但从观众的相对时间来说,观众在博物馆中所能凝视的“物”,往往意味着这些“物”是艺术品、是文化遗产。这些“物”因为博物馆空间的存在而存在,因为观众的感官体验而成为活态的“物”。但由博物馆所建构的“物”并不意味着对于每一个观众来说都具有同样的感官体验过程,观众的感官体验往往具有相对性。
观众进入博物馆,意味着观众进入由展品所建构的空间中,通过感官体验着现代技术手段建构下的各类展品,特别是在某些特殊类型的博物馆中,观众不仅可以观看、聆听,甚至可以嗅闻、触摸、品尝展品,观众与展品之间的距离也在逐渐缩小,这意味着博物馆与“人”的距离正在改变。博物馆由最初的私人博物馆到公共博物馆,由室内博物馆到室外博物馆;由观众与展品保持一定的距离到观众与展品的亲密接触;博物馆的观众也由最初的权贵阶层扩展至现代性社会中的大众,由专业人士转向普通大众;博物馆的展品,由奇珍异宝到古代文物,由异域的民族器物到本土的文化遗产,由传统的村落民居到现代的艺术时尚。这些变化都意味着,博物馆的空间与时间都在发生着变化。博物馆的空间由单一的建筑空间向社区空间延伸,博物馆的时间正在由对展品绝对时间的控制转向对观众相对时间的控制,博物馆正在嵌入现代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从博物馆人类学的视域审视观众,观众这一身份的暂时性并不意味着其参观过程仅仅只是满足各种感官的偏好,而是通过感官体验,观众将博物馆的“展品”再次回归至“物品”,使得博物馆展览能够被观众认同。当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成为公共博物馆的时候,伴随着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兴起,博物馆在通过展品表征现代世界体系的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借助于非西方国家的物品,西方的博物馆通过展示这些物品强化了西方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与政治经济方面的霸权;而随着非西方民族—国家的相继独立,非西方民族—国家的物品又被赋予表征民族多元文化的意涵。尽管西方博物馆在博物馆策展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物品与物品之间地位的平等,但在现代性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资本经济力量,依旧影响着博物馆中的展品,并将这种影响通过博物馆展品,以观众感官体验的方式同化了观众对现代性社会秩序的认同。例如以原始至现代的时间脉络策展,原始意味着“落后”,现代意味着“先进”。博物馆有可能通过有意识地引导观众的感官体验,造成对展品形象以及观众记忆的扭曲。苏姗·克兰(Susan A.Crane)在分析德国历史博物馆(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时指出:“博物馆作为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舞台,记忆是扭曲的:扭曲的‘过去’,扭曲的博物馆历程,扭曲的各种记忆,以及在记忆和认同上用文化话语消极地改变着‘扭曲。’”她进一步指出:“博物馆这一场所,在人们心中的位置远甚于地理空间的位置,通过对博物馆、记忆、知识以及体验的共同作用,博物馆再生产了记忆的体验过程。我们可以倾向于这样假设,即博物馆里的扭曲必然涉及不恰当的事实或者意识形态化的解释。”[5]这就说明,现代性的博物馆,通过展品在表征社会秩序的同时,亦在丰富观众的感官体验,这种“丰富”有可能是以“不恰当的事实或者意识形态化的解释”这一手段来实现的,促使个体认同自身所处的现代性社会秩序。所以说,观众身份的暂时性彰显了博物馆试图通过展品影响和改变“物”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观众的感官体验与博物馆的策展
感官体验对于博物馆的展品来说,意味着观众的参观行为不再只是被动地消费着博物馆所生产的知识,博物馆不再拥有话语解释的绝对权力,说教式的策展并不能绝对刺激并吸引观众的感官。与其说博物馆是在通过展品引导观众参观,不如说博物馆的策展已经将参观的主动性转移至观众身上。但观众在博物馆中以什么样的路线参观、以什么样的方式凝视展品等类似问题并非是由博物馆的策展所能绝对主导的。
因为观众感官体验的存在,博物馆的展品与其说是在表征“物”,不如说是在表征“人”。博物馆展品和“物”之间的距离,与博物馆观众和“人”之间的距离,并非是对等的。物品成为博物馆的展品,意味着这样的物品必然依附于展览与观众才能存在,而展览必然需要考虑观众的感官需求。例如,美国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在展出非洲物品时,组织者就在芝加哥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开展广泛地讨论,并在策展过程中参考了讨论的结果。对于这样的博物馆实践,史蒂芬·拉文(Steven D.Lavine)和伊万·卡普曾指出:“组织者试着对知识和场景设计进行回应,关注观众在进入博物馆之后,确保能够说一些容易理解的话语。观众在这样的场景中可能会明显感觉不舒服,需要对他们进行解说。博物馆将多种美学和智识、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以及新的意识引入,从而使展览设计的能够让观众真正地理解。”[6]这就说明,从博物馆策展开始,博物馆必然期望通过展品吸引观众,而在力图吸引观众参观的层面上,策展的重点也必然倾向于观众的感官体验。博物馆围绕着展品所打造的光影效果、所展现的视频音像、所安排的讲解人员、所创意的文化产品、所设计的互动体验项目等内容,最终指向展览、指向观众的感官体验。
假如博物馆展品的存在并非只是为了形塑民族—国家的形象和教育观众,也并非只是为了学术研究保护与传承某种文化形态,那么观众的感官体验就有可能成为博物馆展品存在的决定性因素。但当观众的感官体验处于无法绝对量化状态时,博物馆展品自然无法绝对地吸引所有的观众参观,尤其是当博物馆与大众之间还存在物理距离或者心理距离的时候,观众的感官体验过程就有可能并非只停留于感官层面,亦有可能引起大众的心理作用。而当这种心理作用上升至生理层面的时候,观众的感官体验就超越了策展层面上的展品,展品成为了观众感官层面上纯粹的“物”,即基于观众自我的感官来决定是否参观某一博物馆、是否观看某一展品、是否聆听讲解,以及在某一件展品前所停留的时间。这时的博物馆展品,对于观众的感官体验来说,其所蕴含的知识、价值、历史背景等因素都可能无法在策展过程中得到很好的解释。
三、观众的感官体验与博物馆发展
对于博物馆这样的空间而言,不同的“物”与“人”可以拥有不同的时间维度。物品的时间维度在博物馆作用下,从其原有的历史文化中抽离,转变为博物馆的展品以及观众感官体验的对象。詹姆斯·伯恩(James A.Boon)曾以批判的眼光指出:“博物馆是各种支离破碎的物品的集散地,博物馆将其搜集物品的动机,与展览的物品结合起来,重新将物品置于其交换或者竞争的时间脉络中,而不是物品本身。”[7]这就说明,展品、博物馆、观众各自的生命历程出现了重合,当博物馆将物品转变为展品,当博物馆向大众免费开放并吸引大众参观,当观众凝视不同的展品,人类社会对“物”的占有与需求在通过博物馆这样的空间得到满足的同时,人类社会也在将“物”与“人”置于同一时间维度中。
当人类社会想要保护与展示人类历史中的各种创造物的时候,博物馆出现了;当人类社会想要掌控人类所创造的书写知识,并期许在有限的空间与时间内收藏各种书籍时,图书馆出现了;动物园、植物园的出现也多是基于此类原因。而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发展,当个体将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与满足自己的文化需求相区别的时候,这些众多的馆与园就有可能由强调人类对物品、书籍、动物、植物等的控制,转变为强调满足人类自身文化的需求,这些馆与园有可能成为人们彰显自我文化权力的场域。
这就说明,人们最初通过博物馆在满足人们占有“物”的同时,亦在通过感官体验着博物馆中的“物”,以“人”的时间赋予“物”以时间,同时又解构着博物馆曾经在“物”与“人”之间所建构的关系。人们最初通过构建博物馆,将世界各地的“物”纳入到现代世界体系当中,通过现代知识体系对其分门别类,进而生产了“物”的知识。这些知识最初在形塑民族—国家、树立西方霸权、确立现代性社会秩序、教育公众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随着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或者说,公众获得“物”的知识的途径,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这些馆与园的时候,包括博物馆在内的这些机构都必将面临着诸如如何缩小与大众的距离等问题。于是,如何降低博物馆“知识权威”这一形象在观众参观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如何消除说教式的策展或者讲解,如何增强观众感官体验的效果,如何不断地提高博物馆对大众的吸引力等内容就成为博物馆需要解决的问题。
博物馆的时间维度,不仅仅指涉的是展品与观众的时间维度,更涉及博物馆自身。观众的感官体验过程,亦是观众自我的时间与博物馆的时间趋于同一的过程,这也是博物馆发展所必经的过程。当博物馆的观众越来越多,是否就意味着博物馆的发展趋于上升的过程?博物馆所收藏的物品、所策展的展品,其对观众的吸引程度往往受到博物馆所处地方性社会的发展、大众关注的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单纯通过彰显博物馆对“物”的控制能力,似乎不能对博物馆进行准确地定位,博物馆发展最终应回归于思考“物”与“人”的关系的层面上。罗宾·布斯特(Robin Boast)曾指出:“博物馆,可以作为收藏物品的场所,也可以作为权威的守门人,还可以作为专业人士研究资源的看护者,更可以作为物品的终极守卫者,亦可以作为物品身份的终极仲裁者,还可以作为物品文档的管理者,甚至可以作为教育者,但博物馆的这些身份必须彻底地被重新改写。”[8]这就意味着,如何将博物馆嵌入现代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将博物馆置于诸如旅游社会与消费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如何增强观众在博物馆中的感官体验效果,如何将博物馆与大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相结合,如何在完善博物馆收藏、教育与研究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发展博物馆服务社会的功能,如何将博物馆置于地方性社会发展过程中等类似的问题,都是博物馆发展所应思考的问题。
[1]Ivan Karp.Other Cultures in Museum Perspective.Ivan Karp and Steven D.Lavine eds..Exhibiting Cultures: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Washington and Lond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1:373-385.
[2]Masao Yamaguchi.Exhibition in Japanese Culture.Ivan Karp and Steven D.Lavine eds..Exhibiting Cultures: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Washington and Lond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1:57-67.
[3]Kenneth Hudson.How Misleading Does an Ethnographical Museum Have to Be?Ivan Karp and Steven D.Lavine eds..Exhibiting Cultures: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Washington and Lond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1:457-464.
[4]Svetlana Alpers.The Museum as a Way of Seeing.Ivan Karp and Steven D.Lavine eds..Exhibiting Cultures: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Washington and Lond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1:25-32.
[5]Susan A.Crane.Memory,Distortion,and History in the Museum.Bettina Messias Carbonell ed..Museum Stu⁃dies:An Anthology of Contexts.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318-334.
[6]Steven D.Lavine,Ivan Karp.Introduction:Museums and Multiculturalism.Ivan Karp and Steven D.Lavine eds..Ex⁃hibiting Cultures: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Washington and Lond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1:1-9.
[7]James A.Boon.Why Museums Make Me Sad?Ivan Karp and Steven D.Lavine eds..Exhibiting Cultures: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Washington and Lon⁃d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1:255-277.
[8]Robin Boast.Neocolonial Collaboration:Museum as Con⁃tact Zone Revisited.Museum Anthropology,2011,34(1):56-70.
Abstract:When the museum turns an object into an exhibit through exhibitions,it also creates condi⁃tions for the visitor to gain sensory experiences.Being positioned in the museum space as an exhibit,the ob⁃ject is given a new time dimension.With the temporal identity as a visitor,one’s sensory experience of visit⁃ing the museum is conducted under a relative time dimension.Due to the temporality of museum visiting,to stimulate the visitor’s sensory experience becomes one of the priorities of the exhibit.The exhibit,which e⁃xists in the process of the visitor’s sensory experience,is the extension of its original time form in modern so⁃ciety.The decreased distance between the museum and the visitor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museum to re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object”and“people”through exhibitions.
Key words:exhibit;curatorial;time dimension;sensory experience;museum anthropology;visitor
(责任编辑:王 霞;校对:张 蕾)
Time Dimension and Sensory Experience:the Visitor in the Perspective of Museum Anthropology
PAN Bao
(Institute of Ethnic Culture,Dali University,Dali,Yunnan,671003)
G260
A
2016-10-01
潘宝(1985—),男,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人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旅游、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