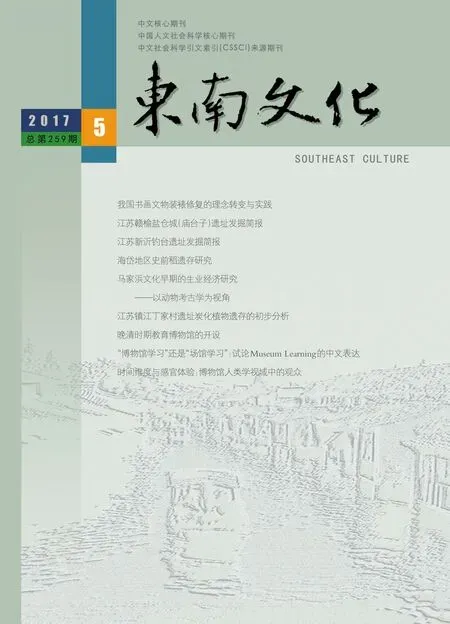晚清时期教育博物馆的开设
李 军
(深圳博物馆 广东深圳 518026)
晚清时期教育博物馆的开设
李 军
(深圳博物馆 广东深圳 518026)
教育博物馆在中国博物馆早期实践中占有数量上的明显优势。清末新政后,教育博物馆经由罗振玉等游历日本的士人宣传介绍,引起清政府要员和教育界的重视,并被写入“癸卯学制”相关章程,得到国家制度层面的提倡和推广。湖南、广东、天津等地率先创设了中国第一批教育博物馆,完成了教育博物馆从理念传入到实际开设的全过程。
晚清时期 教育博物馆 教育近代化 新式教育
中国人至迟到19世纪80年代初就已接触到教育博物馆,它的引进和创设是清末西风东渐和教育近代化的产物。清末新政后,教育博物馆曾一度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特别是教育界的普遍提倡。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优级师范学堂应附设教育博物馆”被列入清政府颁布施行的“癸卯学制”《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1]。这一时期,教育博物馆作为辅助学校教育、推动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机构获得了初步的发展。1904年至1905年,中国第一批教育博物馆在湖南、广东、天津等地率先建成开放,成为中国博物馆事业初步建立的重要标志[2]。本文将在厘清教育博物馆概念的基础上,对教育博物馆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传播过程、早期发展情况等进行考述,借此展现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存在形态和发展状况。
一、教育博物馆的定义
马继贤指出,“在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建设中,教育界走到了前列”,“由学校或教育机关筹建的,占有很大比例”[3]。这类由教育界开办的教育博物馆在中国早期博物馆实践中占有数量上的明显优势[4],其创办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新式教育的发展,推动学校教育近代化。
民国时期的博物馆学家陈端志将教育博物馆定义为“专为教育家而收集校舍、校庭及学校卫生之资料,桌、椅、黑板等校具,理化学实验器械、地球仪、博物标品、模型、挂图等教具之类,并备置有关教育的参考图书,为教育上参考之资的专门的博物馆”[5]。由此看来,教育博物馆是为辅助学校教育和教育家研究而设立的专门博物馆,它收藏陈列的物品涉及学校教育的各方面,可以供教育家研究学校建设、行政管理、组织、制度以及教育教学方法等,这在科举逐步废除、新式教育兴起之初的清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费畊雨、费鸿年进一步区分了教育博物馆的不同形式,德国式的教育博物馆一般专为教员使用,而美国的教育博物馆大多以直接教育儿童为主[6]。教育博物馆的功能包括收藏、展示、研究、教育,具备了现代博物馆的基本职能,应当视作中国博物馆初创时期的一种重要形态。
陈端志还着重强调教育博物馆的特殊意义,指出“各种博物馆,虽然对于教育上总有多少关系”,然而教育博物馆“纯粹以教育做立场而陈列的,他不但和学校有同样的功效,而且和学校是相得益彰,不可偏废的”[7]。同时,教育博物馆与学校博物馆的性质、内容、陈列物品等,既有交叉重叠,又有所区别。学校博物馆是“小学以至大学各级学校在学校内部实行实物教育的一种重要的设施”[8],其陈列物品包括适应各科教授上课要求之资料、养成处世的常识之资料、养成产业思想之资料、研究乡土之资料等[9]。因此,仅就陈列物品而言,两者在博物标本、理化器械等方面存在重叠,而诸如学校建设、教育方法、行政管理等专供教育家研究的资料则为教育博物馆所独有。
在清末的中国以及明治初期的日本,理化实验器械、标本模型等新式教育用品处于初创阶段,极为难得,不仅对于学生,对于大部分教师而言,它们同样属于新生事物。在此背景下,这些新式教育用品必然为教师、学生共同利用,这一时期的教育博物馆也必然面向教师、学生共同开放。
清末民国时期,普遍存在将教育博物馆附设于图书馆或合并举办的情况,如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山西圣庙教育图书博物馆等。同时,教育博物馆的名称也并不统一,与教育博物馆具有相似含义的名词还包括教育品陈列所、教育品陈列馆等。从教育博物馆的基本定义出发,这类教育品陈列所具有明显的教育博物馆性质,应该纳入教育博物馆的行列。
二、最初的接触
1817年,法国教育家朱利安(Marc-Antoine Jullien)最早提出建立教育博物馆的设想[10]。现在一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教育博物馆是1851年由德意志帝国符腾堡王国工业和贸易部设立的教育器具陈列馆[11]。此后数十年间,一场兴建教育博物馆的热潮席卷欧洲和美洲。到1906年,世界各地共有76座教育博物馆,仅德国就开办了36家[12]。日本也于1877年在东京创设了教育博物馆,并发展演变为今日的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
日本1877年建立教育博物馆后不久,李筱圃就曾到访参观并留下记录,清政府第三任驻日公使陈家麟、中国最早的留日学生张文成也分别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和十四年(1888年)造访东京教育博物馆。李筱圃光绪六年(1880年)参观位于上野的“教授博物院”和“教育博览会”[13]。尽管没有留下详细的参观记录,但可以确定李筱圃笔下的“教授博物院”即为东京教育博物馆。该馆的前身是1871年文部省在汤岛圣堂创办的博物馆,1877年上野新馆部分竣工,更名为教育博物馆[14]。光绪十三年(1887年)陈家麟到访东京教育博物馆,并留下了较为详细的记载。他记录说:“教育博物馆在博物馆西,入其内,院宇宏广,分屋置器”,“泰西机器之属,若火车、火船、织纴、针缝等器,均具体而微”,“(后栋)分屋五楹,储窥星镜、测天仪及地球(仪),大小各数十具”。他认为,学生可以通过参考和模仿教育博物馆的陈列物品提高技艺,获得新知[15]。被称作“清末留日学生之嚆矢”的张文成光绪十四年(1888年)入学后不久,也参观了东京教育博物馆[16]。光绪十五年(1889年),东京教育博物馆成为高等师范学校的附属设施。清末留日热潮出现后,曾有大批留日学生及游历日本、考察教育的中国人到访参观该教育博物馆,并向国内宣传介绍。
在国内,伴随着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的舆论,康有为、李端棻等维新人士也倡导建立具有教育博物馆性质的“博物院”、“仪器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提出创设博物院,主张“凡古今中外兵、农、工、商各种新器,如新式铁舰、轮车、水雷大器及各种电学、化学、光学、重学、天学、地学、物学、医学诸机器,各种矿质及动植种类,皆为备购,博揽兼收,以为益智集思之助”[17]。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端棻力主推广新式学堂,提出创设仪器院。他指出:“格致实学,咸藉试验。无远视之镜,不足言天学。无测绘之仪,不足言地学。不多见矿质,不足言矿学。不习覩汽机,不足言工程之学。其余诸学,率皆类是。然此等新器,所费不赀;家即素封,亦难备购。学何从进,业焉能成。今请于所立诸学堂咸别设一院,购藏仪器,令诸学徒皆就试习,则实事求是,自易专精”,“学徒所成,视昔日纸上空谈相去远矣。”[18]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维新派在筹办京师大学堂时,也提议设仪器院,“集各种天算、声光、化电、农矿、机器制造、动植物各种学问应用之仪器,咸储院中,以为实力考求之助”[19]。
康有为、李端棻等人计划创设的“博物院”、“仪器院”,以辅助和改良学校教育、推进格致实学为目的,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至清末,许多学校设立的仪器院,不仅供校内师生利用,也提供给没有设立仪器院的学校师生观摩,还“常利用所藏仪器,开设特别展览会,公开给民众观览,以广扩自然界知识,打破民众迷信”[20]。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类“博物院”、“仪器院”实际上发挥了教育博物馆的功能。
三、开设的背景和过程
1901年“新政”后,科举制度的逐步改革和废除、新式学堂的推广和发展,为教育博物馆的创设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在清政府的大力提倡下,新式学堂和学生数量都出现了井喷式增长[20]。随着学堂时代的到来,科举时代的文具用品,如笔、墨、纸张等根本无法满足新式学堂教育的需要,教学所需的各式教育用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品种和范围都大大地扩展了[22],这对当时的教育界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如何从国外引进新式学堂教学急需的教育用品和科学仪器,并采用适当的形式将这些教育用品、科学仪器以及新式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向各学堂推广,成为教育界的重要任务。
在此背景下,教育博物馆受到晚清士人的重视,并开始了设立教育博物馆的实践。这一时期,教育博物馆被纳入到“癸卯学制”,得到国家制度层面的提倡。其基本途径是通过罗振玉等人游学日本、考察日本学制及东京教育博物馆,进而在国内提倡,并影响张之洞等人,张之洞等在制定“癸卯学制”时,正式将教育博物馆事项写入《奏定学堂章程》。
张之洞注重新式教育,提倡出洋游学。由于路程、费用、文字语言等原因,张之洞认为“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23]。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派遣罗振玉、陈毅等赴日本考察学校,购译教科书[24]。罗振玉将其在日期间的见闻以日记形式记录,并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扶桑两月记》为名出版,书中介绍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内又附设教育博物馆,陈列教育用品,以供参考。其陈列分三部:第一部为家庭教育及幼稚园、小学校用具与其成绩品;第二部为物理学、数学、星学、地学、化学、动物学、生理学及植物学之教授用具、器械、标本、挂图等;第三部为实业教育用具及成绩品、图画音乐教员参考书、杂志之类”。罗振玉“闻每岁来观者,及中学校、实业学校、专门学校生徒携书籍来对照实物者至六七万人”,认为教育博物馆“有裨于教育界甚巨”[25]。同一时期,罗振玉等人创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译介东京教育博物馆的文章《东京教育博物馆述略》,从历史沿革、陈列品、陈列法、参观人、经费等方面对东京教育博物馆作了全面的介绍[26]。
考察回国后,张之洞五次接见罗振玉,并安排他“于督署学务处为幕府及各学堂提调教习与守令演说教育事十日”[27]。这是一次小范围地方行政官员推行新式教育的思想启蒙,对正在兴起的湖北新学产生了积极影响。罗振玉倡导学制改革的《学制私议》也被《湖北学报》转载刊登。在参考日本学制基础上写成的《学制私议》中,罗振玉关于博物馆事项的论述基本源自他对东京教育博物馆的考察。他提出,博物馆“京师及各省各府、厅、州、县各宜次第创立,而先立教育博物馆,搜集关教育各品,以资考求。约分三部:一、家庭教育、幼稚园及小学校用具及其成绩;二、物理、数学、星学、地学、化学、生理学、动物植物学之教授用具及标本、图画;三、实业教育用具及成绩品与图画之类”[28]。
光绪二十八年底,张之洞等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出台了湖北学制体系,这个学制体系的基本框架仿照了日本学制[29],其中有关日本的信息很大一部分来自罗振玉等人的日本考察记录[30]。在全国层面,由于“壬寅学制”的失败,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张之洞会商修订学堂章程,得到清政府批准[31]。张之洞等根据湖北办学经验,与荣庆、张百熙共同草拟《奏定学堂章程》,张之洞的主要助手正是曾和罗振玉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的陈毅。此外,他还经常约请大学堂的日本教习和总办、总教习等行政官员共商学务[32]。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第一个经政府制定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它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罗振玉、张之洞等的教育主张也通过《奏定学堂章程》的出台得到了肯定。《奏定学堂章程》包括《学务纲要》、《高等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等20余种章程,其中《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明确指出优级师范学堂“应附设教育博物馆,广为搜罗中国及外国之学堂建筑模型图式、学校备品、教授用具、学生成绩品、学事统计规则、教育图书等类陈列馆中,供本学堂学生考校,并任外来人参观,以期教育之普及修改”[33]。章程基本阐明了教育博物馆的特殊职能、陈列展览的主要内容和开放参观的基本形式,也从国家制度层面确立了教育博物馆的地位。
在浙江,徐树兰“参酌东西各国规制”“亲手制定”的《古越藏书楼章程》光绪二十八年付梓[34]。章程第六节写道:“研究科学,必资器械样本,故本书楼兼购藏理化学器械及动植矿各种样本,以为读书之助。”其释义曰:“外国标本器械,各学堂皆有之,兹因学校规模未备,故附入藏书楼,将来经费稍充,即别辟教育博物馆,将此项裁去。”[35]也就是说,徐树兰创办的古越藏书楼尚兼有教育博物馆的职能[36]。在湖南,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九日(1904年3月15日)《湖南官报》刊载《创设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募捐启》,筹备设立教育博物馆[37]。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于当年正式建成开放,负责筹备事务的魏肇文、梁焕奎、胡元倓、陆鸿逵、梁焕彝、刘棣蔚、俞蕃同等人都有留学日本、学习教育的经历[38]。在天津,严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第一次赴日本期间参观了东京教育博物馆;光绪三十年第二次东游期间,又同张伯苓等参观了教育品制造所的工场和庋物处,并订购相关仪器[39]。同年,直隶工艺总局筹办天津教育品陈列馆,严修曾参与“会商”[40],工艺总局又派陈宝泉专程赴日本,为创办天津教育品陈列馆作建馆考察并购置设备[41]。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日(1905年3月15日),天津教育品陈列馆正式建成开放[42],从该馆的章程、陈列物品等来看,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已经是较为完备的教育博物馆[43]。光绪三十年,广东学务处也开办了图书及教育品物陈列馆[44];同年,张之洞“广购东西洋书籍图书标本资料以供各学堂试验之用,而校外研究家亦可入馆参考”[45],开办了具有教育博物馆性质的仪器图书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东泰安也开设了教育博物馆,“自日本购到教育品多种,一一陈列,任人观览”[46]。
总的来说,新式教育的普及发展和教育近代化的逐步推进,为教育博物馆的引进和创设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自“癸卯学制”颁布施行以后,教育博物馆一直被置于教育行政部门的管辖之下,受到国家和省级教育部门的普遍重视。在国家、省级教育行政体系中,均设置有专门职能部门主管教育博物馆工作。进入民国后,教育博物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陕西、云南、浙江、江苏、江西、河北、山西、广西等地都曾建立或筹办教育博物馆。1920年,民国政府教育部也曾在北京筹办教育博物馆。而各地发展教育博物馆的目的,其实也都在于“网罗内外国现在、过去有关教育各事物”,以期“扩张教育界之智能识见,促全国教育之进步”[47]。
四、总结与讨论
尽管教育博物馆被视为中国博物馆事业初步建立的重要标志,然而学界对于教育博物馆的研究明显不足,研究成果也稍显薄弱。中国博物馆的最早环节至少呈现为二元格局:一方面是由外国机构创办,以自然史收藏为基础的博物馆;另一方面是由中国人创办,深受日本影响,基于博览会观念,服务于学校教育的博物馆[48]。而在中国人的早期博物馆实践中,教育博物馆占有数量上的明显优势。进入民国后,教育博物馆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当时的博物馆学研究者陈端志、费畊雨等均专章介绍教育博物馆。总的来说,在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发展历史,特别是早期发展史中,教育博物馆实际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应当作为中国早期博物馆的一种重要类型,引起更多的重视和研究。
[1][33]《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703页。
[2]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3]马继贤:《博物馆学通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4]黄春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中国博物馆》2015年第4期。
[5][7]陈端志:《博物馆学通论》,上海市博物馆1936年,第80—81、80页。
[6][8]费畊雨、费鸿年:《博物馆学概论》,中华书局1948年,第44—47、48页。
[9]天民:《学校博物馆之施设》,《教育杂志》1917年第1期。
[10]Marc-Antoine Jullien,Esquisse et vues préliminaires d‘un ouvrage sur l’éducation comparée,谷歌图书网,[EB/OL][2014-03-18] 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id=InNQAAAAcAAJ&printsec=frontcover&hl=zh-CN&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11]吴家镇:《教育博物馆与教育馆之研究》,《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1936年第2期。
[12]Institut Français de l'Éducation,Musées pédagogiques,法国教育研究所网站,[EB/OL][2014-03-18]http://www.inrp.fr/edition-electronique/lodel/dictionnaire-fer⁃dinand-buisson/document.php?id=3241.
[13]清·李筱圃:《日本纪游》,钟叔河主编《日本日记、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扶桑游记、日本杂事诗广注》,岳麓书社1985年,第172—177页。另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0秩,上海著易堂1891年。
[14]《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沿革》,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网站,[EB/OL][2014-03-18]http://www.kahaku.go.jp/english/about/summary/history/index.html.1881年之前,上野公园仅有(东京)教育博物馆一家博物馆。
[15]清·陈家麟:《东槎闻见录》,《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第10秩,上海著易堂1891年,第450页。
[16]王勇:《人物往来与东亚交流》,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182页。
[17]清·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4页。
[18][19]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19、128页。
[20]吴学信:《社会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35页。
[21]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2]杨国强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23]清·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9辑(482)号,第14587页。
[24]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153页。
[25]清·罗振玉:《扶桑两月记》,教育世界社1902年石印本,第15页。
[26]《东京教育博物馆述略》,《教育世界》1904年第67、68号。
[27]甘孺(罗继祖)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28]清·罗振玉:《私议学制》,《教育世界》1902年第24期,转载刊登于《湖北学报》1903年第16期。
[29][32]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11—116、121—122页。
[30]杨千菊:《罗振玉对〈癸卯学制〉的贡献》,《教育的传统与变革——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3)》,2009年。
[31]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五,台湾文海出版社,第3—4页。
[34]来新夏:《古越藏书楼百年祭》,《来新夏谈书》,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35]清·徐树兰:《古越藏书楼章程》,浙江省图书馆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图书馆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第442—443页。
[36]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62—264页。
[37]《创设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募捐启》,《湖南官报》1904年3月15日第593号。
[38]周德辉:《创建湖南图书馆若干历史问题考正》,湖南图书馆编著《湖南图书馆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22—125页。
[39]清·严修撰,武安隆、刘玉敏点注:《严修东游日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199页。
[40]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4—75页。
[41]清·陈宝泉:《天津教育品陈列馆议绅陈宝泉上周总办意见书》,蔡振生、刘立德编《陈宝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15页。
[42]《时闻·天津教育品陈列馆》,直隶学务处编《教育杂志》1905年第4期。
[43]李军:《晚清时期教育博物馆的引入与发展——以天津教育品陈列馆为例》,《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5年第3期,第222—228页。
[44]《本国学事·广东》,《教育世界》1904年第18期总第86期。
[45]转引自湖北省志文艺志编辑室编:《文艺志资料选辑·图书馆专辑》,河南省信阳市印刷厂1984年印刷,第212页。
[46]转引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47]伍达:《拟设教育博物馆简章》,《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第6期。
[48]徐坚:《和声:清末民国博物馆的众流格局》,《东方早报》2014年5月14日第B09版。
Abstract:The earliest museums established by Chinese people in China were often named as“educa⁃tional museums”.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marked by the reform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style schooling prepared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educational museums.With the efforts by scholars such as Luo Zhenyu who had travelled in Japan,the concept of educational museums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Qing governmental officials and the edu⁃cation field and was promoted and advocated at the national policy level especially with its being included in the 1903 School System(Guimao Xuezhi).The first batch of educational museums were established in Hu⁃nan,Guangdong,and Tianjin,turning the idea of the educational museum into a practice.
Key words:late Qing dynasty;educational museum;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new-style education;introduction process
(责任编辑:王 霞;校对:张 蕾)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ducational Museum into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 Jun
(Shenzhen Museum,Shenzhen,Guangdong,518026)
G260
A
2014-03-20
李 军(1984—),男,深圳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