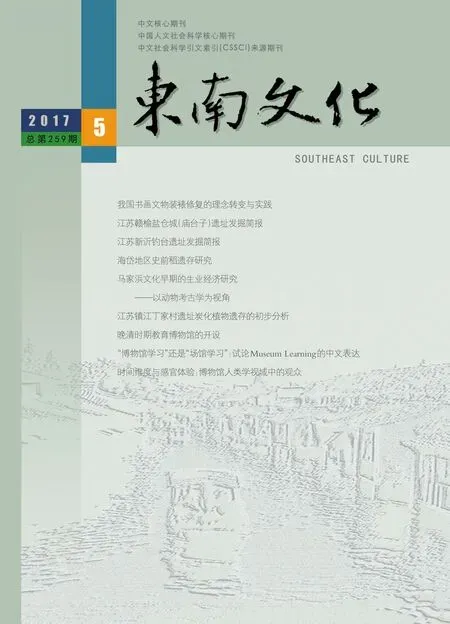“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赵星宇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赵星宇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博物馆学习 场馆学习 语词互译 博物馆定义
一、提出问题:一个术语、两种翻译
观众能够从展览中获取多少信息?这一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重视,而观众研究(visi⁃tor studies)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渠道。但在实践过程中,部分学者发现,传统以“行为”(beha⁃vior)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存在一定的局限。例如,我们可以记录观众在某件展品前的停留时间,但却很少去分析观众接受展览信息的程度。2007年,随着国际博物馆协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下文简称“国际博协”)将“教育”(education)视为博物馆的首要职能,评估展览信息的传播效率愈发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观众在展览前后是否会发生学习行为?观众的学习结果如何测量?观众的学习结果如何反映到展览的实践中?这些问题的实质构成了观众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museum learning。
Museum learning是博物馆观众研究的一个分支,它以观众为研究对象,基于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测量观众在参观前后的智识变化,并寻求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为博物馆成为更好的自由选择式学习场所提供理论借鉴与数据支持。关注观众的“智识变化”是这一领域的显著特点,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亚瑟·梅尔顿(Arthur W.Melton)在美国布法罗科学博物馆(Buffalo Mu⁃seum of Science)对小学生学习能力的研究[1],这是观众研究史上首次直接关注到观众的智识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观众研究的再次复兴,museum learning这一概念也正式出现在相关研究论文中[2];到了20世纪80年代,观众研究的数量增多,研究工作变得愈发细致,博物馆学习也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而有关“博物馆学习”的争论具体体现在“博物馆学习是否真的存在”这一问题上。
罗斯·鲁米斯(Ross J.Loomis)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观众研究时曾指出:“我们是否在做有关学习的研究?这个主题最令人难以捉摸。”他认为,现阶段所谓的博物馆学习,研究的只是观众学习认知的条件而已,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去度量观众的学习,以及如何去设计某种展示方式,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学习”[3]。但怀疑者也以此为据,认为学习本身过于主观,无法度量。例如克兰·瓦莱丽(Crane Valerie)和早年的约翰·福尔克(John H.Falk)均对此抱有不同程度的疑虑,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坚持这一观点[4]。
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观众在博物馆中的行为始终无法绕开学习这一因素,如果忽视博物馆对个体智识变化的影响,那么博物馆的教育职能就显得空洞而缺乏依据。与此同时,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逐渐褪去热潮,人本主义、认知主义等更加注重个体心理因素的学术流派开始活跃。一批新的学习理论也随之诞生,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开始被人们普遍接受,进而取代了传统行为主义者的“刺激—反映”模式,成为博物馆学习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一理论打破了人们以往对“正式教育”(Formal Education)体系下学习行为的僵化认识,使得学习成为一种基于个体的、随时可以发生的“非正式行为”。基于此,现阶段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开始不再局限于寻找观众在博物馆中的学习证据,而是开始寻求有效的手段来测量观众的学习,并分析影响观众学习效果的因素,福尔克与琳恩·迪尔金(Lynn D.Dierk⁃ing)提出的“情景学习模式”(the contextual model of learning)就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事例[5]。
教育学与museum learning之间同样具有很深的渊源。现阶段,在教育学领域中,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属于“教育技术学”的学科范畴,而“教育技术学”这一研究方向的诞生,正是美国于20世纪20年代将博物馆纳入学校的正式教育体系的结果[6]。事实上,在museum learning的学术发展史中,博物馆学与教育学都对其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但在国内,这一领域却被“人为”地分割为看似不同的两门学科,即教育学界普遍将museum learning译为“场馆学习”,而非博物馆学界所认同的“博物馆学习”。
最早将museum learning译为“场馆学习”的观点见于《场馆科学学习:本质特征与影响因素》[7],此外另有文章指出museum learning不应当译为“博物馆学习”[8]。尽管个别文章采用“博物馆学习”的译法[9],但在教育学界并没有形成主流认识。事实上,不同的翻译代表了两门学科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根本原因是对“知识测量”的认识差异,直接原因是对中文语境下“博物馆”一词的理解偏差。
二、分析问题:产生分歧的原因
(一)两门学科对“知识测量”的不同认识
结合“场馆学习”的内容以及山东大学博物馆学习项目组于2017年4月在山东博物馆“夏商周时期历史陈列”展厅中进行的研究,本文认为“场馆学习”和“博物馆学习”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两门学科对“知识测量”这一概念存在认识差异,导致二者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产生分叉。
“场馆学习”的支持者认为,与科学教育相关的封闭结构场所、露天场所应该是museum lear⁃ning的研究对象。原因在于,此类场所的展示内容以科学知识为主,知识的意义与内涵是客观的。相比之下,历史类、艺术类博物馆展示内容的意义与内涵则普遍相对主观。虽然主观与客观的知识都能“产出多元结果”,但museum learning的研究必须要“基于真实问题”[10],即展览中的知识要为量化提供评分标准,而知识的客观性正是进行量化评估的前提。传统的人工制品——特别是艺术品——所蕴含的“知识”往往缺乏一个足够客观的“标准”,这就导致研究人员很难对历史类、艺术类展览中观众的学习效果做出准确的评估,甚至由于评估标准的缺乏而根本无从入手。
然而以上认识存在两个误区。首先,任何知识实际上都有一定的时空范畴,即便是科学类、自然类的常识性问题,也在近百年间因科技的不断进步而被改写,因此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第二,尽管历史类、艺术类展览的内容在意义上存在很大的阐释空间,但策展人在布展时就会赋予展品本身相对稳定的、可以解读的信息与内涵。例如,我们在进行museum learning研究时,让观众在参观前后分别就“夏商周”概念的理解和“青铜器类型”进行自由回答,并对获得的词汇按照“数量”、“广度”、“深度”、“掌握程度”进行分类,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观众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在参观展览前后的确发生了显著变化(表一)[11],而“广度”与“深度”上的变化则体现出观众在智识变化上趋向于展览所要表达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展览信息客观上对观众的智识产生了“干预”,这一“干预”导致的结果并不是散漫的,而是在总体上呈现出指向性。关于非科学类博物馆对观众智识造成“方向性”干预的研究并不少见,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可参考扎哈瓦·朵琳(Zahava D.Doering)等人的研究成果[12]。
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是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综合,量化研究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场馆学习”的支持者认为,科学类、自然类博物馆由于展示内容的标准化,能够基于标准来对观众的智识变化进行量化评分。类似于数学考试,由于答案是唯一的,因此评分的结果也是最客观的,这是进行量化研究的前提。相比之下,历史类、艺术类博物馆则由于展示内容意义的多元,难以根据单一标准进行评分,评分者主观判断的大量介入势必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并不适用于量化的研究方法。
但是,根据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即便是科技类博物馆,也很难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观众对展览信息的掌握程度。虽然科技类博物馆中多数展品的内容指向非常明确,但观众对某一概念的理解程度依然会存在差异。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的是个体的个人、环境、社会文化因素都会对学习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13],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用多维度来对某一现象进行综合考量评定是不可避免的,这比单一的维度更能全面地说明问题。基于这一点,历史类、艺术类博物馆同样可以将展示内容从多个维度进行划分,以求尽可能全面地获取观众对某一概念认识的全部内容。例如,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全面地获取观众在参观“夏商周时期历史陈列”时可能获取的全部信息内容,我们分别使用个人意义映射(personal meaning mapping,PMM)[14]、开放式问答(open-end question)、选择题(multi-choice ques⁃tion)三种方法将观众参观前后的知识内容划分为七个维度(表二)[15]。基于这七个维度在参观前后发生的变化,可以共同视为观众的智识变化。参考福尔克的相关研究,这一结果就是museum learning量化研究的基础[16]。
(二)两门学科对“博物馆”概念的不同理解
“场馆学习”与“博物馆学习”的根本差异源于对“知识测量”问题的不同认识,这使得前者有意将自然类、科技类博物馆与历史类、艺术类博物馆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群体。而导致教育学相关研究者抛弃“博物馆学习”这一译法的直接动因,就是对中文语境下“博物馆”一词范畴的窄化。
在“场馆学习”的支持者中,有学者曾系统地指出:“对比中西两种语境中的museum概念,地域发展的时间维度和文化孕育的物识观差异使两种语境中生成的解释存在较大的差别。从内涵上分析,前者是主体开放且价值多元的描述性表达,后者则是界限厘定严格的规定性定义。从外延上分析,前者是一种广义解释,将场馆边界扩展到人类生活所能涵摄的广泛领域,后者则是一种狭义的界定,专指以收藏、宣传和科学研究为目的的狭义博物馆。从逻辑上分析,前者是演绎性的开放统整,预留一定的伸展空间;后者则是归纳性的封闭集合,难以扩充新的子系统。”[17]但是,从博物馆学的视角出发,这一论述并不能成立。为了更清晰地指出“场馆学习”支持者对“博物馆”一词的认识误区,我们将中文语境下的“博物馆”划分为“管理层面”与“学理层面”两层含义。“场馆学习”的支持者存在的最大误解,就是将“管理层面”上的“博物馆”运用到学术研究的范畴中,反而忽视了“学理层面”对“博物馆”界定的范畴。
在探讨“博物馆”之前,有必要重新梳理西方语境下museum的范畴。正如“场馆学习”者所认同的观点,museum本身的确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然而这并不是与生俱来、一蹴而就的。事实上,通过对比历次国际博协大会通过的定义,从中可以发现museum有很明显的“扩张趋势”。从2016年第24届国际博协大会对museum范围认定的内容可以发现,它通过将具体的范围上升至抽象的范围,最后形成“一切具有museum全部或部分特征的机构都有成为museum的可能”的范畴。Museum learning研究对象的多样性也正是得益于此,以福尔克和迪尔金在“情景学习模式”的研究中对museum的界定为例[18],尽管他们研究的对象是“自由选择式学习场所”,但客观上全部都属于国际博协所界定的museum范畴之中。因此,museum的外延本身就是人为干预的一个结果,而非词汇原本携带。
中文语境下“博物馆”概念与范畴的衍变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回顾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博物馆”的概念具有非常显著的时代特征。作为具有一定传统根基的“舶来品”,“博物馆”与museum的关系呈现出“一致—对立—有条件的一致”的发展模式。所谓“有条件的一致”,反映在本文所界定的两种模式:一种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基于管理层面的、体现在相关法律法规中的定义;另一种以国际博协为标准,基于学理层面的、适用于博物馆学研究工作的定义。现阶段,“管理层面”的定义在我国自2015年3月20日起施行的《博物馆条例》中指出:
本条例所称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博物馆包括国有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本条例所称博物馆不包括以普及科学技术为目的的科普场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博物馆依照军队有关规定进行管理。……该定义的目的在于满足国家对博物馆实施行业管理的要求。[19]
在行政关系上,《博物馆条例》所涉及的“博物馆”仅为文化部门主管的博物馆,将属于科技部门、军队系统下的博物馆排除在外。从中可以看出,该定义以“隶属关系”为依据对博物馆的类型进行划分,在“管理层面”上确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如果将该定义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则明显与当代博物馆学的研究趋势和基本前提不相符。这两种界定均具有其存在的合理适用范围,“管理层面”适用于博物馆机构的组织架设、政策的制定出台、管理的执行标准;“学理层面”适用于作为学科的博物馆学研究的实践与理论架构。前者基于管理、现阶段国情,后者则需要遵循museum的内涵与外延。综上所述,基于学术研究的视角,“博物馆”与museum在内涵和外延是一致的,“博物馆”是包含科技类、自然类、历史类、艺术类、动植物园、水族馆等机构在内的集合体。
三、解决问题:“博物馆学习”概念的确定
“场馆学习”与“博物馆学习”的分歧存在于“一表一里”两个层面。表面上,是前者对“博物馆”概念与范畴的误解;实质上,是前者对历史类、艺术类博物馆中“知识测量”的怀疑。综上所述,尽管“场馆学习”强调的科技类、自然类博物馆在进行museum learning研究中具有优势,但“博物馆学习”不仅在范畴上包含了“场馆学习”全部内容,而且为进一步丰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提供了基础,也为中西语境下同一研究概念的一致性提供了保障,因此“博物馆学习”应视为museum learning在中文语境中的正确表达。
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对同一问题的基本概念基本达成一致,而对museum lear⁃ning的不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博物馆学与教育学之间的联动。“博物馆”与“场馆”的同时存在往往会导致研究过程中的混乱。例如研究者既然将museum译为“博物馆”和“场馆”两种概念,那么当这两种概念重新被翻译回英文语境中时,是否还需要加以区别?如果需要区别,二者实际上确是由同一个词汇翻译而来;如果不加区别,二者在中文语境下的研究范围又并不完全一致。在一些“场馆学习”的研究中,个别研究者为了在文章中体现出“博物馆”与“场馆”的区别,存在将所有的museum都生硬地变为“场馆”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对教育技术领域内的其他研究者产生误导。此外,一些研究者在引用博物馆学的相关概念时,也没能及时了解博物馆学最新的研究成果。例如,在引用museum的概念时,部分学者采用的仍然是1974年国际博协制定的定义,但实际上目前通行的是2007年的版本,而二者之间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目前,国内教育技术领域关于museum learning的研究与推介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相关期刊也专门开设专题并组织专家学者进行讨论,这一点需要引起博物馆学相关学者密切关注。无论是“博物馆”还是“场馆”,如何将教育技术领域内优秀的研究、译介成果准确地应用到博物馆学的研究中,推动两个学科之间的互动发展,才是本文讨论的应有之义。
[1]Melton Arthur.Experimental Studies of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in a Museum of Science.Washington D.C.: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New Series,1936:15.
[2]Kurylo Lynne.On the Need For a Theory of Museum Learning.CMA Gazette,1976,9(3):20-24.
[3]Loomis Ross.“Chapter 1:The Countenance of Visitor Stu⁃dies in the 1980’s.”Visitor Studies,1988:12-24.
[4]Bitgood Stephen.Attention and Value:Keys to Understan⁃ding Museum Visitors.New York:Routledge,2016.
[5]Falk John,Dierking Lynn.Learning From Museums:Visi⁃tor Experiences and the Making of Meaning.Maryland:Al⁃tamira Press,2000.
[6]郑旭东、孟丹:《教育技术学视野中的场馆学习:回顾与展望》,《现代教育技术》2015年第1期。
[7][10]伍新春、曾筝、谢娟、康长运:《场馆科学学习:本质特征与影响因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8][17]王乐、涂艳国:《场馆教育引论》,《教育研究》2015年第4期。
[9]李君:《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博物馆学习研究》,《外国教育研究》2014年第5期;鲍贤清、杨艳艳:《课堂、家庭与博物馆学习环境的整合——纽约“城市优势项目”分析与启示》,《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
[11][15]具体调查与测量方法参见赵星宇、席丽、付红旭、马馨、周柳君:《个人意义映射与跟踪观察法在博物馆学习研究中的应用》,《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17年第3期。
[12]Doering Zahava,Bickford Adam&Karns David.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in a Didactic Exhibition:The Power of Maps Study.Curator:The Museum Journal,1999,42(2):88-107.
[13]Hein George.Learning in the Museum.New York:Rout⁃ledge,1998.
[14]Falk John,Moussouri Theano&Coulson Douglas.The effect of Visitors’Agendas on Museum Learning.Cura⁃tor:The Museum Journal,1998,41(2):107-120.
[16]Falk John,Storksdieck Martin.Using the Contextual Model of Learning to Understand Visitor Learning From a Science Center Exhibition.Science Education,2005,89(5):744-778.
[18]Falk John,Dierking Lynn.Museum Experience Revisited.Oxford:Left Coast Press,Inc,2012:430-432.
[19]国家文物局:《博物馆条例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7页。
Abstract:Most of current researches of museum learning focus on museum visitor studies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studies.The term“museum learning”,however,has been interpreted into two different Chi⁃nese expressions:“bo-wu-guan[museum]learning”in the museum field and“chang-guan[site]learning”in pedagogy.The reason that caused such difference is that the two disciplines adopt different methodologies and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n the concept of the museum.The interpretation of“bo-wu-guan lear⁃ning”maintains the terminological consistency of the word“museum”in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es.More important is that it ensure the equal position of history and art museums with na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in the study of museum learning,which is what“chang-guan learning”could not offer.
Key words:bo-wu-guan learning;chang-guan learning;translation;museum definition
(责任编辑:张 蕾;校对:王 霞)
“Bo-Wu-Guan Learning”or“Chang-Guan Learning”:On the Chinese Interpretation of“Museum Learning”
ZHAO Xing-yu
(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Shandong,250100)
G260
A
2017-03-07
赵星宇(1993—),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