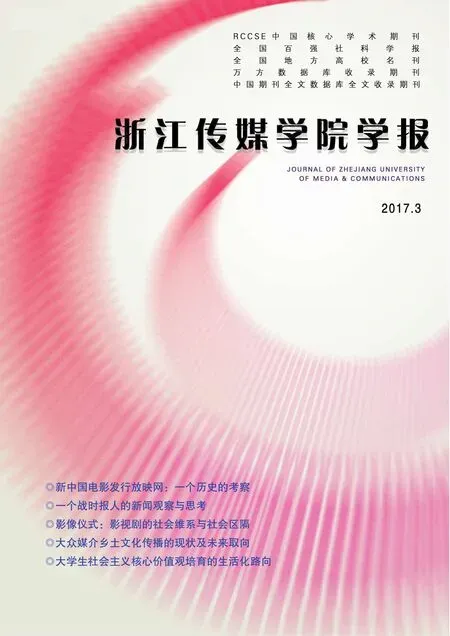全球化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的跨国生产与景观呈现
王冰雪
全球化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的跨国生产与景观呈现
王冰雪
文章探讨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在跨国生产实践中的参与路径与传播策略。研究依托全球化理论、景观理论等相关理论框架,在考察具体电影文本中发现,全球化影像时代的中国电影通过跨国生产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全球影像空间建构,并借此塑造出新的电影媒介景观,突破了电影受众固有思维认知中区域感、地方感与时空界限的限制,阐释了具有全球性特征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多重意义,形成对现实地理空间与虚拟想象空间的弥合,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电影跨国传播的交流渠道与认知空间。
全球化;跨国生产;中国电影;媒介景观
全球化影像时代,电影媒介愈发成为参与文化身份构建、国家形象塑造及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全球电影市场流动性加剧的新格局,中国电影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通过大陆、港台及海外华人社区之间的电影生产与制作呈现出较之以往更为紧密、多元的交流合作态势,塑造出全新的跨国电影媒介景观。本文依托全球化理论、景观理论等相关理论框架,聚焦新世纪以来面对全球电影环境不断变迁、电影格局日益拓展的现状,探讨中国电影是如何参与全球影像传播与跨地交往的?并进一步解析中国电影如何在跨国生产实践中通过塑造新的媒介景观而参与全球化竞争并进行多元身份想象与互动的。
一、全球电影业的环境变迁与拓展
(一)全球化涌现
全球化并非新世纪以来才出现的“新现象”。按照罗伯茨顿的分析,全球化在15世纪至18世纪50年代便已萌芽,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流动的增强,跨国集团的大量涌现以及全球政治格局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出现,全球化意识进一步得以强化。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全球变暖、恐怖主义等问题的蔓延和扩散,也令全球化在世界媒体传播中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全球化”日渐成为连接世界各地、设置共同议题、促进交流往来的核心概念。在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中可以看到,不少学者对什么是全球化都做出了自己的界定。吉登斯对全球化的定义最常被提及,他从结构关系的角度认为“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1]在他的观点中,物质文化资源的全球化是高度现代性的必然后果,其所引发的是关于社会生活怎样跨越时间和空间,即“时空延伸”的难题。
齐格蒙特·鲍曼从流动性角度切入,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全球化“是福是祸”的体验截然不同,并由此提出与吉登斯“时空延伸”相对的另一关注视角。他以“时空压缩”这一术语描绘全球化既分化又联合,缺乏普遍一致性效应的“现实”。全球化进程向全球范围内不断渗透延伸扩散,形成新的社会格局与竞合关系。汤姆林森认为这种关系格局下的全球化是一种“复杂的联结”(complex connectivity),这种联结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亲密依存模式,即全球化这种“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的网络系统。”[2]特希·兰塔能认为在以往研究中“没有界定和区分什么是全球化现象本身,什么是全球化的结果。当我们看到全球化的不同定义时,我们能发现这些定义同时涵盖现象和结果。”[3]新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裹挟在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媒介及新传播形态等层面之中汇聚而来,掀起全球经济、技术一体化、同质化浪潮。
约翰·厄里论及“社会”与全球化时认为“新技术正在创造出一个‘全球时代’,在这个时代,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距离似乎再一次被戏剧性地压缩了。”[4]技术成为实现这种“压缩”的必要手段,而技术本身也成为全球化研究难以回避的关注焦点。特希·兰塔能认为“在现代社会,全球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它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和传播来实现,是媒介化的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超越时空的束缚而媒介化。”[3](18)詹姆斯·罗尔说“现代性与全球化不能简单地看做世界历史的阶段,而应该看做第一世界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破坏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流动过程,而是剥削的世界体系。”[5]鲍曼也提及“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处于本土化,这是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全球化种种过程的一大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循序渐进的空间隔离、分隔和排斥。”[6]萨森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产生冲突空间的进程,其特征为竞争性、内部差异化、不断跨越国界。”[7]全球化并非一个同质化、一体化的运作标准或普遍效应,但同样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全球化的涌现所带来的冲突与竞争。当然也必须承认“正是这些有多重价值的连接现在跨越了现代世界,把我们的实践、我们的体验以及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环境命运捆绑在了一起。”[2](3)这种改变在包亚明看来“已经成为替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和社会想象。”[8]成为了具有改变现状,改变社会发展现实及趋势的“变化范式”,从而衍生出欧阳宏生认为的球土化(glocalization),这一“融合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地方化(localition)两个极端,用以强调二者的相反相成和互动发展。对于构建本土文化与融入全球化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视维”[9]的新的组合观念。
正如上述国内外学者所言,全球化是一个复杂多样,非固定化、标准化的概念,在全球化意识跨越国界涌入全球的时代,尽管国家边界依然存在,但是信息传播却成为跨越边界,通过媒介技术手段传播信息,促进全球化在更广阔层面交流、分享与互动的重要中介。它所带来的不仅是跨越地区的交往互动,也是对于“边界”概念的消解,以及全球格局的颠覆与重构,这在今天也已成为无需争辩的事实。
(二)全球流动与跨地传播
在全球化语境中,电影的跨地形态使得文化层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动,空间成为无法界定的想象空间,对都市的辨识出现可移植性,需要借助媒介的具体描摹来辨别和更新认知;原有的地理界限被频繁交往打破,地域不再是具体的身份界定因素,这也引起越来越多对于文化身份建构的担忧。“在‘去地域化’和‘跨地域性’语境中,想象变成了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社会力量,成为自我认识、身份定位、意识形态和观念建构的重要因素。”[10]并对于亲身经历与本土经验带来颠覆性作用。吉登斯的“时空延伸”概念呈现了这样的关系:“现场卷入(共同在场的环境)与跨距离的互动(在场和缺场的连接)之间的关联。……不同的社会情境或不同的地域之间的连接方式,成了跨越作为整体的地表的全球性网络。”[1](57)文化多元化正为全球带来全新的文化体验,“在文化帝国主义范式的假设中,全球性的媒介使得文化日趋同质化;而在文化多元主义的研究范式中,地方性媒介被认为使文化异质化。”[3](83)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并不亚于在政治、经济、技术层面的钳制,特别是对于本土民族文化而言,全球与本土维度之间的想象成为一个角力的过程。
汤普森认为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会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超越时空的束缚。麦克卢汉以“地球村”精炼地概括这种对时空距离的超越,而今日媒介传播所带来的“跨地交往”正不断验证“地球村”的预言。今日社会,“人们的经历是媒介化的,因为人们经常是通过媒介与传播来联系彼此的。”[3](序言)媒介与食物、水、衣服、住所等这些必需品同等重要,甚至对有些人来说“如同氧气”,没有媒介(这里指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新媒体)就无法生活。这样的表述放置在上个世纪还会显得略有夸张,然而不过短短十多年,这便成为今天社会,今日生活的“现实”。
来势汹汹的全球扩张让国家边界线逐渐“消弭”的同时,跨国影视公司愈发深入地参与到了这场变革之中。杨伯溆认为“冷战的结束和市场经济的胜利使跨国公司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踏步登上世界舞台。跨国公司所追求的是全球化,它们所指的全球化就是占有世界上一切可以盈利的市场。”[11]跨国公司使国界线不再具有重要意义,令边界不再是具有限定与区隔作用的重要尺度。阿尔君·阿帕杜莱参照亨利·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的生产”、“地域的生产”之观点,思考在全球范围内随着媒介技术不断革新而对传统民族、国家以及地理边界等观念的颠覆。孙绍谊以“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ed)或“跨地域性”(translocalities)来表述对于当代全球化现象的理解,他认为“必须超越过去受限于民族国家或固定地域的思维定势,透视当代文化的转型与契合。”[10](38)对“去地域化”概念,孙绍谊所作的注解是:“一方面是指文化产品的全球消费打破了特定地域和文化消费者原来所享有的与该地域和文化所形成的自然关系,另一方面也要求文化产品在制作和传播的过程中不拘泥于原文化、原地域的限制,力求以‘当地化’、‘情境化’的姿态满足不同文化或国度消费者对产品的不同需求。”[12]依照上述观点可见,当文本呈现出“跨地”、“跨境”、“跨界”、“跨国”等状态之时,地理概念上的地域性区分被替代,呈现出无差异、可移植的空间。
二、全球化想象中的跨地实践
(一)中国电影生产的跨地流动
在这个一切皆变的流动时代中,人类生活看似越来越呈现出自我、主导、自主的倾向,然而在深受相互作用、影响、支配的颠覆后,我们每个人都难以逃脱被深陷于全球流动之中的差异和权力的操控。中国电影通过电影生产与传播流通将不同的地方连接起来的实践活动历史已久远,特别是上海与香港在早期电影业发展中已经率先呈现出跨地交往的特征和趋势。早在1926年香港电影先驱黎民伟就希望能够通过电影传播文化传统,改造社会,并以“电影救国”的理念方式促进国家发展。他试图借助其所创办的上海民新影片公司“通过电影把中国固有的‘超迈之思想、纯洁之道德、敦厚之风俗’介绍给欧美,而且‘同人意向所趋,不独在都会,而在穷乡僻壤之间也’,体现了其用电影促进国富民强的主张。”*出自《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宣言》,载《玉洁冰清》特刊,1926年7月1日民新影片公司出版.转引自赵卫防.香港电影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1-2.本质上向外发展的香港文化呈现出分散、混杂的特征,而反映在电影中便与交叉点、边界、裂隙、关系网、代理商和陌生人的意象紧密关联,呈现出一种跨越本土文化的特征,寻找的是多样性文化交融,倾向于文化的流动与汇聚。
电影的跨地实践促使跨越文化地理边界的景观再造与展现,突破了电影受众固有思维认知中的区域感、地方感和时空界限的限制,阐释了具有全球性特征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多重意义,文化的发展亦为社会的变迁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借鉴。“随着跨民族、跨国界信息的流动,世界上已很少有文化可以独善其身并保持对他者文化的隔绝,文化交流、碰撞、冲突、融合的产生正在无可避免地成为国际文化互动的景观。”[13]全球化浪潮引发世界范围内流动性的加剧,因而这一现实之上的中国电影在以中国大陆为地理集聚核心的同时需要将传播的视野向全球辐射,超越中国电影在国家地理边界上的限制,将全球华人社区作为中国电影跨地实践的分支,对目前多少呈现断裂的特别是与海外华人电影之间联系不紧密的关系进行改善,巩固与全球华人之间的传播与链接,推动本民族电影走出本土,向外学习与借鉴。
(二)跨国拍摄的新趋势
正如电影媒介对于都市的表述中所言:景观是都市的内容,而都市是电影的素材。它们都作为媒介而存在也都以媒介身份展开传播互动。“时间、地点和空间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把其归类为自然的和停滞不变的。”[3](57)全球化意识的提升使得全球化不仅是一种意识观念,更在电影的实践中通过电影拍摄与叙事地点的选择,打造出“世界地图版电影旅游指南”。电影作为旅游指南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香港星影情》即为一本专题介绍香港电影与香港地景的专题“旅游手册”,其主打内容均为香港电影中所出现的香港市区、商业中心等知名地,为的是借电影的名气推广香港旅游业的发展。而“跟着电影去旅行”也成为近年来一些报道中的标题。跟着好莱坞电影我们已经习惯于游走世界,如《变形金刚》系列带着我们不仅去外太空,还让我们从美国人家(主人公的家)翻山越岭来到埃及,在金字塔中找寻“魔方”;彼得·杰克逊通过《霍比特人:意外之旅》让世界各地的观众感受到了旖旎可人的“中土世界”。这个取景于新西兰的怀卡托马塔马塔(Waikato Matamata)离奥克兰167公里的霍比屯拍摄基地,[14]不仅为电影的拍摄提供了广阔空间,还因为电影的全球热映而打开了旅游大门,为新西兰旅游增添了新的观光胜地。
吉尔·布兰斯顿认为“我们应该在文化现代性的大框架内去理解电影,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好是仔细阐述电影的历史、体制和再现,尤其要深入研究处于不同时间、空间、地点的电影受众。……一方面它拒绝采用那些更为传统的批判模式,另一方面它对当今电影的不停变换的界限进行深入探寻。”[15]以好莱坞电影工业为例,情感上的共鸣是好莱坞电影在全球获得成功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好莱坞电影不仅在经济利益上获得全球成功,也在推广美国文化、美国精神、美国价值体系上不遗余力。其在全球获得的巨大影响力固然与电影人才、电影资源、电影技术等因素息息相关,但其电影中所融入与渗透的共通性、接近性,如对于人类情感、人类社会所普遍存在的价值准则的把握,以及电影元素和构成的开放性、多元化等,也都为好莱坞这个梦工厂提供着重重保证。
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旅游成为了绝大多数城市人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很多人会参考媒介信息。当前影视旅游热的兴起就是特例,电影所呈现和塑造的“城市”往往成为人们旅游的热门选择,被重点关注,在文学作品、音像制品中也成为重要的参考借鉴和分析对象。更有大量的网站、电子期刊等专题制作类似“跟着电影去旅行”、“浮光掠影环游世界‘好莱坞电影的全球地标热’”等内容,所制造的地标景观不仅成为全球旅游热门地点,更为其所在的城市带来直接的利益。国内有多个城市也都通过电影影像成为热门旅游景点,如《非诚勿扰》中的西溪湿地、《饮食男女2》中的“西溪一号”等,都将西溪湿地作为取景地点,不仅使西溪湿地知名度大增,也推动其所在城市杭州备受关注,影响力不可小觑。以前专门用作影视拍摄的影视基地也已超越其单一用途,被不断开发成为热门旅游度假景点。这些现象不仅反映了国人生活的重要改变,还直观呈现出了电影对于城市、地方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其对景观的呈现和传播出的信息、释放的信号、阐释的意义,对生活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们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关联、互相作用是促使笔者展开本论题研究的重要起点。
(三)多元互动与身份想象
多元在理论方面是一个空间概念:传统的空间概念指涉一个四周封闭、界限分明的稳定结构,由此产生本地认同,抵御外界入侵。对空间新的阐释认为空间是不稳定的,其边界是多孔的,其内涵是多元的,其性质是不断重新塑造的。*张英进教授在其著作《多元中国:电影与文化论集》中特别就此观点进行了阐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陆、香港与台湾地区之间电影生产、实践在各个层面合作的加速,中国电影工业在多元互动推进的同时,也因地理边界、跨地流动的深入渗透与杂合,电影“身份”成为了被关注、探讨并引发争议的“问题”。新世纪以来,大陆与港台之间交流往来的日常化、正常化带来了多层面的跨越、流动与混合。
今日的中国电影制作团队往往是两岸三地电影人、拍摄技术手段、后期剪辑、营销宣传等环节的协同生产,由于交织错综的合作关系,很难清晰界定一部电影的“身份”该属于哪一个地区。那些更在意差异,更在意自己有别于他人的人群不论这种差异是基于历史,还是基于生物学,或者两者兼有,他们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划出一条界线,要么把它当做一种统治形式,要么把它当做一种抵抗形式。[16]通过寻求与他人之间的差异而建构身份,本身就已经划分出“自我”与“他人”的二元对立,这一“对立”不仅时刻强调差异性,也忽略了同时存在的身份同一性。例如香港电影界,如果将目光只拘泥在对香港影片、电影人身份的关注,将其限定在本土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差异、对立中而屏蔽世界的走向和电影工业发展变迁的全局性思考,那么就会既无法充分呈现今日香港社会面貌,也难以展开有效对话促进香港电影工业“复兴”。
近年来中国电影生态结构日益复杂,合拍片就是其中一个普遍性与典型性并存的电影现象。张英进以“超地区想象”来表述电影跨地互动想象,其实不论是CEPA签订之后的香港电影人集体“北上”,还是台湾电影借助两岸交流而频繁互动,这种港台与大陆电影人的多样汇聚和交流,对于中国电影的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合拍片并非充分意义上的融合,合作也并非仅有合拍片这一途径,但在当前看来合拍片的方式仍旧成为电影创作需求同电影观众、消费诉求的有效结合方式。通过合作一方面试图弥合中国电影本土多地市场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多元互动背后的利益驱动,使两岸电影业的流动与合作更趋频繁,同时“电影表演”也开始向“文化表演”拓展,将文化身份与地理身份植入电影,并在跨地电影实践中建构出对于文化身份的想象。
三、结 语
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们集聚起来,这种集聚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对电影创作本身而言,世界范围内人才的合作与集聚,形成了一种跨国界、跨文化、跨种族的协同合作;另一层意思是指通过电影本身将世界上的最为广泛的普通人集聚在一起,通过阐释电影的内容,在人们的情感、思想、意义、体验中寻找共鸣,获得共通,达成共识。
作为象征符号,电影语言代表着所属群体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内容,显示出广阔的可扩展交往空间,是社会交往有效的粘合剂,也成为当前大众媒介寻求发展的有效突破口。全球化带来的媒介技术发展和社会流动,为中国电影的跨国生产创作带来了新的推动力,这并非是一种“绝对的威胁”,反之,如果将中国电影的跨国传播与发展视作对全球电影市场的积极拓展,既可以为全球电影创作提供更丰富、更广阔的舞台,也可以经由中国电影的全球流动,促使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积极沟通、对话成为可能。
[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56-57.
[2][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
[3][英]特希·兰塔能.媒介与全球化[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18.
[4][英]约翰·厄里.全球复杂性[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
[5][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60.
[6][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
[7][美]萨斯基亚·萨森.全球化及其不满[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17.
[8][美]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序言.
[9]欧阳宏生,梁英.混合与重构:媒介文化的“球土化”[J].现代传播,2005(2):6-9.
[10]孙绍谊.“无地域空间”与怀旧政治:“后九七”香港电影的上海想象[J].文艺研究,2007(11):32-38.
[11]杨伯溆.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
[12]孙绍谊.电影经纬:影像空间与文化全球主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4注释.
[13]吴瑛.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战略[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2-3.
[14]随霍比特人游魔幻新西兰[EB/OL].http://news.xinhuanet.com/fashion/2015-02/02/c_1114195268.htm,2015-02-02.
[15][英]吉尔·布兰斯顿.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
[16][美]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图绘:女性主义与文化交往地理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22.
[责任编辑:詹小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梦’影视创作与传播策略研究”(15ZD01),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新世纪中国城市电影媒介景观建构与传播研究”(Y2016367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冰雪,女,助理研究员,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戏剧影视研究院,浙江 杭州,310018)
J992.6
:A
:1008-6552(2017)03-01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