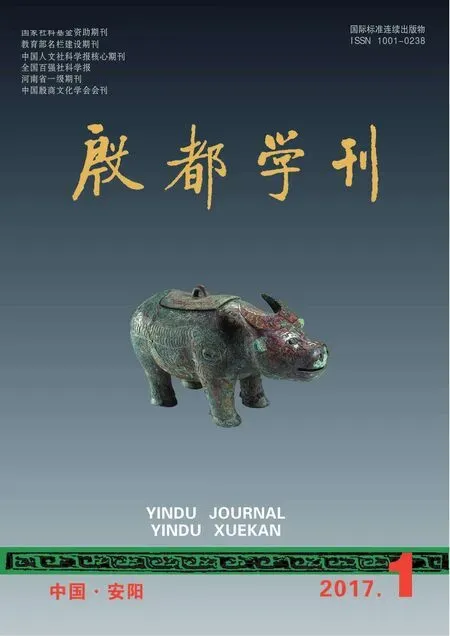《西海纪游草》与纽约城市想象
王锦丽
(1.河南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2.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24)
《西海纪游草》与纽约城市想象
王锦丽1,2
(1.河南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2.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24)
纽约自“西学东渐”开始,就位列于“现代性”输出的西方城市中,成为中国想象现代西方城市的重要空间。本文着重分析了文学中最初的纽约城市叙述,并以“想象”为重要的介入概念,连接了空间文本与空间再现,突出了空间知识生产对于城市意义的赋予过程。最初的纽约城市空间是如何被构建的,体现了晚清文人怎样的想象?这些最初的城市想象又体现了哪些文化差异?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是晚清现代性研究的重要补充,也是考察西方城市如何参与“现代中国”文化想象路径的重要面向。
《西海纪游草》;林针;纽约想象;晚清
一
以“城市现代性”来观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不难觉察所谓“现代性”(Modernity)的城市渊源和西方影响。“现代性”的概念源自欧洲启蒙思想,是关于未来社会的一套哲理设计。[1]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现代性”以“西学东渐”之势进入中国学界,并得到首批接触西方城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力推介。晚清知识分子诸如严复、梁启超、容闳、王韬等,不仅有着西方城市的体验,更是通过译作、著作和现代报刊等媒介,将“西方现代城市”引入中国,并由此更新了中国文学的时间观和空间概念。“这个时间观念改变,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史观念的改变。换言之,他们认为时间是向前进步的、有意义的,是从过去、经过现在而走向未来的时间的概念。”[2]而渗透着西方城市身影的现代空间概念如“群”、“社会”、“国家”,“世界”等,和进化的时间观一起,成为晚清知识分子构想未来中国的重要观念。可见,对于“现代中国”的文化想象一开始便有着西方城市的影响。而纽约从“西学东渐”开始,就一直位列于“现代性”概念输出的西方城市中。不同于巴黎、伦敦等欧洲国家城市,纽约更多是以科技和殖民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学当中。对纽约的城市叙述并不完全是真实城市的再现,往往被赋予了许多并非为城市所独有的意义。[3]本文着重分析了文学中最初的纽约城市叙述,并以“想象”为重要的介入概念,连接了空间文本与空间再现,突出了空间知识生产对于城市意义的赋予过程。最初的纽约城市空间是如何被构建的,体现了晚清文人怎样的想象?这些最初的城市想象又体现了哪些文化差异?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是晚清现代性研究的重要补充,也是考察西方城市如何参与“现代中国”文化想象路径的重要面向。
二
……宫阙嵯峨现,桅樯错杂随。
激波掀火舶,载货运牲骑。
巧驿传千里,公私刻共知。
泉桥承远溜,利用济居夷。……[4](P43)
这大概很难让人想到:这工整的诗句所描述的是竟是美国第一大都会——纽约。当然,诗中所述并非今日之纽约,乃是清朝道光年间纽约都市风貌的惊鸿一瞥。它的作者便是“针程九万夸游迹,笔纪千言备采风”的林针。
林针,字景周,号留轩,今福建福州人。因家道中落,产业又被族人侵占,不得已随家人迁居厦门。正是在厦门,这个1840年以后第一批正式开放的五个口岸之一,林针掌握了外语,靠在洋商那里担任翻译和教授中文为业。道光廿七年(1847年),林针受聘赴美舌耕海外。经过一百四十天的海上艰辛旅程,终于到达美国纽约。在美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游历美国南部,他竟不意亲身体验了一番美国的司法程序:在得知有26位潮州同胞被不法英商诱骗至纽约并受诬入狱之时,他仗义援手最终胜诉,使得同胞脱离苦海得归故里。但是,他也因此被英商记恨而蒙受囹圄之灾,幸而得到美国友人相助才最终得以昭雪。这些见闻轶事在他1849年(道光廿九年)归国之后,著成《西海纪游草》得以传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中美文化交往的史料,而林针也人如其名成为近代东西文化之间穿针引线之人。
《西海纪游草》是近代第一部将纽约城市纳入中国文化视野的记述。它采用中国文学中最为传统和最受重视的文体,较为详细地记录了纽约这一美国都市文明最为突出的代表,是以中国传统解读西方都市的先声。在这以传统文化望向现代都市空间的第一眼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城市日常景观幻灯式的闪现和罗列,述奇猎新的心态浮然纸上,致使城市成为平面化表象化奇观化的“西洋景”。另一方面,城市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现代性的时间维度消弭在文体所带来的文化氛围中,——诗歌和骈体文所代表的古典韵味使得纽约自身鲜活的现代气息同化在庄重雅致的中国韵文中,纽约仅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城市的想象。这一想象的起点就是一幅幅闪现出的纽约“奇景”。
纽约奇观
“足迹半天下,闻观景颇奇。因贫思远客,觅侣往花旗。……”[4](P43)
“……谱海市蜃楼,表新奇之佳话;借镜花水月,发壮丽之大观。……山海奇观,书真难罄;……”[4](P35)
“眼界森临万象,彩笔难描;耳闻奇怪多端,事珠谁记?”[4](P39)
西方城市现代性空间的首次展现是以“奇”而进入中国视野的。异质文化的相遇总不免引人惊奇,尤其是在闭关锁国之后,对世界茫然无知的情况下则更是如此。不仅是林针,彼时任何初游西方城市的中国人都不免合掌称奇:二十年后同文馆的年轻译员张德彝,就用“述奇”、“再述奇”、“三述奇”等*张德彝先后八次出国,共著有八种日记体闻见录,皆以“述奇”为名。作为游记文题,以表达现代城市文化冲击所带来的心理感受。当然,游历异邦是要写出能够足以表现文化差别的异国景致风尚,觅新述奇本也自然,更何况中西文化本就有着巨大的差异,科技迅猛发展的纽约都市的确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在这里我所关注的是这“奇”的文化心态对于空间建构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空间知识和权利的改变。
首先,在传统的“天下观”中,华夷之辨使得地域与文化的差异成为评判民族优劣的依据,在中华文化中心心态的观照下,番邦外族始终处于被检视的边缘地位。更进一步说,在华夷天下的秩序中,异域是不受重视的也不应被重视的;不要说自然地理障碍使得对文化交流较为困难,即使是有机会和条件去了解,“天朝大国”也缺乏去了解的动机。因为一个荒蛮、怪诞和诡异的“他者”的存在是自我正统文化身份确立的前提,也是维持文化中心性,维护文化统治地位的必要。 在这一点上,对外国及外国人奇异化的叙述和想象可说是自然有之。但是,对于林针,张德彝,李圭等人而言,此时“奇”的文化心态已非“华夷之辨”的承袭,虽然仍有华夷之分却少有鄙夷蔑视的故意,更多是对日益强大的西方的惊叹,对先进科技的叹服和些许对现代生活的向往。伴随着城市游历者羡奇的目光,科技成为关注的焦点,其强大的冲击力使得传统的“天下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晚清人士对科技器物和现代社会文明风尚的集体沉溺式叙述,无意中透露出暗中不断比较中的对中华文化中心性的质疑。这种质疑同样表现在对城市问题的较少描述,以及对有违中国传统道德的西方社会现象简单而表面化的批评。例如:“四毒冲天,人有奸淫邪盗(斯亦不免)。”“瓜田纳履,世复何疑;李下整冠,人无旁论。(归舟之出海,主事者每抱客妇在怀,丑态难状,恬不为怪)。”[5](P38-39)可见,虽然传统文化仍然是我们评价异文化时的基础,但是有违传统道德或者与中国文化相冲突的现象,已经不再被当做主要方面来对待,也不会因此而否定他者的文化价值,甚至做“野蛮”和“诡异”的想象。文化容忍度的提高不仅暗示着由“天下观”到“世界观”的改变,而且也预示着科技霸权的建立,西方现代性的侵入和中国传统文化主体身份认同的危机。
其次,这样的文化心理更构成了一种观察城市的模式,这种模式并不是要提供对城市生活中理性的描述,它的意图是捕捉城市空间中的奇观异象以构建差异化突出明显的空间,达到令人惊叹印象深刻的效果。
“百丈之楼台重叠,铁石参差(以石为瓦,各家兼竖铁支,自地至屋顶,以防电患);万家之亭榭嵯峨,桅樯错杂(学校行店以及舟车,浩瀚而齐整)。舻舳出洋入口,引水掀轮(货物出口无饷,而入税甚重。以火烟舟引水,时行百里);街衢运货行装,拖车驭马(无肩挑背负之役)。浑浑则老少安怀,嬉嬉而男女混杂(男女出入,携手同行)。田园为重,农夫乐岁兴歌;山海之珍,商贾应墟载市(每七日为安息,期则官民罢业)。博古院明灯幻影,彩焕云霄(有一院集天下珍奇任人游玩,楼上悬灯,运用机括,变幻可观);巧驿传密事急邮,支联脉络。暗用廿六文字,隔省俄通(每百步竖两木,木上横架铁线,以胆矾、磁石、水银等物,兼用活轨,将廿六字母为暗号。不论政务商情,顷刻可通万里。予知其法之详);沿开百里河源,四民资益(地名纽约克,为花旗之大马头,番人毕集。初患无水,故沿开至百里外,用铁管为水筒藏于地中,以承河溜;兼筑石室以蓄水,高与楼齐,且积水可供四亿人民四月之需。各家楼台,暗藏铜管于壁上,以承放清浊之水,极工尽巧。而平地喷水,高出数长,如天花乱坠)。”[4](P36)
这便是林针笔下的纽约(文中为纽约克),所有的城市景观都必有引人侧目之处:楼台的百丈,博古院中的珍奇,奇巧的灯影,时行百里的舳舻,瞬间通讯万里的机巧,暗藏壁上的水管,天花乱坠的喷水……。没有一处是惯常山水,没有一笔不流露惊羡之情。除去对纽约城市基础设施和现代科技的惊叹,作者对城市公共机构的反映,也选取令人耳目一新的方面进行描述,例如:反映司法的文明:“郡邑有司,置邢不用(其法:准原被告各携状师,并廿四耆老当堂证驳,负者金作赎邢,槛作罪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刻字为碑,瞽盲摩读(盲瞽院华丽非常,刻板为书,使盲人摸读);捐金置舍,孤寡栽培(设院以济孤寡鳏独)。”现代传媒的发达:“事刊传闻,亏行难藏漏屋(大政细务,以及四海新文,日印于纸,传扬四方,故官民无私受授之弊。)”医院的验尸:“医精剖割,验伤特地停棺。(每省有一医馆,传方济世。凡贫民入其中就医,虽免谢金,或病致死,即剖尸验病,有不从者,即停棺细验。”[4](P36-41)以上种种现代经验在勾勒出一个新型社会的积极面貌,言语所至不仅点出空间记忆的亮点,更聚集了这些亮点形成一束照进纽约都市的现代之光,敞亮出空间种种欲望,而这些欲望的产生与其说来自城市的现实,毋宁说更多来自空间叙述者对现代性的想象。虽然叙述者的在场,可以坐实文中所述种种的发生,如博物院,盲人院,医馆等等的真实存在,但是“置邢不用”“华丽非常”等却隐含着跨文化的比较,直至“亏行难藏漏屋”“传扬四方,故官民无私受授之弊”的想象。这想象藏匿着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反省批判,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些许憧憬和期待。这一点在论及城市社会风尚时便尤为突出:如论及男女的平等,风气开放时,就描写了学校有“男师女傅”,“男女自婚配”,市井中“男女混杂”等现实,更添加了“宜其有室家之乐矣”,“春风入座,……;宋玉东墙……”的传统想象。对异国女性的描述则活脱脱是传统文化中柔颈蛮腰的佳人:“桃花上马,蛮姨领露蝤蛴;油壁香车,游女鞭含夕照。”“蛮腰舞掌,轻鸿远渡重渊;莺啭歌檀,玉佩声来月下。”[4](P39)
难能可贵的是,林针并没有完全目眩于奇景大观之中,对于城市中存在的歧视与不公,殖民的阴暗也能加以着墨:“四毒冲天,人有奸淫邪盗(斯亦不免)。”;“屡夺亚非利加黑面,卖其地为奴。”;“远国他邦,道不同目为愚蠢(目崇信鬼神、奉祀土木偶者为贱鄙罪人。)”;“黑面生充下陈,毕世相承(英人以黑面卖于其地,遂世为贱役。)”[4](P37-38)只是在太过炫目的奇景描述下,城市的另一面退却为只字片语的暗点,整个城市依然被想象为“一团和气,境无流丐僧尼。”这样一显一隐的城市空间建构突出了纽约城市的科技性和先进性,而城市的黑暗和罪恶仅仅是发达文明瑕不掩瑜的存在,并没有得到等量的观察,更勿论理性的描述和审慎的思考了。当然,纽约的城市奇观如果脱离中国的传统,不仅无法构建奇异的“他者”形象,也无法完成西方现代性的输入和理解,尽管在当时的语境中,很难找到合适的现代表达,林针还是创造性地用诗句和骈文勾勒出一个带有神秘感的纽约魅影。
科技奇景
采用骈文这种古典文样来表述现代城市这前所未有的新内容,也算是晚清现代性的一种表征,是传统文化吸纳现代内容的一个开始了吧。然而,工整的句式终究遭遇了表意的尴尬,作者不得不加上长长的注解,使之成为中西融合尝试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虽然差强人意,作者还是尽量定格了一幅幅城市奇景:高楼大厦,参差亭台,舟车川流,男女携游……,如果将注释看作背景介绍,工整的句式,意象的叠加,竟使得空间景致如同幻灯一样,一步一景,一格一观地罗列出来:博物馆,孤老院、盲人院、医馆、……。散点式的空间叙述竟仿佛现代主义的意识流表现手法,一明一暗的骈文和注释,让人联想到庞德《在地铁站》的光暗魅影。如果城市是行旅者的阅读文本,那么这不经意间表现出的散漫视角和漂移的城市心态,是现实的表达还是现代的解读呢?
虽然传统的文体最终抑制了更多现代想象解读的可能,但是毕竟现代城市空间的碎片连同镶嵌其本身的现代光影留驻在文本空间中。也正如此,若非借助更多详细的解释,恐怕很难理解经过传统编码过,被中国文化译制的纽约城市空间。例如:“楼头灯变幻,镜里影迷离”[4](P44)字面毫无悬念,但是此“灯”此“镜”却不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烛照之“灯”和理容之“镜”。为了进一步说明,作者在《西海纪游草·自序》中写道:“博古院明灯幻影,彩焕云霄(有一院集天下珍奇任人游玩,楼上悬灯,运用机括,变幻可观)”;“山川人物,镜中指日留形(有神镜,炼药能借日光以照花鸟人物,顷刻留模,余详其法)”。[4](P36-38)现代读者此时大概可以猜得到此“灯”原来指的是幻灯,“镜”指的是摄影。再举一例:“巧驿传千里,公私刻共知。”[4](P43)诗句虽无生僻文字但却让人不明了了。只有联系序文中的描述方知大概:“巧驿传密事急邮,支联脉络。暗用廿六文字,隔省俄通(每百步竖两木,木上横架铁线,以胆矾、磁石、水银等物,兼用活轨,将廿六字母为暗号。不论政务商情,顷刻可通万里。予知其法之详)”;“事刊传闻,亏行难藏漏屋(大政细务,以及四海新文,日引于纸,传扬四方,故宫民无私受授之弊)”[4](P36-38)其实前者描述了新科技:电报;后者描述了新传媒:新闻报纸。试想,连现代读者都要揣测的文意如何能使彼时的读者完全明了呢?所以,林针虽然做了许多的注释,但是在缺少科技常识和世界知识的中国语境中,机械纽约和科技纽约的空间建构也最多是忽明忽暗的浮光掠影。
因此,对科技的沉溺叙述倘若不能使人昭昭,明白其背后的科学原理,其结果可能沦为一种以科学面目出现的新幻术或魔法而已。在中国民间,曾有许多江湖术士利用一些小的科学原理配合相应的道具,如药粉、宝剑、银针等演出名目繁多的戏码,以达到或诈骗或蛊惑等不同的不可名言的目的。而宗教、迷信、神怪传说等,亦为此提供了存在的温床。在这样的语境中,不要说是毫无科学常识的百姓,就连识文断字的先生恐怕也未必全然明了林针罗列的种种科技奇观。而这些描述,因为使用了许多传统词汇,反因母语词汇的语意晦暗,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偏差,以及阅读者科技常识的缺失而导致完全不同的解读与想象。比如,对温度计的描述,“或风或雨,暴狂示兆于悬针;乍暑乍寒,冷暖旋龟于画指(以玻璃管装水银,为风雨暑寒针)”。在不明就里的阅读者眼中,其神奇性不亚于术士手中呼风唤雨的神器。再者,为了加强描述异域科技和风尚所带来的强烈观感,林针用了一些汉语词汇,其本身就有飘渺仙境或鬼魅仙子的联想,如:海市蜃楼、傀儡、鬼气蛙声、逍遥云汉、幻影、彩焕云霄、鬼斧丛奇、桃源、星娥、山海奇观等。虽然作者本意是加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但是在两种文化语境差异很大的情况下, 原本理性的科学却极可能成为极魔幻的外衣,以致述者愈积极愈高昂,仪器功能愈强大,在茫然无知的读者眼中则幻化得愈离奇,愈神秘。科技在这样的情景中为纽约投下的是一层神秘的虚无感和飘渺感,尤如一憧憧现代魅影。
《西海纪游草》是晚清游记中对纽约进行较早也较为详细城市观察的作品,林针在体验了现代城市之后,不仅感慨“去日之观天坐井,语判齐东;年来只测海窥蠡,气吞泰岱。”也非常希望能以此文鼓励更多人走向世界,开阔视野。但是,从上文分析可见,林针对都市文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表面,城市生活的时间的维度被抽离,连续而鲜活的日常生活被碎片化的城市表象和奇观化的城市景观所取代,碎片的空间成为纽约城市现代性的表述。而在缺乏科技语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叙述又不免沦为一幅幅飘渺的“海市蜃楼”。再者,林针个人的社会影响力也非常有限,“其人其事纵有时代的意义”,[5]却最终沉寂于历史之中。要唤醒“铁屋子”里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用理性去除蒙昧的魅影,那就必待一场革命了。
三
当科技的发展使得地域的屏障不再成为文化的藩篱,异质文化的相遇与碰撞就成为必然。当晚清人士远渡重洋身处异邦,时空的改变使旅行本身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跨文化实践。就时间而言,1840年以后的中国正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原有的封建社会结构受到外来殖民势力的打击正逐步解体。在由多个帝国主义构成的政治力量的胁迫下,中国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中来。此时,上至身负外交使命的官员,下至背井离乡的华工,无论是为国家命运还是为个人生计,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使得中国各阶层人士的跨海之行,在对异质文化认知和发现的一般意义上,多出了对已有传统世界观与价值体系进行重新思考的现代意义。由此,不仅开启了中国社会对西学新知的吸纳热潮,更是带来了对传统文化最为深刻的反省与批判。例如,林针的《西海纪游草》,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志刚《初使泰西记》,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等。 在空间的意义上,当晚清人士漂洋过海,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已非传统观念中的“天下”而是现代意义的“世界”,其所面对的也非“番邦属国”而是现代的“国家”,更准确地说是现代的“都市”——西方文明的集大成体现。在这样的异质空间中,旅行者体验着文化主体与他者,民族主义与殖民,消费主义与资本扩张等等现代意识。这样的空间现代性实践开启了晚清对现代西方城市空间的各种记述和想象。
由于文类的差异,游记中的城市叙述较之小说而言是有较大的写实性,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初出国门开眼看世界的晚清人士,对于西方文化和现代都市经验是几无认识的。他们对于现代都市文化的观察和体验也因此无法脱出旧有的意识和经验。在现代都市文明上尚未在中国完全展现之前,对于现代都市的解读和记述无疑是以传统观照现代的想象。西方的都市空间在游历者的空间实践中,经过城市阅读者的解码和编码最终再现于文本中。如果说空间的再现是一个空间被概念化的过程,那么处于异质文化之间的空间生产,则不免带有以传统的概念解析异域空间的过程;被传统概念译制的再现的异域,是有别于真实空间同时又包含实在空间的“译制空间”,——尤如热闹而让人不明就里的“西洋景”。
[1]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641.
[2]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2.
[3]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16.
[4]林针.西海纪游草[A].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C].长沙:岳麓书社,1985.43.
[5]钟叔河.从坐井观天到以蠡测海[A].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5.23.
[责任编辑:舟舵]
2016-12-11
王锦丽(1974-),女,河南郑州人,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I206
A
1001-0238(2017)01-009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