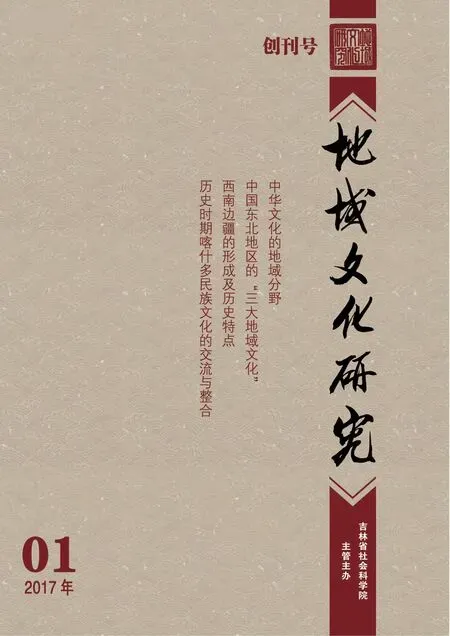历史时期喀什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
——兼论维吾尔文化形成的基础
赵炳清
历史时期喀什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
——兼论维吾尔文化形成的基础
赵炳清
喀什是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化分布的重要地区,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持续发生。从喀什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动因来看,民族、人口的空间移动,导致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化因素不断介入,使得喀什的民族文化始终处于持续的分化、重组和整合中,并在政治与宗教的强势推动下,形成以伊斯兰文化为特质的维吾尔文化。喀什的地理环境,是维吾尔文化形成的自然基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地理格局,不仅现代如此,而且古代也是如此。这种民族地理格局,十分有利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从而形成新的民族文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的文化交流与整合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历史文化现象,那么研究揭示这种历史文化现象,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喀什位于中国西北边陲,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分布地区,文化的交流和整合持续频繁地发生,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形成了具有伊斯兰文化为特质的维吾尔文化,并一直是我国现代维吾尔族的聚居之地。目前,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中,喀什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窗口,必将在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笔者试图探讨历史时期喀什①本文论述的“喀什”,不是专指今喀什市区,而是指以喀什为中心的塔里木盆地西南缘,包括今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州大部分地区。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历程和动因,并兼及维吾尔文化形成的基础。②关于维吾尔族或维吾尔文化的形成问题,学术界以往讨论颇多,没有形成共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古回鹘文化发生明显的变化,在突厥—伊斯兰化影响下,在共同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因此,学者们在讨论维吾尔族或维吾尔文化形成时,多关注突厥—伊斯兰化的作用,如魏良弢的《〈福乐智慧〉与喀喇汗王朝的文化整合》(《西域研究》2000年第3期)、罗淑荣的《喀喇汗朝新型文化形态:突厥—伊斯兰文化表征》(《新疆社科论坛》2005年第4期)、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满的《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社会文化》(《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等,而忽视了其所产生的地域基础。其实,一个新的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形成,是离不开其所在的地域的地理环境的。喀什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喀什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从而形成了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文化传统,无疑应是维吾尔族或维吾尔文化形成的基础。因此,本文以长时段为视角,系统考察历史时期喀什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喀什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地理环境
喀什,全称“喀什噶尔”,地处欧亚大陆中部,我国西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这里三面环山,一面敞开。北有天山南脉横卧,西有帕米尔高原耸立,南部是绵亘东西的喀喇昆仑山,东部为一望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诸山和沙漠之间,有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冲积平原形成的叶尔羌河绿洲和喀什噶尔绿洲。这种草地、戈壁、绿洲相间分布的空间形态,为不同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
从区域的地貌形态来看,喀什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既相对独立又相联系的地理单元,即帕米尔高原与昆仑山山区,叶尔羌河绿洲区和喀什噶尔绿洲区,形成塔什库尔干、莎车、喀什三个地域中心。这样的空间架构又为民族文化的多元化提供基本的地域条件。比如在汉代的西域三十六国中,塔什库尔干一带就形成蒲犁国,经济形态以游牧为主,被称为“行国”;喀什市、疏附县、疏勒县、伽师县一带形成了疏勒国,莎车一带形成了莎车国,由于在绿洲上,这些民族以农耕为主,称为“城郭诸国”。另外,还有依耐(今英吉沙)、子合国(今叶城)等一些小的地域中心。在这些地域中心中,喀什由于位于区域内最大的绿洲上,是欧亚大陆间的通衢枢纽,因而成为全区域的中心。当喀什出现强有力的民族统治或内地中央王朝控制的时候,区域内就会出现统一的政权,民族文化一体化的趋势和局面也会出现,多民族文化的整合就会得到加强。据《魏略·西戎传》记载,三国时期,喀什得到了统一,当时“桢中国、莎车国、竭石国、渠沙国、西夜国、依耐国、蒲犁国、亿若国、榆令国、捐毒国、休循国、琴国皆并属疏勒”①见《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60页。。疏勒国的统一,必然会促进喀什民族文化的一体化。
从文化地理区位来看,喀什由于位于亚欧大陆腹心地区,向南向西翻越帕米尔高原,即进入南亚印度文化与中亚伊斯兰文化区域,向东向北即进入中原文化与蒙古文化区域。由于这种地缘上的优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喀什先后处于古代南亚印度的佛教文化、中亚波斯文化、突厥文化、西亚伊斯兰文化和东亚中原文化、蒙古文化等的交汇影响,因而也使得喀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的特色。而历史时期喀什民族的更替变化,也使得喀什的民族文化处于不断的分化、重组和整合中,新形成的民族文化无疑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别是在内地中央王朝的统辖时期,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传入,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原文化的传入,给当时的民族文化赋予了新的特色,增强了对内地的文化认同和政治上的归属感。如在唐朝之后,在喀什建立的喀喇汗王朝的大汗常在自己的名称前冠以“桃花石汗”。《突厥语词典》载:“桃花石──此乃摩秦的名称。摩秦距契丹有四个月路程。秦本来分为三部:上秦在东,是为桃花石;中秦为契丹;下秦为八儿罕,而八儿罕就是喀什噶尔。但在今日,桃花石被称为摩秦,契丹被称为秦”②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鉴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显然,“桃花石”就是“中国”之意,大汗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君主”,王朝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此,这种农牧相间的自然环境与诸多文化交汇影响的人文环境,决定了喀什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是喀什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的地域基础。
二、喀什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历程
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是新疆民族史上最为活跃的阶段之一。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①《汉书》卷9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1页。。实数当不止此,一个部族或一个中心聚落皆称为“国”。在喀什就存在着莎车国、竭石国、渠沙国、西夜国、依耐国、蒲犁国、无雷国、亿若国、榆令国、捐毒国、休循国、疏勒国、尉头国等。在这些“国”中,居民种属各异。据《魏略·西戎记》记载:“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羌、黄牛羌,各有酋豪。”②见《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59页。上述诸国中应存在着羌人种族,如《汉书·西域传》记:“西夜国,王号子合王……蒲犁及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③《汉书》卷9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3页。可见,西夜国、依耐国、蒲犁国、无雷国皆为羌人之属。又同书记载休循国“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④《汉书》卷9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7页。;捐毒国“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领,本塞种也”⑤《汉书》卷9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7页。;尉头国“田畜随水草,衣服类乌孙”⑥《汉书》卷9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8页。。此三国属于塞人种族。受空间架构的影响,这些“随水草”的羌人和塞人由于经济形态的一致性,应已开始了文化上的交流与整合。如无雷国“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⑦《汉书》卷9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4页。,显然是受到了塞人文化影响的羌人。
在喀什的绿洲上,羌人和塞人则是都走上了农业定居发展的道路,形成了疏勒、莎车等城郭国家。由于位于丝绸之路的南北要道上,使者、商人、士卒、僧侣,来往频繁,因此,这些城郭国家的文化形态无疑更加开放与多元,并且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人员往来的加剧,文化形态上就逐步趋向一致。同时,与“随水草”的“行国”相比,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城郭国家都处于相对先进的地位,而且“行国”还寄田于城郭国家⑧《汉书·西域传》中记载,蒲犁“寄田莎车”;依耐国“少谷,寄田疏勒、莎车”。见《汉书》卷9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3页。。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更加促进了“行国”对城郭国家的文化向往,有利于整个区域多民族文化整合趋势的进一步发展。
在西汉统一西域之前,喀什诸国受到匈奴的统治和奴役,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⑨《汉书》卷9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2页。。汉武帝时期,为了联合西域民族,共同打击匈奴。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张骞的出使,加深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互相了解。此后,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西域各国的使节和商人也接踵而来。喀什诸国也当在其中,承接着来自内地的精美的丝绸织品和各种手工业品,同时,也承接着中原汉文化的熏陶。
西域都护府设立后,喀什诸国开始隶属于中国古代中央政府,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也更加广泛和深入。如史书记载:汉宣帝时,莎车国王无子,死后,“莎车国人计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因此上书请求在内地学习的乌孙公主的儿子万年为王,“汉许之,遣使者奚充国送万年”。①《汉书》卷96《西域传·莎车国》,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7页。再如疏勒王以“成”、“忠”等命名也显然是受到汉文化影响。东汉时期,疏勒国成为班超经营西域的基地。内地传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有力地促进了疏勒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达10余万,军队有3万人,是当时喀什诸国中最为强大的国家,初步具备了统一诸国的实力。公元87年,班超在疏勒调集于阗等国军队征服依附于北匈奴的莎车。公元90年,班超率领疏勒坚壁清野,成功击退月氏贵霜王朝的入侵。班超经营西域的成功,是离不开疏勒等国的支持,也表达了疏勒一心向汉,维护统一的真挚情怀。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原汉文化对喀什诸国的民族文化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一些上层贵族较多使用汉语,汉文化程度很高。②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莎车王延“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延之后,莎车王先后名“康”“贤”等,并领汉大将军印绶。见《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3页。疏勒王也先后以“成”“忠”“安国”等名,臣磐还拜汉大都尉印。见《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6页。
汉祚衰微之后,西域诸国兼并过程加剧,到魏晋之世,已合并成疏勒、龟兹、于阗、鄯善、焉耆、高昌六大政治实体。喀什诸国一统于疏勒,使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持续而大规模地发生。这时,印欧血统的塞人与蒙古人种的羌人相融合,人种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但疏勒国的居民却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魏书·西域传》记其俗曰“人手足皆六指,产子非六指者即不育”③《魏书》卷102《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8页,《北史·西域传》所记悉同。可知手足长六个指头是当地居民的一大特征。洛克希尔记述西藏人特征为:“在西藏所观察各点中,普遍最易发现的畸形即系六指,通常自拇指之旁分歧,然有时也发生在手掌之中,即小指密接之处。”疏勒重六指的风俗与此一致,藏族属西羌。④参见薛宗正《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5页。可见,疏勒的主体民族仍为羌人。到隋唐之世,疏勒的民族种属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唐西域记》记载:佉沙国“其俗生子,押头匾榹,容貌粗鄙,文身绿睛”⑤(唐)玄奘、辨机著,季羡林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95页。。《新唐书·西域传》也记载:“疏勒国,一曰佉沙……生子亦夹头取扁,其人文身碧瞳。”⑥《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3页。可见,“重六指”的民俗被“夹头取扁”的民俗取代,人种明显呈现为“文身碧瞳”的印欧血统特征。
在这一历史时期,除了原喀什诸国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外,其他一些民族也先后进入喀什,不仅促进喀什民族文化进一步多元化,而且还改变了喀什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粟特人的融入。粟特人原是生活在中亚河中地区操中古东伊兰语的民族,在南北朝时期建立了康、安、米、曹、石、何等城邦,汉文史籍谓之“昭武九姓”。由于地处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因此,作为丝路贸易集散地和中转站的喀什,有大量的粟特人到此经商并定居。直到11世纪,喀什噶尔城郊还有大批的操粟特语的村落,这在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辞典》中就有明确记载,说这些土著居民操“坎杰克语”;突厥称西域康居国为“坎杰克”,而康居正是粟特人的故乡。他们的加入,改变了喀什居民的人种特征,并逐步形成以粟特文化为主体的而兼容其他民族文化的复合文化形态。
在唐代,喀什处于我国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关系十分密切。唐政府在喀什除了设立军镇外,还设置了疏勒都督府,都督多由疏勒王担任,代表唐中央管理地方行政事务。当时驻扎在疏勒的军队称疏勒军,兵员多来自内地,用于戍边作战。为维护地方经济的发展,保障军费的供给,唐政府在疏勒进行屯田和征收商税①《唐六典》卷7“屯田郎中”载:河西道“疏勒七屯”,见李林甫等著,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23页。《新唐书·西域传》(上)载:“开元七年,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0页。。内地运往喀什的多是丝绸、瓷器等,喀什输往内地多是香料、玉石等。受到先进的中原汉文化的吸引,一些疏勒王族和僧人纷纷前往长安学习②《新唐书·裴玢传》载:“裴玢,五世祖纠,本王疏勒,武德中来朝,拜鹰扬大将军,封天山郡公。”见《新唐书》卷110《裴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29页。《宋高僧传》卷5《唐京师西明寺慧琳传》载:“释慧琳,姓裴氏,疏勒国人也”。见(宋)释赞宁:《宋高僧传》,载《中华大藏经》第6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5页。。疏勒音乐、舞蹈传入内地。同时,汉文化也深入影响着喀什的民族文化。疏勒王都由唐政府册封,成为唐政府管理喀什的地方官员;由内地徙边的汉民、汉军与汉人官员或一些汉僧,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和技术,如疏勒也有汉大云寺,由汉僧主持③见罗振玉编《敦煌石室遗书·慧超往五天竺国传》,1909年12月诵芬室刊行。。在这种文化交流中,汉文化无疑处于主导地位,深刻地吸引和改变着喀什民族文化,使得喀什的民族文化具有了新的特质,就是对中原汉文化产生了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
安史之乱后,来自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奴隶主逐渐占据了西域,喀什当在其中。但随着漠北回鹘汗国的灭亡,回鹘大部的西迁,吐蕃在西域的统治逐步解体。一些突厥部族如样磨、葛逻禄进入喀什,成为新的统治民族④佚名著,王治来、周锡娟译:《世界境域志》:“喀什噶尔,属中国,但位于样磨、吐蕃、黠戛斯与中国之间的边境上。喀什噶尔的首领们往昔是葛逻禄人或样磨人。”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内部刊行,第64-66页。,在由游牧转变为定居的过程中,他们与喀什原有民族相融合,开始了喀什民族文化的突厥化历程。喀喇汗王朝⑤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即是哪一个民族创建的,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是众说纷纭。魏良弢先生在其著作《喀喇汗王朝史稿》中对这一问题做了归纳总结,共计有七种说法,即回鹘说、土库曼说、样磨说、葛逻禄说、葛逻禄—样磨说、处月说、突厥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29页)。俄国巴尔托尔德先主样磨说,后又改为处月说(《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75-77页);德国普里查克则力主葛逻禄说(《论喀拉汗朝史》,原载德国《伊斯兰学杂志》第31卷第1册,柏林,1953年);国内学者以魏良弢为代表主张回鹘说(《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及其名称》,《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建立后,喀什噶尔成为王朝的两都之一,大量的回鹘部落迁入喀什,更加推动了喀什民族文化的突厥化历程。在突厥化的同时,伊斯兰教也传入喀什。喀喇汗王朝的王族接受了伊斯兰教,并将其立为国教,要求全体国民必须信仰。这样,在喀什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伊斯兰教作为居民的共同信仰,在使各种族文化趋于统一、各族习俗趋于规范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民族同化与被同化同时进行,文化浸入和濡染持续发生,语言的融合与扩散大范围地展开,这就为新的民族及文化产生准备了条件。到喀喇汗王朝后期,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已基本完成,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和共同民族心理的相对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基本形成,近世维吾尔族就在喀什产生了。
从成书于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福乐智慧》《突厥语词典》和《真理入门》等著作来看,当时喀什的民族文化主要整合了东方的汉文化、突厥文化,西方的伊斯兰文化、波斯文化和回鹘的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以伊斯兰文化为特质,以哈卡尼耶语为书面用语的维吾尔文化。
西辽时期,是中原汉文化又一次西渐时期。汉语和汉文是西辽政府的官方语言和文字①陈垣:《西域人华化考》卷1,《励耘书屋丛刻》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页。,无疑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作为属国的喀什维吾尔文化应是受到了汉文化潜移默化的浸润。在蒙元帝国与察合台后汗时期,喀什维吾尔文化进一步伊斯兰化。一些入居于此的蒙古部族,皈依了伊斯兰教,使得他们自身的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异,成为了近代维吾尔族的一个分子。这时,回鹘文逐渐被察合台文取代,教会发生分裂,出现“白山派”与“黑山派”的争斗。
清代,喀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汉人、满人以及中亚人、英国人、俄国人等的进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喀什单一的民族文化结构,推动了族际文化的相互交流。今天,喀什的民族文化更加繁荣,各民族互相学习,相互交流,和睦共处,共同发展。
从上述喀什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民族、人口的空间移动,导致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化因素不断介入喀什,使得喀什的民族文化始终处于持续的分化、重组和整合中,并在政治的强势推动下,以伊斯兰教为主要载体,形成了以伊斯兰文化为特质的维吾尔文化。
三、喀什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主要动因
推动历史时期喀什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原因有很多,既有物质文化交流的需要,也有精神文化的深层次融合。各种不同文化形态持续不断地接触、碰撞和融合,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化。因此,纵观喀什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历程,其主要动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同经济形式的转化和物质文化交流
由于喀什的空间架构影响,在绿洲上的民族往往发展为农业定居的经济形态,而在山区和高原上的民族则发展为随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方式。这两种经济方式是互补的,农耕民族需要畜牧民族的畜力和肉类、毛皮制品,而畜牧民族则需要农耕民族的粮食和手工制品。各有所需的物质文化交流,是造成这两种不同经济形式的文化进行交流的直接动因。《汉书·西域传》中记载,当时的蒲犁“寄田莎车”,依耐国“少谷,寄田疏勒、莎车”,这种经济上的依赖与互助,无疑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整合,为魏晋时期疏勒的一统奠定了基础。
此外,一些游牧民族进入喀什绿洲,受地理生存环境的变化和农耕民族的影响,纷纷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转化为农业定居的经济形式。生产方式的转变,必然引起本民族文化的变异,以适应新的地理环境。如回鹘入主喀什地区后,生活方式由原先居住的穹庐似的毡房变为土木结构的房屋。一般民宅都围有院墙,院中种植花果。饮食由以畜产品为主转变为以面食为主,并佐以干果或果酱。代步除了原来的骑马而外,还出现了以车代步,贫者坐驴车,富者多坐马车。游牧民族文化的变化,是接受了农耕民族文化浸染的结果,其实质上是喀什民族文化的整合。
由于处于丝绸之路的要道上,喀什商业十分发达,自古以来商旅就不绝于途。西汉初张骞通西域时,这里就“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①《汉书》卷9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8页。,进行商品的集市贸易,可以说是当时西域的贸易中心。班固曾发书让班超在疏勒购买商品。到了唐代,喀什的商品贸易有了更大的发展。玄宗在开元七年(719),曾下令喀什征收商税。喀喇汗王朝时期,喀什的商业贸易在前代的基础上是更加兴盛。作为王朝的经济中心,无论是同东方的宋、辽、西夏,还是同南方、西方的印度、阿富汗、伊朗及西亚、北非和东南欧,都保持着频繁的商业往来。《福乐智慧》中对此有形象的描述,“大地裹上了绿绒,契丹商队运来了中国商品”②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著,耿世民、魏萃一译:《福乐智慧》,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页。,“如果砍倒了中国商队的旗帜,几万种珍宝从哪里来?”③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著,耿世民、魏萃一译:《福乐智慧》,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0页。不同时期的各地商人、使团的汇集,给不同时期的喀什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使得喀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色。在汉唐时期,喀什民族文化无疑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最深,除了政治因素而外,人员的频繁往来是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喀喇汗王朝时期,在喀什流传着中原汉文化、中亚的伊斯兰文化、突厥文化等。在王朝的钱币考古中,就可见此等情况。1980年在阿图什逊他克乡发现了一个钱币窖藏,除了喀喇汗王朝自制的钱币外,还有东方宋朝的钱币,中亚伽兹纳王朝和塞尔柱王朝的钱币。④蒋其祥:《新疆黑汗朝钱币》,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46页。据《突厥语词典》记载,当时关内的铜钱在王朝的市场上通用。⑤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词典》维文版,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58页。货物的四至,商人的云集,导致不同体系的文化在此交流、涵化,使得喀什民族文化具有了不同的特质,促进了喀什民族文化的进一步整合。
不同经济形式的转化,给喀什民族文化带来了新的文化因素,刺激了原有民族文化的转变。物质文化的交流,使得不同体系的文化在此交汇融合,促进了喀什民族文化的多元化。这些都推动了喀什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是喀什的地理环境和区位优势所决定的。
(二)多民族语言的交流与融合
民族语言作为民族文化中最稳定的因子,其吸收、移植、借用其他民族文化成分显然要滞后于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多民族分布的喀什,随着民族迁移、人员往来的不断变化,民族语言的融合也持续发生,反过来又推动了喀什民族文化的深层次整合,最终形成具有共同语言的维吾尔文化。
在秦汉之世,喀什应主要流行羌语和塞语。随着中原汉文化的传入,汉语也成为上层贵族使用的语言。魏晋时期,喀什诸国一统于疏勒,喀什民族文化一体化得到发展,其语言的融合应也产生。近世学者在喀什噶尔西北发现了一种尚未完全破解的语言文字托姆舒克语,初步判断比龟兹语或焉耆语都更为古老,被林梅村称之为疏勒语。⑥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在隋唐之际,喀什的民族语言融合应是进一步加强,但还存在着地域的差异。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佉沙国“其文字,取则印度,虽有删讹,颇存体势,语言词调,异于诸国”⑦(唐)玄奘、辨机著,季羡林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95页。;朅盘陀国(今塔什库尔干)“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⑧(唐)玄奘、辨机著,季羡林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83页。;乌铩国(今英吉沙)“文字、语言,少同佉沙国”①(唐)玄奘、辨机著,季羡林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90页。。
粟特人的入居,不仅仅改变了喀什居民的人种特征,而且其语言也逐步融合了汉藏语系的羌语,并仿照印度婆罗迷文字创制了文字,而成为喀什的民族通用语言。虽然隋唐两代在正史中仍称喀什为“疏勒”,但在当地的居民和一些僧人的纪行中却称为“佉沙国”“伽师袛离”“伽师佶黎”等②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称为今喀什为“佉沙”,《往五天竺传》中慧超称为“伽师袛离”,而疏勒国人的慧琳却称自己的家乡为“伽师佶黎”,见《大唐西域记校注》注释(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96页。。据学者研究,“佉沙国”是译为汉语时音译与意译的结合,而“伽师袛离”“伽师佶黎”完全是各种汉语音译的不同形式。在汉文史籍中记载的“碣石”“碣叉”“迦舍”“佉沙”以及“伽师袛离”“伽师佶黎”中的“伽师”都是kash或kesh不同的音译,来自于粟特语,而“袛离”“佶黎”是梵语“国家、城市”之读音。③伊布拉音·穆提义:《塔里木绿洲若干古城地名溯源》,《西域研究》1997年第2期。
盛唐之世,在中原汉文化的强烈光照下,汉语应成为喀什地区的通用语言之一。一些疏勒上层人物取汉语词汇作为自己的名字,如疏勒王族的裴安定、裴国良、裴冷冷等,著名音乐家裴神符、裴兴奴、曹刚等。创作《一切经音义》的释慧琳④《宋高僧传》卷5《唐京师西明寺慧琳传》载:“释慧琳,姓裴氏,疏勒国人也……引用《字林》《字统》《声类》《三苍切韵》《玉篇》诸经杂史,参合佛意,详察是非,撰成《大藏音义》一百卷。”见《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2册,第45页。无疑更是精通汉语的大家。
安史之乱后,唐势力退出了西域,喀什处于依附于吐蕃的样磨、葛逻禄等突厥部族的统治之下,政治上的得势使得突厥语流行起来。喀喇汗王朝时期,随着王都的迁移,大量的回鹘人进入喀什,促进了喀什民族语言的深层次融合,形成了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回鹘文,而回鹘文是所有突厥语都采用的文学语言,即统一的书面语言。在《突厥语词典》中记载:“回鹘人的语言是纯粹的突厥语,在所有突厥语中最优雅标准的语言是哈卡尼耶中央省的语言……喀什噶尔乡村中讲坎杰克语,但城里人均操哈卡尼耶语。”⑤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词典》维文版,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0-41页。可见,哈卡尼耶语获得了主导地位,成为全区域内通用的语言。由于这种语言是在居统治地位的、生活在喀什噶尔周围的回鹘人中所形成,并成为王朝范围内突厥语部落的文学语言的基础,所以,这种语言又被称为“喀什噶尔语”⑥吐尔逊·阿尤甫:《“喀什噶尔”语初探》,载《耿世民先生70寿辰纪念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18-127页;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满:《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社会文化》,《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蒙元和察合台后汗时代,随着伊斯兰教在塔里木盆地的推行,这种多民族语言的融合继续在深度和广度上扩展。大量的蒙古部落进入西域,成为西域各地的统治者。为了取得当地宗教势力的支持,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并将之推行到吐鲁番、哈密等地,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然客观上促进了塔里木盆地各地的语言文字走向一体化。由于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都开始在塔里木盆地流行。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形成的具有突厥语特色的哈卡尼耶语,在这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种语言虽继承了古代突厥语的语言特征,但已经借用了较多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借词、语音及语法形式。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逐步东进,哈卡尼耶语也在随之跟进,至15世纪初,已渐及新疆天山南北和中亚地区,不仅为操突厥语的民族普遍使用,而且也为占统治地位的各蒙古部落所使用,演变成察合台语。语言文字的统一,客观上加速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共同的语言文化区域。
(三)宗教的推动与影响
自古以来,喀什就是一个多民族分布的地域,造就了喀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随着宗教的传播与影响,则又推动了区域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特别是伊斯兰教成为区域内全民族的共同信仰后,促进了喀什多民族文化的一体化,为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秦汉之世,喀什流行的宗教主要是祆教和佛教。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塞人原游牧于伊犁河流域,因大月氏西迁而分散,一部分南下,散处喀什地区各地。在阿拉沟和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古①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l期。和塔什库尔干香宝宝墓地②陈戈:《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的考古发现中,出土一种青铜双兽铜盘,学者普遍认为是祆教礼拜时燃烧圣火的一种祭祀台。可见,塞人信仰祆教。而羌人则是以自然崇拜为主。相较而言,塞人文化对于羌人文化来说,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因此,在二者之间的宗教交互影响中,塞人文化无疑是处于主导地位的。
佛教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很早就传入了喀什。据日本学者羽溪了谛研究,疏勒佛教的传入始于臣磐③[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2页。。臣磐曾为大月氏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的质子,并在迦腻色迦王的帮助下获得了疏勒王位。迦腻色迦王非常崇信佛教,是佛教历史上第四次集结的召集者。当时,犍陀罗是世界佛教的中心。因此,在臣磐时期,佛教从大月氏贵霜传入喀什应是可信的。今喀什市北郊十公里处的伯什克然木河岸的陡壁上,有一处被称为三仙洞的石窟,里面有佛教的残存,有学者认为就是臣磐所开④王时样:《疏勒国佛教兴衰史》,《丝路》(喀什),1987年,总第43期。。臣磐之后,历代疏勒王都信仰佛教,弘扬佛法。随着魏晋时期的一统,佛教也从疏勒传播到喀什的其他区域。法显西游疏勒时,曾记其国佛法之盛况,“其国王作‘般遮越师’,‘般遮越师’,汉言五年大会也。会时请四方沙门,皆来云集,集已庄严,众僧座处,悬缯幡盖,作金银莲花,著僧后铺净座具,王及群臣如法供养,或一月、或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时。王作会已,复劝群臣,设供供养,或一日、或二日、或三日、或五日、乃至七日。供养都毕,王以所乘马鞍勒自副使,国中贵臣骑之,并诸白毯、种种珍宝,沙门所领之物,共诸群臣发愿,布施众僧。”⑤(晋)法显:《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载《中华大藏经》第6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69页。到隋唐时期,佛教成为喀什各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当时喀什的朅盘陀国、乌铩国、佉沙国都淳信佛法,“习小乘教说一切有部”⑥见《大唐西域记》卷12“朅盘陀国”“乌铩国”“佉沙国”条,《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83页、第990页、第995页。。在这三国中,佉沙国无疑是佛教的中心,有“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⑦(唐)玄奘、辨机著,季羡林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95页。,而乌铩国“伽蓝十余所,僧徒减千人”⑧(唐)玄奘、辨机著,季羡林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90页。,朅盘陀国“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⑨(唐)玄奘、辨机著,季羡林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83页。。
安史之乱后,喀什陷入一场多民族势力的相互争斗之中,宗教的信仰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随着信仰萨满教的样磨、葛逻禄等突厥部族的进入,日月星辰等自然崇拜也在喀什的民族宗教文化得到体现。回鹘人的征服,喀什王都地位的确立,使得伊斯兰教在喀什地区广泛传播。据记载,萨图克·布格拉汗是喀喇汗王朝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汗王①《拉失德史》载:“关于他有一个圣训,说‘突厥人中最初成为穆斯林的人就是萨图克’。”见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注《拉失德史》(汉译本),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页。。在他儿子木萨汗时,伊斯兰教被定为国教,并在王朝全境推行。就这样,在政治的高压下,清真寺取代了佛塔,伊斯兰教逐渐成为喀什地区各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并深入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一件出土于19世纪的喀什地区莎车县境内的喀喇汗王朝时期的阿拉伯文书,是一份处理土地买卖纠纷的民事档案,就深刻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在该文书中,一开始就是“以仁慈的安拉的名义,我赞美安拉,请求他的宽恕。”文书中涉及的汗王都有一系列的伊斯兰教封号,纠纷的当事人名称也全部伊斯兰化,从裁判人的头衔“谢赫·卡迪·伊玛目”来看,既是宗教官员,又是世俗官员。②刘戈:《一件喀拉汗王朝时期的阿拉伯文书》,《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可见,伊斯兰教在喀什地区的一统天下,深刻地改变了喀什多民族文化的原有特色,促进了喀什多民族文化的伊斯兰化,从而形成具有共同文化和共同民族心理的维吾尔文化。
蒙元帝国与察合台后汗时期,伊斯兰教随着蒙古统治者的强制推行而东渐,这就改变了元朝以前伊斯兰教在天山北部和东部一带徘徊不前的局面。到16世纪,在新疆占据统治地位一千多年的佛教及其文化终成陈迹,伊斯兰教成为统治新疆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工具,其影响一致沿袭至今。
结 语
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是一种历史现象,更是文化进步的基本动力之一。它既是性质不一的地域文化的交流与整合,又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整合,更是不同体系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整合。从历史时期喀什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这三种文化的交流与整合形态都在不同程度地持续产生和发展,不同文化因素的不断介入,使得喀什多民族文化在不断地分化、重组和整合中,并在政治势力和宗教高压的强力推动下,最终形成具有伊斯兰特质的维吾尔文化。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文化的形成无疑是以地理环境为基础上的。喀什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喀什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才有持续发生的可能。维吾尔族和维吾尔文化的形成是与喀什的地理环境分不开的。毋庸置疑,维吾尔文化是中国民族史上一朵绚丽的奇葩,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涵,更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喀什 民族文化 文化整合 维吾尔文化
K29
A
2096-434X(2017)01-0037-10
赵炳清,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和先秦秦汉时期区域;河南,开封,475001。
祝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