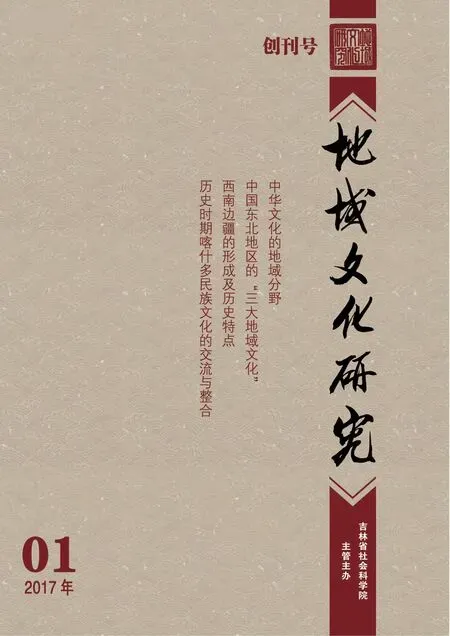中国东北地区的“三大地域文化”
王绵厚
中国东北地区的“三大地域文化”
王绵厚
东北地域文化是中国地域文化和东北亚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有必要对中国东北地域文化的“泛流域文明”等文化命题进行重新思考。科学地界定中国东北地域文化的学术意义,是可以在宏观上正确把握中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区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分布,阐明中国东北地区“三大地域文化”的成因及其基本特征。
中国 东北 地域文化“泛流域文明”
一、中国东北地区“三大地域文化”的提出及其根据
对中国东北地域文化的分布、命名的研究,早在20世纪初叶就已经开始,其中“辽海文化”“关东文化”和“东北文化”为最初对东北地域文化的表述。在20世纪90年代,李治亭先生主持编著《关东文化大辞典》时已经提出过“东北文化区”的概念①李治亭:《关东文化大辞典》前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实际上是对近百年以来,东北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谱系的小结。而对其次文化区的命名,则始于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地域文化热”研究的兴起,并在以“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草原文化”等正式提出以后。以2006年黑龙江省《多维视野中的黑龙江流域文明》编著的为例②潘春良、艾书琴主编:《多维视野中的黑龙江流域文明》,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页。,关于东北地域文化内部的分区命名,就有“多流域文明”假说,如辽河文明、松花江文明、黑龙江文明、鸭绿江文明等。此书的两次编写会议和讨论,我都是亲历者,因此萌生了对“东北地域文化”的不同看法,并主要针对“多流域文明”的“泛流域文明论”,提出以下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
对这一至今有争议问题的思考,我并不是一时灵机而动,而是有其研学基础。至少从1994年出版《秦汉东北史》时,就已深入思考“东北文化圈”问题。诸如上述的“多流域文明论”,看起来比较容易划定文化范围,其实并不完全合理。比如长白山区系,其东、南、西、北发源诸多水系,难道每个河流都应命名为独立文化?所以“泛流域文明”的要害,是只重视了“水系”因素,而忽略了其他综合社会因素,会产生无法科学界定的“泛流域文明”。而在我看来,命名或界定一个大的“地域文化”,尽管因素很多(包括水系),但最主要的应至少有以下不可或缺的三点:其一,有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基础和生态环境(如长白山区系);其二,应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如草原群牧);其三,应有相对独立的、不间断的民族谱系和考古学文化(如辽河流域)。从这三点综合看,如“黑龙江流域文明”,尽管也有较长的历史和较宽阔的领域,但在“经济形态”上,却一直处在“混合类型”中;其在人文意义上的考古文化谱系中,与“辽河文明区”相比,也有断裂和缺环。因此我把它作为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中的“子文化系列”——即黑龙江流域的古代文明,在上、中、下游三个地区,分别表现出“草原文化”“(江河)渔猎文化”“(山林)采集文化”等混合特征。
这样来界定“东北地域文化”,毫无贬低某一区域文化地位的意愿。它的学术意义在于,可以在宏观上正确把握中国东北包括东北亚区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分布。故如我在2015年5月1日《中国文物报》上著所《中国长白山文化“考古编”书后》所说,在近期出版的《中国长白山文化》这样一部专门的地域文化著作中,对“东北地域文化”也没有统一分区,有的章节引用了“辽海文化”“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区等,有的章节又分为“辽河流域文明”“松花江流域文明”“鸭绿江流域文明”“黑龙江流域文明”等“四大流域文明说”或“五大流域文明说”。可见讨论中国东北地域文化,应是中国乃至东北亚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笔者在以下各部分,就此分别逐一解说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的成因及其基本文化特征。
二、辽河文明
辽河文明,又称“辽海文化”和“辽河文化”。20世纪80年代,它在中华文明和中国地域文化中的地位,是随着辽西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等重要发现,不断引起世人关注。笔者关注辽海文化研究始于2002年,为纪念母校北京大学考古系创建50周年,曾撰有《辽河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历史地位》一文。其后在2006年,又应邀撰写辽宁省重点文化工程《辽宁文化通史》秦汉卷。在对秦汉辽宁地域文化源头的历史追述中,曾提出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以“辽河文明”为中脊,以“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为东、西两翼①王绵厚:《辽宁文化通史》秦汉卷第十章,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指出应当从东北亚的大区域来看待辽海文化。
(一)辽河文明的地理概念和“辽海文化”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基础
“辽海文化”“辽河文明”或“辽河文化”,应是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和学科内涵,对辽河流域的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的命名。三者不存在如有些学者认为的主次的问题,也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如同“齐鲁文化”与“黄河文明”一样,前者是地域文化命题;后者是考古文化和“文明起源”的术语。这二者具有共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基础和历史的必然性。概括地说,主要有三条。
其一,在宏观自然地理上,辽海文化或辽河文明,是面向太平洋的东北亚前沿的区域文化。在“流域文明”上,它是黄渤海北岸和“辽河流域片”等大的地理区系。因此审视它的眼界,不能仅放在辽宁省的行政区划内,而应投放在中国东北和东北亚的大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范围内。即“辽河文明”作为一个大区域的文明单元,它的基本区域地理应以黄渤海北岸为腹地。其东界与辽东山地的“长白山文化”南缘接壤和交叉;其西界应以燕山以北、辽西努鲁儿虎山以西至大兴安岭以南,在上辽河地区与“草原文化区”衔接;其北界则至松辽分水岭。
其二,在东北亚大区域的文化地理视野上看,辽海地区应地处黄渤海北岸的东亚前沿内陆。它的广义区位优势,是横跨东亚太平洋北缘黄、渤海北岸的南北相连的三个半岛: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的中脊和前沿地带。
其三,从“区域文明”的角度,看待辽河文化的区域特征。它的东缘有“长白山文化”;西缘有“草原文化”,是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的“中脊”和“桥梁”。如果从“海洋文明”与内河“流域文明”兼容的角度,看待历史上的“辽海”称谓,至少在东汉时曹植给其父曹操的《谏伐辽东表》中已提出,“辽东负阻之国,襟带辽海”①曹植:《谏伐辽东表》,《陈思王集》,清光绪十八年《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而不是过去许多人引证的《魏书》等,认为“辽海”的地名称谓,出现在南北朝时期,比过去应至少提前200年。我们应用更深远的文化视角来审视辽河文明。
(二)辽河文明具有深厚的历史文脉基础
辽海文化或辽河文明的基础是依托辽河水系。辽河古称“大辽水”,是最早见于先秦文献的中华名川。在《禹贡》和《吕氏春秋》“有始览”等已记载:“何为六川?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②《吕氏春秋》卷13《有始览》,引自东郭士编《东北古史资料丛编》,沈阳:辽沈书社,1989年,第113页。《吕览》记载的“六川”,与《尚书》“禹贡”等一样,是大禹平定中华“九州”后,最早确认的九州水系。如同“五岳”“五镇”一样,是代表当时中国九州方域的地标。《吕氏春秋》中的“黑水”,并不是指今天的黑龙江,而是甘陕交界和内蒙古居延地区的“黑水河”。所以“辽水”在战国以前,已是中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唯一载入正史的中华名川。《尚书》“禹贡”的名句“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正是指先秦由辽东和朝鲜半岛,经黄渤海北岸的辽河腹地和辽西走廊,经过今山海关内外的辽宁省绥中县“右碣石”,进入中原黄河的最早文化与民族通道。③其古代交通地理和文化地理、民族地理的深厚根源,可详见笔者所著《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年。自先秦以后,它的深厚历史文脉基础,更传承了数千年。
(三)辽河文明的区位优势和地域文化内涵
我认为从宏观的角度,评价辽海文化和辽河文明的区位优势,至少可以概括为如下六个方面。
其一,依托辽河水系形成的多元生态资源。辽河流域的自然生态的多元性和生态保护,是辽海文化多元兼容的自然基础。这是我们在21世纪研究“辽河文化”首先应当具有的科学文化观。辽河文化的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是当代研究辽河文化的“一车双轮”。从历史上追述,辽河文明从沿黄渤海北岸的横向分布看,其东部为“长白山文化”,其西部为“草原文化”。从纵向地理的分布看,它又是中国北方北纬41度—42度之间,以“长城地带”划分的南北文化的不同分区,即辽河腹地的农耕文化和北缘游猎文化的中冲地带。这一生态资源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的“多元性”决定了辽海地区地域文化和考古文化的多样性。
其二,由多元生态资源决定的综合性经济文化形态。上述多元自然生态资源条件,是决定辽海文化本质特征的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基础。辽海地区这种多元、综合性的经济文化特征,数千年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在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攀升,但其本质特征并没有根本改变。如辽河腹地,以东西辽河交汇的辽吉两省衔接的松辽平原南部,向来就是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牧的农业区,自战国以来就是“汉郡文化”的传布地区。东临以东辽河和浑河、太子河上游为中心的辽东地区,历史上就是山林、川泽地区。具有“长白山南系”依托山林资源的狩猎、捕捞、采集等经济特征的文化区,历史上亦是“秽貊”族系的辽东古代民族的母体(南貊)发源地。而上辽河流域的西部,努鲁儿虎山以西,历史上就是以“游牧”和“群牧”为特征的“草原文化”区,并形成了“燕亳”“东胡”“鲜卑”“契丹”等土著民族文化。辽河流域上、中、下游不同的经济文化区,有一个内在联系,就是在自然和人文地理上,都是以辽河干流为中脊,连接和带动两翼文化的发展。而今辽河下游的鞍山、盘锦、营口等地,更具有辽河平原农业生态的特殊性。
其三,在人文历史上的辽河文明,是中国北方文明起源的中心。这在进入21世纪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已经被确认,“辽河文明”是与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并列的中华文明起源之一。从辽河下游的“早期智人”营口金牛山人开始,辽河流域就是与北京“周口店猿人”先后发展在黄渤海沿岸的最早的古人类,是东北亚地区人类起源和文明发端的重要地区之一。其后从红山辽河文化的“古国文明”,到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我认为应是先秦燕山以北“燕亳”族团)的“方国文明”,直至秦汉以后“汉郡文化”的帝国文明,辽河流域文明有几千年不间断的传承发展。
其四,辽海文化区域在历史上是北方“长城地带”和“丝绸之路”的东端,自古为连接东北亚的桥梁和纽带,在现代仍是东北亚大区域连接黄渤海北岸以及跨国经济、文化区的东西走廊和重要前沿地带,因此被列为国家级经济区。环“长城地带”南缘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了军事上的区域障塞区,变成了南北民族文化交融的“文化熔炉”和历史平台。而“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已达今辽河上游(以今辽宁朝阳古“龙城”为中心),并东传朝鲜、日本,这使辽河文明的影响具有世界意义。
其五,辽海文化在社会人文意义上,应具有独特的“关东文化”的多元人文特色。在历史上,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东北南部地域文化,依托农业为主形成的具有独特地域文化的“长城地带”,汇聚了“汉郡文化”“萨满文化”“骑射文化”“流人文化”等独特的关东地域文化,从而使“辽海文化”同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等一样,毫无置疑地跻身于我国几大区域文明之林,成为相对独立的文化区。
其六,辽河文明从其最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形态”上看,虽然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也有过兴衰,但始终地处“长城地带”以内的沿黄渤海北岸的农业生产区,具有两翼“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不可比拟的自然生态优势。既使历史上有短期游猎民族进入辽河流域,如晚明时期“建州女真”进入辽海,也在不久实行了“计丁授田”制度。这是不以人(民族)的意志为转移的深刻的“自然法则”,它决定了“辽河文明区”在以农业为主导的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东北亚前沿”的地理、经济、人文优势,也是“辽河文明”具有独立性、先导性、多元性、兼容性的内在动因①参见刘厚生主编《中国长白山文化》第二编,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
三、长白山文化
20世纪中叶随着“长白山丛书”的出版,长白山文化逐渐为人们所认同。2014年出版的《中国长白山文化》一书,这样来定义“长白山文化”:“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以长白山地区为地理空间范围,以东夷文化为先导,渐以华夏—汉文化为主体的、东北各民族共同铸就的,具有鲜明历史、民族、地域特点的地域文化。”①刘厚生主编:《中国长白山文化》第二编,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第234页。尽管在对这一文化的认知概念上,可能会有局部的差异。但从其基本文化的定义上看,“长白山地区(或区系)”“东夷(东北夷)文化先导”“华夏(汉)文化为主体”“多元民族内涵”“地域文化”,应当是构成“长白山文化”的基本内涵。笔者以下拟围绕上述几个方面,对“长白山文化”进行解读。
(一)长白山文化的区系地理界定
笔者在解读“长白山文化”中,之所以用“区系”,而不用“地区”,是因为自然地理概念上的“长白山”及其余脉,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交叉性;而“区系”作为文化地理概念,可以兼顾山川、民族、疆域等多元涵盖性,可相对准确地界定其文化覆盖区。从这一视角界定“长白山文化”,它应是以长白山主峰为地标,以相关山系、水系交织组成的特定文化区。即南含辽东半岛千山山脉,北延张广才岭东西;东括狼林山脉和盖马高原;西至医巫闾山和大兴安岭以东的松辽分水岭。在这一“山系”与“水系”并重的地区内,就是“中国长白山文化”的基本文化地理区域。
(二)长白山区系的山系和水系
长白山文化的“山系”分布,上已指出,可分为四个延伸方向。其南支,包括今辽吉两省交界的龙岗山脉和辽东腹地的千山山脉,基本以东北—西南走向,一直延脉到旅顺老铁山。其北支,应包括张广才岭、牡丹岭和完达山脉,即东流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之间的纵向山地。其东支,以老岭以东、今朝鲜半岛的狼林山脉和盖马高原山地为主干。而其西支,以吉林哈达岭以北的松辽分水岭为限,逐渐过渡到松辽平原区。与上述“山系”对应,长白山区系的“水系”,亦由以下几大水系构成:其南系为“鸭绿江水系”,包括浑江、靉河等水域。其北系为图们江、乌苏里江水系,包括牡丹江等水域。其东系,为清川江、大同江水系。其西系(西北)为松花江水系。包括东辽河和伊通河等发源哈达岭的诸水系。在上述诸“山系”和“水系”中,一个重要的区域特点是“纵横交错”,共同交织成“长白山区系”的地域文化格局。
(三)长白山区系的古代民族谱系
长白山区系的古代民族分布和构成,与“山系、水系”相比,是一个具有动态分布的民族谱系。这里介绍的是在汉民族外,在这一区域的土著族团。从东北地区已普遍认同的族系划分看,主要可分为三系:“秽貊系、肃慎系、沃沮(东秽)系”。如以东、南、西、北的山系和水系的自然分区看,这“三系”的大体分布是:南系:为秽貊族系的“南貊”——包括历史时期的“高句丽(高夷)”和“青丘”;北系:以纵向张广才岭分界;其东属“肃慎”,其西为“槖离”——包括其后的“靺鞨”和“渤海”等;其东系:为“沃沮”和“东秽”——包括“古朝鲜”等;其西系:为秽貊族系的“北秽”和“夫余”——包括由“槖离”南下松花江中游的遗民。与这一基本族系分布的相关考古学文化考察,是这一区域进入青铜时代以后,人文历史和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
(四)“长白山区系”已发现的重要考古学文化与民族谱系
上述与长白山区系的“族系相关的考古学文化考察”,是“进入青铜时代以后人文历史和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涵盖三方面含义:其一,考古文化的主述重点是“青铜文化以后”。这主要考虑石器时代以前尚缺乏民族构成的基本因素和社会条件,在考古学和民族学中一般不纳入“族系”考察阶段。其二,“青铜文化以后”的考古文化的考察也不是无限延长,而是终止在“早期铁器文化”的两汉之际。主要是“长白山区系”的民族和考古文化的“奠基期”①刘厚生主编:《中国长白山文化》第二编,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其三,与地域文化分区相比,考古学文化由于受考古发现的阶段性、偶然性和认识程度的局限,其界定和谱系的认知更复杂,所以本文对“长白山区系考古学文化”的分区介绍,区别于各类“考古文化类型学”的分布,是以“长白山文化”的自然地理分区“四系”为基础,从宏观的考古学与族系对应的角度分析,所持的研究方法是地域文化的方法,而不是考古学的方法。以下试分区简介:
1.长白山南系
长白山南系的考古文化,如我在《中国长白山文化》“考古编”中所说,指龙冈山脉以南以辽东山地为主的考古文化。②刘厚生主编:《中国长白山文化》第二编,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这一文化的局部分区,是以千山山脉为标志。在千山山脉以南的辽东半岛沿海区,早期有营口“金牛山人”等旧石器文化和“小珠山”“后洼”等新石器时代文化;进入青铜时代,则以大连地区为主的“双坨子文化”为代表。这一地域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发生在半岛本地的土著文化,但受山东半岛的“岳石文化”等影响显著。从古代辽东半岛南部曾属“海岱曰青州”地域看,这一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可对应为古“青丘文化”。③刘厚生主编:《中国长白山文化》第二编“青丘”条,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第53页。
在千山山脉以北和龙冈山脉之间的辽东腹地,称为辽东“二江”(鸭绿江、浑江)和“二河”(太子河、苏子河)流域的“大石盖墓文化区”。它是典型的辽东“南貊”土著文化区,汉代以后则是辽东“高句丽文化”起源和早期高句丽“五部”的核心地区。
2.长白山北系
该地区考古文化应以纵向张广才岭为界分为东西两区。其东区牡丹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西地区,在进入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代以后,虽然部族分散、复杂,但其主体文化,当以20世纪60年代发现确认的“莺歌岭文化”——“肃慎系”为主的考古文化为主。其文化延续至后来的“挹娄”和盛唐“渤海”时期。在张广才岭以西的东流松花江南北,其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代表性考古文化,应是黑龙江省“索离沟文化”,即北夷“槖离国文化”。这一文化遗迹发现较早,但对其文化和性质的较深认识应在进入21世纪以后。
3.长白山东系
这一区域考古文化的分布,多涉及图们江以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在《中国长白山文化》“考古编”中称为“东秽地区”。其在青铜时代以后实际上的族系问题,还应包括南部的“古朝鲜”和北部“沃沮”等滨日本海地区,故统称“东秽”。在高句丽《好太王碑文》中或称“韩秽”④参见耿铁华《通化师范学院藏好太王碑拓本——纪念好太王碑建立1600年》,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页。。这一区域文化,应统属东北亚“秽貊”文化系统的“北方式支石墓”文化。关于“长白山东系”主要分布于朝鲜半岛北部的“支石墓文化”的渊源,韩国考古学家李亨求是这样总结的:“大凌河流域的积石墓,经辽东半岛(石盖墓)传到朝鲜半岛,在朝鲜半岛从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期相继出现……(支石墓)是在渤海沿岸地区发生并发展起来的。”①李亨求:《关于东北亚的石墓文化——以渤海沿岸北部、东临及朝鲜半岛为中心》,《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5年第1期。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文化在具有辽东“石盖墓文化”影响和东传因素的同时,亦有日本海沿岸的海洋文化因素。
4.长白山西系
长白山西系的考古文化,在地域上属于长白山脉向西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延伸的张广才岭和威虎岭以西、吉林哈达岭以北的松花江中游。在进入晚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后,其公认的代表性文化,为20世纪50年代发现确认的“西团山文化”。董学增先生在《西团山文化研究》中,这样来界定西团山文化的范围:“东界在张广才岭南端威虎岭以西;西界在伊通河和东辽河流域;南界在辉发河、饮马河、伊通河上游;北界在拉林河中、上游左岸。”②董学增:《西团山文化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51页。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笔者与李健才和王侠等两次实地调查,夫余先世西团山文化的分布区,在西汉以后,正是以今松花江中游吉林市为中心,以吉林东团山、南城子和龙潭山为核心区域的“夫余”文化中心区。③董学增:《西团山文化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51页。在吉林市龙潭区的“土城子遗址”等地,明确发现了在“西团山文化”的上层,叠压着西汉时期的“夫余文化”遗存。所以“西团山文化”在考古学和民族学上,普遍认同为“夫余先世文化”,即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以“鹿山”和“秽城”为中心的“北秽”系统的“夫余王国”④(晋)陈寿:《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夫余》,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1-842页。。从西团山文化(夫余先世)的北界在拉林河南岸看,在夫余立国以前,确有一支东流松花江的“北夷槖离国”(索离沟文化)部族,南渡拉林河(古掩淲水)进至松花江中游的夫余故地建国。
四、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与上述“辽河文明”和“长白山文化”,在地域和文化形态上对应的东北地域文化之一,是个具有更广阔覆盖面的文化区。在中国东北(含东蒙古草原)地区,其基本地域范围,应接续上述“辽河文化”的西缘,燕山以北、努鲁儿虎山以西、至大兴安岭南北,西连贝加尔湖以南的蒙古草原。从整个北方“草原文化区”看,东北区域的草原文化,应属于其东缘地带。在燕山和太行山以北一线,基本以历代的古长城南北为分界,即草原文化区,基本在长城线以北的草原游牧区。由于草原文化横跨亚欧大陆的广阔覆盖面,其文化的传布和影响亦具有世界意义。
余对“草原文化”的涉猎,起步在21世纪初。由于2002年起参与《中国长白山文化》的编写。因为全方位审视“长白山文化”,特别是区系考古、民族学,离不开东北亚大陆的另外两个文明——“辽河文明”和“草原文化”的比较。所以在2004年,应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邀请,参加呼和浩特市首届“草原文化”学术会议。2006年,应呼伦贝尔市博物馆邀请,研讨“草原文化”展览,又考察过近年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重要遗物——“哈克文化”玉器与陶器。在呼和浩特市的“草原文化”讨论会上就“草原文化的三个主要标志”的主题发言,后扼要发表于2005年1月28日的《光明日报》①王绵厚:《论草原文明形成的三个标志》,《光明日报》2005年1月25日理论版。。其后在完成《中国长白山文化》“考古篇”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思考了“草原文化”的特质。
其一,从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形态或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草原文化具有三个特征:“群牧业态”的确立、“细石器文化遗产”传承、“骑射文化传统”。其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文化层面上,具有“以自然为本”的人文精神。以下拟按这几个方面对“草原文化”略予阐述。
(一)草原文化的“群牧业态”
我认为,这一经济形态是“草原文化”确立的基础,是草原文化有别于“大河文明”孕育的农业文明、山林文化孕育的“渔猎采集”文化的特质。草原文化作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载体之一,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牧业文明特别是以“群牧”形态为主的生产方式。这种群牧经济形态也有一个长期发展过程,从最初的狩猎到野生动物的驯养,从个别家畜的驯化、储养到规模化的“群牧”,最后形成了具有独立业态形式的生产方式。从中国历史的发展看,在北方真正形成具有聚落式“草原群牧”的民族文化进程,应至少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一是开始于战国、汉魏时期的匈奴、东胡、鲜卑等长城以外草原民族的“帐幕式群牧”,即《三国志》乌丸鲜卑传所说:“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②(晋)陈寿:《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乌丸》,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32页。二是公元10世纪前后,草原帝国契丹辽王朝,把“帐幕式群牧”上升为国家专门管理的群牧机构,从国家级的“总典群牧司”,到各府州的“群牧林牙司”,把“群牧”的管理纳入了国家的根本管理体制。这是“草原文化”从民间生态文化,上升到国家“国体文化”的里程碑。三是举世公认的蒙元帝国初期。在“草原帝国”横跨亚欧大陆的同时,“群牧”作为支撑蒙古汗国兴起的最初“国本”生业,得到了空前发展。至此“群牧”经济形态,可以说发展到了历史高峰。这种群牧业态的确立和发展,为草原民族从狩猎、采集文明走向蓄牧文明,提供了新的生产手段和智慧。所以从“草原文化”的发展看,契丹族的辽朝和蒙古族的蒙元时期,应是“草原文明”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细石器文化”载体
草原文化在当代考古学上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是“细石器文化”传统。包括它的非物质文化形态“岩画艺术”和“自然崇拜”等。限于“岩画艺术”和“自然崇拜”的专门性和复杂性,这里只单独谈考古学上“草原文化”本体的“细石器文化传统”。著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在《中国细石器时代略说》中,对依托“草原文化”的“细石器时代”已有明确界说。尽管对到底存在不存在“细石器时代”,学术界尚有争论,但历史上确实存在“细石器文化”,应当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保留着草原文化原生态特征的石器工艺,蕴含着草原文化的多元生态和生产手段的内涵。诸如:以打制、琢制、磨制结合的“细石器工艺”,表现了草原民族对“畜牧经济”生产加工和狩猎活动的必要手段;而伴随“细石器”的“复合式”工具,如复合式刮削器、骨角器和弓箭等,也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特征。这其中要特别提到“草原文化”和草原民族的最先进的复合式工具(同时为武器)的弓箭。弓箭的发明,是草原文化和草原射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它的发明,连同“骑射文化”,甚至不亚于金属工具的发明。所以细石器文化传统和以弓箭代表的“复合式工具”的出现和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巨大影响,应是凸显“草原文化”历史地位的重要文化表征之一。应当指出的是,“细石器文化传统”不仅在“草原文明”中特色突出,而且在人类文明发展中,也对其他文明(如农业文明)发生过影响。如公认的以原始农业为主的、距今7000年前的下辽河流域的沈阳“新乐文化”,其早期“细石器工艺”和工具,亦曾经是其发展的重要阶段性特色。
在当代考古学上,进入21世纪的呼伦贝尔“哈克文化”的发现,如我在2005年《光明日报》著文中指出,是草原“细石器文化”的凸起异军。该文化因首次发现在内蒙古海拉尔市哈克镇得名,2002年被正式命名为“哈克文化”。这一文化遗址,仅在呼伦贝尔地区已发现300余处。“哈克文化”发现的区域文化意义在于,这一地区自古是欧亚大陆“草原文化”和“草原民族”的核心发源地之一。从秦汉以前的“丁灵”,魏晋南北朝的鲜卑、乌洛侯,隋唐时的“室韦”,到辽金元的契丹、蒙古,均崛起在呼伦贝尔草原南北。所以呼伦贝尔地区这一文化的新发现,应当是“草原文化”特别是“细石器文化”应引起世界瞩目的重要发现。笔者2004年在呼伦贝尔博物馆原馆长赵越陪同下,曾亲自考察其出土文物,观其玉器和陶器,特别是玉器独具特色。而这一距今6000年以上的“哈克文化”,其细石器和玉器的加工工艺水平,可令同时期的内地新石器文化见拙。由此我认为,应当使人们重新审视北方“草原文化”,特别是“细石器文化”的历史内涵和历史地位。
(三)“骑射文化传统”和马具的发展
草原文化的另一个突出文化特征是“骑射文化传统”,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课题。在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草原“骑射文化”总是离不开马具和马匹驯养,所以笔者在这将骑射文化传统和马具的发展一并考察。骑射文化是人类依托“群牧”的经济形态而产生的“草原文化传统”。至少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起,由游猎发展到牧猎的结合,并由此产生了野马驯养。在东北亚地区,它的起源主要在中国北方。最早的见于文献是“土方”和“山戎、东胡、匈奴”等部族。如战国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即针对北方“胡人”,是戍边战略的改革。考古发现证明,东北亚最早的马具,出现在距今3500年至春秋时期的燕山以北、上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族)。考古发现,在其墓葬的骨板上刻有“髠发”的游猎部族形象。在宁城南山根等“东胡人”的墓葬中,发现有最早的草原游牧民族的车具、马具等。
从青铜时代开始发展来的马具和“马具文化”,是“草原文化”发展进程的又一划时代进步。马具连同早期车具的出现,不仅具有新的“生态文化”意义,同时具有“军事文化”和“交通文化”的意义。①王绵厚、朴文英:《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第五章第八节“骑射文化与马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英国著名科技专家怀特曾经说过:“很少有发明像马蹬那样简单,而又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英国另一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也指出:“(在中国)只有极少数的发明像马蹬这样,在历史上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这一“催化影响”,改变了草原民族从一般的“游猎文化”生态,发展到对交通、骑兵、骑战等深刻变革。尽管对马具、马蹬的发现,最早在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产生,还存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草原民族是最早接触和经历马具使用和改革的民族。上举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史记》匈奴列传中明确记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一个“变俗”,一个“习骑射”。说明当时草原民族的骑射必精于长城内的民族。这就是战国时期及其以前农耕民族顺应和学习草原“骑射文化”的历史明证。至少证明当时“草原民族”是普遍精于“骑射”的民族。不仅如此,从考古学上看,在中国北方,骑射文化和马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应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草原民族的鲜卑“三燕”。
三燕时期是继先秦两汉北方东胡、匈奴的“草原文化传统”,在草原文化和马具发展的新时期。所以“三燕”的骑射文化和马具,可称公元3-4世纪最早使用马具,并把马具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先行者。①田立坤:《朝阳发现的三燕文化遗物及相关问题》,《文物》1994年第11期。其后又经历了契丹辽王朝和蒙元时期,草原文化的代表性标志“群牧”和“骑射”均发展到最高峰,“草原文化”也达到了历史意义上的顶峰。而这一切,均与燕山以北至大兴安岭的东西部的“草原文化区”有着历史渊源。
(四)以“自然为本”的人文精神
当代“草原文化”最具有现实社会意义的,是它的生态理念——“以自然为本的人文精神”。这一生态理念的产生,不是后社会形态的人文意义上的哲学理念,而是与“草原文化”与生俱来的自然生态长期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生成的自然和社会基础,而草原文化的“以自然为本”的人文精神,更有其独特性、原生性、永恒性。
所谓独特性,是指草原民族和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相比,更具有依托自然资源的直接性和依赖性。这是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生态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与“农业文明”和“渔猎文明”相比,它更具有连续几千年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几乎没有根本变化的特殊性和稳定性。“草原文明”的连续性,是其生态文明的历史表征。
所谓原生性,是指草原文化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始终保持着“以原生态为载体”——直接将自然的草场、水、土地、阳光,利用和转化为畜牧、肉乳、皮毛等生活品。特别是对草场、水、土地的利用,较少农业文明对上述自然资源的改造和破坏。用现代的经济学说法,可称原生态经济。而越是古代这种现象越突出——草原民族的“衣”,以动物的皮毛及其加工的毛织品为主,其物质资源和工艺均具有原生性;草原民族的“食”,以肉、乳和加工品为主,早期并伴随狩猎和采集;草原民族的“住”,素以“毡帐穹庐”为家,这是传统草原民族适应游牧和狩猎生活的居行方式;草原民族的“行”,前在“骑射文化传统”中已经指出,主要是利用马、牛等及配套的畜力车。
所谓永恒性,是一个既伴随着现实生活又具有历史深度,并超出现实生活的文化生态理念,即指草原文化“以自然为本”的人文理念的永恒性。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讲的“以自然为本”,与一般民族学意义上的“自然崇拜”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是指在长期社会实践中,人类自觉或不自觉产生的对自然的“理性尊重”;后者“崇拜”则是多在对自然无知或朦胧中的“宗教盲从”。在当今世界上,应有两种不因意识形态差别和社会制度不同而存在的“永恒理念”,即“以人为本”和“以自然为本”,这是两个具有自然和人文双重价值的社会价值观和哲学观。但这一生态理论,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不可能在这篇讨论地域文化的文章中尽述。所以,最后笔者只想指出,由“草原文化”及其衍生出来的“以自然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永恒价值”,具有深刻的当代社会文化意义。
G127
A
2096-434X(2017)01-0011-10
王绵厚,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研究方向:东北历史、考古与文物;辽宁,沈阳,110167。
刘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