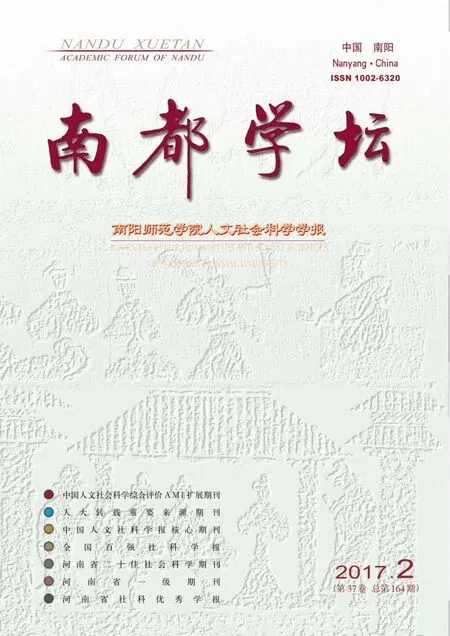宗藩体系:古代东亚地区国际秩序运行及特征
崔 思 朋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宗藩体系:古代东亚地区国际秩序运行及特征
崔 思 朋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历史上,东亚地区因其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区域。对于东亚地区国家关系名词表述较多,有“宗藩”“朝贡”“职贡”等词汇,但“宗藩体系”一词在其演变过程中,成为概括中国与周边番邦与属国之间关系的总称,用其来概括古代的东亚国际秩序应更为贴切。在这一体系中,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享有崇高的地位,各藩属国与中国之间等级有序。东亚宗藩体系的出现是有其必然原因的,同时也经历发端、发展、成熟、稳步推进、鼎盛及衰落等不同阶段。作为宗主国的中国通过政治上的吸引、经济上的往来、文化上的影响、军事上的征讨手段等维持着这一秩序。宗藩体系是古代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主要表现,相比于西欧封建时代的战乱频发,东亚地区的秩序是较为和谐的,这一局面的出现也与宗藩体系影响下的国际秩序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秩序维持了上千年,其所运行的手段包括武力征服、文化教化、利益吸附、宗教笼络等军事、政治、文化策略,这一体系也是有其封闭性、秩序性及稳定性等特征。
东亚地区;宗藩体系;运行手段;秩序特征
“宗藩体系”是古代东亚地区的基本国际秩序,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学界给予了较高的关注,但对于古代东亚秩序的代称名词及其含义仍存在争议。鉴于此,笔者在文中对当前学界就宗藩体系之区域、内容、运行方式及特征等做一梳理与讨论。然鉴于学识有限,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宗藩”“朝贡”“职贡”等东亚国际秩序代名词释义
“宗藩”一词在汉代文献中便有记载,其内涵也是多方面的。第一,代指国家内部的权力关系。黄宪《天禄阁外史卷六》载“汉封晋王以为西北宗藩,每岁受胡虏之患,汉室重寄,何以副之晋王又归笞巨室”。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载“乃封弟交为楚王,爰都彭城,以疆淮泗,为汉宗藩”。此两书中对于“宗藩”一词记载较早,将“宗藩”视为分封之诸侯,是指受封的与君主同宗族的人[1]。持此观点的学者较多①可参见:唐嘉弘主编《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大辞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3页;贺旭志主编《两汉职官辞典》,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2008年版,第316页;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552页。。第二,指代皇族宗室关系。《元史·明宗本纪》载“朕至上都,宗藩、诸王必皆来会,非寻常朝会比也”。此处之宗藩专指皇室宗族。明时,河南地区朱元璋分封藩王较多,宗藩是明朝所册封诸侯[2]。赵全鹏等学者认为宗藩一词是对皇族内部诸侯王的代称②赵全鹏《明代宗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刘志扬、李大龙《“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均认为“宗藩”指皇室宗族或地方分封的同姓诸王。。第三,“宗藩”也指国家间的关系,即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检索期刊论文,近95%以上的论文都用“宗藩”称呼明清与周边国家关系,可知“宗藩”是学界用来阐释明清与琉球、越南、朝鲜等国关系的最普遍的用法[3]。还有部分学者及工具书笼统地将“宗藩”理解为封建王朝的属国或属地,如《汉语大词典》[4]及《现代汉语词典》[5]。
“朝贡”一词在汉代文献中便有记载,《后汉书·乌桓传》中载“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指的是古代分封诸侯、属国与少数民族亲自或遣使朝贡中央君主和进贡方物[6]。对于“朝贡”一词,大部分工具书及论著中都将其解释为中国与属国及诸侯之间的贸易往来*郝迟、盛广智等主编的《汉语倒排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页),莫衡等主编的《当代汉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7页),任超奇主编的《新华汉语词典》(崇文书局2006年版,第100页),邓治凡主编的《汉语同韵大词典》(崇文书局2010年版,第256页),阮智富、郭忠新编的《现代汉语大词典》(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9页),何盛明主编的《财经大辞典》(下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6页)与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史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516页)均持此观点。简军波也在《中华朝贡体系:观念结构与功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中将朝贡解读为中国与属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贸易关系。,较少指称双方的国家间各方面往来。
“职贡”一词出现较早,商周时代便已出现,“职贡”一词所指包括以下三方面。其一,指职方贡物[7]。《礼·夏宫》载“有职方氏,掌天下地图,主四方职贡”。春秋时小国对大国的贡纳也称职贡。持此观点的还包括安德义等人,认为职贡是职方贡物[8]。“职贡”也称“常贡”。三代时起,各地诸侯和弱小民族定期把各种土产、珍宝贡献给三代中央王朝,是赋税的原始形态,所贡品种亦有规定,强制性和固定性逐渐加强[9]。其二,指“古代属国以时入贡曰职贡,亦指贡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说其罪戾,请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职贡,从其时命”。郑天挺等也认为“职贡是古代诸侯国按等级、地区向王朝贡纳的制度”[10]。其三,认为职贡是掌管四方的官吏所进贡的东西。《述行赋》载“通渠源于京城兮,引职贡乎荒裔”。
用来指代古代番邦属国与宗主国之间关系的词语还有“朝天”一词,“朝天”在古代有些时候也指“谒见皇帝、天帝”[11]。杜甫《偪仄行》中“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便指这一内涵。
综合上述四词,笔者认为:“朝贡”一词所指含义仅限在宗主国与属国之间进贡礼仪与方物及朝贡贸易往来,所指内涵较狭隘,而本文所指清朝与东亚地区各国之间关系不仅是进贡与回赐,还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的往来,故而难以涵盖本文所指。“职贡”一词多指宗主国与属国之间朝贡往来的进贡及宗主国对属国征纳赋税等,其所指与“朝贡”有较多共通之处。因此,也难以用于指代本文主旨。而“宗藩”一词在其演变过程中,成为概括中国与周边番邦与属国之间关系的总称,加之清时,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都被纳入清的统治范围,成为国家各地区的关系,因而“朝贡”“贡职”与“朝天”等词难以概括清代的东亚国际秩序。故而本文采用“宗藩”来论述中国主导下的东亚宗藩体系。
二、多维视角下东亚地区宗藩体系的审视
(一)东亚地域范围的界定
对东亚地区宗藩体系的研究,无法规避对古代东亚地域范围的界定。杨军认为,古代的东亚包括“中国、韩国、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的大部分地区”[12]。费正清也提出,古代东亚的范围是由“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及小岛琉球”等组成,这些地区是由古代中国衍生出来,且在中国文化区域内[13]。此两种观点主要是结合现代社会对于东亚地区划分的标准而划分。此外,也有学者界定的标准是那些古代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与中国地理位置接近,且在文化交流、朝贡贸易等方面来往较紧密的国家及地区,认为东亚地区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即以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国及俄罗斯亚洲部分的东北亚地区,东盟十国及东帝汶的东南亚地区[14]3。在西方人眼中,古代的东亚一般包括:东部西伯利亚、中国、蒙古、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15]。本文写作主要采用了唐彦林与费正清等人观点,结合文化影响视角下划分的东亚地区加以论述,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东北亚为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国和俄罗斯的亚洲部分;东南亚包括东盟十国及东帝汶。
(二)东亚宗藩体系出现的原因分析
东亚地区宗藩体系是以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朝贡”为主要表现形式。李云泉认为, 朝贡制度源自先秦,通过藩国向中原王朝进行称臣纳贡,以及作为宗主国中国对藩属国的册封赏赐为基本内涵[16]。先秦时期宗藩体系的出现也体现在一些传世文献与制度中,现代学者喻常森通过对《诗经·商颂》一篇中“相土列列,海外有截”一句的解读,并结合当时国家状况,指出商代,“截”(指代“铁”)便是海外国家向商朝所贡之物,从而反映当时的封贡制度[17]。西周时代,“五服制是周天子对各诸侯及边疆地区所规定的朝贡制度”[18]。在向外征讨的过程中,周王通过军事武功而将分封制度用于所威慑地区,以亲疏远近为标准划为五服[19]。这一秩序的出现与中国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分封制密切相关,随着统治地域的扩大、国家的不断形成与发展,单纯的分封诸侯和土地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影响区域也由黄河流域的一个地域而扩展至东亚地区。在东亚,中国的领土、人口、经济发展、文化、政治等都非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所能逾越。尤其是中国与东亚各国有所接触后,国家间的秩序关系就需由一个强有力的大国领导,中国则当之无愧。因此,其所主导的东亚关系带有浓厚的等级分封特点。当时东亚地区是由文化发达的“中国”和“四方蛮夷”组成,这也孕育了中国“大一统”意识。可见,东亚地区宗藩体系的出现与中国传统政治统治模式下的分封制和等级秩序分不开。
(三)东亚宗藩体系的发展阶段
秦汉至隋唐是宗藩体系发展、成熟与确立时期。《后汉书》载:“肃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20]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汉代时中国的对外交往,为东亚地区形成以华夷朝贡体制为特征的国际秩序做了重要工作,与当时的东南亚、西亚、中亚、北非等诸多国家都发生了联系,也设立了专门的外交机构和与之配套的管理体制。两汉时,东亚地区也初步形成了以华夷朝贡体制为特征的国际秩序。葭森健介指出:早在汉代与六朝时,日本、朝鲜就开始接触了中国汉字、儒家思想、礼制,并与中国构成了古代东亚的国际秩序。中原王朝为巩固统治,需要利用周边民族的朝贡以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各属国为维护自身生存与发展,也需要利用中原王朝的权威。在此利益关联中,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秩序[21]。《三国志》也载,汉至西晋,倭人之国来华朝贡多达三十余次[22]。汉、晋时汉光武帝诏封“汉委奴国王”、魏明帝之诏封倭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可见中日在汉代时就建立了宗藩体系[23]。至隋唐,陈寅恪在论述唐代对外关系时曾指出:“中国与其所接触的外族藩属国的盛衰兴废,多是带有连环性的而不是中国与某外族间的单独性。”[24]128可见,秦汉至隋唐,东亚宗藩体系通过朝贡等往来而发展至成熟。
宋元时期宗藩体系得到充实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与海外国家取得联系,宋代时,建立起了完备的市舶制度,也因此而与海外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更为紧密。宋代的朝贡贸易有了进一步发展,远至波斯湾的勿巡、非洲之层檀[25]。宋代中国对外贸易也有显著发展,前来贸易的大食商人增多,中国商人的活动范围以至马六甲海峡以东地区[26]。宋神宗也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若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中原地区的五代政权)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卿宜创法讲求,不唯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辏中国,亦壮观一事也。”[27]卷5,熙宁二年壬午条例司言条由于宋代统治区域的缩小,加之战乱的频繁,存在辽、西夏、大理、吐蕃、女真、蒙古等政权与之抗衡,因此,宋朝对于宗藩体系的发展也有维护的一面,即维护其宗主国地位。宋以后,元朝继承宋制。据载,元世祖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28]卷4《世祖本纪》,138元朝南征宋朝时,至元十三年曾遣使“招泉州蒲寿庚,寿宬兄弟”[28]卷4《世祖本纪》,122。因为蒲寿庚积极配合元朝,即《元史》中所载“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之利”[29]卷47《瀛国公二王附》。蒲寿庚也被委以高官。据统计,与宋朝确立宗藩关系的国家多达26个[30];与元朝确立宗藩体系的国家也有34个[31]。
经历宋元的维护和充实,至明朝时达到顶峰,在清中后期也走向了灭亡。修斌等指出明清时期是封贡体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其功能逐渐丧失、走向崩溃的时期[32]。明朝之鼎盛,也体现在朝贡国数量的增多,成祖时,郑和七次下西洋,足迹踏遍亚非37个国家和地区。所经之国纷纷派遣使者来明,朝贡国家多达148个,盛况空前。如明与安南之间的朝贡,仅明一朝,中国派往安南的使团有30余次,越南遣使来华有100多次[33],以致出现明时“四方宾服,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34]《成祖本纪》,105。鼎盛局面的出现与明朝统治者的支持有关。明初虽采取过海禁政策,但洪武十六年实行“勘合”制度之后,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这也为东亚地区宗藩体系走向鼎盛时期奠定了基础。
宗藩体系至明朝走向鼎盛,至清末最终解体。宗藩体系的衰落主要体现在朝贡国数量的减少,以及藩属国对宗主国反抗力度的增强。清朝时,朝贡国的数量较之明朝的150个明显减少。康熙皇帝也说过:“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35]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酋,751-752冯天瑜也介绍了17世纪以来英国三次遣使来华商谈通商事宜,但都败兴而归[36]。清朝成立后也积极维护这一体系,但终究未能挽救解体的局面。清时,“通过武力征服及继承明代宗藩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由宗主国清王朝和七个藩邦组成的东亚华夷秩序;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疯狂扩张,亚洲多数国家先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列强在亚洲建立起殖民体系”[37]。1840年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法战争后,越南脱离了宗藩体系,预示着东南亚地区开始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性国际关系向资本主义列强主导下的全球性国际关系转变。鸦片战争是东亚宗藩体系破坏的开端,宗藩体系真正意义上的解体是中国失去了对朝鲜的宗主权。
三、东亚地区传统宗藩秩序的特征与关系
(一)东亚地区传统宗藩秩序特征
在古代,中国及受中国影响下的东亚地区维持了上千年的和谐,虽不时出现战争,但相比于欧洲各国的战乱较为和平,这与当时中国宗藩体系影响之下的东亚政治秩序密不可分。费正清曾勾勒了古代“中国的世界秩序”,概括其是以中国为中心,但又是等级有序的。其所谓的等级即中国同周边的东亚其他民族国家间的等级秩序,同中心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辐射型关系。与此“中国为中心”观点不同的是,任晓认为:传统东亚秩序是一个共生体系或秩序。地区内的各个国家能够认清自己的位置,国家间也坚持并形成了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原则、规范等,成为在古代若干个世纪中这一体系运作的基本条件[38]。本文认同费正清等人提出的同中心——中心辐射型的东亚秩序。费正清将古代中国的世界秩序划分为三个主要地带。
第一,中国化地带。这一地带的构成主要包括朝鲜、越南等国,其主要特征便是文化上的相似与同源[39]。这类藩属国家与古代中国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且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前便与中国中原王朝之间已存在了宗藩朝贡关系。这些国家或者国家的部分地区在古代曾是中国直接统治或所辖领域之内。第二,内陆亚洲地带。这一地带的国家是由生活在东亚内陆地区的游牧民族、半游牧民族或国家所组织,与中原王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国家或部落所组成。这类国家包括“蒙古、翻越青藏高原的部分国家及新疆西藏地区的部族”。这类国家多是由中亚地区部分国家所组成,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少,中国与这类国家确立宗藩体系也多出于稳定边疆的目的。第三,外围地带。这类国家一般是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海外诸国,包括日本、东南亚地区国家、南亚地区国家及欧非海外国家。这种海外国家,即所谓的外夷与清朝的往来则带有较强的目的性,注重与清之间的朝贡贸易换得贸易差,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葡萄牙、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企图通商,俄国公使伊兹玛依洛夫来华与清政府洽谈通商,其发展贸易的目的很明确。以上三个地带的划分,其基础与“朝贡关系”密不可分,中国化地带与内陆亚洲地带都是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例行朝贡是维护双方和平局面、维持中国宗主地位并寻求大国庇护的形式和手段。外围地带则是在与海外各国取得联系之后,中国仍以其对待东亚属国的态度对待外围国家,双方来往的前提是必须承认中国宗主国地位,与海外国家进行所谓的封赐与朝贡,海外各国多数是带来商品货物进行贸易,也被当时的中国理解为进贡并进行赏赐。
(二)传统宗藩体系下的中国与属国间关系
1.文化方面。古代中国文化高度繁荣,位列四大文明古国之列,其文化在东亚地区极具影响力。方铁指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坚持的“守中治边”思想源于中国古代各封建王朝在文化上的优越性,及其对藩属国的吸引,这也是其文化上极度自信的反映[40]。从文化角度言之,就是认同中国文化优越性,这些藩属国为了吸收中国文化与融入这个文化,而主动地接受不平等的宗藩关系并主动地向中国进行朝贡[41]。东亚文化圈的形成源于中国文明的久远,这一文化体形成后,中国文化一直保持着对周边各种文化的优势。韩愈在《原道》中也指出:实现华夷一家,孔子之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42]。中国古代历代王朝以其先进的文化对周围国家形成了文化上的向心力,文化的繁荣也是对周遭国家增强吸引力的条件之一。如日本,18世纪时,经长期流播与浸润,儒家思想对于日本而言虽是一种外来文明,但是已经成为古代日本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家文化既外化为日本的制度、规范,又内化为日本人的民族性”[43]。即使是近代,“日本虽然跻身于主权国家之行列,但在观念上依然没有摆脱古代华夏文明体系的制约,并在国际实践中试图重建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东亚朝贡体系——‘大东亚共荣圈’”[44]。对于藩属国文化影响较深远的还包括朝鲜国,周海宁通过高丽、朝鲜时代的史学体例与史学思想的形式与内容,论述了中国文化对其影响[45]。文化是中国与周边属国确立宗藩体系的纽带,各属国受中国文化的吸引而加强联系,尤其是受到中国传统儒学的正统思想影响,实现中原王朝统治在宗法上的合理合法性。
2.经济方面。就地理位置而言,东亚属于典型季风气候区,其雨热同期的特点适宜种植农作物。中国中、东部地区存在的大面积平原耕地,这都为农耕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存在于中国北方的高原牧区及东部沿海地区,对于畜牧业、渔业发展影响深远,不同类型区域的广泛存在,对于古代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古代中国在强盛国力支配下,积极发展对外交流,活跃于北方的丝绸之路、南部地区的茶马古道、海上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上的玉石之路与黄金之路以及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草原之路等。中国同西域、海外诸国的交流,对于扩大中国的影响力、促进中国的发展、提高中国的地位都起到了巨大作用。“中原王朝与藩属国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合作双赢。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除了正常的朝贡与赏赐外,前往中原王朝的藩国使团也带领商人团队前往中国。定期向中原王朝朝贡也是实现与中国进行商品交换的合法途径和有效方式,这样的朝贡贸易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经济圈。”[14]64强大的经济实力也是加强对藩属国吸引的有利条件,农耕时代,藩属国中多数都是物资贫乏、经济发展落后的小国,诸如琉球一类的国家则仰仗与中国的朝贡换取所需物资。
3.环境方面。学者指出,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即边疆地区存在的诸多高山、大漠、海洋等天然屏障,如西部的荒漠与高山、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东南及东部的海洋、北部寒冷气候及山脉,这些都阻碍了中国同其他世界重要文明古国的联系和了解,这也是历朝形成华夏文明至上观念的原因所在[40]3。高山、沙漠、海洋等地形区形成了天然生态屏障使东亚成为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区域,中原王朝则因一国独强而成为霸主,形成了中国中心主义的优越意识。周围的高山、大海、高原等的独特地形阻隔了中国与外界的往来,中国古老的长江、黄河、草原文明又有其先进性,周边属国无论是领土、人口、经济、文化等都难以与中原王朝抗衡。封闭的环境,闭塞的交通使中国与世界缺乏联系,在中国与周围的小国相比长期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享受着天朝上国的殊荣,以及类似于父兄长辈的崇高地位而自我陶醉着。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以中国为中心,呈现“中心—外围”的国际秩序。受中国的影响,藩属国也以中原王朝马首是瞻,直到地理大发现及沙俄越过乌拉尔山后,外来强国开始介入,才让中原王朝意识到世界和其他国家的存在。因此,在当时特殊的地理环境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宗藩体系得以长期存在。
4.政治、军事方面。古代中国的政治较之周遭属国有其进步性,这些制度在古代社会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都是有其进步性的。双方出于政治利益考虑,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互相承认其合法性也是宗藩体系存在的一个原因。中国军事力量强盛也与经济、文化繁荣分不开,中国的先进文化和进步技术及繁荣的经济必然带来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加之中国疆域庞大,人口相比于藩属国地区较多,这些都使中国在各方面占据优势。《明史》载:“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于独石,世宗时复弃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岭,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34]《地理一》,882因此,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是促成中国对宗藩体系的维护以及东亚秩序稳定所不可忽视的因素,尤其是凭借强盛的军事实力来镇压和威慑藩属国,使其对中原封建王朝的臣服。先进的技术、庞大的人口与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其征服四夷、树立崇高地位的必备条件。不仅如此,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也承担着对藩属国保护的职能。如明朝“援朝御倭战争”,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企图打破明朝所主导的宗藩体系,重新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东亚秩序。明朝先后两次出兵,历时七年,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明朝的出兵即是出于对其宗主国地位的维护,也是宗主国对藩属国履行保护职能的体现。
四、宗藩体系的运行手段
(一)武力征服
通过战争以达到对周边地区、国家的控制。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几次战役,包括西汉时对匈奴的征讨、隋炀帝三次远征高丽、唐与日本战争、清朝平定蒙古准格尔叛乱及对朝鲜的出兵等,这些都是以武力实现对周围地区和属国的控制。武力征服是效果最明显,也是最迅速的方式,明末时,后金曾与朝鲜约为兄弟之国,然随着后金实力的强大与清朝的建立,朝鲜拒承认其宗主地位,引发清廷对朝鲜的战争,最后迫使朝鲜签订了宗藩体系条约。这也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及中国古代西汉王朝提出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践行。武力手段是中原王朝运行和维护与藩属国之间宗藩体系以及发展更多藩属国的重要方式。但是除遇战乱时或藩属国的反抗,武力是很少采用的方式。
(二)文化影响
通过文化和思想的方式教化四夷,包括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礼教的推行,等等,以实现控制东亚地区的目的。如中越之间的关系,越南在境内修筑的文庙、武庙,所供奉敬拜的偶像,有周公、孔子、孟子和孙武、孔明、岳飞等,四时祭祀不绝[46]91。“古代东亚国际秩序,主要不是靠武力维系,而是依靠华夏‘礼仪’,即政体组织形态、儒家理念、法律体系的吸引力,形成非强制性的‘天下秩序’。”[47]如朝鲜,“朝鲜国李氏王朝建立之后,太祖李成桂即在群臣的帮助下,以儒家思想的标准日御经筵,勤读《大学衍义》以及设谏官、史官,还为新官诸殿命名”[48]上卷,51。各藩属国主要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藩属国自身文化的发展也带有浓厚的中国儒家文化的气息。金日坤就韩国当下社会习俗指出:至今,儒家在韩国社会中仍占绝对比重。儒家思想不仅改变了韩国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的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较大变动[49]。礼法是通过思想领域树立宗藩体系的主要方式,也是最为和平、有效的手段。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国人希望用仁政“陶冶万物,化正天下”,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50]。
(三)利益吸附
主要是通过宗藩体系下的朝贡贸易为手段,也有民间及官方的互市贸易。双方贸易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往来,甚至也可影响到边疆及属国生计。有些时候因中原王朝关闭了同边疆地区的互市贸易,边疆地区为开市与中原往来而发动战争。通过“利益”方式而维持宗藩体系是一个有效的方式。如中越间,中越两国山水相连。这种紧密的地理区位也确立了古代越南与中国的地域关系。古代的越南与中原王朝之间经济往来频繁,中国地大物博,越南也需仰仗与中国的经济交往获取所需。主要是粮食、丝绸……双方建立在宗藩体系基础上的朝贡贸易是中越两国进行贸易交换的媒介和途径。这也是双方几个世纪宗藩关系的主要维系途径。……宗藩体系也是两国间友好相处,两国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保障[46]90。利益是吸引属国来朝贡,加强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联系的主要手段,也是宗藩体系的重要纽带。
(四)宗教笼络
随着中国文化向日韩等国的扩散,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佛教也被一同介绍到了藩属国,并成为其国内的一种宗教信仰,中国的宗教也成了东亚文化圈内的一种普及性宗教[51]。祁美琴指出,清立国后,对于宗教采取的态度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即有利有用则推举,无利无用则抑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52]146。利用宗教对国家政权的管理集中体现的是清朝,历代王朝中没有一个超过清朝。“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在蒙疆地区,极力倡导并扶植喇嘛教,作为笼络蒙古族和藏族群众的手段。蒙古族、藏族生活区域多在我国边疆,其游牧生活于经济及对喇嘛教的信奉,对清朝政权巩固、国家统一具有特殊的作用。”[53]如在清成立之初,与东亚紧靠的中亚地区多是游牧国家,伊斯兰教是中亚地区人民的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对于信奉民族和教众有着极强的凝聚力,民族间通过宗教而结合。各个民族间频繁的征伐,势必需要寻找一种超越民族精神的凝聚力,而伊斯兰教则恰好满足了这样的精神需求[52]149-150。鉴于此,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平定准格尔叛乱后,噶尔丹受到重创。康熙皇帝便改变了武力征讨的政策,采用宗教教化方式,利用了伊斯兰教,主张准格尔应与回回各行其道,双方“永相和好”[35]896。
五、中国主导下东亚宗藩体系特征
(一)封闭性
宗藩体系是古代的中原王朝与周边藩属国之间外交关系的主要形态,也是历代中原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遵循的主要模式,也由此而构筑起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且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区域。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指出:“自人类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区域性国际关系时代起,东亚地区就已经成为自成体系的世界。”[54]封闭性出现的原因之一便是统治者的保守意识,固守于东亚地区的共主地位。一方面,作为区域内压倒性大国的中国无意打破现状,向天朝之外做体制性经营,从而维持了东亚地区国家间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另一方面,“朝贡—册封”的秩序扩散,为儒家文化在东亚地区的固化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代东亚区域意识兴起、区域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相应的路径支撑。当时东亚秩序相对封闭,也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无外”的思想。据赵汀阳解读,“天下”是至大无边界的概念,而“无外”则意味着所有事情都是可以被它所容纳的[53]14。中国人将中国看作世界,而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对待,并认为中国是这个世界的主导,世界也即中国。在这个整体内,中国管辖诸国,享受万邦来朝的尊严。其所确立的也是以中国为中心,相对独立区域的封闭环境内的宗藩体系。其封闭性的出现,也是文化因素所促成的,即中国主导的东亚地区文化的形成,是极少受到人类文化其他发祥地的影响,但是尽管封闭,东亚文化的发展水平还是长期高于周边地区的。
(二)区域性
由于东亚地区的独特地理环境,中国文化在这一地区高度繁荣且一家独强,古代社会与外界交流的不便也导致东亚地区的宗藩体系具有极强的区域性。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其理论基础即上下等级有序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具体而言,也可以从地域与文化圈两个角度论述其独特性所在。地域上,滨下武志指出:“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维护,也即在此秩序下亚洲全境密切联系存在的基础即是指朝贡关系,也是亚洲而且只是亚洲才具有的唯一的体系。对于古代东亚秩序的了解,必须要从这一视角出发,在反复思考中才能够推导出亚洲地区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55]文化上,最集中的体现便是受中国影响而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经典的古代东亚地区的儒家文化圈。“这个文化圈内,不论人种、文字系统、家族结构、生产与生活方式及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历史时期形成的共性及相关性,而同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或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圈相比,东亚儒家文化区具有鲜明独特性。”[56]
(三)稳定性
中国与各藩属国之间的宗藩体系维系了近千年,其长期存在体现了极强的稳定性。其稳定性局面的出现也是由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因素促成的。文化因素: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作为秩序内大国的宗主国,对藩属小国要以礼相待,以道德教化属国,展现其统治的仁慈之心与博大胸怀。仁与义是宗主国对藩属国的态度,而礼则是维持秩序有效的、和谐的方式。通过礼仪规范,明确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地位、关系。“双方的关系基本上是以礼仪的形式为其架构。”[48]上卷,96中国与周边属国都在儒家文化圈的辐射范围内,东亚地区也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的儒家文化圈。政治因素:表现为相对稳定的体系规范,东亚文化区域内的各国家和地区普遍遵循着古代东亚地区间的国家关系准则。受中国影响下的东亚共同体就具备这样的秩序,中国凭借其优越的经济、军事、文化上的实力影响着各藩属国。与西欧国际关系相比较,古代中国与朝贡国之间维持了一种更为长久的和平秩序。经济因素:宗藩体系得以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经济利益。“古代的东亚朝贡体制是中国与周边藩属国家之间表示臣属、等级关系的基本形式,也是宗藩国家之间官方贸易的主要形式,通过两国之间的朝贡与回赠,对两国之间特产和物品进行交往,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57]《明实录》也载:“朝贡者悉依品级给赐赍,虽加厚不为过也。”[58]卷233,永乐十九年正月可见,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和各藩属国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但又同归一处。中国为维护其天朝上国和高不可攀的地位而予以藩属国以相当的利益,而藩属国出于自身需要也需借助宗藩体系与中国交往。
(四)松散性
松散性主要表现便是其统治的松散性,中国虽是宗主国,对各藩属国的统治在多数时候是“统而不治”,通过礼与法、道与德、武力威慑、朝贡等方式加以维系,而非西方殖民体系的残酷镇压与野蛮掠夺。这也就是张小明所说的中国与藩属国之间以朝贡、册封等形式发展而成的“中心—边缘”的关系[59]。这种朝贡、册封关系也是不具有约束力的政治关系。东亚地区宗藩体系以朝贡和册封为主要体现,其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中国作为中心具有支配权,而藩属国则是从属地位。这种结构内部组织松散,宗主国对藩属国也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宗藩体系也只是一种礼仪象征。受此松散秩序的影响,各属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可以自立,也可以发展[48]上卷,264。这种松散性的直接危害就是“中国一旦在军事上处于弱势,则无法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这既危害了中国自身的利益,也影响到它的藩邦、属国的国家利益”[48]下卷,559。
(五)秩序性
东亚宗藩体系在历史时期也曾有变动。如: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与北魏和南朝之间关系的变化,高句丽的多方外交政策,活跃于中国大地上各主要政权之间[60];隋炀帝三次远征高丽;唐代玄宗时,与渤海国之间的战争,出现的唐新(新罗)联盟、渤日联盟间的争斗;明朝时日本与朝鲜的战争。上述皆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东亚地区宗藩体系中有违秩序的几个代表性事件,但是东亚地区的秩序并非混乱不堪,而是有其秩序性的,即中国统治下,辐射至周围属国的秩序,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辐射型秩序圈。这一秩序也体现在国家间关系的不平等上,即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等级也由高至低。除中国外,各藩国中的大藩往往把自己的华夷意识强加给小藩和弱藩,并力图使它臣服,大藩的大国意识与小藩的事大主意识相合时形成“藩望”以及诸藩国外交地位上的差别[61]。作为宗主国,对藩属国予以帮扶。如中国对朝鲜渔民的帮扶,彰显大国风范。“乾隆四年十一月,盛京侍郎德福等奏言:朝鲜渔船被风飘至海宁界,资送渔户金铁等由陆路归国。嗣后凡朝鲜民人被风漂入内地者,俱给赀护送归国。”[62]《属国一·朝鲜》这一秩序中,不存在西方列强的那种掠夺性、扩张性行为,大国所扮演的是父兄的角色,对于藩属国也予以一定的照顾,双方多数时候是和平共处的。
[1]秦进才,主编.中国帝王后妃大辞典[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578.
[2]张民服,徐晶.明代河南宗藩浅述[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1):48.
[3]刘志扬,李大龙.“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四[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3):27.
[4]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等.汉语大词典:第9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609.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增补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44.
[6]高文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2173.
[7]迟文浚,等主编.历代赋辞典[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1070.
[8]安德义,主编.逆序类聚古汉语词典[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431.
[9]黄运武,主编.新编财政大辞典[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1033.
[10]郑天挺,等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2617.
[11]顾国瑞,等编.唐代诗词语词典故词典[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94.
[12]杨军.中国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34.
[13]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M].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
[14]唐彦林.东亚秩序变迁中的中国角色转换[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8.
[15]马士,密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M].姚曾廙,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1-11.
[16]李云泉.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3):37.
[17]喻常森.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J].南洋问题研究,2000(1):56.
[18]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43-44.
[19]钱穆.国史大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6-46.
[20]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1]葭森健介,张宇.东亚世界的形成与中国皇权——以六朝时期为重点[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70-78.
[22]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854.
[23]张碧波.汉、晋与日本关系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6):98-103.
[2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8.
[25]卢苇.中外关系史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249.
[26]宫崎正胜,曲翰章.从郑和海图看十五世纪中国对南海的认识[J].国外社会科学,1987(2):68-71.
[27]黄以周,等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4:239.
[28]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9]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633.
[30]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104.
[31]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84-87.
[32]修斌,姜秉国.琉球亡国与东亚封贡体制功能的丧失[J].日本学刊,2007(6):117.
[33]于建胜,等.落日的挽歌——19世纪晚清对外关系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34.
[34]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5]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36]冯天瑜.文化守望[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17-120.
[37]吴蓓.十九世纪亚洲的宗藩体系与殖民体系[J].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8(1):29.
[38]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7):4.
[39]许建英.“中国世界秩序观”之影响及其与中国古代边疆研究——费正清《中国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读后[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1):36.
[40]方铁.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4).
[41]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用[J].国际政治研究,2006(1):75.
[42]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7.
[43]杨贵言.当代东亚问题研究简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2-63.
[44]武心波.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J].国际观察,2003(6):60.
[45]周海宁.中国文化对高丽、朝鲜时代史学之影响研究——以史学体例和史学思想为中心[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3:53.
[46]彭大雍,范宏贵.论中越宗藩关系与清朝保藩固边[J].广西师院学报,1988(3).
[47]卢璟.华夷观念与文化优势[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5):67.
[48]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亚洲华夷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9]金日坤.儒教文化的集权秩序与现代化——“东亚经济发展和儒教文化”专题研究之二[J].当代韩国,1995:56-60.
[50]冯天瑜,主编.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98.
[51]汪高鑫.古代东亚文化圈的基本特征(二)[J].巢湖学院学报,2008(4):1.
[52]祁美琴.清代宗教与国家关系简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6).
[53]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5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237.
[55]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贸易圈[M].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79.
[5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12.
[57]杨昭全,何彤梅.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100.
[58]明实录:第14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3.
[59]张小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J].国际政治研究,2006(1):59.
[60]宋成有,汤重南,主编.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3.
[61]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396.
[62]赵尔巽,主编.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4588.
[责任编辑:岳 岭]
2016-12-10
崔思朋(1992— ),男,黑龙江省五常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清史、生态环境史、内蒙古地区史。
K31
A
1002-6320(2017)02-0035-08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