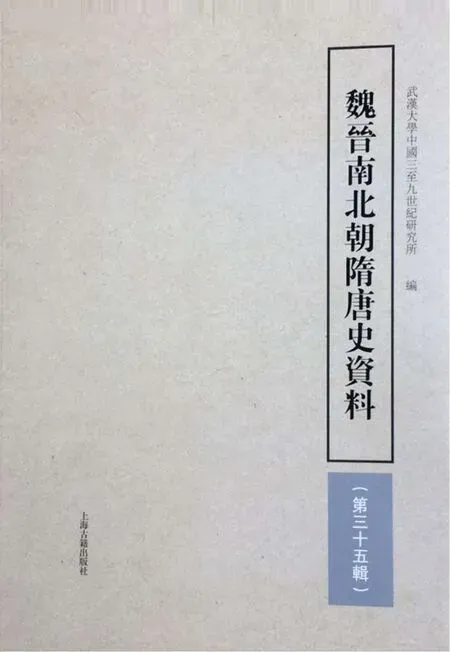家國之間: 北齊宗王政治變遷與末年皇位争奪
姜望來
家國之間:北齊宗王政治變遷與末年皇位争奪
姜望來
由高氏所建立的北齊是南北朝後期一個重要而特殊的王朝: 前期强盛而後期衰亂,矛盾重重而終難解決,立國短暫而影響深遠。與之相關,北齊政治史研究歷來是學界關注的重點並已取得豐富的成果。*有關北齊政治史研究成果相當豐富,筆者僅能就己所知、與本文關係較近者略加回顧。其一,有關北齊史料、史事之考訂。如清人錢大昕《廿二史考异》、趙翼《廿二史札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之北齊部分,近人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齊部分、唐長孺《北齊書》(中華書局點校本)之“校勘記”等。其二,有關北齊史之通論。如吕思勉《兩晉南北朝史》、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録》、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對於北齊王朝之盛衰及相關重要政治人物與事件,作了較詳細的梳理;日本學者尾形勇所著《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雖不是以北齊時代爲重點,但其討論中國古代皇帝與家及國家之關係,從方法論上對本文有着重要啓迪。其三,有關北齊史之專論,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1) 北齊制度研究。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論述了北齊一朝制度流變與對隋唐制度之影響,奠定了北齊制度研究之基礎與規模,對學界有着深遠影響,但陳先生高屋建瓴所論宏大精深,某些具體制度如本文所關注之皇位傳承制度仍待深入。(2) 北齊政治集團與國家興亡研究。如毛漢光《北魏東魏北齊之核心集團與核心區》(收入氏著《中國中古政治史論》)、谷川道雄《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之第二章《北齊政治史與漢人貴族》、吕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 從階級、地域、胡漢、新舊等多個層面對北齊政治進行了分析。(3)北齊胡漢衝突。此方面成果尤多,如繆鉞《東魏北齊政治上漢人與鮮卑人之衝突》(收入氏著《讀史存稿》)、孫同勛《北魏末年與北齊時代的胡漢衝突》(《思與言》第2卷第4期,1964年)、蕭璠《東魏北齊内部的胡漢問題及其背景》(《食貨月刊(復刊)》第6卷第8期,1976年)、胡勝源《東魏北齊政治與文化問題新探》(臺灣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但論者對於北齊是否存在明顯的胡漢衝突問題或贊成或反對,論證方法、角度與所得結論也不盡一致。但是,由於問題本身的複雜性,由於相關史料的相對缺乏與混亂,北齊政治運作與演進及其内在矛盾之問題,仍然存在頗多令人迷惑的歷史疑難或學術研究之薄弱處;已有研究所遺留的分歧、所未及關注或深入之處仍然存在,尤其北齊皇帝及其家族在皇權政治中之動向、矛盾與背景未得到足够的重視,有待在進一步梳理、挖掘、審視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細緻考察和系統闡釋。
如所周知,皇權政治的核心在於皇帝及其家族,*參見尾形勇: 《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序章第一節“序論——所謂‘國家家族觀’”,張鶴泉譯,北京: 中華書局,2010年,第1—14頁。此點在北齊尤爲明顯,皇位的傳承與争奪、皇室的參政與矛盾始終是北齊政治發展的主導因素,尤其宗王政治之變遷與北齊末年之衰亂有着密切聯繫。本文擬參考前人研究成果,並在筆者之前相關研究基礎上,*參見拙撰: 《高洋所謂“殷家弟及”試釋》(《武漢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北齊功臣配饗小考》(《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2期)、《祖宗與正統: 北齊宗廟變遷與帝位傳承》(《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等文。重點從家族盛衰與國家興亡之角度考察北齊皇族在北齊皇權政治演進中的角色與影響,試圖揭示在北朝後期特殊歷史環境下高齊皇族與皇帝在家國之間的困境與衝突;當然,本文所提出的一些見解或看法未必妥當,筆者希望能够抛磚引玉並得到學界師長友朋之教正,或有助於相關論題之深化或解決。
一、 北齊宗王政治之變遷與恩倖政治之興起
《北齊書》卷五〇《恩倖傳·序》云:
甚哉齊末之嬖倖也,蓋書契以降未之有焉。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刑殘閹宦、蒼頭盧兒、西域醜胡、龜兹雜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比肩。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虚。杼軸之資,剥掠將盡。縱龜鼎之祚,卜世靈長,屬此淫昏,無不亡之理,齊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之徒唯左右驅馳,内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大寧之後,奸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
按,北齊後期自世祖武成皇帝高湛以後,和士開、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等嬖倖當權,操弄國柄,勢淩皇族(本文稱之爲恩倖政治),其參與和影響政局之深,無論較之前代還是同時的北周王朝都迥有過之,可謂北齊政治之一大特色,史臣所謂“甚哉齊末之嬖倖也,蓋書契以降未之有焉”並非虚言。*恩倖政治興起於武成時及主要源於君權之需要,前人多有指出,如谷川道雄:“據《北齊書》卷五《恩倖傳序》,北齊政治史上極具特色的恩倖之政並非從來就有,而是始於‘大寧之後’。”(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09頁。)吕春盛:“要探討北齊末恩倖特别嚴重的原因,由君主權問題的探討入手,可能纔是最根本的癥結所在。”“恩倖政治隨着君權發展的需要而興起……君位的鞏固與轉移爲當時統治者最嚴重關切的難題,此一難題到了武成帝高湛時代所采取的解決之道,是用恩倖之臣助其剷除异己,而恩倖人物也循此邀寵求功。”“高湛即位之後大量引用寵倖,恩倖政治隨着興起。”(吕春盛: 《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7年,第160、229—230、257頁。)王怡辰:“高湛和高緯統治時代,政治形勢又有大轉變,爲提高皇權和保障皇位繼承的穩定性,高湛父子及妻妾間有另結班底穩固政權的共識,於是籍着恩倖人物逐步分卸勛貴的大權,另外形成一個政治上的主流派系。”(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北京: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312頁。)按,本文所謂恩倖,其實比較籠統,也没有列出具體包括哪些人,主要是因爲考慮到恩倖成分比較複雜難於盡舉和在某些具體人物上會存在争議;大致上還是認爲主要包括依附於皇權邀寵得幸的一批人,主體是商胡閹宦内廷驅使之人,也包括部分官僚、勛貴、宗室之類;王怡辰謂:“他們的組成成分頗複雜,有皇帝引爲心腹的勛貴和宗室成員,有漢人士族和鮮卑國姓,有婦女裙帶的外戚,有西域胡人,有相命師,有工音樂書畫藝術之人,有蒼頭侍衛門閹驅使,不論何種出身,都只爲一件事:‘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顔色,競進諂諛,莫不發言動意,多會深旨。’”(《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第312—313頁)筆者基本贊同和沿襲其看法。又,某些宗室也可視爲恩倖,如武成時代之高元海、高歸彦等;有一點頗有意味,即北齊後期受到重用的宗室往往是和皇帝關係較爲疏遠的高歡子孫一系以外的疏宗;所以本文認爲,宗王與恩倖之對立大致上可以成立,但並非二者絶不相混。不過,此序雖然概括了北齊恩倖横行的情形及其興起的大致時間,而於恩倖政治何以興起、與皇族輔政之盛衰(本文稱之爲宗王政治)有何關係以及二者之進退於北齊衰亡有何影響等問題並未深究,當然前人已有注目和研究,本文擬從皇帝與其家族矛盾之角度略加補充。
隋人盧思道述及北齊後主時恩倖權勢云:
舞弄王法,掩塞天聽。慶賞威刑,出於婢口;頑嚚弟侄,布於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文苑英華》卷七五一載盧思道《北齊興亡論》。
盧思道,《隋書》卷五七、《北史》卷三〇有傳,出自范陽盧氏,仕歷北齊數朝,後主時爲給事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爲北齊著名文人,齊亡入周,再入隋。思道本齊人,又仕近職,可謂北齊史之親歷者,其所謂“帝戚皇支,不能及也”正道出北齊皇族(皇支)與恩倖小人之進退關係。*又《文苑英華》卷七五三載唐人朱敬則謂:“弃親即仇,高緯之志。”高緯即北齊後主,所謂“弃親”當主要指其壓抑宗室,所謂“即仇”當主要指其信用恩倖。
宗室輔政,歷代多有,北齊亦如之,其統治前期(武成之前即神武、文襄、文宣、孝昭時期)宗王參政尤爲明顯,多有執軍國大權,藩屏王室。以皇權政治中關鍵之皇位傳承爲例,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均以諸王身份以弟繼兄入居大位,自不待言;而諸帝之登位,亦往往有宗王在其間起到核心作用: 孝昭誅楊愔等輔政大臣廢黜廢帝高殷,弟長廣王高湛、侄河南王高孝瑜、族叔平秦王高歸彦、從子上洛王高元海等預謀;武成謀取帝位時,侄河南王孝瑜、從子上洛王元海等預謀,後孝昭崩後宣遺詔至晉陽征武成入居大統者有上洛王元海、從兄趙郡王叡、族叔平秦王歸彦。*見《北史》卷七《齊本紀中·孝昭紀》及《武成紀》,《北史》卷五一《齊宗室諸王上·上洛王思宗附子元海傳》、《齊宗室諸王上·平秦王歸彦傳》,《北齊書》卷一三《趙郡王琛附子叡傳》等相關記載。高氏前期宗室輔政之具體情形及宗王政治之興盛,前賢具有論述,無須多言;*較全面者可參考前揭吕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然而高氏皇族並非一直能够居於統治核心,其地位亦隨時局之發展而變化,下面略加考察。
《北史》卷五二《齊宗室諸王下·廣寧王孝珩傳》云:
齊王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算,展我心力耳。”
廣寧王高孝珩,北齊世宗文襄皇帝高澄第二子,北周滅北齊後爲周人所俘,其對周齊王宇文憲問“齊亡所由”時所謂“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即高齊皇族成員之短命。又同書卷五一《齊宗室諸王上·任城王湝傳》:
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並赦詔,湝並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被禽。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
任城王高湝,齊高祖神武皇帝高歡第十子、廣寧王之叔父,其所謂“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亦從一側面印證廣寧王之歎高氏皇族的促壽。
按《南史》卷六二《顧協傳》:“張率嘗薦之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强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敕唤出。’”北方之人,四十正當强壯之年,但高齊皇族除高歡以外,無人卒時年過四十,可謂極不正常,而此既是高齊皇族内部激烈、殘酷政争之結果,又反映出宗王政治在皇權體制下的兩面性: 一方面皇族是皇權的重要基礎和維護皇權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因爲皇族内的派系分立和利益之争(以皇位争奪爲核心),皇族内部矛盾重重,尤其在北齊皇位傳承制度與現實的複雜情境下,宗室無疑會捲入其中,宗王政治由盛而衰遂不可避免。*當然,本文並非認爲高氏皇族具體成員之短命全爲政治之犧牲品,其中亦有因病、因傷之例;只是説,從高氏皇族整體而言,其普遍早卒主因在於皇族内争。
高氏皇位傳承,前期以弟及爲主,至武成時期通過内禪之非常方式確立子繼模式,然而縱貫北齊統治時期,弟及與子繼之矛盾始終存在且相當激烈,弟及之觀念亦是根深蒂固,並深刻影響到政局變遷。*參見拙撰《高洋所謂“殷家弟及”試釋》(《武漢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北齊功臣配饗小考》(《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2期)、《祖宗與正統: 北齊宗廟變遷與帝位傳承》(《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等文。文襄、文宣、孝昭、武成四帝爲兄弟之現實,所導致的顯然後果就是各帝子孫(尤其是較年長的文襄、文宣諸子)及其擁護者的分裂與對立,對皇位的争奪或覬覦變得順理成章: 如果帝位傳承貫徹弟及,則上一代兄弟盡後下一代當依次兄弟繼立;如果子繼確立其正統性,則各帝子孫(尤其作爲高歡長子的文襄之諸子)皆有當承皇位之理由;無論何種情形,各帝子孫的争奪均將難免。爲防範各支系和諸弟的争奪,“各愛其子”的在位皇帝積極抑制甚至誅殺諸弟和其他兄弟支系就成爲常見之事(《北齊書》、《北史》諸宗室傳不勝枚舉),高氏皇族成員尤其是血緣本更親近的皇帝之兄弟叔侄等核心成員,成爲首要的清洗目標,這正是廣寧王高孝珩感歎“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的背景。
《北史》卷五二《齊宗室諸王傳下》史臣“論曰”在列舉文襄、文宣、孝昭諸子多罹不幸之後謂:“各愛其子,豈其然乎?”一語道出以弟及登位的諸帝卻不遺餘力企圖確立子繼這樣看似矛盾卻又合乎人情之現實,亦進一步佐證弟及與子繼間不可調和之矛盾。隨着皇帝對宗室的猜忌常態化,隨着高氏皇族普遍的壯年甚或幼年非正常死亡,北齊宗王在政治上逐漸失勢、宗王政治逐漸趨於衰落遂成必然之勢。*《齊宗室諸王下·淮南王仁光傳》記載:“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諸王被禁守,天子(後主)之弟仁邕等供給儉薄,與北齊前期宗室輔政重任形成强烈反差,正是宗王政治衰落的鮮明反映。
源於對皇權的争奪,北齊宗王政治漸趨衰落,尤其在武成内禪傳位其子後主高緯、强行確立皇位傳承子繼模式後,原作爲皇權重要基礎的皇族權位更被壓抑;爲加强和鞏固皇權,也爲填補宗王失勢後留下的權力真空,皇帝身邊的近習小人紛紛登場,《北齊書》卷五〇《恩倖傳·序》云“大寧之後,奸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大寧”即武成第一個年號,史臣將北齊恩倖之“浸繁”系於武成以後,大致不誤。不過,儘管武成以後恩倖政治盛極一時,北齊恩倖也不是驟然興起,而是在之前伴隨皇族内部從來不曾完全斷絶的矛盾有一個醖釀發展的過程。
《恩倖傳·序》云:“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之徒唯左右驅馳,内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似乎文宣時並無恩倖干政之事,不過考之史籍卻不儘然。《北史》卷二四《王憲附王晞傳》:
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宫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沖,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沖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
按,王晞所謂“天保享祚,東宫委一胡人”之“胡人”即康虎兒,*《資治通鑑》卷一六八陳文帝天嘉元年二月記載王晞進言常山王高演之後謂:“顯祖常遣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故晞言及之。”王晞特以太子近習康虎兒爲言並深致憂慮,且常山王高演(即後來之孝昭帝)亦認同,至少表明天保之時已有皇帝、太子親任“小人”的迹象,雖然未必已經干政,但已引起高演及其謀士王晞警惕。《文苑英華》卷七五一載盧思道《北齊興亡論》云:
文宣不豫,斃於趨孽。儲君繼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
所謂廢帝即位後“近習預權,小人並進”雖未明言“近習”、“小人”爲誰,卻表明廢帝時恩倖之徒似已獲進用,亦印證此前王晞關於康虎兒之言並非空穴來風。又《北史》卷五一《齊宗室諸王上·襄城王淯傳》:
襄城景王淯,神武第八子也……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
襄城王高淯薨於天保二年,其時已是“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群小之徒充斥諸王府。
武成之前的文宣、廢帝時,無論皇帝、太子還是諸王,身邊多有近習小人且已獲一定程度信用,雖不確知涉入政治至何種程度,但視其爲武成以後恩倖政治興起之濫觴與先聲應無不可。
輔政之宗王與皇帝身邊的恩倖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是天然對立的: 宗王任重並獲信用,恩倖之徒自無多少騰達空間;恩倖勢盛,宗王權位自必遭到削弱,因恩倖實際上也是依附於皇帝,其受重用,不過是皇族内争中皇帝維護自身權威和以之抗衡宗王之工具。常山王高演與王晞關於康虎兒的憂慮已經表明此點。事實上,北齊宗王政治由盛而漸衰,雖然根源於皇帝與皇族在皇權争奪上的矛盾,不過宗王與恩倖在政治舞臺上的表現確呈現出互爲進退之關係,此點在武成以後尤爲明顯:*《北齊書》卷一三:“史臣曰: 《易》稱:‘天地盈虚,與時消息,況於人乎。’蓋以通塞有期,汙隆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之。小人道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博陸之圖,處藩屏之地,而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按,《北齊書》卷一〇至一四爲宗室諸傳,但卷一〇、一一、一二、一四闕失,後人以《北史》卷五一《齊宗室諸王傳上》、卷五二《齊宗室諸王傳下》相關諸傳補全而删去《北史》卷末史臣論;僅卷一三趙郡、清河二王傳乃《北齊書》原文並存有卷末“史臣曰”,以之與《北史》史臣論相關部分比較,可見《北史》史臣論基本沿襲《北齊書》而有所删節。因此,以《北齊書》卷一三“史臣曰”與《北史》卷五一、五二史臣論合而觀之,基本可見北齊宗室諸王傳史臣論之大概。但《北史》有關宗室傳論基本就某一傳主而發論,不見綜合性的議論;只有上引《北齊書》卷一三此段史論頗有綜合的意味,其中所謂“小人”當即指恩倖之徒,從其言論間,亦可略見宗室與恩倖此消則彼長之意。因至武成時代,方成功確立父死子繼之皇位傳承模式,武成一系與皇族其他宗支的矛盾成爲高齊皇室内部的主要衝突,恩倖之徒成爲武成父子抗衡、壓制諸宗王的最有效工具,我們稱之爲恩倖政治的現象纔終於興起。
武成以後,北齊政治舞臺上恩倖進宗王退,兩者間矛盾(實質上是武成父子與皇族其他宗支的矛盾)愈演愈烈,内耗越來越深。*武成以後,宗王每謀除去當權恩倖,恩倖亦多借助皇帝之支持而反噬。較著者如後主天統四年(568)武成崩後,趙郡王高叡謀出和士開等反被殺;武平二年(570)七月,琅邪王高儼矯詔殺録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廣寧王高孝珩、安德王高延宗更欲鼓動其率衆入宫,後陸令萱穆提婆母子主謀殺儼;武平七年(576)後主晉州敗後齊將亡前夕,廣寧王高孝珩猶謀率衆誅殺高阿那肱而不果,而高阿那肱亦始終抑兵權不予孝珩。北齊國家與高氏皇權,在武成時代進入由盛而衰的轉捩點,亦基本上史無异辭。如《北史》卷八《齊本紀下》卷末史臣總論:
(文襄時)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故能氣懾西鄰……(文宣時)外内充實,疆埸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已墜。暨乎後主,外内崩離,衆潰於平陽,身禽於青土。
又《北史》卷五四《斛律金附子光傳》:
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守河椎冰。及帝(武成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
又《文苑英華》卷七五一載盧思道《北齊興亡論》在敍述武成時和士開得寵擅權後謂:
齊室大壞,其源始於此。
可以説,武成以後,北齊由盛而衰,與宗王政治之衰落和恩倖政治之興起俱有所關聯,然其根源,仍在於北齊皇帝及其家族圍繞皇權争奪而導致的難以調和的矛盾。*本節内容曾提交2015年7月底在陝西師範大學召開的“第三届中國中古史前沿論壇”,承范兆飛教授賜示批評意見,並據之做了一些修改和補充,謹在此説明致謝;但是由於本人學識和時間限制以及思考仍非成熟,仍有相當的問題存在和未能補正之處,只能留待將來再加補綴。
二、 北齊末年的皇位争奪
北齊皇位傳承矛盾重重,至武成時雖以壯年内禪、改宗廟與配饗、壓抑宗王、信用恩倖等舉措成功實現了皇位由父傳子並加以相當的鞏固,但因高氏弟及之事實與觀念由來已久,在天統四年(568)十二月武成駕崩以後,年僅十二歲的後主高緯(生於天保七年,556)畢竟資歷、才能與政治經驗均尚淺,宗王的勢力和影響難以清除,北齊末年的皇位争奪仍然相當激烈。
後主親政以後,其權威不斷受到來自宗王的威脅。《北齊書》卷四〇《馮子琮傳》:
及世祖崩,僕射和士開先恒侍疾,秘喪三日不發。子琮問士開不發喪之意。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並秘喪不舉,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意欲普追集涼風堂,然後與公詳議,子琮素知士開忌(趙郡王)叡及領軍臨淮王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之權。
其時和士開所忌、對後主威脅最大者實爲趙郡王叡。叡,神武帝高歡弟高琛子,武成從弟。《北齊書》卷一三《趙郡王琛附子叡傳》:
(天統中)叡久典朝政,清真自守,譽望日隆,漸被疏忌……世祖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遥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内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巵酒!”言訖便出。
同書卷五〇《恩倖·和士開傳》:
趙郡王叡與婁定遠等謀出士開,引諸貴人共爲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宫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以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孤寡耶。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或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士開)進説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朝貴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及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於是詔出定遠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入而殺之。
趙郡王叡以武成從弟之親,聲望隆重,故被疏忌。史雖謂叡忠耿,但觀其武成崩後即與諸貴謀出後主最爲親信之和士開,又對太后“詞色愈厲”、“言詞咆勃,無所不至”,已可見跋扈之迹,又高氏本有弟及之傳統,和士開所謂“觀朝貴勢欲以陛下爲乾明”不無可能。乾明指廢帝,廢帝以子繼父而爲孝昭所奪。“帝及太后皆泣”,亦表明當時後主母子情形之危急。
武成崩後,對後主帝位造成威脅者,除趙郡王叡之外,尚有博陵王濟。《北史》卷五一《齊宗室諸王上·博陵王濟傳》:
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
《通鑑》卷一七〇陳宣帝太建元年(北齊天統五年)正月條:
齊博陵文簡王濟,世祖之母弟也,爲定州刺史,語人曰:“次敍當至我矣。”齊主聞之,陰使人就州殺之。
濟爲武成母弟,其同母五兄除襄城王淯薨於天保二年外,其餘皆先後登帝位,故武成崩後濟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可見弟及之觀念在高氏兄弟間尤其婁后諸子間影響之深,而濟終以此見殺。又《北史》卷五一《齊宗室諸王上·任城王湝傳》:“神武第十子也……及安德王稱尊號于晉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湝:‘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群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湝,竟不達。”任城王湝雖未必有覬覦之意,而神武諸子兄終弟及之觀念直至齊亡仍有相當影響。
後主因弟及傳統之威脅而殺其叔父博陵王濟、從叔趙郡王叡,於諸弟亦深加防範。後主母弟琅邪王儼,“(與和士開、駱提婆不平)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宫,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見太后”,後矯詔殺和士開並欲奪帝位,爲後主所殺。*《北史》卷五二《齊宗室諸王下·琅邪王儼傳》。《北史》卷五二《齊宗室諸王下·齊安王廓等十王傳》:“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帝王之弟,竟同於庶民。
除去諸父諸弟以外,當時對後主威脅最大者則當屬文襄諸子(文襄六子: 河南王孝瑜、廣寧王孝珩、河間王孝琬、蘭陵王長恭、安德王延宗、漁陽王紹信)。文襄皇帝高澄爲高歡嫡長子,文宣、孝昭、武成之長兄,隨高歡創業並以世子身份在高歡薨後繼承王位,雖生前未登帝位,但文宣受魏禪後即追謚爲世宗文襄皇帝,其功勛與地位不容置疑。文宣天保初,不欲文襄神主入於宗廟而遭到“衆議不同”之反對,雖然不明確究竟是哪些人反對,但可以想見忠於或傾向於文襄之舊臣、皇族成員等不可小視;孝昭定功臣配饗時,配饗文襄者爲七人,配饗文宣者爲三人,亦可佐證。可以説,文襄一系在高氏皇族内部有其特殊地位,因之文襄諸子也頗爲自負和不滿。《北史》卷五二《齊宗室諸王下·河間王孝琬傳》:
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撾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唤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静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唤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
按,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文襄敬皇后元氏所生,若當年文襄不暴崩,孝琬本應繼立,故其“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自謂“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招致其叔武成大怒而殺之。文襄諸子在文襄、文宣、孝昭、武成諸帝子中年紀亦最長,同書同卷《齊宗室諸王下·河間王孝琬傳》:
初,孝瑜養於神武宫中,與武成同年相愛。
按,武成生於東魏天平四年(537),而文襄長子、武成之侄孝瑜與之同年。其餘文襄五王雖史未載其年紀,但文襄崩於東魏武定七年(549),其諸子出生最晚亦當在武定七年之前,其餘諸帝子最長者屬文宣長子濟南王殷,生於武定三年(545),大概與文襄幼子漁陽王紹信年紀相近。*河南王孝瑜、河間王孝琬,天保元年七月封,在高歡孫輩中封王最早;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天保六年三月封;蘭陵王長恭,乾明元年三月封;漁陽王紹信,封年不詳。文襄諸子,封王較早,自然與其較年長有關。又文襄諸子,多有才幹令譽。《北史》卷五一《齊宗室諸王上·襄城王淯傳》:
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
所舉齊氏諸王爲時所稱之三王,廣寧、蘭陵二王皆文襄子;又文襄第四子蘭陵王長恭、第五子安德王延宗,皆以武勇聞。*《北史》卷五二《齊宗室諸王傳下》史臣“論曰”謂:“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殲覆有征,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
北齊重大政治事變中,也往往有文襄諸子身影出現。如《北史》卷五二《齊宗室諸王下·河南王孝瑜傳》:
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
同書卷五一《齊宗室諸王上·上洛王思宗附子元海傳》:
(孝昭)恒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厙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南王孝瑜僞獵,謀於野,暗乃歸。
同書卷五二《齊宗室諸王下·琅邪王儼傳》:
(儼殺和士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强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彦,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
無論地位、年紀還是才能,文襄諸子在皇族尤其是文襄、文宣、孝昭、武成諸帝子中均較突出,又屢次涉入政治异動中,故其受到更多的猜忌與排擠自屬難免。武成、後主時,河南王孝瑜、河間王孝琬、蘭陵王長恭相繼被殺,且前二者史均明言與恩倖之徒有關。《北史》卷五二《齊宗室諸王下·河南王孝瑜傳》:
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而親。由是叡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尒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杯。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彦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絶。
武成殺孝琬已見前文所引,其間亦有和士開、祖珽譖毁之故,同書卷五二《齊宗室諸王下·河間王孝琬傳》:
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脱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帝頗惑之。
同書卷五二《齊宗室諸王下·蘭陵王長恭傳》:
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遂飲藥而薨。
文襄六王,至後主時河南、河間、蘭陵三王已爲後主父子所殺,其餘廣寧、安德二王,亦深被猜疑。*《北史》卷五二《齊宗室諸王下·廣寧王孝珩傳》:“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道兵趣潼關,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宫人寶物賞將士,帝不能用……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同書卷八《齊本紀下·後主紀》:“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宫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悦。”同書卷五二《齊宗室諸王下·安德王延宗傳》:“河間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爲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卧延宗於地,馬鞭撾之二百,幾死。”此外,後主似乎還有籠絡文宣一系以對抗文襄一系之意圖與舉動。《北史》卷八《齊本紀下·後主紀》:
(武平元年十月)己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謚號爲“顯祖文宣皇帝”。
按,武成改文宣廟號和謚號,有壓抑文宣一系、鞏固武成一系父子相繼之意圖,*參前揭拙撰《北齊功臣配饗小考》、《祖宗與正統: 北齊宗廟變遷與帝位傳承》。而此時後主復改文宣廟謚,似和其父舉措反道而行。又《北齊書》卷四二《陽休之傳》:
又魏收監史之日,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平中,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後,便諷動内外,發詔從其議。
後主武平中,將齊之起元由之前高祖高歡時改爲顯祖高洋時,亦與其父相反。*《文館詞林》卷六六八《北齊武成帝即位改元大赦詔》:“大齊禦籙冥圖,締構王業,人神協契,年將三紀。”《日藏弘文本文館詞林校證》,第345頁。文宣天保元年(550)受魏禪,武成大寧元年(561)即帝位,其謂大齊王業“年將三紀”,自然是以高歡崛起爲齊元。筆者認爲,後主之改高洋廟謚與改天保爲齊元,並不能謂爲文宣一系在此時興起(事實上,文宣諸子並無過人才幹,功業亦乏善可陳,地位較之文襄一系遠不如之),而是由於後主有聯合文宣一系對抗文襄一系之企圖。*又,文宣長子廢帝高殷被廢時,其心腹大臣楊愔、燕子獻、宋欽道、鄭頤等俱被戮,至天統五年同被追贈(見《北史》卷四一《楊播附楊愔傳》、《楊播附燕子獻傳》及《北齊書》卷三四《宋欽道傳》、《鄭頤傳》),當亦有安撫文宣一系及其支持者之意。
如前所論,文襄一系在皇族與大臣中不乏支持者,所以武成父子雖然深加防範屢有誅戮,仍有三王得以幸存;而在後主末年周師圍逼的情勢下,後主統治摇摇欲墜,文襄之子廣寧、安德二王乃成爲人心之所向,*《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八册收《齊故假黄鉞太師太尉公蘭陵忠武王碑》敍蘭陵之死時云:“兄弟交□,憂若魯喪。”(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5頁)碑文雖有闕字,但其用魯莊公薨後三子公子般、公子開、公子申争立而致魯國大亂之典故則顯然;碑又刻有安德王延宗經蘭陵墓之五言詩一首,内云“獨有魚山樹,鬱鬱向西傾”,所謂“魚山樹”,系用曹魏陳思王曹植墓在魚山之典故,亦影射兄弟相煎之意。按,此碑立於武平六年九月,尚在周師大舉進攻之前,此時蘭陵之碑與安德之詩已能够近乎公然指斥高氏之兄弟相争相煎,可見後主統治後期,文襄一系地位重又上升和公開不滿。頗有勢力圖謀擁廣寧王爲帝,並最終將安德王推上帝位。《北史》卷八《齊本紀下·後主紀》:
(武平七年十二月)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寧王孝珩爲右。
《北史》卷五二《齊宗室諸王下·廣寧王孝珩傳》:
承光即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内,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遊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别宅取便路入宫,事不果。
《北齊書》卷一九《尉摽附子相願傳》:
强幹有膽略。武平末,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并州,及到鄴,每立計將殺高阿那肱,廢後主,立廣寧王,事竟不果。及廣寧被出,相願拔佩刀斫柱而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
《北史》卷五二《齊宗室諸王下·安德王延宗傳》:
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雀鼠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并將帥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與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蕭牆,盜起疆埸。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祗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沭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
按,謀立廣寧王主謀之一尉相願曾爲廣寧王兄蘭陵王親信屬下,另一主謀莫多婁敬顯後又成爲擁立安德王之功臣,可見擁護文襄一系之勢力實具有相當的連續性。而觀後主“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之言及其左右(應即恩倖之徒)附和“理然”,高氏皇族内部矛盾、宗王與作爲皇帝爪牙之恩倖間矛盾不可調和豁然可見,北齊之亡自難避免。局勢發展亦確如後主所願,安德王在并州雖登帝位,旋爲北周破滅,北齊根本與主力隨之傾覆,高氏三世數十年霸業就此成空。
三、 結 論
日本學者尾形勇謂:“(中國)古代帝國基礎的秩序構造,歸納起來就是: 以受‘家人之禮’這一家族秩序制約的‘私’場域的‘家的世界’爲基礎,在其上部矗立着被‘君臣之禮’秩序化的‘公’場域的‘君臣’世界。”*前揭尾形勇《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第251頁。公與私、國與家、君與臣之關係在傳統儒家倫理規範之下達到相對平衡與穩定的狀態,可説是古代中國皇權政治維持良性發展的基本要素。在北朝後期民族關係緊張、複雜的背景下,北齊高氏王朝在文化上的矛盾即胡化與漢化間之艱難取捨與曲折反復,決定了皇權政治演進中的連綿衝突和皇權在衝突中趨於衰弱的路向,並集中反映在皇帝及其家族圍繞皇位傳承與争奪而展開的殘酷鬥争中;無論北齊的宗廟變遷、宗王政治盛衰還是恩倖政治的興起,都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彼此勾連、共同呈現了高齊皇族與皇帝在家國之間的困境與衝突,亦爲我們理解北齊之衰亡提供了重要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