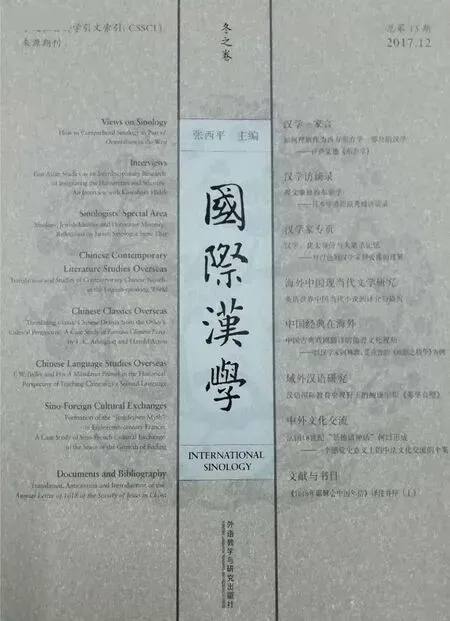东方与西方的相遇:《圣经》中译本中的跨文化议题
□
如何将《圣经》翻译为中国读者易于接受和理解的圣典,是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中最令人瞩目的议题之一。在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后,中国历史表现出对于引入另一种外来宗教的浓厚兴趣,同时,这种现象亦为洞察东西文化交流及其语言体系提供了一个出色的典范。
众所周知,《圣经》译本提供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翻译个案,因为其文本所体现的神圣性在翻译史上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往往激励着《圣经》译者们无私奉献,尽心尽责。①James Barr, “The Typology of Literalism in Ancient Biblical Translations,” Mitteilungen des Septuaginta Unternehmens, 15,Goe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9,明确提及早期《圣经》翻译忠实于原文的问题。宗教文本的神圣性必然增加翻译的难度。当然,从一种文化体系向另一种文化体系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困难并不限于《圣经》这样的圣典翻译中,这种现象也存在于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信息传递过程中。从理论上而言,译入语(receptor language)在传递译出语(original language)信息时应是畅通无阻,但是译本却往往揭示了翻译中所采取的各种策略,如使用一些意想不到的传达方式。于是问题随之而出: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翻译模式?造成文本漏译的诸种原因何在?为何译者选择通过增加文本中并不存在的信息使之得以扩充?选择这些表达方式的理由何在?
通过把译本同原文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分辨出三种主要现象,它们显示出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诸种困难:
1.替代 (Alteration):译文未使用与原文平行对应的语词,而是选择用另一个术语替代。
2.补充(Supplementation):译文增添了原文中并未出现的某些内容。
3.省略(Omission):译文遗失了原文的某些内容。
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列出早期《圣经》中译本中的例子,阐明这三种翻译策略,旨在考察译者采取某种翻译策略的根本原因。文中涉及四个主要的早期《圣经》(新教)汉译本: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和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于1823年出版的第一个开拓性《圣经》译本①罗伯特·马礼逊、威廉·米怜译:《神天圣书》,香港:英华书院,1823年。;1854年的委办译本(Delegates' Version)②“委办译本”指发表于1852年的《新约全书》和1854年的《旧约全书》。;1874年的施约瑟(Samuel I.J.Schereschewsky,1831—1906)译本③施约瑟(又名Shi Joseph),美籍犹太基督徒,1859年来华,后成为美国圣公会驻华第三任主教。1874年12月,在美国上海圣公会的资助下,他的《北京官话旧约》译本出版,这是第一个白话《旧约》中译本。该译本和1872年出版的官话《新约》译本合并为《北京官话旧新约全书》,于1878年出版;1899年又出版了施约瑟的《北京官话旧约》中译本修订版。施约瑟翻译的《北京官话新旧约全书》比马礼逊的《神天圣书》和“委办译本”等《圣经》中译本更广为流传,通行达40多年,直至1919年和合本《圣经》才取而代之。—译者注;闻名遐迩的1919年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本文还援引了一些当代希伯来文翻译中的中译例句,以此表明《圣经》中译本所采纳的翻译策略往往取决于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思考(cultural considerations),它不仅存在于《圣经》翻译中,也存在于其他任何文本的翻译过程中。
一、替代:译文未使用与原文平行对应的词,而是选择另一个术语代替它
在两位《圣经》人物拉班(Laban)和雅各(Jacob)的对话中,拉班询问雅各:“Ha-khi ahi ata va-avadetani hinam?”“Because thou art my brother,shouldest thou therefore serve me for nought?”( 因为你是我弟弟,你就应该白白服侍我么?—《创世纪29:15》)④此处英译使用了英王钦定本《圣经》(King James Authorized Version);括号内的中译文则为译者翻译。
不同的中译文显示,对话中出现的希伯来词“ahi”(我的兄弟)成为翻译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只有马礼逊译本中的“因尔为我弟则应无报而事我乎”从字面上较忠实地保留了原文意思,根据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它使用了“弟”(young brother)来翻译“ahi”。然而,有人认为,由于中国的亲属称谓中没有一个中性词对应“brother”,因此翻译时有必要弄明白究竟是“哥哥”还是“弟弟”,其他中译本则表明此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除了希望将“my brother”翻译为“我弟”(my younger brother)的马礼逊译本,其他中译本对此类不确定的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委办译本在处理词语“wo sheng”(我甥,my nephew)时使用了汉字甥,即“外甥,即我姐妹的儿子”。它是这样翻译的:“尔虽我甥岂可使尔徒劳乎?”(即:虽然你是我的外甥,我怎么能让你白白劳动呢?)
施约瑟译本使用了一个集合概念“我至亲”,从而将“my brother”解释为“my closest of kin”:“你虽是我至亲、岂可白白地服事我?”(你虽然是我的至亲,怎能白白地服侍我呢?),而和合本则使用了“骨肉”(flesh and bone)这个词语,并加入了一个表示“兄弟”的插入语进行说明:“你虽是我的骨肉[原文作弟兄],岂可白白地服事我?”(虽然你是我的骨肉[原文作弟兄],怎能白白服侍我?)
这些各自不同的解决方法表明每一种翻译都在找寻不同层面上的精确性和忠实度:马礼逊译本寻求字面上的忠实性,将“my brother”译为“我弟”(my younger brother),委办译本则对拉班和雅各之间的某种亲属关系进行了精确定义。思高译本(Studium Biblicum Version,1968)、吕振中译本(1970)和《圣经》新译本(1992)等天主教《圣经》中译本,全都遵循委办译本,使用了“外甥”(sister’s son, nephew)一词。这种寻求两个《圣经》人物之间现实关系的精确翻译法完全符合要求“正名”(rectification of names)的儒家原则。因此,这里的忠实度并不是遵照原文本的字面措辞,而是依据事实,把拉班与雅各之间的亲属关系准确地传达给中国读者。
而施约瑟译本与和合本则以各自的方式寻求另一种忠实性:忠于《圣经》文本后面的真实意旨,而非家族亲缘关系。在将“ahi”(我兄弟,my brother)译为“我至亲”(my closest of skin)时,施约瑟找到了一个能精确传达希伯来原文内涵的对等词。同样,和合本使用了“骨肉”(bone and flesh,kindred)这一表述,企图达成一种恰到好处的语义对等。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同样能帮助我们解释译本的内容替代或词汇替代现象,这一例子出自施约瑟对“u-phaneika holekhim ba-kerav”一句的翻译,其字面意为“且你的脸将走入战争”(and your face [will] walk into battle, 《撒母耳书217:11》)。希伯来语原句由一个转喻构成,句中的身体部位“脸”喻指另一个人,即大卫王之子“押沙龙”(Absalom)。中译本并没有像上文一样从字面翻译这一转喻表述(“你的脸”),而似乎与英文钦定版《圣经》的表述一致:“and that thou go to battle in thine own person”,选择使用了与“in person”语义对等的表述方式,将其翻译为“亲”或“亲自”(in person)。与之相对应,和合本进行了如下翻译:“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you yourself will lead them to war)。然而,施约瑟译本则使用名词“王”(the king)代替了第二人称代词“你”:“王亲自率领他们出战”(the King in person will lead them to go into battle)。押沙龙的称呼从“你”到“王”的转变,似乎是基于文化上的考量,因为这一事件中的讲述人是阿希托费耳(Ahitophel,他原先是大卫王的参谋,后在押沙龙叛乱时离开了大卫王,转而支持押沙龙的事业)。施约瑟根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在此处使用的译语巧妙地传达出押沙龙即将做王的盼望。因此,尽管原文并没有出现“王”这个字眼,其他中译本并未尝试使用这种翻译策略,施约瑟却采取了以读者为视角的翻译方式,选择以“王”来称呼篡权者押沙龙。这种替代是译者有意为之,其宗旨在于增强文本的可信度。
二、补充:译本添加了并未出现在原文中的内容要素
在一些例子中,译本出现了并不存在于原文的某些“添加”(additions)。通过考察对希伯来语独特的复合词“zolel ve-sove”(一个贪食好酒的人,《申命记21:20》)的翻译,或许可以说明这种现象。①这两个词语在希伯来《圣经》中再次出现时次序颠倒,即“sove ve-zolel”(好酒贪食,见《箴言23:21》)。《圣经》中的这一部分涉及一个不孝子的故事,描述了父母如何抱怨他们儿子的逆行:“bnenu ze sorer u-more einenu shome’a be-kolenu zolel ve-sove”(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当我们聚焦这句话的最后两个词“zolel ve-sove”如何翻译为中文时,可以看出大多数中译本尽可能精确地传达它们的意义。马礼逊坚持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文,将这个复合词翻译为“饕者醉者”(贪吃且醉酒的人),整句话译为:“我等之子,为颂叛悖逆,不肯顺我等之声,并为饕者醉者也”(我们的儿子是一个那么叛逆执拗的异议者,不愿意听从我们的声音,而且(他)是一个贪食者和醉酒者)。委办译本使用了“沉湎荡检”(沉溺于放荡中)这一表述,其译文如下:“此子悖逆,不听我言,沉湎荡检”(这个儿子叛逆,不听我们的话,沉迷于放荡中)。而和合本则翻译为:“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我们的这个儿子执拗而不顺从,不遵从我们的话语,是一个对食物和酒贪婪的人)。
但在施约瑟译本中,译文为:“我们这儿子违背忤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浪费钱财,贪食好饮”(我们这个儿子悖逆,不听我们的话,浪费钱财,贪食好饮)。我们发现在对这个问题青年的描述中,译者添加了一个补充性的短语:“浪费钱财”(squanders money)。原文中是否提及“钱财”方面呢?我们在《圣经》原文中根本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内容,可是为何施约瑟在此处要添加这样一个短语呢?
答案看来与施约瑟不遗余力地想要提供一个以读者为导向的中译本有关。施约瑟也许很担心中国读者无法理解这个事件中所讲述的不孝子—尽管他不顺从父母,贪食好饮—最终得到的是死亡判决(“所有城里的人用石头砸他,于是他死了”,《申命记》21:21)。为了强调这个不孝子的恶劣行径,并且证明《旧约》对他的惩罚正当合法,施约瑟添加了一个短语,指明这是一个“浪费钱财”的人。此译句成为一个溢出原文的解释性注释,为译本添加了新的内容要素。
三、省略:对出现在原文中的某些内容的删节
在从事有关早期《圣经》中译本如何翻译父子关系的研究时,①Lihi Yariv-Laor, “Facets of Father-Son Relationship in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Raoul David Findeisen(冯铁),Gad C.Isay, Amira Katz-Goehr, Yuri Pines, Lihi Yariv-Laor, At Home in Many Worlds.Reading,Writing and Translating from Chinese and Jewish Culture: Essays in Honour of Irene Eber.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9.我无意中发现某些中译本并未传达出原文的部分内容。例如:“ervat abhikha veervat imekha lo tegale”(你没有发现你父亲的裸体,或者你母亲的裸体,《利未记18:7》)。我以下引用的四个中译本中,只有马礼逊译本(它比较趋向于字面直译)翻译出原文中的每个成分,而委办译本、施约瑟译本和和合本这三个版本都省略了原文中关于“你父亲的裸体”的内容。以下是马礼逊的字面直译和其余三个中译本的翻译对照:
马礼逊译本:“尔父之裸体、尔母之裸体、尔不可露之”(你父亲的裸体和你母亲的裸体,你不允许暴露它)。
委办译本:“勿烝尔母”(不可与你母亲乱伦)。
施约瑟译本:“不可与母苟合”(你不可与你母亲通奸)。
和合本:“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你不可暴露你母亲的下体)。
后三个中译本并未提及“父亲的裸体”,而仅仅提及“母亲的裸体”,在提及“母亲的裸体”时,和合本使用了隐喻“暴露身体的下端”,而委办译本和施约瑟译本都将《圣经》的隐喻性表述“显露母亲的裸体”,按其内在含义翻译为“乱伦”或“通奸”。
如何解释翻译中故意省略了“父亲的裸体”这一内容呢?答案在于儒家的伦理规范,根据这些伦理纲常,千百年来中国人将孝道誉为至上的美德。
这三个中译本千方百计地要使犹太—基督教《圣经》文本适应19世纪的中国文人们所推崇的儒家伦理系统,显而易见,它们当然不愿翻译出任何可能暗示使父亲地位贬低或蒙耻的细节。此外,儒家文化认为孝道涉及儿子对其父亲及父辈先祖的态度,②Alan Cole, Mothers and Sons in Chinese Buddh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因此提及“母亲的裸体”,可能在较少程度上冒犯阅读《圣经》译本的中国文人的情感。和以上提到的三个“删节”某些内容的《圣经》中译本不同,其他中译本(马礼逊译本和其他20世纪出版的现代中译本③如1968年的思高译本,1970年的吕振中译本和1992年的《圣经》新译本。)并不刻意要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也未省略原文中的这一句,而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忠实地翻译了“父亲的裸体”这个短语。
说到“省略”,以下这个例子来自翻译为汉语的现代以色列儿童读物,体现了与以上例子极为类似的态度。在约拉姆·考纽克(Yoram Kanyuk)写的书中,有个孩子如此描述他的父亲:“我的父亲,当他聪明的时候,他会非常聪明,他是邪恶的;而我的母亲,当她温柔的时候,她并不那么聪明,说话像个小姑娘。”(my father, when he is smart, and he can be very smart, is evil, and my mother, when she is soft, is not smart and talks like a little girl.)④Yoram Kanyuk, Job, the Pebble and the Elephant.Tel-Aviv: Hakibbutz Hameuchad Publishing House, Yedioth Ahronoth Books& Chemed Books, 1993.这句话的中译者删去了“他是邪恶的”这一有关父亲的措辞,将句子译作:“我爸爸他聪明时会很聪明,可是妈妈温柔时一点儿也不聪明,说起话来像个小姑娘。”(when my father is smart he might be very smart, but my mother —when she is soft, she is not smart at all, and talks like a little girl.)。现代中译者似乎希望吸引年轻的中国读者,因而顾虑到孩子父母的感觉,这与那些早期《圣经》译者的担心十分相似。
结论
通过对比研究以上几个《圣经》中译本,我们能看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替代、添加或省略原文中的某些内容等技巧。这类翻译现象反映了译者期待《圣经》译本能够更适应、亲近中国读者的强烈愿望,而且通过这种翻译策略,东西两种迥异的文化之间能够获得更好的交流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