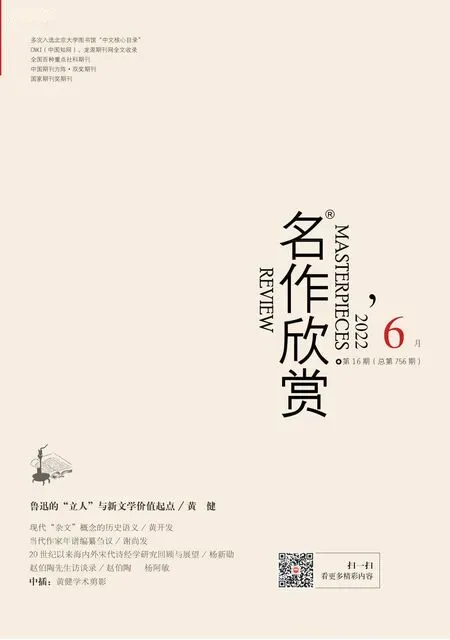《再别康桥》的优柔和严肃
北京 李林荣
《再别康桥》的优柔和严肃
北京 李林荣
《再别康桥》是徐志摩诗歌中的名篇,长期以来它被解读成明快、优美甚至满含甜蜜和欢欣的清浅之作。事实上这只是它的一层表象。细考全诗意象细节与整体意境的关联脉络,并参证徐志摩创作当时的生活处境,可以发现《再别康桥》具有表里冲突、明暗相间的张力结构,对迷茫、优柔、凝重的“过程之美”的咏叹,才是它真正的底色。
《再别康桥》 徐志摩 细读分析 过程美学
一
徐志摩生于1897年,逝于1931年,活了不足三十五周岁,生命非常短暂,而且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过渡在古代的黄昏和现代的黎明之间。古代生活的典雅精致,在他面前,已经破碎风化;现代文明的丰富多彩,在他面前,还没有充分展开。从这个意义上看,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既是一片废墟,又是一片开垦地。
在这个大背景、大环境中,他不算个一等一的强者,他没有大踏步地超越,更没有强有力地支配和影响自己的生活际遇,但也没有像文化上的浪子和精神里的孤儿那样,眼前无路,脚底无根,迤逦歪斜,被时代和社会的潮流所裹挟、淹没。他本身就是自己生活背景和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但他更像浮雕那样,在某些角度、某些局部和某些侧面上,从自己的背景和环境凸显了出来,表现了一种既存在于其中而又不完全属于其中的奇异质地和嶙峋骨感。
从徐志摩有据可查的生平材料看,他人生道路不长,爱情里程更短,但迎来送往的女友络绎不绝,有时候还好几位一起穿梭左右,应接不暇,的确很有资格被人们视作情圣。不过他的爱情生活并不美满、成功,相反,倒是贯穿着一系列的失落、迷茫。如果谁要到徐志摩这里求取恋爱制胜和婚姻幸福的葵花宝典,那他肯定会失望。因为徐志摩这里没有爱情、婚姻的成功学,只有爱情失败学和婚姻受难学。如果换个角度,想看看不一定成功和圆满,或者不以最终一个环节的成败计得失的那种爱情和婚姻,具体是怎样的况味和景致,尤其是一个人在始料未及遭遇到这种预卜不到前景的爱情时,如何用力承受、用心担当,那么,到徐志摩这里来,可找对了地方。
这不仅是因为徐志摩在这方面经历得多,更因为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太会掩饰或遮盖自己所亲历的各种难堪和幽暗,而且还经常好像是不由自主又像是有点着意而为,会把自己的难堪和幽暗翻腾出来,渲染、放大、铺排,写进自己的作品。这类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数诗,诗中最有名的,就是《再别康桥》。
二
1928年8月,三十二岁的徐志摩来到英国,重游六年前自己求学、生活过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这年冬天,他结束自己这趟耗时半年之久,畅游日美英,最后辗转印度的漫长游历,乘船回国。11月6日,船到中国海上,他回想三个月前的剑桥之行,写下了他一生作品中最有名的一首诗——《再别康桥》。一个月后,这首诗发表在他和一帮朋友共同编创的杂志《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十号上,自此往后,广为传诵,至今不绝。
现在很多读者心目中,《再别康桥》这首诗,已经不仅仅是徐志摩的一篇名作,而且几乎成了徐志摩整个人的代号和象征。每读这首诗,我们眼前和心里,就很容易闪现出一个深情而又温和、优雅而又略带些落寞的身影或面容。我们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都乐于把这当成情感和精神上的一幅美景或者一道甜品来欣赏、品味。
但实际上,不论细察作品本身,还是追究创作背景,都可以发现,《再别康桥》的一派优美、敞亮,是遍布着深深的褶皱的,褶皱里满含的,都是忧愁郁闷和艰难苦恨。
我们一般注意不到这一层,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时空隔阂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审美代沟的问题。在文学和生活现实如何匹配、如何对应,或者说拿什么样的文学形式来表现什么样的生活内容的做法上,《再别康桥》问世的那个时代,和我们当前,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文学上的,更是精神风度和人情世态上的。而且这种差异,本身的情况也是很丰富、复杂的,在徐志摩和他的《再别康桥》这里,体现的只是这种差异的一个小小的局部,在其他人、其他作品那里,还有和徐志摩、和《再别康桥》都不尽一致的表现。
时下传说的“民国范儿”如果真的存在过的话,那么,徐志摩保留在《再别康桥》这里的这种给幽暗以明丽、赋痛苦以优雅的做派,或许就该是其中特别的一例。
三
就作品本身看,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显示出《再别康桥》明丽背后的幽暗、优雅背后的痛苦:1.意象的张力,2.韵致的纤弱,3.情思的曲折。
诗是用意象说话的。意象是有特定审美蕴含的形象。意象是为了传达强烈、丰富的意义而被人自觉创造出来的,一旦造成,再提起的时候,就有以一当十、以简驭繁的效果,像三明治、肉夹馍、夹心饼干一样,一口下去众味纷呈,比一样一样分吃单嚼,感觉要醇厚得多。一个特别好的意象存在久了、用得多了,冲击力和表现力必然衰减,渐渐沦为陈词滥调。用玫瑰花来表示爱情,当初肯定也曾跟密电码似的神奇过、新颖过一阵,可滥用之后,就退化成一个扁平透明的大白话字眼,跟直接提“爱情”这个词没有两样。
不论古今中外哪家哪派,凡属好的诗和好的诗人,都给自己所在的那个时代和社会铸造和奉献过精彩、传神、新颖的意象。等而下之的,也得对一些旧的意象多少做出增删、修整。连这都做不到,可能就算不上是诗。之所以诗在各国各时代都被推崇到艺术之塔的尖端,根本上就是因为诗有这么一种文体禀性,它就是为了证明语言在形式和表现上的更新潜力和更新可能而存在的。
读诗首先就是读意象。《再别康桥》的意象不止一个,全诗七节,基本每一节突出一个或一组意象,但这些意象清一色都属于张力型而不是松弛型的,都是把在日常生活经验里打着架、犯着冲的意跟象,硬绑在一起,形成一种类似一张弓被拉到十分满,自己跟自己较着很大劲的紧绷状态。以下从头到尾,边数边看: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再别康桥》第一节)
这里的意象,是一个人——“我”相对于康桥来而复去的姿态,而且一来一走的姿态都重合,都是“轻轻的”。“轻轻的”姿态,也可以贯通到心态,来时“轻轻”,是因为悬着心,恐怕所寻不遇,见不着想见的。走时也“轻轻”,是因为来一趟什么也没得到,空空如也,没比来的时候增添什么,所以同样是“轻轻”。“招手”本来是手上下摇动,自古及今都是唤人趋近的意思,这里却反其意而用,拿来“作别”,而且诗题明明显示,“别”的对象是康桥,来这趟寻访的对象当然也是康桥,可这里的“招手”,却又舍康桥而不顾,直向“西天的云彩”。合起来看,这个来而复去的“我”,显然在纠结中,他的姿态和心态都映衬出一时莫名的巨大失落。
据有些传记作者考证,志摩这诗里写的这次康桥之行,是偶然得空,临时即兴安排,所以很可能碰上了乘兴而来却访友不遇的尴尬:老熟人没见着,新朋友也没结识,白溜达一趟。难怪只好俯看流水深潭,远望树草斜阳,临走也只能把辞行的表情和手势送给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再别康桥》第二节)
这节出现了复合意象,一是河畔的“金柳”,二是夕照下的“新娘”,三是波光里的“艳影”,这“艳影”既是“金柳”的水中投影,同时也是夕照下的“新娘”的水中投影。三者复合为一,从字面上看,靠的是修辞和物象上的关联,内里却是诗人逐渐清晰明确起来的一股情感和思绪在起推动和黏合作用。三者之中,实景只居其一,就是河畔的柳树,因为余晖正烈,所以披了金色,俨然“金柳”,其他二者,“艳影”和“新娘”,都是作者联想到的心理虚像。
依常情常理,“金柳”这个形象,其观感和意味都该是偏于鲜亮明快的。但诗人给它的比喻却是“夕阳中的新娘”。“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夕阳,欢欣、喜悦、甜蜜、兴奋的新娘,被联想为一体,这正显露出一种从亮中见暗、从喜中见忧的幽暗心结。紧接着的“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幽暗心结,并且把它直接归结给了“我”。波光里的艳影之“艳”,既然来自“我”将“金柳”当成“新娘”的联想,那这“艳影”的荡漾,其实也就是“我”自己的意识在起伏波动,自己也有点拿不准自己似的。
软泥上(《新月》初刊时“上”作“生”,似更恰切)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再别康桥》第三节)
这里的“软泥”“青荇”“油油的”“招摇”“柔波”“水草”,或名或状或动,都集中强化同样一点——柔软,一种从外在的形状、姿态,到内在的感受和品质,都是贯通一气的柔软。而“我”,对这种柔软,不但不嫌弃,反而恨不能化身其间,跟着一块儿去柔软——“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水草”缠绵无骨,不够阳刚,但它跟“波光里的艳影”靠得最近。“甘心做一条水草”,就是宁可柔软到底,也要豁出去争取跟“波光里的艳影”耳鬓厮磨,依偎在一起。可“波光里的艳影”,本是水中月、镜中花一路的虚影,并非实物,纵然变得成绵绵“水草”,又哪能勾得住这“艳影”的丝毫?
以上这两节,差不多是在浓缩呈现徐志摩从1920年初到康桥至1928年重访和再别康桥这前后八九年间的真实情感体验。“艳影”“新娘”的意象,叠合着他对往昔的情人林徽因的回想和对暂别的妻子陆小曼的牵念。这回想和牵念,凄美而幽怨,细腻而纠结。
四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再别康桥》第四节)
诗到第四节,发生了转折,取景视野从“河”转向了“潭”,意态也随之从“有我”变为“无我”。虹映潭中,浮藻乱之,这一景象,与“天上虹”降临地上之后遭遇梦碎这一意蕴,结合了起来。很明显,这是在形容隐退景外的“我”的总体心境。什么是“彩虹似的梦”?那句从《红楼梦》中晴雯判词里附会出来的俗话,“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大概可作为最简洁的说明。在《再别康桥》这里,彩虹映潭本无所谓对错,遭揉碎、被沉淀,皆因不巧落在遍布浮藻之处,换句话说,梦之所出,在于天然,实在无可厚非,只是现实太残酷,才使梦碎。而“潭”较之“河”,即静水之于流水,梦碎于静水,也沉入静水,更见这梦的执着难舍。
于是,第五节展现“寻梦”意象: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再别康桥》第五节)
“寻梦”的行为是撑篙行船,但不是顺流而下,却是逆流而上,“漫溯”,“漫”为纵意随性,与“寻”无定向的常理相符,“溯”为逆流而上,却暗示“寻”的方向只在“逝者如斯”的流水上游,也即旧时光中。整个看来,这样的“寻梦”,实际也只能是对过往旧事的一番无谓的缅怀和追思。最后所得的,无非一些恰似星辉般缥缈、零散、寥落的记忆碎片。“放歌”,即为忆旧引起的重重慨叹,喻指写诗本身。第五节这段描述,实际上是在定格写诗当时的心思:想到的很多,也很想把所想到的这些,都说清道明、抒写尽兴。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再别康桥》第六节)
第六节与前一节同样,是诗人当时创作心思的一段写照,不过完全收敛和按捺了上一节里展开的那种想跟往事干杯的兴头,调换出了一种欲说还休、干脆不说的婉约含蓄的情调。但言虽尽,意难平,何况之前毕竟已经“说”了不少,所以,“悄悄是别离的笙箫”中,“悄悄”在外,“笙箫”在内,歌声是没了,心声可正轰响。至于“夏虫”的沉默,一为渲染内心“笙箫”的音效之强,一也摹拟出了离别康桥时渐行渐远听得河畔虫鸣声慢慢低落终至于无的实感。今晚沉默的康桥,就是乍离别之际感觉中怅然若失的那座康桥,随着再次离别,它顿时又从可以亲闻其声、近睹其物的清晰状态,重归于一片静默的记忆。循之生活常情,我们不难理解这种瞬间一别、物非人是的恍惚感和失落感。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第七节)
第七节是对第一节的回应和反复。“悄悄的”和“轻轻的”同有指言收敛、不事张扬的意思,而“悄悄的”更强调不声不响、无语凝咽的情状,“轻轻的”则偏重指动作上不着力,心情上不着意。以“轻轻的”开篇,暗中引领全诗,落下基调:抒怀喻事、感物起兴都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出于真实经验而止于审美尺度。以“悄悄的”收尾,则是对这一基调的复沓和响应。“挥一挥衣袖”,既是“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动作,更是把一片心事拂落在此的动作。末句中这片不带走的“云彩”,当然不是第一节中“我”招手作别的那片“西天的云彩”,因为“西天的云彩”本来也不为此地专有,跟“我”本也无关,带不走也无须带走,更何况,依着第五、六两节里所示的“星辉”和“今晚”,第七节诗境已入黑夜,不是仰看流云的时候。因而,这时所提到的跟“我”有关,并且容“我”选择带不带走的“云彩”,其实只能是从第四节中飘散出的那片彩虹和沉淀进潭水的彩虹似的梦。挥别它们,在漫天星辉的夜幕下退场,这落寞的身影,把全诗各节的意象收束为了屏气凝神、声息皆无的一个表达的终点。
五
通观全诗,意与象、词与义两层面之间的紧张持续存在,但这种紧张始终都约束在了意象内部,最后也随着整个诗境构造的完工,被及时地摒弃在了诗境内部。这使得整首诗没有在任何一个细节上流露出指向诗中的“我”和“我”的世界之外的强硬或尖锐姿态。
从某种强调“我”与“非我”、人与环境等对立二元此消彼长规律的斗争哲学和斗争美学的立场来看,《再别康桥》这种张力内敛的韵致,无疑是纤弱甚至消极的。它缺乏了些纵使明知电光石火也不惜做玉石俱焚之争的刚勇气概,少了些中流击水、拼出血路的壮美。但不可否认,它仍然是一种美,一种确有可能和确有价值的美。
对此,徐志摩本人充满缺憾的真实生活经历传布到今天仍能给人以美感这一事实,就正是一个鲜活印证。而展现在《再别康桥》整首诗中的那条徐志摩特色的情思脉络,则是一个缩聚在文字中的印证。全诗七节,依次凸显了七个主题、七种形态的情思:第一节,挥别西天云——苍凉失落;第二节,心头荡波影——黯然神伤;第三节,甘心做水草——缠绵依恋;第四节,潭中虹梦碎——执着迷幻;第五节,寻梦载星辉——追索挽回;第六节,别离无笙箫——再度失落;第七节,挥袖留浮云——搁置放弃。这七种情态环绕一圈,把为“波光里的艳影”所吸引、蛊惑的那个“彩虹似的梦”,紧紧合围,形成焦点。
从奔着这个焦点而来的向度和力度讲,这七种情态参差不一、错落有致。第一、二节由远及近、由弱渐强,第三、四节静态定向,第五节动态逼近,第六节折返后撤,第七节回归起点。其中,第五节既是向梦逼近的起点,同时也是寻梦无着的幻灭点。此前四节,是前奏,此后两节,是尾声。合起来看,这纯属一场无果而终、无功而返的徒劳。但这一场徒劳的过程里的每一个环节,却得到了同等细致而又各具神采的生动展示。这样的展示本身,正是《再别康桥》的哲学和美学的重心所在。冒用一个术语,《再别康桥》的哲学和美学不妨称作“过程哲学”和“过程美学”。
过程本身是一种美。过程中的美,必定是些碎裂的片断。它们不一定都连接着结果,甚至很可能根本和最终的结果沾不上边,但这毫不减损更不消抹它们的美。因为它们组成了一个切实存在的过程,仅此,已经足够成其为美。结果的有或无、好或坏,影响不到它们。终究,那是它们之外的另一回事。从这个侧面上看,耐心见证过程之美的《再别康桥》,它的优柔里,也满含着说不尽的严肃。
作 者:
李林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基地执行主任,北京老舍文学院客座教授。编 辑:
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