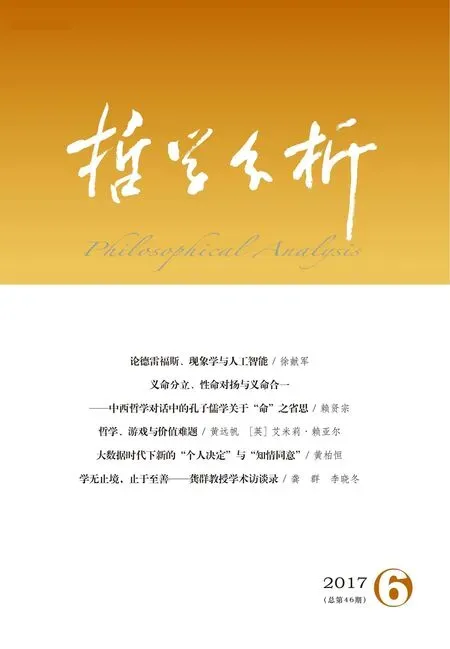行为现象学:德雷福斯的一份学术遗产?
姚大志
行为现象学:德雷福斯的一份学术遗产?
姚大志
生存论现象学通常将置身其中的活动视为一种基本的行为类型,但在某种意义上忽视了思想或理性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德雷福斯和罗丹—罗路的对话围绕受意识驱动的活动展开,所涉及的行为类型不同于置身其中的行为。通过重构德雷福斯和麦克道尔的论战可以发现,理性因素以某种方式上渗透进了置身其中的行为,而后者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亚行为类型。这些工作深化了有关人类具身行为与思想或理性之间关系的认识,拓展了行为现象学的论题域。
德雷福斯;生存论现象学;行为;具身性
生存论现象学家在20世纪对自我意识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在此过程中,人类日常行为现象也获得了有意义的讨论。除海德格尔和萨特之外,梅洛—庞蒂的工作同样值得人们关注,后者重视由运动意向性支配的日常活动现象,如日常身体运动、纯熟运用身体技能、使用称手工具的活动等。此类活动通常被生存论现象学视为人类知觉和行为活动的基本模式。
美国当代现象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L. Dreyfus,1929—2017)在很大程度上接受梅洛—庞蒂对人类日常知觉活动的阐释,也意识到人类行为现象的重要意义。进入21世纪,他与哲学界同行展开相关学术争论,也面向学生开设行为现象学的课程。与人类知觉活动有关的研究,虽然只是他在生命最后十多年关注的部分内容,但仍然有助于廓清行为现象学的论题域,并推动相关研究的进展。
一、生存论现象学行为观遗留的问题
胡塞尔主张,主体与世界中事物的关系必然已经以意向内容为中介。意向内容或者表象内容作为精神状态,使得意识能够指向被描述的某种东西。这种表象主义的立场也扩展到对人类行为现象的说明。在德雷福斯看来,胡塞尔赞同一个正常主体的身体运动必然由某种精神状态引起。“行为的经验具有意向内容,即恰当的身体运动是由执行运动的意向造成的。”①Hubert Dreyfus,“A Merleau-Pontyian Critique of Husserl’s and Searle’s Representationalist Accounts of Action”,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Vol. 100,2000,p.289.我们的行为似乎总是伴随着某种精神状态。该精神状态的意向内容总是与主体行为的目标相关,并可能涉及相关对象,从根本上引发了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表象主义行为观主张,日常活动中的非反思行为,也是由表象运动目标或过程的主体意识状态引发和控制的。相对来说,非反思的行为只是看起来更加流畅、更加迅速,似乎主体是在没有自我意识参与的情况下活动一样。
生存论现象学对人类日常行为的看法与上述认识不同。古尔维奇(Aron Curwitsch)关注现象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关联,曾对日常非反思的熟练活动给予出色描述。②Aron Gurwitsch,Human Encounters in the Social World,Pittsburgh: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79,p.67.他的洞见启发了梅洛—庞蒂。在后者看来,人们将周围环境知觉为世界提出的要求或邀请,对邀请的回应和其当下任务相关。具身主体知觉到行动机会,并通过行动做出回应,无需任何有关行为的表象作为中间环节。在知觉和行为之间,似乎没有留出让意向干预的空间。这种行为可被称为置身其中的行为(involved coping)。
德雷福斯承认,生存论现象学具有自身的问题。③See Hubert Dreyfus,“Overcoming the Myth of the Mental:How Philosophers Can Profit from the Phenomenology of Everyday Expertise”,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Vol. 79,Issue 2,2005,pp.47—65,and Hubert Dreyfus,“Response to McDowell,” Inquiry,2007,No. 4. pp.371—377.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宣称,人们应该在运动意向性的基础上理解表象意向性。但他的主张仅仅停留在声明阶段。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指出我们直接对邀请开放,从具有具体情境特征的事物的经验,转向具有可被把握的抽象特征的对象,但他没有从细节上展开论述。④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New York:Harper & Row,1962,pp.98—99.托德兹讨论了思想范畴和具身知觉经验之间的关系,但他仅关心奠基在运动意向性上的范畴是如何出现的。⑤Samuel Todes,Body and World,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2001,pp.269—277.德雷福斯指出:“我们的沉浸的(absorbed)、情境化的经验如何发生转变,以至于我们经验到脱离语境的、自足的、具有孤立特征的实体……他(生存论现象学家)还没有给出相关的说明。”⑥Hubert Dreyfus,“The Return of the Myth of the Mental”,Inquiry,2007,Vol. 50,No. 4,p.364.
经过几代学者的开拓,行为现象学遗留了一些尚需回答的问题。首先,从自我身体和运动意向性的维度看,受明确的意识指导的行为现象没有获得充分阐释。通常来说,传统理性主义的行为观坚持,人类主体的意识决定行为本身,同时伴随着意识对行为的反思。在生存论现象学的理论框架中,如何说明相关活动现象,是行为现象学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其次,在运动意向性支配的身体行为中,自我意识似乎彻底销声匿迹。是否果真如此?这是行为现象学需要回应的另一个问题。接下来,结合近年来德雷福斯与学界同行的交流和争论,本文尝试对上述两个问题逐一进行讨论。
二、明确的意识和具身行为
作为典型的具身活动,运动意向性支配的行为可被称为置身其中的行为。被知觉的环境对主体提出某种邀请,主体做出相应回应,无需在意识中明确表征所执行的内容或目标,就可引发该行为。这是最基本的具身行为类型。然而,置身其中的行为不能覆盖全部人类行为现象。一些案例明确表明,主体的意识可以引发行为。如果我们承认那些行为现象,同时拒斥笛卡尔主义的、表象主义的解释框架,那么生存论现象学就需要说明,思想或明确的意向如何在人类活动或行为中扮演角色。德雷福斯和罗丹—罗路(Komarine Romdenh-Romluc)在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各自提出了不同方案。借助他们的工作,我们将考察三种可能符合要求的情况。
(一) 在实际情境中转换任务
德雷福斯强调,根据对梅洛—庞蒂的理解,当熟练行为流陷于停止,意向便会引发行为①Hubert Dreyfus,“A Phenomenological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Ethical Expertise and Mastery”,in Moving Bodies,edited by Ejgil Jespersen,Vol. 4,No. 2,Oslo:The Norwegian School of Sport Sciences,2006,pp.300—301.。就此而言,明确的意向能够成为身体运动的直接原因。
他进一步指出,具身行为在正常情况下中断或被打破,应该存在某种干扰。而如何让沉浸在某个任务中的状况发生改变,海德格尔的分析能够为人们提供有益启示。譬如,木匠使用锤子时,完全沉浸在捶打东西的状态中。他有时可能感到锤子太重了。于是,锤子有可能会从上手之物转变成非上手的存在模式。但是为了应对该转变,木匠不需要抽身离开身处的情境,甚至放松他的沉浸状态。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木匠可以不停下来去反思,就径直拿起手边一把更轻的锤子。②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pp.102—103.
在某些情况下,意识明确出现在具身行为的转换中,并引发新的行为。德雷福斯指出,要是手边既没有更轻的锤子,也看不到胶锅,情况将会有所不同。由于视域中缺少对下一步行动发出的邀请,知觉不能充分产生行为,自我意识便出现了。③Hubert Dreyfus,“Reply to Romdenh-Romluc”,in Reading Merleau-Ponty:On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edited by Thomas Baldwin,New York:Routledge,2007,p.61.这时候,作为具身主体的我放弃一直持续的任务,也许开始观察手中之物。锤子不再处于模糊的视域边缘,转而受到我的关注。我也许可以有意识地决定做什么。反过来,这个决定作为行动的意向,又导致我接下来的行为。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意识做出决定,反过来又让我采取行动。
上述任务转换并不对自我身体的变化提出要求。无论新的任务是否涉及情境的转变,主体始终面对实际情境,并置身于其中。新的任务可能要求展示不同的运动技能,但主体的自我身体始终是同一个身体。
德雷福斯的方案遵循知觉现象学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启发。不过,随着梅洛—庞蒂框架下其他解决方案的出现,我们将会发现生存论现象学内部更多的理论生长点。比如,罗丹—罗路在与德雷福斯交流过程中,便对后者的分析不甚满意。她尝试在梅洛—庞蒂的理论框架下寻求其他解决方案。
(二) 在抽象态度中转换任务
罗丹—罗路似乎从神经学家那里获得了灵感,通过描述主体“处理可能事务”的方式,试图回答思想或表象如何在人类行为中起作用。
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对病人施耐德(Schneider)案例①大约一个世纪前,戈尔德斯坦和盖尔布对于病人施耐德的论述,对神经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持久影响。参见Marotta Behrmann,“Patient Schn:Has Goldstein and Gelb’s Case Withstood the Test of Time?”,Neuropsychologia,Vol.42,2004,p.633。进行了细致考察。施耐德是神经学家、精神病医生戈尔德斯坦(Kurt Goldstein)和心理学家盖尔布(Adhémar Gelb)的病人。借助该病例,两位科学家提出具体运动和抽象运动的划分。其中,具体运动是置身实际情境中的运动。比如,受运动意向性支配的日常行为,或者熟练运用身体技能的习惯运动,均属此类。而抽象运动意味着不针对实际情境的运动。比如,处理想象或可能任务的运动,或者处于学习特定技能过程中的非熟练行为。施耐德在具体运动中的表现和正常人差别不大。②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translated by Colin Smith,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p.121—122.但他不能做超越实际情境的运动,或者说不能完成抽象任务。比如,他不会游戏,也不能按指令做指示运动。施耐德明显缺乏一种能力,即不能从实际情境的沉浸状态中抽身离开,不能置身于想象的、可能的情境之中。
以此为前提,罗丹—罗路试图确立处理实际事务行为和可能事务行为的区分。在她看来,正常成年主体能够脱离实际情境,转向可能情境和可能任务,比如进入某种游戏的情境当中,并且可以调动与可能任务和情境相关的身体技能。在生存论现象学框架下,罗丹—罗路接受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启示。按照梅洛—庞蒂的说明,人类主体可以决定接受一个计划,而不仅仅只是将自然本性强加在其身上。罗丹—罗路认为,主体不但有知觉当下任务的能力,也有处理可能事务的能力。后一种能力让我们可以放弃置身其中的当下情境。在这个过程中,思想导致了行为的发生。例如,外部指令的出现,导致主体处于脱离与境的抽象状态,自我意识此时将引发行为。
(三) 在想象的情境中执行任务
明确的意识引导行为,不仅出现在行动任务转换期间,而且涉及思想持续引发行为的现象。罗丹—罗路提出的处理想象任务的情况涉及后者。
从生存论现象学原则出发,罗丹—罗路指出,具身主体在想象情境中执行任务,主体的意识维持了想象的情境,并持续引导处理想象任务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具身主体处理想象任务所用的身体技能并未有实质变化。所在的想象情境不是实际的,却是在场的。
假设有一位武打演员正在拍摄一部功夫影片。①罗丹—罗路本人提出了一个大体相似的案例。参见Komarine Romdenh-Romluc,“Merleau-Ponty and the Power to Reckon with the Possible”,in Reading Merleau-Ponty:On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edited by Thomas Baldwin,New York:Routledge,2007,pp.44—58。剧情需要他和一个不存在的对手格斗。在摄影棚中,演员想象着格斗环境,运用格斗技能与假想的对手抗衡。按照罗丹—罗路的看法,在类似模拟格斗的案例中,主体只是和想象的环境“相互作用”。主体须在意识中投射或表象包括假想对手的环境,以及对手的攻击和破绽。假想对手和对抗场景对演员来说都是在场的。他对环境做出回应使一系列动作成为可能。那些具有表演性质的动作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deliberated coping)。
此类有意识的行为与置身其中的行为是不同的。在罗丹—罗路看来,它们的差别主要是由具身主体身处的环境决定的。②Komarine Romdenh-Romluc,“Merleau-Ponty and the Power to Reckon with the Possible”,p.56.在模仿对抗时,演员很可能需要不断地想象对抗的环境和对手,而该环境并非实际情境。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主体处理的是想象的任务。想象的环境发出运动邀请,而该环境又首先由主体表象在自己的意识中。与处理现实任务不同,处理想象的任务意味着主体能够知觉更多行动机会。
无论在实际情境还是可能情境中,具身主体借助的身体中介是相同的。根据梅洛—庞蒂,知觉本身就是运用自己的运动技能。知觉经验的内容不仅被环境和当前任务塑造,也被主体的运动技能决定。主体的身体并不因为置身于可能情境或实际情境就发生改变。这种想象情境中的活动渗透了相同的身体意义(bodily significance),或者说,主体的运动技能不必有所不同。
(四) 德雷福斯和罗丹—罗路方案的统一性
在德雷福斯看来,罗丹—罗路关于在想象情境中执行任务的分析具有合理性。但其另外一个对任务转换的分析,实则主张主体可以脱离视域或世界,因此违背了现象学基本立场。那么,罗丹—罗路的任务转换方案是反现象学的吗?
德雷福斯和罗丹—罗路提出的任务转换方案均指出,明确的意识参与了实现任务的转换,同时,行动主体的身体和运动技能并不因任务性质的变化而变化。不过,德雷福斯的方案与实际情境始终关联,具身主体似乎只有受到干扰,才被迫向其他情境开放。而对于罗丹—罗路的方案来说,主体能脱离实际情境,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也可向其他情境开放。
德雷福斯和罗丹—罗路方案的冲突在于,思想在任务转换过程中导致行动,是否必然在原有任务的视域内完成。后者相信,必然存在一种完全的放松(total lessening)。这意味着,主体面向可能任务时,沉浸在实际情境的状态可以从根本上被打破。换言之,正常具身主体将采取一种抽象态度。以具体运动和抽象运动的分区为前提,具体姿态意味着主体在实际情境中处理实际任务或转向新任务;而脱离实际情境,面向可能的、想象的情境完成任务,具身主体则持一种抽象姿态。在应对可能事务时,主体投入到可能的情境中,在意识中表征行动的目标或过程,此时,自我意识将与抽象姿态一同出现。
抽象运动本身并不必然与生存论现象学立场相背离。抽象运动概念与表象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论背景具有渊源,涉及“表象功能”和“客观化的能力”等。①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p.139.但是,该概念经过改造后,完全可以在现象学传统内找到位置。梅洛—庞蒂宣称,抽象运动和高级意识活动同样奠基在运动意向性基础上。对于德雷福斯的方案来说,当我们置身于一个实际情境,新任务发出了真实的召唤,而对于处理可能事务方案来说,主体需要在自己四周投射一种抽象的可能性。梅洛—庞蒂指出:“正常人处理可能的事务,而该事务无需转变其可能的状态,便获得一种现实性”②Ibid.,p.125.,也就是说,可能的任务并非不在场。抽象运动从未超出自我身体所投射的视域,同样是具身主体在世界中的一种生存方式。③德雷福斯不接受抽象运动,可能源自他对情境与世界概念的混淆。
从生存论现象学视角出发,德雷福斯可以接受具身主体向可能事务开放的情况。就此而言,行为现象学应该包容德雷福斯和罗丹—罗路提出的上述方案。④罗丹—罗路认为,德雷福斯设定的主体类似病人施耐德一样,始终被禁锢在情境之中。而正常人可以跳出实际的情境,顺利完成任务转换。从某种角度看,我们可以将德雷福斯的方案置于具体运动的领域加以理解。罗丹—罗路有关现象学行为观的近期思考,参考Komarine Romdenh-Romluc,“Thought in Action”,in Oxford Handbook of Phenomenology,edited by D. Zahav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s,2012,pp.198—215;and Komarine Romdenh-Romluc,“Merleau-Ponty:Actions,Habits,and Skilled Expertise”,in Philosophy of Mind and Phenomenology: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Approaches,edited by D. Dahlstrom,A. Elpidorou,W.Hopp,London:Routledge,2015,pp.98—116。
本节阐述了三种由意识引导的行为。其中,前两种情况涉及具身主体在任务转换中的活动,第三种情况指向处理想象任务的行为。上述三种情况涉及的行为与运动意向性支配的具身活动不同,但同样建立在运动意向性基础上。这类具身行为扩展了生存论现象学行为观的研究范围。
鉴于具身行为不再局限于由运动意向性支配的活动或建立在习惯基础上的行为。接下来,我们可以将梅洛—庞蒂重点论述的具身行为类型称为具身熟练行为(skillful embodied coping),以和由意识指导的具身行为相区别。
三、具身熟练行为和理性因素
生存论现象学关注人类具身知觉经验。此类经验以日常的或熟练的具身行为为典型。在德雷福斯看来,所谓日常的或熟练的具身行为是指:“在世界中生活,四处活动,以及处理事物的通常方式”①Charles Taylor,“Foundationalism and the Inner-outer Distinction”,in Reading McDowell on Mind and World,edited by Nicholas H. Smith,London:Routledge,2002,p.111.,包括熟练运用某种技能和工具的活动,如自如地骑自行车等。作为一种基本行为类型,具身熟练行为由运动意向性直接支配。从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出发,由运动意向性支配的知觉活动是前概念的、前理性的。德雷福斯最初坚持这一看法。
笛卡尔主义等哲学传统曾一度忽视此类行为现象。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作为美国当代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尝试思考具身熟练行为现象,并努力将其纳入笛卡尔主义研究传统中。他主张,人类的知觉和行为中渗透着概念的理性。所谓概念就是 “对于事物是否如此这般做出相应判断时显示出的理性”②John McDowell,Meaning,Knowledge and Real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405.。而没有概念就不可能拥有知觉经验。例如,体现实践智慧的具身熟练行为就涉及概念的能力。从某种角度看,他的相关学说可被称为一种理性主义或概念主义的行为观。
行为现象学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在具身熟练行为现象中,自我意识或者理性因素真正销声匿迹了吗?德雷福斯和麦克道尔在21世纪初展开的论战,为人们思考该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 实践智慧:关于具身熟练行为的说明
2004年,德雷福斯当选美国哲学协会太平洋区主席。在主席就职演讲中③Hubert Dreyfus,“Overcoming the Myth of the Mental:How Philosophers Can Profit from the Phenomenology of Everyday Expertise”,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Vol. 79,Issue 2,2005,pp.47—65.,他关心如下问题: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觉经验是否包含着概念?他将矛头指向麦克道尔。后者主张概念的理性渗透在人类具身知觉和行为中。在德雷福斯看来,这不过是在坚持一种心灵的神话,其学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成问题的。2007年,两人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论战。①参见 John McDowell,“What Myth?”,Inquire,Vol. 50,No. 4,2007,pp.338—351;Hubert Dreyfus,“The Return of the Myth of the Mental”,Inquiry,Vol. 50,No 4,2007,pp.352—365;John McDowell,“Response to Dreyfus”,Inquiry,Vol. 50,No. 4,2007,pp.366—370;Hubert Dreyfus,“Response to McDowell”,Inquiry,Vol. 50,No. 4,pp.371—377。这次交锋对行为现象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也吸引了从事现象学、分析哲学、比较哲学研究的众多学者的关注。②参 见 Mind,Reason,and Being-in-the-world:The McDowell-Dreyfus Debate,edited by Joseph K. Schear,London:Routledge,2013。
麦克道尔作为分析哲学家,其工作和生存论现象学不乏相近之处。不少人将其工作视为沟通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桥梁。他试图对人类的具身经验现象做出说明,并意欲借此为整个人类知识大厦奠定基础。
麦克道尔对具身熟练行为的说明集中体现在他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的阐释中。通过日常反复学习和灌输,人形成了第二本性,并拥有了实践智慧。麦克道尔指出,实践智慧是“一种能力,使我们认识并创造了在理性空间中进行理解的可能性”③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79.。实践智慧涉及熟练运用特定技能或工具的能力,可以让游泳运动员在水池中自如游动,令网球运动员轻松挥拍击球等。这种具身活动能力拥有某种理性形式。麦克道尔指出,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包括我们的知觉在内,是由四处弥漫的概念的理性塑造的。由于实践智慧拥有概念的能力,因此,我们一旦被赋予第二本性,也就可以把自己看作本质上渗透了理性的动物。如果人处在可用语言表达的思想空间之中,那么人类和世界的关系明显渗透着概念的理性,因为正是语言赋予我们概念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概念的理性使人类和动物王国的成员区别开来。在某种意义上,麦克道尔对实践智慧做了概念主义的阐释。
立足于生存论现象学,德雷福斯对此坚持不同的认识立场。在他看来,实践智慧意味着主体对完全具体的情境径直做出反应。实践智慧的展开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情境。情境是认识和行动的背景,它具有意义,却是前对象的、前谓述的,不能被概念化。就此而言,作为知觉经验的具身熟练行为,并不处在理性的空间之中。通过社会化过程,一个人的具身知觉和行动最终将会对其特定的情境做出最佳回应,具身熟练行为并不建立在以理性为基础的习惯之上。
德雷福斯认为,将我们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不是作为语言或理性的逻各斯,也不是特定情境中的心灵。我们全神贯注于日常熟练活动时,能够自由超越束缚,而动物缺乏这种自由。不过,人类虽然拥有自由,却不会导致理性在基本的知觉经验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和其他动物分享的知觉能力和具身行为技能不可能渗透着理性。至少,在获得理性之前,我们便已拥有了具身行为技能。至此,本节的问题也可以如此表达,即具身的知觉和行为是否必然被概念的理性所渗透?
(二) 从心灵到心灵要素
对于德雷福斯来说,麦克道尔的理论框架无法接纳非反思的具身行为。一般而言,传统理智主义或理性主义承诺存在某种由心灵指导的行为。所描绘的行为既脱离情境,也非具身。该行为观实际上坚持理性与情境相分离的立场。麦克道尔主张,我们的知觉经验是概念的,概念的能力属于主体的理性能力。在德雷福斯看来,这是在主张理性在我们的知觉经验中无处不在的教条。其行为观在重弹传统理性主义的老调。德雷福斯主张,麦克道尔的错误在于,他关注“知识大厦高层的概念部分”,而忽视了“较低层面进行着的具身行为”。如果具身技能总是发生在具体情境之中,那么,麦克道尔就不大可能去谈论具身熟练行为。
麦克道尔认为,德雷福斯在解释实践智慧的过程中,错误地认为他本人坚持如下看法,即“仅当人们执行某些内容的活动,该内容完全可在与情境相分离的情况下明确起来,理性在参与行动时才可与情境关联起来”①John McDowell,“What Myth?”,p.340.。也就是说,一旦将理性引入日常知觉行为,主体就只能置身情境之外,转而让理性指导自己的行动—— 而这正是他本人反对的观念。
麦克道尔强调实践智慧和概念的理性之间存在特定关联。②参见 John McDowell,“Some Issues in Aristotle’s Moral Psychology”,in Companions to Ancient Thought:Ethics,Vol. 4,edited by Stephen Ever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07—128。他指出:如果说人处在用语言可表达的思想空间之中,那么,我们四处弥漫的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塑造着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包括我们的知觉和世界的关系。这种理性并不要求人类主体置身于具体的情境之外。它和传统理性主义主张的理性或心灵绝不能混同起来。麦克道尔特别将其所刻画的意识称为心灵要素。
经过这个层面的意见交换,我们发现,两者都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的立场,所论及的行为也均是情境化的。
(三) 行动中的最佳状态是如何丧失的?
德雷福斯虽然承认,麦克道尔的观点不同于有关理性和概念的传统解释,但仍然拒绝将后者描述的活动理解为具身熟练行为。相反,渗透心灵要素的活动被视为一种概念意向性指导的行为,可用“置于身外的、概念的意向性来刻画”③John McDowell,“Response to Dreyfus”,p.366.。
德雷福斯指出,当我们全身心地运用身体技能时,其中有一种非表象化的运动意向内容。运动意向内容和概念意向内容不同。后者是范畴的,可以被判断组织,而前者“是非概念的、非命题的、非理性的,以及非语言的”④Hubert Dreyfus,“The Return of the Myth of the Mental”,p.352.。他进一步指出,具身熟练行为并不排斥这样的情况,即我们在行动时有机会监测自己的活动。不过,他提醒道,我们如果将行为监测为自己正在做的,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行为不可能达到最佳状态,至多是合格或胜任(competence)水平。①行为现象学主张,概念意向性指导的行为可以在运动意向性基础上获得解释。不过,德雷福斯对表象或概念意向性指导的行为现象的理解仍有待深化。他在某种程度上并未成功将此类行为现象刻画为一种具身行为。而只有当我们返回到了非反思的状态,我们的身体技能才会再次恢复到巅峰状态,主体意识也才会重新成为非概念的,心灵不再参与其中。
上述批评集中在两处:首先,麦克道尔将实践智慧行为解释成为渗透了理性的行为,这不符合运动意向性所支配的具身行为内涵,倒类似于概念意向性指导的行为;其次,麦克道尔不能解释人类行为为何从最佳状态脱离了出来。
在麦克道尔看来,理性被置于具身熟练行为之中,不是把“我思”加到行动的表象上去的结果。人类行为中的自我觉知(self-awareness)不是“我思”,而是“我做” (I do)。“我做”不是加到表象上的表象,它是对实现行动中具有实践理性能力的第一人称视角特征的记录。②John McDowell,“Response to Dreyfus”,p.367.在这个意义上,心灵要素不能用置于身外的、概念的意向性来刻画。更进一步,他指出:“当心灵要素不再沉浸在具身行为当中,心灵要素可能就是具身行为的敌人。”③Ibid.渗透了心灵要素的实践智慧不能被理解为处在思想监控状态下的行为。后一种行为受手段—目的理性(means-end rationality)控制。一旦沉浸状态的心灵要素转变为手段—目的理性,并试图引导人类行为,前者就不再发挥效用,主体技能也不再保持最佳水平。
(四) 完全沉浸的行为:第三人称视角的剥离
如果麦克道尔思考的实践智慧行为远离了理智主义,也并非概念意向内容引导的行为,那么,行为现象学应如何理解该行为观描述的现象呢?
通过区分手段—目的理性和渗透在非反思行为中的理性,麦克道尔解释了为何人类技能不再处于最佳状态。对德雷福斯来说,即使麦克道尔能够证明这一点,也不能说明心灵要素参与其中的行为就是完全沉浸其中的具身熟练行为。人们发现,德雷福斯将具身熟练行为进一步划分为完全沉浸其中的行为(fully absorbed coping)和一般意义上置身其中的行为(involved coping)。两种行为对应完全沉浸其中(absorption)和一般置身其中(involvement)两种状态。他指出:“沉浸其中的行为不止是置身其中的行为的另一个名字,沉浸其中的行为是最佳状态的置身其中的行为。”④Hubert Dreyfus,“Response to McDowell”,p.373.它是纯粹由运动意向性支配的行为。在完全沉浸的行为中,我思是缺席的。⑤Ibid.换言之,其中不包括一个弥漫其中的自我,甚至也不存在一个隐含的自我。完全沉浸的行为作为一种纯粹的具身知觉经验,排斥第三人称视角。如果心灵要素涉及一种伴随知觉行为发生的反思结构,哪怕是一种弱的、潜在的反思结构,主体都不再能够全身心沉浸在行动之中。
麦克道尔试图将其有关实践智慧的解释扩展到整个具身知觉和活动领域,并希望为人类知识大厦奠定基础。理性可以进入人类的自我觉知当中,但这样一种自我觉知内部隐含着两种视角。它是第一人称视角的,同时也涉及第三人称视角。两种视角同时存在的情况只能是一种混合结构,并始终与纯粹第一人称视角的具身知觉意识相区别。如果不能够排除第三人称视角,那么麦克道尔的实践智慧行为就不是完全沉浸其中的。
德雷福斯的批驳也为麦克道尔的工作留下了空间。首先,虽然德雷福斯重视完全沉浸其中的状态,但完全沉浸的行为和一般置身其中行为的划分,使得麦克道尔刻画的行为也有可能被认同为一种具身熟练行为。与完全沉浸行为不同的是,该行为对应的知觉意识结构可能是混合视角下的自我觉知。德雷福斯一方面论证了具身熟练行为并不必然被概念所渗透,另一方面也似乎为概念主义的具身行为留下了空间,使其进入行为现象学的理论视野之中。
在德雷福斯推进现象学行为观发展过程中,人们意识到现象学有关具身行为的认识仍有待深化。正如罗丹—罗路指出的,他最初赞同梅洛—庞蒂的观点,也将由运动意向性支配的具身行为视为基础的行为模式。事实上,德雷福斯还将具身行为等同于海德格尔理论中此在在世界中的本真存在经验。毫无疑问,这两位现象学家关于人类知觉和实践活动的认识具有共通之处,都关注在世界中存在的生存体验。同时,德雷福斯不否认梅洛—庞蒂的承诺,即明确意向支配的行为可以在运动意向性的基础上获得解释。但是,梅洛—庞蒂并未具体展开论述。泰勒·卡曼(Taylor Carman)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德雷福斯认为:“梅洛—庞蒂现象学有助于描述情境中的注意力在理智上横向的转换,但必须承认,他并没有提及超然的、反思的,以及有意识的、思想驱动的行动是如何可能的。”①Taylor Carman,Merleau-Ponty,New York:Routledge,2008,p.134.这种情况要求现象学继续关注此类行为现象。就意识指引行为的问题而言,在德雷福斯看来,海德格尔的工作可以提供借鉴。在他与罗丹—罗路的论争中,他的立场已经表明:具身行为流被打断时,明确的意向才会显现。但除此而外,德雷福斯本人没有更多阐释相关行为类型及其可能外延。②斯图尔特(Laurel Scotland-Stewart)也如此看待德雷福斯。在其博士论文中,她主张德雷福斯将实践活动划分为“absorbed coping”和“breakdown”。不过,对她来说,这种区分仍然需要回溯到海德格尔那里,而不是以知觉现象学为出发点。参见Laurel Scotland-Stewart,Social Invisibility as Social Breakdown:Insights from a Phenomenology of Self,World,and Other,Stanford University,2007,pp.29—70。
从具身性视角出发,行为现象学有必要深入探讨关于意识指引行为的现象,并扩大对具身行为外延的理解。一方面,德雷福斯承认罗丹—罗路关于处理想象任务的解释。但后者关于任务转换的说明,同样不违背通过身体在世界中存在的现象学立场。对于受意识驱动的具身行为认识而言,德雷福斯最初从经典现象学家那里获得的洞见是不够的,新情况也应获得严肃对待。需要注意的是,由意识指引的具身行为应该不仅包括上述三种情况。本文的相关探讨只是一个开端。①在习惯形成前,学习使用工具的不熟练行为同样可归为此类行为现象,而且具有典型性。相关讨论可参见,姚大志:《具身性与技术—— 德雷福斯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51—67页。
除了受意识指引的具身行为之外,生存论现象学同样需要持续关注由运动意向性支配的具身活动。在知觉现象学的理论框架下,习惯的形成意味着身体图示获得重组,换言之,新的身体技能得以确立起来。在此基础上,主体运用身体技能的行为与非反思的日常活动一样,均属于具身熟练行为类型。
借助德雷福斯和麦克道尔的论战,人们发现具身熟练行为仍需做进一步划分。在他们看来,专家技能行为或者具身熟练行为都可理解为一种实践智慧。不过,对于麦克道尔而言,展现第二本性的活动渗透着理性因素;对于德雷福斯来说,相关行为受运动意向性主导,完全排除了概念和理性。随着论辩的展开,人们发现麦克道尔的行为观既非传统理智主义,也非表象主义。在论辩过程中,德雷福斯以退为进,将具身熟练行为区分了两种亚行为类型,即一般置身其中的行为和完全沉浸的行为。他将完全沉浸的行为确定为剥离了第三人称视角的活动,清除了意识活动中的反思结构。在完全沉浸状态的意向中,并没有麦克道尔的心灵要素的位置。作为让步,他承认麦克道尔的实践智慧行为观描述了置身其中的行为。通过审视德雷福斯等人的工作,具身熟练行为的意向性结构呈现出更丰富的结构和层次。
本文追寻德雷福斯的学术轨迹,呈现了21世纪初现象学行为观发展的某些侧影。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它提供一个反思德雷福斯理论工作的契机。麦克道尔声称,德雷福斯像梅洛—庞蒂一样,始终坚持“概念理性和身体的生命相分离”,这也是一种神话,可以称为“非具身智能的神话”②John McDowell,“What Myth?”,p.349.。针对德雷福斯的行为观,罗丹—罗路指出:“知觉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太紧;似乎没有留下让意向干预的空间。”③Komarine Romdenh-Romluc,“Merleau-Ponty and the Power to Reckon with the Possible”,in Reading Merleau-Ponty:On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edited by Thomas Baldwinl,New York:Routledge,2007,p.48.这些评论指向德雷福斯研究工作的局限,还是行为现象学内部原本隐藏的张力,仍需当代哲学家继续深入思考。
B80
A
2095-0047(2017)06-0017-12
姚大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受中国科学院科技史青年人才研教任务子课题(项目编号:2017K20419)、科学史所重点培育方向项目(项目编号:Y621041001)资助。
韦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