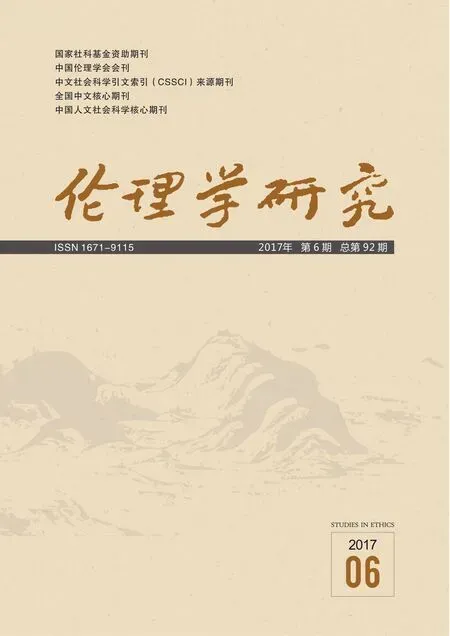神经科学的规范伦理学意义
——以约书亚·格林的双重进程理论为例
蔡 蓁
神经科学的规范伦理学意义
——以约书亚·格林的双重进程理论为例
蔡 蓁
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借助fMRI技术探究人们面对电车难题做出不同的道德判断时大脑的运行特征,提出道德判断的双重进程模型以解释道义论判断和后果主义判断所依赖的不同心理进程,并进而得出:由自动的情感进程优先支持的道义论判断,较之于由有意识的推理进程优先支持的后果主义判断是缺乏可靠性的。虽然格林的神经科学研究对探究规范性问题具有启发意义,但是鉴于其规范性结论的经验性前提和规范性前提都存在重要缺陷,因此尚不足以对后果主义和义务论之争做出实质性的推进。
神经科学;电车难题;规范性;双重进程理论
近年来,一些神经科学家致力于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来探究人类在做出道德判断时大脑的运行特征。这些经验研究对理解道德判断的性质及其心理机制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这些有关道德判断的事实层面的研究对回答规范性问题究竟有什么作用?许多哲学家,如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认为规范伦理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有其“内在的辩护和批评标准”,规范性问题是通过伦理反思和论证来回答的,正如数学问题是通过数学推理来回答的[1](P142-146)。通过考察道德判断时的fMRI扫描数据来回答规范伦理学问题就好象通过扫描大脑在从事数学推理时的状态来解决数学问题一样是荒谬的。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经验研究也具有重要的规范伦理学含义,在这个路向上颇为引人注目的一项研究是约书亚·格林借助神经成像技术考察人们对电车难题的不同反应,由此就道德判断的心理机制做出一个经验论断:道义论的判断是由自动的情感反应得出的,而后果主义的判断则是由有意识的推理进程得出的,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得出一个规范性的论断:我们有理由相信道义论的判断较之于后果主义判断而言并不具有可靠性。格林的工作不仅是在经验意义上探究人类做出道德的时候,大脑是如何运作的,更重要的是试图从神经科学的经验结果中引出规范性结论。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研究受到跨学科的广泛关注和评议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恰当理解格林观点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的挑战和批评,对这一论证的可靠性做出评价。
一、电车难题与后果主义和道义论之争
格林从神经科学角度对道德判断的研究是以考察人们对电车难题的不同反应为切入点的。为了看到格林在处理电车难题上的独特之处,首先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后果主义和道义论围绕着电车难题所进行的争论。电车难题最初是由菲丽帕·富特(Philippa Foot) 和朱迪丝·汤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的讨论而引人注目。这个讨论中涉及到如下两种情形:
电车开关难题:一辆失控的电车朝着铁轨上的五个人疾驰而来。你可以扳动一个开关,从而把电车引向另外一条只有一个人的铁轨,这个人会被轧死,而另外五个人会得救。[2](P23)
天桥难题:一辆失控的电车朝着铁轨上的
五个人疾驰而来。你站在天桥上,旁边有一个胖子,你可以把这个胖子推下桥,胖子会被轧死,但是他的身体会阻挡住电车,从而挽救另外五个人。[3](P1409)
虽然这两种情形看似根本上都是牺牲一个人挽救五个人,但是大多数人从直觉上都会认为在开关难题中扳动开关在道德上是可被允许的,而在天桥难题中把胖子推下桥在道德上则是不被允许的。人们为什么会对后果一样的两个难题具有相反的直觉?对电车难题的哲学讨论通常都预设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道德直觉是有道理的,而哲学家的任务是要搞清楚这两个情形中究竟是哪些道德上相关的因素使得我们有理由对它们做出不同的道德判断,并进而反思现有的规范性理论——后果主义和道义论——是否充分考虑到这些道德上重要但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并基于这种反思对理论本身进行修正。
按照经典的后果主义理论,与行为的正当性相关的唯一因素是行为的后果,它所提出的道德要求就是最大化后果中的善,这样看来,无论是扳动开关还是推下胖子在道德上都是可被允许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中后果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因此,后果主义似乎并没有能够解释也无法辩护人们为什么会对这两种情形做出不一样的道德判断。与之相对,道义论认为行为的正当性不仅与后果相关,也与诸如公平、行为者的意图等等因素相关,并要求对最大化后果中的善施加道义上的限制。道义论由于并不把后果作为唯一重要的考量,似乎就比后果主义更有可能抓住这两种情形之间的区别,一种著名的尝试就是引入双重效应理论(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s)。DDE有许多不同的版本,按照弗朗西斯·卡姆(Frances Kamm)的归纳,大致来说,它区分了有意造成的伤害和仅仅只是可以预见到并只是作为副产品的伤害,在同样是为了促进某种善的情况下,前者是需要施以道德限制的,而后者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促进这种善的时候则是可以被允许的[4](P93)。按照这种理论,扳动开关是可被允许的,因为这样做的意图是挽救五个人,虽然可以预见到另一个人会死亡,但是并非有意把这个人的死作为手段来挽救其他人。而推下胖子则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样做是有意让胖子被轧死以阻止电车撞到其他人,杀死胖子成为挽救五个人的必要手段而不是副产品。但是DDE很快就遭到了挑战,例如汤姆森设计出了电车难题的一个变种,环路难题(loop case),这个情形和开关难题的差别在于,只有一个人的第二条铁轨又绕回到了有五个人的第一条铁轨,这意味着要不把电车引向第二条铁轨并因为撞到那个人而停止,电车就会回到第一条铁轨轧死那五个人。这里,和天桥难题类似,杀死一个无辜者成为挽救五个人所必需的手段,那么根据DDE,扳动开关就是不被允许的,但是从直觉上来说,人们又倾向于对环路难题做出和最初的开关难题一致的判断,而DDE则不能解释这一点。随后,又不断有新的理论和变种案例被提出,而电车难题的困难之处就在于,无论什么样的原则被提出来以解释我们的直觉,总会有人设计出新的难题使得在应用已经提出的原则时会产生反直觉的后果。
二、基于电车难题的双重进程理论
格林处理电车难题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尝试提出能够对我们的直觉进行辩护的规范性原则,而是采取了一条描述性的进路,即借助神经科学的技术手段来考察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进程使得我们对电车难题的不同情形做出不同的反应,并最终得出支持后果主义质疑道义论的规范性结论。格林的论证有三个核心部分。
首先,他提出关于道德判断的双重进程理论(The dual-Process Theory of Moral Judgment),将得出道德判断的心理进程区分为自动的情感进程(automatic emotional processes)和有意识的推理进程(conscious reasoning processes)。这是大脑处理外界信息的两种不同方式,前者直接触发自动的直觉反应,“具有直接的驱动性力量”,这种反应是快速的,不受意识控制的,能够让我们迅速对情境做出反应。而后者并不触发特定的行为反应,是有意识的,缓慢的,灵活、可调试的,能够让我们基于对处境的认识并结合一般性的知识形成长期的、审慎的行为计划。他把这两套进程比作数码相机的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是“效率和灵活性之间的平衡折衷”[5](P120)。
其次,他要探究引导人们对不同情形的电车难题做出不同反应的心理进程是什么。他将人们对电车难题的判断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典型的后果主义的判断”,也就是“很自然地为后果主义原则(即不偏不倚的成本收益推理)所辩护”的判断,例如认为在天桥难题中推倒胖子在道德上是可被允许的;另一类是“典型的道义论的判断”,也就是“很自然地根据道义论原则(即根据权利、义务等)来辩护”的判断,例如有意通过杀害一个人来挽救五个人在道德上是不被允许的[5](P122)。当格林让被试者就包括开关难题和天桥难题在内的道德难题做出判断的时候,他发现当情境中涉及到对他人“贴近与切身的(up close and personal)”伤害时,比如需要亲手把一个胖子推下桥,被试会倾向于做出道义论的判断,这时大脑的情感区域(内层前额叶皮质的大片区域,包括一部分腹内侧前额叶皮质)要更为活跃;而当情境中并不涉及到切身伤害时,比如只需要扳动开关来改变电车轨道的时候,被试倾向于做出典型的后果主义的判断,这时大脑的认知区域(背外侧前额皮质,DLPFC)要更为活跃[5](P123)。他进一步将双重进程模型和两种道德判断关联在一起,认为规范伦理学中具有核心地位的后果主义和道义论之间的张力实际上是情感进程和推理进程之间的张力的表现,并由此得出核心张力原则:“典型的道义论的判断被自动的情感反应优先支持,而典型的后果主义判断被有意识的推理和连带的认知控制进程优先支持”(The Central Tension Principle,CTP)[5](P121)。
CTP本质上是关于后果主义和道义论判断的心理基础的经验论断,而格林的工作中最富争议的一部分就是他试图由判断产生过程中的特征进而对判断本身的可靠性做出评价。这部分的论证过程中我们可识别出三个重要的环节。首先,格林认为道义论的判断是由情境中“贴近与切身的”因素所触发的,而这些因素本身并不具有道德相关性。他从演化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倾向于对情境中的“贴近与切身”的因素立刻做出反应。在人类社会早期,“贴近与切身的”方式几乎是伤害他人的唯一方式,对这种伤害的敏感性并产生充满厌恶的情感反应也是一种具有演化优势的能力,而且在人类的演化历史上出现得要远远早于复杂的抽象推理能力。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天生就会对切身的暴力做出反应,这并不是什么应该令人惊奇的事情”[6](P43),人类对某些直接的人际间的暴力行为具有负面的情感反应是一种不费力的、自动的反应。但是格林认为,切身的力量和空间上的远近,并不具有道德上的相关性,即在伤害一个人的时候究竟是亲手推还是用开关遥控对这个行动在道德上的对错并不应该构成影响。鉴于此,道义论的判断,就其得出过程而言,是对情境中与道德无关的因素做出的自动的情感性的判断,而并非是道德推理的结果,因此并不具有真正的规范性力量。
进而,格林认为道德推理对于道义论者来说所起的作用是对那些通过直觉自动得出的判断进行辩护和合理化。具体来说,“道义论者先是凭直觉分辨出具体的情境中存在哪些权利和义务,然后再寻找出一些原则来解释为什么这些权利和义务的确是存在的”[5](P134)。比如,在天桥难题中,由于对推倒胖子这种切身性伤害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从而激发出否定性的道德判断,然后再用“不能把人类仅仅作为工具”,或者DDE这样的理论来为这种判断进行辩护。格林形象地把这种事后的辩护过程称之为“跟着直觉跑(intuition chasing)”的过程,其典型特征在于“让一般性的原则来合乎那些(大多数情况下是)随着直觉起起落落的判断”,而与之相对的后果主义判断,无论是在切身性的还是在非切身性的情境中,都会按照后果主义的最大化原则,通过成本收益的推理,对行为在道德上的对错做出一致的判断,虽然这意味着要克服一些天生具有的情感反应。这在格林看来是一个“咬牙吞子弹(bullet biting)的过程,不管直觉怎样起起落落,也要让判断合乎原则”[5](P134)。
第三,以上两点中实际上都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由道德推理产生的判断是更为可靠的。对此,格林一方面澄清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自动的情感模式都不可靠,但是也指出“自动模型只有经过试错经验(trial-and-error experience)的塑造才能良好地发挥功能”[5](P131)。另一方面,他强调当我们面对并不熟悉的问题时,无论是从演化的、文化的,还是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都缺乏充分的经验,那么手动模式是更为可靠的。他由此得出认知无奇迹原则 (The No Cog nitive Mira cles Principle,NCMP):当我们在处理不熟悉的道德问题时,我们应该较少地倚赖自动模式(自动的情感反应)并更多依赖手动模式(有意识的,受控推理),以免依赖认知奇迹[5](P131)。他进而提出判定不熟悉的道德问题的两种方式:一是那些从目前的文化发展,尤其是从现代技术和不同文化的碰撞中产生的问题很有可能是陌生的,如气候变化,全球正义问题;二是容易产生道德分歧的问题很有可能是陌生的,在对非道德的事实层面没有疑义的情况下仍旧存在道德分歧很有可能是因为人们具有相冲突的道德直觉,要决定究竟是哪一方的自动模式出了问题,就需要手动加以检验。
三、对双重进程理论的规范性意义的反思
格林的观点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很多批评和讨论,在梳理和评价这些批评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恰当地理解格林的论证的性质。有一种常见的误解是认为格林试图以神经科学的证据来证明道义论判断是错误的。对此,需要厘清两个问题。第一,格林并不是试图从经验研究中直接推导出规范性的结论,而是承认在这个论证过程中规范性的前提也是必需的。例如,单凭“道义论判断是对情境中的贴近且切身的因素做出的回应”这个经验判断是无法推出“道义论判断是缺乏规范性力量”这个评价性结论的,中间势必还需要加入一个规范性的前提:贴近且切身的因素并不具有规范意义上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格林来说,由于规范伦理学理论对不偏倚性的强调,这个前提近乎是老生常谈,而他的经验研究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当这个并不富有争议的规范性前提同他的经验证据相结合之后,却能够得出对道义论的新的挑战。
第二,格林的论证在于表明道义论判断的产生过程使得它的可靠性和揭示真理的可能性都是更加值得怀疑的,但这并不表明道义论的判断就必然是错的。格林的论证根本上立足于这样一种策略,即我们除了可以通过指出一个论断本身存在的问题,这包括其内部的融贯性,证据是否充分来对它提出挑战,还可以通过揭示人们在得出这个论断的思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来对它提出质疑,这些问题包括出于偏爱的考量,受到激情的蒙蔽等等。例如,当你我在争论A是不是一个好法官的时候,我指出你是A的至亲好友,或者你刚刚喝过两瓶烈酒来质疑你能否得出正确判断。但这也无法表明这个判断就必然是错的,即便是在带有偏见或者醉酒的情况下,人们仍旧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严格来说,这种策略在于表明某个判断可能是不可靠的,因此相信这个判断可能是得不到辩护的。这种策略被马修·廖(Matthew Liao)称之为知识论上的拆穿论证(epistemic debunking argument),在将经验科学与哲学问题相结合的研究中,这种形式的拆穿论证是很常见的[7](P28)。如果这样来理解格林的论证,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并不是如内格尔所批评的那样试图通过扫描大脑来解决道德问题,揭示道德真理,而是在于试图揭穿对道德问题的某些回答是并不可靠的。虽然它并不能从一种强的意义上表明道义论判断是错误的,但是通过揭示道义论判断其实是大脑的情感区域对情境中的非道德因素的自动反应,加之自动的情感进程的产物在面对不熟悉的道德问题时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道义论的判断是不可靠的,也是得不到理性辩护的。要评价这个拆穿论证是否有效,我们有必要依次审视得出这个结论的两个前提。
首先来看第一个经验性的前提,这实际上就是上文提到的CPT所表达的内容,格林用来支持CPT的一个主要证据在于:切身的困境产生情感区域的更多活动,人们更易得出道义论的判断,非切身的困境产生DLPFC区域的更多活动,人们更易得出后果主义的判断。这个证据中涉及到三个区分,即切身的困境和非切身的困境,自动的情感模式和手动的推理模式,道义论的判断和后果主义的判断,在格林的论证中,这三个区分是可以一一对应的,但有许多批评者都指出了这三者之间并不匹配的例证。这些反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情境中是否存在切身性的因素并不能将后果主义判断和道义论判断真正区分开来。卡姆设计出电车难题的转盘版本(lazy Susan case),在这个场景中,五个人被困在转盘的一角,要阻止电车冲向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转动转盘,而这样会让转盘另一角上的一个旁观者被撞,即便转动转盘给这个旁观者带来的伤害是贴近而切身的,但卡姆认为从直觉上看,哪怕是一个非后果主义者也会同意在这种情况下转动转盘是可以允许的。这表明在切身性的困境中,人们同样可能倾向于得出后果主义判断[8](P334-335)。另一方面,双重进程和两类道德判断之间的关联也并不是必然的。盖伊·卡亨(GuyKahane)就举出一些例证表明许多道义论的判断也是有意识的推理进程的产物。这些例子具有的一个特征是:做出道义论的判断是和多数人的直觉相违背的,例如,在为了避免伤害而撒谎的情形中,坚持认为这种善意的谎言在道德上是不被允许的。从直觉上看,多数人会倾向于立刻做出后果主义的判断认可这种撒谎行为,而坚持道义论的判断则是反直觉的。卡亨对这种情形的fMRI研究表明,反直觉的道义论判断和慎思推理进程是紧密关联的,和天桥难题中被格林认为是典型的后果主义判断具有“极其相似的神经激活模式”[9](P16)。这就意味着至少在某些情形中情感进程和推理进程并不必然对应着道义论判断和后果主义判断。
格林也援引神经科学研究中的其他证据来支持CPT,这包括大脑情感区域有缺陷的人——如VMPFC区域受损病人和有暴力倾向的精神变态者(psychopaths)——更倾向于做出后果主义判断,哪怕是需要以伤害亲人为代价,相反,同情心更强的人更容易做出道义论的判断[5](P125)。这些证据似乎支持了情感进程和道义论判断之间的关联,但是这是不是就反过来能证实后果主义判断就是为推理进程所支持呢?按照格林的双重进程模型,既然这些人缺乏情感能力,那么这种判断只能是为推理进程所支持,而由于这些人对伤害他人的做法并没有情感上的厌恶和恐惧,这里所涉及到的推理仅仅是五条人命多于一条人命这样一个快速而不费力的计算,而并不涉及到在相冲突的考量之间的任何权衡与慎思。但是,我们在规范性意义上谈论的后果主义判断,却并不是在面对道德难题时对他人的伤害无动于衷,而是对后果的考量在批判性的反思之下克服了道义论的直觉,这种后果主义式的慎思推理显然是这些病态人群没有能力做出的。而且进一步,这些人并不只是缺乏对伤害他人的厌恶之感,而且也并不认为这些伤害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他们因此也并不为此感到后悔。而史蒂芬·达沃尔(StephenDarwall)指出道德判断是与道德责任紧密相关的,因此也与斯特劳森(P.F.Strawson)所说的“反应性态度(reactive attitudes)”相关,如愧疚、怨恨和谴责等等,通过这些态度我们认为自己和他人是能够对判断和行为负责任的。而这些病态人群显然缺乏这些反应性的态度,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甚至可能缺乏做出真正意义上的道义论或者后果主义判断的能力。
面对这些批评,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到格林的确承认双重进程理论存在例外,但他强调“重要的不是双重进程理论完美地预测了每一个案例,而是它抓住了哲学的道德心理学的一般形态”[5](P127)。这就意味着一些反例的存在并不一定否定理论整体的有效性。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反例也揭示出,虽然格林的经验研究可以表明某些道义论判断是与情感性反应密切相关的,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明道义论判断就是情感进程的产物。而且他在考量涉及到病态人群的证据中也表露出他对推理进程的理解是过于稀薄的,而以缺乏反应性态度的病态人群为例也并不能揭示后果主义判断所涉及到的推理、慎思进程的本质,反而有将其简单化的倾向。
接下来再看这个拆穿论证的第二个规范性前提,即自动的情感进程的产物在面对不熟悉的道德问题时是不可靠的。为了支持这个看法,格林诉诸认知心理学中的捷思法(heuristics)概念,把道德领域中的情感进程描述为是自动、快速而不精确的捷思过程,它可能对在我们演化历史中常见的、为人熟知的问题上能够恰当地发挥作用,但却并不适用于我们今天面临的并不熟悉的新问题。这个论证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首先塞利姆·博克(Selim-Berker)反对把道德领域中的情感进程理解为一种捷思法。他的策略是把道德领域和其他领域中的情感进程区分开来,指出在非道德领域里,例如逻辑推理和概率推理中,当我们把某种心理进程称为捷思法的时候,我们对什么是对错已经有很好的把握,但是在道德领域中,究竟什么是对错却是有待争辩的。所以他认为把支持道义论判断的情感进程看作是一种捷思法是乞题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格林的论证作为一种知识论上的拆穿论证,强调的是得出判断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发现得出道义论判断的情感进程在非道德领域内是草率而不可靠的,那这就足以使我们有理由质疑道义论判断的可靠性,无论我们是否已经掌握了道德真理。就好比在之前的例子中,即便我们并不知道A到底是不是个好法官,但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酒精的作用下得出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质疑这个回答的可靠性。
如果我们可以认同格林的看法,把情感进程当作是一种不太精确、值得质疑的捷思法,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追问凭什么认为推理进程就是一种更精确更可靠的心理机制呢?可能有人会说,慎思性的推理不是显然比自动的情感反应要可靠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情感本身也可以是识别道德真理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科学哲学家詹姆斯·伍德华德(J.Woodward)和约翰·阿尔曼(John Allman)基于神经科学的证据表明包括自动的情感反应在内的道德直觉是“更广泛的社会直觉的一部分,指导我们进行复杂、高度不确定和迅速变化的社会交往”,“并能够在道德决策中扮演合法的角色”[12](P179)。甚至是对格林所青睐的后果主义来说,也有这个阵营内的哲学家指出慎思推理也并非必然更为可靠。如尤金·贝尔斯(Eugene Bales)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分,即决策程序和评价标准之间的区分,作为评价对错标准的后果主义并不一定要求行动者在每一个行为决策中都有意识地考量如何尽最大的努力促进后果中的善,在实践当中很有可能发生越是努力促成好的后果,越是事与愿违的现象[13](P263)。所以,并不一定说越是慎思推理得出的判断就越可靠。这本身仍旧是一个需要加以论证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策略是提出一个可靠的道德判断所具有的特征,并表明由大脑中的某些区域做出的道德判断并不具有这样的特征。格林的论证中也的确采用了这样一个策略,从他对切身性的讨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一个可靠的道德判断所具有的特征是:它必须是非切身性的,不能因为距离远近的不同就给予同样处境下的人以不同的对待。但是这样一个策略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切身性因素是否就一定是与道德无关的?的确在电车难题的不同版本中,亲手推还是用开关遥控的方式伤害一个人确实不应该成为我们判断这个行为道德上对错的考量因素,但是在其他情形中,例如是应该用极其有限的物资优先帮助身边的亲人还是远方的陌生人,对距离的远近和亲疏关系的考量就并非是在道德上得不到辩护的,当代规范伦理学的讨论中也日益重视偏倚性在规范意义上的重要性,因此,格林要把非切身性作为可靠的道德判断的特征还需要更充分的论证。第二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也是博克和卡姆都指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把讨论引向一个可靠的道德判断究竟应该对情境中的哪些因素做出反应,这实际上是一个规范伦理学内部的问题,是一个由道德哲学来解决的问题,与神经科学的实验结果是无关的。这也就消解了格林的经验研究所具有的规范意义上的重要性。
如果这个回答是存在缺陷的,我们可以看到格林在认知无奇迹原则中还表达了对可靠性的标准的另一种回答,他将我们的道德问题区分为在人类的演化历史中已经熟悉的问题,和当代社会中面临的陌生问题,对前者来说经过反复试错形成的自动反应可以是可靠的,但是对于后者来说则应该更多依赖有意识的推理进程。但是这样一个回答也同样面临问题。采用这种方式来对道德难题进行分类忽略了行动者本人的背景知识对他们如何感知并处理道德问题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如格林所说,开车对于大多数新手来说都不是一项可以通过自动模式来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有意识的推理模式发挥作用,但是一旦人们真正掌握了这项技能成为熟练的司机之后,在遇到交通状况的时候往往可以自动快速地做出判断,而不再依赖有意识的慎思,这实际上揭示出在人类生活的大多数领域都有一个从新手到专家的过程,这两类人由于其背景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差别,哪怕同样是通过自动模式做出的直觉式的反应,其内容也是大相径庭的。在道德领域当中也是如此,那些更善于道德思考的人拥有更多的系统知识,而且能够更不费力且更有技巧地运用这些知识,这不仅仅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接受默会知识的过程,也涉及到心理学家达西亚·那瓦茨(Darcia Narvaez)所说的“直觉和其他认知(如感知能力、注意力、驱动力和推理)之间“反复迭代地互动(iterative back-and-forth interplay)”[14](P238),这包括对道德敏感性的培养,如何应用默会于心的原则,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尤其是通过处理道德困境而对这些敏感性和原则的应用加以微调。如果把行动者之间存在的新手与专家的差别考虑进来,同样是面对格林意义上的陌生问题,由多种认知能力相互交织发展出的自动的直觉,和缺乏经验和概念框架,为环境中各种杂乱无章的刺激性因素所牵引的自动反应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格林所依赖的fMRI技术是无法扫描到这种差别的,把基于不同的背景知识和实践经验的自动反应都处理为是不可靠的,在根本上是忽略了双重模式迭代互动的重要性。
四、结 论
格林借助fMRI技术探究人们面对电车难题做出不同的道德判断时大脑究竟是如何运行的,他提出道德判断的双重进程模型以解释道义论判断和后果主义判断所依赖的不同心理进程,并进而得出一个规范性的结论说,由自动的情感进程优先支持的道义论判断,较之于由有意识的推理进程优先支持的后果主义判断是缺乏可靠性的。笔者认为格林这种基于神经科学的研究来解决规范性问题的论证最好应被理解为知识论上的拆穿论证,即并非不合理地跨越是与应当的界限,直接以经验证据证明道义论是错误的,而是将新的研究手段得出的经验证据与在他看来广为接受的规范性前提相结合,对道义论判断在揭示真理上的可靠性提出新的质疑。在笔者看来,这一研究为道义论和后果主义之间的传统争论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尝试揭示出不同类型的道德判断的形成机制,以及在形成过程中究竟是对情境中的哪些因素表现出敏感,这对批判性地反思与调试我们的道德判断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必须注意到这个拆穿论证中存在的问题。就其经验性前提来说,某些道义论判断和自动的情感进程密切相关,并不足以说明一般意义上的道义论判断就是情感进程的产物。而且他以缺乏反应性态度的病态人群为例也并不能揭示后果主义判断所涉及到的推理、慎思进程的本质,反而有将其简单化的倾向。就其规范性前提来说,格林对情感进程为何较之推理进程缺乏可靠性也尚未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他的解释一方面有可能把问题引向一个纯粹的规范性问题,即可靠的道德判断究竟应该对情境中的哪些因素做出反应,而这与神经科学的实验结果是无关的,也就消解了这种研究所具有的规范意义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当他把面对陌生问题时的自动反应都处理为不可靠时,也忽略了同样是直觉反应,但是由于背景知识和实践经验上的差异,其内容和可靠性也会大相径庭。因此,虽然格林的双重进程理论对探究规范性问题具有启发意义,但就目前看来尚不足以对后果主义和义务论之争做出实质性的推进。
[1]Nagel,T.Ethics Without Biology[A].Nagel,T.Mortal Questions[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2]Foot,P.The Problem of Abor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A].Foot,P.Virtues and Vices:And Other Essays in Moral Philosophy[C].Clarendon Press,1967,19-32.
[3]Thomson,J.J. The Trolley Problem[J].The Yale Law Journal 1985,94(6):1395-1415.
[4]Kamm,F.M.Intricate Ethics:Rights,Responsibilities,and Permissible Harm[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5]Greene,J.D.Beyond Point-and-Shoot Morality:Why Cognitive (Neuro) Science Matter for Ethics[A].Liao,S.M (ed.),Moral Brains:The Neuroscience of Morality[C].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119-149.
[6]Greene,J.D.The Secret Joke of Kant’s Soul[A].Sinnott-Armstrong,W.(ed.),Moral Psychology:The Neuroscience of Morality[C].Cambridge:MIT Press,2008,35-79.
[7]Liao,S.M Morality and Neuroscience:Past and Future[A].Liao,S.M (ed.),Moral Brains:The Neuroscience of Morality [C].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1-42.
[8]Kamm,F.M.Neuroscience and Moral Reasoning:A Note on Recent Research[J].Philosophyamp;Public Affairs,2009,37(4):330-345.
[9]Kahane,G. Intuitive and Counterintuitive Morality[A].Justin D'Arms and Daniel Jacobson(eds.),Moral Psychology and Human Agency:Philosophical Essays on the Science of Eth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9-38.
[10]Darwall,S.Getting Moral Wrongness into the Picture[A].Liao,S.M (ed.),Moral Brains:The Neuroscience of Morality [C].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159-160.
[11]Berker,S.The Normative Insignificance of Neuroscience[J].Philosophyamp;Public Affairs,2009,37(4):293-329.
[12]Woodward,J.,Allman,J. Moral intuition:Its neural substrates and normative significance[J].Journal of Physiology-Paris,2007,101 (4-6):179-202.
[13]Bales,R.E. 1971. Act-Utilitarianism:Account of Right-Making Characteristics or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J].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1971,9(3):257-265.
[14]Narvaez,D.The 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Some Counter-Intuitions[A].Sinnott-Armstrong,W.(ed.),Moral Psychology Vol.2[C].Cambridge:MIT Press,2008,233-240.
蔡 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进化论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15BZX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