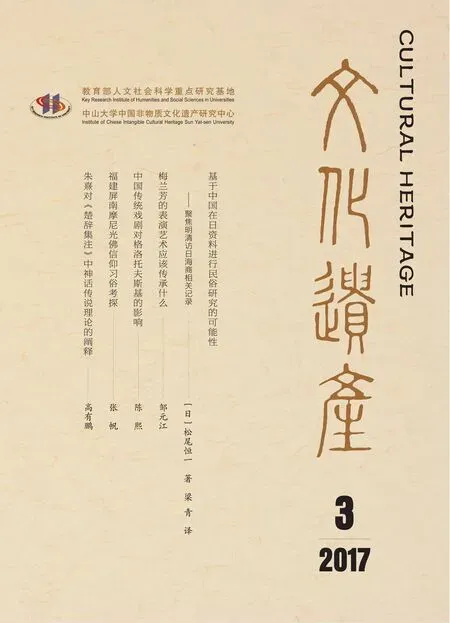基于中国在日资料进行民俗研究的可能性*
——聚焦明清访日海商相关记录
[日]松尾恒一著梁青译
基于中国在日资料进行民俗研究的可能性*
——聚焦明清访日海商相关记录
[日]松尾恒一著梁青译
民俗学是将国家,或是国家内某地区的生产生活及其相关文化实态和特质作为主题,通过田野调查等手段获取传承资料,进而推进研究的。但是也有不少以旅行和贸易为目的造访的外国人,通过他们的观察记录,留下了他们认为奇异的风俗,成为了珍贵的民俗资料。此外,本国的民俗相关文物通过贸易等合法途径,或是由偷盗、掠夺等非法途径流向国外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而这些资料的存在往往被人们忽视。清代,中日间并未建立国交关系,但从大陆造访长崎的海商带来了生丝、砂糖、鹿皮、中药等产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赛龙舟、妈祖巡行等中华文化也传到了长崎,日本人和华侨也继承了这些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在清代唯一一个与日本进行贸易的荷兰也留下了对清代海商的贸易、生活的记录。本论首要考察的是日本人对明末至清代造访日本的中国、荷兰海商的记录,以及访日欧洲海商和天主教传教士对清代海商的生活、信仰等民俗方面的记录。在此基础上,超出以往对一国或者一地区进行研究的民俗学,而对国际关系中某地区的生活特质进行探索,探寻新的民俗学的可能性。
在日明清资料 明清海商 海外民俗资料 妈祖信俗
一、关于在外资料的诸问题
在研究一国的历史和文化时,以纸、木、竹、石为载体的国内的文献和绘画往往是最重要的资料。如果把考察的时间段扩大到文字尚未诞生的史前时代,对出土资料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便凸显出重要价值,甚至还要考虑到一些重要资料存在于海外的情况。
在人文科学中,民俗学以民间习俗、生产生活、地域社会以及信仰为主要研究对象。民间习俗存在于包括史前时代在内的各个时代,探寻每个时代的民俗以及人们的生活状态,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但狭义的民俗学往往聚焦于现代生活的实态和特质,对那些难以呈现于文字的民众的文化,以田野调查的形式搜集资料并进行分析,其目的在于通过重视来自过往的传承来理解现代。
在这一点上,民俗学与通过田野调查、将现代的诸事象资料化、并进行分析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类似。而在重视与过去的关联性这一点上,又与历史学有联系。在民俗学中,又有故事、传说等民间文学,各地区的音乐、舞蹈、戏剧等演艺,它们分别被作为文学和艺术进行分析,在文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地方上的民众文化,在日本和台湾地区被称为“无形文化”,在中国大陆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都强调其文化方面的价值,与之相关的“无形文化财”、“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等专有名词也在各国确定下来。这些民俗文化成为了各国的标签,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提升国家形象、形成观光资源方面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各国都对民俗文化竞相宣传、保护和培育。
本论暂且不讨论民俗在现代风起云涌的各种状况,而是对保存于海外的文献、绘画等有形资料(遗物与出土资料)在民俗学上的运用进行探讨,以寻求民俗研究的新的可能性。为此,举出在日本的部分中国相关资料进行讨论。
在进入正题之前,必须要对海外资料的分类进行说明。海外资料大体而言可以分为三类。
A、外国人到本国进行探险、旅行,或是以贸易为目的的造访,从而对本国的习俗等进行文字和绘画记录的资料。
B、以探险、旅行或者贸易目的出访外国的人,他们被外国政府以管理的名义进行调查询问,记录下的本国习俗,或是外国民间人士因好奇、兴趣等记录的资料。
C、原本存于本国的文物,在某个时期流向外国,被外国的个人、单位、国家所占有的资料。
以上三类中,在现代往往成为国际问题的是C类的部分资料,它们常以战争的战利品、掠夺品,或者偷盗的形式被带到海外,被卖到博物馆、美术馆,并为这些机构所收藏。
如果将C类资料进一步细分,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C1、由于跨国贸易造访外国的商人或者旅行者,以购买美术品、书籍等形式(至少在当时是)合法出境的资料。
C2、通过战争等方式以战利品的形式掠夺至国外,或是在战争或内乱状况下由本国人卖到国外的资料。
无论是C1还是C2,都是由本国流向外国的资料,日语称为“海外流出资料”,或者用最新的名称“在外日本资料”来概括,它们都是本国历史研究以及文学、美术等文化研究的对象。
日本把目光投向海外资料,并进行收集、研究,在国家层面上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由国立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进行。他们调查了欧美的美术馆和大学所收藏的日本文学书籍和画卷,以照片的形式记录下来,作为日本文学的新资料介绍回日本,并着手研究。在2000年以后,笔者所任职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国立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也开展了“在外日本资料研究”,对欧美进行了有组织的调查、研究。海外各个机构虽然有所差异,但他们的研究者或多或少都对这些资料有所研究。因此对海外日本资料的调查,往往以同欧美博物馆、大学共同研究的方式组织。
对海外资料进行研究时,与国内资料研究相比最大的差异在于,这些资料都是由日本生产的,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时间、以怎样的方式流向海外,这方方面面都必须调查清楚。它们不仅要作为本国人文科学研究的资料使用,也应当作为国际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资料。
本国的人文科学,就日本的历史学方面而言,从古代至中·近世时期(隋唐至清代)的历史,常常使用大陆·朝鲜半岛的资料进行研究,这在二战以前就开始进行了。中世末期以后(明代后期·清代以后),在日本列岛、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之间,倭寇等跨越国境的海上活动日益频繁,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也频频进入中国和日本,这些事件在亚洲史中所占比重很大。因此在研究时需要采用东亚、欧洲的资料,在西欧史和东洋史背景下思考日本史,在21世纪以来已经达成普遍共识。
江户时代(清代)以后,日本实行锁国政策,长崎成为与荷兰和清朝进行贸易的唯一港口,长崎的生活文化受到他们强烈的影响。端午节的赛龙舟、中元节(水陆道场)等的先祖祭祀活动等,都在长崎民众间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民俗文化。
清代海商的主要贸易品是砂糖和生丝,这对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有着重要影响。当时的日本没有砂糖精炼技术,只能依赖进口。
以研究本国文化为中心的民俗学,其目的是对本国的地域特色,或者“日本”这一地域内的日本人(生长于日本讲日语的日本人)的民族特色进行探讨,在本国内进行田野调查(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无意识地排除了外国的影响),以阐明日本人的生活实态和生活文化的特色。
但是,在日本也有像长崎一样,从清代以后受到中华文化强烈影响的地区,近代(1860年以后),日本开国后,横滨和神户聚集了一批从长崎迁来的华人,再加上通过来访的欧洲船只抵达日本的华人,在两地也形成了华侨社会。
在长崎县平户和五岛列岛,从禁教时代起就潜藏着天主教的信仰和礼仪,可以说传承着亚欧间交流所形成的地域文化。在明末以后,中国、欧洲的文物以及佛教、天主教等宗教,对日本人的民俗、精神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推进这些民俗文化的研究,不能仅仅关注本国的传承和文献记录,要在看到日本人记录的外国人在日本生活的记录的同时,也关注他们所记录的关于日本的文献与绘画。要探索以更广阔、更国际化的视点来追寻民俗文化特质的可能性。
二、中日欧关系网中明清海商在日贸易与生活
在中国明末清初的时代,日本在京都室町的以足利将军为首的武家政权逐渐衰落,各地大名割据,进入了战火纷飞的“战国时代”。
日本国内的动乱,从16世纪中叶持续到17世纪初,在江户建立幕府的德川将军最终掌握大权。期间,欧洲进入了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人先后经由中国来访日本,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和西方人接触。日本进入这一新时代,与中国也有密切的关系。
经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最早来到中国的是葡萄牙人,他们在16世纪时,以澳门为据点进行的各种活动,被明王朝所承认。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就是日本,而带领他们前往日本的,是明代海商“王直”。
王直在日本被称为“五峰”,亦是拥有庞大船队的海盗。他在日本以平户作为据点,后来平户成为明代海商、葡萄牙海商以及耶稣会的天主教传教士的据点,变成一个国际港。
欧洲航海技术的进步和大型船只的建造,以及向南、向东航路的发现,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动荡。他们试图入侵中国大陆、日本,但由于国家机关和军队的存在而未能如愿,但那些村落、部族等小规模的共同体所在的群岛,如菲律宾、台湾等地区很快就被西班牙、荷兰占领。他们以贸易的形式榨取当地的物产,驱使当地人进行低报酬的强制劳动,甚至将当地人作为奴隶,贩卖至国外。
期间,中国国内也发生了大动乱。满族人推翻了汉族统治的明朝,建立了清朝,郑成功等人存有反清复明之念,与清王朝持续对抗。日本把中国的这一变化称为“华夷变态”,即人口占据多数的汉族“华”,被人口占少数的满族“夷”所统治。对这一激烈变化,日本保持着高度警惕,为了避免战火的波及,甚至想要中断与中国的联系。但日本需要从中国进口高级生丝和砂糖,因此仍需要依靠中国的海商。这些海商中,很大的一股势力就是郑芝龙、郑成功等人率领的以复兴明朝为目的的大船队。日本同时与清代海商和以台湾为据点的郑氏政权保持着贸易上的往来,购买生丝、砂糖、鹿皮等产品,但在政治上保持着不关心不参与的立场。
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除了海商,还派遣耶稣会、方济各会等天主教传教士前往中国和日本进行布教活动。他们把亲身探访到的国情,用书简的形式传到梵蒂冈的罗马教皇、西班牙和葡萄牙,可以说是发挥了间谍的作用。
耶稣会传教士Matteo Ricci(中文名利玛窦)曾到过北京,在1601年被明朝万历皇帝召见,在那以后,耶稣会传教士同在日本时一样,在对贫民进行救济的同时宣传教义,他们在中国平民中的信徒人数急剧增加。
这一世界史上的重大变化中,不仅欧洲的海商,中国和日本的海商也曾带着传教士前往东南亚等地进行贸易活动。
欧洲人凭着大帆船走上了世界舞台的前台,在海外发现新大陆和岛屿,不仅在当地进行贸易活动,还企图将它们殖民地化,编入本国领土。而他们的野心能否得逞,与当地原住民是否有被称为国家机关的政治、经济系统,是否有一定程度的军事力量有关。
中国和日本由于有统一的国家机关和较强的军事力量,欧洲人几乎无法展现他们对领土的野心。而与此相对的,一些仅仅由几个集落或部族形成小规模共同体的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就遭到了欧洲人的占领。
日本对于欧洲人对领土的野心一直抱有警觉,尤其是天主教信徒的增加,让他们产生了佛教、神道等传统宗教信仰被否定的危机感。于是他们把与天主教关系密切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赶出国门,将与中国和信仰新教的荷兰两国的贸易港设在九州北部的长崎,并要求他们不得进行传教活动。他们与中国和荷兰保持联系,一方面是对生丝、砂糖等商品有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解东亚、东南亚乃至欧洲等世界局势的重要性。此外,对洋枪、火炮、手榴弹等武器的关心也促使他们与外界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而对于明清海商而言,日本的白银、海参等产品是他们所需要的,航海贸易虽然有很大风险,但所得的利益非常惊人。
乘坐欧洲帆船或者中式平底帆船来访的海商,在海上遇到船只时,如果判断对方比自己弱小,就会化身为海盗进行抢夺。为了避免受到海盗的威胁,船上都会安装数量不等的大炮,这也使得船体越来越大,其结果是贸易品的装载量也随之大幅增加。这也促使多国间贸易、经济活动更加活跃。
与日本继续进行贸易的清代商人在长崎进行商业活动,其中的一些情景被石崎融思(1768-1846)记录在《唐馆兰馆图》和《长崎名胜图绘》中。
除了《唐馆兰馆图》之外,石崎融思还有不少描绘长崎的中国、荷兰等异国情调的绘画。这些美术作品一方面被艺术爱好者所喜爱,另一方面,这些画具体描绘了清国船只从长崎港入港,通过驳船搬运货物,接受日方检查,以及他们在长崎的商贸活动、在异国的生活状况,可以说是珍贵的历史、民俗资料。这些绘画对于日本来说,可以作为在日外国人活动的资料,对于中国来说,是研究本国海外交流史中,本国人在海外的活动情况,受到何种待遇的研究资料。在两国民俗研究中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包括政治史、经济史、各时代的文化,一般都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畴。但从这些资料在探寻异国生活的实态及其精神,重视它们与现代的联系,寻求其特质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来看,作为民俗研究的资料也是非常重要的。
比起以上观点,更重要的是明代后期以来,欧洲进入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的研究不再是两国间的研究,而是围绕日本列岛-中国大陆、台湾、菲律宾、东南亚诸岛、欧洲多个国家展开的多国多地域间关系的研究。幅员辽阔的中国,自古以来就和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甚至伊斯兰圈的中东、西欧国家打过交道,在欧洲凭借航海技术进入东亚,主导国际关系的时候,日本也加入到这个关系网中来。
在这个新时代,在考察清国人在日本的生活时,对比同样得以在日本继续进行贸易活动的荷兰人的生活情况,可以对他们在异国的活动、生活的特质有更明确的认识。同样,在对海外华人华侨的生活和文化进行研究时,对当地其他外国人予以关注,可以更好地理解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对华人华侨的生产生活状态也能有更清楚的认识。
三、清代海商在长崎的生活与信仰
在日本的清代海商,自1689年(元禄2年)以后,被限定在位于长崎郊外的十善寺乡(现十善寺町)的“唐馆”居住。他们在这里与日本人进行贸易和日常生活。
唐馆里和他们的信仰相关的天后宫、土神堂、观音堂十分引人注目。(见彩页图1: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唐人屋敷景》(唐馆图景))
其中,对于冒着被海盗掠夺和暴风雨的危险航行到日本的清代海商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祭祀有护佑航海安全的妈祖神的天后宫了。他们在天后宫进行妈祖诞等祭祀活动。
唐馆建立以前,有被称为“唐寺”的四座寺院。明清海商根据出身地分别归属于各寺院。
崇福寺(福州寺)——福建北部
兴福寺(南京寺)——上海、浙江
福济寺(泉州寺(漳州寺))——福建南部、台湾
圣福寺——广东
在唐寺中,海商们进行葬礼,在清明节、中元节时进行祭奠先祖的活动,日本方面尊重他们的信仰和习俗,并未禁止这些祭祀活动。
与此相对,在位于长崎的荷兰人居留地——出岛,一切标示出天主教身份的或是让人联想到天主教的物品和活动均被禁止。这种禁令非常严格,甚至命令在当地死去的荷兰人必须把尸体沉到大海中。当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此非常不满*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General)Antonio van Diemen在宽永19年(1642年),于巴达维亚(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旧称)用日语向幕府写的信中有以下文字:日本にて、おらんた人相果申たる時の爲に御座候條(中略)、死骸を海底にしづめ申事(中略)、其上何國にても死骸を海底に沈め申たる例、無御座候へば、四方之風聞無面目次第に候、就中以下之者、口のさがなき御事に候へば、水主共國々へ罷渡り、日本の 御仕置、かやうなる稀代之御事なと申候へはいかゝ、(オランダ人の死者を海底に沈めていることを、オランダ船の水夫たちが故国に戻ったときに言いふらすこともあり、その時に日本の悪評が立つのはよくない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村上直次郎译《長崎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附录、ファン·ジーメン(van Diemen)の書翰)、岩波書店,1956年)意思是希望对荷兰死者进行妥善埋葬。对于荷兰人的请求,日方同意承应3年(1654年)起,荷兰人可以和中国人共同使用悟真寺的公墓。关于平户、长崎的荷兰人墓地,可以参照[日]宫永孝的《日本におけるオランダ人墓》(法政大学社会学部学会《社会労働研究》35(2),1989年2月),宫永的研究中记录整理了墓碑铭,是非常重要的研究。,但为了在日本的贸易利益,最终还是遵从了要求。(见彩页图3:长崎荷兰寺院中的墓地(稻佐国际墓地))荷兰人在长崎出岛建立居留地之前,在平户建有商馆,那里是他们的贸易据点。他们在这个据点大约经营了30年,而后被命令转移至出岛。之所以有这样的命令,是日本规定将长崎作为唯一通商港口,为了便于管理外国人,要将他们迁往一处。但在实际操作上,却是由幕府发现商馆的一处建筑上用西历(天主教历)标示建成的年份,于是勒令其搬迁,终于在1641年5月,随着葡萄牙人被赶出国门,荷兰人转移到了出岛。
另一方面,清代海商不仅在长崎的城内,而且在诹访神社的运营方面进行了资金援助。诹访神社是为了抵御西欧的威胁,保护日本的目的而建造的,为了表示对清代大陆海商的感谢,诹访神社也为他们祈求航海安全。在诹访神社的年节活动中,规模最大的是一直持续至今的“長崎くんち”,由于清代海商对神社运营的贡献,也允许他们参观活动。活动内容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妈祖巡行和蛇舞都是由长崎町人表演的,对于日本人来说,充满异国情调的清代文化很有魅力*黄宇雁:《長崎諏訪神社と唐人生活》,同志社大学《日本語·日本文化研究》,第13号,2015年3月。。
当时在长崎的清代海商习俗中,“彩舟流”非常引人注目。在《长崎名所图绘》(见彩页图4)中,绘有唐馆内燃烧中式平底帆船模型以及对船跪拜的清代海商,四周还有因感到稀奇而围观的日本人。有趣的是,在另一幅画《长崎港南京贸易绘图》(早稻田大学藏)(见彩页图5)中,在海边也有清代商人进行同样的仪式,同样也有日本人围观。在旧历7月进行的盂兰盆会上,日本各地都有被称为“精灵船”的稻草船,以及被称为“灯篭流し”(放河灯)的活动。联系这一活动,可以推测清代海商可能是在进行先祖祭祀活动。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绘画《彩舟流唐船图》(天保15年(1884年))(见彩页图6)中,记有“惣乘组灵二百八人”“灵祭执行、南京兴福寺、福州崇福寺、漳州福济寺”等文字,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彩舟流”是唐寺的僧侣主持祭礼的佛教活动,其目的是为了祭奠在日本死去的清代海商的灵魂。
从妈祖祭祀和祭奠先祖的活动来看,在长崎,荷兰人的宗教信仰及相关的仪礼活动被严格禁止,与此相对,清代海商则被允许进行祭祀活动。
在这里,我们明显看到一种转变,即自古以来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近世=中国清代以来,虽然仅是长崎一地,但中国文化在庶民层面上开始被直接接受,这与以往的隋唐至明代的中国文化的接受是有很大不同的。
在明代以前,日本朝廷、贵族、武家和大寺院神社有专人负责与大陆、半岛进行贸易的事务,大陆的文物、知识作为先进文化被接受,然后再传导至庶民阶层。隋唐时期宫廷的燕乐首先来到日本宫廷成为“舞乐”,散乐演化成能剧和狂言,宋、明代的佛教文化也是从日本寺院进入上流武家社会,茶道和花道的起源就是很好的例子。
而明代后期以后,生丝、砂糖等产品直接被海商带到日本,对日本人的生活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异文化的接受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进入了庶民层面交流的阶段。
特别是在作为贸易地和居留地的长崎,中国人的民俗文化影响很大。清代,端午节的赛龙舟习俗传到了长崎,在长崎港沿岸各地区都有进行。笔者调查的一处临海的林地,赛龙舟的活动的主体是渔民,他们在港口装饰大渔旗(渔业丰收时装饰在船上的旗子),乘龙船争先抢渡到港口的龙神社,以祈祷渔业丰收。中国的民俗文化传到日本渔村,发生了本土化,成为了渔业相关的习俗,作为渔村的民俗活动一直传承至今。
四、日欧贸易相关资料中的明清海商
在日本,不仅有日本人记录的明清海商的情况,来到日本的欧洲海商、传教士等,也在他们关于天主教的资料中留下了对当时中国的信仰礼仪的记录,这也成为了重要的民俗资料。
妈祖信仰始于10世纪下半叶,宋代福建省的官吏林愿的七女儿默娘的传说。从近海从事渔业活动的渔民,到出海进行贸易的商人,在东海、南海的沿海地区常常见到妈祖的信仰者。明代的郑和受到永乐帝命令,于永乐3年(1405年)至宣德8年(1433年)期间,赴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半岛、非洲等地七次大航海,他对妈祖的信仰十分深厚。他第一次出航是在南京,从南京下关的惠民河出发,两年后的永乐5年(1407年),在南京修建了天妃宫。
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其重要目的是与周边国家构筑朝贡关系,扩大册封体制。关于郑和的事迹,被称为《郑和碑》的《天妃灵应之记》碑以及马欢的《瀛涯胜览》(1416年)均有记载。他作为中国去往欧洲的先驱,从东洋远赴西洋。在此后大约过了一个世纪,欧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他们在东南亚、中国、日本等设立了贸易据点,欧洲开始逐步掌握世界贸易的主导权,中国设想的主导西方贸易的愿望没能实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明代不与结成朝贡关系以外的国家进行贸易,一方面是郑和以后,由于倭寇等原因,实行了海禁等一系列锁国政策。
欧洲人进入东亚,不仅是通过海商进行贸易,还觊觎各国的领土。耶稣会、方济各会等天主教的传教士或是以个人身份,或是受到葡萄牙、西班牙的资助来到这里,刺探布教国的内情并记录下来,向梵蒂冈的罗马教皇和资助他们的国家报告。
传教士由于身份和职务因素,对布教地区的信仰、祭祀、宗教相关的记录最为多见,但与此同时,作为欧洲人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中日当时的习俗的记录也是很有价值的民俗资料。
最早造访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士是耶稣会的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他受葡萄牙王若奥三世的委托,来到印度果阿,1549年从广州乘中国海商的船从日本南九州萨摩(现鹿儿岛县)登陆。
沙勿略在萨摩期间,曾向果阿的圣保罗学院写过信,信中对中国船航海的情况记录,特别是船上妈祖祭祀的情景尤为引人注目。
[A]cemlegoas de Malacacaminho da China, tomamoshumailhaem a qualnosapercebemos de lemes&outra madeira necessaria para as grandestempestades, & mares da China. Depoisdistofeito, deitarãosortes, fazendomuitossacrificios, &festasaoidolo, adorando-o muitasvezes, &preguntando-lhe se teriãobomvento, ounão: &sayo a sorte que aviamos de terbom tempo, & que nãoaguardassemosmais: &assilevamos as ancoras, & demos à vela todos com muitaalegria, osgentiosconfiando no idolo, que levavão com muitaveneraçãoem a popa do navio, &candeasacesas, perfumando-o com cheiros de pao de aguila: &nosconfiandoemDeos, Criador do ceo& da terra, &emIesu Christo seufilho, porcujoamor&serviço, vinhamos a estaspartes, para acrecentarsuasantissimafé.
Vindonossocaminho, começarãoosgentios a deitarsortes, fazendopreguntasaoidolo, se o navioem que hiamosavia de tornar de Iapão a Malaca, &sayo a sorte que irião a Iapão, mas que nãotornarião a Malaca, &aquiacabou de entrar [fol. 8r.] a desconfiançanelles para nãoirem a Iapão, senão de invernarna China, &aguardar outro anno. Vede o trabalho que podiamoslevarnestanavegaçam, estandoaoparecer do demonio, & de seus servos, se aviamos de ir a Iapão, ounão, pois o que região, &mandavão o navio, nãofaziãomais do que odemonioporsuassorteslhedezia.(LETTERFROMFR.FRANCISCOXAVIERS.J.TOTHEJESUITSINGOA,Kagoshima,November5, 1549)*基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日本関係海外史料イエズス会日本書翰集》原文编之一(1930年,东京大学发行)。
虽然在沙勿略眼中是“异教徒”的习俗,但他仍然进行了详细记录。在被搬到船上的“偶像”前,中国船员一直供奉贡品和做“礼拜”。这里所说的偶像应当是指妈祖神(虽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观音或者龙王的可能性),他们对妈祖神求签问卦,直到签上预示航海安全,才出发前往日本。在航海期间,还要向妈祖询问海上的风的情况,从这里我们也了解到他们乘坐的是帆船,在船内祭祀中,关于风的问卜也是十分重要的。罗盘的使用,天体观测技术等中国的航海术,在郑和的时代就已经被践行,虽然他们有先进的航海术,但航海时仍然需要祈求神灵的加护,可见航海本身的危险性。
另外,当时也有漂流到中国的日本渔民,他们乘坐福州船返回日本时,也记下了他们看到的航海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到,除了妈祖神以外,他们还对罗盘进行祭祀(宝历元年(1751年)12月《唐国福建省江致漂着候奥州南部之者六人口书》(长崎史学习会编《长崎关系史料选集》第一集,平成16年(2004)年)),这种生产生活技术与信仰祭祀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注意*[日]松尾恒一:《历史与现代:清代华商的航海与妈祖信仰——在长崎旅日华侨社会中的传承与现状》,《2016年国际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16年10月,第211-226页。(见彩页图7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华夷通商考》“福州船图”)。
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祭祀妈祖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没有留下太多详细记录,但欧洲资料和日本资料却补足了这一点,这是很有价值的。与此同时,这些资料记录了身处异文化环境的人们看待异国习俗的感受,以及他们如何接受这些事项,从文化相对化的角度看也是宝贵的资料。
日本各地区的大名出于对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洋枪大炮,以及欧洲红酒等新奇事物的兴趣,在最初的时候允许耶稣会、方济各会的天主教传教士布教。大约经过了几十年时间,他们逐渐察觉到欧洲国家对日本领土的野心,于是日本转向了锁国政策(1639年(宽永16年),禁止葡萄牙等国的船入港)。除中国的海商以外,在欧洲仅同荷兰保持贸易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国内对天主教徒以及转入地下活动的传教士进行严密搜寻,将他们赶出国门甚至处死(例如1597年的“26圣人殉教”等等)。
由于这种警戒心的蔓延,日方开始怀疑中国海商中混有天主教徒,甚至对来到长崎的中国船只内部进行搜查。
在日本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从中国收购生丝、砂糖、鹿皮,然后转卖到日本。因此他们与清代海商是竞争关系,荷兰商人在日本写下的日记中,往往会有关于清代海商动向的记录。清代海商被怀疑混有天主教徒,并在长崎接受检查的事情也被记录下来。
例如长崎荷兰商馆的Jan van Elseracq的日记,在1664年9月22日有“早上,购入商品若干,以现金卖出。各种中国织物,由于中国人大量投放市场(导致价格暴跌),蒙受很大损失。”这样的记录(《长崎荷兰商馆日记》第一辑,村上直次郎译,岩波书店)。明代海商是荷兰在日本的贸易对手,驻留长崎的荷兰商馆,密切关注着从长崎入港的中国船,包括他们船长和船员的动向。
当时的中国海商中,郑芝龙的势力很大,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他的记录也很详细。根据《长崎荷兰商馆日记》记载,江户幕府掌握了郑芝龙等海商是天主教徒的情况,由于这一嫌疑,郑芝龙的船队到访长崎时,被要求登船检查,并对船员进行了拷问。散播明代海商是天主教徒的消息,对于荷兰商人来说,可以打击他们的贸易对手,因此对日记中的内容难以完全相信。但无论如何,至少可以从侧面表明天主教在中国有很多受众*西班牙奥古斯丁派传教士Juan de la Concepción在1789年菲律宾马尼拉所写的《Historia General de Philipinas》(菲律宾诸岛通志)第6编12章21节中,有Tching-tchi-long(郑芝龙)原本是渔民出身,身份低微,在马尼拉接受洗礼,获得洗礼名(圣名)Nicholas,其后前往日本,成为海商和中国舰队的司令官的记载(参照[日]村上直次郎译《バタヴィア城日誌》3,附录二《フィリピン諸島通志》「台湾略記」,平凡社,昭和50年(1975年))。。
基于这一事实,江户幕府怀疑有信奉天主教的清代海商,把玛利亚像伪装成妈祖像带入日本或是安放在船内,也是情有可原的。
中国海商中,除了郑芝龙以外,还有被确认为天主教徒的。平户英国商馆馆长Richard Cocks写的“Diary kept by the Head of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Diary of Richard Cocks, 1615-1622”(《英国商馆长日记》)中有一封他从长崎寄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信(“RICHARD COCKS TO THE EAST INDIA COMPANY NANGASAQUE, MARCH 10, 1619[20], WITH AN ENCLOSURE Nangasaque(长崎)in Japan, the 10th of Marche”)。信中记载了郑芝龙之前,继承李华宇在平户进行贸易活动的是海商李旦(Andrea Dittis),他在弟弟李华宇死后,负责中日间贸易的管理,欧洲海商能参与到中日间贸易,也是经过他的介绍(1620年3月10日)。
And truly to my hartesgreefe I am eavery day more then other out of hope of any good to be donne in Japon, except trade may be procured into China, w’ch I am not yet out of hope of. Although Capt. Whaw(李华宇=李旦之弟) of Nangasaque(长崎) be dead, whoe was a cheefe dealer hearin, yet his brother, Capt. AndreaDittis(李旦) of Firando, telles me it is concluded vpon, & that he expectes a kinsman of his to com out of China w’th the Emperourspasse, promesing to goehymselfew’th me in person, when we haue any shipping com to goe in; for in Japon shipping we caotgoe for China. This Andrea Dittis is now chosen capten&cheefec’ander of all the Chinas in Japon, both at Nangasaque, Firando(平户), & else wheare, & I trust in God will proue the author in soehappie a matter as to gett trade into China.*基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日本関係海外史料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原文编之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
郑和七次下西洋以后,明朝政府为了防范倭寇(中国、日本、朝鲜半岛海域跨国活动的海盗),采取了海禁政策。期间欧洲人开始进入东南亚和东亚,一些海商具有与欧洲人交涉的能力,有率领船队出海航行的实力,他们协助欧洲商人,进行中日及东南亚之间的贸易。
在明清交替之际,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为了复兴明朝,与荷兰和清政府交战。自明朝后期以来,他们以荷兰、英国商馆所在的日本平户为据点进行活动,继王直(五峰)、李旦之后,成为拥有战船的大海商。在平户领主松浦氏的认可下,他们通过贸易获取经济利益,为与荷兰和清政府的作战积累军费。
近年来,关于明清代的中日贸易史,包括长崎的明清代海商的动向,中国历史学界也有很多研究,但据笔者观察,关于日本方面的情况,研究得还不是很透彻。
例如林观潮在2011年发表的论文《明清时期闽商往来长崎商路之旁考》中有以下论述:
在江户社会这样的情势下,长崎也加强了对来航商舶的管制,査禁所有与天主教相关的物品。大陆商人信仰的航海保护神妈祖,在形象上与天主教圣母玛利亚有相似之处,容易引发误解。这样的情况将危及他们的人身安全和经济利益。为了证明自身与天主教没有关系,大陆商人逐步把供奉妈祖的妈祖祠堂改建成了佛寺。而德川幕府为了根除天主教信仰,也鼓励建立佛寺,宣扬佛教。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闽商与其他大陆商人一样,展开了寺院的创建与经营。*林观潮:《明清时期闽商往来长崎商路之旁考》,《闽商文化研究》2011年第2期。
文中指出江户幕府因清代海商祭祀的妈祖与圣母玛利亚相似,而怀疑他们信仰天主教这一点非常重要,可惜没能举出史料予以证实。林观潮还提到“大陆商人逐步把供奉妈祖的妈祖祠堂改建成了佛寺”,将妈祖的祠堂改建为佛寺,在史实上也无法确认。还有 “德川幕府为了根除天主教信仰,也鼓励建立佛寺,宣扬佛教”,这一理解虽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此之前日本为了让全体国民证明自己并非天主教徒,实行了“寺请制度”,即国民必须归属于某个特定的寺院或佛教宗派。这一制度也运用到了居留长崎的中国人身上,这才兴建了唐寺(《长崎实录大成》卷五、卷六“寺院开创之部”上中下)。
在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等“唐寺”中,不祭祀佛和菩萨,而祭祀妈祖和关帝等中国民俗神,是与以往日本的寺院的重大差异。从唐寺的兴建目的来看,主要是为了应对天主教势力的入侵,在清代商人中实行“寺请制度”。因此充分尊重他们的信仰,允许他们在唐寺内祭祀妈祖和关帝,这应当是基于史实的正确理解。
日本的佛教文化起源于隋唐时期的中国佛教,又与日本的神祇信仰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在中国的日本文化史、宗教史中达成了统一的认识和理解。近年来,也有中国的研究者考察了长崎的妈祖信仰与日本佛教的结合,发现了一些日本化的特色*林晶、陈凌菁、吴光辉:《文化传承的融离与回眸——以日本长崎的“妈祖信仰”为对象》,《东南学术》2015年第6期。。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不能说是错误的理解,但对于中国明清交替之际,围绕着中日关系的重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进入东亚、东南亚,形成新的国际关系,我们有必要综合各国的资料,进行细致分析,以得出更正确的历史认识。
五、结语:在国际关系视野下研究民俗文化的可能性
本论考察了有关明末至清代海商访日的日本文献和绘画资料,以及欧洲传教士、《英国商馆长日记》等欧洲海商对中、日、欧之间贸易和航海实态的记录。
明清海商带来的生丝、砂糖对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日本本土的甘薯也是1615年,由英国人威廉·亚当斯(三浦按针)奉德川家康之命,从琉球带回日本本土的。刚带回来时,是由平户的英国商馆长理查德·考克斯栽培,现在平户川内浦还留有“考克斯甘薯田遗址”。这里的甘薯被称为琉球薯,或者直接称之为薯。平户是日本本土在九州以北最早进行甘薯种植的地区。而甘蔗是日本现代重要的农作物之一。虽然在明代至清代进行砂糖贸易的时间不长,但对日本人的饮食生活有着重大影响。。对于中国生丝的流入,日本政府(江户幕府)为了保障本国生丝的流通和利益,于17世纪初制定了“丝割符制度”,以管理中国、荷兰海商的生丝贸易*与中国、荷兰进行生丝贸易的实态,以及丝割符制度对于日本对外政治、经济史的意义,可以参照[日]木崎弘美《糸割符制度廃止の幕政史的意義》,《駒澤史学》第34期,1986年1月。。这些外国人的贸易活动,对日本国内养殖桑蚕业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利益的大小与蚕农的生活密切相关。
清代海商的居留地虽然在长崎十善寺乡的唐馆,但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很大。端午节的赛龙舟和舞龙活动,被长崎的日本人(非华侨)继承,成为日本当地的民俗文化。长崎的华侨和日本人继承的中华文化,作为地区代表性的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当地的观光资源,在现代社会发挥着重要影响。
日本民俗学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生活方式向地方上、农村、渔村的扩散,都市民俗相关研究的比重逐渐增大。但民俗学研究的出发点仍然是关心前近代的传承,即与过去相关联的事象的重要性。
在这一背景下,民俗学一方面对地区文化的独立性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在其中发掘出不限于该地区的国家身份的价值,以推进研究。我们看到的德国民俗学、日本民俗学、中国民俗学、美国民俗学等,与历史和文学同样,是按照国别进行划分,基本是以本国的研究者为中心来进行研究的。但民俗学在通过田野调查进行社会研究这一点上,又与文化人类学在方法和主题上有相似之处。文化人类学最初是由于统治和支配殖民地的过程中,需要理解异文化社会,于是着力于分析社会组织、亲族关系的结构。与此相对,民俗学是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探寻国家存续的精神根源,寻求从过去到现在的连续性≈历史。从这一点看,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在研究的出发点上有着重大差异。
因此民俗学往往倾向于关注本国的国民,以国内的资料为中心进行研究。但事实上,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现代自不必说,在前近代,江户时期/明代后期至清代,民众层面的国际交流不仅在东亚,甚至扩展到东南亚乃至欧洲,这种交流(至少是在日本)对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此外在明末和清代以后,民众层面的贸易活动也对外国的民众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民俗文化,根据研究对象进行国际化视野的考察变得必要起来,要在本国与相关国家之间共享在各自立场上记录的文献、绘画资料以及实物资料(生活相关的遗物等),关注来自不同立场的叙述,进行综合分析。为此,在国际化的框架下进行共同研究也变得更加必要。
[责任编辑]王霄冰
松尾恒一(1963-),男,东京人,日本国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文学博士,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教授以及综合研究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国立千叶大学研究生院客座教授。梁青(1983-),男,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湖北 武汉,430062)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6ZDA16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K890
A
1674-0890(2017)03-0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