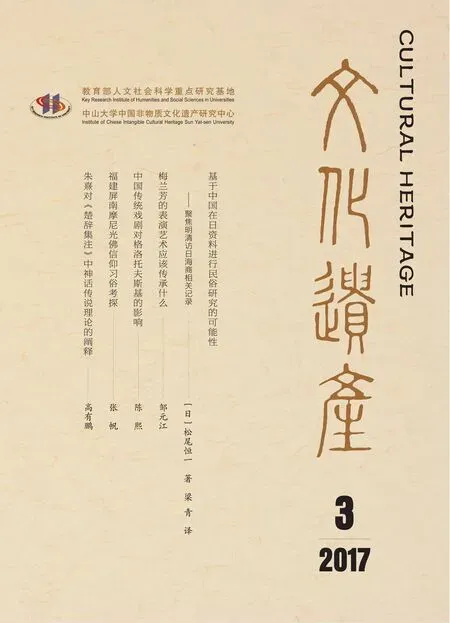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应该传承什么
邹元江
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应该传承什么
邹元江
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应该传承的核心精神是鲜明的时代感——革新精神。这种革新精神基于两个重要的前提,即既要高度重视对“传统表演艺术的积累”,又要“在艺术创造中勤于思考”。前者涉及支撑梅兰芳表演艺术圆满呈现的技术根底问题,即由梅兰芳的童子功奠基的唱念做打功法对他表演艺术的深刻影响,后者则强调创造的理性化思维,而不是被盲目的非理性的创造冲动所左右。这正是梅兰芳五十多年艺术生涯不断探索创新、引领时代潮流的秘诀所在。
梅兰芳 表演艺术 传承
梅兰芳表演艺术的核心价值演艺界、学界的看法大体一致,即是没有显著风格的“中和之美”。所谓“中和之美”也即不偏不倚、中庸平和,不刻意追求所谓的“风格”、“特征”。用梅兰芳的话说就是“我对于舞台上的艺术,一向是采取平衡发展的方式,不主张强调出某一部分的特点来的。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作风。”①梅兰芳:《梅兰芳全集》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正是缘于此,所以凡学梅兰芳表演艺术的人都深有体会,梅兰芳是很难学的,因为他没有画地为牢、自限陷人的“突出”特点。这就是为什么梅兰芳的入门弟子虽多,私淑者亦不少,但却很难说谁真正学到了梅兰芳表演艺术的精髓的根本原因。由此也可以说,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很难传承出具有划界意义的“梅派”——像学界、演艺界不加明证就轻易认同的那样。之所以没有划界意义的“梅派”,正像张君秋所说的,是因为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从开始到成熟,以至鼎盛时期,面貌是不一样的”。*张君秋:《梅兰芳先生的革新精神》,《戏剧论丛》1984年第3辑。这一点梅兰芳就曾说得很明白:“大家都说我演的戏常常改动。不错,我承认这一点……假如有一位多年不看我的戏的老观众今天再来看看,从剧本到表演,都会感到跟从前是大有区别了”。*梅兰芳:《梅兰芳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既然是“不一样的”,“跟从前是大有区别了”,那我们究竟应该对他的表演艺术传承什么呢?这涉及到诸多方面的问题:被传承者的不同层次、被传承者的根底深浅、应传承发扬的核心价值等。
一
梅兰芳一生都非常重视传承,无论是对拜过师的徒弟,还是对听他课的学生,哪怕是对临时请他指点的伶人,他都从不敷衍了事。魏莲芳大概是最早拜梅兰芳为师的,那年他14岁,梅兰芳30岁,时间是梅兰芳已誉满天下的1924年。最初的五年中,魏莲芳每天下午都去梅兰芳家学戏。魏莲芳说:“梅先生好客,他家里几乎天天有许多爱好戏曲的内外行朋友。而他就是在这般热闹的场合中,逢到我有什么问题请教,他总给我作详尽的解答;有需要示范之处,立即离座而起,一遍又一遍地将繁复的身段做给我看,非让我这个理解水平还很低的小孩儿,完全搞懂了才罢休。有时我和王少楼合演《打渔杀家》、《珠帘寨》等几出戏,他教我排戏,连王少楼也找了去,生旦两行都归他一人排,将他和余叔岩等同台的经验,一一分析给我们两人听。”让魏莲芳铭记一生的是,每逢周六、周日梅兰芳都有两场夜戏,梅先生常说“千学不如一看”,所以梅先生“每次演出,必定给我在正厅第三排留好座位,数年如一日。”当魏莲芳初次露演梅兰芳所教授的《红线盗盒》、《霸王别姬》和《廉锦枫》时,梅先生将自己的戏服送给了魏莲芳,并委婉地说:“小孩儿,我已置了些新的,这些留着也没用,你将就着穿吧,不必另费手脚置新的了。”其实魏莲芳非常明白,梅先生是知道他当时难以置办这些服装的,“这些东西都有八九成新,明明是他割爱给我的,只是他怕我不好意思接受,才特意如此说的。”更让魏莲芳感激之情无以言表的是,1929年,梅先生“听说我自行组班赴东北演出,缺少舞台上用的‘守旧’(‘守旧’在过去是头牌演员必备之物,价钱是极贵的),他就慨然将南通张謇送给他的全新蓝缎钩银梅花彩绣的大‘守旧’送给了我。”*魏莲芳:《追忆梅师》,《解放日报》1961年10月14日。这真是令人动容的对弟子的关爱之情。杜近芳对此也深有体会:“梅先生对我可谓是费尽了心思。给我说戏、走台步、分析人物,手把手地教,对我是有问必答,很不一般。致使我的师姐、梅派传人言慧珠对先生很‘不满’,她说,我们都是‘追’先生,而对近芳,则反过来,先生‘追’学生。”*杜近芳:《梅兰芳先生教我演虞姬》,《戏剧报》1984年第10期。李玉茹是1942年夏天开始每天到上海思南路梅兰芳的家中从梅师学戏。她说:“先生教我十分严肃认真。我记得当时单是《贩马记》中《哭监》的一个下场的两句唱词‘等待相公回衙转,把父含冤说一番’,他就不厌其烦地给我说了十几遍,稍不合要求,就要重新来过。”*李玉茹:《学习梅师的革新精神》,《人民日报》1981年8月6日。杨荣环是1948年春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当天在天蟾舞台拜见了正在那里公演的梅兰芳。梅先生不仅承担了家庭生活负担很重的杨荣环的拜师典礼费用,而且还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不仅担负他在上海学习期间的所有费用,还经常资助杨荣环北京家里的生活费用,让他能够安心学习。杨荣环说:“我住在梅师家,一连饱看了梅师两个多月的演出。梅师先后向我传授了《王宝钏》、《汾河湾》、《宇宙锋》、《醉酒》、《别姬》等戏……数月间,梅师时常是在演出后通宵达旦地与我畅谈。”*杨荣环:《艺术美来自心灵美——纪念梅兰芳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天津日报》1981年8月9日。沈小梅也曾动情地回忆说:“1953、1954两年,他在上海歇夏,每天吃过午饭就抽出一两个小时教我戏。不管天气多么炎热,梅老师汗如雨下,却从未间断过一天。他教会了我《醉酒》、《别姬》、《凤还巢》、《宇宙锋》、《奇双会》等戏。”*沈小梅:《忆梅兰芳老师》,《新华日报》1961年8月27日。关肃霜也曾回忆1960年在文化部举行的戏曲演员讲习班里,梅兰芳是如何给他们讲解《游园惊梦》的。她说:“这出戏好些同学都不会,希望梅先生能连讲带做。果然,第二天讲对课的时候,梅先生就搬来一架录音机,他一边讲,一边放录音,一边做,他讲的清楚明白,做的动作熟练自如,比划的姿态准确优美,简直把杜丽娘这个有才学的大家闺秀的形象和内心世界,通过形体动作,完美地再现了出来。这很能诱导我们如何去分析与创造一个角色。当时,我们想到他老人家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天气又热,可是他好像并不感觉似的。讲完了,又还为我们演出了这个戏,使我们学的更加踏实、更加深入。”*关肃霜:《春城秋色忆梅师——纪念梅兰芳先生逝世一周年》,《云南日报》1962年8月6日。从以上这些梅兰芳不同时期的弟子的深情回忆中我们不难发现,梅兰芳对弟子传承他的表演艺术是不遗余力的,他应当是中国现当代戏曲大家中传承的人数最多,弟子成就最大的杰出的京剧艺术的传承人。
毫无疑问,梅兰芳表演艺术的传承实际上涉及到不同层面的被传承者:一是直接向梅兰芳磕头拜师的入门弟子,如魏莲芳、李世芳、言慧珠、杨荣环、李玉茹、童芷苓、杜近芳、沈小梅、关肃霜、胡芝风、陈正薇等;二是与梅兰芳同台合作受益于梅兰芳的指点帮助,如袁世海、王琴生等;三是学梅派戏,又进入梅剧团直接得到梅兰芳指点帮助的艺人,如李玉芙、丁至云等;*李玉芙:《我跟梅先生学戏》,《中国戏剧》1989年10月号。四是私淑梅兰芳的艺人、票友,包括梅兰芳20世纪30年代在他所创办的的“国剧学会”名下开办的“国剧传习所”所招收的75名业余学员;*梅兰芳讲授、郭建英笔记:《梅兰芳先生之一课》,《国剧画报》1932年6月17日第1卷第22期。梅兰芳讲授、郭建英笔记:《梅浣华先生讲授之唱法》,《国剧画报》1932年10月21日第1卷第40期、10月28日第1卷第1期连载。梅兰芳、朱桂芳示范,郭建英笔记:《剧舞笔记》,《国剧画报》第二卷1932年11月4日第2期、11月10日第3期、11月17日第4期、11月24日第5期、12月8日第7期、12月22日第9期、12月29日第10期;第二卷1933年4月20日第14期、4月27日第15期、5月18日第18期、5月25日第19期、6月1日第20期。刘仲秋:《关心艺术,关心人——回忆梅兰芳同志两件事》,《光明日报》1962年8月27日。郭建英:《回忆梅师对我的教导》,《文汇报》1962年8月15日。五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第一次全国戏曲观摩会演中得到梅兰芳指点的各地方戏曲表演艺术家,这其中相当一批人还参加了1960年5月梅兰芳任班主任的中国戏曲学院表演艺术研究班的学习,包括常香玉、袁雪芬、陈伯华、丁是娥、筱文艳、阳友鹤、陈书舫、新凤霞、尹羲等。*《梅兰芳艺术评论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540-566页。六是梅兰芳到各地讲学、看戏对学员和艺人的传授和指点,如高盛麟、严凤英、新凤霞、姚璇秋*姚璇秋:《忆梅师悼梅师》,《羊城晚报》1961年9月5日。等。*如何认定梅兰芳先生的弟子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一般认为梅兰芳的弟子有115位。见李玲玲著:《梅兰芳全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622页。成喻言在梅兰芳诞辰110周年的2004年出版的《梅兰芳画传》中也根据北京梅兰芳纪念馆馆藏整理了梅兰芳弟子姓名一览表,也是115人。见《梅兰芳画传》,北京:团结出版社,第183页。也有人认为“梅先生一生收了102个学生,京剧业余爱好这种学习梅派的则不计其数。”见胡芝风著:《晶莹的戏曲里程碑》,《梅韵麒风——梅兰芳周信芳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正是因为梅兰芳表演艺术被传承的对象纷繁复杂,所以,不同的传承对象对梅兰芳表演艺术的理解和领悟是千差万别的,这是源于被传承者与梅兰芳师承关系的亲疏、行当的差别、剧种的差异,以及理论界对梅兰芳表演艺术解释的引导或误导等多重因素。但从梅兰芳的这些正式拜师*1947年杜近芳拜梅兰芳为师,没钱打理拜师仪式,是梅兰芳“倒贴”在上海举办了盛大的鸡尾酒会将她介绍给了京剧界同行和社会名流们。见杜近芳著:《梅兰芳先生教我演虞姬》,《戏剧报》1984年第10期。1948年春杨荣环的拜师典礼费用也是因他一贫如洗而由梅兰芳全部担负的。见杨荣环著:《艺术美来自心灵美——纪念梅兰芳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天津日报》1981年8月9日。但并不是梅兰芳的弟子都举行过正式的拜师仪式。或未正式拜师的被传承者的记忆和表述里,我们仍可以看到梅兰芳将自己的表演艺术传承给他们的一些基本内涵:
首要的是要顾及到“美”。沈小梅曾回忆梅兰芳对她说过的话:“对唱上要求要严格,不仅每个字要送到观众耳朵里,每一‘气口’、‘劲头’都不能疏忽,要用得恰到好处,不能每字每句都用劲,要掌握重点,应该让人一听就有美的感受。表演上也是一样,一举手,一投足,一笑,一哭,都不能脱离美的范畴。”1959年,沈小梅所在的江苏省京剧团要出国演出。剧团在北京进行剧目加工期间,梅兰芳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她加工《醉酒》。《醉酒》在国外是以“醉美人”的剧名出现的。所以,梅兰芳对她强调说:“必须用醉了的杨玉环通过优美的舞蹈身段来表现出封建朝代里宫廷妇女的痛苦。”*沈小梅:《忆梅兰芳老师》,《新华日报》1961年8月27日。正是从“美”出发,梅兰芳对舞台上表演的所有细微末节的动作、位置等等的处理都非常讲究,比如《霸王别姬》舞剑的位置就是为美感而确立的。梅兰芳说:“《霸王别姬》的舞剑的位置,是环绕在四个犄角和中央,成为一朵梅花式的图案,假使你的舞蹈步法不够准确和严整,就会给观众一种残缺支离的感觉。”*梅兰芳:《中国京剧的表演艺术》,见《梅兰芳全集》叁,第43页。丁至云在表演《霸王别姬》时总不忘梅先生的提醒:“舞剑时不能单纯地卖弄技巧、功夫,更要把感情包含进去。在美的姿态上要稍微收敛一点,但还要照顾到舞台上的美,愁绪要冲淡一些……”*丁至云:《探讨梅剧〈霸王别姬〉》,《光明日报》1962年8月14日。这一点杜近芳对梅先生的教诲也记忆犹新。梅先生谆谆告诉她:“虞姬的舞剑动作是有层次变化的。开始是为了解忧,后来就变成了与之诀别了。当她舞到霸王面前时是强颜欢笑,抑郁中显得优美动人;当舞剑背对霸王时,则是自我克制,显得心情沉重、愁眉冷对,悲剧的氛围很浓烈。在表演上,要保持美的造型,不能狂舞,要掌握好分寸。”*杜近芳:《梅兰芳先生教我演虞姬》,《戏剧报》1984年第10期。关于梅兰芳亮相的浮雕美也给丁至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说:“梅派的亮相讲究大方、敏捷、有节奏感。梅先生生前每演此剧,我都很注意他的亮相动作,无论是舞剑中的许多亮相或是当项羽在唱《垓下歌》时的‘四门斗’的对舞亮相,都给人一种浮雕美的感觉,这是和梅先生平时对于雕刻、绘画的爱好分不开的。”*丁至云:《探讨梅剧〈霸王别姬〉》,《光明日报》1962年8月14日。梅兰芳曾说:“我是个最喜欢改戏的人,但也是最慎重改戏的人。改,就要改好。”*转引自沈小梅:《忆梅兰芳老师》,《新华日报》1961年8月27日。而所谓“改好”的主要标准在梅兰芳这里就是是否给人“美的感受”,或是否脱离了“美的范畴”。
其次是要抓住“神”。梅兰芳说:“我的戏常有改动,所以你们不仅要学戏,还要学我的‘神’。”*转引自胡芝风:《难忘的教诲》,《戏剧通讯》1981年第9期。这一点童芷苓有很深切的感受。她说:“梅师的表演身段美,一颦一笑皆是画。唱腔美,富丽之声遏行云,都是很难学会的。但是我觉得更难学会的,是梅师表演艺术的神韵和魅力。”而与梅兰芳表演的“神”或“神韵”密切相关的是他所显现出来的“仙气”。这就是演艺界学得最少,议论得却最多的梅兰芳表演《洛神》所涌现出来的“仙气”。童芷苓非常坦率地说:“有些同志说,梅师的学生中,把梅先生在《洛神》中的一招一式都学会了。表演时,该唱的唱了,该演的也演了,但是,缺少最主要的:‘仙气’。这里所指的学生,也包括我,我就是缺少‘仙气’者之一。”那么,什么是“仙气”呢?童芷苓说:“‘仙气’,说起来很抽象,看上去又很具体。有或没有,都看得出。但是,我想这不是什么虚幻玄妙的东西,正象‘书卷气’、‘大将风度’这些词的含义一样,是指演员表演人物时的气质。”而“气质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要长期锻炼、修养,逐渐形成的。梅师在《洛神》表演中的‘仙气’,不只是因为他熟读曹子建的诗赋,而是他长期文学诗画修养的积累。梅师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是多方面的。他表演中的‘仙气’——气质,是他多方面勤奋学习,刻苦锻炼,长期修养总和的体现,表演艺术的神韵和魅力,由气质而产生。其中,和人们永远在一起的崇高人品,则是气质的基石。”*童芷苓:《艺如人品——忆我的老师梅兰芳》,《上海戏剧》1981年第5期。田汉认为,“梅先生演‘洛神’之所以有仙气,应该是他认真地研究过‘洛神’的缘故。”见田汉著:《追忆他,学习他,发扬他!》,《人民日报》1962年8月9日。《田汉全集》第十七卷,第628-629页。
第三是开宗而不立门户。胡芝风一直牢牢谨记梅先生当年的教诲:“同样一个戏,各有各的演法。你学戏,不要看我走七步,你就不敢走八步。千万不能学僵了。”梅兰芳最不喜欢的就是学生亦步亦趋学他的样演戏:“你演戏,要根据人物和装束设计身段。你穿大靠做半蹲‘跨虎’的动作不好,我从前也是这么演,后来发现不合适就改了,希望你也能改掉。”*转引自胡芝风:《难忘的教诲》,《戏剧通讯》1981年第9期。这一点,沈小梅也体会很深,梅兰芳绝不让“别人套着他的脚印走路”。*沈小梅:《忆梅兰芳老师》,《新华日报》1961年8月27日。童芷苓说梅先生“常常引用齐白石先生的话说:‘学我者生,象我者死’,鼓励我们在向他学习时,不要限制自己的发展,要有发展变化,直到超过他。”*童芷苓:《艺如人品——忆我的老师梅兰芳》,《上海戏剧》1981年第5期。的确,梅兰芳完全没有门户之见,他说得非常恳切:“如果人人都认为我梅兰芳的化装不错,全按照我的化法来做,由于各个人的脸型不同,有些人就要上当了。”*梅兰芳:《关于表演艺术的讲话》,《文汇报》1962年2月28日。
第四是要永远“谦逊”。关肃霜曾回忆说:“1960年我去北京学习,又看到梅先生演的《宇宙锋》,觉得比以前更加细腻、更加精进了。当我和同学们上台去道贺的时候,汉剧演员陈伯华说:‘梅先生,您今天演的太好了,我一定要跟您好好学习。’梅先生谦逊地说:‘你跟我学啊!我还是看了你演的《宇宙锋》中那些新的表现手法,受到了启发,才给这出戏又添了点新样子。’”*关肃霜:《春城秋色忆梅师——纪念梅兰芳先生逝世一周年》,《云南日报》1962年8月6日。就在关肃霜参加的1960年5月这次中国戏曲学院戏曲艺术研究班上,梅兰芳在《关于表演艺术的讲话》中还提及就在讲台下听课的陈伯华说他扮演的杜丽娘“刚出场的时候显得胖,等脱了斗篷,就不觉得胖了”这件事。梅兰芳当时非常真诚的说:“这两句话对我大有用处”,然后认真分析为什么会给人胖的感觉,主要问题恐怕是出在服装上,由此,他当场作出决定,“恢复老路子,我想斗篷里少穿一件帔,总可以减轻臃肿的模样。”见《梅兰芳全集》叁,第61页。梅兰芳的这种谦逊贯穿在他一生的艺术实践中,这使他能够广泛地吸纳各种意见和建议成就了他的伟业,最令人感慨的是他对并不熟悉舞台表演技巧的文人票友的各种意见虚心接纳的心胸。梅兰芳就曾说过排演《霸王别姬》时戏中的京剧舞蹈“有一部分动作是外行设计的,其中齐如山就出了不少点子。姚玉芙曾说过:‘齐先生琢磨的身段有些是反的。’我说:‘有点反的也不错,显得新颖别致,只有外行才敢这样做,我们都懂身段有正反,也不会出这类的主意。’”*梅兰芳:《梅兰芳全集》壹,第664页。又如《贵妃醉酒》的表演。李玉茹曾提及梅兰芳如何从善如流修改“闻花”次数的。她说:“《贵妃醉酒》中的‘闻花’,究竟是两次好,还是三次好呢?如果当中来个大旋转,多做一次‘卧鱼’身段,准能多要上一个‘碰头好’。但他请教了汉剧老艺人,考虑到舞台上的造型不宜过多地重复,所以他后来只用两次‘闻花’。这完全是从艺术效果来考虑,并非因为年纪大了而省去一次。”*李玉茹:《学习梅师的革新精神》,《人民日报》1981年8月6日。
第五是要有“献身精神”。梅兰芳极其热爱他的表演艺术事业,其痴迷的程度令人肃然起敬。杜近芳曾回忆她1947年到梅先生家准备拜师,将她自己演虞姬的戏装小照给梅先生做评判。没想到梅兰芳端详了半天杜近芳的照片对夫人福芝芳说:“这是我哪年照的?项链上的几颗珠子怎么没弄好?”*杜近芳:《梅兰芳先生教我演虞姬》,《戏剧报》1984年第10期。也即梅兰芳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张照片的真正主人是谁,他关注的只是戏装项链上的几颗珠子的事。可见梅兰芳时时刻刻所思考的都是戏台上的事,生怕自己的哪一点装束有半点瑕疵。正是这种对舞台表演的痴迷,他从不放弃每一次能够演出的机会。沈小梅回忆说:“就是在他逝世前不久,为了到新疆去演出,他还专门买了新疆省的地图,作去那儿的准备。梅夫人告诉我,在梅老师病后,她曾问他:‘给你打一针止疼针,让你唱《醉酒》,你还能行吗?’他的答复是:照样可以唱。”*沈小梅:《忆梅兰芳老师》,《新华日报》1961年8月27日。
二
对梅兰芳表演艺术传承的最基础的层面涉及支撑梅兰芳表演艺术圆满呈现的技术根底问题,即由梅兰芳的童子功奠基的唱念做打功法对他表演艺术的深刻影响。比如,作为京剧演员的梅兰芳为什么会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不间断地学习昆曲呢?我们一般的解释都是依照梅兰芳自己多次解释的,即为了将“复杂而美观”的昆曲身段“尽量利用在京戏里面”。*梅兰芳:《梅兰芳全集》壹,第252页。梅兰芳也曾回忆1932年南迁上海居住,想到南方是昆曲的发祥地,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就“应该在昆曲的唱念和身段方面,再多吸收一些精华,来充实我的演技。”见梅兰芳:《梅兰芳全集》壹,第171页。可问题的复杂性并不仅仅是用昆曲的身段来丰富京剧的表演这么简单,关键是昆曲的声腔唱法对提高京剧的唱腔和字音有很大的帮助。关于这个问题梅兰芳有一篇重要的遗稿《漫谈运用戏曲资料与培养下一代》披露了一个过去我们没太注意的史实。梅兰芳说:“从程长庚先生起,就是吸取昆曲的唱法来丰富提高皮黄腔的字音的。我的开蒙老师吴菱仙先生是时小福先生的徒弟,时老先生是南方人,他先学昆曲,后唱皮黄,所以字音准确清楚,吴先生是根据他的唱法来教我的。以后,我曾问业于陈老夫子(德霖),他也有昆曲底子,而我早年就向乔蕙兰先生等学了许多出昆曲。1932年我从北京迁沪居住,开始和俞振飞、许伯遒同志等钻研昆山腔——水磨调、橄榄腔的唱法,多年来断断续续,始终没有间断。”*梅兰芳的遗稿《漫谈运用戏曲资料与培养下一代》是1961年7月间梅兰芳先生准备在文艺界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已经拟好了提纲,他已经口述了表演记录材料和培养下一代、培养师资问题这一部分。可惜他还没讲完就病了。在医院里他对秘书许姬传说:“……整理遗产与培养下一代的稿子,把我看过的记录抄出来,等我病好了再接着谈别的问题。”没曾想到,8月8日凌晨5时梅兰芳去世。此发言稿竟成了遗稿。该遗稿收入《梅兰芳全集》叁,第170-192页。此处引文出自第181页。这就非常清晰的告诉人们,梅兰芳最初学戏的幼功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学习京剧的唱腔唱法,而是通过吴菱仙所宗的时小福的昆曲的唱法唱京剧。*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在第三章“幼年学艺的过程”第一节“开蒙老师吴菱仙”虽提及“在十八岁之前,我专唱这一类青衣戏,宗的是时小福老先生的一派。”见《梅兰芳全集》壹,第25页。但没有说明时小福是先学昆曲、后学京剧的背景。换言之,传承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前提是要对昆曲的声腔、身段有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学习。这恐怕就是仅仅从京剧层面学习模仿梅兰芳往往非常困难、常常不得要领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梅兰芳的弟子中依照梅先生的路子演戏的演员是主流,比如丁至云就是按照梅兰芳把《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心情发展分为五个阶段来详加讨论并按此路数来演的。*《梅兰芳戏剧散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49-50页。丁至云:《探讨梅剧〈霸王别姬〉》,《光明日报》1962年8月14日。也有一些专业技能好、本事大的弟子是在听了梅兰芳的批评之后加以调整改进的。比如李玉茹演《霸王别姬》。她说有一次梅兰芳来看她演的《霸王别姬》,“当时我才二十出头,又有武功底子,在舞剑一场中,特别来了劲,又是‘探海’,又是‘蹦子’,着实露了几手,博得了满堂彩声,自己十分得意。可是先生看后,却严肃地批评我说:‘你再有武功,可千万别搁在这儿用。虞姬此刻知道自己和项王被困垓下,她是满腹哀愁,强打精神在安慰项王,怎么还有兴致卖“溜”呢(戏班的行话,指动作轻快敏捷)?要考虑人物的处境和情绪,这儿不是卖“溜”的地方。’当时我已是一个挑梁搭班演主角的演员了,平时听到的总是捧场话,像先生这样直言不讳,诚恳的批评,对我来说是特别珍贵的。”*李玉茹:《学习梅师的革新精神》,《人民日报》1981年8月6日。
当然,学梅兰芳的戏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学到家的,即便是得到梅兰芳先生的亲炙提点也未必就得其要领。1960年天津市京剧团青年演员张芝兰到梅剧团学习《穆桂英挂帅》,学会以后在吉祥戏院彩排了一次。梅兰芳说:“这个小青年是一个好坯子,但在看我演戏时,有些动作没有看清楚。例如第五场,穆桂英转身向后听鼓角声的身段,是双手反搭袖,向身后一背,她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劲头使得太大了。我当时就叫人告诉她:这个动作,全靠腰上一点寸劲,把它使在节骨眼上,用不着使大劲把手紧紧贴在背后,手与腰之间,要有个小距离,如果贴紧了,身段就不够大了。还有在第一声鼓响的同时要‘长’(音掌)身,可是在台下学习的人,很容易错觉为用力把手臂紧贴在背后来表示力量,而效果适得其反。”*梅兰芳:《梅兰芳全集》叁,第176页。“劲头使得太大”自然就失去了梅兰芳所追求的“中和之美”的韵味、趣味。但对这个在任何表演词典中都找不到的一个仅属于优伶舞台表演的“劲头”语汇,并不是所有艺术家都能确切理解和言说的,包括以“梅派”自居的很多人也未必能领悟梅兰芳的这个常用语汇的真实含义。因此,这个看似很小的问题,却实实在在就从审美本质上规定了梅兰芳的表演究竟应该传承什么。梅兰芳当年叫人提醒过这个年轻演员,她是否就明白了梅兰芳的意思还真的很难说。或许人们早就忽略甚至遗忘了五十多年前为什么梅兰芳这么看重这种表演的“劲头”。可对梅兰芳表演美学的传承恰恰就是应当从这些最细微的身体感觉出发的。*参见邹元江:《梅兰芳〈奇双会〉表演问题探》,《文化遗产》2012年第4期。
三
张君秋在谈到梅兰芳的革新精神时首先提到“他的艺术具有很鲜明的时代感”,最突出的就是梅兰芳不断探索编演新戏,以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趋新求变的心理欲求。他在几出时装新戏排演并不理想的情况下,仍不放弃对编排新戏的探索,在诸多文人票友的襄助下,他终于创作出了许多既不背离戏曲传统,又让观众耳目一新的古装新戏,如《廉锦枫》《霸王别姬》《天女散花》《麻姑献寿》《洛神》《西施》《太真外传》等,并整理演出了《宇宙锋》《贵妃醉酒》《奇双会》《金山寺》《断桥》《姑嫂英雄》《打渔杀家》《二堂舍子》《审头刺汤》等传统剧目。正是因为梅兰芳的革新精神带有“很鲜明的时代感”,所以,张君秋认为梅兰芳的艺术“从开始到成熟,以至鼎盛时期,面貌是不一样的”。*张君秋:《梅兰芳先生的革新精神》,《戏剧论丛》1984年第3辑。
的确如此,梅兰芳就曾说过,“从不同时期的照片中,还可以了解化装、服装的演变。由于六十年来舞台光线的由暗到亮,旦角的化妆,发髻、服装、图案、式样……对‘美’的要求就比其他角色更为迫切,我在这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拿我各个时期所照的《金山寺》中白娘子的照片来看,从头上的大额子改为软额子,片子的贴法,眼窝的画法……就不难看出这种变化。关于水袖的演变,看老照片似乎太短,不甚美观,而我的古装戏照片就放长了,成为风气。可是现在一般服装的水袖都特别加长,又嫌过长了,我感到对表演没有什么好处。”*梅兰芳遗稿:《漫谈运用戏曲资料与培养下一代》,见《梅兰芳全集》叁,第173页。张君秋说:“梅先生在这里所说的老照片中的化装方法及所穿的服装都是他从前辈先生那里继承过来的,而后来的进步则是他在自己所从事艺术实践的时代里,为了适应观众的新要求,所完成的一段艺术创造,这种创造是他的前辈不曾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如果我们再听一些现有的唱片资料,拿梅先生的代表剧目的演唱同陈德霖等前辈的唱腔相比,同样也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张君秋:《梅兰芳先生的革新精神》,《戏剧论丛》1984年第3辑。梅兰芳的遗稿《漫谈运用戏曲资料与培养下一代》是张君秋最早发现了它的重大价值,也是他最先引用并加以论述的。因为这是梅兰芳临终前最后的遗言,尤其对我们如何运用“戏曲照片”、“戏曲唱片”、“表演的文字记录”、“拍摄表演艺术的电影记录”、“脸谱”等资料研究戏曲的历史进程指明了重要的方向。魏莲芳的回忆完全可以印证张君秋的这个说法。魏莲芳说梅先生“他每排一本新戏,起码要花费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每晚九点钟后梅兰芳就在家里“专心一志地琢磨新戏里的唱腔身段。这些唱腔先由王少卿编谱,然后请徐兰沅老先生审定了才采用;身段和服装由容丰照相馆根据剧情从各个角度拍摄照片,每本戏总要拍三十多张,然后和大家一起逐张研究取舍。”*魏莲芳:《追忆梅师》,《解放日报》1961年10月14日。梅兰芳这样一种精益求精的艺术创造,的确像张君秋所说的“是他的前辈不曾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张君秋对刻板学习流派艺术很不以为然,并对学“梅派”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一针见血的批评。他说:“我感到,刻意模仿流派艺术的一招一式,满足于几出流派剧目的学习,似乎是当前京剧界比较通行的弊病。这样做的坏处不仅仅在于刻意模仿即使是酷似亦不能神似,重要的是这样做的后果是使我们的艺术趋于僵化……譬如某出戏中的出场,梅先生的出场走三步,还是走四步。有的说走三步,有的说走四步,都说是亲眼所见,争论不休。这些都是形式上的争论,多少带有点盲目性,要真正学好梅先生的出场,还得从梅先生出场时是如何体现这个人物的身份、性格及当时的心情这方面推敲,至于究竟走几步,这要看台大台小,台大就多走几步,台小就少走几步,只要把握住人物的身份、性格,体现出这个人物的思想情绪,步子多少就无关宏旨了。”张君秋实际上是真正领悟传承了梅兰芳的表演艺术的神髓——革新精神。这种革新精神并不拘于对梅兰芳一招一式的刻板学习和模仿,而是像梅兰芳一样,高度重视对“传统表演艺术的积累”,在此基础上,“在艺术创造中勤于思考”。*张君秋:《梅兰芳先生的革新精神》,《戏剧论丛》1984年第3辑。这就是张君秋所强调的梅兰芳革新精神的两个“重要前提”。这是两个非常关键的前提。
所谓高度重视对“传统表演艺术的积累”,这实际上是对传统表演艺术的继承问题。梅兰芳在继承传统上是比他同时代的艺术家下过更大的功夫的。他在18岁之前所学的都是以唱工为主的正工青衣戏,如《战蒲关》《二进宫》《桑园会》《三娘教子》《彩楼配》《三击掌》《探窑》《二度梅》《别宫》《祭江》《孝义节》《祭塔》《孝感天》《宇宙锋》《打金枝》等;配角戏如《桑园寄子》《浣纱记》《朱砂痣》《岳家庄》《九更天》《搜孤救孤》等,共约三十几出戏;辛亥革命后为了满足观众“看戏”的新需要,他又“兼学了二本《虹霓关》《樊江关》《穆柯寨》等这些偏重身段、表情和武工的戏”;*梅兰芳:《梅兰芳全集》叁,第7页。还为了将“复杂而美观”的昆曲身段“尽量利用在京戏里面”,*梅兰芳:《梅兰芳全集》壹,第252页。作为京剧演员的梅兰芳却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不断学习昆曲,自然不仅仅是为了学习昆曲的身段来丰富京剧的表演,关键是昆曲的声腔唱法对提高京剧的唱腔和字音有很大的帮助。梅兰芳说:“从程长庚先生起,就是吸取昆曲的唱法来丰富提高皮黄腔的字音的。我的开蒙老师吴菱仙先生是时小福先生的徒弟,时老先生是南方人,他先学昆曲,后唱皮黄,所以字音准确清楚,吴先生是根据他的唱法来教我的。以后,我曾问业于陈老夫子(德霖),他也有昆曲底子,而我早年就向乔蕙兰先生等学了许多出昆曲。1932年我从北京迁沪居住,开始和俞振飞、许伯遒同志等钻研昆山腔——水磨调、橄榄腔的唱法,多年来断断续续,始终没有间断。”见梅兰芳遗稿《漫谈运用戏曲资料与培养下一代》,载梅兰芳:《梅兰芳全集》叁,第181页。在乔蕙兰、陈老夫子(德霖)等艺人的传授下学演了昆曲如《思凡》《闹学》《游园惊梦》《水斗》《断桥》《佳期》《拷红》《风筝误·惊丑、前亲、逼婚、后亲》等三十几出戏。张君秋发现,“梅先生所学的剧目并不见得以后都经常演出,有的剧目很少演出,甚至不演”。的确如此,比如清末民初梅兰芳在北京看了王钟声的话剧,在上海看了春柳社的话剧,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而先后排演的《宦海潮》《孽海波澜》《一缕麻》《邓霞姑》《童女斩蛇》等时装新戏到1928年之后就很少再演出。由此,张君秋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梅兰芳“以前的许多剧目是不是白学了呢?”他说梅先生可不这么看。“按照梅先生的说法,就是由少到多,由多到少,最后的少实际上就是精,是从多中提炼出来的。”*张君秋:《梅兰芳先生的革新精神》,《戏剧论丛》1984年第3辑。关于这一点梅兰芳的确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创造是艺术修养的成果,如果眼界不广,没有消化若干传统的艺术成果,在自己身上就不可能具备很好地表现手段,也就等于凭空的‘创造’,这不但是艺术进步过程中的阻碍,而且是很危险的。”*梅兰芳:《梅兰芳全集》叁,第50页。这就是继承对于创造而言具有前置性。
而“在艺术创造中勤于思考”,这实际上是强调创造的理性化思维,而不是被盲目的非理性的创造冲动所左右。王瑶卿常说:“不是改了就好,而是要往好了改。”那么如何往“好了改”呢?这就要勤于思考。张君秋说王瑶卿的这句话“我们可以从梅先生的许多创新中找到生动的注脚。譬如《宇宙锋》‘修本’一场,赵艳容唱的一段[西皮原板]过去是唱[慢板],[慢板]的演唱就显得拖沓,况且全本《宇宙锋》‘修本’前的出嫁匡门一场已有[慢板]。同时,为了表现赵艳容看到她的父亲要修本保奏匡家无罪,而转忧为喜的心情,他在‘扎、哆、衣’起唱鼓键敲击声中,轻快双抖袖,面部也呈现欣喜情绪,表演上显得十分精彩、熨贴。这就是往好了改的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张君秋:《梅兰芳先生的革新精神》,《戏剧论丛》1984年第3辑。在这里,张君秋实际上看到了梅兰芳是在不断反思自己的创造中而寻找到不偏不倚的革新戏曲表演艺术的发展路径——由中和之路达于中和之美的最高境界。关于这一点梅兰芳曾作过很好的总结:
我从演青衣、闺门旦进展到演花旦、刀马旦,排演时装戏,学习昆曲这几个时期,在表演艺术上,比以前已经丰富得多了。我就在这些基础上,大胆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在舞蹈部分,有《霸王别姬》里的剑舞,《上元夫人》里的拂尘舞,《麻姑献寿》里的袖舞,《太真外传》里的盘舞,《西施》里的羽舞,《天女散花》里的绸舞,《嫦娥奔月》里的花镰舞,《千金一笑》里的扑萤舞,《廉锦枫》里的刺蚌舞等。这里面《霸王别姬》里的剑舞,是把京剧《鸿门宴》和《群英会》的剑舞,还有《卖马当锏》的舞锏的舞蹈加以提炼变化,同时吸取国术中的剑法汇合编制而成的。不过,《鸿门宴》等三个戏的舞蹈,原只有打击乐器的伴奏,《霸王别姬》里的剑舞,却是一部分加入了歌唱,另一部分又配合了管弦乐的伴奏的。《麻姑献寿》里的袖舞,是我从古代的“长袖善舞”这句成语,体会出古代有一种以袖子为主的舞蹈,而根据旦角的水袖动作研究出的一种袖舞。《天女散花》的绸舞,是根据古代绘画“天女散花图”的形象创造出的。天女服装上的特征是两条风带,显示着御风而行,我就想到可以利用这两条风带来加强动作的舞蹈性,创造了《天女散花》的绸舞。服装部分,大都取材于许多古代绘画、雕刻、塑像等等美术品上的妇女装束,因为要适合于舞台上表演的条件、人物的性格、图案色彩的调和,就必须加以适当的剪裁;特别是头上发髻的设计,是经过了若干次的试验和改革,才完成今天的样子的。*梅兰芳:《梅兰芳全集》叁,第8页。
由此不难看出,梅兰芳在周边文人的倾力帮助下,在艺术创造中是非常勤于思考的,他的每一次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对前人的艺术成就,不论是绘画、雕塑,还是音乐、化装等都有着深入精细的继承和借鉴。这其中特别令人敬佩的是他的思考对象并不一定就是大家名伶,不管谁有一点可资借鉴学习的地方,他都会非常认真地加以揣摩玩味。
民国三年(1913)12月8日,是梅兰芳第二次应上海丹桂第一台老板许少卿的邀请与凤二爷(王凤卿)南下表演的第二天。梅兰芳曾回忆说:“头一天因为赶场,没有能够看到头里的戏。第二天紧挨着我的码字,是三麻子的《徐策跑城》,我正在扮戏又是看不成的。倒第四是贵俊卿、赵君玉的《游龙戏凤》,我得早来瞧瞧。”赵君玉(1894-1944)为名武生赵小廉之子,初学花脸,改习武生、小生,后改旦角。曾长期为青衣、花旦名角冯子和配演小生,对冯的唱、做颇有心得。梅兰芳第二次到上海演出时赵君玉刚刚开始旦角应工《游龙戏凤》。虽然赵君玉当时名气并不大,*梅兰芳曾回忆赵君玉说:“我听说他会戏很多,花脸、小生、花旦、刀马旦、梆子全都能唱,在上海的戏班里已经有了地位。”见梅兰芳:《梅兰芳全集》壹,第220页。但梅兰芳却“细细看了他几场,觉得他的唱念做派,是走的冯子和的路子。大概是他跟冯子和同台合演的次数比较多的原故吧。”就是这么细细看了几场,梅兰芳有了重要的发现:
看到他的化装就想起上次在上海看到的冯子和、七盏灯(毛韵珂),还有到过北京的贾碧云、林颦卿,都是一个路子。有些地方,跟我们不同,似乎南方的比较美观一点。
梅兰芳举了两个不同的例子,一个是“画眼圈”的不同,一个是“贴片子”的差异。然后梅兰芳说:“我受了他们的影响,上次回到北京,就在眼圈、片子方面已经开始有了新的改革。你别瞧画这一点小玩艺,手法上还是大有讲究……我是不断地加以研究,不晓得经过了多少次的试验和改进,才改成现在的样子的。”*梅兰芳著:《梅兰芳全集》壹,第221-223页。
综上所述,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我们应该传承的核心精神除了涉及他的表演艺术的基本内涵,如要顾及到“美”、需抓住“神”、开宗而不立门户、永远“谦逊”和有“献身精神”外,关键是要真正领悟梅兰芳表演艺术的鲜明时代感——革新精神。这种革新精神基于两个重要的前提,即既要高度重视对“传统表演艺术的积累”,又要“在艺术创造中勤于思考”。前者涉及支撑梅兰芳表演艺术圆满呈现的技术根底问题,即由梅兰芳的童子功奠基的唱念做打功法对他表演艺术的深刻影响,后者则强调创造的理性化思维,而不是被盲目的非理性的创造冲动所左右。这正是梅兰芳五十多年艺术生涯不断探索创新、引领时代潮流的秘诀所在,也是我们应当传承的梅兰芳表演艺术的精神核心。
[责任编辑]董上德
邹元江(1957-),男,湖北武汉人,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430072)
I207.3
A
1674-0890(2017)03-03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