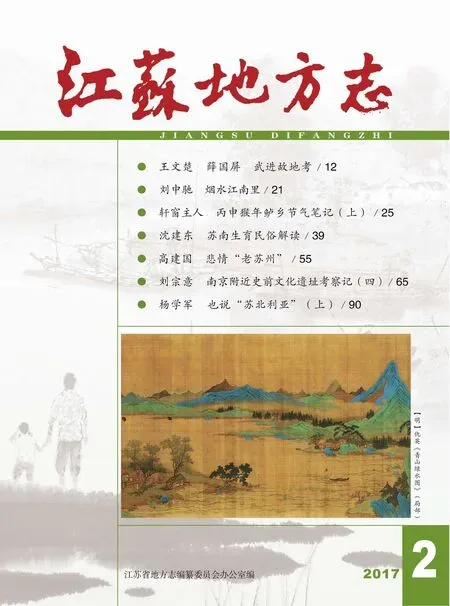解救饥馑的花草
◎ 陈 益
解救饥馑的花草
◎ 陈 益
五彩纷呈的花草,不仅仅用以赏玩,用以入药,还能解救饥馑。记得十九岁去乡下插队落户,荣生帮我扎了个米囤。他说,那年肚子饿得受不了,夜里爬进生产队仓库偷了一把稻种,用两块砖头碾出米粒,慌忙朝嘴里塞。谁知被发现,吊在梁上,打了一屁股的血。至于我自己,以野菜野草充饥的往事,从来不敢忘记。
江南鱼米乡,历来富庶,可是遇到天灾人祸,也会有饥馑的岁月。人们不像北方那样捋榆钱、找观音土,而是以花草填饥。比如红花草,学名紫云英,俗称草头。清明时节开花时,像大片大片的紫红色的云霓,与金黄的油菜花交相辉映,向天际铺展,煞是好看。但在饥荒的年月,诗意就让位给坚硬的现实了。它跟金花菜相似,却质地粗糙,历来只作沤肥和家畜饲料。假如一连几天靠它填肚子,滋味可想而知。这跟南瓜是一样的,难得尝尝,感觉不错。靠它做主食,就是另一回事了。在不见荤腥,缺乏油水的日子里,怎么也挡不住辘辘饥肠。
因为在荒年可以代粮,所以南瓜又称“饭瓜”。《北墅抱瓮录》说:“南瓜愈老愈佳,宜用子瞻煮黄州猪肉之法,少水缓火,蒸令极熟,味甘腻,且极香。”做东坡肉用南瓜,实在是太奢侈了。还有一种瓜,越熟越黄,我们叫“老来黄”,也是当饭的。其中一类,硕大而软糯,干脆就叫“吃得饱”。有瓜吃,还是幸运的。无奈时吃叶子吃花,用盐水浸渍,让它不至于太苦涩。据说从前鸦片泛滥的时候,南瓜常常被用作特殊药物以治疗烟瘾,这倒很有意思。
我们这一代人,在长身体的年月遇到了三年饥荒。记忆中,吃得最多的是胡萝卜漾粉粥。漾粉粥,今天的孩子闻所未闻。说白了,就是在面粉中千方百计加胡萝卜、菜叶和水,煮成糊糊,让它骗过肚皮。“面黄昏,粥半夜,南瓜当顿饿一夜”,有一首民谣就是这样流传的。李时珍《本草纲目·菜部》中记载,胡萝卜“元时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但也有人说,汉武帝时胡萝卜就被张骞引入中原了。只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仅仅记载了张骞从西域带回苜蓿和葡萄种子,并没说到胡萝卜。无论如何,这已经说明文化交流的重要,民以食为天啊!
山芋、土豆和芋艿,也一直是代食品。苏州人历来有中秋节吃芋艿的习俗,相传这跟戚继光抗倭有关。有一次,倭寇偷袭,将戚家军团团围困在山上。粮草断绝,士兵们只好挖野芋艿充饥。饱餐芋艿后,他们奋勇突围,将倭寇全歼在睡梦里。芋艿在吴方言中的谐音是遇难,吃芋艿,正是为了缅怀那些在民族遭遇危难之际,奋勇杀敌的志士。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干屈菜、马兰头、芋艿之类野生的花草茎果,在遭遇灾荒时用来充饥,是苍天的护佑。世界上有许多毫不起眼的东西,却是永远值得我们怀有感激之情的。
明代有一部书,名曰《救荒本草》。作者朱橚,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他在宫廷争斗中处于劣势,甚至被自己的次子举报“图谋不轨”。还好,侄子建文帝没杀他,给他留了一条活路,发配云南,交给黔宁王沐英之子西平侯沐晟管束。流放至人迹罕至的边陲之地,朱橚竟因祸得福。他看到了民间的缺医少药,也看到了滇乡的奇花异草,于是组织学者编写了《普济方》。《普济方》被认为是“采摭繁复,编次详析,自古经方更无赅备于是者”的巨著,全书计168卷。接着又编写了图文并茂的《救荒本草》,广泛流传。他在序言中写道:“因念林林总总之民,不幸罹于旱涝。五谷不熟则可以疗饥者,恐不止荑稗而已也。茍能知悉,而载诸方册,俾不得已而求食者,不惑甘苦于荼荠,取昌阳弃乌喙,因得以裨五谷之缺,则岂不为救荒之一助哉……”
看来,朱橚是饱尝过饥饿滋味的。所以他有足够的兴趣,将那些解救饥馑的花草付诸文字,并绘成图片,以免生灵涂炭。
葵花满畈
芦苇簇拥的湖湾里,有一塘挤挤挨挨的菱叶,浓绿得像是涂了青铜色。满畈的葵花就在它的衬托下摇曳身姿,尽情绽放金黄,伏天的太阳慷慨地给它们镶上金边,令人眼前一亮。远远看去,有两个女孩在葵花丛中嬉戏追逐,帽檐上的飘带画出跳动的弧线,给湖畔平添活力。路边有一凉亭,售卖茶水冷饮,让走累了的游客歇歇脚,顺便欣赏已不多见的景色。
苏州人文震亨,画家文徵明的曾孙。据说有史以来是他第一个将葵花称作“向日”的。所著《长物志》十二卷,涉及现代学科中的建筑、动物、植物、矿物、艺术、园林等方面,可谓包罗万象。字里行间,悄然透显著晚明江南文化人的生活态度。他将葵花分为四类,一是戎葵,二是锦葵,三是向日(别名西番莲),四是秋葵。看得出,桀骜不驯的他不喜欢“向日”。崇祯年间,因朋党之事牵连,锒铛入狱。清军入侵,闻剃发令,他先投河、后绝食,终于呕血而亡。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唱着“社员都是向阳花”长大的。平心而论,那时父母亲工资低,日子过得很清寒,却有平淡的快乐、简单的幸福和天生的满足。彼此间罕见反差,少有攀比,根本不会想到要为拥有别墅、豪车和巨款而殚精竭虑,瘦削的脸上就常常流露笑容。何况,生活中的每一天,有柴米油盐的烦恼,却更有亲情与友情的滋润。对于将来,从来也没有失去希望
那时候看不见成片成片的葵花,也从未想过把它作为观赏植物。宅基与稻田的边缘,有小片隙地,人们栽种几株向日葵,让它自由生长。葵花经历了风吹雨打,又在阳光下昂然朝天怒放。待等秋季成熟,把它晒干,剥出葵花子,在镬子里炒熟,就能招待客人了。嗑着葵花籽聊家常,其乐融融。记得我曾经以葵花为题,写过稚拙的短文,表达的意思是愿意像它一样,任何时候都抬头向着阳光,不垂头丧气,不长瘪籽软壳。文字难免概念化,但是挺真实。或许少年不懂愁滋味,但确也没有那么多忧伤。
其实,生活本来就不必太挑剔太苛求。“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夫子的弟子颜回,颇有些葵花的精神,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它都不悲伤、不忧愁、不为琐事烦恼。犹如葵花一般,未必充溢芳香,招蜂引蝶,却很有些志趣、理想和欢乐,永远朝着阳光,比起那些汲汲于名利者,更韧长,也就更耐久。
飞行的麦鸡
麦鸡其实不是鸡,而是一种鸟儿。或许因为它们常躲藏在麦田和矮草地里,人走过,轰然而散,就像谷场上的鸡群,才称为麦鸡吧?朋友特意将他拍摄几幅照片让我欣赏。站在湿地边沿的麦鸡,颈侧和腹侧的羽毛是白色的,后背和翅羽呈辉绿色,闪烁金属的光泽,尾巴则是淡棕色。引人瞩目的是它的头顶上,有一丛黑色反曲的长形羽冠,颇具贵胄风度。迎风飞行时,在张开的翅翼映衬下,又显得格外俏丽。所以人们喜欢叫它作凤头麦鸡。
朋友说,镜头是在苏沪交界处的一个湿地公园抓拍到的。冬天,它们从遥远的北方南迁,组成一个又一个飞行团队,来这里过境歇脚。麦鸡飞行的速度并不快,翅膀悠闲地煽动着,感到倦乏了,便悄然栖息在湖边或草地间。它们四处寻觅金花虫、小天牛、蚂蚁、蝼蛄等昆虫,也吃虾子、蜗牛、蚯蚓,假如没有理想的食物,杂草种子和植物嫩叶也可以充饥——为了强健身体,繁衍后代,它们没理由挑食。恰恰是杂食,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才不至于淘汰。
我赶紧去了湿地公园。这里有万顷良田,有河流池塘,有绿地花草,也有古风犹存的乡村。即便高速公路和高架铁路穿越而过,仍保留安谧宁静的自然状态。一路上,凤头麦鸡让我陷入童年回忆。那时候,淘伴们在收割后的麦田里,一边跌跌撞撞,一边追鸟,曾经激起多少欢笑啊。好几年前麦鸡就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如今又有过境,无疑是环境改善的缘故,这令人高兴。
除了麦鸡,这里还可以看见雉鸡,就是俗称的野鸡。事实上,鸡原本就是由野生原鸡驯化而来的。今天原鸡依然分布在热带常绿灌丛以及次生林中,与鸟儿无异。在湿地公园,雉鸡到处咯咯鸣叫。
雉鸡多彩,特别是雄鸟,羽毛比雌鸟漂亮得多。它的前额和上嘴基部呈黑色,富有蓝绿色光泽。头顶是棕褐色,在白色眉纹下还有一小块蓝黑色短羽。颈部有一条黑色横带,延伸到颈侧,与咽喉部的黑色相连,闪烁绿色的金属光泽。背部和肩部位栗红色。下背和腰两则是蓝灰色,中部又是灰绿色,并且有黄黑相间的波浪形横斑。尾部尤其色彩纷呈,上覆羽黄绿色,末梢土红色。棕褐色、栗色、棕红色、黄灰色、黑色……和谐交互。这恐怕是上苍给予它们的求偶利器。难怪历来的画家都把雉鸡作为重要题材。南宋宫廷画家李迪的《枫鹰雉鸡图》、明代画家吕纪的《梅花雉鸡图》、清代画家任伯年的《天竺雉鸡图》,近代画家徐悲鸿的《雉鸡山花》等,就是流传于世的代表作。有趣的是,在画家的笔下,雉鸡还往往多于家鸡。
生活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王维,是画家,更是诗人。他的田园诗中也写到了雉鸡:“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村庄到处披满了夕阳余晖,牛羊沿着深巷纷纷回归。老人惦念着放牧的孙儿,拄杖等候在自家门扉外。在雉鸡的鸣叫中,麦子即将抽穗,蚕儿成眠桑叶已经薄稀。农夫们荷锄回到了村里,相见时欢声笑语恋恋依依。如此宁寂安逸的情景,怎么能不令人羡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