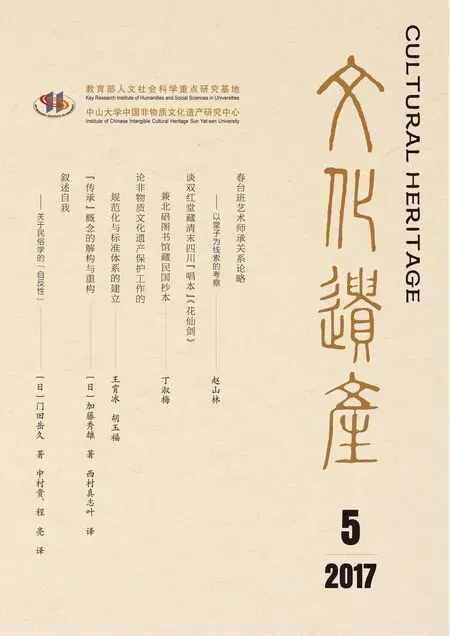从变形规则看东西方新神话异同与交融
黄 琰
从变形规则看东西方新神话异同与交融
黄 琰
21世纪以来,世界文坛和影视界刮起一股“新神话主义”的潮流,“再造神话”的活动在通俗文化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新神话虽然是由作者各自在自我构拟的宇宙观中虚构的故事,但是皆承继了来自本源文化的神话传统,尤其是变形的规则。东西方传统神话中变形规则的主要差异在于:西方神话中的变形以降格为主,东方神话中的变形则呈现了升格的可能性。两者间的差异与东西方哲学传统和宗教传统密切相关。在新神话的叙事中,传承自文化传统的变形规则体现在了故事的结构上。而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产物,新神话也必然呈现跨文化的现象。东西方神话传统在新神话中交融,东西方也各自能从对方那里借鉴对人类面对现代性有所启发的元素。变形规则所体现的西方的人本精神和东方的生态观皆参与搭建了多元文化的新神话世界。
新神话 变形 比较文化
引 言
21世纪以来,世界文坛和影视界刮起一股“新神话主义”的潮流:从英国的《哈利·波特》、美国的《指环王》等,到当今中国网络及各类媒体流行的玄幻、修真小说,超级英雄和魔幻题材的文学及影视作品层出不穷,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着新神话作品的创作*叶舒宪:《再论新神话主义》,《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4期。。有别于对经典神话故事的重述,新神话是作者在借鉴了传统神话元素的基础上,在自我构拟的宇宙观中讲述的全新的故事。这些虚构的故事虽然天马行空,体现了创作者无限的想象力,但是皆有着其本源文化中的神话背景:在宇宙观的构建上遵循神话传统中的结构和法则,在故事的发展情节上借鉴神话故事的母题,人物形象也以来自于神话中的符号为特征。变形,即人与动植物之间外形的互换,是再造神话从传统神话继承而来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尤其是在影像处理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变形这种在科学上、物理上缺乏可能性的变化过程,却能以高科技的手段在荧幕上得到令人非常惊艳的模拟,能够给大众带来一种传统艺术手段无法比拟的审美的体验,因此也成为了影视作品中常见的现象。而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的再造神话中,变形的现象都呈现了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是与古典神话的传统一脉相承的。
一、东西方变形规则之同异
神话的一个重要元素在于变形。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提出:“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性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在中西文化的变形神话中,都体现了一定的生态等级的观念。从神到人,再到动物和植物,是一个从高到低的等级。而从变形的规律来看,西方的等级是个更为分明且固化的等级,变形的规则以降格为主,而东方则表现得更为模糊且具备更强的流动性,变形的规则既有下行,也有上行,而升格变形的可能性体现了东方思想中个人可通过修行而得道的观念。
(一)西方的规则:以降格为主
西方以希腊神话为例,世界由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主宰,在主神之下还有其他的许多散布在自然界中的神,神与凡人所生的子女为英雄,有着比一般人更出众的外表和力量,但往往并不具备永生之身和超自然的能力,而动植物是在人之下的。希腊神话中有许多神祇变形为人类或动植物的故事,以及人类变成动植物的故事。这些变形的故事呈现了一定的特点和规则:首先,主动的变身似乎是高级的神祇所特有的能力,如宙斯变成凡人男子或动物的形态以便勾引凡人女子。其他人物的变形,往往是一种被动的情境使然。凡人一般不具备变形的能力,凡人的变形,通常是神明的惩罚,例如像伊俄这样,是被奥林匹斯神赫拉变成母牛的;还有如《奥德赛》中的女神兼女巫喀耳刻把男性凡人变成公猪。这种使人变形的超自然能力,如果不是由高级的神祇实施,则具有一定的邪恶的色彩。这种能力可等同于巫术,在西方是具有他者属性的。女巫在希腊神话中,有如异教徒:喀耳刻居住的艾尤岛,相对于奥德修斯渴望回归的故土,是异乡;美狄亚的故乡科尔基斯,也被伊阿宋称为蛮荒之地。低等神祇或半神也可能具备变形的能力,但他们的变形往往是不得已的选择:例如达芙妮变为月桂、绪任克斯变为芦苇,皆是为了躲避异性的追求,在无路可走的情境下不得已而变形为不再具备性的特征的植物;又如普洛克涅化为燕子,是为了复仇,是无法消解的愤怒和仇恨使然,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如达芙妮、绪任克斯、和普洛克涅,变形的故事几乎就是有关她们的仅有的故事,所以她们是因为本身就是神灵因而具有变身的能力,或是因为变形的故事而被认为是神灵,已很难说得清楚。但这都透露了凡人不可能具备变形的能力的观念。既然希腊神话中的变形是神这一阶层所特有的能力,则呈现了一种向下变形的趋势,由神化作凡人形态,或化作动物和植物。向上的变形,如动植物化作人形,则是比较罕见的。
向下变形的规则背后的意义,黑格尔认为是“精神界事物的堕落和所受的惩罚*[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5-116页。”。也有学者认为,“神祇主动地投身于较次级的属性,不能以堕落一概而全,有些情况下可理解为是一种献身”*腾奇:《变形神话之法则的若干视角》,《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不得已的变形则是“一种逃避的方式,是从原型中解放出来,逃避被他者同化的命运,实现主体精神的提升。”*腾奇:《变形神话之法则的若干视角》。
向下的变形不仅是一种神的位格的下移,也体现了西方从柏拉图、普洛丁到黑格尔一以贯之的关于世界万物对于神的光辉或神性、或绝对理念的分享的观念。由此可以认为,西方神话的变形规则,不纯粹是一种艺术想象,也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甚至可以认为,西方神话变形规则,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另一个表现方式。不管向下变形是一种堕落还是主动献身,都表现为由神性向人性直至向兽性、魔性的蜕变,这种蜕变,具有审美上的悲剧色彩。
(二)东方的规则:升格的可能性
与西方的向下变形的悲剧色彩相比,东方的向下变形多了一些浪漫的色彩。
《山海经》中就有许多神和人在死后变身为动物的故事,如炎帝之女溺亡后化作精卫鸟。然而,神灵的属性首先就是比较模糊的,炎帝既是人间的帝王,他活动的区域应为人间,但他亦被奉为神明,这里的神灵也并非不死之身,炎帝之女正是因为死了才变形的,而变形为动物反而成为了永生的隐喻*田畦耘:《山海经中变形神话的文化内涵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又如梁祝化蝶,是对世俗规则的逃脱,对美好爱情的追求。虽然也如达芙妮化为月桂一样,是一种被动的情境使然,但是变形后的二人成双成对,自由自在,在感情色彩上,少了一些无奈,多了几分美好和浪漫。
东方神话中与西方最为不同的,一个是东方原始的泛灵观念把各类别的生命归在同一类别上,动植物不但与人类没有优劣之分,且人生之图腾,死后亦归之图腾,人世万物皆投入图腾的怀抱*万建中:《原始初民生命意识的折光——中国上古神话的变形情节破译》,《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在中国道家思想中,“天人合一”、“齐物论”有着深刻的影响,与西方的“分享说”不同,万物具有同等地位不是来自于他们分享了更高一级神性,而是万物自体已经具有某种“灵性”,尽管这种“灵性”有着高下之分,但并非一成不变,“显灵”只是等待机遇,“神性”只是在时间的潜移默化中的内在积淀,所以从飞禽走兽到树木顽石,万物都可以成为人类崇拜的对象,所以向下变形也并非意味着神格的下移,而只是包裹着神性的外在形象的改变,就如《西游记》中的白龙马和《七仙女》中的歪脖子老槐树。
当然,随着道教的发展和佛教的传入,人与神仙界区分、人的善恶与转世投胎观念,直接影响了神话的变形原则,变形就有了等级高低之别,由此也带来了东方观念中呈现的一种从次级往高级流动的可能性:从佛教的释迦牟尼到道教的黄大仙等,在得道之前原本都是凡间的人类。因此在神话故事中,不仅人可以修炼成仙,动物植物亦可修炼成人形,还可能进一步得道成仙。凡界与神界的界线,在于得道。而得道,是个人自身的修为。通过修炼,动物和人都可以突破界线。原有规则中的万物有灵、天人合一观念,逐步演变成为“万物失灵”、“天人分割”的神话世界。变形,就意味着神性或者人性的获得与丧失,从而就具有了崇高或悲剧的审美意味。所谓的“打回原形”在中国后世的神话体系中,是十分常见的叙述模式,《白蛇传》和《聊斋志异》中的诸多故事,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神话的变形原则,基本上是宗教观念的一种延伸,这是与西方变形原则的最大区别。但也正是后世宗教观念的介入,中国的神话变形也由于其等级的形成而与西方有了某种趋同。这种趋同,正是后世再造神话中东西互鉴交融的重要基础。
二、变形规则在新神话中的体现及作用
当代神话元素的文学及影视作品,如近期非常火热的美国的《冰与火之歌》和中国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即使利用了架空历史的创作手法,其构建的虚拟时空,也往往类似于人类的古代。经常出现的元素如西方的城堡和铠甲,东方的宫殿和长袍,以及古代的氏族、皇室的概念,皆是取材于古代神话故事的符号。即使是置于类似当代的有高科技出现的场景中的超级英雄电影,也用远古的符号来对超级英雄进行包装,以示与凡人的区别:例如,超级英雄身着紧身衣裤,显露出发达的肌肉,是对古希腊裸露之美的回归;超级英雄身上的充满古代韵味的披风,在逻辑上只能为超级英雄的战斗力提供障碍,因此也只是一个符号,纯粹起到审美的作用。
(一)西方变形规则在新神话中的体现
无论新神话编织了怎样的一个世界,在西方的再造神话中,我们皆可以若隐若现地看到英雄背负着孤独,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拯救世界,还人类以和平幸福的生活的故事线索。这样的故事结构可视作奥德修斯的远游历险和赫拉克勒斯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变体。奥德修斯面对苦难、面对诱惑,力求回归、力求重拾身份的故事,使他成为一个象征着人类生存状况、人类苦难和人类生活智慧的符号*Jacqueline de Romilly, Pourquoi Ulysse?,Rencontres avec la Grèce Antique, Paris:édition de Fallois, 1995, pp.65-66.。赫拉克勒斯完成了十二项苦功,打败了各种猛兽、魔怪,使他成为人类历经苦难、战胜自然的象征。赫拉克勒斯也是希腊神话中罕见的人类升格成神祇获得永生和在奥林匹斯生活的特权的典型。神话母题为新神话提供的不仅仅是故事的结构,也是神话的精神。故事的结构可概括为英雄通往至善的一个螺旋向内的旅程。螺旋的中心是神性,是至善,而这个旅程之所以非直线,是苦难、诱惑等各种恶的力量在向外牵扯。变形在西方神话及新神话中的作用,就在这股向外的力量之中。
首先,变形为故事中人物所获得的超凡能力提供了依据。动物因为具备人类所不具备的某些能力,因此常常在奇幻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作为具有超出凡人的能力的角色的附加属性。带有动物属性的人,无论他是具备变形为动物的能力,还是因拥有与动物相似的能力而被比喻为“动物-人”(如蜘蛛侠、蝙蝠侠等),都可理解为一种来源于变形神话的修辞术,是对超出凡人的能力的隐喻。这种能力作为凡人所不配拥有的事物,它的获得既是诱惑,也是诅咒。既然人变形为动物具有降格的性质,在再造的神话中,这种超能力的获得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例如狼人是受到“诅咒”,变形的过程非常痛苦。变形者如是反面角色,则代表了强大的反人类的力量;即使是正面角色,如蜘蛛侠、蝙蝠侠等形形色色带有动物色彩的超级英雄,虽然在故事情节上也完成了有如赫拉克勒斯的苦功那般伟大且正义的使命,在人物背景上却有着很浓厚的邪恶堕落的色彩,内心始终在私欲与公共利益、黑暗与光明之间挣扎。而且,超自然能力在为人类服务的同时为人类所带来的灾难也是这类作品中必然探讨的问题。
人变身为动物的情形中,也有带有升格属性的特例,即变身为鸟类。鸟类相比于其他兽类的特殊,在于它是自由移动能力的原始象征。翅膀作为飞行的器官,一旦生长在人物的身上,人就获得了崇高的神性。这与人类对天空的向往和鸟类的隐喻意义有关。
会飞的超级英雄犹如戴上了隐形的翅膀。在空中飞行的超级英雄的形象正如罗兰·巴特的“喷射人”,是“披上了科学的外衣的神话修辞术”:
在喷射人的神话修辞术中,一切都会合起来,共同致力于表现肉体的可塑性,使之遵从集体的目的,正是这种遵从,作为一种牺牲呈现出非人力所能达到之局面富有魅力的独特性。社会最终在喷射人身上发现了古老的神智学协约:总是以禁欲来平衡、校正体力,以人类“幸福”为资支付获取半神性所需的费用。*[法]罗兰·巴特:《喷射人》,见《神话修辞术》,屠有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4页。
除了作为超凡能力的依据之外,变形还增加了故事的悲剧性色彩。变形在作品中,也往往是人物受到的惩罚。这种惩罚剥夺了人物的人的属性,使其脱离了社会性,加之由变形的能力交换而来的短命或永生的诅咒,这些都大大地放大了人物的孤独感。在跨界的爱情故事中,半人具备人的欲望,而其动物属性又让其永远无法如人类那样爱与生活,这种爱而不得的命运也增加了故事的悲剧性,提高了故事的审美价值。
西方新神话中还有一个典型的现象,即主神的离场。
在重述的西方新神话中,我们发现,有这样一种变形情节被逐渐隐去了,即主神的变形。希腊神话中,有最高神的概念。宙斯会变化成各种形态引诱凡人的女子:例如变成牛引诱欧罗巴,变成天鹅引诱勒达。在人类的战争中,雅典娜等奥林匹斯神常常会变作动物或凡人的形象,以迷惑或指点人类。而在新神话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能够主宰人类命运的主神往往不再出席。
一方面是伦理的原因。如宙斯化身动物引诱人类的故事,在伦理上无法为当代人所接受。宙斯为何通过变形引诱人类女性,希腊神话中有提到其神明真身的光芒是凡人所不能承受的,因此神需要以一个化身示人。而神之所以选择变身为动物,也许是对通奸这种行为的非道德性的一种隐喻。变身为低等的动物,使神的属性不在场,也就为神所犯下的罪行找到了存在的理由。而人的肉身与化身为动物的神的结合,也许意味着在远古时期人兽之交并不像如今这般非道德伦理所能容,但也因为伦理的形成,在口传史诗的流传中,也只是对其发生和结果一言带过,其过程是不被言说的。在后世对经典的重新演绎里,则淡化在背景中,或直接隐去。在新的神话中,出于对当代价值观和伦理观的考量,以及大众媒体的道德审判,这类母题不再被重述。
另一方面是理性的原因。柏拉图早就对荷马史诗对主神变形的这种描写提出过质疑。他在《国家篇》中写道:
你认为神是一个魔术师,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在不同的时间显示出不同的形相来吗?他能够改变外貌,欺骗迷惑我们吗?……我说,那么我的好朋友,我们不允许任何诗人对我们说:“诸神常常幻化成各种外乡来客,装扮成各种模样,巡游许多凡人的城市。”我们也不允许任何人讲关于普洛托斯和忒提斯的谎话……*[希腊]柏拉图:《国家篇》,《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344页。
而法国古希腊学家罗米伊则认为,柏拉图所批判的《伊利亚特》中的变形,其实相比于更早期的口传史诗,已经体现出了更多的理性。因为《伊利亚特》中奥林匹斯神的变形情节绝大多数是变形为人,极少变成动物。*Jacqueline de Romilly, “Les Métamorphoses dans Homère”, Rencontres avec la Grèce Antique, Paris:édition de Fallois, 1995, p.37.
到了基督教时代,变形已被摒弃。变形情节的缺失,是《圣经》与神话最大的区别之一。主神化身的情节于是停留在史诗的时代。在理性成为西方思想的核心之后,尤其是在基督教文化接替古希腊文化成为西方思想的源泉之后,神也不再以具体的形象出现。而在当代,即使是在不以现有的科学为依据而架构的奇幻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神话虽然重现了,但是主神的概念要么缺失,即使存在也往往没有形象没有故事,只是出现在人物的言说之中。
主神的缺席,也是为了凸显人的价值。人类的命运不再由神主宰,而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面对超自然的邪恶的力量,是人性战胜了恶魔,是人类拯救了人类自己。
(二)东方变形规则在新神话中的体现
东方的新神话中,变形的规则本身就是故事的结构。东方新神话的结构,可概括为金字塔形,金字塔的底层为众生,塔尖为神(仙)界,变形发生在每一层的交界处,众生通过自身修为往金字塔顶攀登,故事的英雄在攀登的过程中遭遇其他生灵,经过层层磨难,最后作为少数的修行高者到达塔顶。所以在东方新神话中,“修炼”是变形的重要路径。在宗教那里,修炼是人或动物实现蜕变,到达彼岸的通道;在艺术世界,修炼则是从“神变”到“形变”的转换过程。
动物幻化成人形与人类相交的故事,如狐狸精、白蛇精等,被不断重新演绎,甚至可以说,在东方的奇幻文学领域内,此类跨界的情爱的故事占了大半江山。诸如狐狸、白蛇等生灵本为动物,但在修炼成人形的过程中获得了人性,其与人类的结合似乎也就在伦理上获得了存在的可能性。虽然在这些故事中,往往也存在所谓妖孽之阴气可损凡人之阳气一说,这种说法也似乎符合东方传统中的阴阳相生相克的规则,但在演绎的过程中,却常常只是为爱情故事创造障碍的艺术化手段,并不代表动物本身在道德上的堕落,也并不妨碍这些所谓妖孽最后得道而升格成人或比人更高的神。可以说,所谓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在东方的神话故事中与动物的属性无关,而在于个人的修行,也就是说本质由行为决定。
在当代神话重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多这种变形的运用。电影《钟馗》中的钟馗通过“修炼”由普通道士变成“超人”;《画皮》则通过“修炼”,人妖之间可以实现外形转换。“修炼”过程就成了新神话叙述的结构模式,而“修炼”是否得法或者受到外力干扰,则成为情节跌宕变化的重要契机。在当今流行的网络小说,诸如修真、玄幻、穿越等,如逆苍天的《无极魔道》、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夜·水寒的《灵罗戒》等借用甚至直接套用了中国道教中“修道成仙”的级次模式,转换成为故事结构,以此为框架展开叙述。凡修炼得法者,可以顺利晋级成师;凡修炼失法、“走火入魔”者,则可能成妖。这些都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宗教观念对于新神话创作的深刻影响。
除此以外,还有部分作品也借鉴了西方新神话的叙述模式,例如改变时空、进入类似的“异次元”(如唐家三少的《斗罗大陆》)、赋予传统兵器现代物理性能(如逆苍天的《无极魔道》中的魔剑)等,在传统故事的叙述中融进了现代科技和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元素,这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三、全球化语境下东西方神话规则于新神话中的融合
变形的规则根植于神话的传统中。对于每个创作者而言,神话的传统是一种具备社会集体性和普遍性的集体语言,寄居于作者的大脑中。而重述神话的过程是个体语言,是个体机制对整体语言规则做出的表现或发出的回应。*屠有祥:《罗兰·巴特与索绪尔:文化意指分析基本模式的形成》,见《神话修辞术》中译本导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所以在新神话的创作过程中,变形的规则作为整体语言规则的组成部分,是作者所不能绕过的,读者也必须依仗这种规则才能对作品做出解读。
中西方的新神话勃兴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居住的地球变得越来越狭小,越来越透明,新的发现甚至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而与此同时现实生活在理性主义和技术工具的主导下,人的生活能够带来的新的体验空间已经十分有限,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想象空间,新神话主义正可以乘虚而入。近十多年来,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科幻题材,都是新的想象空间的拓展,而且都带有新神话主义的元素。而神话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变形。神话中的变形,则具有无限变幻的空间。当然,任何东西多了,都会产生审美疲劳。刚刚获多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影片《爱乐之城》,之所以受到热捧,可以视为对这种趋势的反拨,对现实诗意的回归。
新神话主义作为全球化时代兴起的思潮,必然也将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现象做出反应。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中,随着网络、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体的迅猛发展,东西文化的交流渗透越来越深入,文化元素的相互借鉴也更加便捷频繁。包括传统神话故事在内的跨文化叙述也已经是家常便饭,美国动漫影片《功夫熊猫》、《花木兰》,中国风靡一时的《盗墓笔记》等,都可以看出不同文化元素借用融合的影子。
在东西方之间的文化界限变得模糊的同时,东西方各自的整体语言规则也变得彼此能够理解,甚至可以说,整体语言规则的相互兼容和统一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东西方古代神话中的一些元素,被互相借鉴,融汇出具有跨文化性的新神话故事。例如,西方的奇幻文学将东方的变形符号融入了西方类型的个人英雄主义战胜反人类力量的故事结构中;中国的奇幻文学也借鉴了希腊神话的系统性神谱和北欧神话的各族各界的世界观,以弥补中国传统神话的碎片状的缺点,使新神话故事具备史诗般宏大的叙事。
从对人类面对现代性有所启发的意义上看,东西方古代神话的变形规则有着各自的优势。
一方面,西方神话史诗虽然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但是英雄身上呈现了一种入世的观念,以人性战胜反人类力量的故事是对人类面对生存状况危机不断自我救赎的体现,是始终具有人文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主题。相比之,东方追求个人升华的修行故事,呈现了出世、隐逸的观念,尤其当代的中国奇幻小说多半可归入言情小说之列,仅仅是嵌在变形的结构中的情爱纠葛,往往缺乏对人类生存现状的深度思考,纯粹娱乐的作用大于发人深省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相对于根植于西方神话传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东方神话中的变形规则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观打破了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关系,体现了人类不应以自然为奴或为敌,而应追求与之和谐的价值观,这对面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现代社会而言,无疑有着很重要的启示作用。
结 语
东西方神话传统在新神话中的融合已然成为一种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借鉴融合的过程中,如果不关注其神话体系所植根的哲学和宗教文化的基础,仅仅是把变形或故事元素当作一种外在的文化符号加以使用,这不仅会失去神话应有的文化内涵,还可能产生误读或误导。同样,读者也必须具有相应的历史文化积累,不然则只能理解皮毛,看看热闹。因此,深度的跨文化的交流学习,就显得十分必要。
[责任编辑]蒋明智
黄琰(1983-),女,广西壮族人,暨南大学翻译学院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420)
K890
A
1674-0890(2017)05-1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