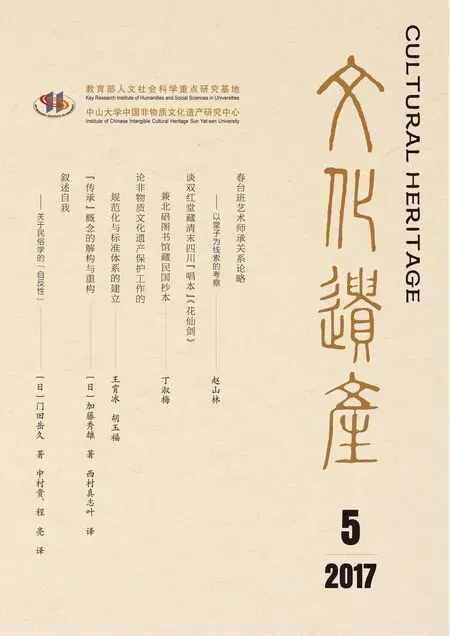谈双红堂藏清末四川“唱本”《花仙剑》兼北碚图书馆藏民国抄本*
丁淑梅
谈双红堂藏清末四川“唱本”《花仙剑》兼北碚图书馆藏民国抄本*
丁淑梅
《花仙剑》是川剧传统剧目之一,作为“江湖十八本”之一的大戏,流传甚广。双红堂藏清末四川“唱本”六十四冊中有三种版刻不同的《花仙剑》,近又发现北碚图书馆藏一种冉开先改编《花仙剑》民国抄本。通过刊本差异与故事截取、安排的“偷窥”与艳妖之缘、丑世之谑与斗打之趣的梳理探讨,可以见出这些本子,在故事主线与人物重心的演绎、关目设置与戏剧情境的生发、角色声口与不对等场面偏离等方面呈现的独特面貌——艳缘截断与喜谑转关。对川剧大戏同一代表剧目的析出段落、故事缘起、多重演绎路向展开个案研究,或许有助于进一步发掘早期川剧故事性与戏剧性因素的酝酿绾合,为川剧的编演过程与受众互动产生的社会影响提供一些思考。
《花仙剑》 双红堂 清末 四川唱本 艳缘截断 喜谑转关
《花仙剑》是川剧传统剧目之一,与《斩花妖》为上下本,叙芙蓉花仙惑书生陈秋林,冒名私奔、为仙人降服事。作为“江湖十八本”之一的大戏,此剧有多种刊本存世,舞台表演亦盛。据目前可见资料,清末民初演述“花仙剑”故事的川剧刊本,包括未见著录的双红堂藏三本及北碚图书馆藏本在内,计有20多种本子*据双红堂藏本、北碚图书馆藏本以及《四川坊刻曲本考略》《中国戏曲志·四川卷》《成都市志·川剧志》《四川省志·图书出版志》《成都市志·图书出版志》等注录:有双红堂藏戏曲188(39)咸丰十年(1860)崇庆州高鸿发堂新刻本《藕花院》;双红堂藏戏曲188(1)光绪三十二年(1906)邛州三元堂翻刻绵邑东街永兴堂新刻本《斌书剑(附游扬州)》;双红堂藏戏曲188(45)民国年间山西会馆世兴堂旧版新刻《花仙剑》;北碚图书馆藏民国间冉开先《花仙剑》罗中典抄本;民国三年(1914)邛崃荣盛堂刻本《游扬州》下册;民国五年(1916)成都福记书坊发兑曲本《丑花仙剑》;民国十六年(1927)年梁山文萃石印馆代印出售《花仙剑》(《梁樵曲本》下卷收);民国十九年(1930)成都黄寿山熙南书社刻本《花仙剑》;民国二十三年(1934)壁邑三合书局刻本《花仙剑》二卷;民国二十四年(1935)成都古卧龙硚湶记刻本《花仙剑》后节;民国三十八年(1949)成都文集书林印福记书庄刻本《游扬州》二卷;民国年间成都卧龙硚发兑刻本《花仙剑》全本二卷;民国间四册合刻《花仙剑》全本;民国年间成都刻本《陈秋林游扬州》上册;民国年间成都云记书坊刊刻《花仙剑》;民国时期成都仁昌书庄刻本《花仙剑》一册;民国年间刘双合书庄木刻本《花仙剑》等。。或题“花仙剑”,或题“游扬州”,或题“藕花院”,或题“陈秋林游扬州”,或题“丑花仙剑”。相较而言,此三种《花仙剑》刊刻于咸丰十年(1860)至民国间,其流行时间应早于其他注录的本子。而近日寓目之北碚图书馆藏民国间冉开先《花仙剑》罗中典抄本*重庆北碚图书馆藏民国间冉开先编《花仙剑》罗中典抄本一册6页,列在川剧剧本目,与《青梅配》、《醒妓》合抄。据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四川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2000年版,第507页),冉樵子辑《梁樵曲本》上下册,上册为《刀笔误》(川剧聊斋戏出《聊斋志异·张鸿渐》),下册包括《孝妇羹》《舟饯》《花仙剑》《妙嫦拜月》《淫恶报》《夕阳楼》《无鬼论》《金山寺》《青梅配》《醒妓》《琴挑》《杀子告庙》等17种,有民国十六年(1927)梁山文萃石印馆代印本,残片存于成都市图书馆,下册藏于成都市川剧院研究室。冉樵子(1889-1927),名正梅,字开先,清末法政学堂学生,曾用梁樵、刀笔误等笔名,以改编川剧高腔聊斋戏见长,是清末与黄吉安一起并称的川剧大家。另,《北平国剧学会图书馆书目》中卷“蜀戏类”著录有《花仙剑》一册,不题撰人,刻本,尚不知于此本异同(北平国剧学会《北平国剧学会图书馆书目》1935年版,第49页)。,亦是未受关注的较早本子。作为双红堂藏清末四川“唱本”六十四册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剧目,《花仙剑》三种刊本,与川剧剧目发展亦关系密切。从其版刻差异,故事截取、戏剧情境的生发、排场布置等层面对照分析,可以见出作为传统大戏析出段落反映出的不同趣味,有助于我们对早期川剧剧目衍变细节的认知,并可进一步了解清末川剧发展的具体过程。
一、刊本差异与故事截取
双红堂藏《花仙剑》三种,无论版本内容、情节场面,角色重心,都呈现了很大的差异。作为早期川剧的“唱本”,这种差异可以看做是随应舞台演出变化而来的,而截取的故事各组独立、又互有串联接续,从不同角度展演了花仙剑故事的丰富面相,体现了川剧剧目选择、融萃的一个自然变化过程。
双红堂藏三种《花仙剑》故事,以《藕花院》刊刻时间确定最早。双红堂藏戏曲188(39)之《藕花院》,封面右列“咸丰十年(1860)新刻”字样,五十册,中书黑体大字“藕花院”,左列“崇庆州高鸿发堂”字样,版心刻“藕花院”,全剧44页,首页大字黑体书“新刻藕花院”,分列标题蔡府祝寿、花园叹亲、秋林会友、游藕花院、才女对答、红面许亲、元虚嫖院、锦兰下山、超化院房、父女相会、度归天台、帽(冒)名顶替、必(毕)纯定计、元虚闹院十四个段落*据黄仕忠《双红堂文库藏清末四川“唱本”目录》,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48册,2005年12月;以下两种双红堂藏《花仙剑》刊本信息亦参据此。。行当与人物名叠用出场,以白口为主,前半部分唱曲多有牌子,如[柳青娘][月儿高][半驻云飞][驻马听][黄莺儿]等,后半部分则几乎没有出现,仅有一曲有[驻云飞]牌名。双红堂藏戏曲188(1)之《斌书剑(附游扬州)》,封面右列“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中上横书“邛州”,下黑体大字列“斌书剑”,左列“三元堂”字样。版心前十四页题为“花仙剑”。首页题“新刻游扬州”,分题(别母赴途)、苏府许亲、父女定计、薗亭观花、拐带花妖末署“绵邑东街永兴堂新刻”;末一节“暑亭题诗”版心刻“游扬州”*此本缺一页面,即第十页下和第十一页上,第十页上“园亭观花”半面与第十一页上文字内容衔接不上,当延至第十页下,据《川剧传统剧目汇编》所收全本《花仙剑》可对证。。大部分以行当出角色,偶有角色与人物名叠用现象。亦以白口胜,唱词无牌名。双红堂藏戏曲188(45)之《花仙剑》,无封面,首页横排小字“新刻”,竖排大字“花仙剑”,分题蔡府要亲、吟诗赏花、责贬花妖、台州拜寿、毕纯探信、报仇吃粮,加上开场之“议计讨亲”,应为七场。“责贬花妖”末有“山西会馆世兴堂行”字样,应是世兴堂旧版新刻。以行当出角色不多,大部分以人物姓名出场,行文以“介”“唱”夹对,曲白相生,完整的唱段不多,亦无牌名。
从刊本差异看,双红堂藏三种“唱本”中,《藕花院》刊于咸丰十年(1860),时间最早;《斌书剑(附游扬州)》刻于光绪三十二年(1889),是为晚出;《花仙剑》刊刻时间不明,至晚在民国间,祖本或可能早于前两种,出于道光间。三本《花仙剑》的刊刻地点和书坊也不同,《藕花院》为崇庆州高鸿发堂刻本,据刊记“新刻”“五十册”信息,或与旧有多曲本合刻。鸿发堂是崇庆州书商高鸿发设于崇阳正北街的书坊,光绪十三年(1887)刊有景其浚辑《吴顾赋抄》一种,民国以后或迁至崇阳西街,刻有《重台分别》、《金真缘》曲本*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图书出版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57、630页;刘效民《四川坊刻曲本考略》,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斌书剑(附游扬州)》为邛州三元堂截取绵邑东街永兴堂新刻部分而成。三元堂,民国年间绵竹与成都都曾有堂号,民国年间汪德九创办的三元堂刻印过一批曲本,但年代晚于此邛州三元堂*刘效民:《四川坊刻曲本考略》,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2页。。永兴堂以光绪十五年刻过《八仙图》曲本的成都堂号为最早;还有光绪年间重庆永兴堂刊刻过《聊斋志异》*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图书出版志》,第457页。。此本封面标“斌书剑”,可能有合刻或异字借用的情况。《四川坊刻曲本考略》录有《兵书剑》,但扫华堂以下六目均为李三娘故事*刘效民:《四川坊刻曲本考略》,第85页。,与此剧不同,或许此剧是与《兵书剑》曲本一起合刻;或是三元堂为避免重版,用绵邑东街永兴堂新刻的本子,加上最后一节“暑亭题诗”,由芙蓉剑花仙引申而异字借用,拟了一个“斌书剑”的新题目刊行。《花仙剑》据版心书“五四六”至“五六四”内页字样看,以及台州拜寿”末有涂抹痕迹,似与他本合刊,以山西会馆世兴堂行本翻刻而成。世兴堂,据《四川省志·图书出版志》,道光年间成都书坊有世兴堂,道光十六年刊刻过《伴花楼》曲本,而绵竹亦有世兴堂,但开业年代不详*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图书出版志》,第450页。。另据《成都市志·图书出版志》列有道光年间成都世兴堂、民国年间邛州世兴堂*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志·图书出版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9页。,按目前所见书坊信息排比,此本《花仙剑》亦或可推测刊于更早的道光年间。从世兴堂与“山西会馆”的关系看,在成都、绵阳、邛州三个地点中,成都可能性较大。
从情节出入与故事截取看,此三剧实有所本。芙蓉花妖的故事,最早见于清代才子佳人小说《铁花仙史》*《铁花仙史》题为云封山人编次,一啸居士评点,前有三江钓叟序,二十六回。据小说中避“玄”字、十八回“原来故明制度,凡有本章,俱系内监经收,转呈……”等句,为清人所作。。小说写钱塘蔡其志与好友王悦联姻,许嫁若兰与汝珍。王汝珍与陈坤化之子陈秋林、知县苏成斋之侄苏紫宸拜为手足。陈王二人于埋剑园中吟诗赏花,引动芙蓉花妖夜来私会陈秋林。责贬扬州时,于苏成斋衙中得会陈秋林,摇身一变为拜苏成斋为义父之前兵部侍郎女夏瑶枝,迷惑陈生。苏紫宸收妖,秋林与瑶枝得成连理。蔡其志因汝珍丧父意悔婚约,若兰不从出走,蔡翁收汝珍为螟蛉子。为苏成斋收养的若兰后终与王汝珍缘定三生。由《铁花仙史》可见《花仙剑》故事的最早源头与完整版本,而双红堂藏三种“唱本”,则是以花开几朵、各表其枝的方式,对此故事进行了截取和重组。
《藕花院》剧叙双亲亡殁的王汝珍赴蔡府祝寿遭冷待。虑父欲悔亲的若兰与丫鬟红渠谋议,游园督学赋诗识才。浪荡子弟毕纯来约夏元虚藕花院寻花问柳,路上撞破展看小姐赠诗的王汝珍,话不投机心生恨意,欲设计拆散姻亲。陈秋林为会才女水无声,邀书友王汝珍、侠士苏子辰同游藕花院。贪淫好色的富公子夏元虚以百两银子欲梳拢水无声,院妈收银设春药迷局。不意三书生至,请水无声陪客,秋林与水姐眼来语往、两下生情,苏王从中说和、赋诗随贺。这边秋林花烛求和,元虚闯入嫖院;那边院妈情急调包,请水幺姑应付夏元虚。这边水无声许亲诉身世,那边院妈许亲骗夏公子;这边水无声遭拒被毒打,那边毕纯来吞银押婚书;最后道长入院救女飞仙,元虚闹院被打约架。其实,《藕花院》是川剧高腔传统大幕戏,全剧九场,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藏有手抄本,叙宋代西湖藕花院妓女文无声,因父文景南杀人逃亡而卖身藕花院,隐姓更名,只吟诗陪酒,绝不卖笑从淫。富家子夏元虚欲以千金聘娶,院妈贪财逼嫁毒打,无声誓死不从,后为父所救同往天台修道*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四川省川剧学校、四川省川剧院:《川剧剧目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2页。。如此看来,双红堂藏《藕花院》三线互织,是与川剧高腔大幕戏故事主脉一致却敷演有别的一部戏。这种嫁接,以王汝珍和蔡若兰亲事磋磨为前线,以三书生游院为转关,以陈秋林与水无声定情为后线,牵出鸨儿丑旦与浪荡公子之群丑戏;又牵出苏子辰拜师学艺、文家父女入道之修仙戏。
《藕花院》中并未涉及的瑶枝一线故事,在《斌书剑(附游扬州)》中被敷演为故事主线,成为主角。《游扬州》叙钱塘陈秋林父亡阻试,除孝后辞别母亲,游学父亲生前好友苏成斋府。从前误戏秋林的花仙责贬扬州途中思念陈生,追至苏府,欲成就三生姻缘。秋林拜见年伯,成斋劝勉力学。瑶枝若兰互诉衷肠,原来夏瑶枝因父夏映在兵部侍郎任上遭谗被斩,被过继堂兄夏元虚献画入宫,船行遇难;而武林蔡其志之女蔡若兰,自幼许与王汝珍为妻,因父亲悔亲另许而深夜出逃,二人被扬州知府苏成斋搭救收为螟蛉。秋林于园亭观花,引动芙蓉花仙。苏成斋相中秋林才貌议亲而遭拒。秋林夜梦美人打架,思妖魅蛊惑,欲求脱身决定辞行。成斋定计与秋林辞行日安排酒宴,命瑶枝暑亭题诗,二人“邂逅”,秋林为瑶枝才貌倾倒,欲陈情告悔却被苏成斋以双关语宕开话题。此剧以陈秋林和瑶枝议亲之事为明场,以花妖求爱秋林为暗场,虽以苏成斋牵出两个不幸女子的复线,但若兰一线隐去,专从瑶枝一线生发。花妖的爱是隔世影行的执念,暗喻着陈秋林自我选择的内在合理性;瑶枝的才貌是现世姻缘的依凭,成为陈秋林拒绝叔父代父母之命的反证。
而《花仙剑》则以王汝珍的讨亲苦恼递入,将逃走之后生死未卜的若兰一线作为伏脉,以陈王二人苏府要亲、蔡翁认义子为前场,以陈秋林与芙蓉花妖的情缘为转关,接续三书生与夏元虚、毕纯来的斗打后场,带出瑶枝的才气与苏子辰的豪侠。故事从王汝珍因家道中落、蔡翁悔亲、若兰逃亡、不幸落拓,而与陈秋林议计讨亲开场。陈王二人怒气冲冲蔡府要亲,蔡翁念女生死未卜,回心欲招义子,汝珍改姓立志勤学。蔡翁设宴传酒,秋林赏花赋诗,引动芙蓉花仙。秋林花亭醉后,花仙入梦,欲与秋林共偕连理,被风雨二神捉拿于圣母面前问罪,被责贬扬州看守野苑。秋林回想梦境,守候花园门外得见梦中佳人,却是冒犯天庭被贬的花仙前来道别,共赴阳台之梦又被二神撞破。陈生于书亭会友汝珍,欲解吉凶不得。故事于此转关,倒叙苏子辰赴台州拜寿,放神箭射杀了盗库银的水贼,此际回来访友,恰遇撺掇打手报仇的夏元虚,武戏文唱,斗打旁叙,直教败北蛮奴远逃异邦。而作为《藕花院》主线故事的元虚闹院、文家父女飞仙段落,于此剧全部隐去,仅以“台州拜寿”一节由苏子辰出场道出。
如果说《藕花院》是妓女修仙与秋林遇艳两个完全不同的戏本的掺入和重组,那么,《斌书剑》即是《花仙剑》某些部分的放大和展开,而《花仙剑》又可看作《藕花院》另一版的抽绎和改写。据《川剧传统剧本汇编》整理的《全本花仙剑》上部有“别家”、“下山”、“收巴”、“路遇”、“进府”、“入衙”、“议婚”、“三许三推”、“装病”、“夜会”、“私奔”十三场戏目*《川剧传统剧目汇编》第九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3页)之《花仙剑全本》前序称,据四川省川剧院藏刘栋梁抄本校勘,并参考刘双合书庄木刻本、古卧龙桥湶记木刻本、及其他单折本增补校正。看,五场《斌书剑》虽然主线情节大致相同,场次和唱词则迥然有别,全本中出现的芭蕉精和巴世龙故事,则又与北碚图书馆藏民国间冉开先《花仙剑》抄本刻意渲染花仙与蕉精仙战*与此抄本故事相同的还有书词诙谐、唱腔别致的莲箫传统曲目《花仙剑》(中国曲艺志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四川卷》,中国ISBN中心2003年版,第105页),以及流行于贵州道真、务川、正安等地的傩堂戏传统剧目《花仙剑》(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贵州卷》,中国ISBN中心2000年版,第98页);重庆巴县阳戏《花仙剑》(王秋桂主编《四川省重庆市巴县接龙区汉族的接龙阳戏——接龙端公戏之一》,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4年版)等。的故事相合。三剧在场面上,都有祝寿、许亲、宴吟、赋诗、游园、遇仙等重要关目,但主线支线的隐伏、前场后场的调度、明场暗场的措置,递入戏出的转关,都独出机杼、各有理路。三剧故事的发生背景在西湖、扬州和台州之间,经由四川“唱本”的敷演,却打上了浓郁的地域印记和轻艳喜谑的趣味。
二、安排的“偷窥”与艳妖之缘
在双红堂藏《花仙剑》刊本中,不同的故事段落,却有着人物行动、场景布置的共同演绎路数——以安排的“偷窥”,作为一种间离手段,预设了角色与角色、角色与观者看与被看、主动与被动的位置关系。旁眼偷窥,表现了角色人物之羡艳、私语、诳言、痴遇的隐秘内心活动,演示了艳妖之缘的欢情美意。只安排邂逅,未刻意计较婚姻,则着意于体贴人情事理,亦假设戏场满足了观者潜在的偷窥念想。
作为“唱本”,《藕花院》呈现了舞台观演场面的巧妙预设与递换。在王汝珍和蔡若兰亲事磋磨的前场,经由安排的“邂逅”在敞开的空间里,表演了女性主动的“偷窥”,和男性的“被偷窥”。女性主动的“偷窥”,是若兰通过丫鬟了解汝珍品貌的前提下,自设“偷窥”之局,以一场假意游园安排了一场真心邂逅。有趣的是,在若兰入园的路上,先有暗场出花仙一段唱曲:“满园风飘梨花脂,桃红杂绿色。李花闲似□□□,亭园轻步金莲折,对景自叹息,满园草木飞蝴蝶”。花仙以花色正艳、春光正好的过场影子,暗衬了美人正青春、游园正当时,为汝珍推窗观小姐摘花而引动春情埋下伏笔,带出汝珍见花台美女而放胆向前问话的动作线。若兰一见汝珍,即引入轩中叙话,一段叮咛点化,汝珍如梦初醒,已见若兰行事机敏。接着吟诗唱和、当场考校汝珍才情,则更见其慧心。“何不将这柳枝挂绿作诗一首,妾身观看”,汝珍作诗,不仅以浓艳之笔写百花争艳,且以绿腰、柔条之缠绵,暗送鸾凤相交之情款。若兰在旁“仔细瞧”,接唱“俊美才高,又胜似潘安无双毫,一笔挥成许(疑为诗)稿,笔走龙蛇字迹高”。闺中女子的偷窥因赋诗而成,滤去了初见的羞涩,若兰意会情来,将汝珍作诗念诵一过,曲白相生,方遂了既端详汝珍俊貌、又试探郎君诗才的心愿,“喜眉梢果称了中俊英豪”。这种正场作诗、侧场观看,预设若兰作为偷窥者的表演情境,绝妙地切割了角色活动的舞台空间,通过眼线穿梭传达了才情相赏、芳心暗许。至此,以花仙之艳引领若兰主动偷窥的灵动意趣已臻至,二人的相会戛然而止,而汝珍索诗、小姐赠诗的暗场处理,又成为打开汝珍读诗被偷窥的后场的机窍。担心岳丈悔亲的汝珍,不仅得小姐一念支持,还得小姐一首和诗,只因院公闯入未及观看。妙的是,小姐和诗,原本是汝珍“此间两下无人,不如去处细看”的,却不想被闯入者毕纯来偷听了去。汝珍自顾自“偷窥”小姐赠诗,毕纯来又从旁“偷窥”汝珍读诗的感叹,耳闻汝珍满腹心事、追问不果,两下话不投机,故事才得以扭转,使得秋林会友的关目和才子邀游藕花院的故事得以铺展。
相比于前半故事里“邂逅”是若兰自己安排,“偷窥”是若兰有意主动的“偷窥”,《藕花院》后半故事里的“邂逅”,则是水无声迫于院妈安排,意欲借姻亲之想,躲过一场被夏元虚强娶的飞来横祸而待时飞仙。水无声虽与秋林“邂逅”私会,“偷窥”却如此仓促,“奴观见陈相公面如美玉,又是个宦家后富贵有余,奴本待与他人面把亲许,怕的是负义男翻落沟渠”。且不说这耽虑搁置了私情,与若兰安排邂逅全为现实姻亲之想不同,这后出里的水无声,毕竟是仙不是妖,注定与人情缘浅,所以其前疑后探、悬下终局,可见并非是为了托付终生,艳缘刚一显露端倪,即向还真修仙戏的另一种趣味转关。
而同为才子佳人的“邂逅”,在《斌书剑》里,被苏成斋安排的“偷窥”,瑶枝则被动地卷入进来,参与和实现了“邂逅”;而“偷窥”的动作发出者,却换成了生角陈秋林。此剧以花妖求爱秋林为暗场在前接引,以瑶枝议亲秋林为明场转后递进,而苏成斋牵出的两个不幸女子的故事线,隐去若兰一角,又从瑶枝一线生发,榫卯脱合,多线穿行。
瑶枝议亲的明场,作为故事的主线,自议亲、许亲至拒配、缓配而成。前兵部侍郎夏映之女瑶枝,才貌娉婷,能诗善赋,家变遭陷成苏府养女。苏成斋为义女姻亲思虑,欲将瑶枝许配才如子建、貌如潘安的秋林。岂料秋林以“孝服未满,母命在身”拒配,苏成斋“回二堂与瑶枝用个主见,管叫他狂生辈自求姻缘”,戏弄秋林欲挽回颜面。秋林辞行,于被安排的送别宴上,“无意”撞见暑亭题诗的瑶枝,为其才貌倾倒,悔不迭求亲,却为苏成斋缓配之计所阻。扬州知府苏成斋,作为才子佳人邂逅的安排者,具有双重身份,既要为义女择良门姻缘,同时作为秋林好友苏子辰叔父,秋林的年伯,又担负着父兄代友择亲的“权威”角色。他一面让夏瑶枝“避暑亭书案上挥洒诗篇”,一面“略备酒宴与贤侄”,这种刻意安排,提供了“邂逅”可能性。而“邂逅”之后的“偷窥”,方是一段艳缘展开的正场戏。秋林“进书房见姣娘连忙转步”,夏瑶枝“羞得奴裙钗女低头而出”,才子佳人的慌乱,造成了情感的断点,为接下来的“偷窥”留足了空档。只见秋林唱道:“偷眼看小姐姐恰似花蕊,赛得过广寒宫月里嫦娥。青丝发挽并头金簪插住,小金莲穿高底分外姑苏,观形容必是个才貌之妇。藕香腮恰好似荷花初出,小金莲慢慢移进了后府,看得人浑身上骨肉皆酥。”如果说花蕊、嫦娥以喻秋林初见瑶枝美貌之艳,那么,接下来细细端详发式、脸颊、小脚,从头看到脚,则将“无意”邂逅递转入艳情之缘。其实从“父女定计”一场自述,瑶枝在家难自危之间“修本章去把君见”的胆识,奇女子的不凡,早已为二人“邂逅”的荒乱和惊叹做足了铺垫。秋林的“偷窥”之举与“骨肉皆酥”、神魂颠倒的痴相,与此前开口闭口服孝未满、母命在身的自律之言形成了对位调侃。这一拒一痴,一忧丑一骨酥,一“君子”一“无赖”,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拂开了秋林此前“又未曾把他的女儿瞧见,若依允又恐怕丑陋不堪”的过虑、“婚姻大事不敢自作主张”的假意,更显此后醉倒席前极力自择良偶、挽回才貌双全姻缘的“钟情至诚”。
富有意味的是,在秋林与瑶枝议亲的明场戏进展过程中,花仙求爱秋林,作为暗场穿插,却在开场秋林别母之际、苏府拜见成斋之地、园亭观花之时、秋林拒亲之后、夜梦美人相争之刻,作为特定场景不断接入牵引,使得艳妖之缘在故事暗层里不断翻出嵌入。花仙的爱,作为“形而上的永生追随”,其光彩甚至在某些段落压过了瑶枝的现实姻亲之想。游扬州时,“误戏”秋林而责贬扬州的花仙即已暗中追随,忆昔赏花叹艳、引动花心,如今酬恩负罪,一心不舍。“远观那边来了一个人,好似恩兄陈生”,不免站在云端眺望,期待“金风玉露”之逢。因不知秋林去向,遂驾动祥云跟赶,一意成就宿世姻缘。入苏府时,在瑶枝、若兰二旦上场互诉衷肠之前,“奴爱他风流稚俊”、直盼望银河有信遂奴心”的花仙,再一次驾动祥云,尾随美郎君,飞身潜入府内花亭,要“太湖石上定三生”,与恩兄成就百年之好。如果说,路上、亭间的花仙是暗中出场,角色是正面表唱心声的,是以实化虚;那么,以秋林拒亲之后,芙蓉花仙的过场暗上,“方才间变芙蓉亲眼看见,苏老爷将瑶枝许配良缘,陈秋林不允亲连推数遍。……细思量这件事凑奴机变,到不如变瑶枝去配良缘。将身儿权且在二堂打探,看一看苏老爷是何机关”,于此虽是尾声带出的一个过场戏,却不可小觑。因为一变而为芙蓉以观动静,引出二变欲为瑶枝伺机凑缘,或许此际花仙求爱的幻觉替身与瑶枝许亲的现实姻缘才真正接榫。在秋林观花、夜梦之时,花仙则幻为影子,场面转为以虚带实。在园亭观花一处,拜见年伯之后,秋林信步入园,“抬起头用目观看,又只见满园花开得甚鲜。这一旁牡丹花犹如血染,那一旁芙蓉花妖艳含鲜。观此花在哪里会过一面,恰好比埋剑园芙蓉一般”,心下思忖,“这朵花好茂盛真果妖艳,不由我这一阵喜上心间”。从芙蓉花鲜艳夺目、秋林观之不尽的对面着笔,也从年伯以草花不堪入目、责备观花秋林意痴情迷、“贤侄然何这般容颜”的侧面抑扬,渲染了由春意盎然引逗而出的艳缘。而为缓亲之计所困,秋林羞悔决定辞行的前夜,却又梦得蹊跷,“适才打睡,梦寐之间见两个美女相争,穿红衣女子将那著玄女子推倒在地,将我惊醒,二女不见,这是何故”?在现实的艳缘邂逅之前,一红一黑以“妖邪相戏”,秋林对自我内心情感诉求的窥探,抑或为将要展开的“偷窥”之艳事,做了某种梦兆式的铺排和映衬?花妖的爱,带携或者“引诱”秋林与艳妖芙蓉所在的春天接近,及至懵懂书生注目生情、酿情成深,悬在秋林心上这一盏润色情感的明灯作用已尽,瑶枝成为父女定计的同谋,并绽放才华、暗许芳心,秋林则在父兄之命以外解开了情感的自我束缚。恰证了花妖的爱是隔世影行的执念,瑶枝才貌方是现世姻缘的依凭。艳妖之缘如此映衬,反证了陈秋林前拒叔父之命、后而自我选择的行动一致性。
而双红堂藏《花仙剑》的中段,则凭空撰出以花妖为主角的一段人鬼之恋。花仙一出场就以“妖”的身份示人,此后二度入梦,欢会辞行,都以花妖现身。秋林与王生蔡府要亲、认子设宴时,秋林陈诗“青铜镜里遇芙蓉,遇见花枝月更浓”,突然插入“杀妖走一场”打戏,可见“春情太露”引动妖艳花心。一度入梦欢会,花仙于花荫下偷窥“芙蓉满面”的陈生,埋剑修炼储灵气,只为巫山会楚君。秋林醉后花亭小憩,惊醒悠悠梦魂,夜会秀色花神。一边是花妖冒名邻家女孩剑花,吟诗爱才求聘;一边是秋林心猿意马魂飞,笙歌难稳春情;当此欲结连理之际,却被风雨二神撞破。秋林并未因“一夜梦相思,鬼魅也相逢”而感到恐惧,不但且自宽心释怀:“莫非是鬼?如不是鬼,他也便是花月之妖”,而且期待明日请兄解梦“再来觅形影”,可见其心意相许,缠绵不舍。而春心已动、迷惑秋林的花妖,被四季花仙簇拥的百花圣母捉拿问罪,责贬扬州看守野苑,二度入梦辞别。这边是,良宵欢会不成,惹下一场灾祸,冒犯圣母发贬、还望共赴阳台的幻想奢念,已是在陈明真身、以夫妻相称之际;那边是,秋林梦醒忆梦、打定主意夜卧花园门外,“纵是妖纵是怪我不惧害,与美人再会合死也快哉”的痴念招引。这待兄诉说的异梦奇情,或许是秋林对自我内心欲望的一番斟酌与窥探?这形影相随的酬恩深情,或许是花妖瞩望红尘、恋恋人间的历劫甘愿?
在双红堂藏三种《花仙剑》中,“邂逅”与“偷窥”不仅成为故事推进、场面转接的重要关目;角色之间这种富有情趣的看与被看,还盘活了人物位置身份的转换与可能的表演互动。自家安排的偷窥,机关触发,引起了一连串的看与被看,与打背拱带来的动作情理形成意外的呼应;被安排的偷窥,不仅让才子佳人的被动邂逅转变为相知相恋,而且将生角单向的偷窥延展为生旦对看互望,使得艳妖之缘与现实姻亲得以随所截断、缀合、展开、幻化,而繁枝茂叶、自成一格。
三、丑世之谑与斗打之趣
双红堂藏三种《花仙剑》以精魅与人的艳妖之缘为主调,穿插了不少市井之间的人情喜谑,通过不断的故事转关,衍展并戏弄了与神仙戏相对出的恶行乖张与漓俗浇薄;以有意偏离主调和放大丑行的纡徐之法,形成机关撤动、连环解套的丑世之谑与武戏文唱、反角集体表演的斗打之趣。
《藕花院》在三书生游院、秋林与水无声定情的故事中,牵出了浪荡公子与鸨儿丑旦的一场群丑戏。如果说元虚嫖院与毕纯定计是两个看点,院妈食利与幺姑顶包是喜谑的重要关目,那么,嫖院也只是作了机关发动的引子,而食利者反成了渔利者玩弄的骰子。而以幺姑偷欢、一对色鬼缠身,与秋林求亲、一对璧人心许打对台,方解了丑世与念世的扣。“只恋嫖淫两门”的富家子夏元虚,为梳拢水无声,与院妈议较一百两银子以求“快活一夜、歇宿一晚”。被院妈设计支开的元虚,转头进了会场游荡,一观《偷笋》二看《裁衣》,都是“粉戏”不说,又去药店买了春药吞服,足见色中恶鬼之丑。及至进院书房躲避,被安排“颠鸾倒凤”,还不知中了院妈掉包计,抬价强娶不成,恼羞成怒而只好打戏凑手。院妈自以为诓得夏公子一百两银子再加一千两银子逼女另嫁,却不想节外生枝,银子被夺去六百两却栽赃不成,“女儿”又被借机入院、使动法力的道长“拐去”,真可谓毒打禁闭唯利是图、食利贪狠反被操弄。相比于夏元虚的无赖流荡,毕纯来则惯熟市井之间皮条客的深心机诈。从偷窥汝珍读诗话不对板而含恨结怨开始,毕纯来就不仅是一个拆散姻缘的小人。他不断挑唆秋林难娶之意,说动院妈嫁女元虚,说破嘴皮子费尽心机,似乎是为兄弟出头、成人之美之举。及至婚书画押,一千两银子吞了四百,卖身契假手中人弄鬼,方现出其欺骗玩弄的伎俩和贪心渔利的嘴脸。一场闹院私念披纷、鬼胎各显,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丑世之谑,最后道长假以受毕纯来、夏公子之托说服水小姐、却金蝉脱壳父女归仙的剧情反转,才给人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快意。
《斌书剑》中的秋林,抱定“蓝衫换紫袍”、蟾宫折桂的梦想,却因守孝三年而顿挫了人生际遇。看上去,穷书生上行的人生路似乎与喜剧故事无缘,但怕丑拒亲的“怪念头”,却出其不意地与才貌相当的美姻缘形成了错位怪谲的喜谑性。“蒙年伯许姻亲推却有错,误下了一着棋满盘皆输”,羞悔辞行之际,秋林还能为自己打回圆场吗?有意思的是,“唱本”以巧妙的言语迤逗,生发出了“做文章”的趣味。且看他如何言语回转——一边是秋林的小心试探和急切追问:“年伯昨日在此亭所言的姻亲一事……”“不是那样,是年伯昨日花园中言说的一个香闺”;另一边是苏成斋的三推六问、佯装糊涂——“哦,贤侄你问的那姻亲,亲者是贤侄思亲甚急,姻是昨日天阴”“贤侄问那香闺?香是贤侄思乡,闺是贤侄要归家甚急”。这一递一接形成了“姻亲”与“天阴思亲”,“香闺”与“思乡归家”这样饶有趣味的文不对题、谐音错语。故事在尾声部分出现这一调谑打趣的小场面,将这一场以浪漫邂逅始、以“偷窥”为悔亲转关的才子佳人团圆之趣有意中断,以“我昨日许亲你不允、这下你忙我不忙”收提顿住,打开了缓亲结局的可能性,带来跌宕惊奇、意犹未尽的谐世喜幸。与《斌书剑》在结尾运笔出奇不同,《花仙剑》则于夏元虚上场诗中,即以“摇摇摆摆摆摆摇摇过鹊桥,是人打从桥上过,唯有学生摆的高”,抖落了其终日游荡花街柳巷的丑态。接着在自报家门中,唠唠叨叨诉说身世——前日游院与小姐“和诗”,被苏子辰暴打;回家喊妹子报仇,遭妹子责难;二次去蔡府求亲,出妹子黑莓诗对海棠诗,被秋林“凌辱”;回家诉苦求助,再遭妹子耻笑。这一丑谑,虽说是恶人自揭其丑常见的套路,但在外被打、回家被责,二次三番遭“凌辱”的尴尬,不仅活画出这个窝囊废、拙才鬼、浪荡子的愚妄无知、廉耻丧尽,而且引出“请了四个打手,藏在书坊,天天东打西打”的另一丑谑,为下一场的武戏文唱做了水到渠成的铺垫。
双红堂藏不同刊本的《花仙剑》故事,表里出入而相互关涉,不仅常常偏离主调、从反面发挥借以丑世,还多以反派人物集体表演、武戏文唱,凸显另类的斗打之趣。《藕花院》于父女飞仙之后,以王生“我本得要打你心中胆战,怕的是打不赢被人笑谈”做蓄势,在夏毕二丑与陈王苏三生之间展开一段斗打之戏。苏子辰开打“向前来抓住了两个丑汉,两个头拚几拚全当做完”,以抓住背肩提点、打一个“黄龙滚”了断;以头顶撞断威胁,让帮凶丢手讨饶。本该有的一场武斗,看上去象一场“假打”的动作游戏,“鸡毛凤胆”之嘲令人忍俊不禁;以俗语行话抖包袱,“生铁嘴豆腐脚杆”象提线木偶般“装烟倒茶”,活现出恶人胆虚与侠士威仪。如果说《花仙剑》开篇的“蔡府要亲”,以文生反智为勇、斗口夺妻,形成了富有意味的身份反转和武戏文唱,那么收场的“毕纯探信”则以夏毕二人与二丑四打手的对白接唱,虚武弄文,让恶人卖乖露怯,出尽洋相。“蔡府要亲”之际,原本文弱的二书生,怒汹汹恼恨蔡其志“欺压穷秀才另选才郎”,撞上喜盈盈款待贵客的岳丈。秋林为王生抱打不平,二人理直气壮进府,虎视昂昂坐堂,“嫌贫悔亲另许名望”,“移花接木哄骗婿郎”,“好好献出来免遭魔障”“若不然休想太平安康”,这一递一声口,声声不饶人,逼出了蔡翁回心认子之举,使得无戏处生戏,开场就掀起波澜。而收尾“毕纯探信”斗打之戏,由二丑四净接续《藕花院》结尾的准备复仇。夏毕二人打听到苏子辰去台州拜寿,陈王去蔡府要亲被收为义子,今早去西湖边游玩,请出四位打手伺机斗打。如此一来,原本苏子辰行侠镇恶的打戏方向,却让位于二丑四打手的反角集体表演与武戏文唱。一介“性情刚一生好勇”赛过伍员,静候公子吩咐;二介“性情暴气贯长虹”黑飞熊,接令火速奉行;三介“铁金刚无人敢动”如铁背牛,明言不可迟误;看似强蛮之下必有一场恶战;然而,在四打手的轮番接唱中,四介“铜罗汉肚内虚空”比望山猴,恰好比三句半,临了刚强中落了懦软。四打手接活计时,一逞强“孺子辈只要我动一根指动”,二恃勇“打他个半条命不受惊恐”,三吆喝“先打他血道处拳头要重”,四歪缠“他纵然不得死也要吐红”,看起来个个趾高气扬、雄威耀武。而转过场苏子辰一到,“二丑鬼因甚事磨拳挽袖?在哪里带来了一干死囚”,这声口分明激怒了四打手,一净叫嚣“说大话言语太陡”,二净愠怒“把我们比成了草豆木猴”,三净大呼“叫一声众兄弟一起动手”,四净“把狗子先剥皮后把筋抽”。如此形容之下,似乎难免一场恶斗;然而来势汹汹、摆谱太甚,未交手却分明泄了元气,抱头逃窜、花落水流的“打一场”遂带过处理。而尾声中续出的“报仇吃粮”一节,正好借二丑四净的窝里斗,从反面补足了“苏子辰汉子我不够斗”,“打得我背带砖肿烂额头”“不是我跑得快险遭恶手”“把鞋子都跑烂踢破指头”的真相。夸下海口“又吃铁又吃火又咬骨头”的四个打手,到头来现原形“水泡胀几条犇牛”,而二丑耍奸滑躲过了近身挨到,不得已也只好一不做二不休与四净落荒而逃。二丑四打手你一句我一句的“自我贬损”,虽说抢了文弱书生豪侠士的戏份,却在转口接唱的热闹中让造恶者自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正题逻辑。
而民国间冉开先改编《花仙剑》抄本,则于短折中翻出变化,在花仙追赶秋林赴扬州途中,演绎了不一样的花仙与芭蕉精的仙战斗打之趣。与双红堂本《斌书剑》借吟诗赏花之局、《花仙剑》借夜梦寤寐之兆,虚落实出,写瑶枝的情与花仙的爱不同,民国间冉开先改编《花仙剑》抄本隐去了秋林的内心戏,截取花仙责贬扬州路的一段插曲,以花仙为主角敷演鬼情仙趣。以擅编川剧高腔聊斋戏著称的冉樵子,以遭遇芭蕉精而展开的神仙大战为前场,以花仙日夜相随、偷窥秋林上路为后场,着意放大了花妖的英气与痴情,专一宣叙精魅加害之苦与仙家相思之惑。千年得道芭蕉巴世龙洞中占课,算得芙蓉仙子凡心已动,欲抢回做压洞夫人,并喝令喽啰们带好法宝准备一场恶战。而悟道修真的芙蓉花仙,原本是一股“千锤百炼出红炉,真个削铁如泥土”的清风剑,于临朝之际为蔡翁爷玩不释手,后获御赐回府,因夜射寒光引人恐怖,埋于后园以芙蓉镇之。与因秋林滴酒惜花而引动凡心一念、欲成红袖添香之想、受圣母责贬仍念念不能释怀的芙蓉痴爱相对照,算得巴世龙欲栖凤梧,“麈尾化作剑一股,待他来时断他的头颅”的“芙蓉剑仙”,却表露了花仙恩怨分明、除恶务尽的决断与强横。只见腾云驾雾、净旦交战,一回合净败;芭蕉精执扇,二回合旦败;芙蓉执剑,三回合巴世龙被斩。好一场花仙与蕉精的仙妖征战,先有神应算课之卦象互占,后有芭蕉扇与芙蓉剑的法器较量;剑气横扫的斗打之趣,快爽利落而了无俗情气息。
此四种《花仙剑》戏本,可以说将风情戏、妖鬼戏、神仙戏、武打戏的段落各自沿着不同的方向演绎发挥,又意外提顿抟合,在艳缘主调之中,上下左右挪移,打开了世情变幻的“戏场”和轻艳喜谑的转关。
在川剧剧目的发展中,以芙蓉花仙为扭结点敷演的故事,既连接着传统,又在后来的川剧振兴改革中掀起了新的编演热潮。考察双红堂藏《花仙剑》“唱本”的存世面貌,并兼及新发现的北碚图书馆藏冉开先改编《花仙剑》民国抄本,可见其在故事的截取接续、关目的选择安排、风情主线与喜剧性重心的迁移、神仙生活与市井习俗交织等方面显示出的戏事缀连和明显差异。对川剧大戏同一代表剧目的析出段落、故事缘起、多重演绎路向展开个案研究,或许有助于进一步发掘早期川剧剧目故事性与戏剧性因素的酝酿绾合,为川剧的编演过程与受众互动产生的社会影响提供一些思考。
[责任编辑]黎国韬
丁淑梅(1965-),女,陕西西安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 成都,610064)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双红堂藏清末四川唱本研究”(项目编号:14BZW075)的阶段性成果。
I207.3
A
1674-0890(2017)05-010-08